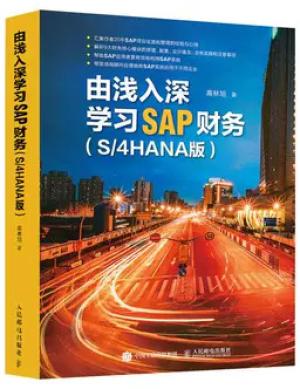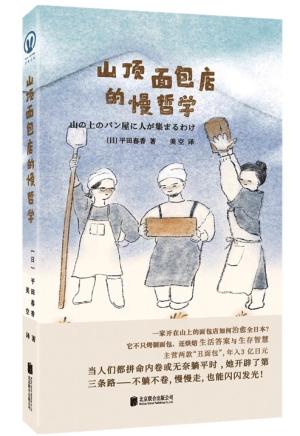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味水轩日记校注
》
售價:HK$
85.8

《
人生舍弃清单
》
售價:HK$
65.9

《
趋势2025:解码中国互联网营销新地图:中国互联网营销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94.6

《
这才是最好的数学书 日本数学大师笹部贞市郎扛鼎之作 探讨学校所教数学的来源 揭秘公式、定理背后的故事
》
售價:HK$
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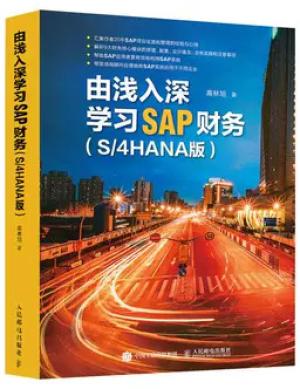
《
由浅入深学习SAP财务(S/4HANA版)
》
售價:HK$
1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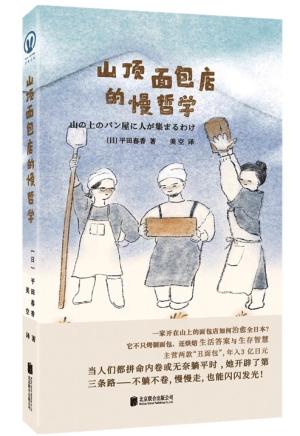
《
山顶面包店的慢哲学
》
售價:HK$
49.5

《
图画天地——七世纪前中国山水的图式
》
售價:HK$
171.6

《
民国教育的记忆与重构
》
售價:HK$
151.8
|
| 編輯推薦: |
|
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重磅新作,一部珍贵的自我探索之作。曹文轩以深情细腻的笔触,从童年的河流记忆写到阅读的精神磨砺,从行走世界的文化凝视与生命感悟写到现象级作品《草房子》的诞生,成就了一部在曹文轩写作生涯中极其罕见的精神自传式散文集。书中首次公开曹文轩私人阅读清单,并特别收录曹文轩走心自序,让你读懂“塑造”的力量。
|
| 內容簡介: |
一个人的未来,是如何形成的?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这是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一部珍贵的自我探索之作。
全书共四辑,从童年的河流记忆、阅读的精神磨砺、行走世界的文化凝视与生命感悟,到现象级作品《草房子》的诞生,曹文轩以朴素真挚的文字不懈追寻“我是谁”,并在回望与前行中不断抵及新的“自我”,被誉为其“继《草房子》《青铜葵花》之后最重要的生命之书”。
这部诚挚之书将告诉你:童年、阅读、行旅,是一个人生命中极其重要的自我塑造。
|
| 關於作者: |
曹文轩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
1954 年 1 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从 1970 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草房子》《青铜葵花》等 35 部、短篇小说 100 余篇、绘本 80 余本、学术性著作 10 余种,创作作品在国内外多次重印。其中小说《草房子》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重印 500 余次。
曹文轩的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希腊、日、韩、瑞典、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阿拉伯、波斯等 40 余种文字,共 230 余册,为世界文学留下中国美学的精神财富。
曹文轩曾获国际安徒生奖、瑞典彼得·潘奖、国际杰出童书奖、英国笔会·品特奖等 30 余项国际文学艺术奖项和荣誉。
|
| 目錄:
|
序:我是一个捕捞者 / 01
河流
童年 / 003
疲民 / 009
天堂之门 / 016
圣坛 / 024
柿子树 / 028
关于肥肉的记忆 / 038
游说 / 052
痴鸡 / 061
群星
鲁迅 / 073
沈从文 / 096
川端康成 / 107
契诃夫 / 127
普鲁斯特 / 146
卡尔维诺 / 164
凝视
汤 / 187
乌鸦 / 194
白冢 / 204
神性 / 208
圣河 / 213
写作是一种回忆
因水而生 / 219
附录
清单:喜欢的作品和作家 / 237
|
| 內容試閱:
|
序:我是一个捕捞者
我在问自己:我是谁?本来我有三个回答,但现在我只回答一个:我是一个捕捞者。
我就是那个古巴捕鱼老人桑提亚哥,但不同的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出海捕捞了,他这一次出海,是因为他要向人们证明,他没有老,还能出海打鱼。也许,当他将一袭马林鱼的骨架拖回港湾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出海打鱼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出海。而我呢,将可能会在这辽阔无垠的大海上漂泊终生。
我得用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心灵,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捕捉着:两个恋人的小声对话、一个瘸腿小孩从小巷里跑过、一条鱼在岩石上蹦跳着、黑暗并不一定就是夜晚……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我捕捞的对象。
捕捞既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职业。我对生活始终向往。我拥有一个很不错的对生活的态度。我曾经对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的“生活”下过一个定义:所谓“生活”,就是生机勃勃地活着。“生活”在我这里,既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我驾着小船,在这大海上游弋、漂流,从来乐此不疲。它的无法穷尽、它的波涛和细纹,它的颠覆欲望和载人去向远方的善意,我都喜欢。这片大海对我而言,不只是给我带来了喜悦,带来了生命冲动,带来了人生的启迪,还在于它能慷慨地向我呈示和奉献一个作家所需的东西:文学的素材与故事。
捕捞需要耐心和技巧,更需要一番诚意。几十年里,我一直在磨炼我的耐心、提高我的技巧、修炼我的诚意。当听说一些同行还并未老去,却已经处在山穷水尽、搜肠刮肚的状态时,我庆幸我还未与这样的尴尬和难堪相遇,我还在捕捞,并且觉得这大海越来越丰饶了。
我拥有的不只是一片海,而是两片海——还有知识的海洋。我早就意识到,一个作家如果只是拥有生活的海洋,其实是很难维系捕捞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捕捞。他如果要使创作的香火延续不断,则必须同时拥有两片海,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后面说的这片海——知识的海洋——可能更加重要,没有这片海,生活的海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最多也就是一片海而已,是一片空海,是不能发生捕捞的。生活的海洋本身并不能给予你捕捞的本领,这一本领从根本上讲,是知识的海洋培养的。博尔赫斯讲,他的创作是依靠书本知识而进行的。我想,他是为了强调知识的至高无上才这么极而言之的。他是一个在生活的海洋中流连忘返的人,即使双目失明,依然像一面孤帆在航行。而海明威又是另一番形象,这一形象给那些初学写作的人造成一个错觉:一个人只需在生活的海洋中浸泡、畅游即可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整天就是养猫、泡酒吧和咖啡馆、打拳击、打猎、捕鱼、开飞机、在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参加战斗,他们无法将“老狮子”与书房和书籍联系起来。殊不知,海明威对书籍的热爱丝毫不亚于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人生时间表上,留给知识海洋的时间更多。只是因为喜欢打鱼,就能自然而然写出《老人与海》?不可能。说到底,他还是一个读书人。是知识让他成了生活海洋中一个本领高超的捕捞者。我去过他在哈瓦那郊区的别墅——别墅中有一间很大的书房。
知识海洋不仅让我们发现了生活海洋,它本身也可供我们捕捞。一个单词、一个短句、一个观念、一个隐藏在他人作品中未被作者感觉到的动机,都可能是难得的捕捞之物。这种从书本中获得惊喜的情景,我已无数次地经验了。所以,我必须拥有两片海洋,我要驾着我的小船,自由地出入于这两片海洋,只有这样,我才能使我的一生成为捕捞的一生。
海洋浩荡,远接天际。捕捞之物各种各样。于我而言,它们有些适合诗,有些适合散文,有些适合小说——而有些适合长篇小说,有些适合短篇小说。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今的作家,往往眼中只有长篇的素材和故事,那些适合短篇的素材和故事,他们根本无意捕捞。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捕捞风气。所以,最近一两年我在到处宣扬“短篇意识”。因为我永远记得,当年开始海洋之旅时,就是从捕捞短篇练起的,正是在这里练出的捕捞功夫,才使我后来较为完满地完成了一系列的长篇捕捞。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或是狂浪大作或是风平浪静的海洋中,不只是有鲨鱼、马林鱼那样的大鱼,也有中型的金枪鱼、马哈鱼,还有许多小型的鱼,如秋刀鱼、多春鱼。不只是大鱼才能让我们领略美味,小鱼的美味是别致的,也是无法替代的。慷慨的海洋,就是这样为我们准备下捕捞之物的。
我们离不开海洋,正是因为海洋博大。
童年
听母亲说,我小时长得很体面,不哭,爱笑,爱整天转着眼珠打量人,揣摩人,很招人喜欢。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上。庄上人家也都沿着河边住。我一两岁时,常被人家抱去玩,然后就沿着这条大河一家传一家,有时竟能传出一二里地去。母亲奶水旺,憋不住了就找我,可总要花很大工夫才能将我找回。重新回到她怀抱时,我已不肯再喝她的奶了。因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亲已经用她们的奶喂饱了我。母亲说,我是吃了很多母亲的奶长大的。当然后来我却慢慢地长丑了,也不再那么让人喜欢了。
长到三岁,我就已经变得有点“坏”了。我到风车跟前玩,不小心,穿一身棉衣摔到水渠里。我一骨碌爬上来,一声不哭地回到家,将湿衣服全部剥下,钻到被窝里。当母亲回来要打我时,我却一口咬定:“是爷爷把我推到了水里的。”被陷害的爷爷不恼,却很高兴,说:“这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当然,长大了以后,我却从未生过害人之心。至于有无出息,这就很难说了。
当长到精着身子拿根树枝在地里、河边到处乱走时,倒也做了不少坏事。比如在田埂上挖陷阱让人摔跟头,将人家在河边的盆碗推到深水之中,等等。但我不恶,没有让人讨厌。另有一点,不管谁逗我(甚至用稀泥涂满我全身),我都未恼过,未骂过人。如今回到老家时,那些大爷还在说:“文轩小时候不会骂人。”其实骂人还是会的,我只是在小孩中间骂,不骂大人罢了。
长到九岁时,我已是一个贪玩、想入非非、不能管束自己、总是忘记大人的训斥和告诫的孩子。正在课堂上听课,见到外面有一条陌生的白狗走过,竟忘了讲台上的老师正讲课,“呼”一下冲出教室撵狗去了,后来遭到老师严厉的惩罚。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一个大我三岁的大孩子偷偷离家出走,去县城看国庆焰火。当时,只有水路通往县城。我身边只有一块钱,还是从父亲的口袋里摸来的。那个大孩子也只有一块钱。这两块钱不能买船票,得留着到城里看电影看焰火时买小食品吃(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奢侈的安排)。于是,我们步行三十几里来到县城。到达时,天已晚。我们向人打听哪儿放焰火,回答是哪儿也不放焰火。此时,我们身体疲乏难熬,既不想下馆子,也不想看电影,只想睡觉。我们在一个黑森森的大门洞里找到了一条大长凳,倒头就睡。
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见满天大亮,便商量说买小笼包子吃,吃饱了就回家。于是,就出了大门洞,走上大街。街上空空荡荡,竟无一人,这使我们好生奇怪。正纳闷着,走过几个民警来,将我们逮住,押到一幢房子里。我们一看墙上的钟,才知是夜里十二点。刚才见天大亮,实际上是城里的灯火在大放光明。我们被关在屋子里,像两个傻瓜。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节日里的“宵禁”。天真正亮了,民警放了我们。
小时的印象很多,其中之一:穷。
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我的家一直是在物质的窘迫中一日一日地度过的。贫穷的记忆极深刻。我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的,记不得了。青草是我从河边割回的。母亲在无油的铁锅中认真地翻炒,说是给我弄盘“炒韭菜”吃。十五天才能盼到一顿干饭。所谓干饭只有几粒米,几乎全是胡萝卜做成的。整天喝稀粥,真正的稀粥,我永远忘不了那稀粥。读中学时,每月菜金一元五角,每天只有五分钱。都是初二学生了,冬天的棉裤还常破绽百出,吐出棉絮来(当地人叫“出板油”),有时甚至竟然露出一点臀部来,这使我在女孩子面前总觉得害臊、无地自容,下意识地将身子靠住墙壁或靠住一棵树,尴尬而腼腆地向她们憨笑。
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汗毛孔一一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着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死了——饥饿的欲望。
按遗传,我应是一位所谓身材伟岸的男子。然而,这一遗传基因,被营养不良几乎熄灭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脑子都被饿坏了。有一段时间,我竟然粘在地上不肯上长。这引起家里人的恐慌:莫是个小矮子!常常仰视,使我有一种自卑感,特别是当我走到高个孩子跟前时,莫名的压抑便袭往心头。大年三十晚上,我带着要长高的渴望,就勇敢地爬门板。这是当地的一种迷信,据说这样可以长得比门板长。无论怎样努力,后来也没有长得比门板长。但基因的不屈不挠,使我忽然又拔高了一截。
饥饿的经验刻骨铭心。因此,现在我对吃饭很在意,很认真,甚至很虔诚,并对不好好吃饭的人,大为不满。
但,我又有着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
我有一位慈和的老祖母,她是一个聋子。她有一头漂亮的银发,常拄着拐棍,倚在门口向人们极善良地微笑着。她称呼我为“大孙子”。后来我远行上大学了,她便日夜将我思念。她一辈子未走出三里方圆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知道三里外还有一个宽广无垠的大世界。她认为,这个世界除了她看见的那块地方外,大概还有一处,凡出门去的人都一律是到那一处去的。因此,她守在大路口,等待从那地方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
母亲对我的爱是本能的,绝对的。她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品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地先尽孩子们享用,剩下的她随便吃一点儿。父亲的文化纯粹是自学的,谈不上系统,但他又几乎是一个哲人。一次,我跑到八里地外的一个地方看电影,深夜归来,已饿得不成样子了,但又懒得生火烧饭去。父亲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对我说:“如果想吃,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三里外堆着,也应去抱回来。”就在那天晚上,他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
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刺泼刺”的水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这一切,使我“舞文弄墨”成为可能。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发达自己。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进了坚韧。难怪福克纳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祖母、父亲和母亲给我仁爱之心,使我从不知道何谓仇恨。我从未抓住不放地仇恨过任何人。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题材、主题和故事。开门可见的水,湿润了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