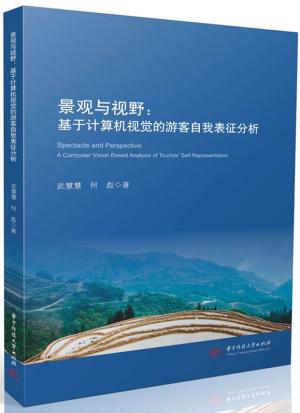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颌面肌功能治疗学 原书第2版 牙?? 肌肉 身姿 国际经典口腔颌面外科译著 一本口腔医生、康复师与宝
》
售價:HK$
294.8

《
东方问题 地缘政治原典级著作
》
售價:HK$
118.8

《
《亚洲文明史研究》(第2辑)
》
售價:HK$
140.8

《
中国海洋鱼类图鉴(全三册)
》
售價:HK$
1628.0

《
观念与秩序:儒学的现代性建构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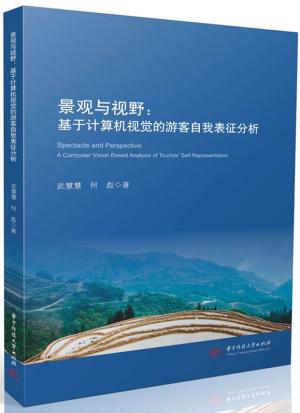
《
景观与视野: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游客自我表征分析
》
售價:HK$
87.8

《
穿越西方文明 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全球时代(全二册) 世界史图书馆
》
售價:HK$
283.8

《
知识的流动:中德文化关系史(1600~1945)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我们与世界的所有关系,都从我们拥有一个感觉中的身体开始。
在图像淹没日常、技术包围生活的当下,我们不断“观看”,却越来越忽略身体真实的感知与在场。
我们身体的触动、欲望、脆弱、疼痛、缺席……是否被我们认真地对待过?
我们是否还真正“活在身体里”?
———————————————————————————————
我们不是抽象的“观看者”,而是以身体回应影像、回应世界的感知者
索布恰克结合现象学理论与自身患癌、截肢、佩戴假肢的身体经历,向我们揭示:观看从来不是纯粹的视觉行为,而是一种全身性的“具身经验”:当我们观看影像时,我们的手指、神经、呼吸、疼痛、欲望、义务和感知力,都在参与这场看与被看的“身体对话”,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感知者。
———————————————————————————————
技术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与我们的身体、欲望、记忆、文化经验密切交织的现实存在
从打字机、键盘、触摸屏,到剪辑、虚拟现实、数字图像……生活在技术构造的空间中,我们早已不再用“原始身体”感知世界。当我们“通过技术感知”,我们是否也成了技术的产物?索布恰克提醒我们:技术不仅延伸了我们
|
| 內容簡介: |
在高度技术化与图像主导的当代,我们的身体还如何“在场”?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是一部从“身体”出发横跨多个领域的影像文化研究力作。作者薇薇安·索布恰克将现象学哲学与自身具身经验相结合,通过电影、纪录片、视觉文化、假肢、手术、技术物、感知逻辑等多样场景,探讨我们如何以“活体”经验世界并承担责任,在图像文化中重构感知与伦理。
本书分为“可感的场景”与“负责任的视觉”两个部分:“可感的场景”探讨我们如何在不同媒介与空间中以身体定位自我、生成意义;“负责任的视觉”则进一步延伸至身体的伦理责任与感知限度,最终指向身体与客体之间不可分割的感知共鸣以及一种肉体与物质世界关联模式的现象学——客体间性。
这是一本兼具理论锋芒与人文温度的书,它不仅挑战主流理论对身体的抽象化,也唤醒我们对肉身经验的重新尊重,还原身体作为人类经验的起点、作为“活体”对世界的感知与回应之核心地位。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薇薇安·索布恰克(Vivian Sobchack)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电影和电视学院教授兼副院长,第一位当选为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会主席的女性,也是美国电影学会董事会成员。研究兴趣广泛,涉及美国电影流派、哲学与电影理论、感知史与现象学、历史学与文化研究等。
译者简介:
李三达,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译有《朗西埃:关键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
夏开丰,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艺术与文化产业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访问学者。主编《当代艺术评论》,著有《美学的政治:从康德到斯蒂格勒》《绘画境界论》,译有《何谓艺术》等。
刘昕,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艺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理论与技术哲学。
|
| 目錄:
|
致 谢 / i
导 论 / 01
第一部分 可感的场景
1 森林中的面包屑:对空间迷失的三次沉思 / 16
2 可怕的女人:电影、手术和特效 / 47
3 我的手指知道什么:电影感觉的主体,或肉身中的视觉 / 70
4 收缩空间中扩展的凝视:偶然事件、风险以及世界中的肉身 / 112
5 “苏西写字娃娃”:论技术、Techn?与书写化身 / 146
6 屏幕的场景:展望摄影、电影和电子的“在场” / 181
第二部分 负责任的视觉
7 打败肉体/在文本中生存,或者如何活过整个世纪 / 216
8 有身体在家吗?具身化想象以及从可见性中被驱逐 / 236
9 单腿而立:假肢、隐喻和物质性 / 272
10 铭写伦理空间:关于死亡、再现和纪录片的十个命题 / 300
11 真实的重负:具身知识和电影意识 / 344
12 物质的受难:通往一种客体间性的现象学 / 379
索 引 / 423
|
| 內容試閱:
|
导论
客体……描述的是人之身体的生气勃勃,这不是说身体中有纯粹意识或反思,而是将其作为生命的一种蜕变,身体作为“精神的身体”。
——莫里斯·梅洛 -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法兰西学院讲座,1952—1960》
(Themes from the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52—1960)
这或许是一本“不规范”的著作,这一点体现在我的跨学科背景和我对电影及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在美国显得有些古怪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趣上。然而,不规范并不表示本书中的文章都是任意妄为的。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其专题及其变体(inflection)是什么, 它们都采用了单一的核心主题以及单一的方法,尽管这个方法相当开放。
本书的首要主题就是人类生存具身性的(embodied)和根本的物质性,因此活体(lived body)的本质含义在于从身体“感觉”出发产生“意义”。从我们的肉体感官中产生有意识的感觉正是我们所做之事, 无论是当我们在看一部电影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以及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活动时,甚至是对影像之谜、文化的形成以及我们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进行抽象思考时。因此,无论是探究我们在银幕内外如何在空间上定向,还是追问电影“触摸/ 打动我们”(touches us)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是思考从笔到计算机再到假肢的技术发展对我们身体形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是思考在一个充斥着图像的文化里“可见的”(visible) 与“能见的”(visual)之间的差异;或者,无论是透过某个银幕形象的“实在性”而努力思考,还是思考我们的美感以及伦理感“在肉身(flesh)中” 交融展现的方式,本书中的所有文章关注的都是活体。也就是说,它们不仅关心作为抽象客体的身体,而这一身体总是属于其他人,而且关心“具身化”是什么意思,以及体验我们生气勃勃的、变形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并且我们把这种存在当作具体的、外向的以及精神性的主体,而我们客观上都是这种主体。首先,我希望本书中的文章足够“有血有肉”(flesh out),以严肃的(偶尔有点轻率的)描述为现在大量客观地(但粗浅地)聚焦于“身体”之上的当代人文学科文献作出贡献。这里的关注点在于什么使某人的身体生动活泼,而不只是看身体—— 尽管视觉(vision)、视觉性(visuality)、可见性(visibility)不只对具身存在(embodied existence)的主观维度而言是核心,对其客观维度而言也是核心。总而言之,本书中的文章强调具身性(embodiment), 意思是说,活体既是具有客观性的主体,又是具有主观性的客体:一种有感觉、感知和意识的各种物质化能力(materialized capacities)以及能动性(agency)的集合体,可以直接或者以比喻的方式理解自身和他者。
为了与这个核心主题一致,本书采用了一种以存在主义现象学为指导的方法和批判实践。就像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概括的那样,存在主义现象学“是一种哲学风格,强调对人类经验的特定解释, 尤其关心知觉和身体活动”。确实,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哲学根基在于主观意识介入世界之时的肉体、肉身的客观基础,并且当主观意识进入世界时也会被其改变。因此,现象学的探究注重经验现象和它们的意义,这些意义在空间和时间上由具有客观性的主体加以体现、激活和评价——正因为如此,这些意义也总是已经受到历史和文化可变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具身性绝不会是先于历史及文化的存在。再者,与反历史、反文化的观念论不同,我们经验的现象无法被还原为不变的本质;相反,存在中的它们的形式、结构和主题是暂时的,因而总会对存在和意义开放新的、其他的可能性。因此, 莫里斯·梅洛- 庞蒂,一个关注具身性的哲学家,从先验(或构造) 现象学转向了存在主义现象学,他告诉我们“[现象学]还原最大的经验教训在于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那么,现象学方法不是追求本质,而是追求在特定情况下,在语境之中以具身的方式感受到的经验意义——在经验的主客观“综合”中出现的意义与价值。
谈到我所选择的主题和方法,就像本书中的文章对具身性经验描述和解释的那样,我希望它们的分量和偶尔的严肃性可以揭示我们“在肉身中”的具身存在之性质如何为理解美学和伦理学奠定了唯物论而不是观念论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在整本著作中,我所希望的是理解我们自己的活体是如何提供物质前提的,这些物质前提使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感觉到世界与其他事物并对之作出回应——不仅以“肉体的思想”作为基础为美学和伦理学提供逻辑前提,而且使得我们有意识的关注承载了能量和义务, 这些能量和义务激活了我们的“感知力” (sensibility)和“责任感”(responsibility)。这是美感和伦理感自下而上的出现,因为它被肉体经验写在我们的身体之上,并且这种肉体经验被当作了我们的身体,而不是说在身体之上强加一个自上而下的观念论之物。在这方面,尽管这些文章注重的是特殊的(有时是个人的) 实例和经验,但是这些实例会被用来打开(而不是封闭)我们对我们与其他人更为一般的关联性(往往是社会性关联)的理解,而且事实上,这些实例也会被用来表明我们与所有其他人和其他物的亲密联系(无论我们否认还是接受它们),这种联系往往在物质层面有着巨大影响。
如果说本书的核心目标是为了像梅洛- 庞蒂说的那样描述“人类身体的生气勃勃”以及“作为‘精神之身体’的身体”,那么这个目标就必须被放入语境之中。就像已经指出的那样,“身体”对于从事当代人文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焦点。尽管如此,更为常见的是,身体,无论多么被看重,都主要被当作诸多客体中的一个客体——大部分时间像是一个文本,有时则像一台机器。的确,在我们当代图像意识和消费文化中,身体已经被客体化和商品化了,许多学者甚至在对这些客体化和商品化的方式提出中肯批评的同时仍然试图救赎身体,就像托马斯·索达斯(Thomas Csordas)写到的,“在他们的分析中,对身体性(bodiliness)没有太多的感觉”,他接着说,这样的趋势“带来了双重危险,一个是消除了把身体作为方法论起点的力量,另一个则是将身体客体化为没有意向性和主体间性的物。它因此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即把感觉能力和感受能力添加到我们关于自我及个人的观念中去,并且坚持把物质性维度添加到我们的文化和历史观念中去”。因此,索达斯指出,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身体及其变化,同时仍然认为具身性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身体和具身性之间作出区分很重要,身体要么是作为经验物要么是作为分析的主题, 而具身性则是作为文化及自我的存在基础”。 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从身体转向具身性。
具身性是人类存在的根本物质条件,它必然会使身体和意识、客观性和主观性处在一种不可化约的整体(irreducible ensemble)之中。因此,我们产生作用和表达意思都需要通过产生意义(sense-making)的过程和逻辑,而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肉体生存,就像是它们对我们的意识产生影响一样。另外(以及回应一种偶尔出现的批判,即认为现象学的目标是在意识和身体存在之间建立起过于轻松——以及“开心”——的对等关系),具身化意识的不可化约性并不意味着身体和意识、客观性和主观性在我们的意图或意向性中总是同时产生或者价值相等,又或者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即使在它们完全同时出现时——会对彼此完全敞开。此外,在既定经验中,它们并不一定完全等价,有时是身体占据了我们,有时则是意识占据了我们,并且当我们处在作为“客观的主体”和“主观的客体”这种双向的(reversible)但权重不同的感觉中时,一方也许可以支配另一方。总而言之,如加里·马迪森(Gary Madison)写的那样:“感知主体本身被辩证地定义为既非(纯粹)意识,亦非(物质的、自在的)身体。意识……不是纯粹的自我在场;主体仅仅通过身体的中介(mediation)而向自身呈现,也是如此了解自身,也就是说这个在场始终是被中介的,即间接的、不完整的。”
既然不可化约的整体就是活体,而且它是辩证的,如马迪森所说“从来不能与自身完全一致”,因此绝不会获得一个固定的身份。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所有具身化经验并不涉及一种“直接”经验的素朴感觉(na?ve sense)。也就是说,无论它看起来是否直接,我们的经验不仅总是以我们所是的活体为中介,而且我们的活体(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经验) 总是被我们与其他身体和物的关系所中介,并且被其限制。因此,对我们经验的中介和限制,不仅通过转变各种知觉和表达的技术而实现, 也通过历史和文化系统而实现,这些系统不仅限制了我们知觉的内部界限,而且限制了我们世界的外部界限。事实上,正如我心目中的现象学研究所展现的那样,直接经验并不像它透明的时候那样直接—— 这既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投射发出意向,而不是对我们的知觉和表达的模式和过程发出意向;也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历史和文化,因而经验中给予我们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而不是通过一种与世界和其他人的潜在的开放态度而被接受。
因此,尽管现象学从一种经验开始描述,就像这种经验在所谓的“自然态度”(称为“自然化态度”更合适)中是被直接给予的,但是它接着要“解开”并且弄清主客观特性与条件,而正是这些特性和条件把那种经验建构和限定为有意义的经验。另外,尽管现象学也许从特殊经验开始,但它的目的则是描述和阐明一般的或可能的结构和意义, 这些结构和意义则体现了经验,并且使这种经验潜在地与他者共鸣, 成为他者的栖居之地。也就是说,尽管在历史和文化存在中,特殊经验也许是与众不同地被体验着,但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一般而又传统地被体验着——在第一个例子中,依据的是诸如时间性、空间性、意向性、反思性、自反性之类的具身存在的一般状况;在第二个例子中,依据的通常是透明的、支配性的文化习惯,这些文化习惯与其说是规范性的(regulative),不如说是规定性的(determining)。总而言之, 现象学的描述和解释,一方面试图充分描绘(adequate)一个给定的具身经验的主客观特点,另一方面也承认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上的不对称性。这意味着不仅关注具身经验的内容和形式,也关注它的语境。对一个充分的现象学描述的检验,不在于读者实际上是否已经拥有了所描述的经验的意义和价值,或者与之产生了共情,而在于这种描述是否引起了共鸣,以及“可能”身处这种经验中的(尽管稍有变化或赋予的价值不同)读者是否可以充分理解这种经验结构。
考虑到它对“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重视,现象学探究也常常有意识地关注和反思自己对语言的使用。确实,这意味着要实现哲学的精确性(有时由于它所阐述的特殊关系结构和空间结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尝试选择最合适的介词)。然而,对语言的此种关注同样也是为了真正地倾听和复活日常语言丰富而又被认为理所应当的那些表达方式,以及为了重新发现日常语言对经验密切而广泛的整合。就如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写道的:“日常语言……对我而言……成为一种储藏种种表达的温室,它保护着关于人类经验的最高的描述力量,尤其是在行动和各种感受的领域中。来自日常词汇的某些最精微区别的这种妥帖性(appropriateness)向所有现象学分析提供了语言层面的指导方针。”因而,在本书中,我不但借鉴专业的哲学或理论著作,而且借鉴日常语言、电影评论、广告、笑话、自助手册,以及其他针对大众的流行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凸显了日常语言的生命力,还意味着某种对具身性经验的共同理解或一般理解——即便它们从未在每一个身体(every body)中拨动同一根弦,但也会指向大家广泛的共鸣。
关于语言和经验,我希望本书中的文章相对来说友好易懂,因而会与我的早期著作——(在我看来)历史上必然充满争议——《目之所及:电影经验的现象学》(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Film Experience)形成对照。我不仅用罗列流行资源来帮助自己,而且这些文章中很多都是明确基于对(我的还有别人的)自传和/ 或逸闻经验的再现(representations)。然而,个人经验或“主体”经验的再现(以及这些再现有时带来的迷惑),为探究提供了起点,而不是终点。事实上,把广泛的社会诉求建基于自传以及逸闻经验之中,不只是对严格客观分析的一个模糊而主观的替代品,而且是有目的地为一种更具过程性、广泛性以及共鸣性的唯物论逻辑提供了现象学(以及具身化)的前提条件,通过这种唯物论逻辑,作为主体的我们可以去理解(或许是指导)那些作为我们客观的历史和文化存在而流逝的东西。因此, 就像罗西·布拉依多蒂(Rosi Braidotti)写的那样:“尤为重要的是不要混淆主体性过程与个体主义或特殊性:主体性是一种社会性的中介过程。因而,新社会主体的出现总是一项集体事业,它‘外在于’自我,同时也调动了自我的深层结构。”
尽管我的许多同事认为,我对具身性的研究兴趣与对自传逸闻的利用源自我做癌症手术的经历、大约十年前的左腿截肢以及随后对假肢的适应性融合——这些假肢将在后续多篇文章中出现,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一名女性,我时常会因为一些不一致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情况(我的物质存在被[或不被]看待和赋予价值的方式)而大吃一惊,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具身体”不仅很陌生,而且具有相对性。因而,我转向了关注具身性和经验结构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这一切发生在截肢之前,而且因为我的好奇心,这种新奇的身体经验让我的身体(而不是“那具”身体)成为一个做现象学研究的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实验室。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我不仅能够反思我的病理学境况,而且可以利用它去反思具身化(being embodied)通常所具有的透明性和规范性特点,就像现象学家常常做的那样,我从我所谓的残肢中学到的东西和从我所谓的失去的那条腿中学到的东西一样多。甚至是像“在场的”(present)与“不在场的” (absent)这样的词语也会接受拷问——它们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再现不足以表达我实际的活体经验,对于我实际的活体经验来说仍然是不充分的。在这方面(如果换个语境的话),凯瑟琳·加拉赫(Catherine Gallagher)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看法比较中肯:
从文化文本的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再现……与物质,尤其是与人类身体的象征距离之间不再存在固定关系。身体为人所理解的作用方式、男人与女人的差异、激情的性质、疾病的经历、生死的界限,都和特定的文化再现密切相连。身体作为一种“破坏者”(spoiler)而起作用,始终困扰着或逾越了它被再现的方式。
然而,如果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总是困扰或“逾越”它的再现,那么同样——这对我来说变得非常清楚,当我发现以及试图找到词汇向自己以及他人表达我的经验的具体特殊性之时——“我的身体”(还有“你的”身体,只要我或你谈到或写到它)有时可以为我自己和他者找到足以表达——甚至是拓展——它的经验的象征表达方式。因而,我会认为,当下向着自传和逸闻的转向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破坏者,而且, 我敢说,也可以作为身体的客观解释的解毒剂,而这种客观解释无法向我们讲述那些我们非常想知道的与身体之亲历有关的东西。
最后,走向身体自身的解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可感的场景”和“有责任的视觉”。尽管这里所有的文章研究的都是活体,而且这些活体总会体验着某些类型(经常但并不总是电影)的专业和技术媒介(mediation),但是这两个部分各有不同。第一个部分关注的是探索再现的某些经验场景和“难题”, 使这些难题变得明白易懂并为它们找到暂时的解决方案,用活体具体而积极的“感觉- 能力”(sense-ability)而非一种抽象的方式。这个部分的重点在于,我们的肉体思想如何能不仅让活体的主观感知有意义和感觉能力, 也让活体的客观再现有意义和感觉能力。在《森林中的面包屑:对空间迷失的三次沉思》一文中,我探索了各种形式的空间知觉,以及在空间上迷失方向的具身经验,为的是追问“迷失”(being lost)是否有不同形状(shapes)和时间性(temporalities),而这些“迷失”构成了不同的存在经验和意义——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与性别有关。《可怕的女人:电影、手术和特效》追问的是这样一种关于变老的场景,在那时我们的身体受制于变形(transformation),该变形不仅来自手术技术,而且来自电影技术。在开头的两篇文章中,电影还不是探究的焦点,尽管它们已经被用来作为说明和参照了,但是相反,我希望它们可以被更宽广的世界及肉身语境所阐明,它们正是在这些语境之中被调动起来。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更侧重于屏幕,尤其关注电影。《我的手指知道什么:电影感觉的主体,或肉身中的视觉》试图理解具身结构,这种结构不只是顾及一种仅仅是认知性的或基本自动的电影感知能力,并且试图揭示电影艺术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意义和价值如何通过我们的各种感觉而在肉体上出现。《收缩空间中扩展的凝视: 偶然事件、风险以及世界中的肉身》探索了电影凝视的暧昧及含混的性质,这不仅因为它在哲学中被理论化了,而且因为它在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电影中所阐述的杰出的唯物论形而上学中被具体地体现了出来,且与他者和物处在同一个世界之中。最后两篇文章探讨了所谓的“有意味的场景” 的现象学——尤其是因为这是以各种表达性的和知觉的技术的直接整合作为中介的,这些技术不仅作为工具而且作为空间、时间和物质层面的转变而发挥作用。《“苏西写字娃娃”:论技术、Techn? 与书写化身》这个题目来自从玩具反斗城买来的电子“书写”娃娃,这篇文章关注书写的物理活动和技术,也关注书写工具,这些工具各种各样的材料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时空意识,也改变了我们身体表达的感觉和形状。最后一篇文章《屏幕的场景:展望摄影、电影和电子的“在场”》延续了这样的探索,特别关注我们对摄影、电影和电子成像等感知技术的具身化介入,以及关注它们是如何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感觉和我们对自身的感觉。
第二部分“负责任的视觉”同样以活体的意义生产能力为根据, 但是它关注的是它们的经验和表象,这些经验和表象倾向于唤醒我们肉体的“反应- 能力”,并且为伦理关怀、意识和责任行为建构物质基础。另外,它强调我们的“肉体思想”教给我们的具体教训。《打败肉体/ 在文本中生存,或者如何活过整个世纪》是对一部分人的批评, 在当代的批评中,有些人把身体仅仅看作一个文本,因而愉快地给它“解惑”,否认活体造成痛苦的弱点,希望搁置(常常通过书写)给予我们严肃性的道德。《有身体在家吗?具身化想象以及从可见性中被驱逐》延续了当代有关身体客观化的探讨,通过对三个案例的思考,将它与视觉在伦理方面的贫瘠关联起来,视觉只会对可见的事物负责。我的癌症手术、截肢以及假肢最先出现在开头的两篇文章中,但在第三篇文章中成了最显眼的内容。《单腿而立:假肢、隐喻和物质性》关注的是近来作为隐喻的假肢为什么会“性感”,并且试图负责任地——以及从物质层面—— 把这个比喻重新植入对假肢的现象学描述(既包括比喻的,也包括字面含义的描述)之中,并使得这个比喻重新成为这种现象学描述的基础——以后不仅能为我所用,也能为其他文化批评家和被截肢者所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彼此相关,一篇是对另一篇的深入扩展。《铭写伦理空间:关于死亡、再现和纪录片的十个命题》既关注银幕上(尤其是纪录片)对死亡的“再现”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关注这样的再现如何(及以何种模式)表现了制片人的“伦理凝视”,以及如何“掌控”着观看者的伦理反应。事实上,第二篇相关的文章《真实的重负:具身知识和电影意识》,它探讨的是前一篇文章遗留的问题,关注的是纪录片和虚构影片中的真实感,以及它为什么不仅是从电影外(extracinematic)的知识被建构而成,也从“肉体知识” 被建构而成,而这种肉体知识要求它具有反应- 能力。最后一篇文章不仅是这一部分的高潮,也是本书核心内容的高潮,我们这本书的核心就在于我们为什么无法把自己同我们的物质性分离开来。《物质的受难:通往一种客体间性的现象学》最为清晰地——且丝毫没有化约地——揭示了我们既是客观的主体也是主观的客体,正是由于我们具有根本的物质性,所以我们对事物之美的超验感觉或对他者的义务才能得以出现和兴盛。就这方面而言,本书明显可以说是论战式的。也就是说,通过密切观察我们是什么样的物质存在者,以及我们如何感觉和回应世界及他者(绝不是直接的、纯粹的或“直露的”),我希望我们的图像意识和可见文化可以在其最根本上重新与唯物主义产生联系,并且认识到不但作为基础的重力(gravity)很重要,超验的可能性也很重要,这对我们的技术和文本来说是如此,对我们的血肉之躯来说亦是如此。
总而言之,我的愿望就是,本书中的这些文章能在阐明具身性前提这方面作出些许的贡献,我们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隐隐约约地体验着这些前提,而且这些文章鼓励对我们所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验物质保持更深入、更广泛的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