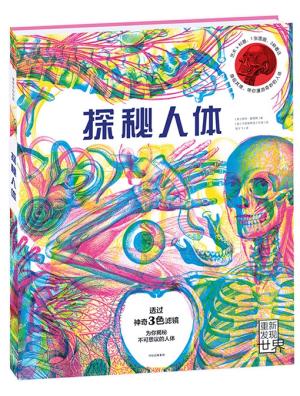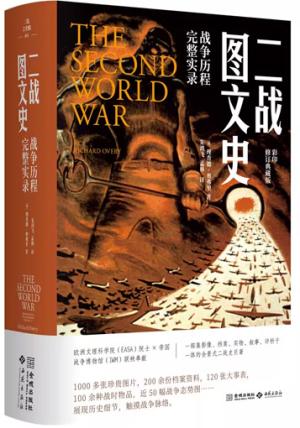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儒学即实学:历代道学讲义选说
》
售價:HK$
96.8

《
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
售價:HK$
129.8

《
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
》
售價:HK$
82.5

《
发明与经济增长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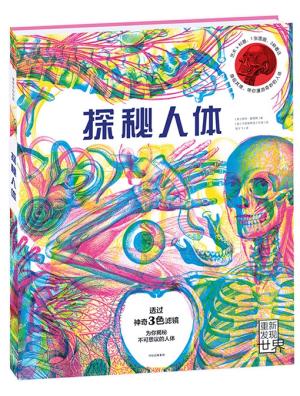
《
探秘人体
》
售價:HK$
108.9

《
从奥林匹斯山走来:德意志的考古学与爱希腊主义(1750—1970)
》
售價:HK$
140.8

《
乱世流离三百年:两晋南北朝十二讲(3版)两晋南北朝历史入门读物,东晋仍为皇权政治时代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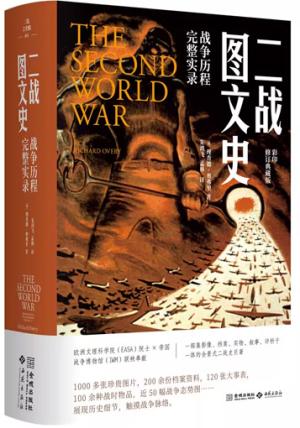
《
二战图文史:战争历程完整实录
》
售價:HK$
239.8
|
| 編輯推薦: |
1. 费孝通社会学经典作品,官方正版授权。内文参照费老生前审定文本,尊重原著风貌,增加100多条详细注释,扫清知识盲点与阅读障碍。
2. 快速理清全书脉络,深化阅读理解。随书附赠:阅读思维导读(由世界思维导图锦标赛中国区总决赛专业裁判张超绘制) 名家1小时精华领读课(知名讲书人、文化研究者张子航老师)。一次读懂听懂,深入感悟学习。
3. 大咖引领,重新发现经典的价值与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 认可推荐,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 撰文导读。
4. 细节拉满,追求舒适阅读体验。版式舒朗,类笔记样式,随手记录思考
5. 精装典藏版本,精美装帧,大开本设计,可平摊阅读
6. 内文双色印刷,重点突出,绿色护眼易读
|
| 內容簡介: |
|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一本关于乡村研究的经典著作。在这本书中,费老讲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书中讲到的乡土中国,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理解了费老的乡土社会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
|
| 關於作者: |
费孝通
(1910-2005)
美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曾写下数百万字的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民族学的奠基人之一。
博士师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先生, 并在其指导下,结合对开弦弓村的调研,完成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是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79 年,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20 世纪80 年代初,率先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
1980 年,被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
1981 年11 月,被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授予该年度赫胥黎奖章。
1982 年12 月,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1988 年,获不列颠百科全书奖。
|
| 目錄:
|
导读 从《乡土中国》认知中国 周其仁 XI
重刊序言 XVII
乡土本色 1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文字下乡 13
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
再论文字下乡 25
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差序格局 37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51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
家族 63
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
男女有别 73
“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礼治秩序 83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
无讼 95
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无为政治 105
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长老统治 115
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二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
血缘和地缘 125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137
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不会发生这距离的,但是事实上完全固定的社会并不存在。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
从欲望到需要 147
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后记 159
|
| 內容試閱:
|
从《乡土中国》认知中国
周其仁 知名经济学家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很多,不过这十数亿中国人,也可以说仅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这样看,城乡中国、中国城乡,拆开并拢,应该就是一回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城乡美国、城乡德国、城乡法国或城乡日本,更可以说城乡巴西、城乡印度和城乡俄罗斯,因为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人口,差不多一概都是城乡两分天下。“城市国家”(city country)是有的,譬如新加坡,整个国家由城市组成,完全没有乡村,不过那里的城市人,不少还是从周边其他国家的乡村里来的。倒是没有“乡村国家”这回事——整个国家全部由乡村组成,完全没有城市——不但当今没有,似乎很远久之前也从来没有过。《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名著,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时候,中国早有了城市。费老本人受教过的苏州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在有名的中国城市里;后来他到伦敦大学深造,更是地处世界大都会。或许是城乡之间深刻的分野,才激发前辈学人认知城乡、认知中国。
这是说,一个国家分为城乡两个世界,是相当普遍的现实。当然,普遍性总是隐藏在一个个的特殊性当中。概而言之,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所占比例高,城乡之间的差别不那么大,所以人们一般不取城乡角度讨论经济社会问题。像美国和法国,2012皆大选之年,不过好像没有听说哪一党哪一派拿那里的城乡问题说事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城市部分比例小,城乡之间鸿沟大,这就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础、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这也不难理解,要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那么离开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状况的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城乡中国本就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所以无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大的特征。可是几十年来中国在战略、体制和政策方面不断的选择与实验,也让今天的中国城乡具有若干鲜明的、不容漠视的特色。其一,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其二,市场改革激发了天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其三,城市化加速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造就了城乡关系极为夸张的紧张。
并没有把握说,这些现象他国全无,唯我中华独有。但是横看竖看,这样的三个现象交织到一起,把以十亿计数的中国人都网罗其中、欲罢而不能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多见的机会。不是吗?2012年的春节,仅铁道部公布的春运人数就达2.21亿人次;算上公路、水路和民航,春节前后40天全国客运量过了30亿人次!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世行有报告说美国每年3 500万人更换居所,也是人口流动的大国。不过,那边是长期搬迁,这厢却是短期探亲,过完了年节还要“打道离府”的。再往上追,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无疑也是个发展中国家,西部大开发、大搬迁青史留名。可是以我2003年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里查看到的资料,当年的美国移民多半就是举家西行,不似我们这里,光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就有好几千万。
让我辈无法别过头去置之不理的,不仅仅是城乡中国悲喜纠结,还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尚不容易阐释的逻辑。工业化搞不起来,城镇给不了乡下人更多的机会和容纳空间,好懂;可是国家工业化如火如荼,城市大门却对农村日益紧闭,却实在不好懂。再有,人往高处走的动力学,好懂,所以工业化、城市化伴随大量移民,不断从低收入的乡村地区移向机会与收入较高的城市,也好懂。从这个逻辑出发,城乡的收入差距大,才刺激强劲的进城移民运动,等到更多的农村移民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趋近。可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城乡差距激发的似乎只是“进城打工”,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到城市赚钱,年纪大了还是回家。这岂不是说,城乡收入之差,缩短一段时日之后又要重新拉大?还有那所谓的“土地城市化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从没听说过这个别扭概念的读者,要容我以后细说——岂不是确认,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意味着人口在空间分布的密度下降?如是,叫城市化,还是叫逆城市化呢?!
最不好懂的,是工业化城市化驱动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居然给城乡中国带来出乎意料的紧张。我读到的相关新闻,十之六七,要件不是一幅地,就是一处房。奇了怪也:房和地不就是“生产要素”吗?平平和和地“配置”不就得了?就算市场上供求双方利益相向,不是还有句老话“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怎么要闹得如此火爆,个别场景居然还要舞枪弄棒的呢?个人不相信那些深不可测的“斗争学说”,而倾向于认为,这里面总是哪个制度和政策环节没有妥帖,才让中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的城市化加速,从某个角度看去好像是中了什么诅咒一般可怕。
就城乡中国的大题目,我曾根据自己的探查写过一系列的评论,结集成了《城乡中国》,有向费老致敬的意思。那本书中,妙趣横生的小题目多得很,比如“城中村”,也许各位略有所闻,不过欲知其详,我们还需要一道前往探查。“村中城”呢?很少听说,怕要实地看了江阴地方号称“天下第一村”里那座300米高的摩天楼,我们才算知其然。还有“城中城”哪,几年来区区在下追踪访问过那么几座,颇有感悟,很乐意与读者分享。“是城似乡”则所在多有,费老当年刻画的“乡土中国”,不但在观念与人际关系方面依旧覆盖着今日的城乡中国,而且直观地看,很多大都会城市的很多空间其实还“相当的农村”,人们见怪不怪就是了。中国的城城乡乡之间,有多少现象值得梳理,又有多少道理值得探究?
当下的时代跟费老的时代相比,当然有了很大变化,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那个年代学经济和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很多都读过费老写的《城乡中国》,他在国内做过很多田野调查工作,在英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回国后写了《乡土中国》。这本书虽然不厚,但一直不断被后学者不断学习和引用,时至今日,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仍然有很多启示。所以我乐见其不断再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