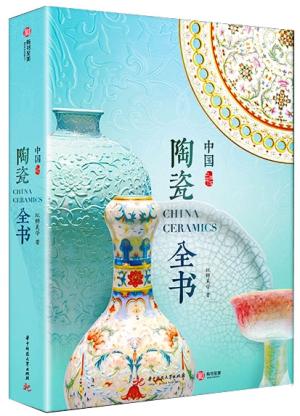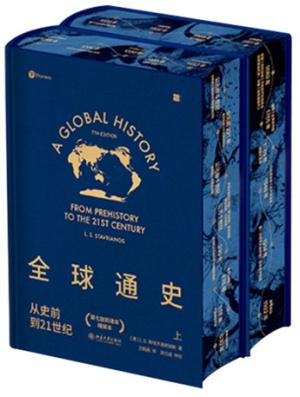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函套精装版)
》
售價:HK$
43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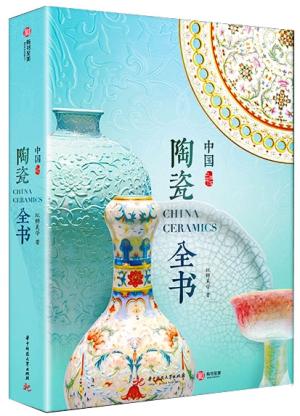
《
中国陶瓷全书【珍藏纪念版】
》
售價:HK$
1097.8

《
世界中国学:当代发展与未来展望
》
售價:HK$
140.8

《
低空经济蓝皮书:低空经济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217.8

《
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理想国译丛074)
》
售價:HK$
107.8

《
跨越学习曲线:成就非凡的行动指南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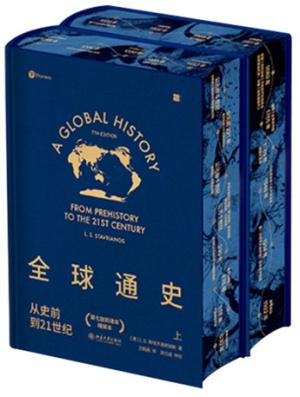
《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七版 特装版 新译本 上下册】
》
售價:HK$
316.8

《
财富的秘密:一部瑞士经济发展史
》
售價:HK$
52.8
|
| 編輯推薦: |
通过随涂随抹的写作,人们得以将美、将生命的信息凝固在纸上,暂时战胜时光的暴虐。
透视文本包罗的万象世界,辨认东西方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思想情感。在剖析文本的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及生命关照。
《繁花》中审视世界的方式、格非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李洱的知性写作美学、张怡微的青春书写……
薄伽丘、加缪、毛姆、迟子建文本中的瘟疫书写折射的人世万象,昆德拉热,颠覆传统认识的《哈姆莱特》前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群天生反骨之人……
|
| 內容簡介: |
|
本书聚焦不同时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前沿话题,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下,关注富于时代性的文学话题。在线性时间的批评文本中,了解中国现当代热门作家莫言、余华、格非、张怡微等的创作创新,探望世界文学经典文本中的人事物象。在中西文本的对比剖析中,作者不仅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作家在汲取西方有益经验、激活传统资源、破立并举的创新创作,而且表达了关于文学批评的视界及观点、文学创作的追求及人本关照。
|
| 關於作者: |
|
王宏图,上海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长篇小说《Sweetheart,谁敲错了门》《风华正茂》《别了,日尔曼尼亚》《迷阳》《无所动心》,中短篇小说集《玫瑰婚典》《忧郁的星期天》,文学研究专著《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批评文集《快乐的随涂随抹》《眼观六路》《深谷中的霓虹》《东西跨界与都市书写》等,并译有J.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
|
| 目錄:
|
目 录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 1
文化立场 ……………………… 2
共同经验 ……………………… 5
知识传统 ……………………… 8
代际差异 …………………… 12
东西纵横
在西方的目光下——当代文学价值评判与世界文学标准 ………… 19
诺贝尔情结: 西方文化的霸权和东方的边缘性 …………………… 30
遥相对峙的国度: 纯文学的衰微与大众的文学接受模式 ………… 42
比较文学的危机和价值 …………………………… 55
时文别解
老树繁花 “闪耀的韵致” 和迷津——《繁花》审视世界的方式及其他
………………………………… 75
中国传统审美资源的回归、 化用与价值——从格非近作看其新古典
主义风格 …………………………………… 103
通向 “文城” 的漫长旅程——从余华新作 《文城》看其创作的演变
……………… 122
知性写作的美学与小说疆界拓展的限度——从 《应物兄》说起
…………………………………………… 144
家国叙事与个体精神叙事的叠合与断裂——从 《财主底儿女们》
为出发点看中国小说的叙述特质 ……………………………… 158
痛, 且飘浪在风中———张怡微的青春书写 ……………………… 191
超越于真实幻觉之外———兼论 《纪实和虚构》《务虚笔记》 …… 205
私人经验与公共话语: 陈染、 林白小说论略 ……………………… 220
在都市狂欢打击乐的背后: 读邱华栋 《城市战车》 ……………… 234
西土屐痕
文学与瘟疫的不解之缘 …………………………………………… 239
昆德拉热与文化犬儒主义 ………………………………………… 253
猎手与猎物间的权力游戏——耶利内克 《钢琴教师》及其他 …… 264
复仇的正义性与身体政治——读 《葛特露和克劳狄斯——
<哈姆莱特>前传》 ……………………………………………… 273
从受害者到虚无主义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反叛者的形象
……………… 286
左顾右瞻
“我城” 叙事模态新变的潜力 …………………………………… 299
青春物语——20世纪70年代作家散论 …………………………… 306
欲望的凸现与调控: 对 “三言” “二拍” 的一种解读 …………… 315
话语的冲突: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种外来话语 ……………… 335
|
| 內容試閱:
|
序
清风明月人自适
王宏图
日月运行,寒暑移替,时光悠然流逝。当年孔夫子面对滔滔滚流的河水,百感交集,发出 “逝者如斯夫”的喟叹。1780年,德国诗人歌德正担任魏玛公国枢密顾问,公务繁冗,觅得闲暇,便登高望远,一时兴
起,便在山顶小屋的墙壁用铅笔写下了意味隽永的 《浪游者的夜歌》:
群峰
一片沉寂,
树梢
微风敛迹。
林中
栖鸟缄默。
稍待
你也安息。
(钱春绮译)
初读此诗,人们多半会将结尾两行解读为歌德对人生短暂不无伤感的感叹。但那时歌德刚年过三十岁,尚处风华正茂之年,离人生的终点尚有五十多年之遥。因而,有研究者认为诗中的 “安息”并不意指死亡,而是内心的宁静。然而,诗歌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它有赖于一代代读者的接受与阐释。三十三年后的1813年,歌德故地重游,惊喜地目睹旧日的诗行。由于字迹被时光剥蚀得有些模糊,他遂重描加深。此时歌德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安息”在他的心中真被赋予了死亡的意味。十八年后,在1831年8月八十二岁寿辰日,歌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此山,重读旧诗,感慨万千,自言自语吟诵着 “稍待/你也安息”,不禁潸然泪下。这一诗句成了死神悄然而至的脚步声。翌年三月,他便安然长逝。
眼前这本小书,初版于1998年5月,迄今已近二十七年。它汇集了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下的一些有关中外文学的理论批评文章。以当今严格的学术规范加以审察,它们大多显得粗陋浅薄,无的放矢,学养功底更是无从谈起,只不过留存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与烙印。我从没奢望这本小书能有机会重版。承编辑美意,它得以以修订版的面目在同一家出版社推出,给人老树萌新枝的惊喜。这次我删除了一些不忍卒读的篇章,增添了一些近年新写的批评文字。当年不无轻狂的青春激情早已烟消云散,有的只是略显沉重的思索与怅惘。冬日已去,又到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踏青时节。近斯重读苏东坡 《前赤壁赋》,文末那段文字再次在耳畔回响: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正是以苏东坡寄情山水的旷达之情,我敝帚自珍,将这本小书推出,并对在出版过程中付出诸多心血的编辑谨致谢忱。
2025年3月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
有被史无前例的癫狂的漩流所裹挟、冲撞……但这种幸运反过来成了我们的劫运——由于一帆风顺 (相对而言,将那些小小的崎岖、波折忽略不计),我们的成长期格外地漫长:在自身的迷乱、焦灼中,在忽忽欲狂的等待与期盼中,在生涩而鲁莽的尝试中,我们辨不清方向,而有意无意之间沾染上的对一切神圣价值目标刻毒的嘲谑又使我们有了一副未老先衰、矫情、面目可憎的世故相。
但这并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一无所有:们不必像某些人那样故作姿态地自诩为 “苦难历史的魔鬼终结者”,①但我们有着尽管卑微却也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它熔铸成了我们的文化视角和立场,建构了与自己的精神世界相匹合的知识传统与结构。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人的映衬下,我们的色彩虽不绚烂璀璨但却鲜明丰盈,我们的声音虽不激越高亢但却从容沉着、跌宕有致——总之,它们不是任何人的摹仿、放大或者延伸。
文化立场
一代人有一代人独特的文化立场,但在某些人 (主要是上一代人)的眼里,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立场总显得有些可疑、暧昧不明。有一种看法认为,19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不太关注社会和重大事件,缺乏高昂的人文精神。②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指责。与其说上述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真实的精神风貌,不如说它是上一代人话语的一种习惯性反射——实际上他们要指斥的是我们没有全心全意地承袭他们对当下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的那种激昂的热情和根深蒂固的救世情结。但我这儿要说的是,凭什么我们非得像前辈人那样,以他们的方式和姿态来看待世界和人生?
我丝毫不认为人在动荡不息的社会现实面前应采取一种漠然处之的犬儒主义态度。但应该打上问号的是人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 我们并不缺乏人文精神,但我们与前辈人的主要分岔点在于我们心目中的人文理想立足于我们个体的生命存在,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
我们理解,前几代人由于特定的社会情境的制约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认定他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切都要在社会的舞台上得到体现与确认。我们会对他们抱有适度的敬意,但决无可能再重复他们的历程。
对我们来说,我们依据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独立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尽管其间你可以最大限度地与亲友分享欢乐与痛苦,参与投入各种群体活动,但最终你得独自承担生命的重负与虚无。当你的生命历程结束时,你是孤独一人离开这个世界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 “死总是自己的死”,任何慰藉、祷告都无济于事,任何盖世的伟业与巍峨的丰碑都无力抗衡死亡摧枯拉朽的淫威。人生这种永恒的悲剧性境遇在加缪的剧作 《卡利古拉》中一语道破:“人终有一死,却并不幸福。”
然而,我们并不是虚无主义者。我们和前辈人一样热爱此生此世的生活。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又会遭到前辈人激烈的责难:你们这一代人是多么地虚怯啊! 你们口口声声地说热爱生活,但你们又付出了什么! 鬼才相信你们热爱生活,如果真是热爱,为什么不像我们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入? 为什么不关注当下沸腾的生活和重大的社会事件? 离开了这些,个体还有什么真正的生活? 说到底,你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永远是冷漠的旁观者。加缪 《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倒是你们的真切写照。你们反复声辩你们有着并不比我们黯淡的人文理想,但你们从来没有为它的实现倾注过心血。你们从来没有奋斗过,从来没有忘我地投入过一项事业。你们永远只是纸上谈兵,只是一味贪图安逸。不错,你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你们不费吹灰之力便享受了改革的年代带来的全部好处,并以此沾沾自喜。你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 你们只是像影子一样地飘浮着。
诚然,在我们的心目中,个人精神的独立追求与自我完善比殚精竭虑地作种种救世的高贵尝试更为重要。由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系的局限,人永远不可能臻于至善的境地。堕落、腐败源于我们内在的天性,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剔除它们。在污浊的大地上,正义的实现总是要打折扣的,除非你将这个世界整个地毁灭。对于俗世,我们不抱过大的奢望。文明只是粘附在人肉体上的一层貌似坚固的膜,野性说不定在哪个凄惨的清晨便会肆意横行起来。我们的确很渺小,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穷尽个体生命的可能性。我们不依恃任何人。我们不必为名利的得失而戚戚惶惶。死亡为我们的生命设定了最终的归宿和边线。然而,我们并不因为我们必有一死而颓唐不振,相反,正因为我们必有一死,生命才显得如此可贵,才如此值得尝试与呵护,我们才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投入一次性的生活,即使像西西弗斯那样徒劳地将滚下山的巨石一次次地推上高岗。如果说西西弗斯最终能声言他是幸福的,那么我们也将是幸福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我们归于尘土之前的一次潇洒的腾跃与飞翔。这样我们能在离去时像古巴作家卡彭铁尔那样说上一句:“回归种子!”
生活是这样,写作又何尝是例外。对于我自己,写作是一种快乐的涂抹,一种速朽的随涂随抹。写下,随即被抹去,消散得无影无踪,正如一代人的出生、成长、死亡,从地球上被抹去,来自尘土又回归尘土,新一代人又在出生、成长,再一次被抹去。里尔克的一首诗概括了我们的基本的立场: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 ——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 ——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 ——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 ——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
与星光似地认识你? ——因为我赞美。
共同经验
20世纪60—90年代,急剧的历史变迁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过去,它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基本的感性资源。在我们的心目中,它似乎还没有成为历史,似乎依旧留存在当下的生活之流中,触手便可叩击、抓捏、秤量。然而,在细细的辨析和回味中,一种往事如烟的隔世之感却慢慢地爬上了心头。
多少次,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震惊,依旧是我的第一感觉。一切到来得是那么的迅捷、那么的突然、那么的不可思议,仿佛技艺高强的魔术师在一夜间将魔法抛撒布施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无法断言这几十年所发生的一切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但其变迁速度之迅捷,规模之浩大,震荡之深远,代价之沉重,实在难以找到可相与匹敌者。在我们诞生之初,全中国沉陷在前所未有的乌托邦的狂热中。等到这股红色的狂潮耗尽了它的全部威力而趋于疲软之际,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旋即启动。尽管身历其境,我还是感到眩目。
在我们贫瘠而苍白的童年,我们被亲切而又武断地告知,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和地球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劳苦大众比较,我们有幸享受天堂的富足与美满。我们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地高呼着打倒牛鬼蛇神和帝修反的口号,吟诵着光芒四射的词句,陶醉在不知其然的所谓的献身的热情中。我们不自觉地为自己的高尚无私而感动。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童年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有着极为充裕的时间 (尤其在假期中)玩耍、游乐,沉迷于打牌、捉迷藏、“造房子”游戏,摆四国大战、海陆空大战的浩大棋阵,这在今日里匍匐在升学的悬剑下,战战兢兢到唯分数是瞻的学童眼里,真可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转眼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不必再为上山下乡的前景而惴惴不安。我们总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自己的命运。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长辈和老师们长年累月在我们头脑中苦心浇铸而成的海市蜃楼般的理想王国崩坍了。我们从一个恶作剧般的噩梦中醒来。先前紧紧锁着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宏大的新世界展露在我们眼前:自欺欺人的神话在一夜间被打得粉碎,我们不但不是生活在天堂里,而且还面对着令人难堪而又难以忍受的贫困与落后。我们变得空前地清醒,我们一时间变得一无所有,这一冲击波的力度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完全显露出来。
这便是1980年代,充满希望、高亢激奋的年代。那时我们为即将降临的美好的新世界而激动不已。20世纪80年代是呼唤人性、自由与青春的时代:西方在本世纪内又一次向我们作着媚眼,允诺着自由与福祉。我们一下坠入了情网,变得那么地自作多情,以为白种人对黄种人的爱慕也会报之以桃李。这一切都变得那么地顺理成章:我们疯狂地汲取着海外传来的新福音,吞嚼着闻所未闻的新信息。对我们爱恨交加的本土传统,我们自以为有了崭新的解读——平心而论,与对西方的爱慕相比,这种理解既不深入,又显得有些苛刻。
然而,在希望的亮色的边缘部位,绝望与焦灼不断地增加着浓度。我们游荡着,不知将飘向何方,这正如帕斯卡尔在 《思想录》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航行在辽阔无垠的区域里,永远飘移不定,从一头被推到另一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停留。这种状态对我们既是自然的,又是最违背我们的意志的”。我们不停地在两个极端间游移摆动,一时间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坚固的基石。也正是在1980年代,出国潮席卷全国,人们急躁不安地蜂拥着迈出国门,携着各种黄金色的梦想,提前体味着充当现代人的兴奋与窘迫——这成了时代焦灼的一种典型症候。
然而另一支旋律 (它在1980年代已经若隐若现)渐渐地响亮起来,并压倒了先前的一切音色——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起飞。人们又一次地激动、亢奋起来。但这一次与1980年代完全不同:如果说充溢着浪漫情思的1980年代像是一张多种色调竞相交映的彩色照片,1990年代则是一幅黑白对比过分鲜明的照片,务实,但又凝滞、沉闷。它在使我们一步步远离贫困并初次领略到空前的富足与丰裕的同时,也将物欲横流、良知泯灭重重地压在了我们的头上。在消费主义近乎将人吞噬殆尽之际,留给人们的是自我消沉的愁闷与放浪形骸的狂欢。时时刻刻,人们祈求着股票、债券、邮票、磁卡、不动产几何级数地增值;时时刻刻,人们期盼着别墅、豪车、美女蜂拥而来;然而,人们忘记了我们的道德在一天天沦丧,忘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在一天天恶化。
如果说1990年代的人欲横流是1980年代人文主义思潮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直接操演与翻版,我还是感到震惊与晕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所包蕴的众多的不可测与混沌未辨的因素都对人类高傲的理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我只是凝视着这万花筒般变幻沸腾的生活之流,为人们的热情与变革的勇气,为人们的痴狂与无知,为人们长江后浪推前浪、亘古不绝的青春活力与美艳而惊叹、迷醉。也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永恒的魅力和一切大写的意义得以衍生的源头。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去耕种自己的园地。
知识传统
这儿的 “知识传统”不应被理解为纯粹学理层面上知识信息的延续与接受,它更多指涉的是一种精神气质上的浸染与传承。它并不表现为某种明确的信条、原则或是方法,但却像大气一样环绕着一代代的人们,滋润着他们的心灵,间接地引导着一个时代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基本走向。在详尽地剖析我们这代人自身的知识传统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前辈人的知识传统——在这样的比照中,有可能对我们自身的特性认识得更为清晰。
我们的前一代人有一个梦想,而且历史似乎也提供了机遇让他们实现这个梦想——将自身个体的奋斗追求汇入历史的大潮,促使人类走向至善的王国。我们在这儿一点没有揶揄嘲笑这一梦想的企图,它可以说是世世代代蛰伏在人类心灵深处改造世界的冲动,没有了它,这个世界将永远沉没在漫漫长夜之中。但梦想是一回事,将它搬移到现实中加以实施是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黄昏时分,密涅瓦的猫头鹰起飞了,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向人们展示出一幅绝对理念王国迷人的图景:交织着千千万万人互相抵牾、冲突意愿的历史活动在它们纷乱错杂、光怪陆离的表象背后竟蕴藏着同自然界相似的规律,在螺旋型的曲折上升过程中,人类一步步地迈向光辉璀璨的自由王国。依照着这一蓝图,人们可以充分地自觉意识介入历史的发展历程,对它进行大胆随意的改动、剪切、拼接和重组,以吻合他们善良崇高的目标。尽管一切都涂抹着无神论的色调,但人们毕竟需要一个神灵。当基督教和其他古老宗教的上帝趋于式微之际,理性的上帝便充当了替代品。它那宗教般的感召力吸引了无数虔诚的信徒 (当然也包括为数不少的投机分子),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它奉献出自身的一切。然而,他们并不是毫无偿报,在理性的高歌凯旋中他们的救世情怀和道德热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这成了他们人生价值最为深厚的源泉。尽管前几代的不少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蒙受了难以想象的煎熬,但他们虽九死而不悔。因为他们坚信大地上最终会出现一个正义与理性的王国。
早在18世纪末叶,仿佛是有先见之明,西班牙画家弗郎西斯科·戈雅曾作过一幅题为 “理性之梦召来妖魔鬼怪”的浮雕,隐喻启蒙主义的理性导致了拿破仑血腥的战争。理性有一种僭妄的梦想,它企图将由具有丰沛活力的人创造的历史如同无机的自然一样笼于股掌之间,然而也正是在这儿,它遭到了致命的失败。况且,近年来的科学发展使数百年来建立在形式逻辑体系和以求索因果关系为宗旨的实验基础上的巍峨的科学殿堂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在世界深层的微观结构层面,经典科学的原则束手无策,取而代之的是不确定、不可测、非决定、随机、混沌等非因果性的概念范畴。理性的权威在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先前独擅胜场的自然科学领域尚且如此,在比自然界复杂得多的人类社会,理性更愈益显示出它先天的局限性。这一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的自白中得到了极为充分、完整的阐述。正如地下室人所说的那样,在理性的视野中,“无论是意志还是任性,在人的身上实际上都不存在,而且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人本身充其量只不过是钢琴或风琴的琴键之类的东西罢了……人不论做什么事,都绝非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身不由己地按自然规律行事的”。但事实上这只是理性武断的假设,因此地下室人质问理性道:“人要是没有愿望,没有意志,没有欲念,那还成什么人呢,岂不成了风琴上的一个键子?”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呼喊和抗议,这是繁衍、生息在整个大地上的生命在诉说、争辩: “人,不论他是何等样的人,也不论在何时何地,总喜欢随心所欲地行动,而绝对不喜欢按照理智和利益的指点去行动……自身的、自由自在的、随心所欲的愿望,自身的、即便是最最乖僻的任性,自己的、有时甚至被撩拨到疯狂程度的幻想——这一切便是那种被遗漏掉的、最最有利的利益”, “他要为自己保留的正是荒诞不经的幻想、庸俗不堪的蠢事,用以向自己证明(好像这是非常必要似的),人终究是人,而不是钢琴的琴键”。这个撒旦般的爱捣蛋的人成了理性实现其目标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他对理性用甜言蜜语允诺的拔地而起的 “水晶宫”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死命地抱住自身卑微、怪戾、荒诞的习性不放——他所要捍卫的一切看似是某些极端个人化的怪癖,实则牵涉整个人类乃至生命世界的尊严与自由。
这并不是将世界描绘成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混沌未辨的黑箱,而是要标明理性的限度。理性并不是所到之处无所不能,它只在一定范围、区域内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一旦越出了边界线,它便会像真空中失重的物体、断线的风筝,轻飘飘无所适从。这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和前几代人的重大分野之一。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产生于西方不同时代的思想学说,从1980年代起汇合在同一个时空,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丰富了我们的心灵。
应该说,我们是以一种复杂的心情走近马克思主义的。出于对人类现世苦难的深切同情,出于对天上的王国在地上实现的坚定信心与急切愿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勾勒了未来美好世界的蓝图。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唤起了千百万下层群众起来反抗自身被奴役的处境,为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我们无法绕开马克思主义,像萨特所说,它是当代无法被超越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早年所写的 《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点燃了我们的热情,他的人类学的思考取向,他对人类生存异化状况的思考,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成了我们理解世界与人生的门槛。我们由此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还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一时间,各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南斯拉夫的 “实践派”等)也成了我们关注的热点。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推动着我们从新的途径去接近它。
尽管马克思主义最终为人们树立了一个终极性的信仰,但在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时,它充溢着大胆的怀疑精神和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它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秘密,打破了它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具。它将一切事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阐释。这已成为我们血脉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了一切人文学科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
在谈及性这个私人化的隐秘领域时,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富有革命性了。他传授的不是什么房中秘术,而是对人的无意识世界和内在的精神动力结构的精湛描绘。在经过弗洛伊德思想洗礼之后,性成为我们思考人、理解人的一个基本向度,尽管在他那儿唯性论和机械的因果论触目皆是。于是,自我不再是一个稳固的实体,不再是通过一系列古典式的道德修炼可达到的一个超人的理想境地的载体;相反,它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所在,一个由本我、社会化了的自我与伦理化的超我角逐的赛场,一座行将喷发的活火山。东方民族的性伦理与风俗在此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之后剔除性因素的任何纯粹完美的道德修行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了。
当然我们不会遗漏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巨大启迪,它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文化立场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抗荒谬、追求自由、独立地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充满激情地生活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此外,我尤其钦佩敢于抵抗一时风气的加缪,他在 《反抗的人》中对以适度与平衡为核心的古希腊地中海思想的强调,否定了当世盛行的导致世界与人走向毁灭的虚无主义思潮。
福柯对迈入信息时代的我们有着特殊的价值。在这个被铺天盖地的信息遮得密不透风的世界,他对知识话语类型的考古学溯源,对与知识交相纽结的权力网络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并从界外观察这世界,从而有可能相对清楚地认识这个被各式各样眼花缭乱的话语屏蔽了的世界。话语只是话语,只是粘附在大地表面的一层泡沫,而不是大地本身,更不是生命本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