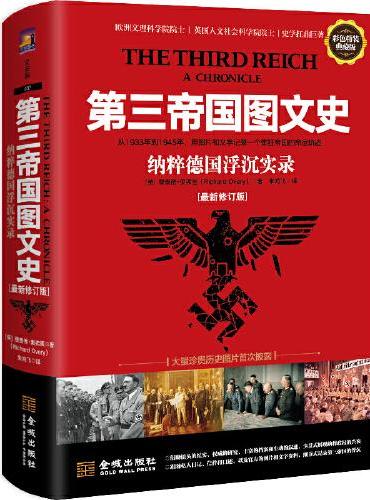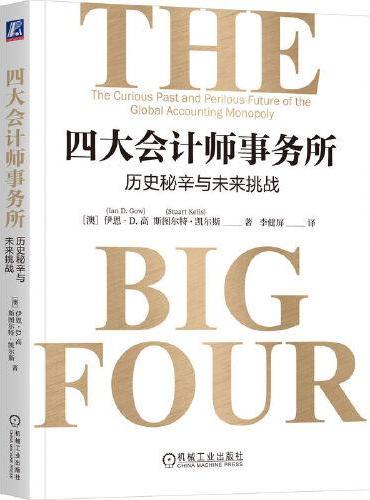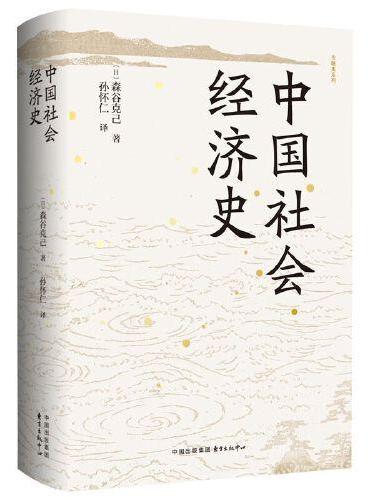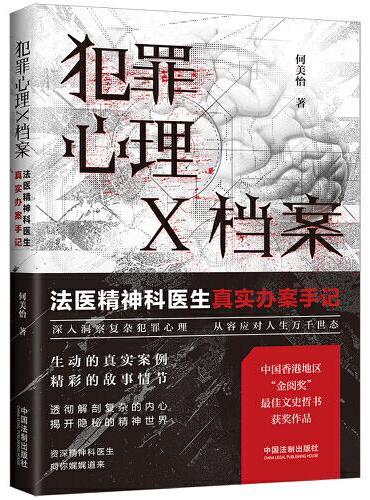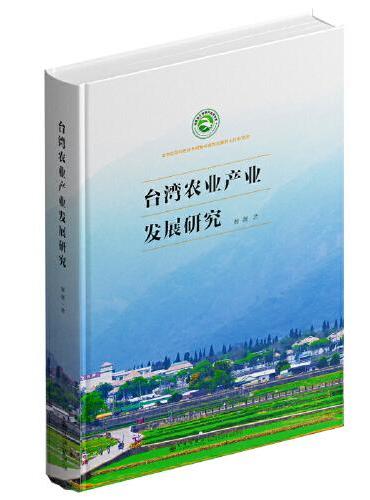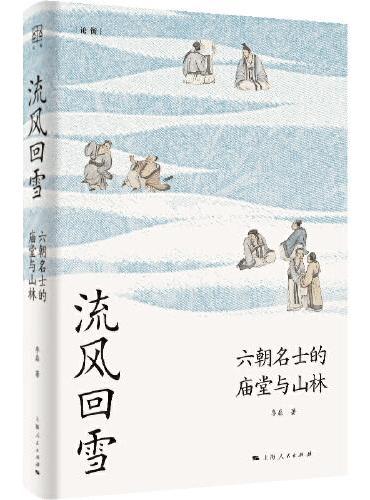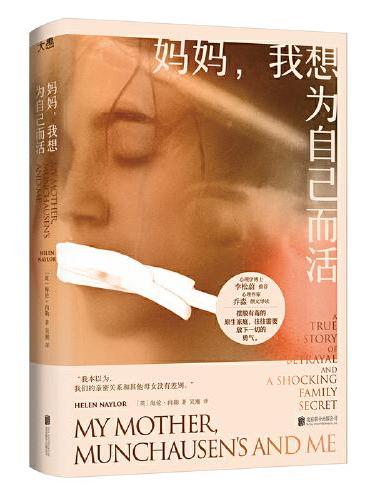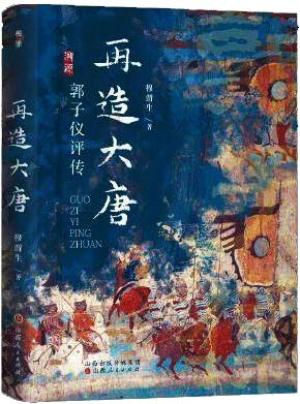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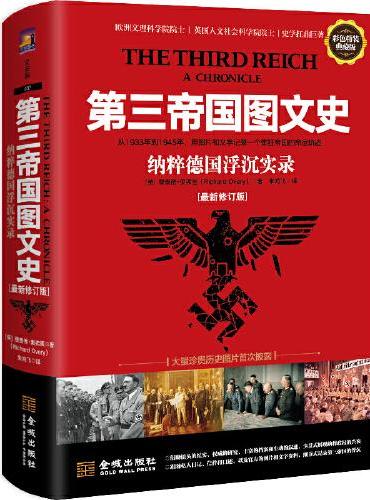
《
第三帝国图文史(修订版):纳粹德国浮沉实录(彩色精装典藏版)
》
售價:HK$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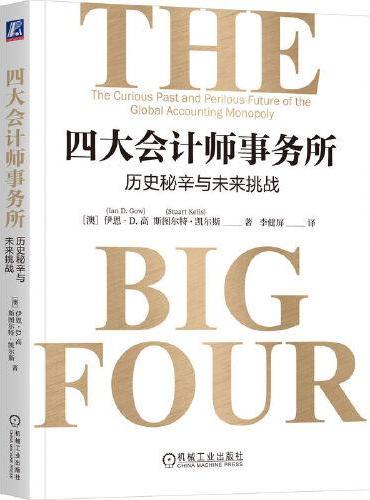
《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历史秘辛与未来挑战
》
售價:HK$
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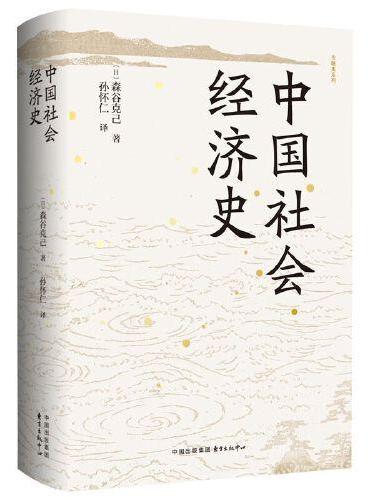
《
中国社会经济史
》
售價:HK$
1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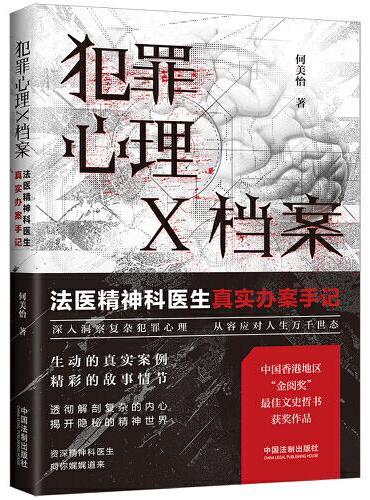
《
犯罪心理X档案:法医精神科医生真实办案手记(第一季)法医精神科医师心理解剖手记
》
售價:HK$
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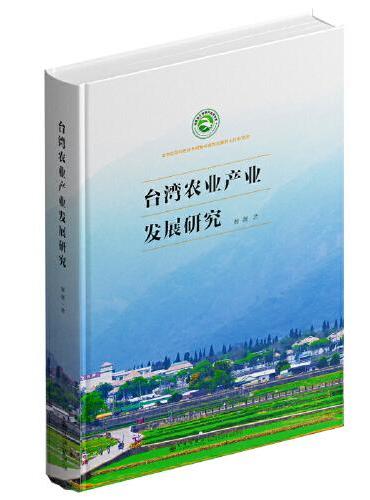
《
台湾农业产业发展研究
》
售價:HK$
1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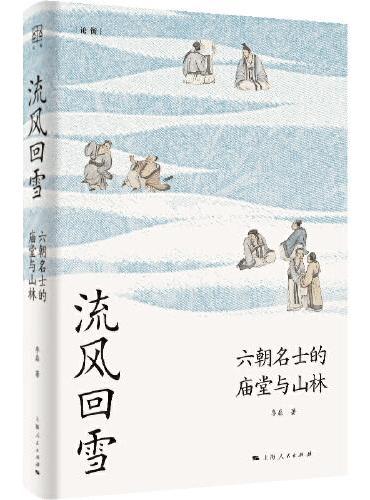
《
流风回雪: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论衡系列)
》
售價:HK$
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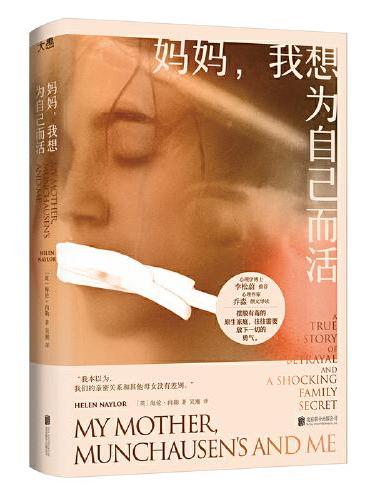
《
妈妈,我想为自己而活
》
售價:HK$
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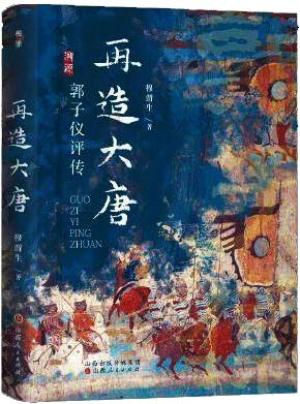
《
再造大唐:郭子仪评传
》
售價:HK$
93.6
|
| 編輯推薦: |
1、单口相声演员方清平的人生故事集,演的笑料,都是真的人生。
2、冷面笑匠的快意人生“包袱”,“清平式”幽默叙事法,有趣有料也有泪,读来令人唏嘘与感动。
3、五十余载人生经历,教人看懂人心、人情、人性。
4、从底层到顶峰,从台前到幕后,这是方清平的人生百态,也是普罗大众的百态人生。
5、给当代青年的一本反焦虑之书:年轻时都心急,到了中年才明白,路很长,慢慢走。
6、作者亲绘封面及内文插画,幽默或反讽、别样有意趣;双封面设计,书名烫黑金工艺,立体呈现主题寓意。
|
| 內容簡介: |
《越冷越幽默》是相声演员方清平的个人随笔集,也是他横跨五十年人生故事集。
他曾籍籍无名,也曾站在顶峰。他讲述自己在相声圈里的摸爬滚打,记录自己退居幕后的厚积薄发,也谈到相声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一个时代的变迁……
全书将“冷幽默”一以贯之,读来令人感动与唏嘘。那些在他生命里留下珍贵记忆的家人、朋友、师长,以及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勾勒出一幅有趣的精神家园画卷。
|
| 關於作者: |
方清平:
相声、小品演员,编剧,北京青门海派创始人,师从李金斗先生。粉丝称其“冷面笑匠”。
2010年因参加第五届CCTV相声大赛,表演单口相声《幸福童年》一炮而红;2013年2月初登央视春晚舞台,同年3月,因担任BTV《脱口而出》主持人而广为人知,后一直活跃于各类晚会的舞台。
参演电视剧《老酒馆》《生活有点甜》《乞丐大掌柜》等,并参与创作多部剧本。
|
| 目錄:
|
我的多半生
为什么不爱笑
打工记
师恩若水
台上的尴尬时刻
南漂儿
码字生涯
我要上春晚
重出江湖
我要出圈儿
故人和故乡的故事
我的母亲
赵家三辈人
一些故人
寻找故乡
有定数的生活
我有酒,也有故事
吃货精神
饭局漫谈
借钱的艺术
理想会变成现实
相声画儿
|
| 內容試閱:
|
一不留神就老了
虚度了五十年,不是谦虚,真是虚度。我读名人传记,看人家经历了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而我的人生呢?仿佛文笔拙劣的编剧写的剧本,刚有个开场,没有悬念和波折,马上就进入了结局。
回首往昔,我也想努力地感慨一番,不然就显得我的人生太无趣了。
而立之年,我写剧本挣了几万块钱。朋友前呼后拥,每天吃晚饭至少能凑一桌,都是我请客!后来买了辆两厢夏利,在我心目中那车相当于现在的顶级路虎。那时候我很快乐。
在不惑之年参加相声大赛,说了段单口相声。某天晚上打车,师傅说:“你不是说单口相声的方清平吗?”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第一次碰见粉丝,我当时的高兴程度,不亚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脑海里想起了大杂院里那个守在破收音机前听相声的穷孩子,想起了在公园说相声,招来路人轻蔑眼神的无业游民。
我愣是到金鼎轩花三百多块钱,请这位知音喝了顿酒(师傅把车停饭馆门口,吃完就打车走啦)。
后来我把单口相声说出了北京,说遍了全国。走在拉萨的街头,一位藏族同胞喊我:“方清平!”到了西双版纳的基诺山,一位基诺族的兄弟看着我说:“你是说单口相声的?”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富豪有抑郁症,在当地华人医院的电视屏幕上看到我的相声演出,很是喜欢,从那以后他听我的段子慢慢缓解了抑郁的情绪。他托一个回国的医学教授带话给我表示感谢,还委托教授为我诊病。我心想:作为一个说单口相声的演员,我这辈子值啦!
我仿佛有点儿悟了。
“人生如梦”这话太准确了。回忆起过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仿佛是另一个自己,一切都变成了过眼烟云,没在生命里留下一点儿痕迹。
在我年轻的时候,社会上讲究资历,都是岁数大的人说了算;如今我上了点儿岁数,也到了给别人指手画脚的年龄,情况又不一样了,现在没人听老年人“掰扯”了!
那我也想拍拍老腔儿奉劝一下年轻人,不论你正经历着幸福或者煎熬、荣誉或者羞辱,都别当回事儿。那就是个梦,早晚有醒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一觉睡舒服就行了,保养好身体,等梦醒了的时候,还能出去活动活动。
我还悟明白了四个字—“人生如戏”。
这话在追悼会上体验得最深刻。以前参加追悼会,锥心刺骨地难受,痛哭失声。现在呢,感觉跟演了一场戏差不多,恍恍惚惚就过去了,唯一的区别就是没地方领劳务费。
以前听说身边有亲友去世,无比震惊、悲痛。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离去的亲友多了起来,也就逐渐淡然了。生死是自然规律,谁都有那么一天,包括我自己。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人生还是演戏,从人的内心感受来讲没什么区别。
我十几岁时的理想是跟马三立先生一样,每场演出都那么火爆,一出场就赢得满堂喝彩,我冲观众频频作揖。
二十岁时,我的目标是挣好多好多钱,天天吃卤煮火烧,隔一天来一顿爆肚,一个星期涮一次肉,一个月去一回全聚德。
三十多岁时,我希望的是出去跟哥们儿喝酒的时候,有个漂漂亮亮的女明星跟着我。我轻描淡写地向哥们儿介绍:“这是我女朋友。”女朋友羞涩地冲我一笑,“讨厌!”
四十岁,说单口相声有了点儿名气,我的想法是用这点儿知名度多赚点儿钱,哪怕过气了也有钱花。
现在五十岁了,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身体健康,多活几年。怎么突然不着边际地发了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我生病了。
医生给我开了一摞检查单,这十几天我把所有的项目全检查了一遍,也顺便把医院内部复杂的地形全摸清楚了,估计当个医导都没问题。
我把化验单交给医生—他是我的哥们儿,看了我的化验单,他跟我说:“方哥,你太不注意了!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情况吗?七八十岁的老年病的指标,都该进ICU了!”化验室的哥们儿还说,我的情况真的离死不远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感觉病房有点儿像寺庙,让我可以把尘世的欲望和烦恼都抛在脑后。眼前一片雪白,脑子里也一片空白。
外面传来凄惨的哭声,我突然冒出个念头,感觉死的人是我,哭的人是妻子……后来哭声变成了骂声,再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是一位病人喝多了,在撒酒疯。
隔壁一个怪老头儿又在骂人了。估计给他输液的不是年轻护士,而是上了岁数的护士长。怪老头儿已经病危了,连儿女都不认识了,但是他能分辨出年轻护士和岁数大点的护士。年轻护士给他输液,他就笑;岁数大的护士给他输液,他就骂街。
护士长又在数落对门病房的那个护工。护工是一位中年农村女性,照顾一个单身老头儿。两人私订了终身,女护工到了晚上总是跑到老头的病床上睡,让老头儿睡她的折叠椅。
白天老头儿的儿女还把女护工骂了一顿,说她想霸占老头儿那两室一厅的房子,“没门儿”。
医院是个神奇的地方,外面很乱,我的心却出奇地宁静。以前脑子里想的是前途、事业、金钱,现在脑子里考虑的是健康、死亡。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假想着妻子听到医生说“我已经尽力了”之后,痛哭失声的情景。
我假想着亲友们听到噩耗时惊讶的表情。
我假想着自己的追悼会—
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举行,老字号讲信誉,保证骨灰是自己的!估计进不了一号厅,我的级别不够,团里不给报销。不进也好,一号厅太大,万一去的人少,显得太冷清。
二号厅就可以,大小适中,显得温馨。二号厅有四个:梅、兰、竹、菊,就在梅厅吧,离洗手间近,亲友们上厕所方便。
致悼词的是谁呢?理想的人选应该是冯巩,他是我们单位领导,我又是他调进团的,这事儿他应该帮忙。他会不会说那句“我想死你啦”?这回是真给我想死了。
要说死了也挺好!平常我见着他得点头哈腰的,这回他得给我鞠躬。我连礼都不用还,一还礼能把他吓死!
亲友们还要转着圈瞻仰遗容。不知道给我化妆的师傅手艺如何,我不希望化得面无表情,最好有点儿笑容。活着的时候大家说我是“冷面笑匠”,死了的时候总该笑着跟大伙儿告别。
我估计没几个真哭的,好多都是来看热闹的!追悼会结束还得请大家吃饭。在中国,结婚、生孩子、办丧事……干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请客吃饭。
这帮人吃饱喝足,拿着打包的剩菜回家了。家里人还问呢—
“今天干吗去了?”
“参加追悼会去了。”
“谁去世了?”
“就那谁……哎,今天烧的是谁来着?哦,想起来啦,是方
清平。”
“方清平死啦?”
“啊!”
“……你带回什么菜啦?”
这事儿就算永远过去了。
第十天,大夫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指标大部分都恢复
了,看来就是喝酒造成的。”
突然间,出大名、挣大钱、买别墅这些事情又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
但我还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本书。
我摸着黑打开电脑,开始写。
我应该总结一下,活了大半辈子,虽然没有多大成就,但是有经验教训,给年轻人当个反面教材也好。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反面教材,生了好多不该生的气,着了好多不该着的急,也享了好多不该享的福。
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候真有这书我也看不进去。俗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了,也有一辈子糊涂的。在庐山里头就能看清楚庐山长什么样的人,那才是真诸葛亮呢!
为什么不爱笑
有人叫我“冷面笑匠”,因为我在台上不爱乐,到了台下,也跟面瘫似的。小时候我就这样,整天面无表情,心事重重的。
那时候的孩子,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但是快乐并不比现在的孩子少,不过我跟一般孩子不一样。
首先,我爸爸有海外关系。我爷爷在印尼做过生意,当然了,跟李嘉诚、霍英东没法儿比,也就属于“小商小贩”。20世纪50年代末,印尼排华,我爷爷的资产留在了国外,人逃回老家。后来赶上自然灾害,我爷爷倒是没受什么罪,直接饿死了。
我们家唯一的海外关系死在国内,却给我爸爸弄了个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就有人说你可能是外国特务,有可能在北海公园跟人接头,把咱们的图纸卷在一本画报里,交给另一个特务。
我爸爸原来在铁路部门搞技术,后来不让他搞了。干脆,修铁路去吧。一个搞技术的人,被派去干全单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他跟一般修铁路的人也不一样,随时被监视,防止他给外国人发电报。我爸爸哪儿会发电报呀?他有急事儿跟老家联系,还得去电报大楼那儿。那时候的人思维都比较跳跃,他们假想我爸爸会发电报,他的手表、皮鞋或者自行车坐垫,都有可能是发电报的工具。他们假想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爸爸会拿出皮鞋,用手指敲击着鞋跟,“嘀嘀嗒嗒”地给外国人发电报。
雪上加霜,我爸爸又犯了重婚罪。我爸爸在福建老家结过一次婚,那时候才十几岁,父母包办,没什么感情。二十岁时我爸爸跟着王震将军的铁道兵修鹰厦铁路,从老家出来之后,他就跟老家的女人彻底断了。
老家的媳妇儿不甘心,找上门来。我爸爸当初跟她结婚的时候就没领过结婚证,后来也就没办离婚证。但按当时的政策,我爸跟我妈结婚,就等于犯了重婚罪!
那年头,两人搞对象在河边亲热,让纠察队遇上了都得定为“流氓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更甭说犯重婚罪了。我爸爸差点儿因为这事被关进监狱,领导让他在工地上接受改造,工资停发,只给生活费。
单位逼着爸妈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两人谁也离不开谁,所以还同住在娘娘庙胡同那间小平房里。我的记忆里,我妈每天回家就是躺在床上骂我爸爸,扯着脖子骂,她心里委屈呀!我爸爸有海外关系,停发工资,住妈妈单位分的房子,这些她都忍了。如今她又由名正言顺的妻子变成了“第三者”,搁谁谁不生气呀?
我妈气出了心脏病,经常是骂着骂着就昏过去了。爸爸赶紧从房管局借来手推车,送她上医院。我快步跟在爸爸后面,惊恐万分,担心妈妈会出现生命危险。
第二天早上,我出家门总是低着头,因为爸妈头天晚上吵架了,我觉得丢人,觉得邻居会看不起我。后来上小学,只要学校让带户口本,我就特别紧张。因为我被判给了我妈,所以户口本里没有我爸的名字,我妈的婚姻关系一栏填的是“离异”,我怕老师跟同学看不起我。
有时候在家睡觉,我会在半夜被吵醒。睁眼一看,家里站着一屋子人,是街道居委会的大妈来查户口。爸妈已经离婚了,还住在一起算是非法同居。我爸被居委会的大妈们训斥一顿之后,深更半夜的,还得骑车带着我回单位住。因为房子是我妈妈的单位分的,所以他得离开。
我在爸爸的单位住过一阵儿。我们就住在废旧的火车车厢里,一节车厢住了十几个工人,夏天的车厢让太阳晒了一整天,晚上睡觉跟进了蒸笼一样,我热得整夜睡不着。
爸爸心疼我,晚上就带着我到野外露宿。蚊虫太多,爸爸就从野地里拔了蒿子,点燃熏蚊子。那时候爸爸没有朋友,他一肚子的委屈只能向我倾诉。我虽然岁数小,但是大人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大人的烦恼也是我的烦恼。
爸爸经常问我:“你现在被法院判给了妈妈,万一警察让你跟妈妈过,怎么办?”我小时候感觉妈妈很凶,害怕妈妈,赶紧说:“我跟警察说,就跟爸爸过。”
爸爸欣慰地笑了,我可发愁了。我担心那天真的到来,我害怕见到穿制服的警察。
白天爸爸干活,我独自在铁轨旁玩儿,会有好奇的工人过来问:“你爸爸还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没!” 我怕这人是便衣,来打探我爸爸的情况。
远远地看到我爸单位的领导过来,我会迅速地躲起来。我知道单位不让带孩子来上班,让领导看见我,爸爸又会被狠狠地骂上一顿。
整天担惊受怕,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我小时候长得脑袋大、身子小,还有点儿鸡胸脯。医生说我严重缺钙,有得软骨病的危险。
我为什么不爱笑呀?受到小时候这些经历的影响,我还笑得出来吗?
我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奶奶家度过的。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是个街坊邻居。我出生一百天就住到了她家,直到上小学才离开。
他们家三个孩子,加上她和老伴儿总共五口人,就靠老伴儿每个月的几十块钱工资生活。奶奶靠着精打细算,把家中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老两口非常和睦,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虽然穷,但是孩子们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绝不比别人家孩子差。
三个孩子慢慢长大,爷爷那点儿工资实在不够花销,奶奶就帮人带孩子贴补家用。要买菜、做饭、做家务,照顾老伴儿和三个孩子,再帮人看护孩子,奶奶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是奶奶脸上从来没有过一丝愁容,一家子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跟大多数老
百姓一样,知足常乐。
奶奶家虽然缺钱,但是她不是守财奴。我刚出生一百天被送到奶奶家的时候,说好了一个月给她十五块钱。那年代物价虽然不像现在天天涨,但是也有缓慢的浮动。我四五岁的时候,别人给人看孩子的价码已经是三十块钱一个月了,她跟我们家还是只要十五块钱。她知道我们家日子也不好过。老人还会把自己家节省出来的粮票送给我们家。她心疼我,担心我回家吃不饱。
等我上小学时家里不给奶奶钱了,她还是让我放学后到她家去做作业。赶上父母下班晚了,就让我在他们家吃饭。
后来奶奶家的三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家里的日子总算好过了。奶奶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医生说了,她的病就是常年营养不良造成的。她把肉都留给老伴儿吃了,因为奶奶总说她老伴儿得上班挣钱养活一家人。
奶奶从十几岁嫁到北下关,一直到去世,都是在那两间小屋度过的。这么多年她从来没跟邻居拌过一句嘴,街坊邻居也从没有说过她的坏话。
她走得太早了,去世那年才五十岁。
一辈子受累,却没享过一天福。
师恩若水
我的师父是李金斗先生。
传统的师徒关系,不但对徒弟的艺术负责,对徒弟为人处世、道德品质方面也做约束,连娶妻生子、买房买车、买菜做饭等大事小事,全都得手把手教。自从说相声能养活自己,我就不在家待着了,天天跟师父混。
从清末有相声这个行业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相声界拜师都有很严格的程序,要操办一回酒席,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请来引师、保师、代师到场,只有这样,别人才承认你是说相声的。
拜师的时候还要有拜师帖,请到场的同行在上面签字,作为入行的凭证。还要写保证文书,在师父家学艺三年,期间如果出现任何人身意外都跟师父没关系。出师之后,三年零一节(一节就是四个月),徒弟挣的演出费都归师父所有。
“文革”期间谁还敢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拜师这事儿就废除了。一直到20世纪90 年代,拜师之风又渐渐兴起。如今相声界人士大聚会,往往不是在演出的后台,而是在两个地方。一处是某某的追悼会,一处是某某的拜师会。
如今很多拜师之“徒”并不说相声,只是喜欢相声这个行业,喜欢老师的名气和为人,或者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觉得让师叔、师爷等前辈聚在一起是挺好玩儿的,跟武林大会一样。如今的辈分跟岁数、艺龄、业绩、资历全都没关系,就是个排序的方法。
当初我们没什么钱,师父说了:“别花钱摆酒席了,我承认你们就行了。”
初次跟师父相识,是在丁广泉老师家。丁老师要举办一个煤矿安全主题的相声专场,有师父的一个节目,他去给丁老师送本子,丁老师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师父已经听说过“小马三立”(我当年的外号)这个人,说了几句鼓励、表扬我的话。我跟付强送师父下楼,当时师父还没买汽车,骑一辆生了锈的老式自行车。后来我们才知道,那辆车是美国进口的,要是搁到现在拍卖,能卖出一辆小汽车的价钱。
后来这个相声专场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录像,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师父在后面演。他站在台边看了我们的表演,我们请他提意见,师父很热情,说:“有时间到家里去,慢慢给你们说。”
过了几个月,我跟付强要参加一个区办的文艺会演,到师父家请他辅导。那时候师父虽已成名,但尚未大火,一家三口还住在五十平方米的单元楼里。客厅是个狭小的长条形,而且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灯。
进屋换拖鞋时,我跟付强都露怯了。我们那时候靠演出挣钱挺难,不跟现在的孩子似的,会狮子大张口跟家里要钱花,所以我们那会儿的生活有点儿窘迫。我们俩的袜子,全都露了肉。师父打开抽屉,取出两双袜子,让我们俩换上。当时虽说有点儿尴尬,但是又感觉很亲切,师父这个举动一下拉近了师徒之间的距离。
中午到饭点,师父请我们吃的麻酱面。师父家的麻酱面很讲究,花生酱跟芝麻酱以3∶7的比例调配,要搅拌很久,调得都出油儿了,用筷子挑起一点儿来,呈线状流下。吃的时候再配上花椒油、醋、黄瓜丝儿,感觉奇香无比。
那时候我没单位,没本事,没钱,属于标准的“三无”人员。虽想拜师,成为相声的正宗门里人,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
后来,我跟搭档付强当兵到了部队,四年换了三个单位,辗转奔波,跟师父的联系就更少了。
但是师父并没有忘记我们,在我快要复员的时候,师父给我打来电话,说南京前线歌舞团需要一个相声演员,可以介绍我过去。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能提干,还能从文艺兵转为职业相声演员。
我到前线歌舞团考试,很顺利地被录取了。由业余的转为专业的,我终于有勇气提出拜师的请求了。感觉自己跟师父说分量不够,我跟付强托王丹蕾老师介绍,师父听王老师说完,满口答应。
王丹蕾老师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干部,话剧艺术家杜鹏先生的公子。可惜后来英年早逝,在五十岁出头的时候,突发急病去世了。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会上,我给他磕了四个头。因为他是我拜师的介绍人,对我有恩,我必须大礼参拜。
我跟付强作为徒弟到了师父家,跟师父提出了摆酒席拜师的事儿,师父当即拒绝。他说:“你们没钱,花那冤枉钱干吗呀?”
我拜师没给师父买任何礼物,师父还给我二百元钱,让我到南京之后,用这钱买礼物探访一下在当地的相声前辈,也算是到当地的相声界挂个号。
就这样,我拜师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二百块。
那年我二十三岁。
在南京待了半年我就离开了。一是水土不服,二是付强一个人在北京没有搭档,我又回到了北京,再一次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付强得着个信儿,燕山石化有个文工团缺说相声的。他把这事儿跟师父一说,师父马上花钱雇了一辆专车,带着我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
燕山石化。因为我们是师徒关系了,我们的事儿就是他老人家的事儿。领导一瞧师父去了,看着名人的面子,马上答应录用我们俩。
学艺
师父的名气大,艺术造诣太深,我们见了师父就紧张。师父让我跟付强表演一段相声,我们俩说得磕磕绊绊,紧张得满头是汗。
师父自然不满,一顿训斥。然后他亲自示范,让我们再来一遍。这下我俩更紧张了,说得还不如上一遍。师父更加生气,又一顿数落。
我把师父教的东西都记在心里了。回到家里放松下来,回忆师父示范的过程,一遍一遍地练动作、练表情。
相声这种东西不但要靠学,更需要靠熏陶。那几年我们跟师父朝夕相处,他四处演出,我们就在旁边观摩。跟着他排练、对词儿,细心揣摩,久而久之也潜移默化,受益匪浅。
随着师父的名气越来越大,演出也越来越多,他已经没有时间教我们俩了。他深感我们的基本功底太差,就介绍我们到他的师父、我们的师爷赵振铎先生那儿去学习。后来赵先生去世,师父又把我们介绍到他的师叔丁玉鹏先生那里学习传统相声。
丁玉鹏先生跟师父本没有太多的来往,但师父隔三岔五地就去看望丁先生。丁先生去世,师父给了一笔钱买墓地,还从头到尾帮着张罗后事。
我那时候一直给付强捧哏,相声说得不怎么样,还自以为说得不错,师父恨铁不成钢。每次到师父家,我都要让师父数落一遍。为了避免挨训,我去师父家的次数渐渐减少了。有了段子也不让师
父排练了,自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三十岁开始,做了十年职业编剧,跟师父学说相声的时间就更少了。
四十岁的时候,我重返舞台说单口相声,深感自己传统相声的基本功太浅。这时候我才后悔起来,年轻的时候太贪玩儿了,没把师父的一身本事学过来。随着社会经验的增长,我终于明白,师父当年对我们的批评,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如果当年听师父的话,现在我的表演还能更上一个层次。
亡羊补牢,我又开始到师父家跟师父学段子了。师父为了见效快,还亲自给我捧哏,合作表演。这也是他从王长友老先生那儿学来的经验,当初他学艺,就是他的师爷亲自为他捧哏。
有一次在师父家喝酒,师父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你现在知道用功了?晚啦!一定要珍惜跟我合作的机会,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说不定哪天,就上不了台喽。”
学礼
我独自在外面闯荡了几年,才正式拜师。师父教育我:“要想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必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当时不理解师父的话,后来跟在师父身边观察,发现自己确实得学。
我在外面自由散漫惯了,说话办事都毛毛躁躁的。师父说了,处事要稳重,遇见什么着急的事儿都别慌。跟人交往的时候,说话办事要慢条斯理,条理清楚,轻声细语,注意礼貌。我父母都说,跟着师父一段时间之后,我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懂事儿了。
师父对待艺术界的前辈们非常敬重,也很大方。隔三岔五地请老先生们吃饭,陪他们聊聊天。如果老先生家里有什么事儿,师父出钱出力,永远是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外地的相声演员来北京,师父更是尽地主之谊,请客吃饭,安排住宿。
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照着师父的样子学。有付出就有回报,许是因为我做得比较到位,所以老演员也愿意对我的节目进行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我们热情招待。人心换人心,外地有什么演出,人家也总是想着我,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
师父的社交面非常广,各行各业都有朋友。经常应付酒局,还时不时地花钱请人吃饭。过去我不理解,认为这样很累,浪费了精力和财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我才发现,师父积累的这些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晚辈都跟着受益。
比如说北京的各大饭店,赶上生意火爆的时候,如果你要请客吃饭,很可能订不到包房。但是很多饭店都有师父的朋友,我可以去找他们。不但有包房,价钱打折,而且服务到位,在客人面前很有面子。
我现在跟师父住一个小区。当初师父先买的房,他告诉我这个小区环境不错,我想买可惜已经没现房了。又是师父的朋友帮忙,给我找了一套房。三年的时间,我这套房子的价钱已经翻了近一倍了。
后来就连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买墓地,都是托师父的关系才办成。
我没办过婚礼,觉得太麻烦。但是我曾经举办过一次订婚宴,是师父给掏的钱。师父把我们当作儿女看待,认为我们的终身大事理当由他操办。
师父还准备了红包,师娘准备了首饰和衣服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儿媳妇”,以表达作为师父、师娘的那份心意。我却不争气,没过多久就跟对方分了手。
我母亲曾几次住院,师父每次都亲自到病房探望,还带着钱来。
母亲的葬礼,师父从早晨六点多帮着忙活,一直到取出骨灰,他才离去。他总是不放心我们办事儿,非得亲自张罗。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到灾区采访。赶上一次6.4级的余震,刚从危险地带撤出来,我的手机就响了,是师父的声音:“电视里说你们那儿震了,没事儿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师父对徒弟也同样担着心。
徒弟出名了,师父脸上有光,但是徒弟惹了祸,师父也得帮着了事儿。有一次我在酒桌上跟一位相声同行顶撞起来,师父听说了这件事,赶紧拨通那位前辈的电话,向人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