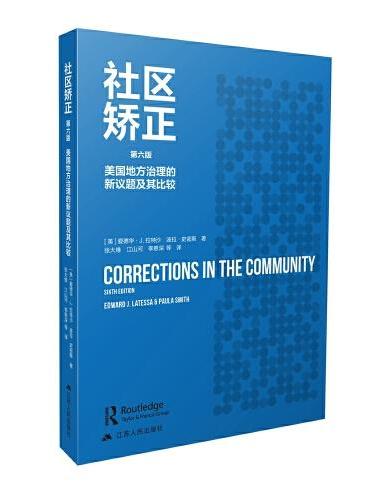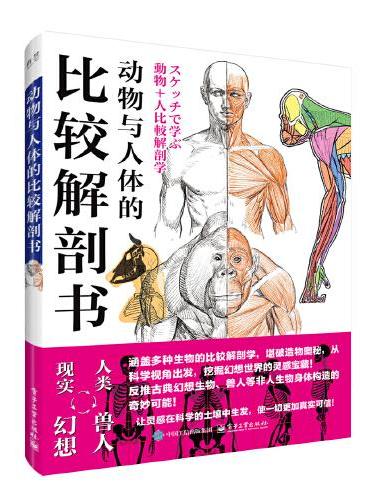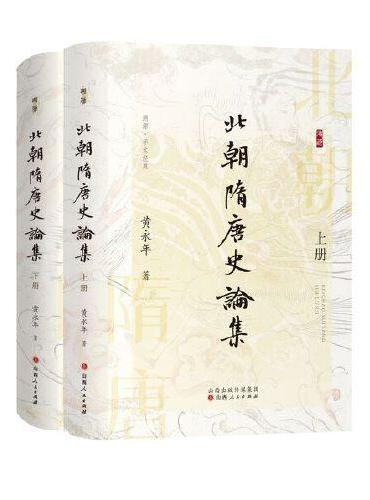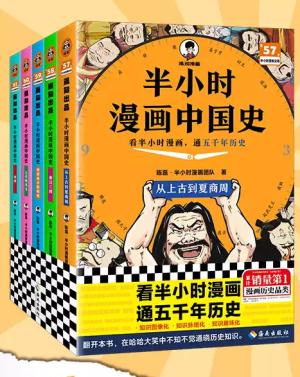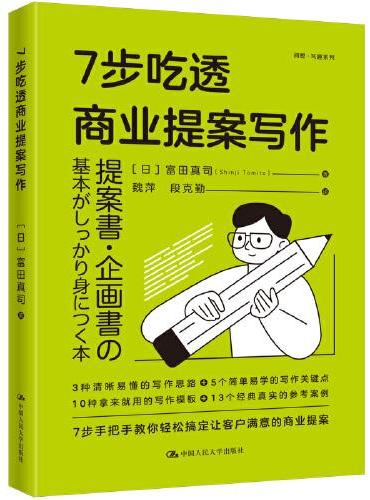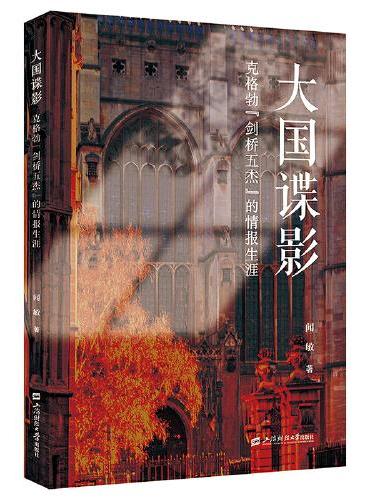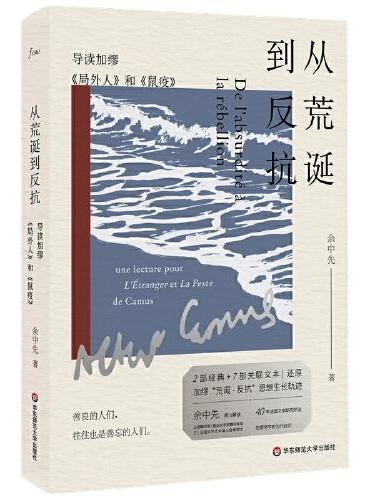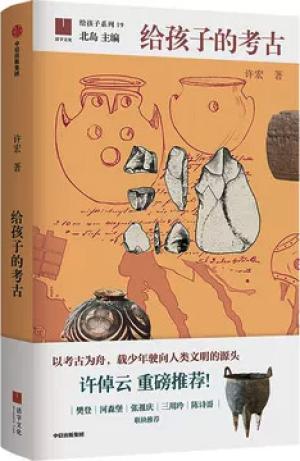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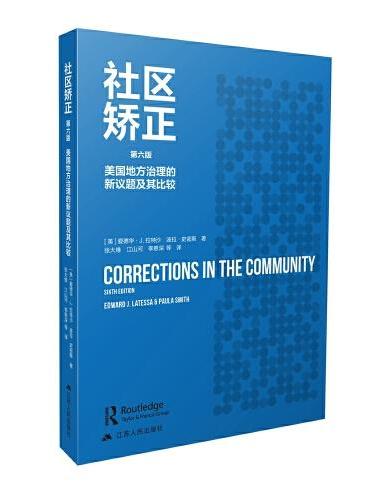
《
社区矫正(第六版):美国地方治理的新议题及其比较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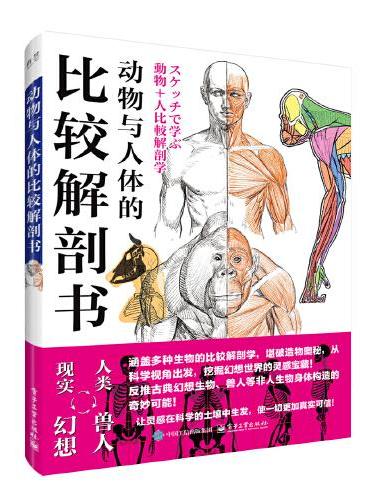
《
动物与人体的比较解剖书
》
售價:HK$
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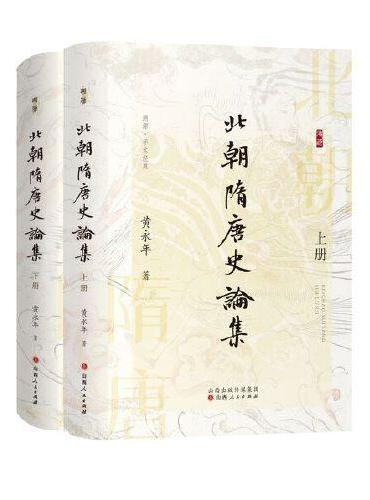
《
北朝隋唐史论集
》
售價:HK$
27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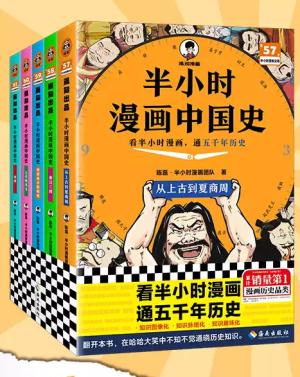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HK$
2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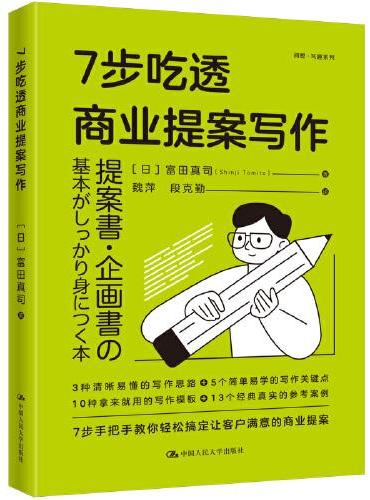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HK$
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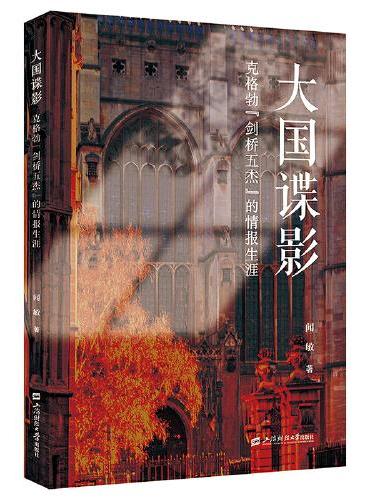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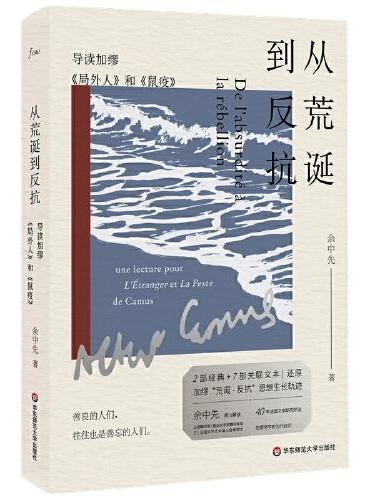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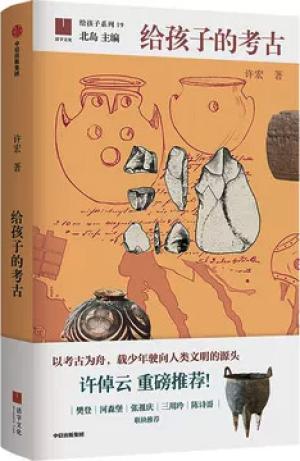
《
给孩子的考古
》
售價:HK$
63.8
|
| 編輯推薦: |
|
我常常和读者开玩笑:如果说托尔斯泰无人不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无人不服的话,契诃夫则是无人不爱。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契诃夫以短篇小说为业,内容也往往带些诙谐幽默,更主要的是,契诃夫始终坚持为“人”写作,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人,他曾经是,现在依旧是,将来恐怕也依然会是最有人文关怀的作家,在他的笔下,人首先是人,然后才具有其他身份。而体现这一特点最突出的,恰恰不是契诃夫的小说作品,而是他的非虚构作品《萨哈林旅行记》。作为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文学艺术大师,《萨哈林旅行记》中尽管充满枯燥的数据,却依然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出自大师之手,但是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并不在于文本中数据的“实事求是”和文字的文学性,而是字里行间闪耀的“人类的良心”。
|
| 內容簡介: |
|
《萨哈林旅行记》是契诃夫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却堪称契诃夫最重要也是最感人的作品,因为这是契诃夫一生文学实践乃至世界观的宣言书。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契诃夫进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阶段,然而作家本人却深陷精神危机同时身体状况堪忧。在第二次咳血之后,契诃夫不顾沉疴未愈,决心冲破作家的“枷锁”,进行一次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出走”。他以医生身份深入不毛之地萨哈林进行考察,将此间的亲身见闻创作为《萨哈林旅行记》。从表面上看,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地方志,内容包括随笔、人物特写、人口普查、气候观测、监狱日常情况记录等,但是在看似枯燥的记录中,蕴藏着契诃夫的人道主义关怀,他用现实的正反两面向人们揭示着人何以为人,反抗着一切对人的不公和压迫。诚如契诃夫本人所言,在《萨哈林旅行记》之后,他的一切都“萨哈林化”了。
|
| 關於作者: |
|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在俄国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短篇小说为业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简练的文笔革新了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后世许多世界闻名的作家都自称为“契诃夫的信徒”并引以为荣。
|
| 目錄:
|
【目录】:
第一章从尼古拉耶夫斯克至鞑靼海峡沿岸 001
第二章地理概况:码头、宴会和灯会 016
第三章人口普查:我的提问与得到的回答 031
第四章河谷之地:萨哈林的巴黎 043
第五章监狱、牢房和作坊 055
第六章苦役犯伊戈尔的故事 069
第七章灯塔、村屯和气象站 076
第八章河谷沿岸各屯住房、隧道、监狱和戴镣囚犯 093
第九章特姆河漫游 115
第十章小特姆屯 132
第十一章拟建中的行政区基本概况 142
第十二章南部、西海岸、洋流和气候 159
第十三章哨所、农场、村屯和大海 175
第十四章移民、日本人和日本领事馆 194
第十五章流放犯、强制移民、农民和乡间政权情况 212
第十六章流放犯居民的性别:女性流放犯与自由民妇女 231
第十七章居民的家庭状况:年龄、婚姻和出生率 247
第十八章流放犯的劳动技能:务农、狩猎和捕鱼 261
第十九章流放犯的生活概况:饮食、着装、礼拜与识字 277
第二十章自由民种类:士兵、屯监和知识阶层 295
第二十一章流放犯在当地的犯罪、审判和刑罚 311
第二十二章萨哈林逃犯:重新犯罪的原因、出身和类别 331
第二十三章流放犯居民的疾病与死亡情况:医疗与医院 349
|
| 內容試閱:
|
译序
契诃夫与《萨哈林旅行记》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一位跨越了文化界限的作家。两个世纪以来,在很多国家的文学史中,著名的文学家经常被冠以“某国的契诃夫”称号。这充分说明了,契诃夫在世界上广受喜爱的程度。除了具有持久声誉的大部分作品之外,契诃夫作为创作者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他的作者形象,也就是他内心千军万马而落笔不动声色的别样面目;至于作品的构思,契诃夫承担了思想狂野而落笔轻盈的角色;在文本处理上,契诃夫的素材普遍而轻飘却主题千钧。在契诃夫的生活年谱中,他承担的社会义务有悬壶济世的医生、在乡村中奔走的人口普查员、积极的救灾赈济者、俄国科学院院士、自治学校的资助人、救助贫困儿童的热心募捐者、为结核病人建疗养院的集资人、为抗议不公而毅然声明放弃名誉院士称号的斗士……而在这位伟大作家的写作史中,有一部作品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位置,这就是完成于1893年的《萨哈林旅行记》。这是契诃夫一生世界观和文学实践的宣言书,诚如其本人所言,他的一切“都萨哈林化”了。因而,要了解契诃夫的整体创作主题和艺术手法,《萨哈林旅行记》是一个可供估量的维度,它不仅显示出文学创作史方面承前启后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更是契诃夫具有世界意义的起点和观照。
《萨哈林旅行记》于1893至1894年间在《俄罗斯思想》月刊陆续发表,1895年单行本出版。尽管它的体裁被圈定在“旅行摘记”上,但是,这本书所具有的严谨性和多方面的精细研究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尤其是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哲学思考,将契诃夫的写作主题、创作的性质和文学史意义凸显出来,形成了广阔的文学阐释空间;尽管契诃夫本人称这部书是他的“散文衣柜里的一件粗硬的囚衣”,但是,毫无疑问,《萨哈林旅行记》是作家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全面展现,具有19世纪现实主义潜在的惊人新意。
一、 《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的创作体裁
《萨哈林旅行记》属于俄罗斯文学中的“病室文学传统”。在19世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在20世纪,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这些作品都有强烈的作者形象,即作者为亲历者或者是记录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监狱、苦役地、劳改营等拘禁空间是主要的写作地点和历史感受来源,因而其真实性从未受到过怀疑;每一位写作者,都不是单一的自然主义描绘者,而是以自己的真实感受来体悟这个叙事空间多侧面的现实主义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发表于1860年到1862年之间,在两部二十一章的篇幅中,作家对沙俄时代西伯利亚苦役犯监狱进行了冷静、客观的描述,对社会制度、人性、犯罪心理、个人和社会的终极救赎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思考;对监禁制度和强制性劳动的质疑和批判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人的灵魂这一终极关怀之基本底色。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评论说:“《死屋手记》是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由此开始的病室文学,不断在各个方面强化“纪实”文体的内涵与外延,每一部作品都呈现出“灰色史诗”所特有的体裁特征,每一位作家都是那样的善于隐瞒自己的主观印象,而完全倾向于客观与理性,却绝不会将叙事引向神秘或者超自然的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在面对特定的人群即囚犯的时候,洞察的是周围的一切没有什么是虚构的这一现实主义要义。契诃夫也一样,他作为叙事者,而不是偊偊独行的先知与高高在上的权威,也不是一个大声疾呼的揭发者,他和读者的关系在于,他不向读者隐瞒自己的怀疑和困惑,他需要的是“弄清楚”和“求道问世解惑”。因此,谈及《死屋手记》《萨哈林旅行记》《古拉格群岛》和《科雷马故事》,是无法将它们从体裁上视为简单的“旅行记”的。尽管契诃夫本人并不曾作为被囚禁的一员居于其间,但是,他绝不是为了做一次“地理上的旅行”而出发的,他在19世纪80年代所感受到的“精神上的苦闷”是萨哈林之行的起点。他自己确定了这部书的体裁是“考察报告”,应该是文艺性和学术性兼而有之;无独有偶,索尔仁尼琴在确定自己的《古拉格群岛》的体裁时,认定小说的全称是《古拉格群岛,1918—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显然,两个世纪以来,伟大的作家们探索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这是一种特定艺术作品的种类和样式,诸如《死屋手记》《萨哈林旅行记》《古拉格群岛》和《科雷马故事》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已经是一种具有极其稳定的艺术结构的文体了,它不仅有整合各种一般体裁的能力,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混合了各种文体的体裁样式。“病室文学体”包括人物特写、环境描写随笔、大量资料数据,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将自传、他传、考证、资料融于一体,犯人的证词、回忆录、历史文献穿插其间,监狱、劳改营、流放地的全貌跃然纸上。
因此,《萨哈林旅行记》是以旅行记的外壳,写了一份文学化的起诉书。
二、没有禁锢:契诃夫的创作题材
站在《萨哈林旅行记》的远处来回望契诃夫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写作题材,特别令人深思。在涉猎戏剧剧本和短篇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契诃夫以一种罕见的“克制”来整理自己的素材。因为如果没有“克制”,这些题材无一例外的别名都是“沉沦”和“毁灭”,而这毁灭的深度和广度,只消看契诃夫的小说名称就一目了然了——1884年,作者从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前在地方自治医院实习,1883—1885年,发表的小说有一百五十九篇,其中包括《现代祷告辞》《问题和答案》《萝卜》《冤家路窄》《冠军路》《盗贼》《沙拉酱》《新病和老处方》《补习教师》《打猎》《有自尊心的人》《荒唐的想法》《人间仙境》《变色龙》《越描越黑》《在墓园》《祸从口出》《野鹅的闲谈》《面具》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日常所见的生活事件和生活现象,所有生活场景中的各色人等都进入了契诃夫的广阔视野之中;不惟如此,各行各业的人的心理流程也在题材之中涌动。有的小说直接冠以主观词汇,例如《可恶的孩子》《混乱的广告》《文官考试》《傻瓜》等等。但,对一切必须面对的现象与人,契诃夫的态度是《宽恕》:在宽恕日这一天,遵循基督教的习惯和出自我的慈悲心肠,我宽恕了一切……选材广泛,却在概括、集中、提炼上面采取无限“克制”的剪裁方式,这是契诃夫写作之初就已经确立的原则。
契诃夫早期创作的底色是“灰色的世界”和“忧郁的人”,这一底色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了高潮。除了小说,作家写了一系列的“小品文”“戏剧小品”以及“须知”类的各色故事,《丈夫须知》的标题还煞有介事地标注上“科学论文”。《噩梦》和《白嘴鸦》就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沉沦”已经是不少小说的主题,包括相关知识阶层的各类人物:律师、作家、教师、警察、公务员、农业专家……“我”以第一人称进入了小说,成为人物之一,我,“不愚蠢,也得不到安慰”。显然,看,观察,思考……都已经达到了极限,追问的意愿浮升至作家思维的高度,这已经不是“生活的烦恼”,而是需要“详解”的生活。
19世纪90年代前创作的两部剧本《无父之人》和《伊万诺夫》选择了“多余的渣男”来演绎对生活的绝望。《无父之人》中的普拉东诺夫说:“哈姆雷特害怕做梦,我害怕生活。”而伊万诺夫则觉得全世界都在嘲笑他,“我耻笑我自己,觉得就是那些鸟,那些树,也都在耻笑我啊”……戏剧中清晰地出现了死亡的意向,出现了生和死的纠缠。生存还是死亡,俄国的哈姆雷特既想自杀,又渴望生活,契诃夫在选择写作素材的时候,对玩世不恭者、心理变态者、不安分的人、多余的人以及痛苦的人,表达了一种完全的承担:写作,这是一种十字架,他强烈的使命感出现了。对于卑微的芸芸众生,他还没有完全付出自己应尽的同情;1888年,在发现自己第二次咳血之后,契诃夫对自己的精神危机和身体预后进行了评估,决定到苦寒之地、人性边缘的萨哈林岛上进行考察,实际上,是期望对自己的“苦闷”进行一场救赎。
萨哈林岛之行是契诃夫写作题材的一次升华。19世纪80年代,俄国社会特别重视道德问题,契诃夫甚至对托尔斯泰的道德探索充满兴趣,然而,在社会的病态已经成为急迫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的答案却在社会生活的法定准则之外。在暴力镇压的司法程序之内,苦役地中身体的囚禁与物质条件的苛刻,还有自由的禁锢和希望的缺失,正是契诃夫关注的俄国生活的悲剧现实的集中体现和社会病理学根源所在,他不愿意在哲学的抽象意义上来探索这个问题,而是想在书中以文学的形式将其形象地再现出来。可以肯定,这是契诃夫在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岔路口的一次转身,显然,这个华丽的转身是更具陀思妥耶夫斯基色彩的,是追随《死屋手记》而来的,只不过,他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得更远,越过了西伯利亚,来到了萨哈林,而且,比起被迫至此的前辈,契诃夫的自觉实践是对道德说教和道德沉沦并粗野化的一种离弃。因此,《萨哈林旅行记》本身是作家写作题材种类的一次塑形和汇总,在总共二十三章中,有随笔,人物特写,人口普查数据汇总,监狱日常生活实录,殖民区的生产生活,苦役犯的待遇,地理与气候、气象条件阐述,殖民地人员分类:流放犯、强制移民、农民,乡间政权情况,流放犯居民的性别研究: 女性流放犯与自由民妇女,居民的家庭状况: 年龄、婚姻、出生率,流放犯的劳动技能概述:务农、狩猎、捕鱼等,流放犯的生活概况:饮食、着装、礼拜与识字,自由民种类:士兵、屯监、知识阶层,流放犯在当地的犯罪、审判、刑罚,萨哈林的逃犯的出身、重新犯罪的原因和类别等,流放犯居民的疾病与死亡情况、医疗与医院的基本情况,监狱、殖民地和司法机构的管理等情况,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在这里,灰色的世界已经是暗无天日的世界,忧郁的人已经是绝望的人群了。题材内容的扩展已经是契诃夫式的全景化空间场景了。
《萨哈林旅行记》之后,即19世纪90年代以后,契诃夫的写作题材没有了任何的禁忌。选取素材的视野进一步扩大,《无名氏的故事》《第六病室》《决斗》《枯燥无味的故事》《脖子上的安娜》《女人王国》《凶杀》《三年》……评论家别尔德尼科夫认为,契诃夫是在处理政治题材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社会伦理机制,这不是新的内容,而是旧题材。是的,民意党人、自由主义集团的代言人、地主、贵族、医生等知识分子在资本实力和私有制关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之下,成为社会不公的新配合者和牺牲者。“拯救心灵生活”所要求的高度使陷入混沌之中的人,哪怕是小市民,都有了对生活、环境、制度不合理的痛苦控诉。“为什么人世间的事情安排得这么古怪,人生仅只有一次,却在一无好处中度过,这是为什么?”(《罗德希尔德的小提琴》)
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上处理所有的篇目时,并没有隐藏他作为全能叙述者的立场。因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即艺术地处理叙事者和叙述对象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方面,一切事件与现象都因为社会基础的扭曲和人的心灵不完善而似是而非,另一方面,契诃夫强烈地流露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的抵抗和不妥协,对,正是:作家的职责是摧毁同时代人的幻想,全力筑就真理的长城。无论这个真理是在现实的废墟(监狱、苦役地)上,还是在精神的废墟(精神病院)里。同样,在戏剧创作中,契诃夫贯彻了这个由《萨哈林旅行记》发散的思想,所有的无能为力,所有的怀疑,所有的逃避,所有的幻想、自我陶醉以及伪善和欺骗,都需要用实践性的认识来摹写,把生活的潜流和“变革的引信”展示出来,萨哈林之行的意义即在于此。与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相比,不是“监狱”和“苦役”亲历者的契诃夫的苦心孤诣更值得记取。
三、 不是淡淡的忧伤:契诃夫的创作主题
《萨哈林旅行记》是一场精神跋涉,从文学上确立同情心就是在精神上服苦役。在评判一个微缩社会和它的精神景观的时候,严峻深沉的话语用最为隐忍的方式来表达,这导致了轻浮的评论者对契诃夫创作主题的误解,即作家的小说和戏剧表达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呜呼!选择了特定空间表达的作者,恰恰是重视空间题材的隐喻性内涵,全篇笼罩着全方位、无死角的反思话语,把以病态社会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对人、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思想的禁锢,对人性的极端压抑,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践踏以及对自由和真理的蔑视冷静地表达出来,这是契诃夫最为清醒的主题意识。
契诃夫小说的开篇永远是不动声色的,他的批判与控诉是社会心理根源的集中表达,因此,即使是在旅途中,对于外在环境乃至于地理环境的认识也是冷静的,“亚洲大陆在这里已经到了尽头,而且可以说,若是没有萨哈林岛横亘在对面,阿穆尔河就直接由此注入到太平洋里了。眼前就是浩荡宽阔的河口湾,前方就是隐约可见的黑色带状目的地——苦役岛;左边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在一片雾霭中隐匿到不可思议的北方。就好像那里才是世界的尽头,再往前就无处可去了。心底里涌上一种悱恻莫名的感觉,就像是古代的希腊史诗中的俄狄浦斯,在陌生的海域漂泊不定,心里惶惶不安地预感到可能会与各种妖魔鬼怪遭遇的场景”。一切固有秩序的断裂都与非正常的系统运行联结起来,殖民地政策和苦役地司法像是一个黑洞,吞噬着人对于世界的正常认知。庞大的终生流放苦役犯群体的存在,使自由与价值判断失去了依凭,“皮鞭”主宰下的腐败政治和司法,黑暗人性盛行的监狱,村屯殖民过程中官僚体系的颟顸无知,都在每一篇章的“简约”叙述中流淌出来。契诃夫的“游踪”只有一个粗略的线条,所有的景观和情感中浸透的,无不是悲惨人生的摹写。不仅是犯人,还包括了各行各业服务于此的人们,例如,“水兵送我回舢板船,他仿佛猜到我要问他什么,叹了一口气,说道:‘要是让自己选的话,谁会乐意到这个鬼地方来啊!’”以及,“船上的机械师在发现我对岸上的景象忧心忡忡的时候,对我说:‘等您看到杜埃就知道了!那里呢,海岸陡峭难行,峡谷昏暗,煤层都黑黑地裸露着……那才是阴森森的海岸!我们这艘“贝加尔湖”号曾经朝杜埃运送苦役犯,每次都是二百至三百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啊,看到海岸就大声地哭嚎起来了。’”因此,“所有人都想逃离这个地方,”总督说,“无论是苦役犯、移民还是官员无一例外。我暂时还不想逃离,但工作千头万绪,我已经殚精竭虑,疲倦不已了”。契诃夫就是这样,像一架精密的扫描仪,一只睁大了的、万分警觉的眼睛,扫过了历史时间(1890)的横断面,在萨哈林岛的各个空间驻足,解构了充满暴力的历史的每一方面。《第六病室》《恐惧》和《在流放地》的写作时间距离《萨哈林旅行记》都很近,这是契诃夫意犹未尽的诗学在主题方面的延伸,就像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症楼》,就像沙拉莫夫的《红十字》《生意人》《一手好字》……均为“病室”的异曲同工之作。
《萨哈林旅行记》这部文本充分体现了在一切荒谬之中的精神悲剧和信仰失落,而作者偏偏是在这里注入了最为深切的人道主义溪流。在人口普查中,在入户走访中,在各个村屯的移民情况调查中,在对监狱和矿井事无巨细的讲述中,契诃夫看到了每一个人群的苦厄,每一个生命的凋零。渔业的粗放、农业的凋敝、气候的恶劣,使苦役地的人们既无法安身立命,也没有任何的人身保障,只能随波逐流,任凭人命被草菅。契诃夫写道:“如果生活不是自然地、按照应有的程序流淌,而是靠人为的安排,不取决于自然状况和经济条件,而是依赖个别人物的理论和独断专行,那么,类似的偶然性就必然决定着生活的性质,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人为的粗糙生活的法律法条。”苦役地的很多人物的人生境遇实属荒唐,比如,第六章中的伊戈尔的遭遇,他明明没有杀人,但是,“但是法官不相信呐,他说:‘你们全都这样说,一会赌咒发誓,一会谎话连篇。’就这么着了,把我们判了,扔进了高墙大狱”。契诃夫在文本中为妇女和儿童设立了专章,详细描述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写得简约,点到为止,很多地方都用数字说明;字里行间,可信度极高,对读者来说,振聋发聩的效果胜过了长篇大论,比起引人入胜的情节,戏剧性的张力一点也不缺少。
四、 无望与绝望:契诃夫的创作意义
在很多作家的传记中,“出走(уход)”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精神标识。契诃夫也毫不例外。如何突破写作的瓶颈、局限与困境,如何诊断历史文化与时代要求,在深刻领悟了“事件的无解性”之后,又当如何自处呢?
《萨哈林旅行记》是契诃夫的一次“精神出走”,是他作为写作者调整人与生活的关系的一份精神考量系统的坐标。在讲故事获得成功之后,一个作家需要做的无非就是“正眼看人”,而人的意识与想象,人的历史与未来,人的局限与困境,究竟在哪一个层面上,值得一个拥有盛名的作家的良心检视呢?在最底层。契诃夫的全部创作都在阐释人与生活的冲突,而不是人与人的冲突,这正是他艺术思维中最为重要的理念,这也是作家创作《萨哈林旅行记》的意义。从这个入口处,可以见到契诃夫构建的“文学人类学”的全部风景和文学史认识价值。苦役地的囚犯作为在可见法条禁锢下生活的人群,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附属特征昭然若揭(契诃夫就像写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一样引用数据详细地写出来),但是,伴之而来的是随遇而安、猥琐自私、逃避现实的生活中的懦弱者。浸透在苦役地的希望、彷徨、失望、无望、绝望也是过着庸常生活的“知识阶层”的精神写照。经过《萨哈林旅行记》的洗礼,经过苦役地的犯人们对“永远回不到故乡”的真实描述,契诃夫的“三姊妹”心心念念回不去的“莫斯科”,契诃夫获得了完整的精神世界的图谱,在随后的写作生涯中,镶嵌上去的还有《海鸥》《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樱桃园》……在这些作品中,生活的循环往复“像莠草一样窒息着我们”,而我们只是渴望生活的人群,我们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在的“苦役地”不甚了了,以至于契诃夫认为,那些苦役地非常隐性、非常狭小,大不了是一个家庭、一段关系、一个不起眼的中学、一个模糊的外省小城等等,但是,“心之为役”,百般无解。无数的芸芸众生延续的只是“以前的生活秩序”,“仿佛再过一会,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似的”,契诃夫平淡无奇地处理小说中和戏剧中的一切冲突,意在说明,精神的恐惧完全是以一种生活的本来面目出现的,不狰狞,无恐惧,毫无逃避和变革的可能性。
在《萨哈林旅行记》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片段,省长对契诃夫说:“我允许您自由出入您想去的任何地方。”科尔夫男爵说:“我们这里没什么可隐瞒的。您可以在这里好好观察,会发给您出入所有监狱和移民村屯的通行证,您可以使用对您的工作来说有用的所有材料和文件,一句话,所有地方的大门都会向您敞开。只有一件事我不能允许您做:就是无论如何不许与政治犯有任何的交往,因为我没有任何权利允许您这样做。”(第二章)这个片段是典型的契诃夫式的“境遇”,即,虽然有一个广阔的社会图景的存在,有轰轰烈烈的殖民运动,有被钉上连车镣铐的政治犯,但,表面的野蛮、暴力、麻木、落后、极端之外,微观的人性和生活的激情都在不断地被毁灭,这才是生活在别处,这才是形而上学的关于人之为人的整体的思考。契诃夫“在杜埃监狱,目睹了鞭刑实施的整个过程”(第二十一章),他详细写出了整个场景,特别是所有人的不同感受,包括作家、医生、典狱长、录事、“强烈要求旁观”的军医助理、负责实施鞭刑的刽子手、受刑的犯人普罗霍洛夫(契诃夫只记录了他的名字)。在作者对血肉横飞、犯人悲惨哀嚎忍无可忍而退出行刑处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离开这里,走到外面去了。外面的街道上,一片寂静,但我觉得,看守房里那刺耳的声音能够传遍整个杜埃。一个穿着便装的苦役犯,正从看守房旁边路过,他朝房子那里瞥了一眼,他的脸上,甚至走路的姿势里都流露了内心里的恐惧。我又走进看守房,看守还在数呢,我又退出来了。看守仍然在数鞭数”。而军医助理则说:“我太愿意看行刑的场面了!”他兴高采烈地说道,他非常满意自己把这个恶心的场景看了一个够,“太喜欢看啦!这些坏蛋!这些该死的家伙……把他们都绞死才好呢!”
契诃夫总结说:“肉体惩罚不仅使犯人变得冷酷和残暴,而且也让在场观看的人变得野蛮和残忍。甚至连受过教育的人也不例外。至少我没有看出来,受过大学教育的官员们对待行刑场面与这个军医助理、士官学校或者神学校的毕业生有什么不同。有些人已经如此适应用树条子或者皮鞭子抽打犯人这种事了,他们变得相当野蛮,已经开始从这种对犯人的肉体处罚中找到乐趣了。”因此,从冷静的笔触和力求客观的态度来看,契诃夫的“怎么办”是文学性的,以人学为中心的,这也是契诃夫文学文本的现代性价值,《萨哈林旅行记》的美学超越性即在于此。在契诃夫与《死屋手记》之后、寻求宗教解释善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宣称“内心寻求冷漠胜利”的索尔仁尼琴互为确证。据说,托尔斯泰创作《复活》期间,他的家庭每晚朗读的作品正是《萨哈林旅行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