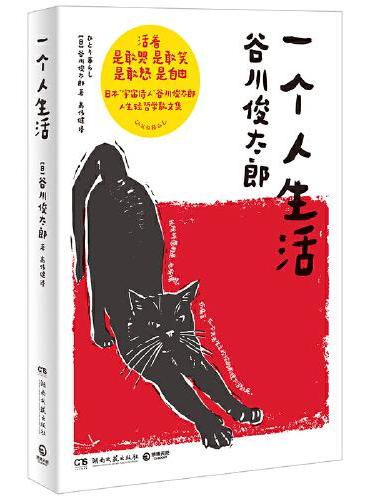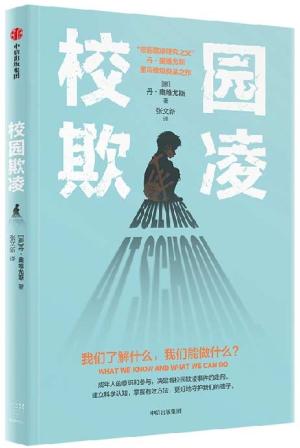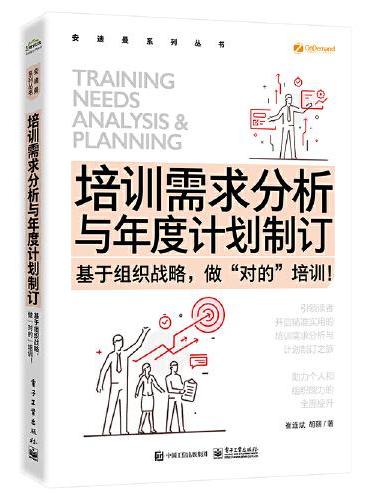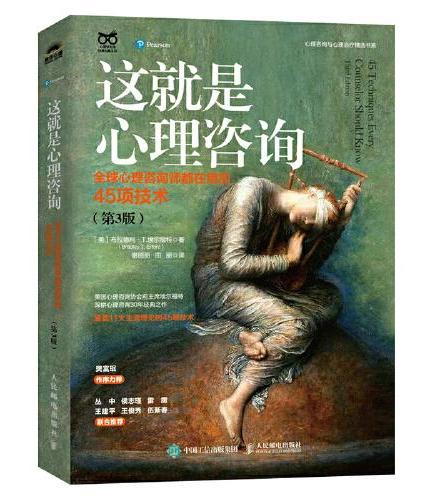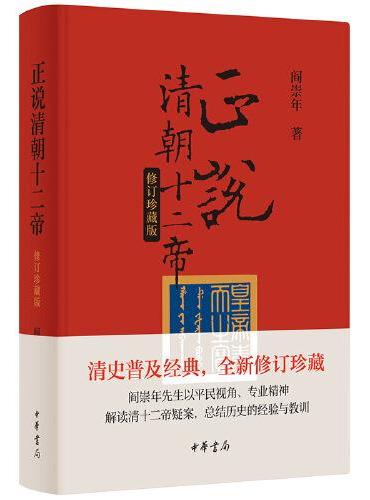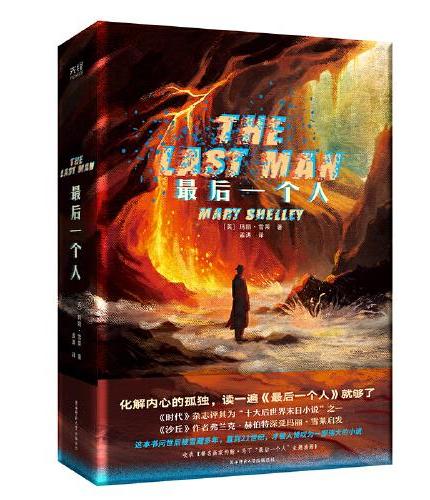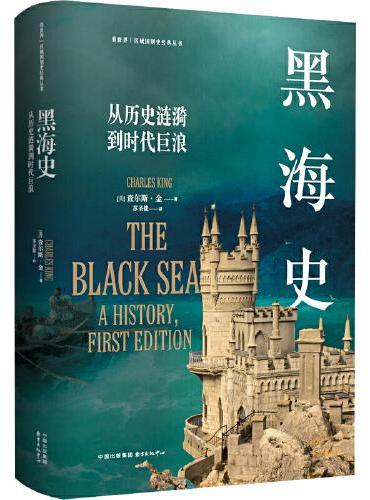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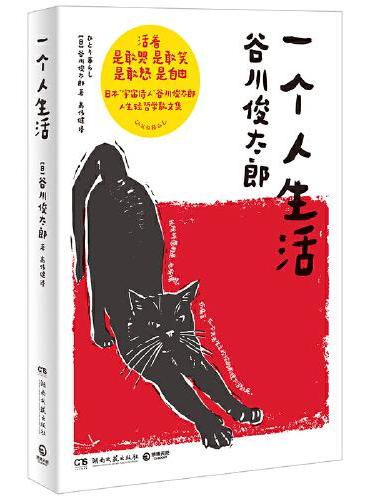
《
一个人生活(2024版,日本“宇宙诗人”谷川俊太郎人生轻哲学散文集)
》
售價:HK$
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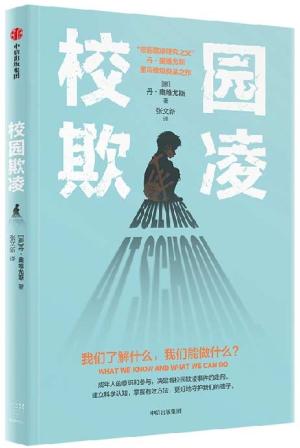
《
校园欺凌
》
售價:HK$
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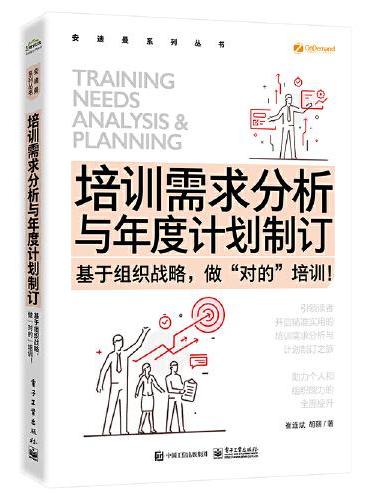
《
培训需求分析与年度计划制订——基于组织战略,做”对的”培训!
》
售價:HK$
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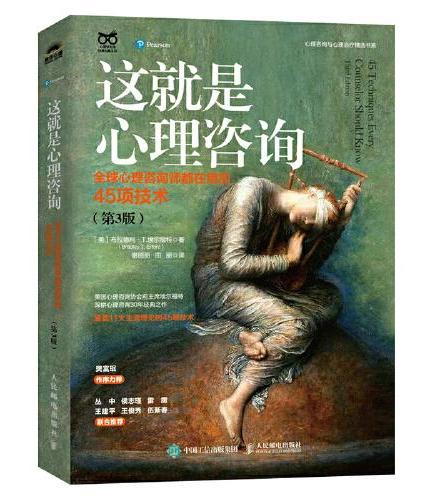
《
这就是心理咨询:全球心理咨询师都在用的45项技术(第3版)
》
售價:HK$
1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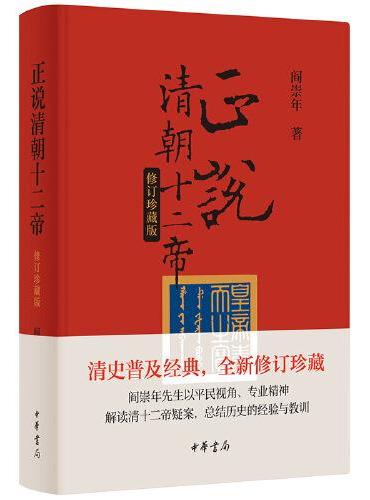
《
正说清朝十二帝(修订珍藏版)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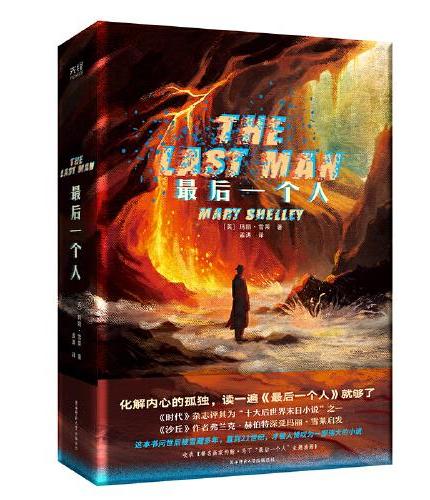
《
最后一个人(《时代》杂志评其为“十大后世界末日小说”之一)
》
售價:HK$
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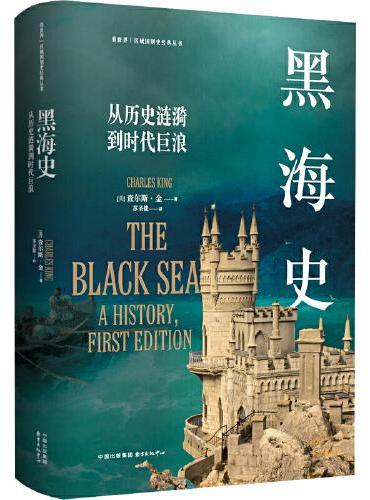
《
黑海史:从历史涟漪到时代巨浪
》
售價:HK$
115.2

《
楼边人似玉
》
售價:HK$
56.2
|
| 內容簡介: |
生逢乱世,苏离离曾以为此生注定漂泊无依。
直到,她遇见江秋镝和祁凤翔。
祁凤翔于她,处处算计谋求,唯独漏算对她的深情。
“我会对你好,好到我可以做到的地步,可是你没有给我机会。”
江秋镝于她,事事妥帖呵护,心甘情愿做她的木头。
“我飞得出去,就飞得回来!”
屋檐月光下,苏离离与木头并肩坐,仰观星河灿烂。
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
当时相见早关情,蓦然回首,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
| 關於作者: |
青垚,非科班出身的文史爱好者,中度选择困难症的天秤座,相信科学的有神论者,手速极慢的业余码字工。
已出版《改尽江山旧》《天子谋》。
|
| 目錄:
|
壹 青瓦闲作坊 月明人倚楼
贰 人生足别离 客来桃叶渡
叁 月暗孤灯火 夜雨透关山
肆 有恨无人省 转身隔汀洲
伍 似是故人来 山青横云破
陆 岐山惊闻讯 心安即吾乡
柒 谈笑皆兵马 前生乌衣巷
捌 河畔木叶声 万物为刍狗
玖 军中谈契阔 欲辨已忘言
拾 请君同入瓮 月凉千里照
番外 天涯各一方 此情可追忆
|
| 內容試閱:
|
试读:
壹
青瓦闲作坊 月明人倚楼
乱世,京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架宽大的板车在郊野小道踽踽而行,四个轮子碾在地上,周身咿咿呀呀呻吟不已,只怕一快跑就得散架。夜色薄雾中隐约可见车头挂着一盏红纸灯笼,上面浓墨写着一个隶体的“苏”字。字迹漆黑,红纸鲜艳欲滴,照见路上三尺远的道,在这初春夜里显得分外诡异。
拉车的是几匹骡子,跟那板车一样不得劲。赶车人裹着一件大皮袄子,缩着脖子,埋着头,晃晃悠悠地打瞌睡,有一下没一下地打着骡子。忽然前路上一声震喝:“呔!钱财留下,要命的快滚!”三个高大的汉子拦住板车,其中一人点起了一支火把。
骡子猝然止步,那车“嘎”的一声停下。空气中是沁人心脾的冷冽,郊野的空旷透出一股寂静,使得那骡子跺蹄的声音空洞地回响。赶车人仍然缩着头,裹在皮袄子里一动不动,火把微弱的光线中看不清其面目。
三个拦路的盗贼互相看了两眼,觉得有些古怪。为首那人方脸阔额,胆色,抢上前去揭开板车上的毡布。车上高高地堆着货物,那人拿火把细细一照,上面全是木材;外面散放着几块棺材板,都系着绳索;木料处,却赫然放着一具旧棺材,斑斑驳驳还沾着泥土。
那剪径的汉子心底生寒,才一起怯心,就听棺材里传出夜猫子似的嘶声怪笑,声音又尖又邪,“嘎嘎嘎”三声。两个站在赶车人前的盗贼惊得跳了起来,便见那赶车人缓缓抬起枯老的双手,抱着脖子转了两下,竟把头拧了下来,胸腔里“咕噜噜”两声喉音,含混沙哑道:“拿去……吧。”
赶车人双手捧着的头一抬,一张干枯惨淡的死人面孔赫然出现在两人眼前,眼珠突出,目下流血,既惨烈又恐怖。三个汉子瞬间跳了起来,“啊——鬼呀!”一边喊着一边落荒而逃。三人虽是年轻力壮,身手敏捷,却因为惊吓逃得跌跌撞撞,连滚带爬。
车头上的红纸灯笼刹那熄灭,周遭一片黑暗。半晌,有轻微的挥鞭声响起,骡子们再次起步,板车惨叫着往前奔去。车上的棺材里扑腾扑腾响着,过了片刻,棺材盖子抽开来,黑暗中一个纤巧的人影灵活地爬了出来。
那人影推好棺材盖子,拉着绳索走到板车车头,挨着那无头的赶车人坐下,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火折子,摇了摇,小心地摘下灯笼罩子,将熄灭了的灯芯点燃。淡淡灯光下,一个十四五岁眉目清秀的少女吹熄了折子上的火苗。
那少女虽穿了一身男装,却掩不住俏丽,望着赶车人银铃一般笑道:“快走到城边大路了,出来透口气。”说着,她便一手夺过赶车人抱着的人头,一手解开赶车人的衣领。那赶车人伸了伸脖子,从衣领中露出脑袋,沧桑的脸上写满笑意。少女便捏着嗓子用刚才那怪笑声“嘎嘎”地笑了起来,一老一少相顾大笑。
少时离了小道,走上进城的官道,天光已透着青白,赶车的中年人咳了一声,道:“少东家,外面冷。”
少女苏离离摇了摇头,不应,忽一眼看见手上拿着的木雕鬼脑袋,便对着人头做了个怪相,扬手将其扔到车后面的木料堆里,笑道:“这些个强盗,杀人放火都敢做,却怕鬼。”听着板车“吱吱”地响,她又道,“程叔,车该修修了。”
程叔赶着车,叹道:“京城边上都闹起强盗来,这天下果然乱了。少东家,今后你别跟车了,路上不太平。”
苏离离却笑得格外灿烂:“千亏万亏亏不着咱们,越不太平,咱们越能挣银子。”她望着渐渐清晰的官道,仰头哼起了一首婉转的山歌。
这悠扬的歌声一路唱进城,城里的街市渐渐苏醒。板车驶过如意坊后面的菜市,停在街角的一道小门前。苏离离利落地跳下板车,一面找小门的钥匙,一面对程叔道:“你买点菜,我去前面开门。”
程叔便就近买了两根笋。卖菜的农家早已认熟了他们,望着苏离离开了小角门进去,笑道:“老程,又去拉板材了。你们家离离可不容易啊,小小年纪就独自经营铺子。”
程叔回道:“祖上传下的,守着过活吧。”
卖豆腐的田婶也插话道:“今年夏天一过,离离也该十五岁了。这眉目俊俏得,倒跟个大姑娘似的。”
这回程叔但笑不语。
远远地,只听苏离离大声叫道:“啊——谁死在我门口,可真会挑地方!”
代写书信的王先生摇头轻叹:“就是粗鄙了些。”
程叔连忙放下手上的菜,转过街角,到了店铺大门前。苏离离抱着一块门板,皱着眉,咬着唇,纠结地注视着地面。门前台阶上果然趴着一个人,衣衫褴褛,洇着暗红的血迹,一动不动,不知死活。
程叔抢上前去将那人翻过身来,拂开他脸上的乱发,叫道:“小兄弟,你醒醒。”那人唇色惨白,面目瘦削,喉头涌动了两下,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苏离离搁下门板就往外走,程叔问:“你做什么?”
苏离离道:“他还没死,我叫官府来把他收去。”
程叔道:“离离,把门打开。”
苏离离一下子站住。程叔平常都称她少东家,一旦叫她离离,说的话苏离离就不好抗拒了。于是她折转身,又拆下一块门板。程叔便抱起那人,进了店铺大门。苏离离转身,见门前聚了好些人,怜悯的少,看热闹的多。有人笑道:“那孩子是看准了地方,跑到棺材铺来死,嘻嘻。”
苏离离心头恼火,冷笑一声:“没错,他是个会挑地方的,你死了可别挑到这里来。”说罢,也不看那些人,径直进了大门,将门板对上,“砰”的一声按实了,只留下铺面门楣上“苏记棺材铺”几个大字映着朝阳熠熠生辉。
苏离离穿过铺面正堂排列整齐的成品棺材,斜插过一道影壁,到了后院。后院原是个天井,堆着散乱的木料,整板花板一应俱全。苏离离直奔楼梯下小角门那间小工住的临时木阁子。程叔正半扶着那人,喂他清水。
那人没醒,却将水咽了下去。那人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左腿裤管更是沾满了血迹。程叔缓缓卷起他的裤脚,苏离离便倒抽了一口冷气——小腿上伤口狰狞肿胀,骨头几乎要戳出来。苏离离瞠目结舌道:“他……他……怕是活不下来了。你把他弄进来,莫要死在我家里。”
程叔叹道:“他不过是个孩子,死在这里也好过曝尸荒野。”
苏离离手指头一点,铿锵有力地说:“他要死在店里,我只有薄皮匣子给他!”她话音刚落,顺着自己纤长的手指,便见那人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正幽幽地望着自己。他虽面目染着脏污,眼珠子却乌黑明亮。他的眼神冷冽而沉静,像失群的幼兽,既胆怯畏惧又戒备凶狠。
苏离离被他望得愣愣的,猝然收了手,拔腿就往外走。程叔叫道:“你又做什么?现在官府哪里还管这些事。”
苏离离一边走一边仰天长叹:“无事出门就破财,这回破财破到家里来。我去找个大夫!”
将近傍晚时,大夫晃晃悠悠带着小学徒离开棺材铺,临去还带走了苏离离五两四钱银子,足够苏离离吃喝半年了。苏离离暗自心痛之余,跌足懊悔,怎么这么蠢,竟请了个好的大夫,不仅给他全身裹了伤,还开了无数方子要熬给他喝上三五个月,这下亏本亏大了。
苏离离愤愤地切着豆腐,撒了几粒盐。为了这小子,她歇业了一天,上门做活的木工也打发回去了。这会儿到了吃晚饭的时辰,程叔却不得不去送货。她将肉末排在嫩豆腐上码好,搁到水汽缭绕的蒸笼里小火蒸着,又走到外面院子的菜畦里,摘了四棵葱翠的青菜。她拿到厨房,择了叶子洗净,想了想,细细地切碎,用虾米碎菇煮烂收汁。
待青菜烧好起锅,苏离离便把蒸笼揭了盖。上层是鲜嫩细滑的豆腐肉末,下层是松散清香的米饭。用一个白瓷敞碗各盛一半,添了两箸美味多汁的青菜,苏离离端了碗来到木阁子里。下午大夫给他正骨时,他便昏了过去。这人真是倔,死死咬着牙,不肯出声,眼睛一翻就昏过去了,把苏离离吓得,还以为他真死了。
苏离离搁下碗,坐到床边,用手指戳他的额头:“喂,醒醒。”
那人不动,昏睡的脸上血迹泥浆已洗干净了,看着有些青涩稚气,虽然脸色蜡黄,却是剑眉薄唇,鼻梁挺直。苏离离心中龌龊地想:他这副样子是手不能挑,肩不能扛,委实没用得很;一张脸倒长得不赖,只怕卖到某个地方还能做个头牌……
她正胡思乱想,那人动了动。苏离离赶紧推推他的肩膀:“你快醒醒,再睡就得饿死了。”那人一醒便微微皱了眉,待睁开眼睛看到苏离离,神色便又平静冷漠起来。苏离离大是不悦,骂道:“疼就疼吧,装什么样?!撑死的英雄,饿死的好汉。这里有饭有菜,有本事你别吃,省得放低了你的身段!”她把碗重重一敲,端起来,用勺子扒拉饭菜,顿时鲜香四溢。
那人咬牙望着她。苏离离道:“想吃吗?”
他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微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
苏离离嘻嘻一笑:“你若还这样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便不给你吃。你纵然恨得我咬牙切齿也只得活活饿死。”
那人眸子一低,不再看她,只望着床沿。他此时俯首低眉,显得比先前冷然的样子更加无助。苏离离心头一软,放了碗,将他扶起来,嘴里却道:“现在才知道低头,白白找人骂。”她将枕头给他塞好,让他半倚在那枕上,端了碗一勺勺喂他饭菜。
豆腐入口即化,青菜她也切得极碎,无须多么费力便可咽下去。那人默默地咀嚼,眼神不再凌厉,却沉默异常。苏离离喂他吃完,放下碗,用手帕给他擦净了嘴,又端了水喂他。那人也喝了,苏离离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漆黑的眼珠子不看苏离离,却望着虚空,不答。苏离离皱眉道:“怪不得你连正骨都不叫唤,原来是个哑巴啊。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恶事,这辈子业报现眼前。”
他额上的青筋跳了跳。就在苏离离端了碗要走时,他忽然开口,沙哑地问:“什么是薄皮匣子?”
苏离离万料不到这人句话是这样问她,愕然半晌才反应过来。“就是废料做的薄棺材,一百钱一具。”她咽了下口水,“那个……实在没钱,白送也行……”因她早晨说要给他睡薄皮匣子,此刻见问不由得心虚,声音便少了底气。
“我的腿怎么了?”他仍然望着床沿,淡淡地问。
“骨头折了,大夫已经给你正好了。”苏离离机械地回答。
“能好吗?”
“若是骨头接得好,你也好好休养,不一定会残疾。”她照样把大夫的话说了一遍,心里诧异,怎的他像是主子,她倒像是奴才,有问必答。
他听完,不再问,慢慢撑着身子倒下去躺着。
苏离离愣了半天,觉得不对,此人不明事理,需得跟他说明白,便径直走到他面前,一手端着碗,一手指着自己道:“喂,你记住了。我,叫苏离离,就是离离原上草的那个离离。我救了你的命,是你的救命恩人。”
他默默地看了她两眼,漠然道:“我知道了。”
见他丝毫没有衔环结草的感激之情,苏离离有些来气,指着他道:“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何方人氏?有钱没钱,叫你家人来赎你?”
他闭着眼睛道:“没家没人,更没有钱。”
“连名字也没有?”
“没有。”
苏离离看他倒在那里,有气无力,咬牙道:“你别以为我好心救了你,你就可以白吃白喝耍无赖。没钱就给我做小工,没名字我给你起一个。我满院子都是木头,你从今儿起就叫木头了!”
她自然是不等他答,转身出去时,将那破木门摔得“啪”的一响。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苏离离便起床洗漱。
晨曦中的后院静谧清新,从井里汲来的水流晶泄玉般从她指间滑过,凉凉的触感让她玩心忽起,一扬手,一串水珠洒了出去。她仰头看见院外的一棵玉兰树,正抽着嫩黄浅绿的新叶。
古来文人骚客多爱咏春伤秋,苏离离独不喜秋天。天气实如人之心性,隆冬严寒,盛夏酷暑,都是至情至性,毫不做作。春天万物欣然,如人微笑;秋天却似幽闺怨妇,虽是色衰伤情,偏不肯痛快零落,只哀婉个没完。
苏离离洗完脸,略略浇了一下菜地,觉得离那怨妇还有大半年光景,心情甚好,提了水便去厨房做饭。不多时她便端了碗甜米粥,推开了角落里那间小屋的门。那块“木头”睁着眼,望着屋顶斜支出来的一块板子,见苏离离进来,目光勉强落在她身上。
苏离离将他扶坐起来,自己坐在床沿,用勺子挑着粥,香糯清甜。那人脸色不似昨日蜡黄,然而苍白得没有血色,唯有一双眼睛仍清冷犀利。苏离离将勺子伸到他唇边,他便抬手道:“我自己来。”声音低沉,却带着沙砾相撞的清越。
苏离离隔开他的手,冷笑道:“自己来?一会儿你就得离了这里!”
他并不表示讶异,只眼神微微一沉。苏离离顿了顿,接道:“搬到东面那间空屋去,嘻嘻,你也自己来吗?”
这本是个小玩笑,他却很不赏脸,抿着薄唇道:“为什么救我?”
苏离离觉得此人防备之心太过,性子又冷,便也收了玩笑的态度,正色诚恳道:“不是我要救你,是你要死在我门口。你若死在我隔壁的门口,我连花板的薄皮匣子都不送。既救了你,你在一天,我不会饿着你冻着你;你若有仇家寻到这里,我也护不住你。这是你的命。你明白吗?”
苏离离说得分明,他听得清楚,点了点头。苏离离展颜一笑,赞道:“这样好,我喜欢明白人。”她舀起一勺粥送到他唇边,“昨天刚拉回木材,吃了饭我还要忙。这屋子潮,你筋骨有伤,住久了会落下病根。东面还有间厢房,堆着东西,一会儿我收拾了,你住那里去。”
她再舀一勺,又喂到他唇边:“你叫什么?当真不说,我就叫你木头了。”他竟又点了点头,苏离离便笑道,“木头,你多大了?这总不是秘密吧。”
木头注视苏离离半天,缓缓吐出两个字:“十四。”
“你的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以后叫我少东家吧,过两天再看你能做什么。”苏离离淡淡道。
“我?”木头惜字如金。
苏离离眉毛一挑:“难不成我白养着你?你要觉得叫少东家折了你的身份,叫我大哥也成。”
“你?”他声音更高。
苏离离不再应他,端了碗要走。木头打量她两眼,闷声道:“你多大啊?”
苏离离嗤笑出声:“还不服气,你十四,我十五,你不该叫我大哥吗?”
吃完饭,苏离离便烧了热水,让程叔提到澡间,将木头擦擦洗洗,换药。木头腿上有伤,打着木夹板,身上也多处外伤,一洗洗了大半个时辰。趁着他梳洗,苏离离腾出东屋,扫净积尘,铺了洗净的棉褥。虽是普通的蓝棉布,却散发着淡淡的洁净气息。少时,程叔将木头背了过来。苏离离多的是男装,拣了两套给他,他穿着有些嫌小。
苏离离扶木头倚床坐好,伸手推开了一旁的窗户。太阳已升了起来,阳光慷慨地洒进房中,照在木头脸上。木头合上眼,微仰着头,深深吸了一口气,仿若隔世重生。苏离离见他舒展开来的样子,心底似有泉水细细流动,柔声道:“等你伤好了,我带你去郊外逛逛。”
木头微微睁开眼,阳光映在他的眼睫上,像镀了一层金。他唇角轻轻扯起一道弧线,笑容虽浅淡,却如和风暖阳。苏离离抬头看去,窗外三分春色,平添了一分。
棺材铺子的生意从不会门庭若市,也不会颗粒无收。苏离离的铺子在如意坊的尾端,因为她家的棺材做工精良,在京中小有名气。
柏、樟、松、楠,应有尽有;方、圆、阔、窄,各成气象。雕花意态峭峻,彩画栩栩如生。板间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用朱砂打底,大漆罩面。几道漆下来,棺木锃亮如鉴,屈指一叩,声如珰玉。
苏离离对着账本订单安排活计。每天上午木工师傅过来把板裁得曲直合度,张师傅援刀雕刻,苏离离调漆勾绘,程叔拉板送货。生意不徐不疾,不饱不饥。
木头既然不肯吐露一字,苏离离便一字不问,只对人扯谎说木头姓木,雍州人,家人死在战乱中,他孤身流离,落脚在此,留在店中给程叔帮把手。
世间一隅静好,却是乾坤缭乱。放眼天下,各州兵马并起,因怕担了反叛之名,成为众矢之的,还不曾有乱兵入京。外面州郡已是兵荒马乱,四野奔逃。个把流民,官府不管,百姓也见怪不怪,木头之事也就被苏离离顺理成章地遮了过去。
程叔抽空做了两支拐杖。月余之后,木头伤势稍愈,虽整日沉默,偶尔也挟着两支拐杖,单着一只脚,在院子里走动。苏记棺材铺,前门临如意坊,后角门却在百福街。苏离离平日坐在大堂,偶尔往后院看看活计。后院九丈见方的空地便是做棺材的地方,从左至右,从整木到成板,零落散放。
院子东西分厢,各占两间。苏离离住在西面间,隔壁却是个大书房,四壁书橱,积尘厚薄不一。木头随手翻出几本,却是天文地理、人物杂记、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东面厢房第二间住着程叔,间如今便是木头住。
从窗户望去能见着一块葱翠的菜地,是个院外之院,从东墙小门就可走到那里。院里一口水井,波澜不惊。井侧却是一道葫芦架隔出的荫凉,葫芦蔓攀着架子,正作势要结果。白墙青瓦外,长着一株粗壮的玉兰树,正挂着满树白玉兰,清晨落入院中,幽香四溢。一墙之隔,意趣横生。
木头行走不便,更帮不上什么忙,常拈了本书,坐在小院晒着太阳看。这日午后,院落寂静。苏离离对了一遍订单上各家棺材的制作进度,一一记了,闲下半天来,便去后院洗两件衣服。
她挽了半截袖子,白皙的皮肤映在水里,明澈得晃眼,搓板上揉着衣服,抬眼见木头坐在葫芦架下,不眨眼地看着自己。苏离离微微一笑,问:“木头,你知道什么叫作棺材脸吗?”
木头感到不妙,眼神应着她的声音黯了黯。苏离离已接着说道:“你若是块木头,我把你砍砍削削做成棺材,倒应了你成天挂着的这张脸。你既是个人,这脸便该笑时笑,该哭时哭,该悠闲时恬淡适意。我这铺子只卖棺材,别人见了你,还以为我额外奉送哭丧的孝子贤孙。”
她一番抢白,木头的表情非但没有灵活生动起来,反而越发阴沉了几分。苏离离眼波流转,笑意怡然,牵起衣裳抖了抖,散晾在竹竿上,正泼了水拿着盆子要往里走,后角门上传来三声响,有人扯着嗓子喊苏离离。
苏离离放下盆去开门,一个短衣乱发的方脸少年扛着根扁担站在门外,正是这百福街上的闲人莫大。莫大十七八岁的年纪,有娘生没爹养,整日混迹市井,干的营生并不那么光明。苏离离觉得他义气,不管他做什么,也结交起来。
见莫大晃着扁担进来,苏离离奇道:“你不在正堂叫我,跑到这后角门来。恰好我在这儿,不然你叫破了嗓子我也未必听得见。”
莫大咧嘴一笑,露出白森森的牙:“棺材铺子的大门那是买棺材的人进的,谁没事去找晦气。”
苏离离便赶人:“是是,我这里晦气,你快找个吉星高照的地方去。”
莫大一眼看见木头坐在那葫芦架下,虽穿着布衣素裳,跷着一条腿,却掩不住清贵态度;虽不发一言,却足以令人自惭形秽。世人有高下之分,有贵贱之别,有时是超越性格与心志的。见着比自己优越的人,往往心生愤恨;待见这人落难,便心喜意足。
无论欢喜与仇雠,总不能弥合差别,共做一群。这,也许就是所谓的阶级。
而莫大,一眼瞧见木头便不顺眼,对苏离离道:“听说你上次救了个叫花子,就是这小子啊?”
木头斜斜地靠到椅子背上,也不见恼怒,只默然不语。苏离离叹口气道:“他家人离散,可怜得很,我认了他做我弟弟,你别叫花子叫花子的喊。”
莫大皱起眉头道:“本来就是叫花子,敢做还不让人说吗?”
苏离离仰头看了他两眼,皱了眉,对木头道:“这是街对角莫家裁缝店的莫大。莫大是个诨名。”她转头看了莫大一眼,抑扬顿挫地说,“他大名叫莫寻花。”
木头原本一语不发,此时却极有默契,不咸不淡道:“名字风雅,兼且凑趣。”
莫大顿时涨红了脸,大是不悦道:“离离,你……”
苏离离和蔼地笑着:“什么你你你,我还不知你口吃。”她转向木头,款款道,“莫大哥的爹爹早年逛窑子,与人争风时失手丧命。他娘亲开着个裁缝店拉扯两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莫寻花,他还有个兄弟,叫莫问柳。”
她清脆地落下后一个字,木头眼睛也不抬,毫无起伏地接道:“字字血泪。”
苏离离“哈”地一笑,只觉木头被她刻薄时无辜得可爱,损起人来也不差分毫。
老子逛窑子被打死可谓窝囊,儿子偏还给起了这么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莫大生平恨的便是别人叫他莫寻花,苏离离今天偏要揭他短,他顿觉在木头面前矮了气势,苦脸道:“你就这么护着他,他给你银子了?”
苏离离擦着手道:“我说了,他是我弟弟。你找我有事?”
莫大道:“我听人说定陵太庙闹鬼闹得厉害,今晚想去捉一捉;即便捉不着,也可以见见世面。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瞧瞧?”
苏离离大笑:“你去挖坟盗墓我还信,捉鬼?你骗鬼吧。”
“你该不会是胆子小,不敢去?”
苏离离笑着摇头:“我不受你激,大半夜的不睡,跑去墓地闲逛。你要去,我别的没有,看在朋友一场的分上,大方一回,杉木的十三圆倒是可以白送一具。”
莫大“呸”的一声啐在地上:“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不是咒我吗?”见木头望着自己吐的口水皱眉,莫大大声笑道,“我以为你照顾这瘸子弟弟肯定闷坏了,才趁着天气好,约你出去逛逛。你既不想去,那就罢了。”
他说完抬脚要走,苏离离叫道:“等等。”她黑白分明的眼珠子,水润光泽,斜睨着一转,道,“我至多给你放个风。说吧,晚上什么时候?”
“酉时三刻,我在这角门外等你。”莫大指指角门,大步离去。
苏离离应着,回头见木头默然看着莫大走远。苏离离扑到他椅边,蹲下笑道:“好木头,你别告诉程叔。我悄悄地去,悄悄地回来。”
她一声“好木头”叫得未免有些亲热,直把木头叫得皱起了眉。本是光润华贵的椴木,也皱成了横七竖八的黄杨渣子。
苏离离不管他的冷淡,按着他右腿无伤的膝盖摇了摇,一脸谄笑地站起来,端着盆子进去了。
这天苏离离吃过晚饭,在院子里逛了逛,便说头疼,早早回房里歇息了。临去时,程叔毫不察觉,木头摆着一张棺材脸横了她一眼,被她瞪了回去。
她回房里换了身深色的短衣,扎上裤脚,绾起头发,扮作小厮模样。天刚蒙蒙黑,她探头一看,程叔与木头已各自回房,白纸糊着的窗棂上投来淡淡灯火。苏离离踮着脚,猫一样走过正院,蹿出后院角门。
门外莫大牵着一匹马,背了个包袱,包袱束得很紧,只有一把方便铲的铲头露在外面。见了她,莫大翻身上马,苏离离便也踩了镫上去,抓住他的腰带。一路越走越荒凉,苏离离问:“你娘的病还没好?”
莫大叹气:“怕是好不了了。”
“二哥还是没有消息?”莫问柳离家一年,音信全无。
莫大摇头:“没有消息,且再等等看吧。”
少时到了定陵,莫大早已踩好了点,引着苏离离穿丘越陵,往偏僻的角落而去。定陵,是皇家历代帝王后妃、文武大臣的陵寝,也是藏金葬玉的宝窟。苏离离等着他辨方向时,不知让什么蚊虫咬在了手上,一边抓着,一边皱了眉轻声道:“这禁军也太过渎职,皇陵荒芜成这样。”
莫大“哧”的一声笑:“不荒能有活干吗?主陵那边还住着人,这些陪葬大臣墓早没人管了,天天都有人来逛。”逛,是个行话,不言自明。他指点苏离离道:“你在那棵矮树下看着,若有人来还是学夜猫子叫。”
苏离离应了。莫大身子一弓,摸向前面方冢。苏离离也弓了身子,退到那棵矮树下。趴在地上,泥土和着潮湿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苏离离从怀里摸出百草堂买的清凉油,抹在手腕脖子上,竖起耳朵听动静。
夜色转深,荒野陵墓间没有一丝声响,又似有万籁千声。远方微微起伏的地平线上,七颗明亮的星星排成勺状。夜空深蓝,大地反显得苍茫空旷,所谓大象无形,一时激起人的亘古之念。苏离离看着那北斗形状,有些愣怔。
耳边一丝若有若无的声响,似有人轻声叹息。苏离离精神一振,回过神来,细听之下那声音仿佛是从东南面来。她趴着不动,凝神细听,少时又有几声呻吟。苏离离大奇,荒野墓地,除了盗墓贼,就是狐狸精,怎会有这声音?
她犹豫片刻,转身往东南方摸过去,行了十余丈远,便见一座屋宇的轮廓隐约矗立在一片林木边,仿佛祭拜的庙宇。苏离离蹲下身子,慢慢爬近一些,还未落稳脚跟,就听“啊”的一声惨叫。
一个声音低沉地问:“当真不说?”方才叫唤的人虚弱地喘息道:“小人……小人确实不曾找到。叶知秋十年前……已隐退山林,不问政事。朝廷宫中都不知他的去处……”
苏离离闻言一愣,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心中思忖个来回,便贴着地面,如觅食的猫儿,蹑手蹑脚地再爬近些,微窥大庙正殿。
正殿地上横躺着一人,狼狈不堪。他身侧站了一个人,却是阔袖散发,皂衣拂地。两人俱看不清面目。站立的男子身材挺拔,不知对地上那人施了什么刑,此刻只负手而立,缓缓道:“叶知秋即便死了,那东西总有落处。就是随他葬了,也必定有葬的地方。”
地上那人哀求道:“小人……只掌管宫中采买之事,此事……实在无从打听……”
皂衣男子手轻轻放下来,冷冷道:“你既不知道,便不该欺哄主子。”他从怀里取出一个不大的瓷瓶,拔开盖子。地上那人陡然大声道:“不,不,我……”话未喊完,几许清亮的液体洒在他身上。那人顿时没了声,只喉间发出咕噜的声音,像是放了水的皮囊,身体在地上瘪了下去。
一股腥浊之气弥漫开来,苏离离猛然伸手捂住口鼻,半是恶心,半是害怕。眼睁睁看着那人化成了一地尸水,只有衣服覆地,苏离离竟僵了手脚,动弹不得,既想逃跑,又不敢动。只是这一抬手的动静,皂衣男子似有所觉,已微微转头,垂手缓步出来。
他后脚踏出门槛边,便站住了。夜色青光下,这人脸上如罩着淡淡的寒气,纵横蜿蜒着十数道刀疤,仿佛将脸作地,横来竖去细细地犁了一遍,狰狞可怕。
他眼光缓缓扫过苏离离趴着的那片草地。苏离离捂着嘴,本不想发抖,然而那手自己要抖,她止也止不住。此时此刻,只怕一只蚊子落在她手背上她都能惊得跳起来,何况是后脑勺上有什么东西静静吹动。
脖子带点痒痒的凉,竖立警戒的汗毛被触动,苏离离猛然尖叫一声,凄厉胜过夜猫子。一回头时,一张人脸很近地凑在眼前。
她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朝着大庙的方向退了几步,定了定神,才看清身后这人是个年轻公子。他一身月白锦衣,暗夜中略有暧昧的丝光,狭长的眼睛映着星火,清浅流溢,态度竟十分温和优雅,手撑着膝盖,正弯腰俯看着她。苏离离半天吐出一口气来,拍着胸口,将一颗心拍回原处,忽想起那个皂衣人,猛地一回头时,愣住了。
庙门空空地开在那里,一个人影也不见;正殿的地上,方才化成水的那人,衣裳也不见了,仿佛是一场幻觉。苏离离抬头嗅了嗅,空气中淡淡的尸臭味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幻觉。她努力镇定了心神,从地上爬起来,扯了扯衣角,平平稳稳地对那锦衣公子拱手道:“月黑风高,公子在此游玩,真是好兴致。”
那人直起身,颇具风雅,缓缓吟道:“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他的声音听起来,像细砂纸打磨着锯好的棺材板,光滑低沉。咫尺之距,他虽笑意盎然,却让她后背生寒。
她吸了一口气,道:“杀人放火大买卖,挖坟掘墓小营生。都是出来逛,公子说笑了。”苏离离假笑两声,站起来就走。
她刚走两步,手腕一把被他扣住,手劲就如同他的声音,不轻也不重:“这位公子,方才为何惊叫?”
苏离离的清凉油抹对了路,手上有些滑,一挣,脱开了手。她仰头看他:“因为公子你悄声出现在我身后,荒郊野地吓着我了。”
“荒野无人,你趴在这里做什么?”
苏离离虽不聪明,也不蠢,自不会说她是来盗墓的,更不会说方才看见如此这般的事,张口就编道:“这位兄台,实不相瞒。在下的父母为我定了桩亲事,可我心有所属,不愿屈就。今夜收拾金银细软,正要与人私奔。方才是在等人。”
话音刚落,莫大扛着一个又沉又鼓的包袱,鬼鬼祟祟地摸了过来。苏离离暗自哀叹了一声,合上眼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