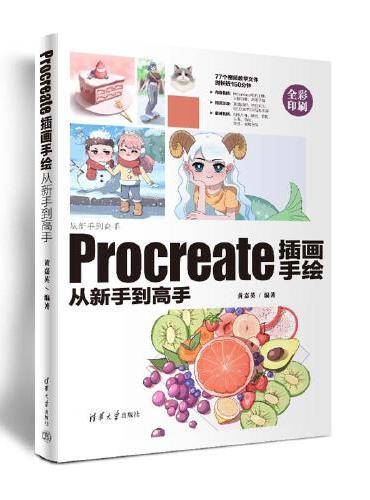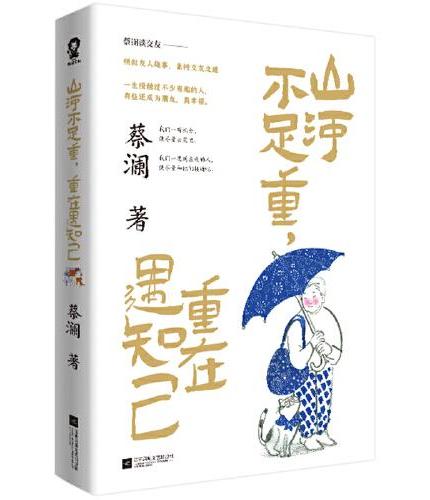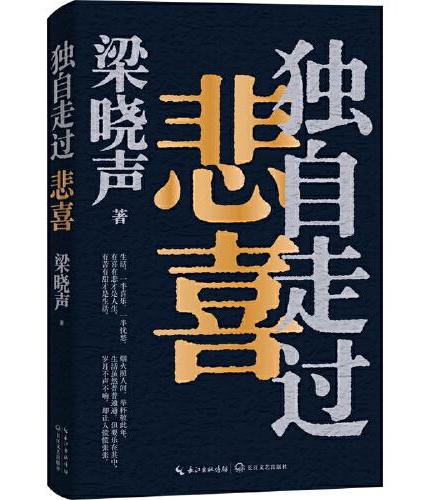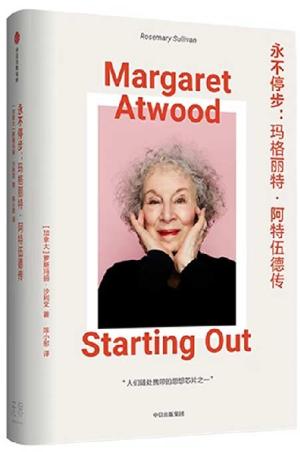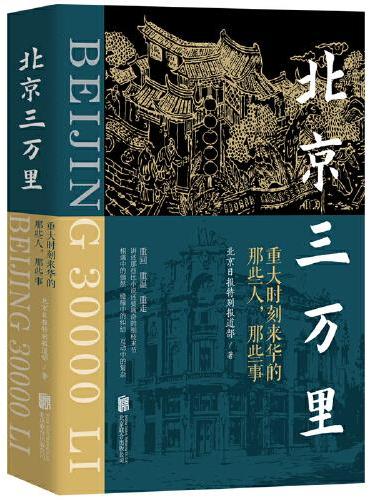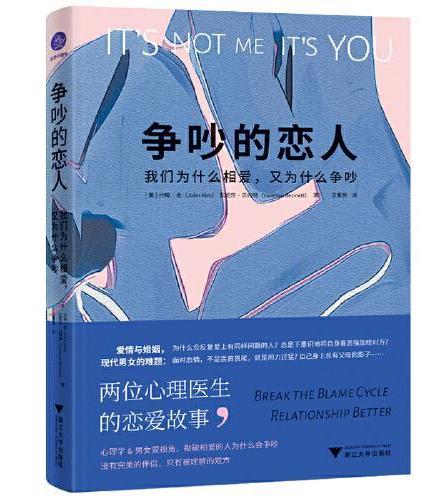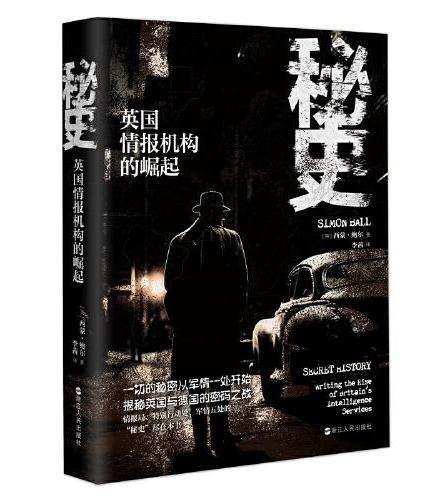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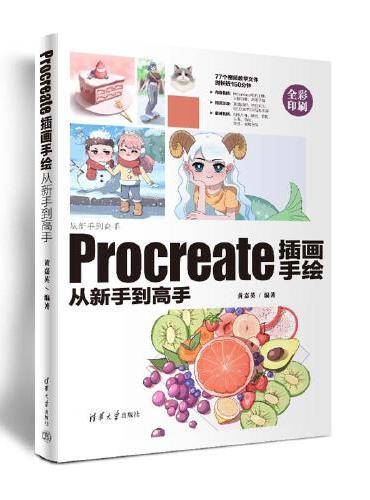
《
Procreate插画手绘从新手到高手
》
售價:HK$
10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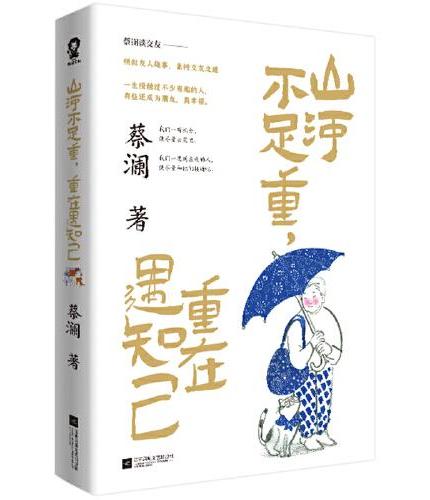
《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
售價:HK$
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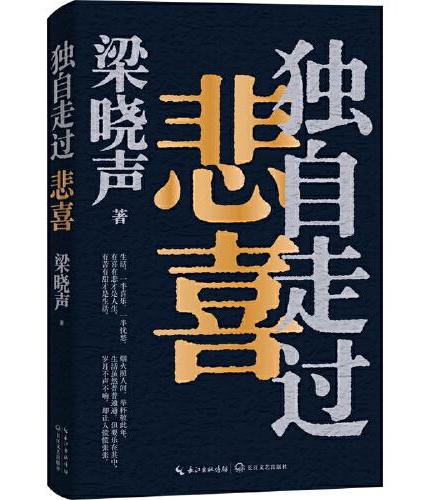
《
独自走过悲喜
》
售價:HK$
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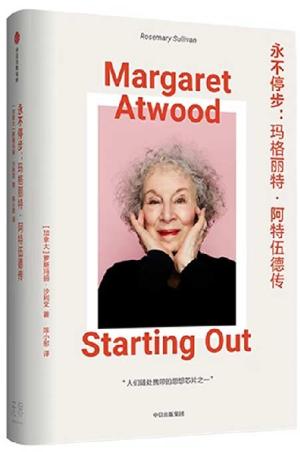
《
永不停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
》
售價:HK$
94.8

《
假努力:方向不对,一切白费
》
售價:HK$
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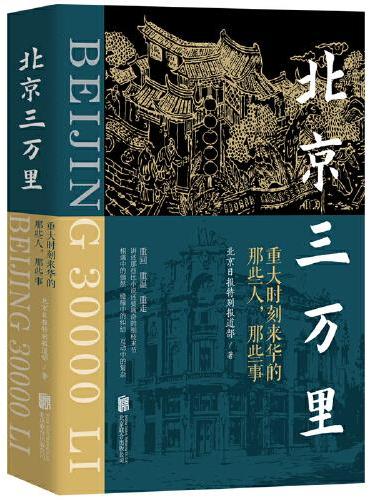
《
北京三万里
》
售價:HK$
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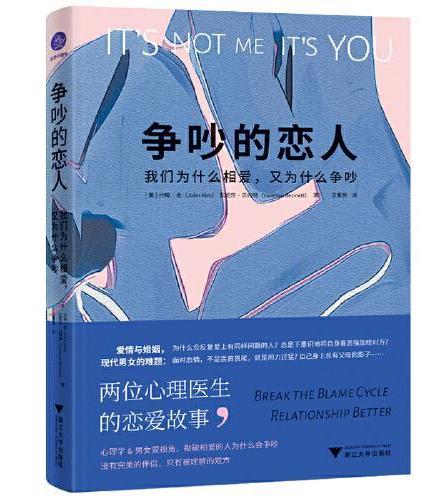
《
争吵的恋人:我们为什么相爱,又为什么争吵
》
售價:HK$
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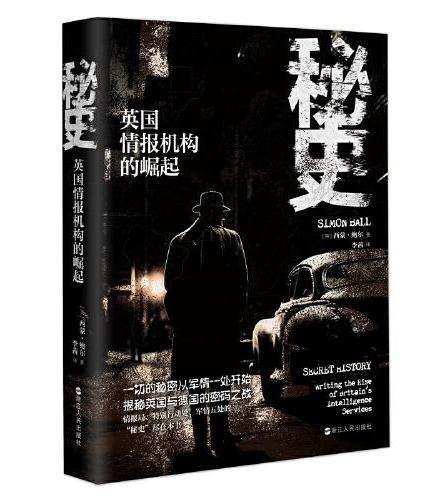
《
秘史:英国情报机构的崛起
》
售價:HK$
81.6
|
| 編輯推薦: |
我一直很欣赏马笑泉的小说,这当然不止是因为他的勤劳,更因为他在艺术上有一种不断开拓新空间的执着劲。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吧,马笑泉初涉文坛,我读到了他的小说《愤怒青年》,就被他的充满血性和刚毅的文字惊住了。以后陆续看到他拿出了一部又一部新作,一步又一步地在文学的山路上跋涉和成长。如今他已是当代文坛的一名非常有实力的作家。
——贺绍俊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收入作者创作的四个中篇:《对河》《离乡》《诗兄弟》和《笼中人》,分别发表于《十月》《芙蓉》《文学界》等刊。《对河》在空灵飘逸的叙述中表现人物灵魂与故乡人事风物的微妙互渗,具有水墨画般的氤氲感和朦胧美;《离乡》则于紧致密实的描写中呈现出理想和现实的深度交错,构思独特,别具意味;《诗兄弟》和《笼中人》均叙述基层青年诗人的成长,人物鲜活,情绪浓郁,释放出强大的冲击力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
| 關於作者: |
|
马笑泉,回族,1978年生于湖南隆回。著有长篇小说《迷城》《放养年代》《巫地传说》《银行档案》,中篇小说集《对河》《愤怒青年》,短篇小说集《回身集》《幼兽集》,诗集《三种向度》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意大利等文。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湖南师大文学院兼职教授。
|
| 目錄:
|
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 贺绍俊 /1
对河 /1
离乡 /51
诗兄弟 /99
笼中人 /206
|
| 內容試閱:
|
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
贺绍俊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吧,马笑泉初涉文坛,我读到了他的小说《愤怒青年》,就被他的充满血性和刚毅的文字惊住了。以后陆续看到他拿出了一部又一部新作,一步又一步地在文学的山路上跋涉和成长。如今他已是当代文坛的一名非常有实力的作家,他在小说、散文、诗歌等领域都有所造就,即以小说为例,就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集。这一次他告诉我他又有一本小说集要出版了,并将整理好的电子版发给我看,我却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了,因为这对于马笑泉来说,无非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像一位勤劳的农夫,日复一日地耕耘在土地上,同时他从土地上得到的收获也是非常丰沃的。
我一直很欣赏马笑泉的小说,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勤劳,更因为他在艺术上有一种不断开拓新空间的执着劲。《愤怒青年》是马笑泉的首秀,这篇小说也是他的自然天性的真实呈露,他带着一名湘中汉子的刚烈和淳朴,用冷凝的笔,挑开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征象,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经典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马笑泉所塑造的愤怒青年楚小龙作为一个时代的征象,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典型化的文学形象,这一形象可以接续到以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为代表的坏孩子形象谱系中,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中国元素。愤怒青年由特定时代形塑而成,但他表现出的冷峻、刚毅的品格却是人类历史性的精神存在。马笑泉成长于一个文化迷乱的年代,他若继续以《愤怒青年》的方式,书写这个年代的精神乱象,也许能成为中国的“塞林格”。但马笑泉并不想把自己困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和风格里,他接下来写的《银行档案》仿佛像四川的“变脸”一样完全换了一副笔墨。他不满足于像《愤怒青年》那样真性情地自然书写,而是把重点放在形式上面,自觉探索小说的形式感。小说借用档案的文体形式,给银行的二十余位职员重新立了二十余份档案。因此它也被人们称为“档案体”小说。这种档案体看似没有主人公,没有中心事件,但作者通过这种形式找到了散点透视的视角,每一份档案或人物就是一个视点,每一个视点又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整体。另外,从意识层面说,马笑泉的“档案体”其实是反档案的意识,体制内的人事档案是苍白的,它用层层伪装把活生生的人包裹起来。马笑泉反其道而用之,他为某银行职员书写的档案,是把他们身上的伪装层层剥去,直到裸露出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书写是一种毫不留情面的书写,它让我们感到了文学的力度。《银行档案》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马笑泉完整的文学观:一方面,他立足于自己的家乡体验,在文化内涵上进行深入开掘;另一方面,他将小说当成一件艺术精品仔细打磨。长篇小说《放养年代》是他对自己的童年记忆进行一次文学化的修饰。长篇小说《巫地传说》则是他对自我基因的一次文化溯源。《巫地传说》取材于家乡的异人轶事和民间习俗,如放蛊、落洞、通灵、还愿、鲁班术、梅山术等,既不是严格的写实,又不是神话式的想象,用作者本人的话说,他要超越唯物与唯心,找到一种“唯象”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他从家乡亦真亦幻的传说里,看到了一种介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象”,我想,马笑泉所看到的“象”,可以说就是历史岁月附着在这些传说中的文化密码。马笑泉的家乡属于梅山文化的范畴,梅山文化即蚩尤文化,在湖南中部地区影响深远,马笑泉显然意识到梅山文化对于自己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他未必就没有过认为自己坐拥着一座宝山的窃窃自喜。他在很多作品中对梅山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诠释。他所说的“唯象”可以说就是领悟梅山文化的一种收获。长篇小说《迷城》也许是他下功夫最足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就对家乡的文化和历史做了较为深入的开掘。但这部作品是发生在一座小城市里的现实故事,对家乡文化和历史的开掘只是为了对现实的把握更加透彻。我在这部反映现实的小说里,看到了马笑泉深沉的政治情怀。马笑泉的政治情怀不是由教科书或领导培育出来的,而是向民间学习的结果,因此他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世俗人生。按他在小说中的说法是:“官方有官方的政治,民间有民间的政治,两者互相渗透。”他以这样的政治情怀去观照自己生活过的城市,最终落笔在民生和民情上。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情怀,只不过有的作家在写作中要尽量掩饰自己的政治情怀,马笑泉则将自己的政治情怀当成一副开垦现实生活的犁铧。因此他没有像有些青年作家那样完全走内心,纯粹去叩问心灵世界,他既走内心,又投奔外面世界,他的文学空间不仅非常大,而且也是开放的,只要他有精力,完全可以无限地扩张。若说到马笑泉以后的创作,也许更重要的不是扩张,而是如何在广袤的空间里,寻找到几个最坚实的立足点。
这一回出版的是一部小说集。马笑泉已出版过多部小说集。我发现,马笑泉对待小说集也是非常认真的,或者说,他总是将小说集当成一次新的写作目标来对待,具有比较统一的主题,或是对某种文学构想的系统尝试。比如《回身集》,收录了八个短篇小说,都是以武术为题材的;又如《幼兽集》,收录了十二个短篇小说,都是以南方小城飞龙县为背景,刻画一群不同阶层的县城少年。前者马笑泉是由武术进入到中国传统的术文化,并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后者则是马笑泉在小说中追求诗意的尝试。收到这本《对河》的文稿,我就在想,这一回马笑泉给自己定了什么目标呢?
《对河》的书名就很有意思。我看到这个书名,心中不由自主地用湖南方言念了一遍。“对河”应该是湖南方言中的一个熟语,而且在南方其他省份的方言中也普遍流行。但在我的印象中北方似乎不说这个词语。我特意查了一些字词典,都没有“对河”的条目。“对河”是一个关于地域的词语,是指一条河流的对岸。《现代汉语词典》收有“对岸”的条目,其释义为:“一定水域互相对着的两岸互称对岸”,这条释义完全可以搬来解释“对河”。马笑泉这本小说集的目标显然与“对河”有关。其中有一篇小说名就是“对河”,写的是一座县城里有一条河流过,县城的主体在河这一边,对河虽然也属于县城,但在童年时的“我”眼里,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有一座桥通往对河,“我”总想从桥上走到对河去,但似乎最终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阻止了“我”。后来“我”的文学与爱情都和对河建立起了联系,“我”最初最崇拜的诗人就来自对河,去城里读书时遇到一位心仪的女孩也是住在对河的。小说的结尾却是假期里“我”兴致勃勃地去对河寻到女孩的家里时,女孩惊恐地将“我”拒之门外。“我”返回桥上时,“怀着越来越深的后悔和悲凉,离那个对河越来越远。”这篇小说表现出马笑泉在面对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虚与实之间的冲突时一种困惑和追问。小说集里的另外三篇作品大致上都与这一主题有关联。《离乡》中的雷安野练就了铁布衫的武功,以为就可以放心闯天下了,但他走出去所遭遇的一切完全不是他所预料的。《诗兄弟》中的诗人廖独行确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与世俗的一切似乎完全格格不入,小说最终是以他烧死在洞中的悲剧而结束。《笼中人》的“我”进入县地税局当公务员,“我”不满于笼中人的生活,最终凭着自己的文学才华考取了南京大学作家班。这几篇小说写于不同的时期,可见在马笑泉的心头一直萦绕着那些精神性问题,这大概也证明了他一直在研习梅山文化吧。如果一名作家不仅要将自己的家乡作为自己的文学原乡,而且要从哲学和精神的层面上去探测家乡的文化基因,那他就有可能构建起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马笑泉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对 河
一
长期以来,我都把对河看成另一个地方。实际上,它跟河这边同属于一个镇。而我们的镇又是县委县政府驻地,所以其实它也是县城的一部分。但许多河这边的人,恐怕和我一样,在潜意识里便把对河的人与我们区分开来。其实这种看法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它只不过是在我身上得到一次延续和扩散而已。谴责其中包含的歧视色彩无济于事,因为连那边的人每逢被询问住哪时,也总是不假思索地说,对河。当他们准备穿过大桥来这边时,总是会说,到街上去,似乎那条弯月形的街算不得街。但他们也没把自己当成乡里人,若是那样,说法会变为:到城里去,或是,到县里去。总之,它是介于县城和乡村之间的一块地方,一个边界和归属都难以确定的过渡地带。而长期以来,在我的感觉里,它就像一个近在咫尺的梦境,既贴近又遥远,既亲切又神秘,仿佛会在瞬间飘走,但一伸手又能触及。后来又像一个曾在远方漂泊多年回乡定居的亲戚,日渐熟悉的面容下总藏着些永难摸清的陌生,而这陌生感又吸引着我用各种方式去接近和打探。
大约是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或者比这更小,幼儿园大班,我就想去对河。但每次到了水边,面对那道大桥,我都没有勇气踏上去。也不知是谁在我的意识中画下一道深深的边界线。但这道边界线是移动的。起初,它就在桥的这端。只要我踏上桥头,便意味着走出县城,进入一个陌生之境。很多次我都久久站在桥的这边,脚尖和桥头挨得很近,却没再往前挪动半分。在那时的打量中,大桥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尤其是在雾气氤氲或暮色弥漫之际。仿佛只要我踏上去,就会一直走,一直走,永远到不了桥的那边。这也是我迟迟跨不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而只要转过身,就会看到两边熟悉的悬铃木,树叶手掌下悬挂着黄绿色的绒毛铃铛,三五成串,仿佛只要风吹过,便会发出脆响。树荫下幽凉的街道缓缓地铺展开来,往前走上五六分钟,一定会到路口。路口的斜对面是车站,而往右一转,即进入繁华的大街。再前行两百米,右边就是大人和小孩都无限向往的县电影院。对这一切我都很有把握。尽管它会让刚进城的乡里人眼花缭乱,甚至晕街,但在年幼的我眼中,早已条理分明,连看似流动的小摊小贩,其实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大桥其实更为固定、清晰,但它通向的是一个我没有丝毫把握的地方。我徒然地羡慕着在上面自如穿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年岁与我相仿的小孩。他们有的牵着大人的手或跟在其身边,有的是几个结伴同行,有的则孤单地走着。最后一类让我格外注目,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那个理想中的我。我长久地凝视着他们的背影,有时暗自希望当中的某个回过头来,向我招手,这样我会迅速奔过去,顺便也上了大桥。但没有谁向我回首致意,这愈发印证了对河于我的彻底陌生:那里没有一个亲戚,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看清这点,畏惧和向往的感觉同时加深。
我问妈妈,有没有带我去过对河?她不明白我为何会提这个问题,但见我的表情空前严肃,显然不能敷衍作答。凝神回想了片刻后,她摇摇头。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失望。我又问她去过对河没有。她当然去过,而且很早的时候就去过,那时大桥还没有修起来咧。这个无意中泄露的真相让我大吃一惊。我本以为大桥五百年前就横在那里了。我赶紧追问,桥是什么时候修起的?妈妈说,刚好是你出生那一年。原来雄伟神秘的大桥竟是跟我同一年来到这个世界的,这让我怅然若失,以至于忘记了问妈妈那时候去对河做什么,没有桥又是怎么过去的?
也就是在这一天,朱兵兵告诉我,其实对河跟我们这边的分界不是桥头,而是桥中央,我们跟对河的人其实各占桥的一半。用不着他发誓赌咒,我已经信了。朱兵兵有个亲戚住在对河,是他爸爸那边的亲戚。尽管他妈妈不爱搭理这门亲戚,但终究否认不了他家跟对河的关系。所以关于对河,他的任何说法,在小伙伴中都是有权威性的。更何况那么长的桥,又是我出生时修的,凭什么让对河的人全占了去?面对我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的相信,朱兵兵发出了邀请,星期天一起去对河玩。我晓得他那个亲戚自从被他妈用冷饭招待过一次后,很久没有上门了,而朱兵兵非常挂念他做的麦芽糖。街上随处可见卖麦芽糖的,但没有一家有他亲戚做得那么好吃。朱兵兵曾经慷慨地分了我小半块。透着醇香的甜,吃着不腻,软硬恰到好处。确实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麦芽糖。我点了点头。
那个星期天我并没走到对河。一路上朱兵兵兴奋地说个不停,口水屡屡溅到我脸上。但他说得越多,我就越感到他心里其实没底。我甚至怀疑他并不记得亲戚到底住在对河哪里。他所能确定的是,对河街上。再具体一些,就是,离供销社没好远。此外便不能说得更详细。他起劲地描述亲戚家支着口大锅的后院和摇着尾巴的小黄狗,反而让我觉得这一切变得虚无缥缈起来。我甚至觉得他滔滔不绝的样子有些可怜和可笑。但这并非我没有陪他过桥的主要原因。上桥的时候,我既没有超前也没有落后,和他并排迈出了那一步。脚步落在桥上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随后就是长风从江面吹来拂过耳际的声音。虽然我们称那边为对河,却把它叫作江。这确实是条大江,又宽又长。它是从苗疆的山岭间流出来的,到了我们这里,还只能算上游。苗疆的那两个县,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中,都显得异常遥远、偏僻,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跟它却都在这条江的上游。那么,这条江不晓得还要过多少道滩,拐多少道弯,才能走到中游,奔向下游。这种长度远远超出了当时心灵的容纳范围,我只有尽量避免去想象,甚至不敢把目光投往下游方向。我努力望着前方。桥面辽阔,只有零星的单车或缓慢或快速地驶过,我和朱兵兵却老老实实地走在桥边的人行道上。越来越接近中间了,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其实并没有一条准确的线摆在那里,我只是凭着目测加感觉。拉开五六步的距离后,朱兵兵才意识到了,回过头来,嘲笑我慢得像乌龟。也许是这嘲笑使我改变了想法。往前走了三步,我告诉他,我不过去了,就在桥上等他回来。朱兵兵脸上的疑惑跟早上的雾气一样浓。他劝了我好一阵,我却只是摇头。后来他横着眼睛说,我要到那里玩很久的,还要在他们家里吃饭。我说,我讲了等你就等你!起码等到太阳落山!我的声音又大又坚决,充分表明了我其实是个讲义气的人。至于为什么不肯过桥,我自己也说不清。朱兵兵也没有问,只是气哼哼地说,你等就等喽。扭头往前走了两步,他又回过头来说,等着我,给你带糖来。我又一次大声说,你放心呢!我就在这里!
望着他窄窄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黑点,我心里到底生出些愧疚来。其实我明白他很想我陪他过去。但那道无形的边界线拦住了我。边界线那边有他的亲戚,而我没有。也许我一开始就只想走到这条新的边界线。大桥的一半已足够长足够宽,这新的领地能让我暂时心满意足。我踩着栏杆底,双手攀住上面的横栏,探出大半个头。江面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漩涡。看得久了,每一个漩涡里都仿佛有一只手伸出来。这种幻觉把我吓了一跳。赶忙闭上眼睛,过了好一阵才睁开。还好,漩涡只是漩涡,而且离我那么远。漩涡下面有另外一个世界。至少我晓得江里面住着可怕的水猴子,最喜欢把小孩拖到水底。这是大人说的,他们以此告诫我们不要到水里去。当然,大白天在岸上还是安全的。如果是夜晚,水猴子们会成群结队到河滩上来乘凉,那时连岸边也不能去。据大人们描述,它们浑身长毛,眼睛发着绿色的光。这种形象让所有的小孩都不寒而栗。当然,它们也不是没有弱点,只要有阳光,它们便不敢现身,只能躲在水里。我抬头望了眼太阳,阳光虽然淡,但终究让我感到安心。
目光回落的时候,很多条巨龙从远处游了过来。双手一软,我差点一屁股坐在桥面上。透过栏杆的间隙,那些巨龙缓缓地然而又无可阻挡地游过来。我想大喊,喉咙却紧张得发不出声音。左右扭头看了看,两边都有人走动,这让我放松了一些,镇定了一些,目光中的景物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那是木排,前后相接,左右相连,从天际慢慢地爬出来,探入水中,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更近一点,便能看到排上还搭着一痕一痕的棚子,每组排上都有两三粒人。过县城这段江又开阔又舒缓。等人影越来越大的时候,排也越来越慢,最后靠边停住,然后一条一条的木板伸出来,搭在滩上。排上除了留下看棚子的人外,其他人都上了岸。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排都停在我们这边。这意味着即使是远方的放排人,也明白我们这边才是繁华好玩的街上。我想他们应该是从苗疆来的。这么长这么大的排,得砍多少根树才能扎成。只有全部是山的地方才一次拿得出这么多树。排停在半边街到老码头一带。我只要往回走到桥头,再下一道坡,走过采沙场,就到了半边街上。半边街建在高地上,在土坡上还砌了许多层青石块。虽然从街边一跃而下就可到河滩上,但太高,估计只有城里最猛的好汉才敢这样做。至于从河滩直接蹦到半边街上,那恐怕只有霍元甲陈真燕子李三才做得到。不过半边街只有四五百米长,那一头就是老码头。只要再花费几分钟,便可沿着老码头长长的石板路下到江边,到木排上去看一看。但我并没有挪动脚步。我跟朱兵兵说好等他,就一定会在这等他。就算要去木排上,我也会等着和他一起去。他在木排上肯定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完全和我一样,那样子我很乐意。
那天我没有等到朱兵兵。我眼睁睁地看着占据了半个江面的排重新游动,分别穿过三个巨大的桥洞,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全部过去。我看清了棚顶上当瓦盖的树皮,还发现有几张排上蹲着黑色的大鸟,它们居然不会飞走,而是像蹲在自家的门槛上,悠闲地打量着江水,似乎想发现些什么。我明白这些排、这些人,会一直漂,漂到下游的尽头。只要稍微想象一下那种遥远,我的心就变得又酸又软。所以我没有跑到桥的那边,目送它们消失在拐弯的地方。对于我那时微小而脆弱的承受力而言,对河这么远的距离才是适合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凝望它,揣摩它,一点一点去接近它。这天我来到了桥的中央,完成了重大突破,已经足够满意。等太阳完全沉入江中,暮色四合,到了水猴子出现的时候,我就撤退了。我想等到这个时候,够意思了,朱兵兵没有什么好怪我的。
朱兵兵没有怪我。事实上,他绝口不提那天的事,当然,也没有给我麦芽糖。后来我想,他可能没进他亲戚家,或者是没有受到欢迎,所以灰溜溜地从桥的另一边回去了。我并不感到失望,甚至有种隐秘的欢喜。我其实有些嫉妒他跟对河的联系,现在释然了。至于大人,我倒很乐意听他们和对河的往事。但大人们并不怎么在意对河,他们喜欢谈论街上或单位里的事。对河虽然有条街,却没有谁觉得那是街上。既不是街上,也不是乡里,那就只能是对河,这是它唯一贴切的名字。
我终于记得去问妈妈当年是怎么去对河的。妈妈说,坐船去的。在哪里坐呢?老码头。这不出我的意料。出乎意料的是,妈妈说当年大舅下放的时候,在对河打过铁。大舅可是我的偶像,头发很长很先锋的画家,居然在对河打过铁。这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瞬间觉得跟对河建立起一种曲折但坚固的联系。我无数次想象大舅光着膀子,站在对河街边铺子里打铁的场景。等过年大舅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缠着他打听当年的事。他哈哈一笑,说当年本想不下放到云南新疆,起码也要去苗疆那样的地方,结果下放到离城只有十多里的天福乡,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想办法跟着队上的人出来搞副业,到对河街上打铁,虽然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但学会了喝白酒。妈妈说,你还记得那年你差点淹死在江里吗?大舅更是笑得两眼放光。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我更加要问个明白了。原来大舅当年得空的时候,喜欢去江里游泳。他游泳的本领,同伴中没有一个比得上,尤其擅长栽闷子,栽得又深又久。有次他一个闷子栽进江里,等到浮出来时,发现头顶竟然一片乌黑。原来是上游放排下来了。还好他当时脑筋异常清楚,摸清了排向,横着游向岸边。这口气憋得空前的长,等到终于能探出头,整个人几乎虚脱。上岸后,躺在草地上睡到太阳快落山,才能爬起来走回去。大舅说,如果当时慌了神,没搞清方向,那就真的游不出来了。我想象着木排那几乎没有尽头的长度,心里发颤,再看看大舅神采飞扬的脸,更添崇敬。如果大舅提出去对河看看,我一定会跳着陪他去。但他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接下来忙着接待陆续前来拜访的老朋友和城里的艺术青年们。这让我有说不出的失望,却又不敢表露出来。老朋友和艺术青年们都向他打听北京的美术界动向,对河这种地方的事,压根儿不在他们的谈论范围之内。我听了一会儿,就闷闷地走开了。但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更了解大舅的对河往事,显然也加深了自己跟那个地方的关系。
此后我在城里待得腻了,便会去大桥上站一站,望望对河,也望望江的上游。如果正好碰上放排,我会站上许久,直到排全部穿过桥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去排上转一转,却总是没有迈开那一步。也许是每次都想着随时可以去,不急着这一次,也许是跟我的天性有关。对于引起憧憬的事物,我总爱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这距离只是一指长。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憧憬并享受这种憧憬的美好。我似乎害怕一旦真的接触,会发现事物不像我憧憬的那样。为了逃避这种失望,我宁可长久地逡巡在那条临界线前,哪怕只需轻轻地再往前挪动一小步就能触到。应该是这样的,否则无从解释当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为什么没有过桥。但我也并非完全没有行动。我一点点地把独属于我个人的边界线往桥那头推。每次推进几米,便觉得此行有了收获。成绩最大的一次是推进了十几米,但这反而让我忐忑,迅速撤了回来,并立刻后悔这次走得太远了。虽然只是一点一点推进,虽然大桥在我的感觉中,好像跟排一样长,但有一天我终于站在了桥尾,只要再跨前一步,就会踏上对河的土地。那一刻我突然生出悚然之感,转身迅速往回跑。跑到桥的中间,心才安下来。在这个位置,即使有人拽我,或者在后面推上一把,我也不会踉跄着踏上那块土地。我更习惯站在边界线这边,看着对河的人走过来,观察他们的穿着打扮、走路的姿势、说笑的口音。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又有那么点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对河的人。看得久了,看得多了,我总结出对河的男人比我们稍微显得土气。这种土气并非因为打扮得不时髦,相反,对河很多青年比街上的人穿得更加街上。飘裤、花衬衣、蛤蟆镜、电子手表,街上的青年还没怎么穿戴他们就亮出来了,但就是因为太使劲、太刻意,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对河身份。但对河的女人更好看。或许是因为她们笑起来更明朗、更放肆,或者是因为她们脸上的红霞更鲜艳、更润泽,总之,有种让我怦然心动的新鲜感。我靠在栏杆边,等着她们走近,有时从我身边擦过。我闻到了她们身上的气息,散发着自然的芬芳。她们比城里的女人更接近田野和青草,又不像乡里女人那样成天陷在牛粪味里,所以,这样的气息是最好闻的。我最喜欢看那些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她们比城里的女孩似乎要腼腆一些,又似乎要大胆一些。她们见我傻傻地站在桥上,总是用又黑又亮的眼睛深深地瞅上一眼。回来的时候如果发现我还在,又会瞅上一眼,仿佛在问,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呀?如果我胆子大一点,跟她们攀谈,她们也许会在短暂的羞涩后,叽叽咯咯地告诉我想知道的关于对河的一切。但我只是傻傻地看着她们走过,用眼睛映照着她们可爱的脸。我那时拥有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还有一张清秀得像女孩子的脸,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油腻狰狞。舅母曾打趣说我像欧阳奋强,长大后跟小时候完全不同。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徒然地伤悲。但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好看,或者对此毫不在乎,从没想过要利用这点。我只是感到女孩子们愿意跟我玩,这让她们愉快,也让我愉快。但那时有那么多对河的女孩子从面前经过,我却没能上前一步,结识当中的任何一个。那时我们都还是祖国的蓓蕾,美丽的欲望含在内心深处,自己都看不清楚。那时我只是老老实实站在桥上,认真又茫然地看着这一切,任清澈缓慢的时光从身上淌过。
大约是十岁左右,大人认为可以带我去江里洗澡了。尽管男的会肩着汽车内胎当游泳圈,年轻或不那么年轻的阿姨们会在江边换上蓝白相间的泳衣,大家还是管这叫洗澡而非游泳。这是整个炎天县城人们的盛大节目,从六月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四个秋老虎完全消隐。对于上学的小孩而言,幸福的时光没这么长,他们只能在暑假期间跟着大人前去参加这集体的狂欢。也并非每个家长都这么开明,于是有些小孩会趁家长上班时,顶着巨大灼热的太阳,结伴偷偷前往。因为耳朵进了水,回来时一路单脚侧头蹦跳。运气好的在路上能把水倾出,运气不好的到了家里还在摇头晃脑,难免被大人觉察,挨上一顿痛骂或是“笋子炒肉”。运气最不好的便永远埋葬在江水中。每年城里都会发生几起这样的溺亡事件,被大人们反复引用,告诫我等不要偷偷下河。我一方面喜欢独自游荡,有着惊人的倔强和不张扬的野性,另一方面又是个听话的小孩,至少父母和老师的话都会刻在心上,而不像有些小孩子那样,把它们当成耳边风。所以我从来没有偷偷去江里洗过澡,充其量只是在工厂澡堂的水池里扑腾一阵,喝上几口真正的洗澡水。但对山与水的向往是每个人的天性,因为人类是从山里走出来的,而在这之前,那些源头性的生物是从水里爬到陆地上来的。回到水里就是回归最初的源头。这种天性隐秘又强大,驱使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带着莫名的欣喜奔向水中,即使不会游泳,扑腾几下也会感到畅快。所以听到大人的允许时,我根本就坐不住了,在堂屋和里屋之间不停穿梭,焦灼地等待他们准备停当,根本没去思考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边的江,水要深许多,水面下藏着不少凶险的大漩涡。城边临江的地方,不是高坎就是泥滩,只有老码头以人力加青石板砌出一条并不宽敞的通道。而对河那边的江岸,有大片大片平坦的鹅卵石滩,或者舒缓的草坡。最关键的是,有段一里多长的区域,快到江面三分之一的时候,还是浸不到大人的肩膀。这个地方自然成了天然游泳场。即使不会游泳,在这里也是安全的。那些泳技精湛或自以为精湛的男人们,把女人和小孩留在这里练习游泳或玩水,自己可以放心地往江心游去。也就是说,我要想参与这期待已久的戏水盛宴,必须到对河去。当我快看到桥的时候,陡然意识到了这点,蹦跳着的脚步立刻缓了下来。但大人们没有注意到,他们谈笑风生,依旧阔步向前。小伙伴们也领会不了我的心思,只顾着叽叽喳喳。我们是和邻里要好的两家一起出动的,阵容浩大。尽管心生犹豫,但我被裹挟在集体的步伐中,无法逃离。实际上,我也不想逃离。前面的诱惑太大,而且,回来的时候,离桥头只有十几步远的冰厂门市部,还有爽口的冰绿豆沙等着我。如果我溜掉了,不过是令大人少出两毛钱而已。只是这显然并非我想象中的第一次去对河的方式,但到底怎么去,我其实也没怎么想好。在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准备的时候,就到了大桥的另一头,然后,踏上了对河的土地。这是一条毛马路,不仅坑坑洼洼,还夹杂着许多探头探脑的石头。但仅仅是走了两三步,大人们就拐向右边。我松了口气,又夹杂着丝丝遗憾,跟着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狭窄的青石阶梯走下去。阶梯连着田埂。田埂左边是青中透黄的稻田,右边是缓慢下倾的草坡。草坡横连着宽阔的鹅卵石滩。看到更辽阔的江面,我复杂的心绪顿时变得单纯和明朗起来,带头欢呼着奔向鹅卵石滩。
那天傍晚的时光仿佛一瞬间就滑过去了。当夕阳洒落最后一把碎金,风中也开始透着凉意,我站在水里,突然有些恐惧。那些成群的水猴子会不会突然冒出头来?但江边依然热闹,不少大人还在江心施展他们的泳技,看上去他们一点也不担心水猴子的事。我不能说出我的忧虑,只悄悄往岸边挪动了几步,待在水深及腰的地方。这样就算水猴子出现,我也能够迅速跑到岸上。头顶的蚊子越来越多,它们远没有水猴子那么可怕,但让我感到厌烦。深吸一口气,再次把全部身体扑进清凉的水中。我不会游泳,只能以这种方式短暂地漂浮。等到憋不住的时候,方从水里站起来,抖落满头满肩的水珠。
天快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上了岸。妈妈和阿姨们再次在草坡上那棵大树下展开床单,轮流换好衣服。走到阶梯顶端,我扭头望向右边,那里街道寂静,许多昏黄的灯光凝固在大大小小的窗口后。那些灯光映照着一些陌生的人和陌生的事,我却来不及去探究,便被大人们带着上了桥。就这样,我来了对河,却又像没有来过一样。等到坐在冰厂门市部的冷饮室,喝着那碗闻名遐迩的黏稠扎实的绿豆沙时,我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进入对河,只不过是去江里洗了个澡而已。
此后许多回,我都以这种方式擦过对河。渐渐地,我把整条江都看成是我们这边的。我始终没有学会游泳,连笨拙的狗刨也没有,唯一的长进,是在水中憋气的时间长久了些。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年轻阿姨或大姐姐们白嫩的长腿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潜入水中。我试图着靠近。但不管我靠得多近,这些长腿是属于那些同样年轻的叔叔或大哥哥们的。他们无所顾忌地托着这些散发着迷人光泽的身体,指导她们在水中摆动长腿,有时突然放手,惹出一串串清脆的叫声。他们偶尔也顺便摸摸我的脑袋,仿佛是对我辛苦潜水而来的犒劳。这种漫不经心的大度反而让我生气,后来我尽量避开这些沉浸在欢乐中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往人迹相对稀少的上游方向走上几十米,再顺流漂下来。我已经不担忧水猴子的事,甚至开始怀疑它们到底存不存在。水里只有长长的油滑的草和同样滑手的鹅卵石,还有无数的螺蛳和细小的鱼。有时我站在水中,呆呆地望着远处夕阳,明明不远的打闹声和欢笑声却仿佛离我很遥远。孤独的感觉原来是在热闹中产生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不自觉地品尝到了它的滋味。后来我又想到,其实对河的人们是孤独的。他们孤独地活在那块狭窄地带,既不能真正融入城里,也无法回到更广大的乡村。但它的独特魅力,也源自这种两边不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获得了一种边缘性的自由。在这样的地方长大或生活过的人,懂得如何在严密的社会组织构架中,获取这种自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