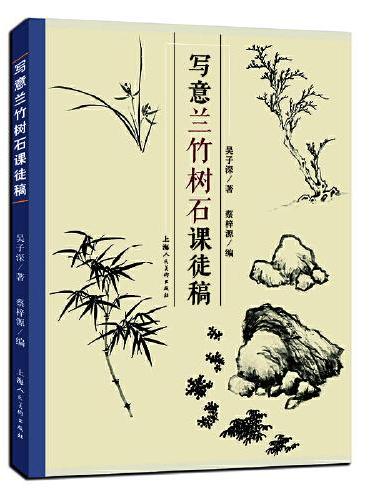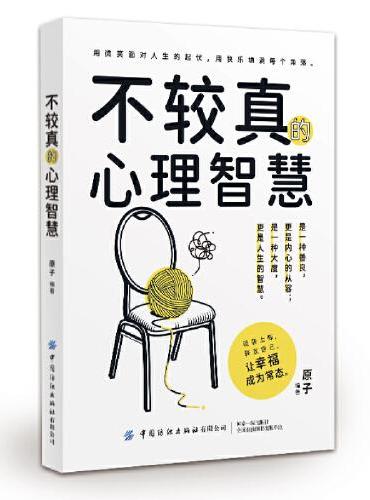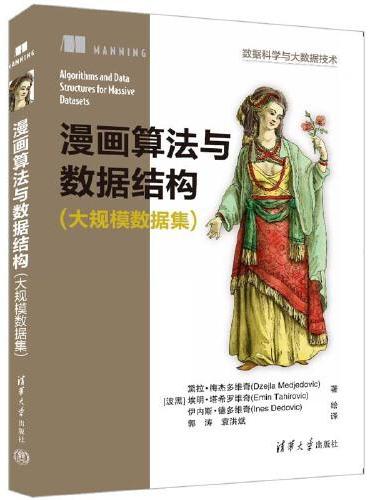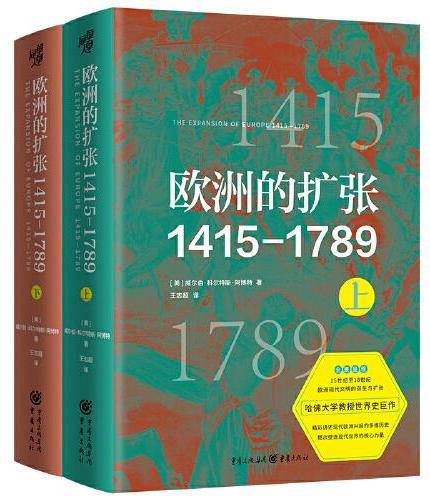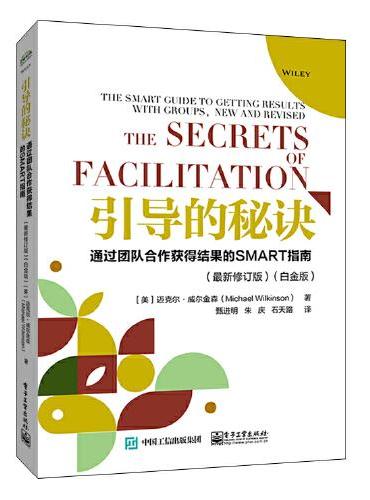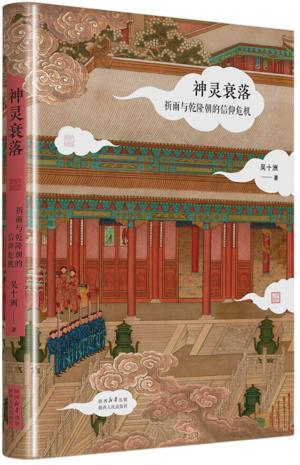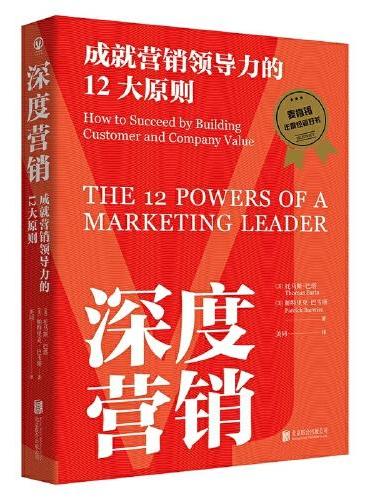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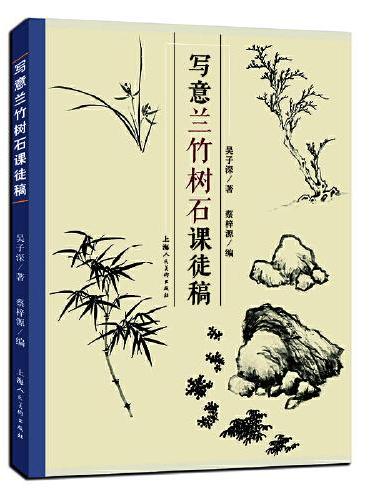
《
写意兰竹树石课徒稿
》
售價:HK$
1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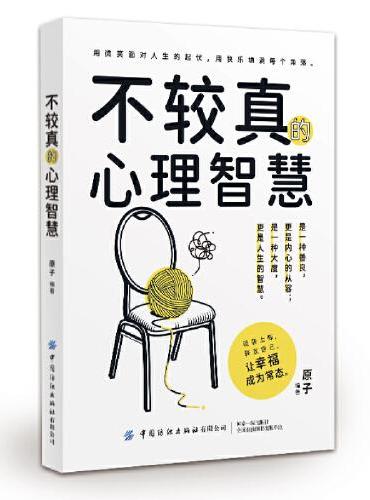
《
不较真的心理智慧
》
售價:HK$
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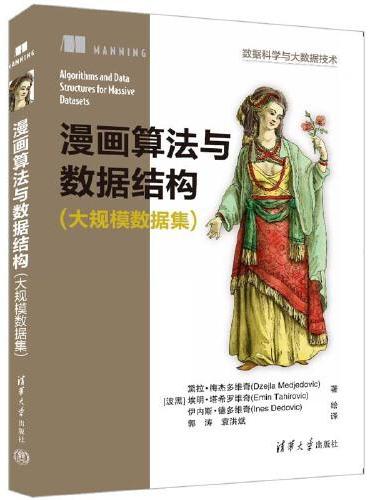
《
漫画算法与数据结构(大规模数据集)
》
售價:HK$
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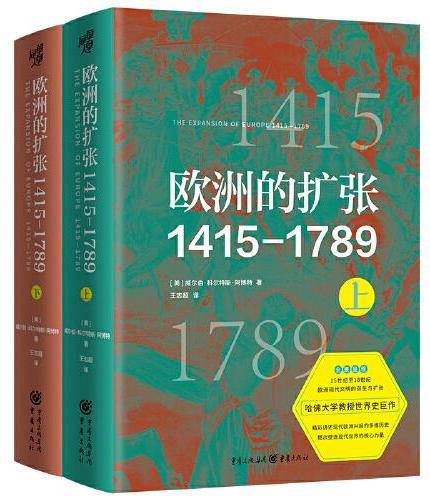
《
欧洲的扩张1415—1789:现代世界的奠基
》
售價:HK$
1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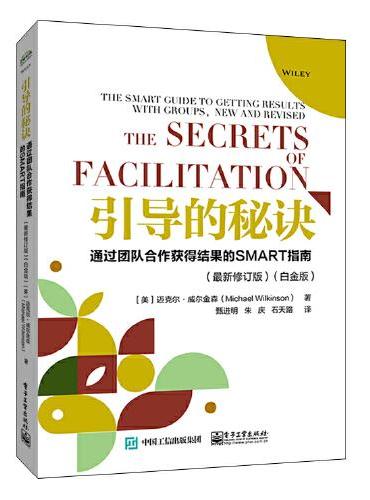
《
引导的秘诀:通过团队合作获得结果的SMART指南(最新修订版)(白金版)
》
售價:HK$
118.8

《
文史星历:秦汉史丛稿
》
售價:HK$
1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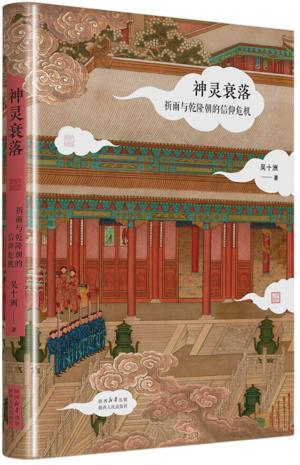
《
神灵衰落:祈雨与乾隆朝的信仰危机
》
售價:HK$
1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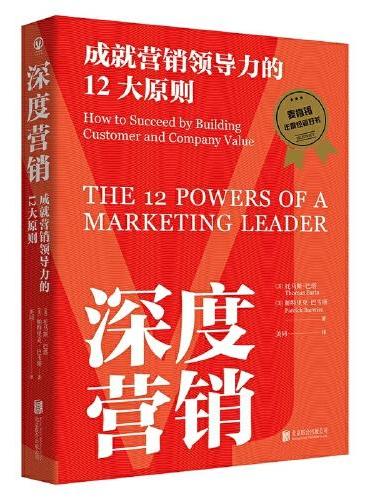
《
深度营销:成就营销领导力的12大原则(麦肯锡年度经管好书,12大原则揭秘营销本质,带好团队就是从领导力到影响力!)
》
售價:HK$
69.6
|
| 編輯推薦: |
|
本书辑录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从正身旗人到为人奴仆,从普通平民到没落贵族,均囊括其中。扎实、精彩的访谈材料使得本书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具有很强的史料与研究价值。
|
| 內容簡介: |
本书辑录了十六名满族老年妇女亲口讲述的个人经历。是作者将口述史方法纳入历史研究所作的一个尝试。访谈主题集中于这样三点:
1、相对汉族而言,这些有着旗人背景的妇女,对于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的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
2、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状况与族际通婚情况。
3、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妇女的家庭变迁和个人的生活经历。
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弥补以往文献资料的不足,并为族群和社会性别的研究,寻找新的角度和层面。
|
| 關於作者: |
|
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48年12月生。先后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获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专业为清史、满族史。著有《清代八旗驻防研究》、《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人合作)等,有关口述史的著作有《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下集)与《口述史读本》(与人合作)以及数十篇相关的学术论文。
|
| 目錄:
|
目 录
一、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
祁淑洪女士访谈录...... 1
后续访谈:胡同里的姑奶奶...... 16
李清莲口述...... 17
胡秀清口述...... 46
吴效兰口述...... 67
张国庄口述...... 81
二、我什么光也没沾着
爱新觉罗毓臻女士访谈录...... 98
后续访谈:守坟的四品宗室...... 110
金秀珍口述...... 111
金竹青口述...... 121
金恒德口述...... 131
三、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
张寿蓉女士访谈录...... 136
后续访谈:再访金鱼胡同那家的后人...... 147
张寿椿口述...... 148
蒋亚男、蒋亚娴口述...... 162
四、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
鄂凌英女士访谈录...... 182
五、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
胡福贞女士访谈录...... 191
六、您说我们家封建到什么程度
赵颐女士访谈录...... 211
后续访谈:清华园边内三旗...... 225
司文琴口述..... 225
七、什么事都要做到头儿
吴淑华女士访谈录...... 238
八、我什么活都能干
高引娣女士访谈录...... 251
九、我俩这辈子挺好的
孙宝芝女士访谈录...... 258
十、谁知道他们咋就通婚了
景双玉女士访谈录...... 263
十一、最值得回味的生活是在那三个工厂
刘澈女士访谈录...... 274
十二、你要想过好日子就别闲着
赵秀英女士访谈录...... 285
十三、到沙漠上来了一直没受罪
白惠民女士访谈录...... 307
十四、我就不愿听满族不好
安荣华女士访谈录...... 318
十五、不受点灾难,一生就白活了
文毓秋女士访谈录...... 325
十六、那清绪女士的五封信...... 342
附表1...... 366
附表2...... 367
主要参考文献...... 370
|
| 內容試閱:
|
一、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
祁淑洪女士访谈录
时间:1997年11月13日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淑洪家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您是让我说我母亲、我们家里的事是吧?我姓祁,属狗的,民国十一年(1922)生人,75周岁了,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原来我们在东城北池子住,属正黄旗。我妈说旗人都是东北过来的,根儿都是东北的,来了就跑马占地1,我也不懂得这句话。我为什么没报满族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还说这老旗人没多大意思。
1.我母亲
我妈挺开朗的,我父亲常说:别瞧我比她大11,她什么都记得。她文化大革命时死的。我哥哥在地质部工作,他过去当过督察,文化大革命时因历史不清楚,1966年7月被轰到山西朔县,我妈受他的连累,也跟着去了。她是老北京人儿,觉得挺狼狈的,说:人家那儿都有穿夹的了,我们还拿把大芭蕉扇,可现1了,谁都瞅我们。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我妈要活着,这会儿算起来也该一百多岁了。
我妈老和我说,说得还怪可乐的,说:你们多好呀。有父母,我从小就没父亲,跟着你姥姥,受多大罪呀,从小就订了婚,你爸爸有什么能耐呀。
我妈说我姥爷特精,她那会儿就是我姥爷教的,《三字经》,《百家姓》,什么《女儿经》,都念过。
我姥爷入过义和团,穿着黄衣裳,好像有什么妖术似的,指哪儿就着哪儿。特神气。光绪二十六年(1900)我妈跟我姥姥逃难的时候我姥爷还在。
我姥爷是痨病死的,那会儿我姥姥才32岁。我妈十几岁,我姨四岁,我妈比我姨大11。我姥姥就生了这俩闺女。她没有什么亲戚好友,守寡也没有主张。就净上我父亲这家来,求我们家帮助她关俸银、俸米,因为我姥爷那会儿跟我大爷他们都是朋友,莫逆之交,俸银、俸米什么时候不关了我可说不清。反正我姥爷死了以后我姥姥说这大家庭挺好,就求这儿吧,我妈说她那会儿才十几岁。有一次我姥姥就说我带着你串个门儿去吧,那会儿到人家还得叫婶婶大妈呢,我二大妈那人比较爽,就是没心眼儿,她就紧盯着我妈,摸摸我妈的辫子呀,看看呀,我妈比起我姥姥来就挺精的,回去就说:妈(那时我家就改叫妈,不叫额娘了,不过我妈结婚以后,这边还是管妈叫额娘,管爸叫阿玛),我可告诉您啊,我可不给1老祁家,您可别跟我身上打算盘,他们都比我大。我父亲还比她大11呢,她那些哥哥嫂子们可不是更大了么:您求他们关钱,您可别拿我还愿。我姥姥就说: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带你串个门儿。我妈那年才16,果然是到19岁就聘了,我姥姥说:给的这婆家挺好的,我又没儿子,就你和你妹妹,我就依靠你了,我就希望给你找个大家庭,我也有个照应。我姥姥那会儿不是孤单么。
这边儿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加我妈是妯娌仨。我妈不是去过吗,结婚时一拉盖头,一瞅,果然是那家儿。那会儿结了婚,得坐到第四天才能回门,我妈回去就和我姥姥闹,说:果然你把我给了老祁家了,你看他那哥哥嫂子多精啊,就他傻,怎么把我给他!其实我父亲也不傻,他就是憨厚,老被人家欺负。看我妈又哭又闹的,我姥姥就说:那反正也把你给人家了,还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了。我妈后来就和我说:要是你姥爷活着呀,高低也不能给他们家。老祁家哥儿仨,就他最小,又没本事,就他是步营。
2.祖母一家
老祁家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爷那会儿干吗,哥儿仨之中长子掌权,由我大爷过日子。他没儿没女,也没营生,一辈子身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篮,我奶奶死后留下点钱,他老是坐吃山空,就靠卖家产,卖一点吃一点,吃了十几年。我妈常说:那会儿你奶奶留下的一点钱都让你大爷给放了秃尾巴鹰了。秃尾巴鹰就是放了债一去不复返,让人给坑了。我大爷得的是喘病,才四十来岁就死了,死时满口的牙都没掉,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
我二大爷比他强点,是个小排长什么的,那会儿照的相身上还带着刀么,后来是做小买卖。他有三个姑娘。我到今儿记着呢。他俩好像都比我父亲强,挺精的。
我们那时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黄带子1,那时候打官司,都不跪着。我奶奶60岁就死了,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旗人就老把着自己的孩子,没出过门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出。我父亲那会儿当步营,头一次是开往廊坊。按说是挺近的,一听儿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东家去,西家去,告诉人家说我这小儿子要走了,上哪儿哪儿。晚上回来她就紧痰,就死了,刚刚60,你说,就为这事儿!我父亲也就刚到那儿,那功夫人家就告诉他,说你母亲死了,他就折回来了。
我妈嫁过来时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块,就属我妈小。她怀着我哥哥要生还没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后来又搬到西城的鱼雁胡同,我就是在西城生的。我母亲不同意搬西城,她说穷西城,干点什么都不发展,东城那边守着东安市场,抓挠点生意都好抓挠。到西城什么也别打算做了,穷。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了主。我大妈乐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买的这西城的房是我大爷的钱,一个院儿,那时还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爷当家。五间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三间,两边耳房是我二大爷住。那时候生活比较好一点的家家都有葡萄架,还有十几盆石榴,一边八盆两溜,我记得我家比我婆家强,摆设都挺好的,还有冰箱、条案、八仙桌,每天还要窖冰。一边一个立柜,还有柜塞子,搁着钟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后来分家才把这些卖了。我大妈的屋比我们屋更好点,都是榆木擦漆的,红的。亮着呢。我妈这屋就黑了吧唧的,搁着大躺箱,可能装东西了。自从鱼雁胡同的房卖了,就把家具也都卖了。没地儿搁了。
住西城那房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单吃了,有老太太活着能够团着,老儿子得益,没有奶奶,没人过日子了,哥儿兄弟就不成了,没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过了。哥儿仨谁也不管谁,我妈也吃了不少委屈。我们就搬到对门那院去了,还是鱼雁胡同,我大爷跟我们隔着一堵墙,挨着。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几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儿结的婚。
我父亲结婚时30了。那会儿男的结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农村的早。到城里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亲因为是步营,挣的钱也少。我妈说就是他那会儿勺道1,就是不严肃的意思,岁数大了还像小孩似的,爱跟孩子一起玩,没个大人气,没正形儿,又搭上没能耐,就没人愿意把姑娘给他。
我父亲就是步营,他上哪儿吃俸银俸米去?民国二十六年听说把外国也打得够呛,咱们北京旗人都练武,哪个都讲武术。大爷二大爷都会,别看干活懒,这都不懒。我父亲考步营,也是凭拉弓考的。我大爷他们都养活鸟儿,没事儿就拿着鸟笼子,去茶馆喝茶去。见天儿得花十几个子儿,挺爱议论各种事儿的,买鸟儿也不少钱呢。我妈说是有人出主意什么也不让这伙人干,就养着这伙人,实际是害了这伙人。我大爷、二大爷都念了十几年的书,到我父亲他又傻,小时候又出(天)花,有细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学了。
后来步营就没啦,散了,那时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亲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把脚崴了,我妈说从那他忌了酒。
步营散了,我父亲就做小买卖为生。做买卖也不容易。过去都讲究俸银俸米关着,皇上养着,到没地儿拿钱去的时候,喊也喊不出来,比如卖糖葫芦,叫不出这糖葫芦的名儿来,顶好的也就在墙旮旯没人的地方喊一声,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碜,也不容易,哪儿像现在的年轻人,多能喊啊,捯饬得多漂亮,都能喊出来。
那会儿找工作特困难,穷人太多,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们管他们叫豆皮子。他们来到咱们这儿,就特鬼,特机灵,咱们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了。从他们来了,买东西都拿着秤,差一点都不要,咱们北方人、旗人穷大方,没有跟人家争过,给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亲先做买卖,后来我姨给他找了个工作,在政委会当茶役,提个茶倒个水的,我父亲就说:别瞧我做买卖,但是我是掌柜的,我给人拿东西,这侍候人的事我还真不行。那会儿当茶役的都得给职员打手巾把儿,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拧成团递给人家,有那好的职员就说:老祁,看你这样儿,你也没外头工作过,我教你怎么递,你得把手巾抖搂开了,这么递。我父亲几次回家都说我不干了,干这侍候人的事我觉得特难受,我还是做我那买卖吧。我妈就说,如今孩子们都大了,再做小买卖人家都瞧不起你。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呀,你就做着去吧。做了几年。日本在北京八年,胜利又是四年,我哥哥就说别干了,在家吧。我们房后头打出去一间,开一个小铺,我父亲说待着也是待着,正好挨着扶轮学校,卖点小孩吃的东西,卖点烟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样维持生活。我哥哥那会儿也工作了,孩子们也都大了。
3.哥哥、姐妹和我
我们这屋里头,就我父亲傻不是,还就是他有儿子。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八岁。我母亲27岁生的我,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共四个孩子,我从小过继给大爷屋了。那时候家里也挺苦的。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学校,叫求知学校,说是冯玉祥立的,在井儿胡同,我们在鱼雁胡同,都挨着。这学校能够白上学,不花钱,收完钱又把钱都发了,多好呀。1我姐姐喜欢上学,那会儿正好上五年级,家里就不让上了,她急得哭,家里生活逼迫的,家里还一个妹妹,她得看我妹妹。我哥哥也是在那儿上的,上的高小毕业。我不爱上学,没出息,也就上了三四年,说什么也不上了。我妹妹比我小五岁,她愿意上学,就供她上学,可她也是不成气候,她在三中,那会儿还算不错的,上到高二了,正好要上高三,解放军就在外头围城了,傅作义守北京城么。我妹妹正好那会儿得的病,重感冒改了肺炎。我哥哥还不错,那会儿没短给她花钱,给她打盘尼西林,特贵,有那么一盒,盒里就那么一点儿,就七块大洋,搁上蒸馏水,给她打,也花了不少钱,可是城都关了,哪儿瞧病都不成。最后她还是死了。
我妹妹死时我就二十几了,那会儿我妈死活不让我工作,说不能去。没文化上工厂也成啊,我们小时候有工厂啊,什么被服厂,澡堂子的女部也招,我记得我们同胡同的小朋友去了被服厂,我就也去了,去了一个礼拜就给揪回来了,就舍不得,说你要上工厂,就是非要找婆婆家了。
那年我28了,算晚的了,给外地人舍不得,怕不知道人家根底,只要不是城里头的,就都叫外地人。上海呀天津呀,都不给,乡下人更不给了,你想城里人能给乡下吗?想给本地的,又得旗人找旗人。给人家做小,说那人多有钱,那更不能够了,家穷死也不能。这就耽误着。后来还是我们这胡同里胡同外,这胡同出口过一个小街就是福绥境,就给的这个老头子。他也是在旗的,姓傅。他父亲也是步营,按生活我们家比他们家强。
我姐姐给的那家也是旗人,他们家在郊区,在圆明园那边住,我妈就说我姐夫他们那旗人呐,就不如我们,是什么旗我就不记得了,说:他们那旗人哪,特贫,啐口唾沫都得啐到砖缝儿里头。贫的那样,我都不知是什么意思,买点茶叶,都得挂到这儿,就是显摆1。
我嫂子家也是旗人,三姑左右都是在旗的,谁都知道,根本不懂近亲结婚孩子不聪明这一出。旗人一般不娶小,除非没儿没女,那也还得正太太发话。旗人的老规矩就是把孩子特看得重,宁可大人吃亏不能让孩子吃亏。穷人养娇子。我老头子到现在也扎着手什么都不会干。到现在也不成,像成敏插队,(其女婿的插话:老太太就不理解她(指成敏)为了那身军装和为坐火车这两件事怎么就能一走三年,连面儿都见不着。)没办法了,逼着你必须得走,这才让出去,但凡有一点地步,宁可自己少吃点,不能让孩子走,女孩子更不放心,简直是七个八个的不放心,那会儿急得我几宿几宿的睡不好觉。大串联(文化大革命时)我都不让走。
我叔伯姐姐也是在求知上的学,高小毕业。同学有给介绍个唱戏的,家里说那哪儿行,说什么也不能给,悄悄把定礼退回去了,就赶紧给她找婆婆家,给了一个教武术的,也是旗人。我妈就诳她,说把你给的这婆家呀这么好那么好,她以为就是(唱戏的)那家呢。把她诳去了,给了,结果不是。姑娘给婆婆家不能给唱戏的,不能给推头的。推头的得站着给人推,唱戏的你坐着听他站着表演。这都是下等人。这都是旗人的规矩。
我老头子是会计,他们也是哥儿仨。我嫁给他时他就有工作了,我们都是民国的人了。穿的衣服都和汉人一样了。我们也是在福绥境住。说的时候就说单过吧。我婆婆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听她讲过什么。也没在一块儿过,在一块儿也不提这个。
这都是解放后的事了,我们先搬到花市,那两间房特小,住了一年,我老头的宿舍分配下来了,又弄着仨孩子搬到白石桥这儿。我们搬来的时候白石桥这儿一片荒地,就一排房,住到那儿就能瞅着马路,全是砂石子堆着,砂石厂啊。头里就是大坟圈子,一米多高,都砌着,和尚坟么。那边儿是个小动物园,刚进来的动物就在那儿训练。我说我下乡了,搬城外来了,觉得在城里住买东西多方便呀。
那时候城里住的人,像我嫂子她们就都有工作了,城里头成立街道,我这儿出来就是大石头子儿,哪有商店呢,就甘家口商场那会儿才刚盖。我搬来才盖天文馆。
4.旗人的生活
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那年我妈4岁。解放后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我妈离得近,就来瞧我。她说一看二里沟,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她说:我来过这儿,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我说: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她说: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抱着我,我记得就是这点地方,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我就闹,说奶奶(那时候管妈叫奶奶)咱回家吧。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熏死了。那时这边都是马棚,养的马,旗人都兴骑马。
我父亲那年15了,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那时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就都没回家,那时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我奶奶就说,他们不回来,可能让外国给杀了,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那家子也冒烟了,都殉死了,咱们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亲本来就有病,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抽风,也没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没了,他死就死吧。那会儿都住的大炕,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耷拉着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样也不管,家家都不活着了,都要点火了,我父亲才15。他就说:奶奶别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烧死多难受,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正央告的工夫,我二大爷回来了,打着一个日本旗子,那会儿说不让过人,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就叫门,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我们就当故事讲。
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就不活着了,要到那儿上吊去。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外国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让给祸害的。就说咱们这官园,地方脏着呢,咱们的人也死的多了,特别是旗人,外国人也死的多了,都堆在那儿。那会儿就听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就说旗人软弱,提笼架鸟。我妈就说是没能耐,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他们在西口,我们在东口,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我二大妈也到这儿聊聊,穷有穷欢乐。也没电视,点个小煤油灯,用一个碟儿,弄点棉花捻儿,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后来发达了,就点电灯了。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亲也有工作,就安的灯。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买木头杆子,自己埋,算不点煤油灯了,煤油灯点的鼻孔都是黑的。
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热闹着呢,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梳着美人鬏儿,骑着大马。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头子上朝呢,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梳着大美人鬏儿,在里头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就说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见了她也没礼貌,拖拉着衣服。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他死在前头了,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带着孝。
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袁世凯要做皇上,所以不许说元宵,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就说汤圆。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灭了是吧?
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从南小街出来,宫门口,锦什坊街,这个应该还有,白塔寺那条街。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鬏,那会儿旗人都(把头发)抄上去。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就梳后头的鬏了。我妈岁数小,想法就不一样,说梳那旗鬏干吗,像打着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头了,她说我没受过皇恩。我大爷就说,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我姐姐比我大,就梳过大辫子,跟唱铁梅的似的,打红头板儿。后来不兴扎了,就兴编辫子了,也是红头板儿。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必须都是红的。我那时梳俩辫儿,就扎了一个黑的,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花蝴蝶,一边插一个,我妈一把把我揪过去,抽冷子吓我一跳,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你看你看,黑头板,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
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1顶着玩呢,那时也不当回事,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走。一个架子,这么一个圆,铁丝的,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讲究梳真燕尾儿,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费劲呢。我姥姥就说: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每天三点多钟起来先梳头,这头就得占一功夫,真燕尾儿还得缝,得多大功夫!真要懒的话,睡觉就别打算躺着,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侧着躺着,支着。我说那受得了吗,多困呐,多受罪啊。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要娶媳妇,涂那大口红,就得挨一天饿,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这会儿有地方擦去,拿着个小镜子,那会儿不兴啊。
我妈就老说,你大妈捯饬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妈浓眉大眼,就是黑点。我二大妈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这大两把头,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来垮,就没我大妈好看。我大妈就合适,特有派。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长极了,都讲究戴着指甲套,是银的,保护指甲的,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你们都听过坐宫吧?戏上就那样,也好看是吧。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几双,都是自己绣的,女的都是扎花、绣、锁扣子,都是自己弄,绣出来,外边去绱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1什么的。都不兴买。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什么样儿,真好。
我大妈那时候,人家娶媳妇聘姑娘,轿子得过一火盆。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盖子。(参加婚礼的女人)一不能吃东西,二回来腿疼,都是这安请的,都讲坐下请,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且蹲呢,且起不来呢,慢功。我大妈老说,像你们这个,打醋似的,哪儿成啊。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一岁,他那会儿上学,不兴请安,我姥姥老催着他:上你大姨那儿去,别就那么一鞠躬,学着点,请个安。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这手进去,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大姨父,您新喜,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他没学过,不会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错了。(我爸爸)就说: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我姥姥那时候来了,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不请安她不高兴:噢,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没解放的时候,再怎么也得点个头,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到一年了,拜年。亲友都上这儿来,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兴。自从解放,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虽说我是旗人,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一不抽烟,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说爱喝茶,我喝点白水就得。我说我倒是省钱。
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最低也是两家,还都是老街坊,到今儿想来,女孩子不让串门子,不许站街,不许卖单儿1,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不像这会儿净搬家,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谁都知道谁。我大妈那时抽水烟,托一个吸管,铜的,这点地方搁烟丝,我管吹那个纸捻儿,那也得会吹呢。我大妈二大妈都抽,我妈不抽。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到年节来瞧瞧,进门先抄烟袋,坐到那儿,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妈就点上一袋烟,双手递过去:嫂子,您抽烟。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就那么敬奉。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叫你一声就不错。
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说,把这伙旗人都给他养起来,不让他干什么,就跟裹小脚似的,成残废了。冯玉祥来了才不让裹脚的么。旗人都是大脚,外地人才是小脚。总而言之,旗人的男的就是懒。冬天搁花得挖那窖,挖窖得找人挖,那自己就不能弄么?再说拾掇房,登高不成,男的那会儿都不能登高,害怕。墙倒下那么一小块都得找人,一是好面子,二是没学过,大事做不了,小事他也不做。
访谈者记
祁女士现在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她却是我访谈的几十名老人中,最有旗人味儿的北京旗人后代。而北京旗人正是八旗中人数最多、地位最高、影响也最大的部分。
1644年清朝入关,建都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将精锐悉集于京师,平时镇守中央,有事调集出征。八旗额兵二三十万,隶于京师的就有十余万之众。清廷在北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强令城内汉官汉民迁往外城(又称南城),经过顺治五年至六年间(16481649)的大规模清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人无论官民被一律迁出,内城从此成为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的聚居区。形成了清代京城独特的旗民分居格局。
清代的北京旗人,是根据所在旗分。按照八旗方位居住的,其具体方位是: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并在西方;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清廷还以皇城(紫禁城)为中线,将八旗划分为左、右两翼: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位于城东,为左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四旗位于城西,为右翼四旗。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之间设立栅栏,京城的九座城门均由士兵把守值勤,按时启闭,清廷还将明朝时建立在城内的会馆、戏院悉数迁出,严禁在城内开设戏园赌场,使整个北京内城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
为使八旗子弟职业当兵,以作为清朝统治稳固的基础,清廷不准旗人务农经商,使他们断绝了一切生计来源,而完全依赖朝廷的俸饷为生。八旗甲兵的饷米,都需从江南一带通过漕运送至京城,每年漕米的额数约为四百多万石,均贮于京仓之内。京城共计十三个仓,其中内城七仓,即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兴平仓、富新仓和旧太仓;还有城外四仓以及通州的中、西两仓。八旗饷米均由京城仓内放领,这对于如祁女士姥姥这样的寡妇来说,确有诸多不便,所以才有求人关饷,而以女儿还情之说。
居住于这种与汉人相对隔绝环境中的京师旗人,就这样陶冶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京城文化,这在满族著名作家老舍未完成的作品《正红旗下》中,有着真实和生动的体现。祁女士自述只上过几年学,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将她的口述与老舍先生的作品相参照,细品其中的同异,是饶有趣味的。
祁女士口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她的母亲。在上述记录中,祁女士谈到其母因受儿子(即祁女士的大哥)株连,于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1966年7月)即被遣送山西,此后如何没有再讲。据她的女儿和女婿所说,老人终因不堪此种羞辱而自尽,这是祁女士因伤心而不愿提及的一段往事。但此事却非常鲜明地凸显了老人那种自尊、刚烈的个性,恰与祁女士所述她平日的言谈作风相合。故征得其女和女婿的同意,补注于此。我在寻找满族老人作为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听到过不止一例像老舍先生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事例。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此话平时说来多为贬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却是这个民族特有的高贵和自尊,这在那些普通妇女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再不能与她们作促膝谈,实为憾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她们的敬意与追悼。
祁女士读了这篇整理稿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发议论说:满族人的末落(应为没落)状况,我的子女谁也说不清了。满族人的末落与其他民族不同,满族人名存实亡。特附于篇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