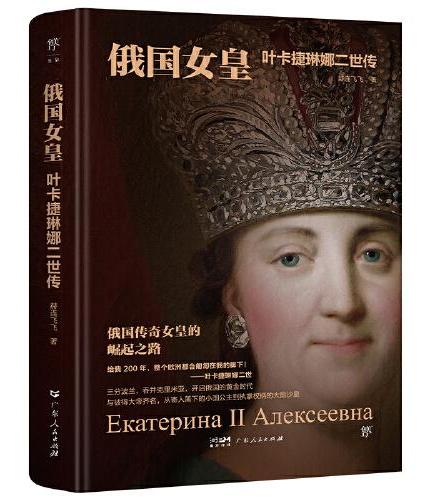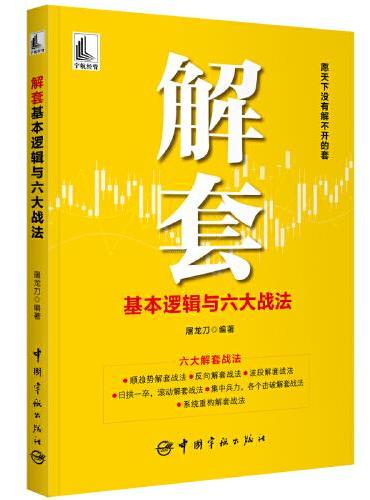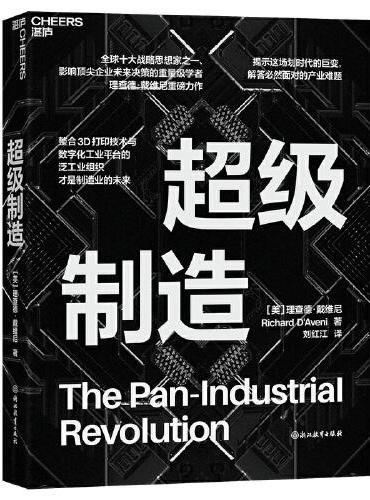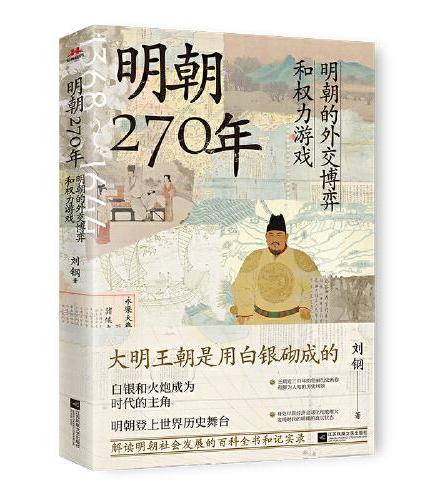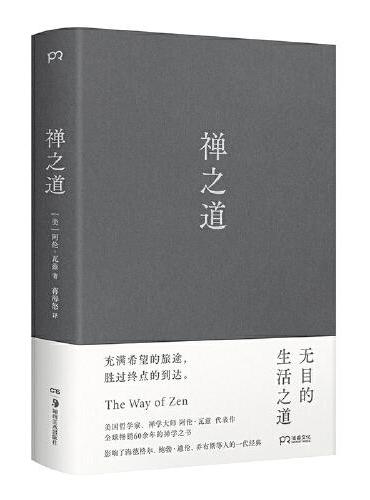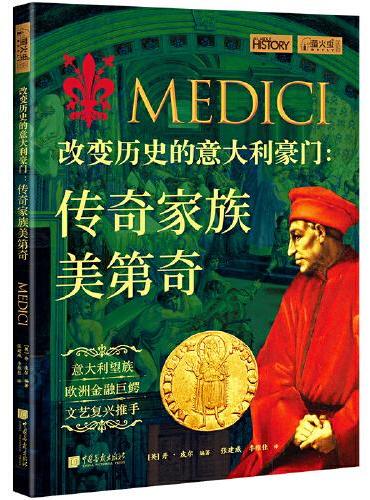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晚明的崩溃:人心亡了,一切就都亡了!
》
售價:HK$
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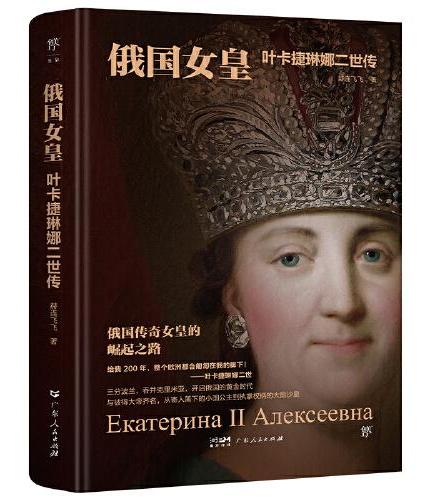
《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精装插图版)
》
售價:HK$
81.6

《
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
》
售價:HK$
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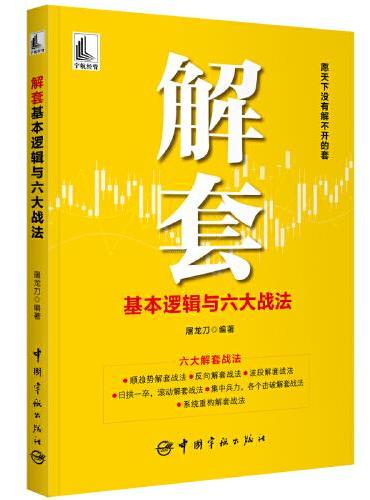
《
解套基本逻辑与六大战法
》
售價:HK$
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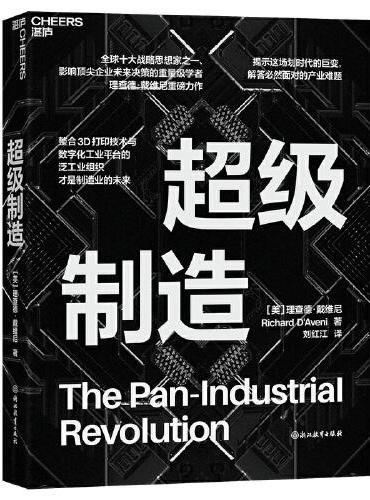
《
超级制造
》
售價:HK$
14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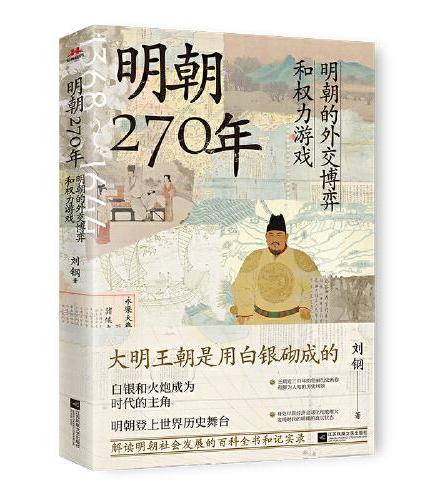
《
明朝270年:明朝的外交博弈和权力游戏
》
售價:HK$
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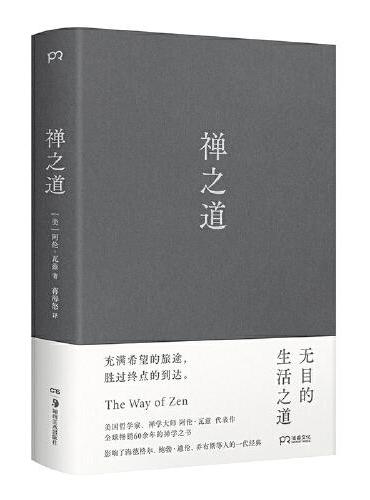
《
禅之道(畅销全球60余年的一代经典,揭示禅对现代人的解脱意义)
》
售價:HK$
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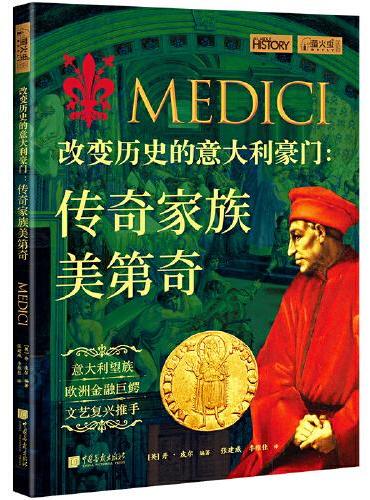
《
改变历史的意大利豪门 : 传奇家族美第奇
》
售價:HK$
90.0
|
| 編輯推薦: |
作者笔下的唯美乡村不欺不诈、不卑不亢、不弃不离,不怒不怨;作者笔下的美食有情有味,来自民间、食在民间;纯粹的野生美食,原始的土生食材,带给你舌尖上的快意人生……
※※友情推荐:
饮啄杂谭、吮指谈吃、人间烟火、民间有味、川味好安逸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作者选择从一条味蕾的小径回乡,将川北民间饮食从文字中复活、唤醒,这一篇篇舌尖上的记忆,一道道大道至简的纯粹民间山野美食,浓浓的乡土感铺天盖地而来,过瘾、快意,有味道。
|
| 關於作者: |
|
李汀,男人一枚,四十好几。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做人从善,做事从简。孤陋寡闻,不通世情。文字敏感,想象简单。活着走着,走着累着。有时读闲书,无聊观山水。感谢文字,感恩生活。
|
| 目錄:
|
第一辑土风
豆花珍珍饭
酸菜面鱼儿
风中灰搅团
黄金炒炒饭
火烧馍
甜浆饭
酸菜杂面
荞面软面子
炕饼
五彩炒面
熬腊八粥
蒸花馍馍
凉粉
烩面
柴火锅巴
第二辑寡味
嫩豆腐
鼎锅炖菜
野味小菜
四坛土酒
山沟木叶子鱼
桃花水里桃花板
偶尔刺克巴
月亮坝里烤黄鳝
坨坨肉
铜火锅
清汤寡水
野花可吃
清脆黑木耳
山村野菌香
小手蕨菜
第三辑清欢
粮食和爱情
黄花姐姐
红薯大叔
土豆兄弟
喜感的茄子
油渣子香香
两种野果
四种野菜
两只坛子
月光光闪亮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第一辑土风
豆花珍珍饭
缺吃的年代,有玉米面吃的是殷实人家。把玉米磨成针尖一样的颗粒,黄的、白的堆在一起,闪亮闪亮的,不叫珍珠,我老家叫珍珍。这叫法现在一想起,感觉就像叫一个殷胖的女人,洁白、干净。
清晨,天蒙蒙亮,母亲要把一簸箕玉米磨成珍珍。玉米倒在磨台上,牵了磨坊外站着的枣红马,轻轻把拉磨的套子架在马背上,把磨杆咕噜咕噜推到马屁股后套好。母亲走到马前,把眼罩给它戴上。枣红马静静地站在磨坊的阳光下等待母亲做好这一切。母亲一拍马的肩膀,喊一声“走”,枣红马慢悠悠地摇晃着铃铛,稳稳当当地在磨道上来回转,玉米面筛糠一样磨下来。太阳在悠悠的铃铛声中慢慢升起。
母亲站在磨坊边上箩玉米面。深口的大簸箕上架着两个枝条的树杈,用镰刀把树枝打平,马尾箩儿放在上面,来回箩,树杈被磨得油亮。一箩儿玉米面来回箩四五遍,细面落在大簸箕里,粗颗粒留在细面箩儿里,匀出粗一点的颗粒重新倒回磨台,留在马尾箩里的就是颗粒均匀的珍珍了。细面用来蒸玉米面馍馍。珍珍用来煮豆花稀饭。悠悠马铃铛,悠悠箩面声,早晨的阳光照上木窗子。
先点豆花。铁锅上放一木架,将生丝或马尾箩儿放在架上,再把从手磨上磨好的豆浆倒进箩儿内,再让豆浆淌进锅里,同时灶内的柴火烧得正旺,并用水瓢往箩中投水,让豆浆一次次注入锅内,往返三四次。不断加温,豆浆慢慢沸腾,豆浆煮起来,将准备好的酸水,沿锅边倒下,将灶火退去。这一连贯性的动作,有民谣说:“屎胀、娃儿哭、豆浆瀑”,这是家乡妇女煮早饭的情境,自己的肠胃胀流了,内急;背上背的娃儿还在哭,心急。就是有这两急的事情,也要先解决最急火的事情,止住沸腾的豆浆瀑出锅沿。此后,数次注入酸水,直到大砣的豆花浮起,豆浆水转清。再加柴火将水煮开,放些红苕或者洋芋煮,等红苕、洋芋半熟,然后抓一把刚磨的珍珍,摇晃摇晃让珍珍从手掌里徐徐漏下,用饭勺不停地搅动。这时候,柴火要旺,不能闪火。一边煮一边搅。放上盐,二十来分钟就可以吃豆花珍珍饭了。
再拌一盘火烧青椒拌蒜泥。地里的青辣子摘了洗净,用火钳钳着青辣子在滚烫的柴灰里翻滚,听见青辣子在柴灰里噼噼啪啪响。青辣子在柴灰里烫过后,辣味减了,清香溢出来。撸三五下,把烫蔫的青辣子放在木碓窝里,和着新蒜和盐捣碎,装进瓷盘子。一盘火烧青椒拌蒜泥放在木桌上,满屋子都是瓷实的清香。一筷子青椒拌蒜泥,一口豆花珍珍饭,那个香啊。
山里人每天早上都吃豆花珍珍饭。端一碗豆花珍珍饭,蹲在土院坝里,一条狗陪在身边。有时候,丢给它一块红苕或洋芋,狗歪着脑袋吞下去。然后,又静静地坐在主人身边,望着主人。稀点的豆花珍珍饭要沿着碗沿往下喝,“呼呼呼”,像是口技比赛。一碗豆花珍珍饭吃完,主人站起来舔舔舌头,又去厨房盛第二碗,狗也跟在主人身后舔舔舌头。
吃剩的豆花珍珍饭,一锅铲铲进厨房门外的狗盆里,狗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再把钢瓷盆子舔得“噌噌”响。遇到邻家的狗跑过来,两只狗兴奋地碰碰脑袋,亲热亲热。就像东家的主人端碗珍珍饭,西家的主人端碗珍珍饭,一边吃,一边谈论着庄稼地里的收成。再是,趁着院坝里的阳光好,狗也追撵追撵院坝里踱步的一群鸡,把鸡撵上房顶、撵上树枝、撵上草垛,撵得一院坝安静的阳光飘飘摇摇,撵得一院坝的尘土飞扬。
我已经离开村庄多年,老家木门上的锁已经锈迹斑斑,土院子里野草丛生。但我一想起村庄,心里立马翻腾起对农家饭菜的奇妙感觉,口水生津,我隐隐觉得,我草木结籽的内心,一直没有远离过乡村。而我终于明白,草木结籽的内心,豆花珍珍饭填饱的胃,我永远超越不了一个普普通通乡村人。
酸菜面鱼儿
酸菜缸挺着大肚子放在案板下,要吃了,掀开木盖子,舀一瓢出来。酸菜漩漩扯起,地上马上流出一条酸菜水滴成的路线,从酸菜缸到土灶台,就像一条水蛇躺在地上。
萝卜菜、山油菜扯回来,太阳坝里晒干露水。女人搭根板凳坐下来,把萝卜菜、山油菜上的泥巴抖干净,放进竹篾篓里切细。那青菜的山味,青菜的气息扑进鼻子。
女人端起切细的萝卜菜、山油菜,一阵风去了小河边,蹲下,翘起钩子,淘菜。阳光打过来,女人白嫩嫩的手臂上下翻动,青菜浮在竹篾篓里。翘起的钩子露出一抹白,时隐时现。河水里的木叶子鱼,在阳光里跳跃,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菜淘好了,女人把竹篾篓从水里拉出来,放在河边石头上,等竹篾篓里的水渗下。女人站在河边,看见水里印着自己的影子,笑了笑。一只五彩的水鸟飞过,“呀”叫了一声。女人抬头端起竹篾篓,走上那条小路,竹篾篓里的水还在“滴答滴答”滴。
淘好的菜放在街沿上,等铁锅里的水烧开,再把淘好的萝卜菜、山油菜在开水里煮上约十分钟,等青菜稍稍变了颜色,连水舀进案板下的缸缸里,加上一小把玉米面,再加上小瓢酸菜缸里原来的酸菜,搅匀,盖上木板,第二天,就可以吃酸菜了。一缸酸菜,一家四五口人,够吃上半个月了。
酸菜越酸越好。酸得人口水直流,那个酸呀,泥土的气息,陈醋的味道,木质的香醇,阳光的瓷实,都在那酸里。要是山油菜榨的酸菜,还有短短的苦,还有青草的脆,还有露水的净。如今,酸菜已经登上了大雅之堂,某品牌老坛酸菜牛肉面撑起这个品牌方便面的半壁河山,靠的就是酸菜那股味儿。乡村的酸菜缸放在案板下,要吃了,舀一瓢倒进锅里,从酸菜缸里扯出来的酸水漩漩,一路滴进锅里。那个酸呀,大热天渴了,喝一瓢生酸菜水,渴倒是不渴了,可酸得打战战。
酸菜做好了,做一顿酸菜面鱼儿。舀一瓢酸菜,用菜油,加生姜丝、大蒜片、干红辣子爆炒。炒好后,用碗把酸菜盛起来。烧水和面。用柴火将铁锅里的水烧开。烧水的同时,把小麦面盛在面盆里,倒进冷水,用竹筷朝一个方向调,一圈一圈调,小麦面和水融成一体,干稀适度,过干,滴不成“面鱼子”;过稀,就成了面汤。干了,加点冷水再调;稀了,加点小麦面。
水烧开后,把面盆端在手上,欲往锅里倒的样子,但又不能叫面溢出盆来,然后用竹筷迅速往锅里刮调好的麦面。这时灶里的柴火不能“闪火”。一“闪火”,刮进锅里的面鱼子就结成面团团,就不是“面条条”了。等面鱼儿在锅里煮起来,再把爆炒好的酸菜倒进去,再煮上一阵,香喷喷的“面鱼儿”就可以起锅了。说起来,我小时候,家里穷,一年难得吃到一回“面鱼儿”。母亲做“面鱼儿”时,我个头就土灶头那么高,踮起两只脚,两眼看母亲往锅里刮面,就想,哪天长大,会做“面鱼儿”了,一定做一大锅,吃个够。
土灶,柴火,做出的酸菜面鱼儿,唏嘘吃着,那个香啊。再一想,这面鱼儿的叫法,就不由想起小河水里跳跃的木叶子鱼,把小麦面做成小河鱼的样子,做成小河鱼的味道,只有在这乡村了。再一想那柴火“噗噗”燃着,俗话说:“咬紧牙关,绝不能‘闪火’。”这样的紧要关头,犹如背一背东西爬坡上坎,腿上一“闪火”,那情景想得出来,山坡上滚石头一样越滚越快。
面鱼儿吃得大汗淋漓,那个畅快,像是打开身体的血管,身体变得异常干净、清新。
风中灰搅团
在我乡村的风里,拂面的人群里,已找不出几个我熟悉的身影。但我可以借助乡村的炊烟,找到贴近乡土胸膛的呼吸。
一位老人站在院坝里,端着一碗灰搅团,“呼噜呼噜”吃着,我对乡村的记忆,一下子被摇醒了。老人起身,那草木一样的身子,草木一样的表情,使我的脸上,有一双手滑过的感觉。熟悉的温度,重新回到我的脑海。
我说:“灰搅团开胃,最好浇上一小瓢熟油辣子,辣乎乎的,酸溜溜的。”
老人又咂吧一下嘴巴说:“用腊肉颗颗炒青菜,做成腊肉汁浇在碗里,好吃。”
我说:“用郫县豆瓣炒料,烧成汤汁,过瘾。”
老人说:“吃搅团,关键是汤汁呢,少不了麻油。”
我说:“别说了,我口水都下来了。”
老人一拍大腿,说:“你看,光顾着说话,你来一碗搅团?”
我迫不及待地说:“来一碗。”
挨着老人坐下来,一碗灰搅团端过来,金灿灿的搅团卧在土碗里,就像一小座冰山卧在湖水里。山油菜酸菜,用豆瓣炒了,用姜、蒜、葱调配的汤汁,浇在金灿灿的搅团上。用筷子夹一小坨,用汤汁蘸了,吃上两三坨,满满当当的辣,满满当当的酸,满满当当的香,弥漫进胃里。
灰搅团的灰,是土灶膛里的冷柴灰,用细箩筛过,细细的,软软的,温暖。把手插进去,像是触到婴儿的皮肤,不忍心动弹一下手指,怕弄醒了这熟睡的婴儿。
苞谷颗粒是去皮的,磨成大米大小的颗粒。然后用一碗筛好的柴灰,拌一碗去皮的苞谷颗粒,搅匀泡在冷水里。柴灰要放合适,多了,渗进苞谷颗里的碱就重,吃起来夹口;少了,无味,吃起来粉嗒嗒的。柴灰是强碱弱酸盐,还含有少量的硼、铝、锰等微量元素。泡十个小时左右,如果泡的时间太长,发臭;太短了,未入碱性,无味。苞谷颗在微强碱弱酸盐的作用下,渐渐呈现出淡淡的浅绿,用清水反复淘洗去柴灰。苞谷颗粒清水洗涤,弥漫着清水的味道、柴灰的气息。
把泡好的苞谷颗粒磨成浆,在小石磨上磨。淘净的苞谷粒掺清水,苞谷粒本来的颜色被柴灰包裹,被那种淡淡的绿色包裹。一手舀半瓢带水苞谷粒,灌在小石磨的磨眼里,一手握着石磨的木柄开始磨,带水苞谷粒磨成浆,慢慢流进石磨下放着的木盆里。石磨转动,柴灰的味道、石磨的味道、苞谷的味道像一股股白色或金黄色的乳汁流出来,浸染了乡村沉静、醇厚的早晨。
“雷声隆隆不下雨,雪花飘飘不觉寒。”“千军万马城里过,个个出来脱衣裳。”这两个谜语的谜底都是石磨。这苞谷颗粒就是在石磨上脱了衣裳,磨成了浆。
苞谷浆磨好了,倒少许在铁锅中,灶内燃以柴火,待锅内苞谷浆温度逐渐升高,这时右手要用擀面杖慢慢搅动,左手拿瓢慢慢将盆中的苞谷浆添加到锅内,锅内温度不断升高,右手搅动的力量和速度也要加快、加大。一直到苞谷浆全部添加完,这时需双手紧握擀面杖用力回旋搅动。“要得搅团好,就得三百六十搅”,搅到三百六十搅左右,将擀面杖平行于锅面举起,擀面杖上浓缩的苞谷浆能挂起像窗帘状的帘子,搅团就搅好了。灶里柴火开始时要烧得大,中间要最大,然后是由大转小。见母亲搅搅团,随着擀面杖一圈圈地搅动,她脸上的肌肉在跳动,长发在飞舞,那分明是一种旋律、一种舞蹈、一种意志、一种韧劲……搅出的是甜蜜,是希望……有时候,父亲从城里回到乡下,赶上母亲搅搅团,父亲接过母亲手里搅动的擀面杖,“我来吧。”父亲就像接过一种甜蜜、一种希望,柴火印亮灶房。
灰搅团冷热都好吃。趁热吃,用菜油加豆瓣炒酸菜,加入姜、蒜、葱、盐、水调配汤汁,浇在热灰搅团上,就可以吃了。冷灰搅团切成细条,红油辣子凉拌,有嚼头,烩上吃,滑口鲜嫩。舌尖上的辣、舌尖上的酸、舌尖上的灰,让整个身体舒坦起来、流畅起来。
在城里想吃灰搅团,就买了擀面杖,买了磨好的苞谷面,做了搅团吃,总吃不出乡村那种味道。就想,城里哪里去找那种土灶、那种柴火、那种柴灰、那种石磨。
灰搅团在民间。
黄金炒炒饭
炒炒饭也叫“金裹银”。
金裹银,黄金和银子裹在一起,那是怎样一种金黄?那又是怎样一种银色?黄,诱人。银,诱人。山里早晨的太阳染在瓦房上的颜色,金黄。山沟里溪水跳跃的颜色,银亮。树笼笼里突然冒出的一两句山歌,金黄。“一把扇子里面黄,上面画着姐和郎,郎在这边望情姐,姐在那边望小郎。”野花笼笼里跳出的山歌,银亮。
山里水田少,几分水田,打不了多少稻米。要吃一顿米饭,得等到过年。在那个缺衣少食、不得温饱的年月里,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足矣让人垂涎欲滴。读初中的时候,寄宿在亲戚家里,亲戚是挣工资的,晚上吃白米饭,还配一两个小菜。吃剩下的一小坨白米饭,盛在小瓷碗里。我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在食堂定量吃的一碗糊面条,不一会儿,肚子就空了。总也睡不着,就想亲戚放在案板上,剩在小瓷碗里的白米饭。越想越饿,越饿越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起来看案板上那碗白米饭。拳头大一坨白米饭卧在青花瓷碗里,小小白米挤黏在一起,亲密、甜蜜。我嗅到白米的味道,口水直流。顾不了亲戚要是发现一小坨白米饭不见了,会生气责备。端起小瓷碗,倒一点白开水进去,再放一两滴酱油。酱油在碗里散开,白大米在厚厚的红褐色里铺开。我几口扒拉进了肚,甚至连白开水也一口气喝了。现在一想起那一小坨白米饭,米饭的香甜,酱油的气息,一下子把味蕾激活了。记得那夜我还做了一个美梦,梦见好多的白米饭,把肚皮撑得圆滚滚的。
姐在灶房里箜炒炒饭。把一大把大米放在清水里淘净,把大米放在铁锅里煮,大米六分熟,就连铁锅里的米汤、米一起舀进筲箕里,米汤从筲箕里漏下来,漏进事先准备好的瓷盆里。把米汤滤尽,然后再把筲箕的米,和上黄苞谷珍珍重新倒进铁锅里箜。这时候,灶里的柴火要小,用微小的火苗舔铁锅底。火候要掌握好,柴火大了,铁锅里的苞谷珍珍和大米会焦。慢火蒸,慢火箜。姐姐把这些做好后,就倚在厨房门上,轻轻哼上一首山歌:“哥也勤来妹也勤,二人同心土变金,你在行船我发水,你要下雨我布云。”
铁锅里箜的炒炒饭,有香气飘出来,姐姐揭开锅盖,用铁铲翻一遍,盖上锅盖继续箜。把酸菜炒了,撒在炒炒饭上箜,就成了酸菜炒炒饭。把青菜切细,炒三分熟,撒在炒炒饭上箜,就成了青菜炒炒饭。箜上二十分钟,揭开锅盖,米饭的香气、珍珍的香气、青菜的香气糅合在一起,飘出好远都还闻得到。放上盐,翻动几次,就可以吃炒炒饭了。要是有人从厨房后墙经过,闻到香气,会不自觉走过来:箜炒炒饭啊。遇见大方人家,铲上一小碗炒炒饭,让路人吃了。路人走到哪里,都会记起那碗炒炒饭:“那天,李家吃了一碗炒炒饭,香。”咂吧几下嘴巴,那个香还在嘴里回味无穷。
姐姐成家后,姐夫总是夸姐姐箜的炒炒饭。“一碗炒炒饭,哄到一起的。”对呀,男人都是好吃的,要哄住男人的心,首先要哄住他的胃。一碗炒炒饭、一首山歌,姐夫不醉才怪。
炒炒饭稍微箜久点,铲了炒炒饭,锅里就有一层锅巴。黄苞谷珍珍,金黄;白大米,银亮;青菜苔,青绿。黄里有银,银里裹金,金里泛绿。铁锅里一层锅巴,也是黄里点上那么几点银,银里透出一些绿来。把锅巴放在米汤里泡了,慢慢嚼起来,有一点柔润,有一丝脆香。
那时候放学回家,放下书包,首先就是冲进厨房找吃的。揭开锅盖,一碗炒炒饭沏在锅里,会端起碗风卷残云般狼吞虎咽。箜苞谷珍珍和小许大米的金裹银,一年里吃不上几回。多数时候,为了把苞谷珍珍吃出白米饭的味道来,就用全是苞谷珍珍和酸菜箜成炒炒饭,苞谷珍珍的糙,会满口窜。即便那样,能吃上一碗苞谷珍珍炒炒饭,也是香的。
几十年过去了,炒炒饭满口窜的香和糙还在梦里萦绕。可不知怎的,现在的饮食变得越来越精细,却再也吃不出炒炒饭那满口窜的香和糙了。
火烧馍
一到冬天,每家每户老屋的堂屋里生起疙瘩柴火。
堂屋是老屋的正房,乡村许多重大的决策都在堂屋议定,祭祖、婚丧喜庆的礼仪,以致拜年、重要客人会面,都在堂屋。堂屋正墙上有神龛,在正墙上掏一个神龛一样的窟窿,再把做好的木雕神龛锵进去,木雕上有太阳火焰蒸腾图饰,有吉祥纹饰。神龛正中铺上红纸,红纸上竖写着“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字,还有“某氏(本门)宗祖”、“东厨司命”等小字分列。有的还在神龛前摆放先人雕像、画像或木牌位,有的也摆上香炉烛台,逢重大节日先给先人们上一炷香。
堂屋背风的一角掏上一个大坑,大坑里镶上烂底的大铁锅。乡村总是能变废为宝,一个烂底的铁锅舍不得丢,就镶成堂屋烤火的用具。铁锅内堆起疙瘩柴,一天一天燃烧,慢慢地就堆起半铁锅柴灰。疙瘩柴燃烧的时候,柴灰的温度就升起来。柴灰烫,老家叫烫灰。在烫灰里放上洋芋,一家人围着疙瘩火烤火取暖、唠话,洋芋也在柴灰里烤火。舒服极了。看过寓言故事:温水里的青蛙。要是把青蛙直接扔到开水里它会蹦出来,但是把水慢慢加温,直到煮沸,青蛙也不会跳出来。在温水慢慢加热的过程中,青蛙舒服死了。我就想,要是青蛙在柴灰里过冬,也会在慢慢升温的烫灰里变成一具化石。
烫灰里的火烧馍馍,别有一番味道。火烧馍馍可防霉变,夏天也能存放七八天,不发霉、不变味。乡村外出做活路,或者赶场,要带的盘缠干粮,就是火烧馍。火烧馍馍,是在麦面或者麦面里掺上苞谷面,加适量的菜油和水,使劲在面板上搓揉。搓揉成团,在面板上团成瓷碗大小的圆形规模,再擀成饼。然后放在温热的铁锅里,用微火炕,炕成黄黄的一块饼,再放进堂屋滚烫的烫灰里烧。柴灰的温度不要过高,达到馍不焦灼,又能使馍里外熟透。烧火烧馍馍要有耐心,保持烫灰的温度不高不低。乡村许多事情急不得,一急,就乱了阵脚。看着风在村里横冲直撞,母亲却一点也不急,坐在老屋屋檐下,静静地飞针走线,用善良、柔情观看着这世界的疾风骤雨。母亲说:“急啥,该来的,总要来。”急也急不来。母亲把手里的一块布摊在一件大衣上,她要把大衣上的一个洞补上,母亲细心地裁剪着那一块布,就像裁剪着身边的一块土地。那块布染着阳光和泥土的气息,不急不躁。
火烧馍馍要粘上泥土和阳光的气息,只有不急,只有让那金灿灿的阳光慢慢渗透进火烧馍里,只有让那滚烫的柴灰慢慢渗透进火烧馍里。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和麦面、苞谷面混合在一起。把火烧馍馍从烫灰里夹出来,用手在火烧馍的平面上拍击,发出“噗、噗”的鸣响,这火烧馍就熟透了。火烧馍熟透了,乡村熟透了。
乡村的许多粮食,都夹杂着泥土的气息、阳光的气质。我走出乡村的那个早晨,带着瓷碗大的火烧馍馍。乡村小路上的蒲公英、蒿蒜子,还有那岩边的闷头花,一路开着,一路香着。草叶上的气息,火烧馍的气息,让我走出乡村的那个早晨充满了温暖。
这个充满泥土和粮食气息的早晨,总能围绕着我的行走,在我的前方忽明忽灭闪现,照亮着我生活的许多细节。
甜浆饭
初夏,乡村的阳光和空气都是甜的。谁发现的?
是这些灵性的鸟儿。乡村立在苞谷地里的稻草人一动不动,这些鸟儿早知道那是个假人儿,不闹不叫的,穿着的衣服七长八短,它们笑上一阵子,还站上稻草人的头发呆、瞭望。见没有人来,就站在苞谷穗上啄食嫩苞谷。啄一下,望一下四周。再啄,再望。嘴里不时发出“甜、甜、甜”的叫声。一发现不远处的人走过来,它们扑棱棱飞走,叫嚷着“甜、甜、甜”。鸟儿铺天盖地地在阳光里弹起又落下,看见它们的高兴劲,真想伸手抓一把,放在手掌心里仔细认一认: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鸟儿?跑进苞谷地的农人,捡起地里的小石块,向鸟儿飞翔的方向打去,驱赶它们少吃苞谷。石块“嘭”一声闷响落在苞谷地里。鸟儿在树梢上还没有停稳,又弹起往远处飞。
苞谷地里最烦人的是这些诡秘的老鼠们。苞谷灌浆的时候,乡村老鼠的鼻子灵透,一丝的甜味它们都嗅得到。老鼠缩头缩脑钻出洞,望望金黄的阳光,望望碧绿的庄稼,一溜烟爬上苞谷秆,咬开苞谷壳,就开始不停地啃嫩苞谷。老鼠用牙齿“吭吭吭”撕咬苞谷的声音,在乡村初夏的阳光里显得格外清脆。有脚步声传过来,老鼠赶快从苞谷秆上溜下来,躬起背一溜烟逃进了洞里。
这甜是土地温润的气息,乡村生灵们一生与草木相伴、与这些气息相融,许多自然的物语,也只有它们能够感知得到。确实,春天来的时候,是蚯蚓先咬开泥土的大门。夏天来的时候,是青蛙叫嚷着星星坠落。这嫩苞谷的一丝丝甜味,当然也只有这些纯粹的小家伙们首先感知了。其实,乡村的幸福也就在这些家伙们的捣乱中存在。
乡村风里的气息,裹着这甜,裹着这泥土腥味。地上的尘土被风吹起来,空气里丝丝缕缕的甜味被风搅动起来。这是怎样的一种气味?就是在这风里,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唐山大地震前几个晚上,一户人家被老鼠折腾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它们在追赶老鼠的途中,躲过了地震中房屋的压塌。地震中土墙房屋倒了,山石飞走,乡村一片狼藉。乡亲们逃出家园,站在高处,人声嘈杂,惊恐声、哭喊声混成一团。牛羊猪被房屋堆压着,一些逃出来的牛羊猪也颤颤巍巍地站在山坡上,惊恐地望着乡村。乡亲和他的那几只老鼠都站在一个山坡上,乡亲已经是吓得寸步难行,但几只老鼠站在不远处,用爪子洗刷着小脸,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是在与主人玩一场游戏一样。这场游戏显然是老鼠成了赢家。难道这老鼠是灵鼠,它懂得在地震来临之前如何撤退?老鼠在地震来临的前几个晚上,就开始向乡亲通风报信。然而,乡亲们听不懂老鼠的语言,也不知道和老鼠周旋的过程,是逃生的过程。地震改变了一切,主人的粮食已经被尘土深深淹没,老鼠跳到废墟上,拼命用爪子刨尘土,主人顺着老鼠刨的地方,用铁棍撬,一点一点又抢出了粮食。粮食堆在平地上,主人搭起简易的灶台,开始生火做饭。炊烟升起,乡村又活过来了。主人这时候,望着那一眼鼠洞,感慨地说:“这些老鼠,还晓得报答。”一抹阳光照在乡村半坡上,风吹来,吹得苞谷林“哗哗哗”响。主人望着快成熟的苞谷,心里甜滋滋的。
主人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了一句:“人是铁来饭是钢,整个甜浆饭来吃。”主人走进苞谷林,掰了几个苞谷,撕了苞谷壳,主人蹲在刚刚搭起的灶台边,把苞谷米一颗一颗掐下来。苞谷米还有些嫩,一掐,浆就蹦了出来,弄得手指甲上到处都是,一会儿,指甲被染成了黄苞谷米浆的颜色,嫩黄嫩黄的。主人掐完四五个苞谷的米,太阳都升高了,照在主人的额头上,闪闪发光。主人站起来,又习惯性用双手拍了拍身子,对着阳光咧嘴笑了笑。主人把掐下来的苞谷米,用水磨磨成浆。主人烧开了铁锅里的水,又找到尘土里的酸菜缸,舀了一瓢酸菜到锅里。主人把磨好的苞谷浆在一个小勺子里兑水一小勺一小勺搅化,然后倒进锅里煮。煮上二十多分钟,甜浆饭煮好。一家四五口各舀一碗,蹲在歪歪倒倒的房屋院坝里,就着碗边边“嘘嘘嘘”喝起来,那声音甜啊。这时候,乡村的其他声音都得为这甜蜜的“嘘嘘”声让路。
要是有空,把嫩苞谷磨成稍微干点的浆,捏成团,摊开擀成厚皮,裹上炒半成熟的南瓜丝,或者裹上炒了的豆芽,捏成三角形,外面用桑叶或者桐子叶包裹,免得粘笼床。放在蒸笼蒸半小时后,就可以吃水面角了。外面用桑叶包的,可以不剥桑叶直接吃。桑叶的清香和嫩苞谷的香甜裹在一起,有粗糙的苞谷味道,也有桑叶的细腻气息。要是包的桐子叶,把桐子叶剥了,桐子叶的味道还裹在嫩苞谷面上,一口咬下去,迅速触动味蕾,打开身体。
酸菜杂面
我们乡下人顿顿吃酸菜。几个乡里人在城里下饭馆,坐定之后,不是点菜,而是直接各要一碗酸菜面,再各来一碗毛干饭。搞得饭馆老板直瞪眼。用酸菜面下白米饭,有谁见过?谁见过都觉得没有关系,乡里人已经就着一碗酸菜面下白米饭,热腾腾吃起来了。
一碗酸菜面,是乡村缺吃少穿年代最珍贵的接待了。
山里盛产苞谷、黄豆,小麦是要用来换稻米的,一般舍不得吃。于是,乡里人为了吃上面,就在麦子里掺上苞谷,再掺上黄豆,用这三种粮食混合在一起磨,磨成一种杂面。母亲常常是白天要在地里干活,晚上才开始磨杂面。月明星稀之下,母亲在磨坊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磨过一遍了,母亲就开始箩面,把箩在上面的粗面又重新倒回石磨上,又开始一圈又一圈地磨。看见母亲吃力地在磨坊里推着一扇石磨一圈一圈地走,我和弟弟跑过去,推着磨杆帮母亲跑上一圈,母亲跑不赢我们,就在磨道里小跑着说:“不要跑那么快,一会儿就没力气了。”一会儿,母亲喘着粗气,我们兄弟俩也喘着粗气,蹲在磨坊里,笑得肚子疼。记得那个时候,月光透过竹林,走在磨坊的台阶上,月光里印着我和弟弟的小影子,母亲的影子很高大。有浅浅的风声从磨坊山梁轻荡下来,翻卷起夜的衣衫,竹林开始婆娑起舞,田地里的虫声密集。磨碎的黄豆、苞谷,还有那小麦,像是被撕开封纸的酒坛子,生黄豆的气息、甜苞谷的味道、稠小麦浆的流动,你抓我,我抓你地拥挤着、伸展着、飘扬着,黄豆的身体、苞谷的穴位、小麦的味道,在月光里被打开、放大。我身体忽然抖动了一下,月光里我前所未有地把身体张开,像是一只越过旷野的夜莺。
好大一片黄豆地,五颜六色的黄豆花盛开,还有好多的鸟儿,在黄豆地上空歌唱。我躺在那五颜六色的黄豆花里,像是躺在一条丝绸里,更像是躺在一片偌大的五彩羽毛上,我的身体是那么轻盈,飘呀飘,我暗自欢喜。突然,一只鸟儿俯下身子,拥抱着我。哦,她好像是一位仙女。一头长发,像羽毛那样柔柔的、软软的。突然我身体抖动了一下,我的身体穿过重重群山,“轰”一声落地……我的梦醒了。我的身体在月光下的黄豆气息里,完成了第一次打开。
我和弟弟趴在磨盘上睡着了。母亲喊我们醒来的时候,杂面已经磨完。母亲说:“做梦了吧,看你笑的。”我揉了揉眼睛,月光里生黄豆的气息一阵阵浓烈。母亲说:“快去睡吧,明天又有杂面吃了哦。”
母亲擀杂面的时候,我就帮着看着灶膛里的火。母亲撮上一木瓢杂面,用水和了,揉成一块小小的面团。这面要和得软硬适中,母亲用手来回搓揉,把面团揉得瓷光瓷光的,那面团的颜色像是月光照在瓷器上,柔和,瓷白。搓揉好的面团,母亲并不急着擀。母亲说:“叫那面再醒醒吧。”醒面?母亲是要那面团里的气息都醒过来吗,生黄豆的气息、甜苞谷的味道、稠小麦浆的流动,都要在母亲的搓揉中醒来吗?母亲望着天边的一抹彩霞,一会儿变幻成山峰,一会儿变幻成万马奔腾,母亲转身走向案板,我仿佛看见那搓揉的面团在案板上晃动了一下,醒了。母亲用二尺长的擀面杖把面团擀开,把擀开的面卷在擀面杖上,母亲躬着腰,身体一前一后,一起一伏,双手随擀面杖前推后拉,左右压均匀,不断重复。那面团在母亲的擀面杖下一次次变薄。擀上一会儿,母亲要停下把卷在擀面杖上的面展开,再在面上撒一些干苞谷面,用手铺均匀,以防止粘连,然后继续卷在擀面杖上擀。卷起,展开,擀上那么四五遍,展开用手指捻捏一下整张面的厚薄,合适了,就把整张面展开,再撒上一层苞谷面。把整张面皮叠成手掌那么宽,就开始切面,菜刀在母亲手中伴随着“当当”声起起落落,均匀的面条一口气就切好了。宽细一致、薄厚一致,母亲用手轻轻拿起一把面条,抖了抖,苞谷面纷纷落下来,母亲微微汗湿的脸上,绽开了像一朵花,一朵淡紫的黄豆花。
等母亲把杂面煮好,整个厨房就只听到吃面的哧溜声,没人说话,母亲笑了一声说:“像你们这么吃,有谁家养得起。”我们三兄弟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养自己。”这时母亲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乡里人,想去女方家当上门女婿。一天,这男的去女方家里串门,女方母亲擀面招待这即将成为的上门女婿,面擀好,煮好,给男的盛了一小面钵端上来,男的二话不说,埋着头一口气吃完了。看得老丈人目瞪口呆,心里想:“这么能吃,谁养得起呀。”最后,这门亲事就这么完了。母亲总结了一句:“这就叫,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得见。”
后来,我知道这“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得见”出自《红楼梦》。母亲断然是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但母亲这心谁也蒙不了。我总惦记那个能吃的男的,要是今天,结局肯定就大不一样,能吃就能干呀。可惜,那是个缺吃的年代,都要勒紧裤腰带。
荞面软面子
荞麦是乡村的一块紫云。紫红的荞秆,黑红的籽粒,青青的荞叶,白色的花。籽已结了,花却还在开。荞麦在收割时,有果实,还有花。远看,那一大片荞地,像镶嵌在秋天天边的一团紫云,更像爱情的颜色。近看,那黑压压一坡厚实的黑红荞籽,像一颗颗会说话的星星,让人想到爱情的那个乡村夜晚。
荞子是乡村紫黑的女子。在我的家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一千年前,有一位民间医生上山采药,忽然看到有两位仙女在山间一会儿结伴游戏,一会儿尽情歌舞。民间医生看傻了眼,仙女笑呵呵地走过来和民间医生搭讪。霎时,云绕波涌,如鱼滚动,民间医生竟不知不觉地跟着仙女走进了山间的一个洞中。哪知洞内温暖如春,四季常青。仙女对民间医生百般照顾,一日三餐,必吃两顿荞面。民间医生只待到第三天,便思念亲人想要出山回家。哪知,民间医生走出山洞,已物是人非,子孙已历五世。这时民间医生方才知晓,他在山洞里过的时日,人世间已经几百年过去了,他却还长生不老。民间医生这才恍然大悟:山洞每日两餐吃的荞面,原来是长生不老的食物。从那以后,乡亲们开始祖祖辈辈种荞麦,吃荞面,变着花样吃。那以后,荞子更像是紫黑敦厚的女子,时时站在山头,静静守候着乡村。
想到一个词,山河入梦,岁月静好。只要那山间还在就好,只要那山间的荞麦花还在就好。
秋天的荞麦刚刚收割打理磨成面粉,那长着棱角的黑脸的荞粒里面,打开全卧的是白胖子。山间农家的土灶上,黑红的乡村女子正忙着蒸荞面馍。先将荞面粉用水和成稀稠状,然后将其倒进垫着纱布的竹笼,猛火蒸半小时,将蒸笼揭开,竹笼里蒸成的大块状荞面馍冒着热气。在清香苦甜的热气里,那黑红的乡村女子的笑容是那么瓷实亮光。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乡村医生描述的那个仙境了。云蒸雾绕,芬芳怡人。其实,进入一种境界更多是靠一种气息的形成来维护的。热气散开,回到现实中,用菜刀将竹笼里大块的荞馍切开,切成一块一块的,那放在蒸笼里的一块块紫玉,和站在一旁的黑红女子,竟是那么的神似。黑里透着红,红里闪着亮光。荞面馍是一块紫玉,乡村女子是一块紫玉。二爷是乡村养蜂人,几槽蜂子架在山坡上,蜂子每天飞出飞进采花酿蜜。起蜜的时候,二爷笑开了花,用喝净的沱牌酒瓶子,满满接一瓶子,然后用荞面馍蘸着乡村蜂蜜吃,花的气息,露水的甜,还有乡村青草的苦,都在这荞面馍里。二爷笑着说:“晓得不,这就是地主家的生活。”
母亲把荞面做成软面子。母亲说:荞面不是有些硬吗,那就用酸菜把它软一下。于是,母亲把荞面和水稀成泥,再放点酸菜进去,用筷子搅均匀。柴锅里的火生旺,把菜油煎熟后,退了柴火,用菜油把锅涂透,然后把和好的荞面倒进锅里,用锅铲把荞面摊开,薄薄摊开在锅里,用余火慢慢焙,等焙烤到荞面边边金黄的时候,再翻过焙另一面。反复焙烤几次,就可以起锅了。母亲说:焙酸菜荞面软面子,急不得。不用急火,不用急脾气。一急,就焙焦了。一急,就坏了好好的荞面。急不得,母亲说,说话急不得,再有理也急不得。一急,话说不伸展还得罪人。急不得,母亲说,做事急不得,毛手毛脚做不好事。不是火烧房子牛滚岩的事,急啥?急了,就是焙荞面软面子这小事,都做不了。急不得,母亲说,活人急不得,人活一辈子得一天一天过,一山一山过。急了,把人都急老了。
所以,母亲在焙荞面软面子的时候,静静地把荞面摊开在锅里,就站在土灶边,看天边的那一抹彩云,欣赏飞鸟在空中飞翔的姿势。有时候,母亲还把我喊到她身边:“天边那彩云,像什么?像不像一匹飞翔的骏马。”我无心欣赏天边的彩云,丢了一句:“管它像啥。”跑开了。母亲不急,等把荞面软面子焙好的时候,递一块给我,然后再指了指天边。我一边吃荞面软面子,一边对母亲说:“不像是骏马,像一头狮子。”母亲慢慢说:“像骏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母亲就是在这种“急不得”中来教育我们的,现在想来,荞面软面子的那一点点的揉劲,就是母亲慢慢焙出来的。
一次,高中同学元去我家里,母亲正好焙了荞面软面子,同学元接连吃了两搭子,元说:“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味道了。这荞面正宗,这酸菜正宗。”后来,元这样记录在我家吃荞面软面子的情境:“家乡的味道一下子浓烈起来,一边吃着荞面软面子,一边想象一个母亲站在土灶前默默焙软面子的样子,心里那种温暖直往外蹦。多想回家,种田一畦,梦在瓜下,粗粝终老,所愿止此。”
炕饼
还有许多馍和饼:炕肉客蚂,炕洋芋馍,炕红苕馍,炕茄子馍,炕南瓜花馍,油炸茴香鱼,油炸椒叶,软面馍馍蘸蜂蜜,水面角,火烧馍等。这些馍和饼炕的也好,炸的也好,蒸的也好,都活泛着乡村水的清凉,散发着乡村风的气息,渗透着乡村草的味道。
从山里忙活一天回到家的女人们,喝上一罐老鹰茶,又开始在厨房忙起来。木碗柜里取出一块煮好的腊肉。腊肉油浸浸的,夕阳从厨房木格子窗户透进来,打在油浸浸的腊肉上,打在女人汗渍渍的脸上。腊肉切成片,在案板上泛着油光。小麦面在木桶里,揭开木桶,舀上一木瓢,盛在面盆里,倒进冷水,用筷子朝一个方向调,一圈一圈地调,小麦面和水融成一体,干稀适度,再把切好的腊肉放进调好的面里。
这时候的夕阳已经退出厨房,有点暗的厨房里,女人哼起了山歌:“想郎想得四念三,白日当作月夜天。清风吹得花枝响,像是情郎在眼前。”女人幽幽唱完,绯红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意。
这时候的炊烟已经升起,在灰灰白的天空下游走,绕过竹林,绕过房前的庄稼地,绕过草地上那一群花花绿绿的鸡,绕啊绕,力气尽了,星星在天空眨着眼睛。一只狗在土路上疯跑,它要追逐什么,是天空那一抹夕阳,还是无影无踪的炊烟?也许,就是一趟追逐,什么也不去追。狗在乡村,更懂得与乡村一种气息的同时存在。
这时候的女人,已经停止哼唱。菜油倒进滚烫的铁锅里,不要倒太多。女人开始在心里默念丈夫吃肉客蚂的样子,开始想着丈夫幸福的笑容。菜油在铁锅里冒起了热烟,女人急忙退了柴灶里的柴火,女人又悄悄说了一句:丈夫呢,在外面吃得饱不?女人有热泪从眼眶流出来,有甜蜜,也有辛酸。
女人用筷子夹起面盆里裹好的腊肉片,丢进滚烫的油锅里。油锅里马上吱吱冒着油泡泡,炕上一两分钟,又翻到背面炕。四五分钟,两面泛黄的肉客蚂就炕好了。让腊肉片裹上面泥,睡在热油锅里,那些腊肉的香味就开始一点点唤醒过来,那些小麦的气息开始一丝丝抽出来。女人咕噜了一句:这个香哦。炕好的肉客蚂趁热吃,满嘴的腊肉油咂出来,香;面泥炕得焦黄,脆。香脆,香脆。
炕肉客蚂是老家农村的名小吃。沿海一带的老板到川北来,一盘肉客蚂端上桌,老板问:这是什么东西,挺好吃的。一桌陪客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其中一个偷笑着说:这个东西啊,好吃。沿海老板一边吃,一边重复:这个好吃。
把洋芋、红苕、茄子切成片裹上面泥,花椒叶、南瓜花裹进小麦面泥里,在油锅里炕出来,又别有一番风味。那种泥土瓷实的味道,清晨露水的清新,鲜花绿叶的野味,一起进了肠胃。种子入土,鲜花盛开,绿叶舒展。青花一样的瓷盘里放上这些炕饼,让人有一种在自然沐浴的感觉。有时候自然的东西离我们远了,但一想起就会被无边的渴望覆盖。哪天,坐在鸽子笼的房子里想起这些东西了,就咽着口水怀着美妙的想象,做上一回,感觉里像是回到乡村的土院坝里,吃着炕饼,望着天边的星星。
夏天,嫩青苞谷在田野里鼓着腮帮子,扳几个青苞谷回来,撕了青壳壳,把青苞谷米粒一颗一颗掐下来。一颗一颗的青苞谷米粒在筲箕里堆着,一点一点的苞谷浆溢出来,淡淡的黄,浅浅的甜。一颗颗苞谷米放在小水磨上磨成稠密的浆浆,再把稠密的苞谷浆摊在嫩桑叶上,再在苞谷浆上摊一点炒南瓜,然后按桑叶的主纹络对折,用苞谷浆的黏性黏住,放在蒸格上蒸熟,就成了可口的水面角。苞谷的粗糙,苞谷的甜糯;南瓜的水汽,南瓜的清香;桑叶的清爽,桑叶的绿色,一起都在水面角里。桑叶一起吃了,夏天的阳光、雨露都在桑叶上。
川北农村女人都有一手绝活,她们把山里粗鄙的粮食做得精细又可口。一碗小麦面粉,她们只单单在面粉里和上水,山里清凉的山泉水,什么都不加,就能做出可口的擀面,还能做出可口的火烧馍。冷水和面,再揉面,揉成面疙瘩,一点一点把面和水揉在一起。水知道答案,女人的心思揉进了面里,女人的辛酸揉进了面里。水知道答案,草木的隐忍在面里,尘土的沉静在面里。水知道答案,亲情融融、和乐一片,全都揉进了面里。许多好吃的东西,都是慢慢做出来的。快不得,快了就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农村女人不急,她们天生活得本分、自适、皮实。她们把面揉得都醒了过来,面醒了什么样子?小麦在田野里随风摇曳,蛐蛐在田野里卑微低鸣,露水上来了,月亮升起来。那一坨面,女人揉了又揉,揉出了油,夕阳落山的油彩挂在天边。
再揉,面团能印出女人红彤彤的脸庞。
再把面团用手掌摁平实,摁成一个两厘米厚的圆形,然后放进温热的铁锅里慢慢炕,用手指轻轻转动圆形的面团,保证均匀受热。一面炕好了,再翻过来炕另一面。炕好了,用牙签一样细的竹签在面团上扎上小孔,放气。最后把炕好的面团放进柴火燃过的烫灰里烧,隔上二十分钟翻一次再在烫灰里烧。从烫灰里夹出火烧馍,草木灰的味道,面的味道,慢慢释放出来。
火烧馍也是陕北女人送给男人远行的干粮,远行的路上饿了,从行囊里摸出火烧馍啃一口,远行的路上就能让人定心、安心。因为,男人知道,不管走多远,女人的眼光和热度都在身边。所以,男人啃着火烧馍的时候,会有感激的泪花在眼眶里。
哦,这些乡村的炕饼,其实是多么温暖的饮食。温暖,是两个人的感应,哪怕是和无声无息的粮食。
五彩炒面
这里说的炒面是将五谷杂粮磨成面粉炒熟后直接吃的那种,并不是现在的那种炒面条。
我一直对这种炒面保留着温馨鲜活的记忆:中学时代,那种饥饿的感觉在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沉重地侵袭着我的黑夜。在通往教室与寝室的那条通道上,月光从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缝隙间透下来,星星在密集的白杨树梢上跳跃闪烁。这一切都引不起我的注意,我的肚子像是被风掏空了一样叫嚷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咽着口水。
留给我们就寝的时间只有半小时,我们十多个同学拥挤在过道洗脚、洗脸,悬挂在我们头顶的那盏白炽灯一点也不明亮,好像很无奈地照着我们。我们更无奈了,灯一熄,我们就开始摸黑做没有做完的事情。有被踩着脚故意大声叫嚷的,有骂学校管熄灯的老头儿的,有唱“黄土高坡”的……就在这些杂乱的声音中,睡在我上铺的安,悄悄地解开一个塑料袋子,躲在上铺蚊帐里吃炒面。那种拌了葱花,撒了白糖,裹了花生米的炒面。尽管安吃得很静,非常轻手轻脚,我还是嗅到黑夜里游走的那一丝炒面香,我还是听见了安轻嚼细咽的声音。我使劲咽了一口口水,把头伸进他的蚊帐说:“不够哥们儿吧。”安按住我伸进他塑料袋的手,示意我不要作声。他舀了一铁勺子炒面倒进我嘴里,要我睡回去。我摇头,他再舀一铁勺子倒进我嘴里,我才倒在床上细嚼慢咽着炒面。月光从玻璃窗透进来,诡秘地笑着,我满嘴的炒面像是香爆了一样。那白砂糖的脆甜,我不敢一下子嚼透,怕寝室的同学听见,只敢一点一点放轻牙齿嚼。那五谷和小葱的香味直往外窜,我掩着嘴轻启着双唇,不敢让舌头舞蹈。月光里,我双眼里闪现着炒面的样子,五谷粮食磨成不同颜色的面粉,苞谷面盛黄、青稞面迅白、黄豆面微黄,白砂糖是一点点的粗甜,青葱是炒面里的小调皮。用微火在铁锅慢炒,让这些颜色相互认可,让这些味道彼此买账,慢炒慢熟,急不得,慌不得,这炒面的味道是慢慢起来的,值得慢慢回味。这是我年少时代吃的最美味的炒面了。
学校的灯熄了,月光照了进来,风也在这个时候来凑热闹,赶了进来。月光进来,风进来,我们寝室就没有秘密了,炒面的甜蜜在月光里散开,炒面的香味在风里到处乱窜,就像我们少年疯狂的身体一样,成长的汗味气息把人熏得要倒。“哼,炒面,哪个的炒面?”冬娃子凑了凑鼻子,大声吼叫着,吓得月光抖动了一下,风也停止了蹿动。我赶紧停止了咀嚼,停在月光里不敢出大气呼吸。我担心是自己的咀嚼声音太大了,冬娃子听见了。冬娃子翻身下床,一张床一张床地清理。走到安的床边,安假装打鼾熟睡,冬娃子一把扯开安的铺盖,从铺盖里抓出一塑料袋子炒面,说:“安,还说啥子‘苟富贵,无相忘’,你有了炒面,都不晓得让我们一同享受?”听见有炒面,一寝室的同学都围了过来,顾不得那么多了,用手就开始抓了吃,你一把,我一把,在月光下狠狠饕餮了一回。一会儿,一塑料袋炒面就被我们消耗完了,我们吃得满嘴带香,月光在窗外一抖一抖地笑,我们心里也甜透了。可是,安流着泪水,哭着说:“这是我一星期的伙食,你们全部给我吃完了。”我们都不敢说话,还是冬娃子开腔说:“哭个啥?只吃了你的一点炒面,又没有要你的命。”
那一夜,我的梦起来了。在月光里,我仿佛飞翔在五谷飘香的风里,五谷粮食成了五彩纷呈的花的海洋,我游弋在浓郁的气息里,炒面的香醇厚浓重,像是要把我的鼻子呛歪。好香好甜的炒面,我想高调地打一个喷嚏。好像是在我家瓦房背后的山路上,我家黄牛在菜地里欢快地吃着青菜,黄牛对我说:“快来,这青菜比炒面好吃。”我吓了一大跳,黄牛怎么会说话,梦醒了。我惊奇地望着窗外,月亮挂在学校破旧的窗子上,贼亮贼亮。一只猫顺着墙头,影子一样快速跳过窗子,消失在茫茫月光里。我嘴里还残留着炒面的香味。
在那个年代,读书能够带点炒面、带点泡菜去学校吃,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点的。我记得我带的比较多的就是一口袋苞谷面馍馍,冬天还好,可以吃上一周,要是夏天,吃不了几天,苞谷面馍馍就会尸臭,起绿色的点点,生绿色的丝网。在高中的三年时光里,懵懵懂懂地陶醉于学校背后的小山坡。小山坡的白杨树林里,印象最深的是夏天的一个下午,一山坡的彩霞把白杨树照得流光溢彩,我和同学安在学校食堂各自打了一碗面条,就神秘兮兮地相约到了山坡的白杨树林里,安打开一罐头瓶子泡菜。那泡菜用菜油轻炒,再放进干花椒、干红辣子、葱段、生姜粒一起炒了,装在一个空罐头瓶里。泡菜是萝卜、青菜头泡的,一点辣味、一点酸味还有菜油的香。当时觉得安好幸福,带的泡菜都那么好吃。下午的蝉鸣声懒懒地在白杨林里响起,草地上有蝴蝶和蜜蜂在低飞,风吹起来,感觉浑身上下都是熨烫过一样舒坦。那时候,我好羡慕安有一个为他炒泡菜的母亲,我甚至怀疑,我的母亲是不是爱我,连泡菜都不为我炒点。
多年之后,当我回到学校,看见当年那个温馨的小山坡和茂密的小白杨树林时,立马唤起我软绵绵的感情,顿时觉得一阵清风扑面,双眸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我急切地在心底喊出:炒面,五彩炒面。
熬腊八粥
农历腊月初八,源于远古的“腊祭”,流传为“腊八节”。这天,要做“腊八粥”。腊八粥是春节的前奏,一进入腊月,年味儿就开始浓了。腊月是年岁之终,农闲的人们无事可干,便想方设法做吃的,为春节团圆做准备。用杂粮做成“腊八粥”,还甩洒在门、篱笆、柴垛上,来祭祀五谷之神,来祈祷来年五谷丰登。
说起腊八粥,就想起《红楼梦》第十九回中宝玉给黛玉编的一个故事,说一群耗子要学人间熬“腊八粥”,故事讲完,惹得黛玉和宝玉笑打在一起。这故事好听,不妨我们再来听一遍:宝玉只怕黛玉睡出病来,便哄黛玉道:“哎哟!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见他说得郑重,且又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什么事?”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诌道:“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黛玉笑道:“就是扯谎,自来也没听见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黛玉道:“你且说。”宝玉又诌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腊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议事。因说:‘明日乃是腊八,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干的小耗前去打听。一时小耗回报:‘各处察访打听已毕,惟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问:‘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仓,不可胜记。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听了大喜,即时点耗前去。乃拔令箭问:‘谁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只剩了香芋一种,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并众耗见他这样,恐不谙练,且怯懦无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众耗忙问:‘如何比他们巧呢?’小耗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众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你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小姐。众耗忙笑道:‘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小耗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说着,便拧的宝玉连连央求,说:“好妹妹,饶我罢,再不敢了!我因为闻你香,忽然想起这个故典来。”黛玉笑道:“绕骂了人,还说是故典呢。”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故事。腊月初八,寒霜覆地的清晨,乡村在一点一点清醒,关了一晚上的木门慢悠悠打开,偌大的天空像母亲擦拭的瓷器一样被一点一点擦亮。乡村的早晨格外清静,没有风的声音,没有鸟的叫声,风藏在林子里等待,鸟儿停在树梢上静候,偶尔有一两片树叶飘落,也是在空中飘了又飘,才静悄悄落下来。母亲把院子打扫完,看了看堂屋门上的年画,那是一张门神画,门神下面印着日历。母亲惊讶地说:“咦,好快哦,今天是腊八节了。”想来母亲是知道《红楼梦》里的这个故事的,母亲说:“小耗子们都晓得熬腊八粥呢。”说完,开始张罗熬腊八粥。没有白米,就以苞谷粒代替。母亲说:“凑够八样儿呀,杂七杂八,八面风光,八仙过海,嘿嘿,图个吉利。”母亲把凡是好吃、能吃的东西,都尽量放一点在锅里,黄豆、绿豆、豇豆、豌豆、洋芋、白萝卜、红萝卜,要是有腊肉,还要把腊肉切成颗粒炒了放进锅里。要是有豆腐,还要把豆腐和着腊肉一起炒了,一起熬。杂七杂八一锅,不只八样儿。母亲说:“吃得全,收得全。”收回家藏在柜子里的庄稼都听得见母亲说话,它们也都懂母亲的意思,看着母亲那么卖力,庄稼再也不好意思为难一个母亲,来年庄稼们都要卖力长得好点,让母亲感到丰收的喜悦。
乡村的腊八粥都是晚上吃,这也许是因为晚上有一个更充足的时间,也许是乡村的晚上更散淡、缥缈、阴柔,在夜晚更适合享受那种静谧。这时候,乡村发着黯淡的微光,发出绵长的沉香。晚上吃腊八粥更像是一种盛典,先是把腊八粥用刷把甩洒一些在猪圈、鸡圈门上,甚至甩洒一些在小路上。这是我们乡村人祈祷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出行平安的一种仪式。仪式完毕,一家人才坐定在木桌上,享受那黑夜的静谧和腊八粥的香甜。记得有一年腊八节,母亲熬好腊八粥,先是盛了一碗,就着腊月的月光,神秘兮兮地走到我家屋后的一棵核桃树下,在核桃树干上轻轻开了一个口子,然后把腊八粥喂在口子上,母亲喃喃低语了几句。母亲转身见我在身后,像是叮嘱核桃树,更像是一种承诺:“明年结更多的核桃果儿哦,我再来喂腊八饭。”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们乡下的一种风俗,核桃树要是不结果,或者结的果不繁茂,在腊八节那天就喂腊八粥给树,第二年就会结上累累果实。有俗语说:“砍一斧,结石五,砍一刀,结十稍。”乡村的庄稼和植物们就这样默默接受着母亲神谕一样的呼唤。
乡村的腊月夜,静得像堂屋门上的那张年画沉稳而无迹,母亲的一声咳嗽,重重沉降在夜的深处,母亲说:“过了腊月就是年。”时间一趟赶一趟,又一年腊八节,我站在窗前,遥想乡村腊月的夜晚,像是翻动古诗词神秘而恬静的那一页,有簌簌的月光,有微微的泪水。
蒸花馍馍
一进入腊月里,家乡有许多像仪式一样的农事庄重而神秘。蒸花馍馍就是腊月二十八的一种仪式。“腊月二十八,把面发”“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土坝院子打扫干净,土的味道和炊烟的味道一见钟情,它们愉快地融合交织在腊月的空气里。年画、春联已经鲜活地贴在了门上。
母亲已经在头一天晚上发了蒸馍馍的面,八成麦面和二成苞谷面兑水,发在一细箩筐里。然后把箩筐放在灶房的大铁锅里煨着,用灶房的余温发。第二天,天蒙蒙亮,母亲就揭开箩筐,用手指按了按箩筐里发的面。还有些昏暗的灶房里,传来几声小老鼠唧唧的声音,声音尖而细,它们像是发现了什么好吃的,没有忍住发出的一点点笑声。母亲骂了一句:“鼠儿子们,也晓得过年了?”母亲把煨在铁锅里的箩筐抱起来,把一箩筐发好的面扣在木案板上。“哐”一声,我的心跟着猛地晃动了一下,有一种浅浅的激动,我知道母亲要揉面蒸馍馍了。我从床上弹起来,抬眼看见木窗外晃动的竹梢梢,心里充满了年的甜味和气息。
母亲站在案板前先是揣面,三木瓢麦面,半木瓢白苞谷面,化点儿碱水往里揣,使劲揣。揣碱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馍馍就蒸黄了;少了,蒸的馍馍紧绷绷的不开花,还酸吱吱的。母亲有一绝技,等把面揣匀后,就掐一小疙瘩面捏成条儿放进灶膛里烧,烧熟了放嘴里嚼,看碱放的合不合适。母亲一连串的动作十分娴熟,用手背撩那一头秀发,面粉粘上秀发,母亲也顾不了。一个人的秉性与食物的对话,它们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看母亲蒸馍馍,看母亲揣面,再看院子里洒了一地的阳光,几乎成了我记忆乡村生活的所有细节。在乡村就是人与动物的相处,人与植物的相遇。母亲对待每一样食物,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小心、淳朴。比如,母亲在揣那一团面的时候,用手触动面粉,把面粉叫醒过来,然后兑水,面粉见水的样子,“吱”一声,隆起的面粉堆降了一截子。那时候,我心里一定相信了母亲说的: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有生命的。
母亲把面揣好后,再开始做馍馍、卷花卷儿、包包子。在一大坨面上扯一小团下来,再揉再揣,揉成一长面条条,用菜刀切成无数小块,再把小块用双手捧起不离案板把它捧扯圆。包包子是把小块面用手掌按平,把炒好的腊肉馅儿包在里面,用手提折旋转捏合成。这时候,灶膛里的火旺旺的,竹蒸笼已经上汽,垫在竹蒸笼里的竹叶已经蒸得散发出竹叶的清香。母亲揭开蒸笼盖子,从最低层一格蒸笼开始,案板就在灶膛的后面,母亲捧起案板上做好的馍馍、包子,一个一个捧到蒸笼格里,摆好一格,又把另一格合上摆好。蒸笼有三四格,一格一格摆好,最后盖上盖子用猛火蒸。
二十几分钟后馍馍蒸好出笼了。出笼的馍馍放到案板上晾一阵子,趁热气,要做最后一道工序了,一个白瓷酒杯里是绿膏子,另一个白瓷酒杯里是红膏子,母亲把两根竹筷子的另一头剖成一个十字架儿,用小竹签撑开。另一根竹筷子用撑开的一头蘸绿膏子,一根用来蘸红膏子。母亲蘸了红膏子点在开花馍馍的顶上,母亲的动作很麻利,一点一点,一笼床的馍馍不一会儿就全点上了红膏子。母亲再点绿膏子,一个馍馍上,红膏子点了两点,绿膏子就在四周点上四点或者三点。这时候,母亲是一个乡村美术师,她把对红花的理解点在了馍馍上,她把对绿叶的叙述点在了馍馍上。那种笨拙的红配绿,一种最乡村的绿叶衬托红花。拳头大的包子也点上红膏子、绿膏子,母亲深知,大红大绿是过年最热闹的颜色。膏子在馍馍上还没有干,我们兄弟三个就抢起来了,腊肉馅儿的包子,一口气吃下五六个。吃完,追着落山的夕阳高一声低一声唱:“大月亮,小月亮,八月十五看月亮;大馍馍,小馍馍,家家都有花馍馍……”
那时候,过年蒸馍馍、包子是蒸一大笸箩。家家户户蒸的花馍馍够吃一个正月。亲戚朋友来了吃“八大碗”,也吃包子和花馍馍。过年来亲戚了,刚在喝黄酒摆龙门阵,母亲就把热气腾腾的“八大碗”和花馍馍端到桌子上了。这个过程很快,母亲说:“过年就是摆龙门阵和吃。”
忽然想起老家一宗事来,正月里都要走亲戚,走亲戚不能空着手,想着法子拿点什么。几个花馍馍、一把挂面,一包白糖,是正月走亲戚的厚礼了。出嫁女人回娘家走亲戚的时候,为了便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