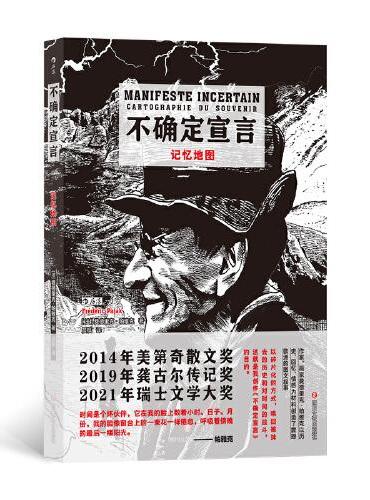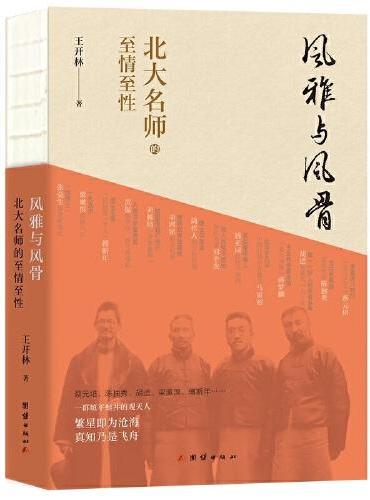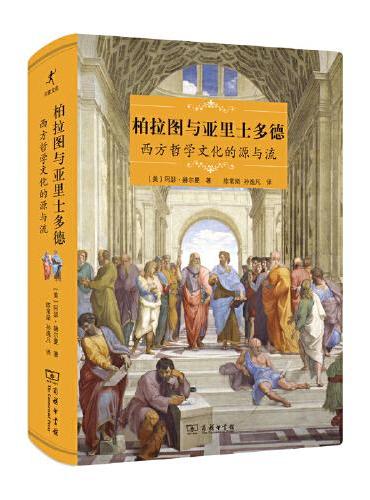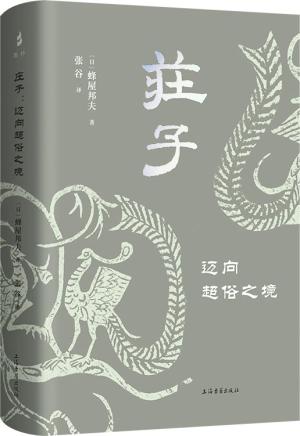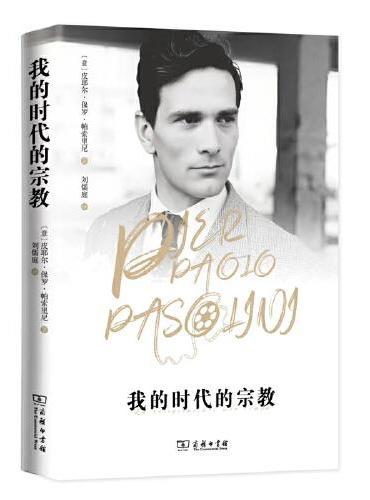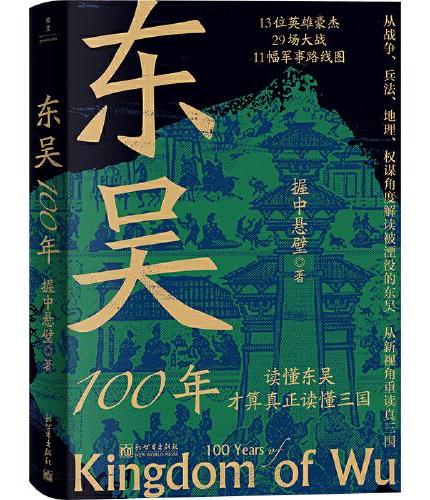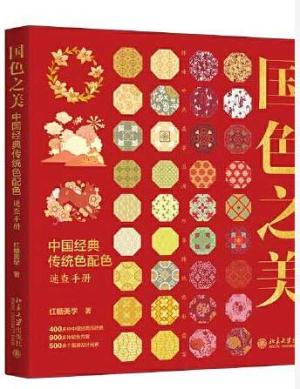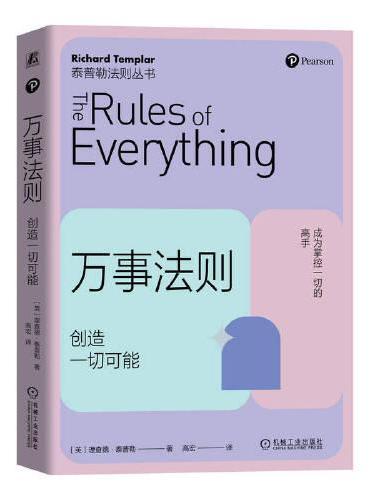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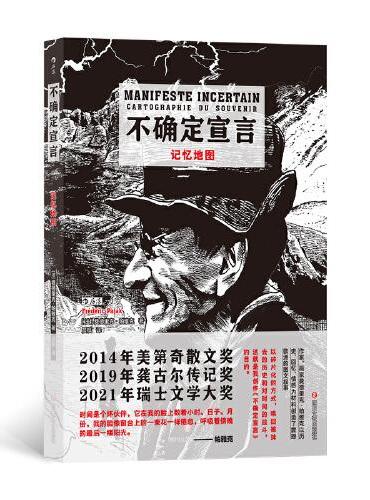
《
不确定宣言:记忆地图
》
售價:HK$
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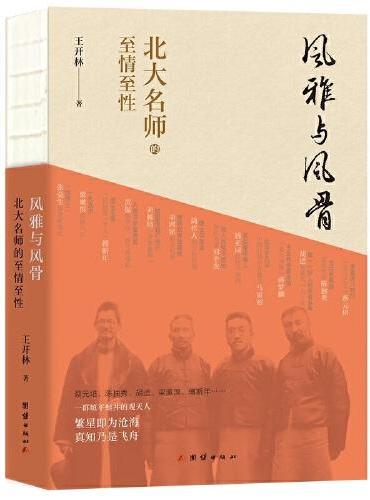
《
风雅与风骨:北大名师的至情至性
》
售價:HK$
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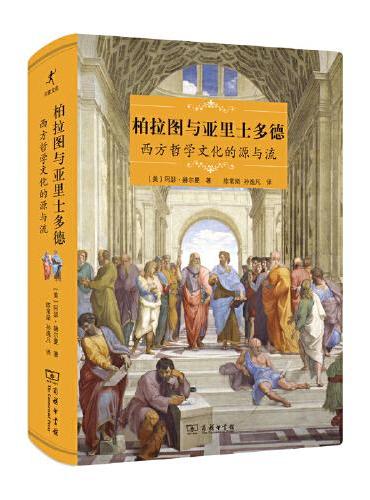
《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启蒙文库)
》
售價:HK$
2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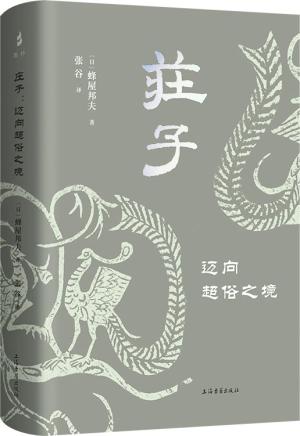
《
庄子:迈向超俗之境
》
售價:HK$
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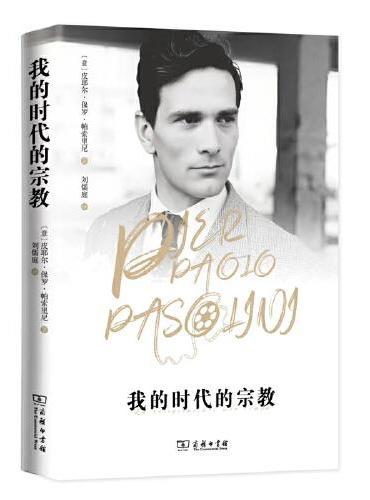
《
我的时代的宗教
》
售價:HK$
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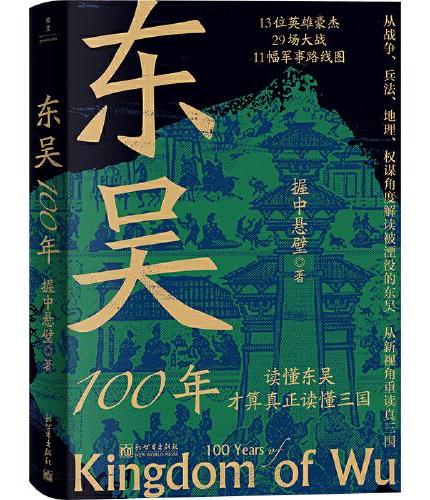
《
东吴100年
》
售價:HK$
1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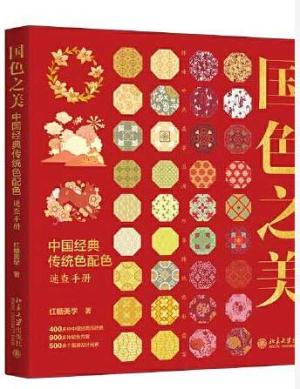
《
国色之美:中国经典传统色配色速查手册
》
售價:HK$
1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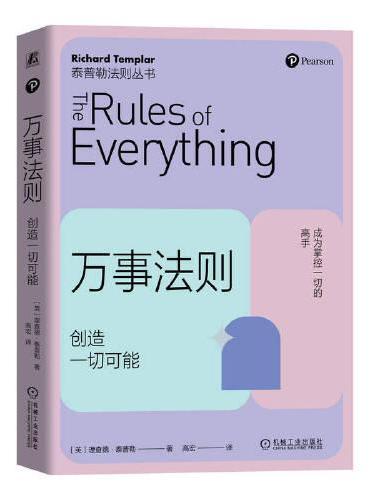
《
万事法则:创造一切可能
》
售價:HK$
69.6
|
| 編輯推薦: |
|
张玉书先生2009年获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自从事德语文学教学与研究以来,译介和评述了大量德语文学中的名家佳作,如歌德、席勒、海涅、茨威格等,本书是他最具代表性的译作的精彩结集。
|
| 內容簡介: |
|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玉书先生是我国德语教学权威和杰出的德语文学翻译家。本书选入他60年翻译生涯中的优秀代表作,包括大诗人海涅的诗选与经典评论《论浪漫派》以及小说家斯台芬?茨威格的一系列脍炙人口之作,如《夜色朦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与人物速写、传记《人类星光灿烂时》、《约瑟夫?富歇》、《巴尔扎克传》等,其中《巴尔扎克传》为译者首次发表的新译。所选篇目充分体现了译者的精湛修养、兴趣爱好与译文风格,对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具有较高的参考借鉴意义。
|
| 關於作者: |
|
张玉书,当代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4年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多年来从事德语教学与教学研究工作,为德语文学的译介及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2年当选为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德语学会)副会长,1984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0年起任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理事。1995年当选为国际日耳曼学会理事。1999年当选为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同年创办并主编中国日耳曼学第一本德语年刊《文学之路》。2006年创办并主编德语文学翻译、研究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论文集《海涅、席勒、茨威格》、《茨威格评传》、德文论文集《我的通向“文学之路”的道路》等;主要译著有海涅的《诗歌集》、《论浪漫派》、《卢苔齐娅》等;席勒的戏剧《强盗》、《华伦斯坦》、《唐卡洛斯》等;主编有《海涅文集》(四卷本)、《席勒文集》(六卷本)等。
|
| 目錄:
|
[德]海因里希?海涅
海涅诗选
海涅:论浪漫派(1833,节选
[德]斯台芬?茨威格
中短篇小说选
人类星光灿烂时(节选)
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节选)
巴尔扎克传(节选)
附录:张玉书主要文学译著
|
| 內容試閱:
|
学习外语六十年
张玉书
1953年,我上北京大学学习德语,到今天为止,正好六十年。我这里指的“学习”是正规的学习,其要求是听说读写全面发展,既要胜任教学,又能充当译员。要做到这点是我毕生的追求,常常感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危险。时时警醒,不敢懈怠。
榜样在前争相效法
西语系系主任冯至教授兼任我们班的班主任。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青年抒情诗人,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就有他的《五一前夕在德累斯顿》和《莫斯科》这两篇散文作为课文。他的著作《杜甫传》和译著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也在这时面世。我们全班同学都把他视为学习的榜样,都想走他的道路,成为能教书、能译述的日耳曼学学者。当时课外阅读材料奇缺。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德文书甚少,即使找到几本,也都是用“花体字”(哥特体字母)排印的,直如天书。一位热情的年轻讲师林书闵先生,用工整的字体把拉丁文和哥特体的字母写出来,并列比较,帮我们解决了看不懂花体字的困难。同学们找到一本十九世纪出版的海涅的《诗歌集》,大家欣喜若狂,几乎全班都成了海涅的崇拜者,半个班的同学都在翻译海涅。
1987年,我在第一届北京大学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里这样提到这段经历:
“恐怕没有一个德国诗人,其语言会像海涅的语言那样简洁明晰、优美动人,使中国学生在初学阶段就能读懂他的诗句,兴致勃勃地背诵他的名诗。海涅的迷人的诗歌,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感到德语的优美,鼓舞他们去学习这种连海涅自己也认为难学的语言。”
就在这时我一面翻译海涅的《抒情的插曲》,一面背诵海涅的名诗《歌之翼》、《罗累莱》、《颂歌:我是剑,我是火焰》……既练习了语音语调,也增强了语感, 收获很大。
1954年暑假,我译完了《抒情的插曲》,开学后交给冯至先生,满以为他会把我表扬一番。不料几周后他把我的译稿只字未改地退还给我,给我的评语只有短短的八个字“流畅有余,含蓄不足”。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悟出这八字评语的真谛乃是要我继续努力。我便把我的译稿锁进箱子,老老实实地集中精神学好德语,越学越感到自己自不量力。德语如莽莽森林,怎么可能走了几百步就已经探尽了林中的幽微?不努力跋涉怎能看到林中的绮丽风光?我于是定下心来,走自己的路,全面锻炼自己掌握德语的能力,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提高口语能力,争取尽快能够自然流畅地对话。到三年级学完,冯至先生派我去国家体委担任口译译员,居然能够胜任了。1957年留校担任助教,负责二年级的教学工作。
边教边学练习翻译
1960年下放回来,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打开久违了的德文书,如饥似渴地朗读起来,发现德文并未荒疏,口语依然流畅,德语思维的能力还有所增长。在乡下养成用默默背诵代替有声朗读的习惯,用德文思维代替阅读德文书籍,竟使我的德文水平并未下降,不觉又惊又喜。我似乎不是下放回来,而是留学归来,承担三年级的教学工作,自己编选三年级的教材,用德语授课。这时我发现教学中的薄弱环节除了口语,便是翻译。自己没有足够的翻译经验,又怎能进行中德文对比,指导学生翻译。于是我的备课任务除了朗读,便是翻译。
刚开始进行翻译,难免犯“对号入座”的毛病。我练习翻译封塔纳的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极其认真地先看懂原文,然后动笔。译完一段,念给我太太听。她认真地听完之后,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外文味道太浓,我能听出你的德语句型。”怀着侥幸的心理,我把译文寄给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同学。他比我高两级,已经发表了两部俄文小说的译著。他看了我的译文后,诚恳地告诉我:过于拘泥于原文,犯了典型的“对号入座”的毛病。他希望我跳出原文,进行“形象思维”,把同样的内容,用汉语表达出来,顾及汉语的特点,并且建议我多学习别人的翻译。
于是我对照原文,阅读前辈译者的译文,得到启发,收获很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实践。教学任务很重,编选教材的任务也不轻,正在运动期间,一整段一整段的时间包括晚上都在开会。我只好开早车,减少睡眠时间,赢得拂晓前的两小时,进行自习。读点德文,读点古文,便开始动笔翻译。稍有心得,便记下来编进练习,成为教材。
就这样练习三年,认真琢磨;汉语水平有所提高,翻译能力也有所增长。
这三年正好是物质困难时期,每天饥肠辘辘。有的朋友晚上七点上床,为了节省热能。学生病倒不少,学校也不搞运动了。我仗着年轻,又有攻克难关的决心,便充分利用这个不开会不搞运动的时机,提高德语,学习翻译。不仅如此,我还积极参加李赋宁先生特地为青年助教和研究生开设的拉丁文课。生活非常充实,时间实在太少。有人说我躲在小楼走白专道路。冯至先生有所风闻,便把我叫到他家问个究竟。我如实告诉他:我教学负担太重,只好抽清晨的时间开早车。冯先生非但没有责备我,反而把他留学海德堡时,自己用过的拉丁文课本送给我。
1963年秋天某日,冯至先生突然打电话叫我去找他,给了我一项紧急翻译任务,为《世界文学》下一期翻译几篇《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录》,本来请朱光潜先生翻译,因为朱先生另有重要工作,冯先生自己也分身乏术,这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我只问了一句:“我行吗?”冯先生说:“行!”于是我利用国庆节休假加上礼拜天,全力以赴,在两天半时间内译出一万一千多字,周一向冯先生交卷。这篇译文发表在同年11月号的《世界文学》上,就像当年高考时考上北大,同样地令我喜不自胜。我等于取得了翻译合格证,自信心大大增强。
接下来,一位好友约我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翻译席勒的美学论文。《译丛》主编李健吾先生是写作、翻译双绝的大师。我的译文得到他的肯定,被《译丛》采纳,给我很大鼓舞。接着我又为《译丛》翻译了莱辛的《论寓言》和海涅的《论浪漫派》。每天都在进修,每天都在进步,教学质量也随之提高。
翻译中断学习不停
在《论寓言》发表之后,《论浪漫派》尚未发稿之际,刮起了漫天狂风。史无前例的劫难突然自天而降,大学成为战场,文坛一片凋零。外国文学成了禁区。翻译练习就此中断,但是学习外语并未停顿。
“文革”期间,图书馆关门。我自己藏书有限,整理书箱,发现我的一位世伯在我考上北大时送给我的礼物:法文写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入门教材,和意法法意、西法法西两本字典。这是我世伯三十年代留学巴黎时用过的书籍。我想起他给我的临别赠言,让我在德语、英语之外,多学一点其他语言。我便利用大学二年级时和法专的同窗好友互教互学学到的那点基础法语知识,学起意大利文来。正好是停课闹革命的时候,不打派仗者如何打发光阴?有人自己动手制作沙发,工艺还颇为精美,有人上下午都用来对弈,棋艺大有长进。我便学习意大利文。当歌唱家的表姐帮我找来普契尼歌剧《托斯卡》的文学脚本,我边学边译,在一年之内抄完全剧歌词,并且断断续续地把它译成中文。“四人帮”倒台后,这篇译文发表在《音乐艺术》1981年第二期上,让我又一次尝到新译者得到承认后的激动、欢欣和兴奋的心情。
可是另一种声音也在我耳边响起。1969年底,北大、清华一半以上的教职员下放到江西鲤鱼洲。鄱阳湖畔夜里寂静无声,可是要我们通宵看守材料场,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我们全班不是女教职员,便是年长老师,我给自己安排了夜里两点到四点值班。六十岁的老教授赵绍熊先生主动要求和我做伴,一同看场。赵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是位经验丰富的英语教授。我们一老一少在夜深人静时海阔天空地神聊,不觉谈到外语学习。谈得投机,我一时忘乎所以,竟不顾禁忌,向老师吐露心声。我告诉他,一旦“文革”结束,除了德文之外,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语,譬如英、法、意、西等等,很想听听他的意见。赵先生沉吟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慢慢悠悠地对我说:“我看能把一门外语真正学好,就很不容易了。”赵先生这句话我也没有忘记。
事实证明,要学好德文和中文,做一个称职的日耳曼学学者,做一个好的翻译家的确花去我绝大部分的精力。可是,再学一些其他外语,有助于专业外语的学习。我从不奢望像有些大师那样精通十几种外语。我在兼学其他外语时,绝不忘记以德语为主。在海涅的作品里,有很多法文。在谈论西方艺术时,必须知道一点意大利文。至于英文,如今已成国际语言,连理工科的学生都要掌握英文,文科学生怎能不会英语?
海涅 席勒 茨威格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5年我被国务院特批为博士生导师。仅仅能教德语,能进行翻译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要求,必须加强科研。我便根据教学需要在以往教学和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科研。我的科研和翻译都以海涅、席勒和茨威格为重点,并由他们三人延伸到德国浪漫派,德国古典主义和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德语国家的文学。
海 涅
海涅的理论名著《论浪漫派》我在“文革”前早已译出,经过认真修改,在1979年发表后, 反响强烈。十年浩劫,文风败坏,浮夸虚饰之词泛滥,乱扣帽子之风盛行,评论挥舞大棒,褒贬随意、语气专横,中国语言横遭蹂躏。这时海涅的《论浪漫派》译文面世。读者发现,海涅以诗人的笔触,思想家的睿智,一反德国学究贫乏干瘪、枯燥无味的风格,论述德国文学的发展,介绍各派作家的特点,写得轻盈流畅、深入浅出,显示出诗人海涅思想家的风范。1986年,冯至先生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我主编的《海涅文集》, 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会,使我把教学科研和翻译结合起来。《海涅文集》共四卷,第一卷便包括《论浪漫派》和其他理论文章。第二卷是诗歌卷。海涅的诗,自然质朴、诗意浓郁,充满了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和失恋者的多愁善感,哀而不伤,艳而不俗,新颖独特,不落窠臼。诗句音乐性强,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感染力,让学生感到德语的美。冯先生让我重译《诗歌集》。我拿出三十多年前锁进箱子的旧稿,看出当年的不足,句子淡而无味,拖泥带水。诚惶诚恐地开始重新翻译。几十年来,我从未忽视提高汉语的努力,为的是借助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来丰富我译文的表达能力。在翻译海涅的诗歌时,我有意识地每天阅读唐诗宋词,还背诵或熟读了其中的名篇,得益匪浅。学习外语的人,汉语往往是他的薄弱环节。必须努力提高汉语水平。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古代文学是我们的优秀教材,认真学习,有助于我们语言的凝练。
海涅是个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诗人。从青年时代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想挥动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驱散笼罩在德国大地上封建势力的妖风鬼气,到后来同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希望实现共产主义。从歌唱夜莺玫瑰的爱情诗人变成剑和火焰的战斗诗人。极“左”分子凭着海涅在《卢苔齐娅》法文版前言中的一句话,断章取义,批评海涅害怕共产主义,于是我们于1987年和1997年,在北京大学两次举办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为海涅平反昭雪。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自然是海涅自己说的话。在《海涅文集》第四卷《杂文卷》里,我集中力量翻译了海涅后期的著作:《自白》、《回忆录》和通讯集《卢苔齐娅》。中国读者可以从译文看到,海涅真正反对的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行绝对平均主义之实的政治骗子。读者通过完整的译文全面了解诗人,自己会作出判断,给诗人以公允的评价。
席 勒
大学二年级时正值纪念席勒逝世150周年。为这位伟大诗人的生平所感动,我开始阅读他的成名作《强盗》。可是水平太低,查了许多生字,仍然看不大懂。一晃三十多年过去,1979年底我初访德国,正好纪念席勒诞生220周年。我开始认真阅读席勒的作品,为席勒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和卓越成就所折服。这位天才的戏剧家只活了四十六岁。这短短的一生, 活得辉煌, 活得精彩,富有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生活在封建势力顽固的德国,却从未停止反抗封建暴政。他的一系列名剧,从《强盗》到《威廉?退尔》是一声“打倒暴君”的战斗号召的变奏。席勒一直处于贫病交加的逆境之中,长年为疾病折磨,在生死线上挣扎,却一直分秒必争地奋笔疾书,无视病痛,不畏死神,以昂扬激奋的乐观主义高唱《欢乐颂》,歌颂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把人的尊严、价值、勇气发展到极致。明知来日无多,更加珍惜光阴。直到弥留之际,他的羽毛笔,方从他的手中脱落。这样一个为人类献身,可惜英年早逝的德国古典大师,世界文学的伟大诗人,他的精神和他的著作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于是萌发了翻译席勒戏剧的念头。
为了做好准备,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我给博士生硕士生开的古典文学课,有几学期就是和学生一起认真细致地阅读分析席勒的剧本,用日常的德语来解释艰深难懂的词句和段落。
但是理解和翻译是两回事。理解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轻而易举地以恰如其分的词句把原意再现于中文。翻译席勒的戏剧不同于翻译海涅的诗文,要正确理解原文已属不易,而要用中文再现原文的气势和深邃就更加艰难。尽管我一直在提高汉语水平, 但要做到流畅准确而又含蓄,仍然感到力不从心。
几十年来,我从未忽视提高汉语的努力。现在翻译席勒,我更有意识地学习古人行文的语气,总不能把三十年战争时天主教国家的联军统帅的语气写得和海涅的诗歌一样佻达轻快,那股凝重庄严的气势必须由文字,由中文来展现。于是有意识地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作为我的必修课。经过朋友们的帮助,大家的共同努力,《席勒文集》六卷集终于在2005年席勒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时完成。
茨威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译的《茨威格小说四篇》出版,接着,两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发表《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茨威格悄然来到中国的图书市场,疯魔了最敏感的读者群大中学生,不久就以燎原之势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茨威格热。到九十年代,这股浪潮越过海峡传到彼岸,在台北有两家出版社,志文出版社和光复书局出版了我翻译的茨威格小说。德国的读书界对于中国的茨威格热深感意外,德国《图书交易报》约请我介绍茨威格在中国何以如此受人欢迎。我为该刊撰文说明原因,主要是由于读者对深层心理描写的兴趣。意识流小说和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几乎和欧洲同步介绍,同步发展。1949年后,这种文学流派和弗洛伊德的学说都被封杀,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重新介绍。
读者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简单化平面化的人物描写深恶痛绝,接触到意识流派文学,感到耳目一新,发现人性和爱情不该被否定。茨威格作为这类流派的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浓郁的诗意,得到中国读者持久不衰的欢迎,也是情理中事。读者的需要成了对译者的命令。我自当竭力满足读者的需求。于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便致力于研究和介绍茨威格的小说。2004年我开始撰写《茨威格评传》,这是我几年来研究结果和教学心得的积累。
由于茨威格的爱情小说广泛流传,造成一种错觉,就仿佛作者只是一个醉心风月不问政治的作家,不应得到高度评价。我在教学和评论中,尤其在我的《茨威格评传》中,虽然努力对茨威格作出全面的评介,但是归根到底,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依然是茨威格自己的作品。于是我着手翻译《约瑟夫?富歇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约瑟夫?富歇,法国大革命时期翻云覆雨的历史人物,法国政坛上臭名昭著的千面人和变色龙,三朝元老,始终位居要津,是个丧尽人格,投机革命,玩弄政治,牟取私利的无耻政客。此书于2007年翻译出版,至少让人比较全面地看到,茨威格不屑于像富歇那样地过问政治,他想用这本书让读者认清这个政治骗子的嘴脸。 2012年8月和11月,我翻译的两部茨威格作品《人类星光灿烂时》与《良心反抗暴力》分别出版,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茨威格的认识。他实际上是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斗士,他以自己的方式跟当代的专制暴政、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分子进行不懈的斗争。
2012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国际斯台芬?茨威格研讨会和《茨威格读本》的首发式。与会的中国作家纷纷谈到自己从茨威格的作品中获益良多,有助于他们的创作。而年轻的学生,新生代的茨威格之友表现出来的激情和渴望,使我思考,是不是把茨威格生前未能发表的作家传记《巴尔扎克传》译成中文,献给中国读者。我征求几位朋友的意见。一位年轻的朋友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翻译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另一个朋友设法消除我的顾虑:宁可三年后,来不及完成这项工程,使之成为未完成的交响乐留给后人,也不要踌躇不前,因而贻误时机,最后喟叹时光虚度,追悔莫及。于是我欣然命笔,开始翻译。翻译的过程历来是我学习的过程。这次更是如此。所幸有老朋友和热心的年轻朋友帮忙,使我克服了心理障碍和具体困难,得以实现“活到老学到老”的夙愿,完成了前三部分的初稿。现在把其中第一部分共六章,经过修改,整理出来,作为这本《自选集》的最后部分,连同歌德、海涅、茨威格的其他作品,献给读者。
2013年4月7日蓝旗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