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登入帳戶
| 訂單查詢
| |
||
| 臺灣用戶 |
| 品種:超過100萬種各類書籍/音像和精品,正品正價,放心網購,悭钱省心 | 服務:香港/台灣/澳門/海外 | 送貨:速遞/郵局/服務站 |
|
新書上架:簡體書
繁體書
四月出版:大陸書
台灣書 |
|
|
||||
|
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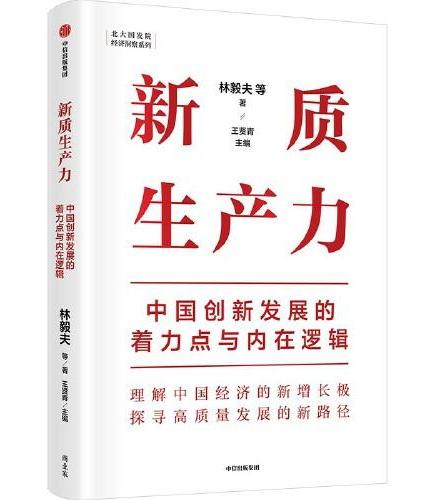 《 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 》 售價:HK$ 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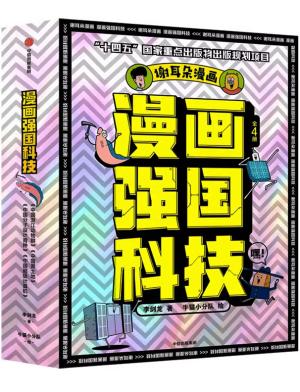 《 “漫画强国科技”系列(全4册) 》 售價:HK$ 1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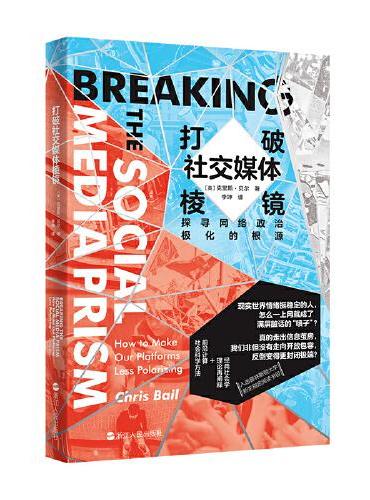 《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 售價:HK$ 69.6  《 那一抹嫣红 》 售價:HK$ 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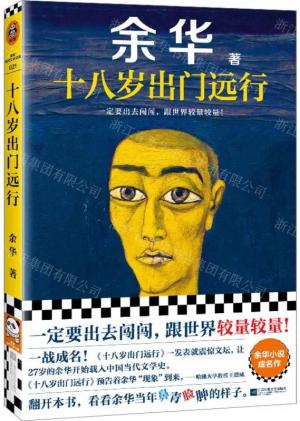 《 十八岁出门远行 》 售價:HK$ 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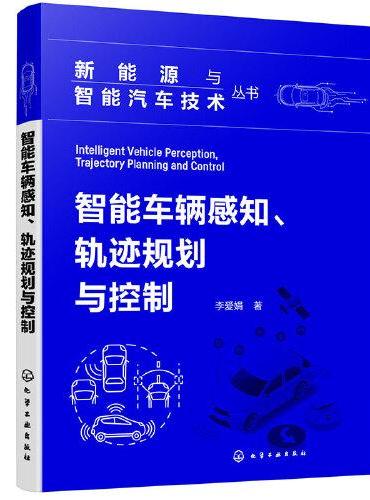 《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技术丛书——智能车辆感知、轨迹规划与控制 》 售價:HK$ 1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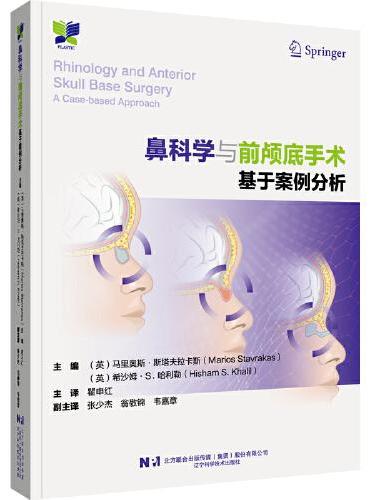 《 鼻科学与前颅底手术——基于案例分析 》 售價:HK$ 3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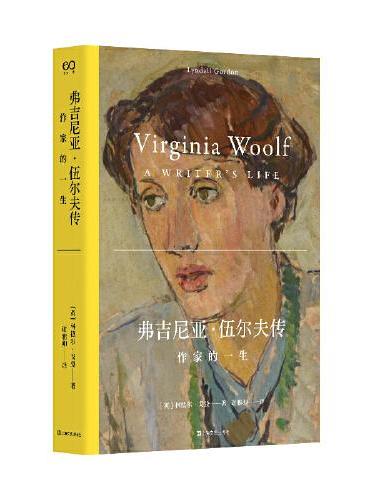 《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作家的一生 》 售價:HK$ 105.6
|
|
| 書城介紹 | 合作申請 | 索要書目 | 新手入門 | 聯絡方式 | 幫助中心 | 找書說明 | 送貨方式 | 付款方式 | 香港用户 | 台灣用户 | 大陸用户 | 海外用户 |
| megBook.com.hk | |
| Copyright © 2013 - 2024 (香港)大書城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