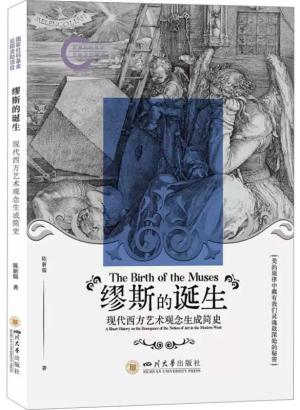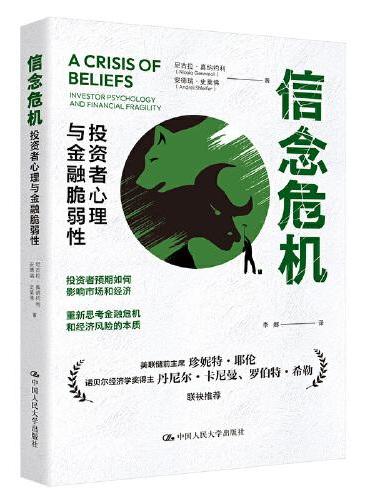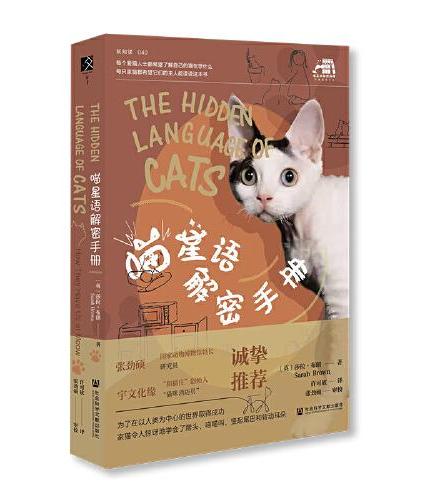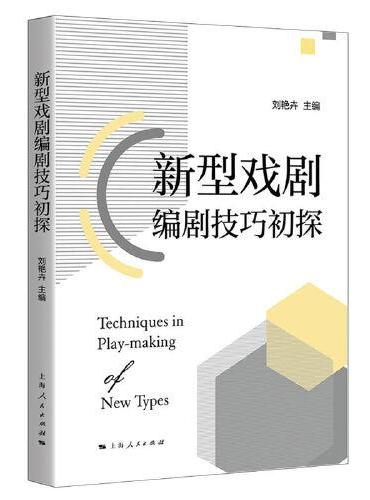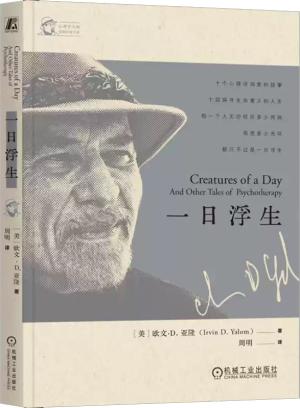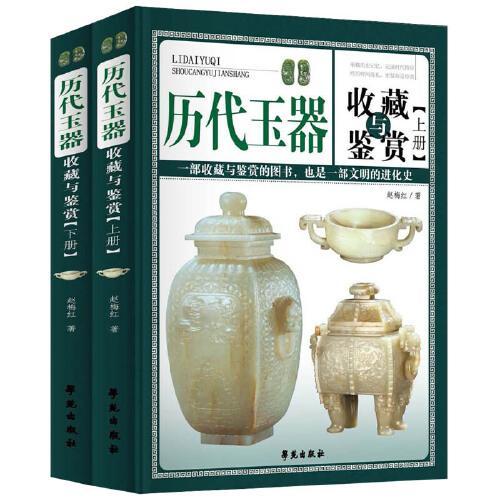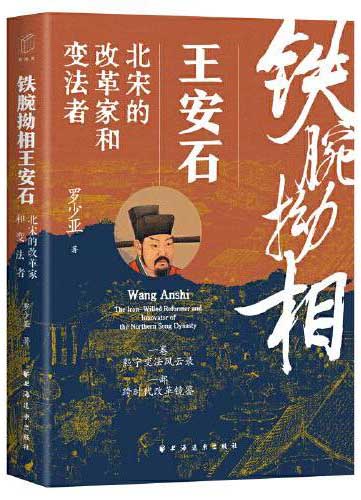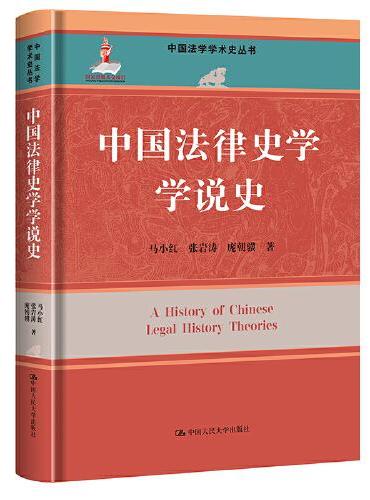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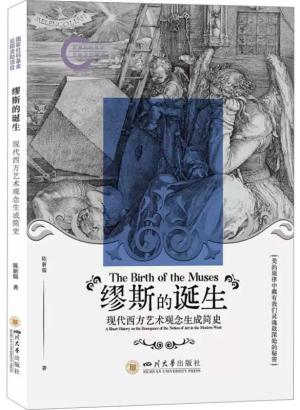
《
缪斯的诞生 现代西方艺术观念生成简史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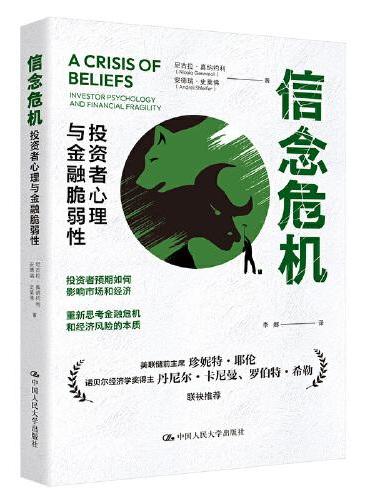
《
信念危机:投资者心理与金融脆弱性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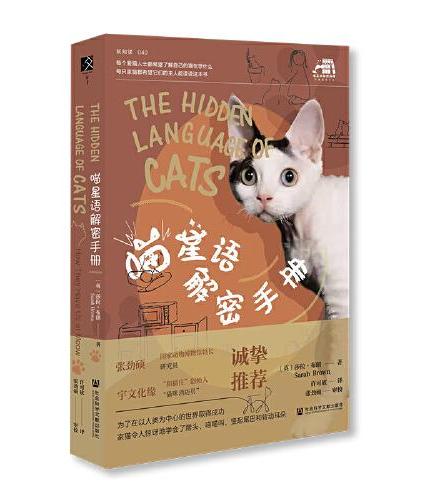
《
喵星语解密手册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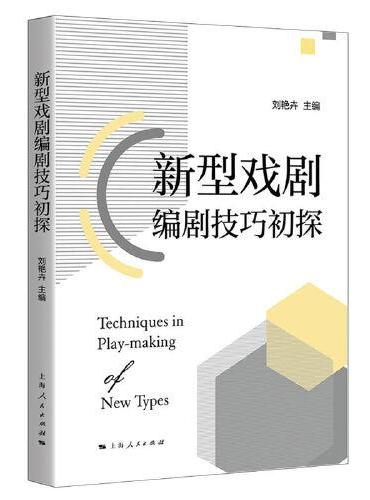
《
新型戏剧编剧技巧初探
》
售價:HK$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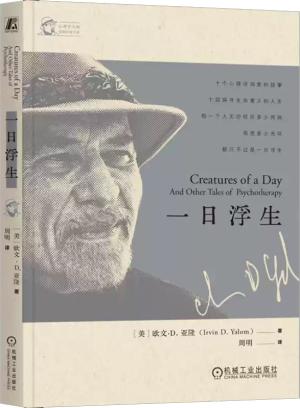
《
一日浮生
》
售價:HK$
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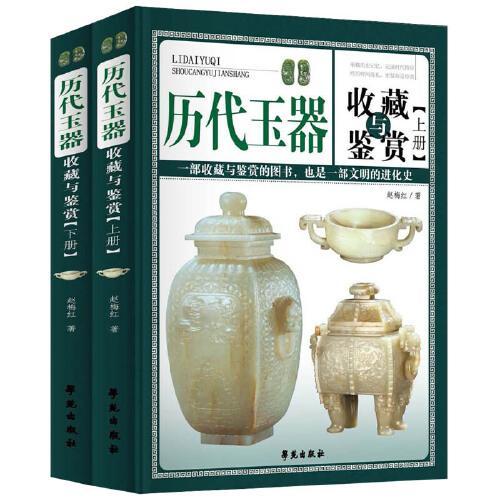
《
历代玉器收藏与鉴赏
》
售價:HK$
3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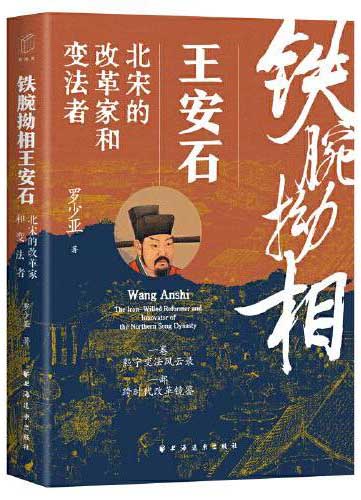
《
铁腕拗相王安石:北宋的改革家和变法者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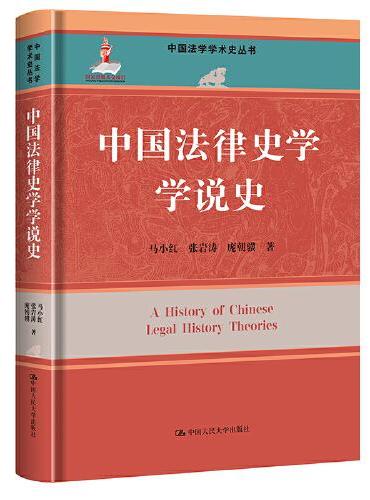
《
中国法律史学学说史(中国法学学术史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HK$
184.8
|
| 編輯推薦: |
1.该书立足中国实践、富有全球视野,是推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服务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一部力作。
2.该书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破解经济金融化时代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
|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公共风险为逻辑起点,突破传统理论框架,提出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全新认知范式。全书从财政与货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与央行三个维度展开,揭示现代经济中财政作为货币基础、政策协同枢纽和公共风险最终承担者的核心作用。
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国家信用源于国家拥有的征税权,主权货币本质是国家信用的具象化。财政收支直接嵌入基础货币循环,赤字常态化体现货币的内生性。国债不仅是融资工具,更是资本市场定价基准和货币政策操作载体。人民币国际化需依托财政向全球提供无风险资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趋向一体化。经济金融化推动需求管理转向公共风险管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财政作为“最后兜底人”只是公共风险治理中的行为分工,稳估值优先于稳币值。
财政与央行的协同治理逻辑。全球公共风险治理实践显示,央行独立性随着通胀机理的改变而改变。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应统筹包括铸币税在内的公共资源。财政与央行应共同构建基于公共风险导向的政策框架。突破界域思维,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目标,实现财政金融治理体系的动态适应性变革。
本书创新性提出“货币状态论”、财政货币“量子观”等理论,强调财政在信用货币体系中的本源地位,为理解现代经济运行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对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
| 關於作者: |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监委第一届、第二届特约监察员。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级专家称号。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担任多个中央部委及地方省市的政策咨询委员、顾问或专家。曾长期担任国家医疗卫生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
| 目錄:
|
绪 ? 论
第一篇? 财政与货币的关系
第 一 章? 货币、国家信用与征税权
第 二 章? 财政收支与基础货币、货币流通
第 三 章? 赤字、债务与铸币税
第 四 章? 利率与财政的可持续性
第 五 章? 财政与人民币国际化
第二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第 六 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变迁
第 七 章? 货币政策独立性与财政政策
第 八 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第 九 章? 金融救援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第 十 章? 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第三篇? 财政与央行的关系
第十一章? 财政与央行的职能和机构关系
第十二章? 央行的利润来源与上缴财政情况
第十三章? 主要国家外汇储备管理中财政与央行的关系
第十四章? 央行的资产与央行持有国债情况
第十五章? 金融监管中财政与央行的关系
第十六章? 财政与央行的政策协同机制
第十七章? 主要国家国库管理制度与比较
参考文献
|
| 內容試閱:
|
绪论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的重要性在现代经济中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金融化,商品在金融化,社会财富在金融化,定价机制在金融化,经济关系也在金融化,金融与实体经济正不断融合,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金融化将经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关联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隐性“风险链”,一旦触发,风险就会外溢,快速系统化、宏观化和公共化,形成公共风险。在此背景下,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不断变化,其底层逻辑也变了,用传统理论已经难以阐释新的现象(刘尚希,2024),亟须重新认识财政与金融的关系。
本书尝试以公共风险的新范式和新认知,探讨财政与货币的关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中央银行的关系。这个认知框架的“新”体现在: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超越以宏观均衡为目标,以虚拟理性超越实体理性,以行为分工超越界域划分,以货币状态论超越货币数量论,以财政货币“量子观”超越财政货币“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思维,以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超越财政货币政策二元协调论,稳估值优先于稳币值,等等。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从理论层面探讨财政与货币的关系,从政策理论与实践层面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基于国际实践和国际比较来阐释财政与央行的关系。这三个层面是宏观经济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对这三个层面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决定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效能。
一、财政与货币的关系: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
从理论上探讨财政与金融的关系,要从研究财政与货币的关系开始,货币是财政金融中最基本的问题。
(一)国家主权信用是国家主权货币的基础
从本源出发探讨财政与货币的关系,需要从外到内,从表象到基础,层层递进地深入分析。纵观经济学思想史和金融学家对货币起源的研究,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这种看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金属货币的时代,金银等商品自身的稀缺性和内在价值创造了货币自身的信用。在信用货币时代,国家信用是货币流通的基础。而财政的征税权支撑着国家信用。征税权的可实施性代表着民众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认可和对施政者的支持,是社会共同契约达成的标志。马克思曾说:“赋税是国家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中,只有可以用来缴税的货币才具有信用,整个社会才会接受它。顺着这个逻辑链条推理,征税权衍生了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又衍生了主权信用货币。因此,可以说,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
(二)财政收支过程即货币流通过程
财政收支本身就是货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影响和调节货币流量。财政收支活动和银行信贷活动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但从货币流通层面来观察,却发现它们是相互贯通的,呈现一体化特征。财政收支直接嵌入基础货币投放和回收过程:一方面,税收收入、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财政资金进入国库,相当于等量基础货币从经济中收回;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国库现金管理等财政资金从国库拨付,相当于等量基础货币投向经济。保持经济中的流动性合理充裕,不仅仅是货币当局的任务,更需要财政收支活动来协同支撑。财政收入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具有紧缩效应,而财政支出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具有扩张效应,其净效应取决于是财政盈余还是财政赤字。若出现财政盈余,则是净紧缩效应;若出现财政赤字,则是净扩张效应。当然,从时间维度来看,若财政盈余扩大,则是紧缩效应的增强;若财政赤字缩小,则是扩张效应的减弱,也可视为时间维度上的收缩。
当经济运行出现“流动性陷阱”时,减税增支,实行赤字政策,能把经济从陷阱中拉出来。财政收支具有调节货币流通的功能,使货币由中性转变为非中性,这是财政政策得以存在的金融基础。单一货币规则理论一度流行,是以财政收支平衡为条件的,且假设经济中的货币收支循环与财政无关。其实质是小政府、小财政观念下的自由市场逻辑,且假设不存在公共风险。公共风险、经济金融危机不仅产生了政府财政救援的需求,也持续扩大了财政规模。财政规模占经济规模的比例越大,财政收支对货币流通的影响越大,货币的非中性化也越强。不过这种影响和变化常常被忽略,误认为货币流通仅仅由货币当局所决定,并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上争论不休。这种误导与货币主义的流行是分不开的。
(三)财政赤字、债务的常态化,是财政金融属性外在化的表现
目前人们对财政赤字、债务的认识尚未跟上政策实践的发展。回溯中国赤字政策实践的历史演变,20世纪80年代前后从追求预算的年度平衡到预算的跨年度平衡;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盟发布《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赤字、债务常态化,只不过是设定了天花板,基本上放弃了收支平衡的财政规则。从经济金融化和财富虚拟化的趋势来看,不顾现实变化再回到财政收支平衡的状态几乎难以想象。近年来热议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提出了更大胆的观点:以通货膨胀、就业为底线来设定财政赤字的天花板。该理论彻底抛弃了财政自身平衡的必要性,国债在其利率为零时相当于货币,无须归还,也不构成财政负担和国民负担,相反,还能给国民提供金融资产。这时,货币转化为“国民资本”,不只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按照这个逻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是由货币当局来提供,还是由财政当局来提供,似乎不再是什么问题,其条件是利率的高低,只剩下付息成本的约束。赤字、债务的常态化,以及规模的不断扩大,反映出通过财政方式来投放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表面上看,赤字、债务是政府财政的需求导致的,而从深层次看,是经济社会的需求导致的,这种需求源自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公共风险改变了货币状态(不同主体持有的货币的非同质性),也需要财政来强化货币的非中性,通过财政赤字、债务来投放货币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从货币供求关系来看,政府财政赤字、债务的常态化也反映出货币不再是由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经济社会的内在需求导致的内生变量。即使货币当局可以控制货币的供给,也无法控制流通中的货币状态。货币状态可以改变货币供求关系,例如,从货币数量论来看,货币供大于求,似乎是流动性过剩,而从货币状态来看,却是相反的,货币供小于求,实际是流动性不足。现实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货币存量(如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却是流动性紧张,物价下行。从货币数量论来看这是矛盾的,于是乎经常被人问“货币到哪里去了”,从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答案,反而令人迷惑不解。而从货币状态[ 货币状态可借用物体的三种存在状态来说明。任何物体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可以有三种形态:气态、液态和固态,货币的常态就像水,一定条件下则会转向气态,或固态,从而在货币存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出现流动性过剩或者不足。作为价值尺度,货币是同质性的,但对于不同的货币持有主体来说,则是非同质性的,这是导致货币“相变”的根源。货币状态的变化与公共风险直接相关。]来看却是可以解释的。可见,传统的货币数量论遮盖了货币状态的变化,从而偏离了现实。货币状态一旦发生改变,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会失灵,需要财政来供给货币。在公共风险水平上升、大众预期转弱的条件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就会大幅度下降,甚至失效。这就需要财政一方面供给货币,另一方面控制公共风险,为货币政策创造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