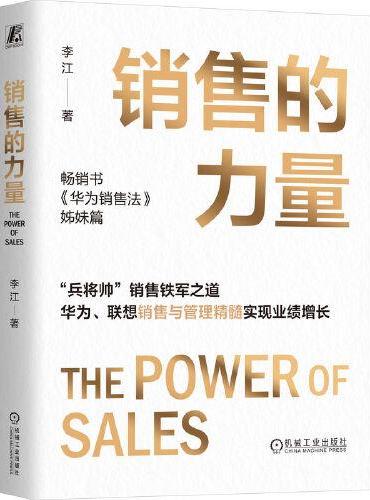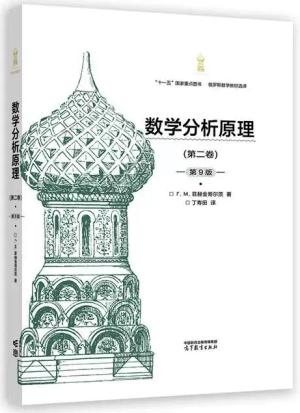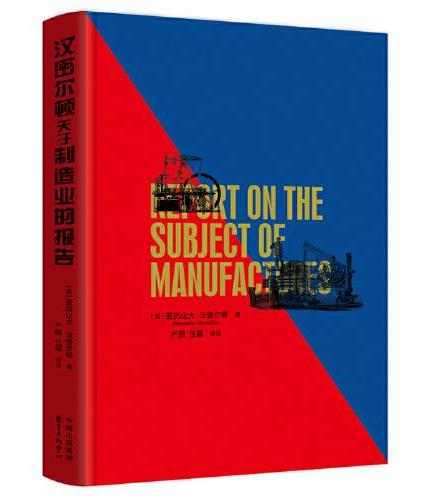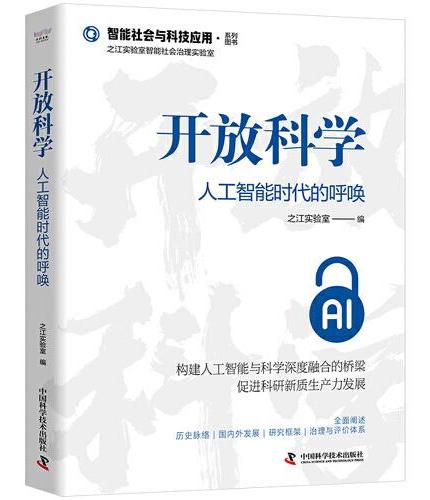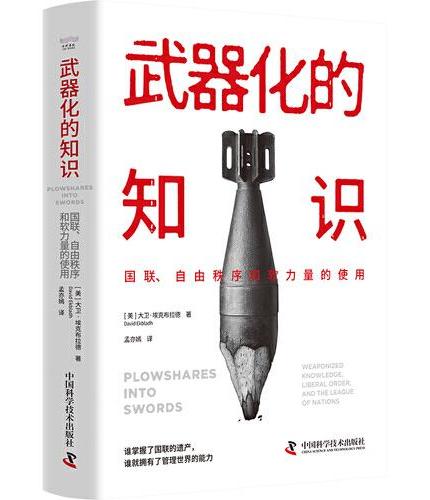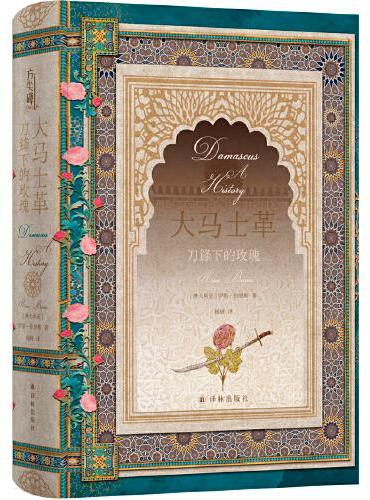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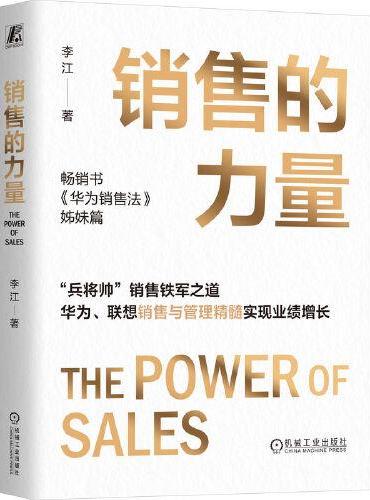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HK$
97.9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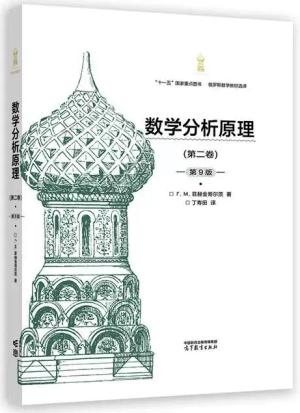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HK$
86.9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HK$
3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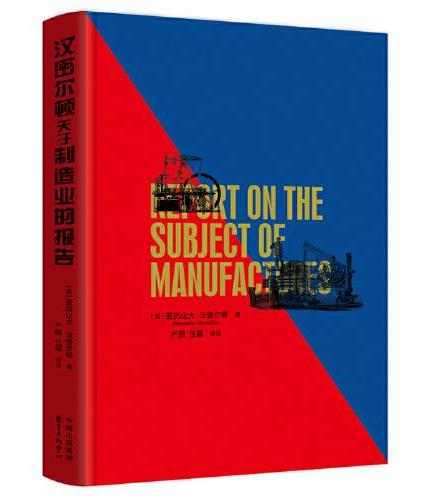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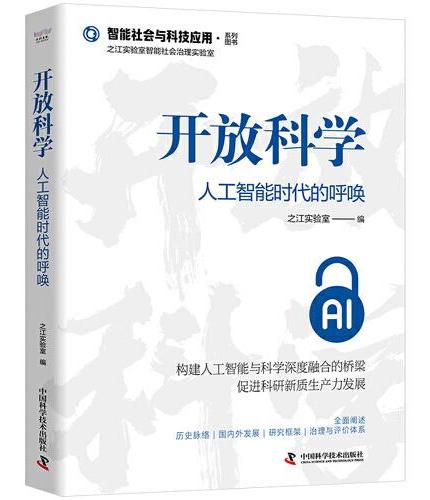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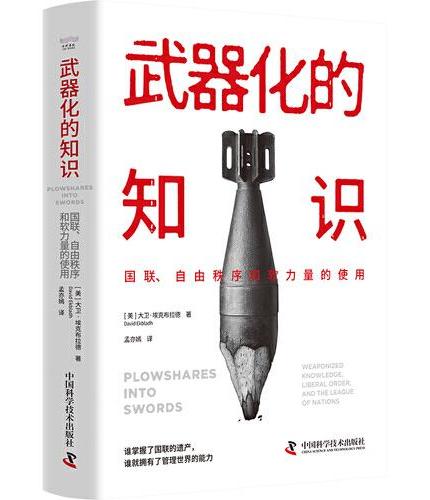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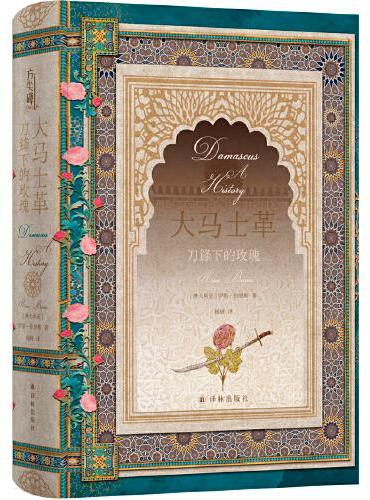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HK$
130.9
|
| 編輯推薦: |
|
一个孩子的记忆深处,充满烟火气的童年史诗,富含诗意与雅趣。孩子眼里的花草树木、鸡鸭蚁虫、田野泥巴、四时节令,独属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童年印记。远去了的乡村图景,一代人共同的生活经验,照见你我来时路上的至亲至情。关于故土之上的故旧、故事,关于生命、爱、聚散,既是一个人的文学回望,也是一代人的精神根系。附赠“童年印记”收藏卡,知名插画师范薇绘制。随机赠送,书签、摆件两用。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回顾自己鲁南农村童年生活与见闻的随笔集。
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有很多树,树上有很多鸟,虫子,果子,叶子,花……树的上面是云和天。太阳是亮的。每个白天都是在这些树下吃,玩,跑来跑去。家里的人,狗,猫,客人,也都在这些树下走来走去。
为了有出息,她按照别人说的,离开了自己的院子和大树……
四十多年后,当她回望来时路,才惊觉这段尘封旧事是她的人生之丹、内力来源,使她的生命不致凋零。
|
| 關於作者: |
|
廉萍,山东滕州人,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近年师从扬之水研究中国古代名物,著有《荷叶浮萍:〈红楼〉万象随笔》。
|
| 內容試閱:
|
1
有一个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有很多树,树上有很多鸟,虫子,果子,叶子,花……树的上面是云和天。太阳是亮的。每个白天都是在这些树下吃,玩,跑来跑去。家里的人,狗,猫,客人,也都在这些树下走来走去。
有一天,有人说,你要长大,将来要有出息,就把她送到了学校。在学校里,她很努力,成绩很好,所以,小学毕业上了初中,初中毕业上了高中,高中毕业考了大学,然后一路读到博士。博士毕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孩提时候的那个院子,那些大树,早就不知哪里去了。
她的工作是出版。她知道这份工作的流程:先砍倒一些大树,锯开,树汁浓烈的味道弥散在林间,晒干后仍不消散。把大树送到工厂,变成纸。把纸裁成一样大小的一摞摞,把别人想说的话印在上面。如果有人想看这些话,这本书就会被卖出去,变成钱。钱里面的一小部分,变成她的报酬。这份报酬,就是她那么多年努力读书和工作的市场价格。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还想做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这本书里,每一页都画上大树,大树上有鸟,有虫子,有果子、叶子、花,有原来认识的那些人在树下走来走去,有狗卧着,有猫在伸懒腰,舔爪子。
是的。为了有出息,她按照别人说的,离开了自己的院子和大树。努力很多年,如今每天,就是去砍倒别人的树,在树做成的纸上,印些不知什么东西。能想到的最好结尾,就是有一天,坐在光秃秃的世界上,一页页翻看,书上的大树,和树下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努力。
二○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
十岁以前,我跟着姥爷姥姥,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进院门,是一棵木槿树,碗口来粗,歪脖子。印象里,这棵木槿好像一直都在开花。不过这不可能,因为鲁南的冬天也很长。也许因为冬天我基本不出屋门,反正开花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树下,或者树上。可是我并不怎么喜欢它。花朵那么大,随随便便就开了,又随随便便落了。还开得满树都是。自己都不重视,别人自然也不爱惜。再说每天爬上爬下,近则不逊。落了的样子也不好看,紫了吧唧黏黏糊糊,都不爱碰,踩到了,要去沙子里搓半天鞋底。花开的样子也不好看,花瓣又大又薄,一碰就坏。小时候用的作业本分两种,一种五分钱一本,纸张光亮挺括;一种两分钱一本,纸软趴趴的。木槿的花瓣就像两分钱的。开的时候,大敞四开,花蕊都亮在外面,一点不害羞。所以这种花都是伸手摘下来,坐在树上,往人头上扔,或者砸水缸,砸蚂蚁,砸马蜂,砸蜘蛛网,砸枣树,砸石榴树。或者摘下来几朵,堆在一起,用石头砸。砸得花汁四溅,弄一手,再去洗。溅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会被大人说一顿。也就是说说,并不禁止。
后来就离开家,读书去了。第一次在书上读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的时候,真是呆了一下,因为看注释说“舜华”就是木槿。这种花,如果用来形容女孩子,印象里也只能是那种疯疯张张、没心没肺的傻大姐,怎么就《诗经》还“舜华”了?后来又看到,说它朝开暮落,朝荣夕悴,一下子就注入了人生无常的感觉。好像一个认识了很久的普通人,突然就文艺了,或者发达了。心生敬意,却又不太适应。
北京街头有很多木槿。每次看见,都想抬手,抬抬又放下来。站着看一会儿,就走了。感觉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大都是灌木,没有那么粗,也没有歪脖子可以让人爬上去。
二○一三年四月一日
3
房文,据说是个疯子,但我没看出来。只记得他个子高,胡子、头发都很长,脏且乱,穿一件破大衣。像个要饭的,但不是要饭的。他会大清早站在院子门口,一言不发。姥爷有时给他一个瓶子,一毛钱。他很快就把东西买回来。那时酱油好像八分钱一斤,醋七分,剩下的零钱就归他了。家里的这种零活儿差不多都是他的。他也像家里的一个人,就是不在家里住。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等我长到差不多五六岁,就瞧破了这里面的机关,主动要求去打酱油。剩下的两分钱,可以买一大把糖豆。还包揽了买烟的活儿,一包“普滕”一毛四,运气好可以剩六分钱,买一大把糖块。房文少了这两份差事,好像有点不高兴,来得少了。不过那时候,谁又能争得过我呢?
上学后,学校操场一角有个破房子,门窗都没有。我和几个胆大的孩子跑过去看。里面没人,没有床,地上铺着麦草。一件破大衣挂在墙上。我认识那件大衣,才知道原来房文住在这里。地上还有几块砖头,支着一口锅,锅里几块煮红薯。我们每人拿一块,吃完,就赶紧跑出来了。因为有人说,他看见了会骂人。
后来,就没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么多年,好像也从没人跟我再提到过他。没听说过他有父母,兄弟,家,也不知他还有其他什么经历。房文,究竟只是他的名还是连姓带名,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无端觉得,如果写下来,确定无疑就应该是这两个字。所以,读大学后,当有一次看书,看到房龙《人类的故事》时,我盯着作者的名字看了很久,觉得自己像是无意间找到了房文失散多年的兄弟,亲兄弟。
二○一三年四月九日
4
清明上坟,印象里小时候只有过一次。因为后来,这个日子大半都是在学校,或者单位。家人从没因为这件事,让我耽误了学习,或者千里迢迢回一趟,从没。我也从没要求过,好像上坟,就是父母那一辈人的事情。
上坟前,要先准备祭品。其中最有趣的是纸钱,这个要自己动手做。先去人家借模具:十来厘米长的木柄,一头装着铁箍,铁箍里是钱样子。拿一沓黄表纸,对齐,放平,把模具立好,锤子一敲,纸上就出现了清晰的钱样花纹。然后挨个敲下去,嘭,嘭,嘭,嘭,一张纸从头至尾敲满,一沓纸钱就做好了。如果最底下一张不清楚,要抽出来,放在新沓上,重新敲。仿佛印得不清楚的钱,在阴间也不容易花出去。我最喜欢干这个,先是抢锤子,但毕竟力气小,底下好几张都不清楚,要返工。大人不耐烦,我就退而求其次,要求帮着扶模具,这个只需留心手不被敲到就可以。大人的劲儿果然大,每敲一下,手心都麻一下。
终于,厚厚一沓纸钱做好了,整整齐齐码在窗台下,等着出发。它们和酒瓶、馒头、香烟等,静静靠在一起,笼在清晨的阳光里,安详又富足。像每次预备走亲戚的东西一样。
出门也是郑重欢喜的,好像去做一件大事。大人还没动身,自己已经先跑出去一趟了。等不见人,又折回来,站在门口等。终于都出门。一路上可看的东西也很多,发芽的柳树,出土的小草,早开的荠菜花,赶路的蚂蚁。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落后的时候,就迈大步,踩着大人的脚印走,一会儿踩妈妈的,一会儿踩舅舅的。因为刚换了夹衣,身体和脚步都是轻的。关了一冬天的小孩子,放到春天的田野里,就剩下撒欢了。大人们停下来干了些什么,如今已经都不记得。
几年后的一个春天,也是在田野里。整片的土地都被翻开,平整。几个大人说说笑笑,一个人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你姥姥白疼你一会子,什么济也得不到。”又说:“知道你姥姥去哪里了吗?”我不说话,她用手里的锄头敲了敲脚下的土地,说:“现在住在这下面。”我不说话,感觉这整片土地,一下子都压在了姥姥身上,压在了我心上,重得透不过气来。
我愣了一会儿,开始跑回家。以前我总是跑得很快,跑几步还要跳一下。那一天,怎么也跑不动。只能慢慢跑。
现在想来,那是平生第一次,有人把悲伤,土地一样厚沉的悲伤,不经意间,放到我的心上。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