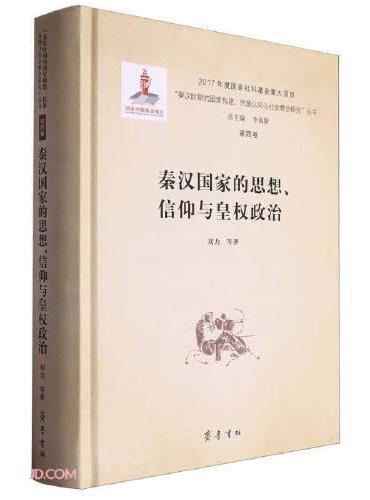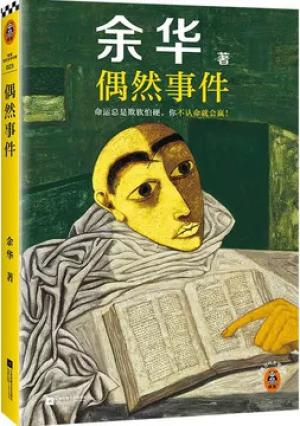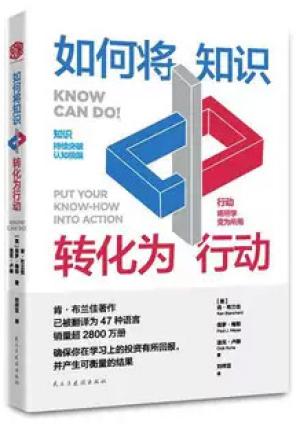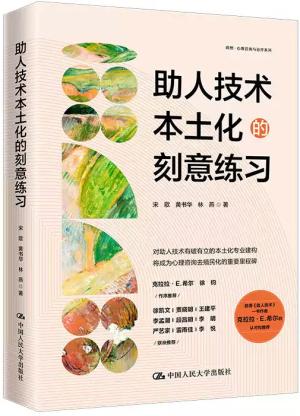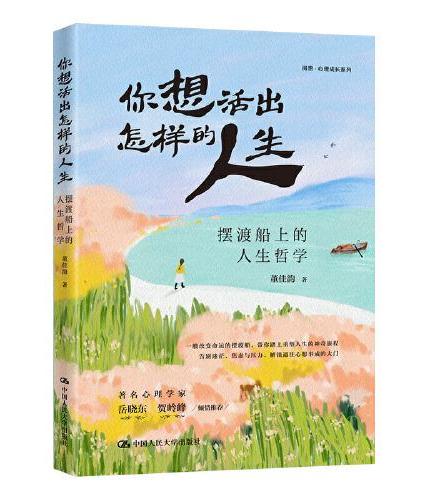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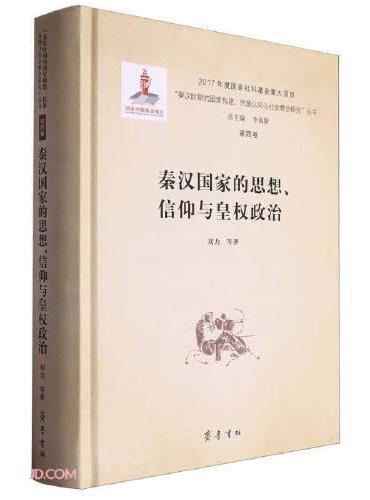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HK$
215.6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HK$
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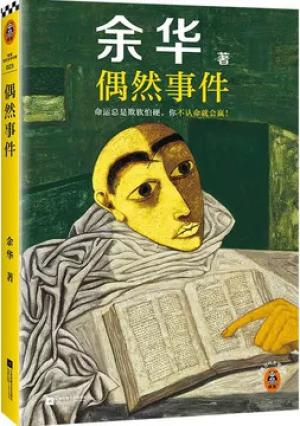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HK$
54.9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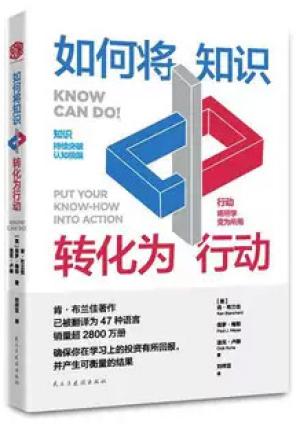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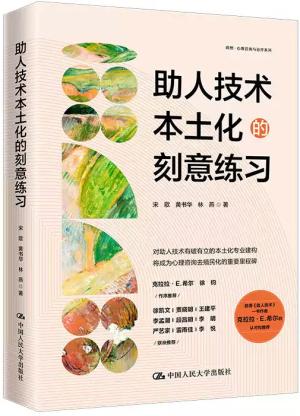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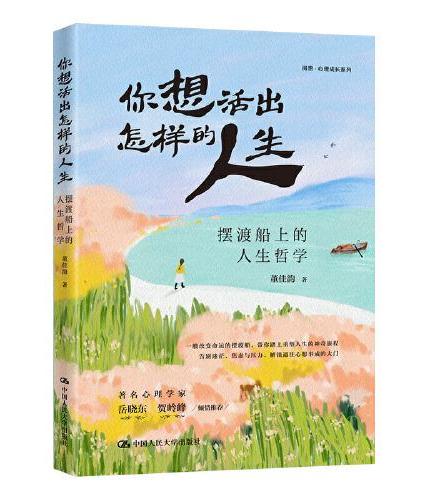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
| 編輯推薦: |
“新坐标”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坐标”涵义:新世纪、新文学、新坐标,新写作为新时代画像。书系单本书之间互相促进,联动上市。
“新坐标”书系遴选当代顶尖青年作家及其代表作,展示文学年轻的力量。每位作家单独成册,收录其重要作品、重要评论、访谈对话、创作年表等,兼具文学审美和研究价值。
作者甫跃辉系凤凰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得主。其生于云南,在上海工作,他的创作中既有云南的乡土气息、故乡的风物人情,又描摹在大城市如粒子般飘零的年轻人的精神肖像,书写一代青年人共通的彷徨与挣扎。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收录甫跃辉的五篇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如《动物园》《收获日》《朝着雪山去》等,特别收录名家评论、创作谈、访谈,如李敬泽的评论《独在此乡为异客——关于甫跃辉短篇小说集<动物园>》。甫跃辉生于云南,在上海工作,他的创作中既有云南的乡土气息、故乡的风物人情,又描摹在大城市如粒子般飘零的年轻人的精神肖像,书写一代青年人共通的彷徨与挣扎。该书为新坐标书系之一。
|
| 關於作者: |
作者
甫跃辉,1984年生,云南人,居上海,曾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十余年,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文学院签约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嚼铁屑》三部曲、《锦上》《刻舟记》、中短篇集《鱼王》《动物园》《万重山》等十余部小说;2017年至今,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第12届十月诗会,著有诗集《去大地的路上》;2023年夏天独自从上海骑行回云南老家,并完成长篇非虚构《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创作奖、十月文学奖、高黎贡文学奖、凤凰文学奖、芳草女评委奖、三毛散文奖等。
编者
谢尚发,1985年生,安徽临泉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创意写作,兼及文学创作。论文散见于《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评论》等刊物。文学作品散见于《十月》、《天涯》、《青年文学》、《台港文学选刊》等,著有小说集《南园村故事》,编著有《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荣获“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论文奖新人奖”,《青年文学》第二届东阿阿胶杯“重阳·念亲恩”征文大赛二等奖。
|
| 目錄:
|
Part1作品选
动物园
收获日
朝着雪山去
阿童尼
鱼王
Part 2 评论
独在此乡为异客——关于甫跃辉短篇小说集《动物园》(李敬泽)
故事尽头,洗洗睡吧(杨庆祥)
巨象在上海:甫跃辉论(黄平)
时代的精神状况——甫跃辉阅读札记(项静)
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我们时代的侨寓困境——甫跃辉论(丛治辰)
个人生活史、梦的解析与生死命题的文学讨论——论甫跃辉《嚼铁屑》(刘小波)
越轨的自由——论甫跃辉的小说(李琦)
经验的虚构,或召唤痛感的文学——论甫跃辉的小说创作(曹禹杰)
Part 3 创作谈
我们不是一个人活着
人类、历史、地球上的这个“我”
Part 4 访谈
笔涉城乡之间,叩问苍茫人生——甫跃辉访谈录
Part5甫跃辉创作年表
|
| 內容試閱:
|
动物园
顾零洲租住的小区紧挨着动物园。“我和老虎狮子是邻居。”他介绍自己时常这么说。他说这话时,总带着一副调侃的神态,还有一点儿无可奈何,然后,在对方愣住的一瞬间,他会呵呵呵地笑起来,又有了一点儿得意。他说:“我住在动物园旁边。”对方也跟着笑起来。双方似乎在笑声中变得不那么陌生了。久而久之,朋友们都知道了,顾零洲住在动物园旁边,和老虎狮子是邻居。偶尔,同事还会以此和他开个小玩笑。譬如吧,因为工作的事儿,彼此意见不统一了,同事会说,哟,我哪敢不同意你?我可没老虎狮子做邻居。如此一来,顾零洲反倒不坚持了,笑着说,算了算了,还是照你说的弄吧。仿佛是,因为他有那么厉害的邻居,应该显得大度一点儿。
这样的自我介绍,只有一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那天,顾零洲转了一次地铁后,总算赶到了约好的地点,却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足足半小时。他四处张望,在一溜小摊边看到了一个穿紫红竖纹长袖衬衫、黑长裙、高跟鞋的女人。顾零洲几乎一眼就认定了是她。他走过去,略带夸张地喘着粗气,说:“欸……不好意思,没想到地铁也这么慢。”
女人背对着他,快速翻检着小摊上的袜子,眉眼间有着一丝不耐烦。迟了一会儿,才转过头来乜斜他一眼。“你就是顾零洲?”
顾零洲心里一惊,女人比他想的要漂亮,眼睛里有一种凌厉的东西,小刀子似的刮在他脸上,冷冰冰的。他用手背擦着脸上的汗水,露出一个笑容,“对不起,第一次见面就迟到……你是虞丽吧?”
这一刻,顾零洲想,他们简直是陌生人。
女人很轻地嗯了一声算作回答,又乜他一眼,重又低头翻检袜子。那是一些颜色极其浓烈的线袜,大绿,大红,大紫……像是一大堆油画颜料肆无忌惮地泼出来的。顾零洲盯着袜子看,想什么人会买这样的袜子?正想着,虞丽已经挑好了三双袜子,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十块两双。虞丽飞速地转了一下眼珠,“三双十块吧?不卖我走人。”说着把挑好的袜子放回了小摊。老板愣了一下,说得得得,你就拿三双吧。虞丽迅速转回来,给老板绽出一个微笑。老板转身找了塑料袋装袜子,嘴里喃喃道,“天天遇到你这样的顾客,我就亏大了。”虞丽笑得更媚了,“天天顾客盈门,您还不偷着乐?”虞丽把袜子塞进手里的紫红色小包,沿着路边走了几步,上了一座天桥。顾零洲跟着她往上爬,黑裙子像一朵硕大的灯笼花在他眼前摇晃,他感觉心也那么摇晃着。到了天桥中央,摇晃的心停了下来,虞丽转回头,迟疑了一下,眼光如风里的蜡烛,有了一忽儿闪烁。
“欸……你也不说一句话,去哪儿呀?”
“我还以为你知道去哪儿呢。”
“我知道去哪儿还问你啊?”虞丽垂下眼睑,嘟囔着,“哪有你这样跟人约会的?”
顾零洲有些不好意思,怅然道:“还真不知道去哪儿。”
“唉。”虞丽叹了一口气,手上的紫红小包荡来荡去,啪啪地轻敲在髋骨上。
天色慢慢暗下来了,灯火渐次亮起。先是路灯,然后是广告牌、窗户,镶嵌在墙上的霓虹灯勾勒出一幢幢高楼的轮廓。黑暗像浓稠的糖浆,被灯光一点一点地稀释开,终于只剩下一点儿淡漠的气息在眼角萦绕。他们望着那些灯光,那些灯光也望着他们的脸。
顾零洲搜寻着可以说的话。
“我和老虎狮子是邻居。”顾零洲又使出了这百试不爽的招数。
虞丽并不搭腔,仍痴痴地望着那些灯光,灯光清晰地照出她的脸。她白皙的脸颊上,散落着两三粒浅浅的雀斑,泪痕似的。
“其实,我住在动物园旁边。”顾零洲自说自话。说出来的话很是寡淡。他心里掠过一丝后悔,若此刻没出来见面,他可以多么舒服地待在屋里呵。一瞬间,他无限怀念起自己那小小的屋子来。
“我们到你住处去吧!”虞丽忽然转过头来,眼睛里闪映着灯光。
顾零洲心里又是一惊,仿佛心里的秘密被偷窥了,不由得微微地红了脸。
跨进地铁时,顾零洲转身抓住了虞丽的手。这时,他才想到,从见面第一眼,他就想抓住她的手,他的心为这念头灯笼花似的摇晃着。她扭头瞥他一眼,嘴角动了动,任凭他握着。地铁已经过了最拥挤的时段,两人很快找到了空位。坐下后,顾零洲顺势揽住了她的腰。她的衬衫有些短,露出一截细白的肉,顾零洲便把手放在上面,手指蠕蠕地动着。虞丽转过头乜他一眼,“别人看着呢。”他小声地嬉笑道:“让他们看吧。”谁也没再说话。
他们认识一年多了,这会儿却如同陌生人一般。他们是老乡,顾零洲在出版社做美编,虞丽在郊区一所小学做美术老师,偶尔也会做些美编的活儿。他们聊了几次,先是聊家乡,后来渐渐发现在平面设计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理念,为此还一起做了好几本书的封面。他在心里感叹,竟然还真有一个人能如此理解自己,她也对他说过类似的感觉。他们还有着一些共同的朋友。有时,他们会间隔不了几天见到同一个人,会和那人谈论起对方。奇怪的是,他们从来只通过网络和手机联系,都没想过要见面。一个月前,一位共同的女性朋友结婚了,他们在网上聊起来,都有些或真或假的唏嘘。他随意问道,你怎么还不找个人嫁掉?她也问他,你怎么还不找个人结了?几乎同时,他们都说,找不到合适的啊。他心里动了一下,就对她说,那你做我女朋友吧。他都吃了一惊,竟会这么说。她回道,那好呀。他又吃了一惊,竟然如此简单。他觉得简直不像真的。她也这么觉得,过了两天还问他,不是开玩笑吧?他说,当然不是。一副笃定的样子。他们开始每天联系,网上聊了,还要打一两个电话,认真做出和以往不同的架势来。时间久了,就聊到了性。虞丽说起这个毫不扭捏,倒有点儿让顾零洲意外。他也露出自己在这方面随意的本性来。说得久了,自然而然想到对方,都说,不知道我们做那事会怎样。话到这儿,见面才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顾零洲努力显得坦然一些,可脑海里止不住浮现出一张床,巨大的云朵一般压下来,几乎让他无法呼吸。他想,她会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她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惜不能直接问她。就转过脸去看车窗外。不知什么时候,落雨了,三三两两的雨点划过车窗玻璃,留下粗大的痕迹,很快,雨大起来,雨水已来不及分行,鸭子的蹼似的连成一片,让人只觉着车厢一头扎进了水底。听着啪啪的雨声,顾零洲想,真有点儿像世界末日。这时,虞丽把头靠在了他的肩头。
在地铁站的麦当劳吃了东西,又坐了一阵子,雨仍旧落着。顾零洲说,走不走?虞丽说,那就走吧,总不能一直这么等下去。麦当劳门口就有临时卖伞的,可他们像是约定好了,只朝地上那堆花花绿绿的伞扫了一眼,就拉着手冲进了雨里。柏油马路积了手掌厚的一层水,细细密密地起了一层水花,晃动着路两边的灯光,仿佛沸水上漾着一层猪油。湿热的水汽一蓬蓬迎面扑来。他们蹦跳着,跑着,转瞬间就湿了鞋子。顾零洲看到虞丽的黑裙子好似快要萎谢的灯笼花,豁口处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虞丽自己似乎并没注意到,不停地尖叫着,笑着,有一股疯劲儿,甚至,有些做作。
“没用了,全湿了。”顾零洲一进屋就嘟囔,下意识地甩着手上的水。
“脱了吧,洗一下,晾起来明天就干了。”虞丽打量着正对着门的、占了大半面墙的窗户。木色的窗帘垂着,偶尔被风撩动一下,听得见哗哗的雨声。原来窗户都打开着。
话音刚落,顾零洲就抱住了虞丽。虞丽并没拒绝,两个人搂抱着,湿淋淋地躺到了宽大低矮的床上。顾零洲往下伸手时,虞丽推开他坐了起来。“我自己来吧。你把灯关了。”顾零洲关了灯,还是能够看到那硕大的灯笼花开上了椅背。过了一阵,两人相拥着坐在窗边,顾零洲无意间瞅见那花彻底谢了,花瓣落了一地。
雨还在下,屋里有些闷热。虞丽拉开了一角窗帘,探头望向窗外。窗外黑黢黢的,两三粒白炽灯好似深嵌在蛋糕里的果核,散不出一点点光。顾零洲从后面抱住虞丽,盯着她精致的侧脸,右手在她胸前摩挲着。
“我们……是不是太快了?”顾零洲佯笑着。“那总不能憋上一夜吧。某人有那么正人君子?”顾零洲哑哑地笑了两声,握住了她小小的乳。“唉……一股什么味儿?”“动物园里的……”顾零洲一愣,起身关上窗户。“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哦,你说过的……动物园。”“嗯,白天可以看到不少动物。”“这会儿能看到什么吗?”“很多动物进屋了,这会儿还可以看到大象吧。”他伸手指点着,“就在那儿,看到没?”“只看到黑漆漆一团啊。”“就是黑漆漆一团嘛。”他看到她唇边浮动着笑意。
多数情况下,虞丽每周五下班后会到顾零洲这边。忙的时候,两周会来一次。有一次三个星期了才聚到一起,一见面,虞丽就抱怨道,那些学生,真够烦人的!他们并没多少事情可做,通常是,一见面便迫不及待地扑到床上,然后,一起到卫生间里洗澡,再然后,虞丽打扫卫生洗衣服,最后,一起坐在床上一边做事,一边隔着窗户看看动物园。顾零洲租住的是三室一厅,另外两间屋住的都是单身小伙。他和他们都算不上认识,见了点个头而已。
“他们会不会听见啊?这门隔音效果也不知道行不行,床也太响了……都不好意思见人了。”每次从床上坐起,虞丽总是很担心。
“不会吧……动物园里猴子那么吵,谁会听得见这个?”
“你才是猴子!瘦巴巴的猴子!”虞丽脸唰地红了,小姑娘似的拍打着顾零洲。恍惚间,他们都成了初高中谈情说爱的小恋人。
“那你去找大象吧。”顾零洲很无所谓地说。
“不!”虞丽猛地抱住了他的脖子,嘴唇拱进他的耳朵,“我就喜欢猴子。”
顾零洲反身又把她抱住了。
“他们会不会听见呀……”虞丽眼瞅着门。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乐此不疲。一开始,虞丽就以非常惊讶的语气说,她从没有过这样的。“以前我从来没觉得这事有什么意思,老公真厉害。”虞丽脸色绯红,尽是陶醉的神色。每当她这么说,顾零洲心里就有些郁郁的。他当然知道她有过其他男人,在她之前,他也有过其他女人。他们都没向对方隐藏什么。可他听她这么说,仍还是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梗住了。他有时候都为自己的心理感到奇怪。有时,他还挺想听她说说过去的,一旦她说起,他又会觉得不舒服,心里空得要命。
“老公真厉害。”虞丽眼神迷离地望着顾零洲。
“是吗?”顾零洲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还是不知说什么好。
“是呀。”虞丽靠紧他,娇声道,“老公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顾零洲默默无言地躺着,眼瞅着空无一物的天花板,忽然很担心虞丽会说出他比她以前的男人厉害之类的话来。他越来越感到沮丧,心里空荡荡的。
“老公?”虞丽轻声喊道,“怎么不说话了?”
顾零洲还是不言不语。沉默如同一片温柔的沙幔裹住了他和她。又躺了一会儿,顾零洲用脚趾在被窝里找到了内裤,慢腾腾地穿好衣服,唰一声拉开窗帘,大片阳光瞬即占据了半间屋子,仿佛在黑暗的地洞里突然拧亮了手电筒。
“讨厌!”虞丽拥着被子,迅速躲到黑暗里去。
顾零洲翘首注视着不远处的动物园。真是好天气,阳光晃得人眼睛生疼。几只土红色的亚洲象悠然自得地挪动着笨大的身躯,鼻子好比沉甸甸的橡胶管子,不时甩到背上。
“我们去动物园逛逛吧。”顾零洲说话时并未回头。在一起三四个月了,顾零洲不止一次提出要带虞丽去动物园看看,总是为这样那样的事没去成。
“好呀,”虞丽也坐了起来,“天天看,你还没看够啊?”
“你不是没去过嘛。”
“也是,”虞丽呵呵笑着,背对着顾零洲穿好了衣服。“我都多少年没逛动物园了,算算啊,上次去还是中考结束后,我妈为了奖励我带我去的。你还记得市中心那家动物园吧?记得有一张很大的蛇皮。想想真是骗人,动物园展出的不是活着的蛇,竟然是蛇皮。”
顾零洲当然记得。小学六年级时学校组织旅游,他第一次到了那家动物园———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给他最深印象的就是这张巨大的蛇皮。他隔着笼子久久地盯着它,莫名其妙地觉得只要喘一口气,它就能活过来。那次旅游回去,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长大了要当“动物学家”———这是从动物园工作人员口里听来的词。可能因为这理想比较特殊,作文还被语文老师在全班念了。为此,有一段时间,他被同学们起了个绰号:动物学家。有那么几年,他还真煞有介事地做过动物学家的梦呢。现在虽然不做了,他还是特别喜欢看有关动物的纪录片……虞丽穿衣服梳妆的时候,他对她讲了这些。她侧脸对着镜子戴一只亮晶晶的耳钉,有点慵懒地说:“小时候啦,谁都这样的。”他便没再说什么。
“逛动物园还要带包?”他瞅着她臂弯上的紫红挎包。
“逛动物园就不能带包吗?”她对他妩媚地一笑。
顾零洲有年票,要给虞丽也办一张,虞丽说,再说吧,谁还天天逛动物园啊,我们又住得这么近,一抬头就能看到了。
进门不远,是一座用水泥墙围起来的假山,假山建在低于围墙外地面的深坑里,和围墙又有一段距离,猴子们并不能够跳出来。猴子们吱吱呀呀地叫着,跳着,好似和墙外的游人们吵闹着,有的还将空矿泉水瓶扔向围观的人,人群笑着散开一个口子,重又回拢来。猴子一点办法没有。趴在墙上看猴子的大多是孩子,他们和猴子一样,有着用不尽的精力。顾零洲和虞丽挤在兴奋的孩子们中间,往假山上望了一会儿。“走吧?”虞丽拽了拽顾零洲的胳膊。顾零洲想说再看一会儿吧,看到虞丽没什么兴致,改口说,那就走吧。他太熟悉这家动物园了。他像带着虞丽参观自家后院一般,带着她一路看了山魈、斑马、羚牛、长颈鹿、红袋鼠、土狼、豹子……在喂养老虎的几个笼子前,顾零洲指给虞丽看一只纯白的老虎。白虎原产自印度的某片丛林,据研究,属于变异品种,数量极少,是这家动物园的“镇园之宝”。虞丽捂着鼻子,偏着头听着,偶尔嗯呀一两声算作回答。顾零洲瞅了一眼她臂弯上的紫红挎包,陡然失了继续介绍的兴趣。
“你这样子,怎么看怎么不像逛动物园。”
“那怎样才像逛动物园呀?”
“总之不像你这样……你这是逛商场嘛!”
“讨厌!”虞丽娇嗔道,“我都快给熏死了,你还说。”
关猛兽的笼子附近,气味确实很大,好似堆满了尿素等肥料的仓库。
走到黑熊的笼子前,顾零洲又变得兴味盎然了。
一头黑熊紧贴笼子站着,两只前爪扒住竖着的铁栏杆,半张脸挤在栏杆间,看上去很是狰狞——黑熊正竭力伸出舌头舔栏杆外的一颗水果糖。铁栏杆是立在一段水泥矮墙上的,水果糖就落在水泥矮墙顶上,黑熊已经将它舔得湿淋淋的了,可就是没法把它卷进栏杆里去。黑熊停下来,伸出手去够,干脆连碰都碰不到,又低下头去,长长地伸出舌头舔,换了一个又一个角度舔。顾零洲看着看着,禁不住也伸出了舌头,仿佛他就是那只黑熊,感到虞丽怪异的眼神,
他才缩回了舌头。尽管如此,虞丽还是笑了起来。“你也想吃糖了?”虞丽笑得咯咯咯的。“没有啊。”他脸色略微红了红,心里涌起很深的失落感。“那你跟着舔什么?”“哪有。”他心里的失落感更强了。“还狡辩!”虞丽斜觑着他,眼含狡黠。他没理会她,只顾往四处看。“找什么呢你?”“棍子啊,帮帮黑熊。”“还真有劲儿啊你!”虞丽惊呼道,“看熊不抓了你。”竟然没找到一根棍子。他真想直接伸手拿起那颗糖扔进笼子里。顾零洲没能这么做。虞丽挽着他的胳膊,半拉半拽地带着他离开了。走了很远,他回过头来,仍看到黑熊两手扒着栏杆舔那颗糖。这真是令人忧伤的画面。忧伤源源不断地涌上心头,几乎令他措手不及。有一瞬间,他很想跟虞丽说说这种感情。可一想到刚才的对话,他就打消了这念头。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继续接下来的路程,任由虞丽挽着随意地走。他们走到鸟类展馆,看了丹顶鹤,看了斑头雁,看了黑天鹅,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转回到了猛兽区。他们面前的笼子里,关了七八只狮子。
虞丽一看见狮子,扭头便要走,给顾零洲硬拉住了。“气味怎么这么重啊。”虞丽捂着鼻子,皱着眉头说。“没事,”顾零洲安慰她,“动物园里那么多参观的人,哪有你这样的。”“可人家就是觉得很臭嘛。”虞丽娇嗔道。“哪有那么娇气,适应一下就好了。”顾零洲坚持说。他不再看虞丽,专注地盯着笼子里的狮子。
大多狮子都趴在笼子最靠里的墙角,唯独一头看上去邋里邋遢、神情疲怠的公狮子不紧不慢地踱步,走到狮群身边,又折回头走到铁栏边,来来回回的,仿佛潜心思索着什么。铁栏外的几个青年男女不满足,用矿泉水瓶敲打着铁栏杆,“嘿嘿嘿”地大声呵斥,似乎想让另外几头狮子也站起来。顾零洲一眼一眼瞪他们,他们丝毫没在意。这时,那头公狮又走到了铁栏边,在几个人的笑声中掉头往回走,猛然间,公狮的尾巴根动了动,一大股淡黄色的腥臊尿液激射而出,那几个男女躲闪不及,给溅了满头满脸,笑声戛然而止。惊呼声里也有虞丽的。她衣服上也给溅了一些。顾零洲没有惊叫,反倒是咧开嘴笑了。
“你笑什么?”虞丽没好气地说。
“笑那些人啊,”顾零洲没注意她的情绪,兀自笑着,“这狮子真够聪明的,也只有这么一招能够治一治这些人。”“不是吧,你是笑我吧?”虞丽仍旧冷冷的。“你想哪去了……”顾零洲意识到她的情绪变化时,已经晚了,
“你太敏感了。”
“我今天究竟什么地方不遂你的心了?”虞丽一面用卫生纸擦拭衣服,一面盯着他。“还没出门你就对我拎包有意见,进了园子你又说我不像逛动物园的,我受不了这些畜生的屎尿味,你又说我娇气。我大老远地到你这儿,究竟图个什么?”
虞丽越说越激动,顾零洲有点慌了手脚,几次想要打断她,都没能成功。等她终于说完了,他只是很淡地说了一句:“不是你想的这样。”
“那是哪样?”虞丽的目光像一柄小刀子,冷冰冰地刮着他的脸。
顾零洲一瞬间想起了他们刚见面那会儿。他想,他们简直是陌生人。他沉默了许久,想着怎么解释,却没再说什么,无所谓地挥了挥手。“随你怎么想吧,”他说,好像还不过瘾,竟又恶狠狠地加了一句:“爱想什么想什么!”
虞丽三个星期没来,顾零洲又过上了单身生活。这周末,报复似的睡到了下午四点,饿得受不了了,才起来煮了方便面。吃完后,开始看美国国家地理的纪录片。这曾经是他无上的享受,和虞丽在一起后,竟然没再有过。去他的吧,他这么想着,接连看了三集。最后看的一集是《象族》,当大象的身影从摄影机前慢慢远去,解说员说:“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顾零洲无限感慨地回味着这句话,抬起头来,窗外已黄昏。暮色温柔地笼罩了动物园,游人正在散去,一切渐趋静谧。隔着窗,看得最清楚的正是大象的领地。他看得清楚,有十二头亚洲象,厚重的身躯覆满红色的灰尘,矗立在寸草不生的泥地上,像一堵堵沉默的红砖墙。
他蓦然想到,那天,他们竟没去看大象。他原本想,一定要带她去看看大象的,因为站在大象的领地边,正好可以看到他们小小的窗户。
他抓过手机,输入了一句话:“这周末可以过来么?”想了想,把“可以”两字删掉,发了出去。他忽然觉得,不会有回音的,她可能从此消失了。这段时间,他一直恍惚觉得,她似乎从未来过。———不过虞丽很快回了消息:“好呀,前段时间太忙了。”他仔细咀嚼着这句话,知道她已经不生气了。他回复道:“上次的事很抱歉,以后———”他不知道是不是该说,他以后想要带她去看看大象。他迟疑着,最终删掉“以后”,把短信发了出去。好一会儿,她只是简单回道:“没事了,下周见。”
顾零洲到地铁站接她,出乎他的意料,她似乎彻底忘了上次的不快,脸上尽是轻俏的笑,“老公”,她低声喊他,旁若无人地在他嘴边啄了一下。虞丽一句没提上次的事儿,顾零洲也不再提。回到屋里,虞丽放下挎包,径直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关上窗户,重又拉好窗帘。回过头来,顾零洲正盯着她。
“看我什么?”她莞尔道。
“没什么。”顾零洲迟了一会儿,嘴角也往上翘了翘。
“老公不想我吗?”虞丽瞟了一眼床,又瞟了一眼他,眼神中满是温软的俏皮。
“想呀,怎么能不想?”他有点干巴巴地说。
抱在一起时,仍旧有一点勉强。顾零洲持续了很久,脑海里不断闪现出那句话:“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这话让他莫名地焦躁。后来,虞丽柔声道:“停下来,好吗?”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不知道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虞丽轻声说。
顾零洲把她抱紧一些,心里莫名地充满了歉疚。
大体上说,他们恢复了过去的生活。顾零洲发现,唯一不同的是:虞丽以近乎执拗的态度坚持关窗。以前,她也会要求关窗,但总是撒着娇征求他的意见:“老公,我们把窗子关上一会儿好不好?”现在,不了。只要一看到窗户开着,她立即会关上。哪怕窗帘拉着,她一闻到空气中那股臭味儿,也会很警惕地拉开窗帘查看窗户关了没有。其实,顾零洲也不喜欢那味儿。但他喜欢开窗,屋子本来就小,老关着门窗就会显得愈发小。在屋里待久了,他会有种窒息的感觉,就如一条被闷在密闭水箱里的鱼。他将什么也做不了,就像那头走来走去的狮子,只能不停地走来走去。
这天,他们在屋里待了一下午,一起设计了两个封面。配合很默契,自己想到的,对方也会想到;对方提出的意见,总是能让自己称心如意。顾零洲喜欢和虞丽一起工作,工作总能让他们的心紧紧挨在一块儿———那种心灵相通的感觉令他痴迷。她还在说着自己的想法,他偏着头瞅着她的侧脸。初秋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在她脸上,睫毛的影子水草一样在脸上轻微地晃动着。鼻子、嘴唇、下巴,淡淡地笼着一层光润,白皙的脸庞仿佛一件易碎的瓷器。她丝毫没发现他正注视着自己,仍盯着电脑上的图片说着自己的想法,那样的专注、单纯。他无声地笑了,眼睛里也跃动着笑意。忽然,他想,把她的侧脸用线条勾勒下来,即可做成很好的封面。他抑制着兴奋,凑近她的耳朵,小声说,我上个厕所,回来跟你说件好玩儿的事。她转过脸,微笑着望着他,揶揄道,某人又神神秘秘的!临出门,他下意识地推开了窗户。等他匆匆上完厕所,干干净净洗了手,再回到屋里,发现虞丽神情淡漠地瞅着电脑。他看到,刚刚打开的窗户又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开窗和关窗,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往往是,她刚关上窗户,趁她不注意,他又给打开了,他再一疏忽,窗户又会被她关上。他们暗暗较着劲儿。若窗户打开后长久未被关上,他禁不住有种成就感;若窗户刚打开就被她关上,他不免会感到沮丧。很多时候,他们习惯拉着窗帘,所以,并不能看到窗子关着还是开着,那就全凭嗅觉了。他早习惯了动物园的气味,此时,重新让自己加以注意。———他觉得,自己就如臭鼬一样尖起了鼻子。当他的嗅觉越来越灵敏时,她丝毫未居下风。他们活得越来越像动物,机警而且多疑。
他们默默地恪守着一条原则:不在对方眼皮底下去关窗或开窗。双方的战争成为名副其实的“暗战”。表面上,始终保持着应有的礼节;内底里,其实寸土不让、硝烟弥漫。战争很快由白天蔓延至夜晚。两人躺在床上,总是暗暗较劲儿,看谁先睡着,先睡着就意味着放弃了对窗子的控制权。为了迷惑敌人,两人在伪装上都下了大工夫。顾零洲的伪装方式是打鼾,她知道他很少打鼾,为了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他装作鼻塞。响了两三声后,她小声嘟囔了句什么。他试着调大一点声音。他的嘴巴和她的耳朵挨得很近,他相信,在阒寂的夜里,这可以说是声若惊雷了。她只咂巴了一下嘴。睡得真够香的,他无声地笑了一下,慢慢从她脖子底下抽出手臂,起身推开了窗户。为了保证不发出一点声音,他推得极其小心,推开一点,又回头觑她一眼。月光下,她的脸安静而柔和。花了三四分钟,他才推开了窗户。夜晚的空气清冷、潮湿,什么味儿也闻不到。他眺望着月光下的动物园,大象影影绰绰的,在人们安睡的夜里,它们仍清醒着。这样静谧的时刻,他才真正体会到那句话的含义: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
一早醒来,顾零洲发现窗户关得严丝合缝。
他有点恍惚,难道昨晚自己并没开窗?不对啊,他分明记得自己的一举一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虞丽也像自己一样装睡,或者半夜醒来过。他偷偷观察她,她没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完全是一副无辜的样子。还装得挺像的,顾零洲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他并未由此退缩。除了躺下后努力争取最后睡着,他还想出了一个绝招,就是睡前多喝水。这样,便能保证他半夜醒来上厕所,也就能够保证半夜再检视一遍窗子。渐渐地,他又更进一步,摸索出喝多少水便能在天亮前醒来,这样,可以在白天到来前最后检查一遍窗子。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不管他怎么努力,他早上一觉醒来,窗户总是关着的。他一次次怀疑,睡前开窗加上夜里复查,难道都是梦里发生的事儿?如果不是,那虞丽是怎么做到的?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可怕!她对他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他却对她的所作所为懵懂无知。他看她的眼神,越来越充满了困惑。他总是怔怔地盯着她看,她有太多他所不能了解的了。她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陌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