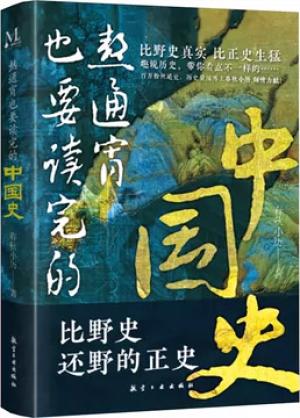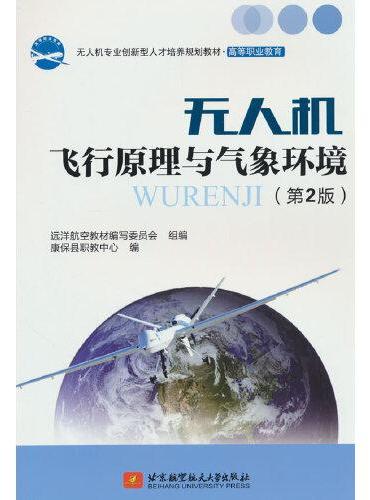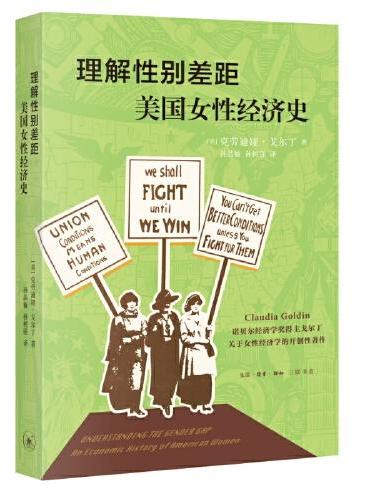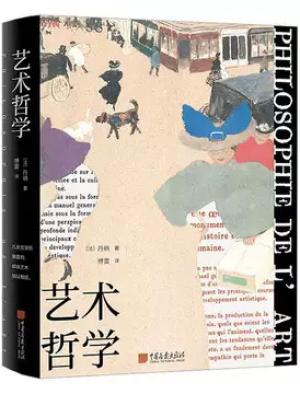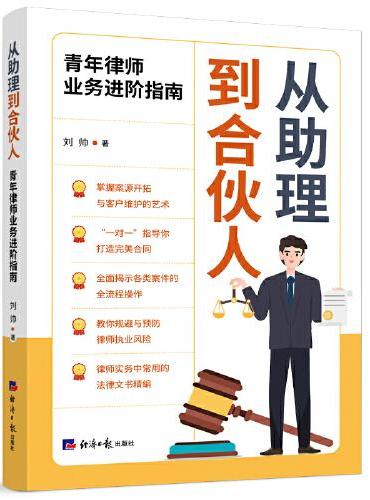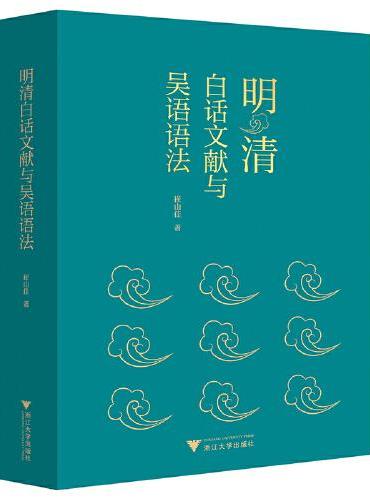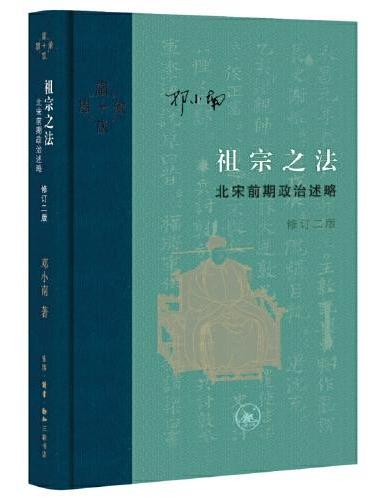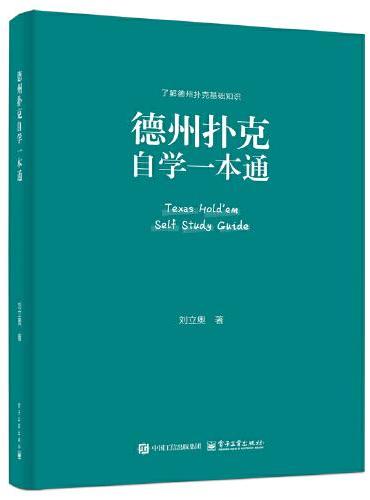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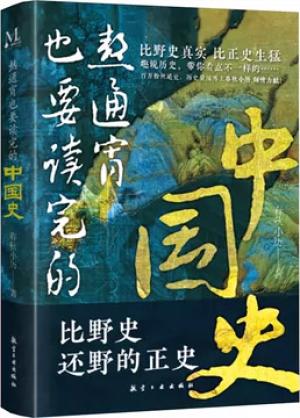
《
熬通宵也要读完的中国史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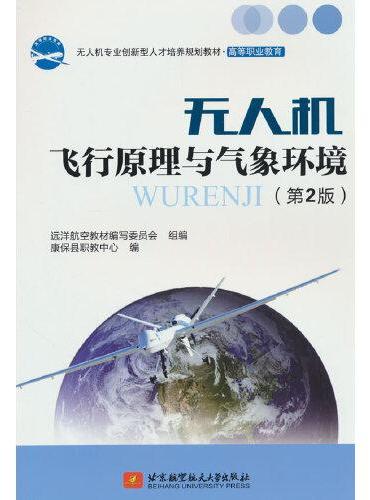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HK$
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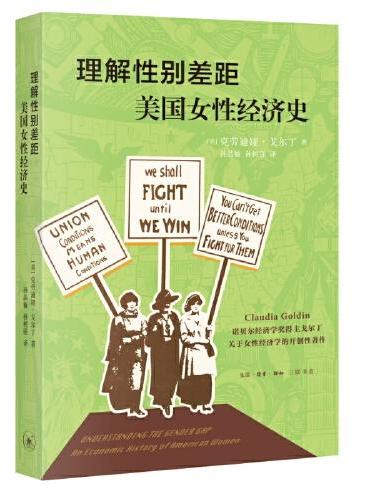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HK$
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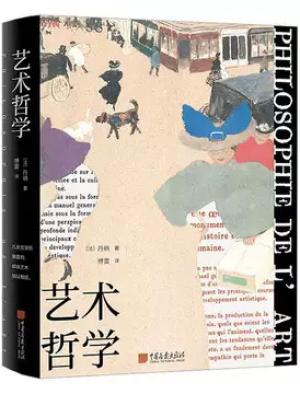
《
艺术哲学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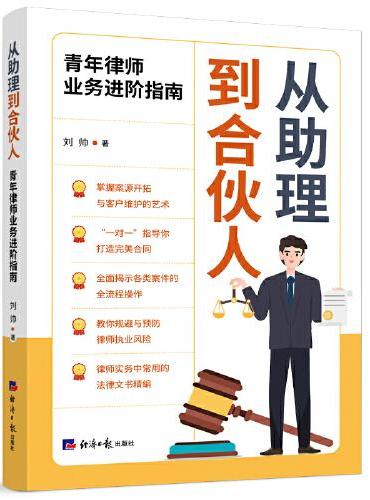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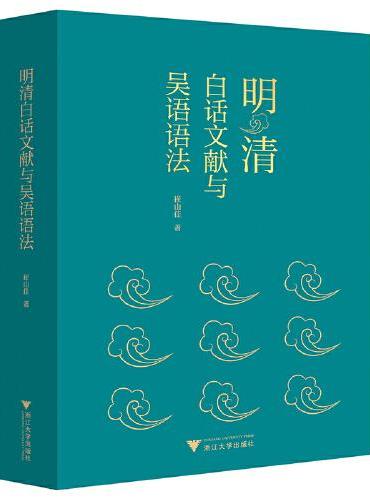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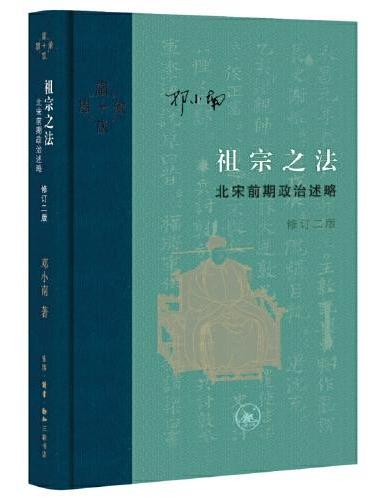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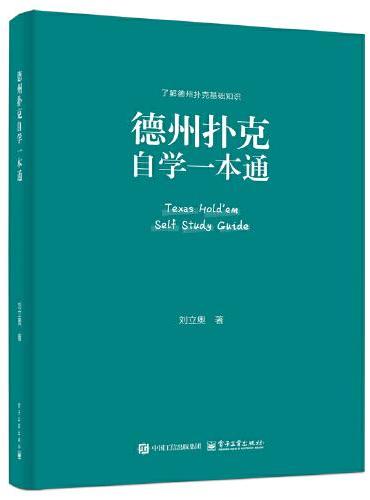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HK$
55.0
|
| 內容簡介: |
吴谢宇案是一起备受关注的刑事案件。2015年7月,时年21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吴谢宇在家中杀害母亲谢天琴,制造母亲陪同其出国留学的假象,骗取亲友144万元用于挥霍,购买十余张身份证件隐匿身份逃亡,直到2019年4月在重庆机场被捕。法院审理认定其作案前精心预谋,手段极其残忍,严重违背人伦道德,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mai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2024年1月被执行死刑。
在2016年、2019年、2022年、2023年这几个与吴谢宇案有关的不同时间节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都进行了追踪、采访和调查。《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一书正是在这组封面报道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记者吴琪、王珊围绕家庭、友人、学校、法庭等社会关系网络走访、调查,先后联系了上百位采访对象,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并借助吴谢宇的狱中自述、书信、法庭供词等,还原了大量细节,写就了这部以吴谢宇案为切入点的深度纪实作品。
本书不仅是对吴谢宇案翔实、深入的全程报道,还尝试从时间维度梳理一个家庭、两大家族、几代人的成长历程和家族历史,探究案件背后的复杂动因与症结,挖掘悲剧发生的根源,引发读者对人性、伦理与教育的反思,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非虚构纪实力作。
|
| 關於作者: |
吴琪,《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2003年进入三联从事社会调查报道。
王珊,《三联生活周刊》主笔。2015年开始做调查记者。
|
| 目錄:
|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妈妈的消失
第二章 两个家族
第三章 疾病和封闭
第四章 父亲去世与成为“宇神”
第五章 初到北大
第六章 大学的小社会
第七章 踩空
第八章 弑母
第九章 秘密
第十章 后来
记者手记
我们都不是社会的“陌生人” / 吴琪
活成孤岛的“我们” / 王珊
附录
时间线
困在二手时间里的“宇神” /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吴谢宇案与当代中国家庭的纠结 /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关系中,理解时代与人性 / 李鸿谷(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
| 內容試閱:
|
写在前面的话
逃亡与真实生活
2015年夏天,21岁的吴谢宇开始了逃亡生涯。到2019年4月被公安机关抓获,他逃亡了将近四年。
说起这四年的经历,吴谢宇把它描述得像参加了一场漫长的夏令营:“我第一次自己考虑去哪里,学会比较路线和路费。我第一次自己挑衣服、套被套、洗衣服、搞卫生。我第一次自己租房子,学会和房东谈价格。我第一次自己做饭,学会怎么买菜、切肉、炒鸡蛋、洗碗。”
在做出杀害母亲的残忍行为之后,他从2015年7月到12月,找亲戚和爸爸的朋友们,一共骗取了144万元,说他要去美国做交换生,带着妈妈一起到美国生活。但事实上,他和性工作者刘梦在上海同居,其间还花钱找过其他性工作者。他在上海花费了58万元买彩票,又在福州花了3万元买彩票。2016年3月1日,吴谢宇账户里只剩下910.44元,144万元被他挥霍一空。从2016年2月与刘梦分手后,他一路逃亡到了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后来在重庆生活时间比较长,一直到2019年4月在重庆被捕。
吴谢宇想体验的是他之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在被捕后的自述材料里,吴谢宇说他“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小世界里:爸爸妈妈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全、温暖的家,我窝在里面,不愿也不敢走出来”,而“逃亡中我无法再自我封闭,只能投身真实生活”。
在这种“真实生活”里,似乎性交易、挥霍金钱与学会洗碗、炒鸡蛋是同一等级的事情。吴谢宇描述自己21岁之前的生活:“对我而言,我的人生就是从一个年级到一个更高的年级,从一个学校到一个更高的学校,从一本课本到下一本课本,从一场考试到下一场考试。”当他觉得自己失去束缚后,真实的生活与他之前通过小说、影视作品所想象的很不一样。在2021年4月写给合议庭的自述里,吴谢宇说,“我过去所以为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课本里、小说里、影视里对这个世界的描绘。说直白点,我以为我看过‘这个世界’,其实我只不过看过了‘世界地图’,看过了其他人走过看过这世界后写的‘游记’而已”。
他说他终于“真正去经历爸爸妈妈曾经经历过的所有喜怒哀乐”,哪怕逃亡生活只是真实生活中的沧海一粟,那也已经“无穷尽的丰富、无穷尽的复杂、无穷尽的未知、无穷尽的精彩”。他甚至天真地说,他感受到“心中头一遭,有了热情、生机与活力……原来生活这么有趣、这么有意思”。但伴随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可怕、更深刻的痛苦,他想:“要是我能让我妈妈也一起,感受到我心中这全新的一切,该多好啊!”
如果他需要的只是离开父母的生活,实际上从15岁在福州一中住宿开始,吴谢宇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特别是18岁考上北大,大学离家乡几千公里。如果是一个健康的18岁青年,这正是打开自己、融入同龄人的大好时光,一群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到一起,互相碰撞。一个人很多时候正是通过与他人碰撞后回弹的力,进而发现“我何以为我”。但吴谢宇的眼里看不到“人”,只要大家做同一份卷子,学同一套教材,同学就是竞争者,而不是情感上的滋养者。
从吴谢宇在看守所写的大量自述材料来看,他的分裂显而易见:在掌握知识、考高分方面,虽然学得很苦,但是他能让自己像一台精准的机器一样,获得好的产出;可是在情感、价值观、辨识能力方面,他处在一种令人吃惊的蒙昧状态,比如相信“书上写的、电视上播的,就是真的,就是对的,否则怎么会让它们出现在我的面前呢”。他还列出自己从小到大的好成绩、竞赛名次、“省三好学生”的荣誉,向合议庭证明自己有“赎罪的能力”。他表现出的高智商和低情商,给一审律师冯颖也留下深刻印象。
为什么要杀害妈妈呢?如果他渴望的只是有女朋友,只是自己做饭、洗衣服、套被套的生活,他完全不用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吴谢宇自己很难解释清楚,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分为不同的阶段。从2019年被捕到2021年8月一审被判死刑后,他都极力维护妈妈,说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很辛苦,很完美。他在2021年10月写给舅舅的信里说:“我对妈妈,是爱,不是恨或世人可能会猜测的其他任何负面情感。我太爱太爱我妈妈了,可,我从小就不知道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去好好爱一个人。”一审律师曾建议他做精神鉴定,吴谢宇拒绝了。从辩护的角度来说,诉说妈妈谢天琴的问题对他是有利的,但他也坚决拒绝,“我妈妈是决不能被怪罪的,一丁点都绝不行的!”
在对妈妈这种绝对服从的爱里面,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极端的爱就像一把利剑,稍微偏转一点,就是巨大的恨。
一直到2023年5月19日二审开庭,吴谢宇提到“我母亲性格确实不太好”,这是他极为罕见地表达不认同妈妈。在此之前,他在看守所写了一百多页的自述材料,反复回想自己的人生,对妈妈都是极尽赞美和认同。
封闭的三口之家
1994年出生的吴谢宇,被父母寄予了对经济高速发展下出生的一代人的期望。妈妈谢天琴和爸爸吴志坚都是1967年出生的人,20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开始了一路向上的人生。他们的童年各自有着深刻的不幸,在福州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他们希望孩子不要再重蹈他们的人生覆辙,只用一心一意念好书。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他们人生获得重大转变的现实,也是他们对孩子的最大信念。
敏感而聪明的吴谢宇,在踏出最后那一步之前,看起来都在本能地满足着父母殷切的期望。用他的话说,他很快摸清了自己的生存法则:只要考第一,就万事大吉了。父母都是莆田仙游人,在家说方言,他听不懂。他想学,但父母说,大人的事孩子别管,还是学好普通话。
吴谢宇不用做学习之外的任何事情,也几乎没有同龄人朋友。大姑小姨的孩子是他每次回老家时的玩伴,但这些孩子成绩不好,吴谢宇和他们后来明显疏远了。住谢家楼上、与谢天琴亲近的马老师提到,谢天琴不让小宇和他们一起玩。吴谢宇在2021年10月给大姑的信里也提到,小时候他还追着表哥到处跑,后来即使回老家,也是关起门来读书,与他们完全不谈心。
谢天琴是个无微不至的妈妈,她对外人冷淡,但是对丈夫、孩子的情感浓度特别高。马老师对谢天琴的评价是,莆田女人非常传统,必须听老公、听儿子的。虽然谢天琴在工作之初表达过想长期单身的愿望,但与吴志坚相爱后,她觉得自己在情感上的价值是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
由于出生在“右派”家庭,父亲又因为批斗而戳瞎眼睛,谢天琴内心非常没有安全感。在和吴志坚感情生活的早期,她会因为出差的吴志坚电话不够多、写信不勤奋而数次表示伤心、活不下去。“志坚,你好残忍,说好来电话的,我等了一天都不来,要将泪水为你流干,现在我心中悲痛异常,思来想去,你的变化为何如此巨大……上帝,我该何去何从,现在一下子又坠入万丈深渊了。”
谢天琴急切地盼望着新生命,“我非常迫切地想给你一个礼物——孩子”。吴谢宇带着期盼来到人世,他不用忍受父母小时候的物质匮乏,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也没有多少人际交往,父母为他排除了学习之外的一切“干扰”。
从小到大的第一名,给了吴谢宇极大的自信,他成为所有人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吴谢宇非常享受这种待遇,他说自己就好似“舞台上的主角、小说里的主人公”,即使偶尔违反纪律,老师们对他也是疼爱有加,所以他一直把自己区别于“普通人”。在他被捕后的自述里,他说他认为校规校纪只是约束“普通学生”的,而法律是“学校外边的事情,自己不用考虑”。他觉得自己学习上这么有天赋,看问题比别人深,所以总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根本问题、本质问题”。
他几乎不跟任何人交流内心想法,即使对爸爸妈妈。在被逮捕后的自述书和写给亲友的信件中,他把他亲手杀害的妈妈谢天琴描述成一个具备一切女性美德的人:每天起早贪黑,既要照顾爸爸这只“大病猫”,也要为从小体弱的他这只“小病猫”操心,妈妈会因为照顾他们“饿得前胸贴后背”,把自己弄得很累,“她总是把自己压到最低、放到最后,全是为了别人”。
而谢天琴同时是固执的,她在写给吴志坚的信里,表达了她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她觉得自己需要依靠,希望被人安排、听人指挥;另一方面她也知道,即使一些事情她问过吴志坚的意见,最后也都是按自己的想法来。
吴志坚的公司离家远,他早出晚归,喜欢和朋友相处,还要为在农村的一大家子操心。对于谢天琴表达的高强度情感需求,他选择了回避。儿子的出生,更给了吴志坚情感上的回避机会。儿子成了谢天琴最大的寄托。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妈妈贤惠而深情,无微不至,但也忍不住常常抱怨;爸爸显得温和而退让,却始终在回避冲突,回避真正参与家庭生活。孩子与妈妈,妈妈与孩子,越绑越紧。吴谢宇说自己从小就极为在意别人的看法,总是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别人盯着。
吴谢宇特别强调,他从小就非常黏妈妈,他把自己从小到大活着的唯一价值描述成——让妈妈开心、让妈妈为自己骄傲。
谢天琴童年不幸,她靠高考、结婚、生子,一步步走向看上去幸福的人生。但是丈夫吴志坚的肝病越来越重,丈夫43岁早逝后,谢天琴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命不好的隐痛再次被狠狠刺激。
丈夫死后的一两年里,她非常频繁地给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吴志坚写信:“(我)是失败的,抓不住爱情,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无能为力。做人,我也是失败的,知音何在?朋友在哪?可怜的几个电话都是有关工作的,四十好几的人了,仍是中级职称,无法见人。”“志坚,我也知道我心理不太正常,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我知道这些病症的成因在于你的离去。没有你的支持,我真的无法正常做事。”
吴谢宇这时16岁,看到了妈妈的痛苦。他说,那时候他觉得他和妈妈的位置该换过来了,由他来照顾妈妈。但实际上,生活中的事情仍然是事无巨细地由妈妈操心,他在回忆性的自述里说,他每次出门都跟在妈妈身后,去银行、超市、公园,都是被妈妈领着。即使读高中了,还是很依赖妈妈,“很怕一个人出门”。
我们采访的吴谢宇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邻居、大姑、表哥、父母的朋友等,对他基本都是夸赞。只有少数同龄人觉得他特别自律,多数人认为他似乎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不过,在自傲的同时,吴谢宇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是没有主见的,他总是在观察别人,快速琢磨怎样获得他人认可。他缺乏真正的辨识力,哪怕是考试第一,他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别人如果愿意像他那样苦学,是很容易赶上他的。
他从来不认为需要真的与同学交往,只要大家做同一套考题,他眼里看到的就是竞争不过他的“普通人”,他不需要去关注这些人。实际上,除了一家三口的小世界之外,吴谢宇确实从小就没有与人真实深入地交往过。
在2021年4月写给合议庭的自述材料里,吴谢宇说他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思想观念是多么的扭曲、颠倒和错误”。他提到自己内心极度的自以为是,见到小姨、舅舅这些亲人,从来没有想过问问他们过得怎样。从小到大,他也遇到过向他倾吐心声的朋友,但他从不开放内心,也没有问过他们准备考什么样的大学,希望去哪个城市。他表面对人礼貌,但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要有“第一名”的身份保驾护航,自己就根本不需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吴谢宇其实很早就感受到自己“只是一台会考试的机器”。当以一台机器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发现情感是多余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所以他要求自己动用意志力来强压。但他一直沉浸于小说和影视作品中,这些为他提供了一个情感的虚幻世界,里面有“完美的主人公、完美的亲情友情爱情、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世界”。在虚幻的世界里,他不用真的付出什么。
2015年开始的逃亡之旅,让吴谢宇突然发现,他之前对这世界的真实感知少得可怜。他知道自己做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弑母,所以他努力忘记自己是谁、干了什么。而他后来经历的真实世界让他发现,从小被安排好的生活使他的情感被抽离,也剥夺了他为生活而大笑、哀叹、痛苦的机会。
大学生活与巨大的崩塌
在北大经历的大学三年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外人看来他走向了高峰,但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崩溃呢?吴谢宇提到大学,最深的感受就是“再也考不了第一了”。在北大经济学系34个人当中,即使他的成绩是第二名,也让他觉得世界坍塌了。他认为,考不了第一,他对于妈妈就没有价值,妈妈不再以他为骄傲,他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他在自述材料中说,有一天晚上他在高楼上徘徊,想跳楼,但一看快十点了,这是他每天约好和妈妈打电话的时间,他就赶紧下楼了,去做这件最重要的事情。
大学时期本来是一个人走向更大的舞台、与全国各地优秀的年轻人发生各种碰撞的岁月,而像吴谢宇这样看上去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却走不出家庭的世界。大学是进入社会的预演,吴谢宇在北大碰到各个维度优秀的同龄人,他感受到很深的挫败感。考不了第一,只是最外显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学早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谢天琴经历的大学了,谢天琴的老师说,那时候“大家的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学生们朴素而自信,家长们也很满意。但经济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同一所大学的学生,带着的家庭视野和资源已经天差地别。所谓命运,可能正是一个人在新环境里不断调试自我的能力。
当考分不再是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当谁都不是所有人羡慕的对象,一个人必须直面自己的内在价值。而吴谢宇的自我并未建立。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可是他习惯了躲在妈妈身后,任何事情都由妈妈操心,他知道自己胆小懦弱、躲避责任,但是他并不愿意真的改变自己。他后来在写给大姑的道歉信里,承认自己害怕毕业,害怕走向社会。
当他在高中是学霸的时候,他表现出对同学的热情,大家都接受。可大学里他不再是中心,他从没学会怎么与人交心,他那种非常表面化的热情,同学显得很不在乎。他想融入,却不得其法。我们采访了吴谢宇的同学、师兄师姐,在他们看来,在北大这样一个丰富的小社会里,学生们可以分为“社团咖”“学生会咖”“恋爱咖”等,各有各的圈子,也各有各的取舍。大家都在努力适应新环境,有快有慢。但吴谢宇这样只看重分数的学生,很难获得大家内心的认同。吴谢宇后来在信里说,他曾想开口求助,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口。他过去都是站在高处,以胜利者的姿态俯瞰同龄人。
只有妈妈最在乎他,妈妈最重要。当一个人遭遇外部世界的打击,很容易想到的情感资源还是自己的父母。但吴谢宇眼中的妈妈似乎总在哀叹她不想活,说自己熬着只是在等吴谢宇读完书。
在丈夫去世后,谢天琴抱怨他们住的一楼的房子不好,蟑螂多,抽油烟机也不好用。她讨厌住在二楼的退休领导,觉得自家被欺负了。她期望吴谢宇通过高考远走高飞,离开这套房子,“离开这个鬼地方”,要“光宗耀祖”。吴志坚在世的时候,他在公司附近的马尾买了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谢天琴准备把它装修后出租,补贴家用。但谢天琴又忍不住对儿子哀叹,房子给别人住过之后,就不是自己的了。她有洁癖,不太接受房子给外人住。
这些被吴谢宇看在眼里。他在后来的自述材料里写道,他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妈妈那时经济上的压力。但妈妈真的像他认为的那样,不想活了吗?在给合议庭的自述材料里,他说他仔细回想后记起一些细节,说明妈妈也是热爱生活的,比如妈妈逛超市喜欢买零食吃,就在他杀害妈妈的前半年,他还看到妈妈从超市买回染发膏给她自己染发。
事实上,在经历丧夫之痛几年之后,谢天琴正从哀伤中走出来。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物理组的郊游,有老师看到她惊呼“谢老师来了啊”。她带过的最后一届学生王钦宁告诉我们,虽然谢天琴所在的“铁二中”是一所排名靠后的学校,但谢天琴是他唯一感谢的老师,因为她像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一样,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他曾在傍晚时分看到谢老师在宿舍楼下随便走走,偶尔低头看着土里的花花草草,“她一个人有些孤独,但我感觉她也在享受这种生活”。
总是与妈妈的情感紧紧捆绑的吴谢宇,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什么,该怎么在真实生活里爱一个人。当他在大学遇到挫折,发现自己原定的出国留学路在经济上和心力上的负担都超出预期时,他内心崩溃了。他说妈妈“没有亲情、爱情和友情”,实际上也在说自己。他说自己“无比强烈地渴望着去爱与被爱”。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书信日记里的谢天琴。
他过去以第一名的姿态,极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对于要杀妈妈这件事情,他竟然也坚信自己的判断,用一大堆大学里学到的经济学推导方式和“理性人假设”等各种概念,为自己找一种合理性。
那时候,他内心即将释放的极度的恶,已经严重偏离正常人性,是没有察觉,还是有所察觉但被他自己用概念掩盖了起来?我们不得而知。
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开庭后,他在2021年4月给合议庭写的材料里说——当时想的是,爱一个人要为她做别人做不到的。他觉得如果自己像普通人一样,看重道德、法律、良知、前程,那就说明自己对妈妈的爱不够。他要像影视作品里那样,他幻想着“一次性、一步到位、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地为爱的人做一件最大、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事情,就是对她最深的爱、为她负最大的责任”。哪怕用极端的方式,吴谢宇也要将自己区别于普通人。
他说,过去他不是在家就是在学校,在哪里都有妈妈带着,他什么都不用想,跟在妈妈后边就好。而这次,他要做那个带领者,他要带妈妈“回家”。在他的各种自我辩解中,究竟什么更接近真实,外人很难知晓。但在这桩人伦惨案的背后,人性深渊中那将人吞噬的恶,打倒了一切。妈妈的爱,既让他感动、认同、服从,又让他感到禁锢。他但凡能看到妈妈的局限,能够理解自己和妈妈的不同,就不会如此失去人性地对待妈妈。
在各种自述材料和书信里,吴谢宇表达自己情感的语句又长又绕,初读之下让人觉得他的情感很虚假。但是在了解他的整体经历和各种矛盾之处后,我们发现,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他一直不知道怎么真实地表达自己,他极度渴望温暖,但是又以自我为中心。当他只活在自己的想法里时,他连剥夺妈妈生命的事也做得出来。
在2016年、2019年、2022年、2023年这几个与案件有关的不同时间节点,我们的记者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它既是一起让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也是一桩让人痛惜的家庭悲剧。它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典型家庭特征,让人看到了家庭背负着的负担和局限,以及过去几十年里社会超速发展给人带来的不安。
正如吴志坚的朋友张力文向我们感慨的,在法律的判决之外,我们的社会又该怎么理解这起悲剧呢?
吴家和谢家早年为吃饱饭而挣扎,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吴志坚和谢天琴吃苦考上大学,有了城市户口,找了公家单位,紧接着结婚生子、分到福利房、买了车。这是一个个从农村出来的家庭在城市里立住脚的经历,也是一个个中国家庭既重大也平凡的愿望。张力文问我们:“中国人不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吗?吴谢宇考上了那么好的大学,走到了我们不曾到达的远方。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