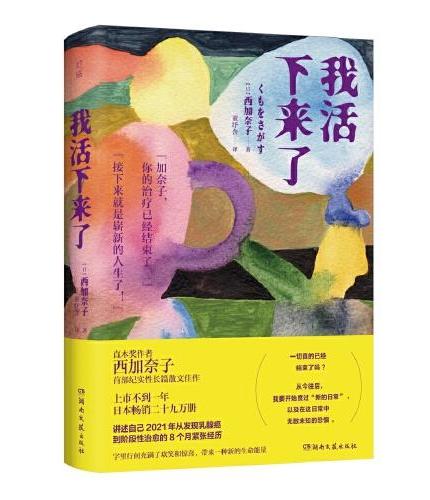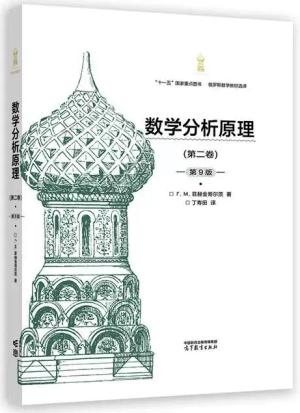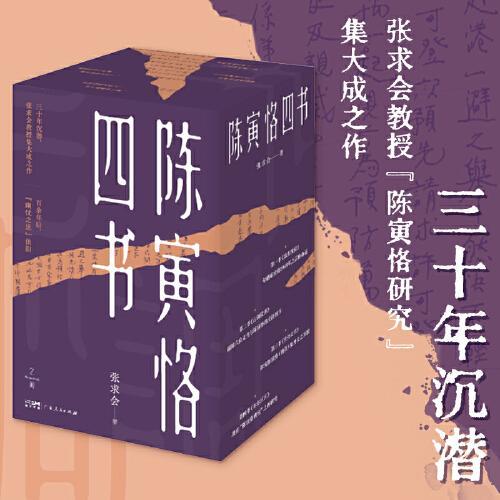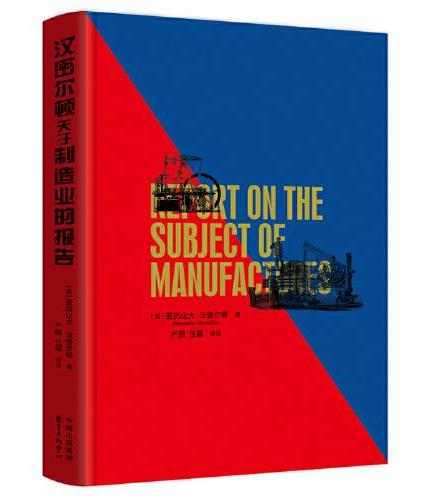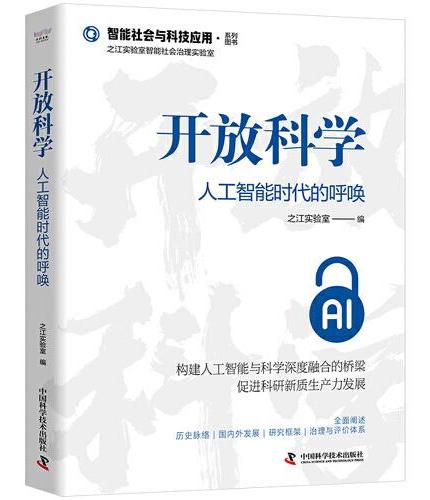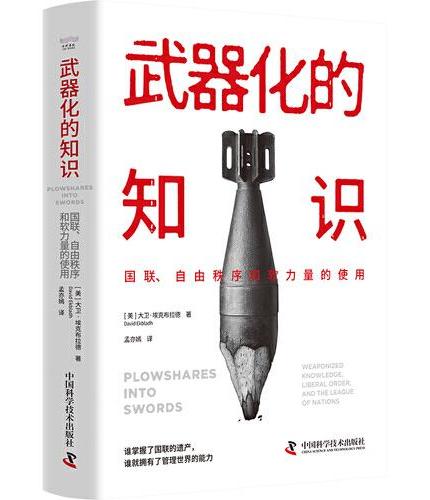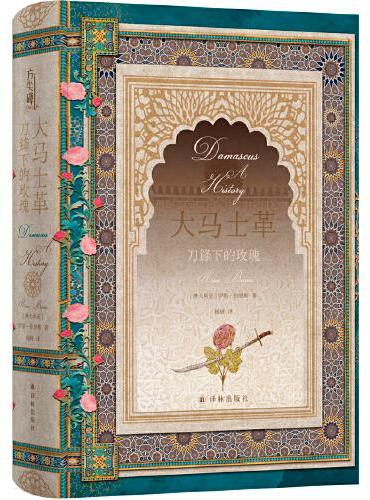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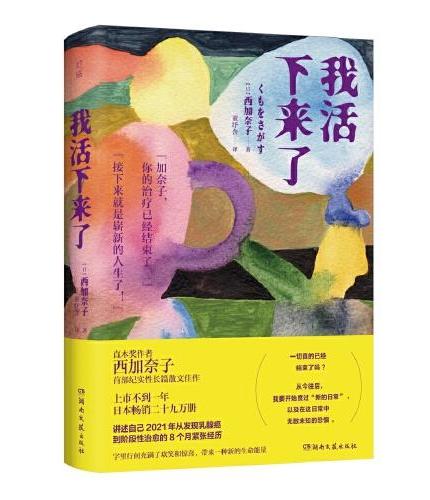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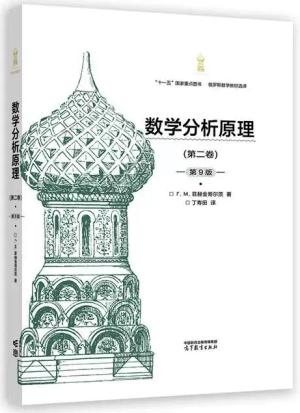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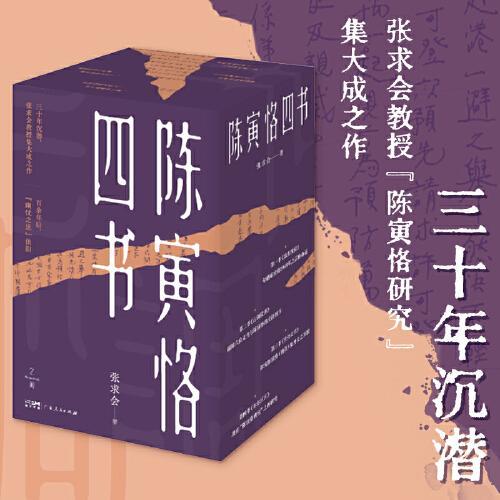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HK$
3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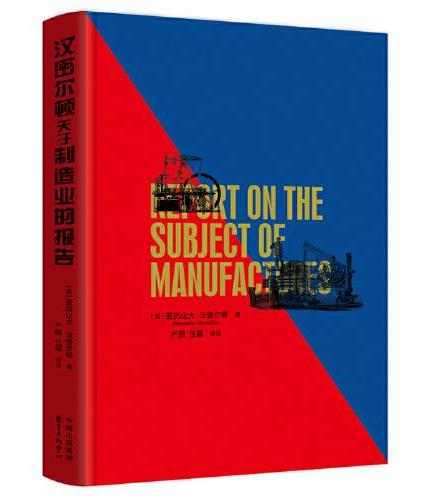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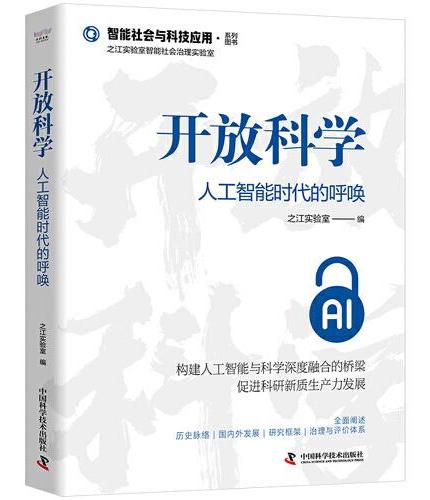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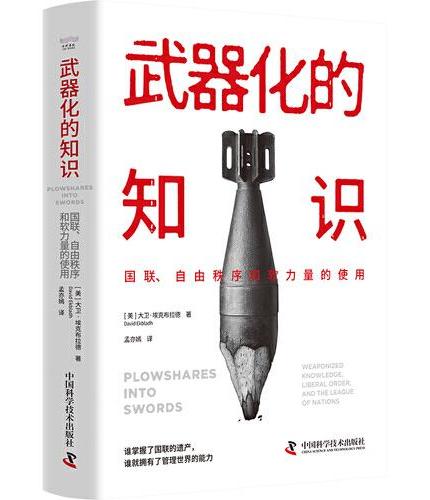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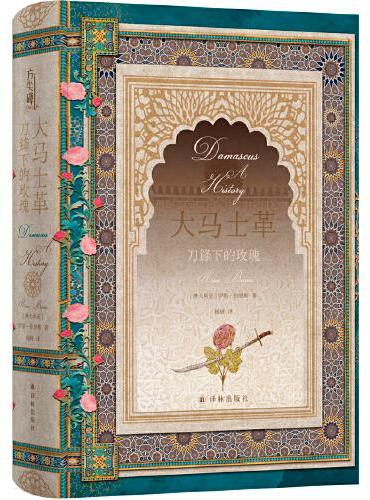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HK$
130.9

《
造脸:整形外科的兴起(医学人文丛书)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
★ 一位被诊断为“疯子”的法官在长达九年的囚禁后为争取自由而写的自我辩白
★ 20世纪最优秀的100本非虚构作品之一,一部神经疾病患者孤独而坚韧的精神抗争史
★ 所有精神分析师都绕不开的元文本,中文世界首次完整译介,拉康倾情作序,附德语原版插图
★ 日本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中“NERV”机关与“SEELE”组织的终极灵感来源
☆ 教科书级的精神分析bi读文献:精神病学史上最著名的经典病例,记录了震撼弗洛伊德、启发拉康的妄想和震惊德勒兹的“疯狂”。
☆ 20世纪思想史的“棱镜文本”:雅斯贝尔斯、卡内蒂、齐泽克……的理论泉眼;尼采思想的回声,福柯现代性批判的案例标本。
☆ 精神病叙事的文学典范:“疯癫”成为叙述主体,呼应陀思妥耶夫斯基狂人独白、卡夫卡的异化法庭、贝克特的荒诞等待以及博尔赫斯的灵魂哀歌!
☆ 跨学科研究的枢纽文本:哲学、医学、心理学、文学、性别研究(如对施瑞伯“女性化妄想”的酷儿理论解读)、宗教与神秘主义研究(“与神对话”)等多学科与领域交叉分析的焦点,也是研究精神病体验、身份认同和权力结构的经典文本。
|
| 內容簡介: |
妄想就像一块补丁,贴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最初裂开豁口的地方。
——弗洛伊德
○ 一本回忆录——胡言乱语和自省理性的奇怪混合体
不曾有人像施瑞伯这样疯狂、有如此生动的幻觉,同时又如此详细清晰地记述了自己经历的一切,这些文字直接出自理智与疯狂的边界。
● 一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在疯狂想象力的丰饶之中,蕴含着一种令人惊赞的文学性
施瑞伯首次打破了精神病患者被凝视、被阐释的宿命,用法律文书式的严谨与动人心魄的诗意书写了他的妄想世界,在这里,“疯狂”成为一种主动的、生产性的叙事力量,写就了一部关于人类精神坚韧不拔的崇高论著。
○ 一部严肃的神话作品——被一切熟悉的真实之物弃而不顾后,他通过妄想发明了一个复杂的神话世界
施瑞伯将精神崩溃升华为自我神圣化的创世叙事,以性别转换的荒诞仪式与末日预言书写了一则凡人僭越神权的渎神启示录。
1884 年,德国杰出的法官丹尼尔·保罗·施瑞伯首次遭受了精神崩溃,此后他多次发病,一系列的精神崩溃折磨着他的余生。在他发病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由一个掠夺性的上帝所主宰的神经结构,而这个上帝与他的医生弗莱希格正联手通过操纵他的神经来对他进行“灵魂谋杀”。施瑞伯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个人危机与他所说的“上帝领域的危机”有关,这场危机终止了全人类的福祉,而补救危机的办法只有一个:施瑞伯认为自己是被选中来救赎这个世界的,他要恢复这个世界失去的福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只能先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丹尼尔·保罗·施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1842—1911)是一名德国法官,出身法学世家,曾任德累斯顿地方法院首席法官,患有当时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的疾病。他在《一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一书中描述了自己的第二次精神疾病(1893—1902年),并简要提及了第一次疾病(1884—1885 年)。该书于1903年出版后引发学界震动,成为现象级精神分析案例。后来,他再次入院,在灰暗萧索中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于1911年4月离世。
译者简介
苏子滢,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期间因精神问题肄业并着手个人精神分析,持续至今(8年),写作者,自由译者,译有多部哲学学术著作。
|
| 目錄:
|
目 录
总 序 翻译之为精神分析家的任务 /V
法译版序言 /XIII
英译版导论 /XXIII
序 言 /XXXV
致弗莱希格教授的公开信 /XXXVII
回忆录
导 论 /3
1 上帝与不朽 /6
2 上帝领域的危机?灵魂谋杀 /16
3 (未印出) /23
4 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神经疾病初期的个人经历 /24
5 续;神经语(内部声音);强制思考;在某些情况下,世界秩序假定了去男性化 /32
6 个人经历(续);异象;“灵视者” /43
7 个人经历(续);疾病的特殊表现;异象 /54
8 在皮尔森疗养院的个人经历;“过验灵魂” /64
9 转院至松嫩施泰因;光束交流中的变化;“写下系统”;“绑定到天体” /76
10 在松嫩施泰因的个人经历;与光束交流相伴的“干扰”;“心境操弄” /87
11 身体完整性被奇迹破坏 /95
12 声音所说的内容;“灵魂观点”;灵魂语言;个人经历(续) /103
13 灵魂福乐作为吸引力的一个影响因素;其结果 /111
14 “过验灵魂”及其命运;个人经历(续) /120
15 “人类把戏”和“奇迹把戏”;求救呼喊;说话的鸟 /127
16 强制思考;其效果及表现 /135
17 前文续;灵魂语言意义上的“描画” /143
18 上帝和创造过程;自生成;奇迹创造的昆虫;“视线方向”;检验系统 /149
19 前文续;上帝的全能与人的自由意志 /157
20 光束在与我有关的事情上的自我中心性;个人事务的后续进展 /163
21 福乐和欲乐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169
22 最后的考虑;未来的前景 /178
“回忆录”补充说明
第一辑
1 关于奇迹 /185
2 关于神圣智识与人类智识的关系 /186
3 关于人类把戏 /187
4 关于幻觉 /189
5 关于上帝的本性 /196
6 关于未来:杂谈 /205
7 关于火化 /210
第二辑 /213
附 录
论文:《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违背其意志表达地将一个被视为精神失常的人拘留在疗养院?》 /223
补充说明 /230
补充说明二 /231
补 遗
(关于取消监护诉讼的官方文件)
A 医学专家递交法院的报告,松嫩施泰因,1899 年12
月9 日 /235
B 疗养院及地方医务官员报告,松嫩施泰因,1900 年11
月28 日 /243
C 上诉理由 /252
D 韦伯医生的专家报告,1902 年4 月5 日 /281
E 德累斯顿皇家高级地区法院的判决,1902 年7 月
14 日 /294
英译版注 /323
译后记 /339
|
| 內容試閱:
|
英译版导论
施瑞伯《一名神经疾病患者的回忆录》(下文简称《回忆录》)想必是所有精神病学文献中被评论最多的一部,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书籍文章,主要以德语和英语文献为主。历代精神病学作者都把这本书当作后继提出的一系列理论的焦点。自从弗洛伊德于1911年发表了他关于此书的著名论文以来ad,每个人关于施瑞伯都有话要说。
施瑞伯本人相信,他的书向世人传达了一条信息:不仅揭示了他所罹患的疾病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这本书也传递了某种隐晦的神启。这些文字直接出自理智与疯狂的边界。本书根据他病情最严重时的笔记整理而成,也结合了在他神志清醒后重新得以运用的思想资源。他希望这本书能广为人知,他也的确做到了,这本书以其生动丰富的细节触及到了我们关于现实、可感世界的结构、时间与空间,以及客观同一性的许多假设。施瑞伯在他痛苦和精神错乱期间见证了这一切的烟消云散,以及它们如何被重塑为神话和噩梦的素材。
《回忆录》在1903年出版时就令人震惊;医学领域的评论家纷纷推荐同行阅读。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弗洛伊德也被它深深吸引,施瑞伯的故事现在可能已经被遗忘了。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对这本书着迷,早在1910 年,弗洛伊德就在信中开玩笑地对荣格说,“了不起的施瑞伯”应该被任命为精神病学教授和疗养院院长。荣格一直对精神病现象尤其感兴趣,是他首先让同行们关注到了这本书。在书信往来中,这两个人常常借用施瑞伯的说法,比如“flüchtige hingemacht”(被草率捏造的[fleetingly-improvised])。不过,在他们分道扬镳后,荣格表示弗洛伊德从同性恋愿望方面解读施瑞伯个案是“让人很不满意的”。近年来,人们尤其从施瑞伯与他父亲——一位德国著名育儿专家——的著作的关联出发讨论了施瑞伯,这个角度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家尼德兰(W. G. Niederland)提出的,后来莫顿·沙茨曼(Morton Schatzman)又在他的《灵魂谋杀》(Soul Murder,1975)中给出了更通俗的版本。
事实上莫里茨·施瑞伯(Moritz Schreber)曾经很有影响力。我听一个德国朋友说,直到1930 年代,如果德国小孩坐得不直,还会被威胁用上莫里茨·施瑞伯的笔直固定架(Geradehalter),一种由木板和绑带制成的奇特装置。莫里茨对一切事物都有相应的系统和手册——冷水健康系统、不健康习惯矫正系统、室内健身操系统、户外游戏系统、终身饮食系统化指南。但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自杀, 一个疯了(即保罗·施瑞伯,《回忆录》的作者);莫里茨本人在去世前十年就陷入了深重的、与世隔绝的抑郁状态,当时保罗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保罗·施瑞伯生于1842 年,长大后先是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又当上法官;他结了婚,但夫妻两人经历了死产和流产,没能生出孩子。他42 岁时第一次精神崩溃,后来顺利康复了,直到1893 年,51 岁的他再次严重发病并住院(起初是自愿的),销声匿迹长达9 年。《回忆录》是他在松嫩施泰因公共疗养院(Sonnenstein public asylum)住院期间写的,既是对他深信的独特经历的记述,也是他请求出院的辩词。
经过两年的法律斗争后,保罗·施瑞伯出院并回到自己的家,与妻子和收养的女儿一起度过了一段看似风平浪静的时光。但是在他妻子萨宾娜(Sabine)因中风失能之后,他又病倒了,从那时起直到1911年去世,他一直住在疗养院。“几乎不和医生说话”,他的病历里这样写道,“只说他正被他不能吃的食物折磨等等。他一直受幻觉困扰。晚上通常睡得很差。呻吟,站在床上,僵硬地站在窗前,闭着眼睛,露出倾听的表情”。这位可怜的病人时不时地在纸片上涂写一些文字:“奇迹”——“坟墓”——“不吃”。他曾经的愿望是:“在我临终之际,我将不再置身疗养院,而是身处秩序井然的家庭生活,有亲人在身边,因为我大概需要比在疗养院能得到的更多的关爱。”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弗洛伊德对该个案的基本解释——基于《回忆录》,他从没想过亲自去见施瑞伯——和他当时的观点如出一辙:施瑞伯幻想自己变成女人(他的精神病症状之一)表明了他对父亲——体现在疗养院院长弗莱希格(Flechsig)的形象中——压抑的同性爱,弗莱希格在整部《回忆录》中都是某种恶意的半人半神形象。人们不得不同意荣格的说法:这种解释是非常有限的,弗洛伊德也确实补充说“从这个天赋惊人的偏执狂的幻想及妄想的象征性内容中,还可以提取出更多素材”。当施瑞伯在与世隔绝中开始相信整个世界已被毁灭,只有他自己被上帝选中,以便借他的子宫让人类重新在世上繁衍生息,这体现的无疑是他自身生命的灾难,而不是同性恋的愿望。他和妻子没能生下一个存活的孩子,那么上帝计划从他身体里孕育出的新的施瑞伯种族可以补偿这一点。这与其说是对男性的欲望,不如说是对女性生育力的认同——但弗洛伊德把父子关系置于分析的核心,一如既往地忽视了女性和母亲。
同样,当写到他“两腿之间的那个东西几乎完全不像正常形态的男性器官”,施瑞伯似乎是在总结他在疗养院中遭遇的种种屈辱,他的朋友、职业、婚姻生活的丧失。正如兹维·洛瑟恩(Zvi Lothane)教授重新评估施瑞伯个案的诸多含义时指出的,讨论过施瑞伯个案的所有作者中,只有托马斯·萨斯(Tomas Szasz)批评了弗洛伊德尽管长篇大论地推测施瑞伯疾病的性质,却对他被监禁的痛苦只字未提。
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施瑞伯的幻想中,他的精神科医生是残忍和全能的。弗莱希格,他入住的第一家疗养院的院长,首先是一位神经解剖学家,他的指导格言是“精神障碍就是大脑障碍”。他的治疗方法是药物加身体束缚——绑带、栏杆和软垫病房;女病人可能会被摘除卵巢或子宫。况且,他曾向一位同事坦白说,他对精神病学没什么真正的兴趣,他认为这是一门“没有希望的学问”。施瑞伯后来被送去的公共疗养院的负责人吉多·韦伯(Guido Weber)同样如此,他强烈反对施瑞伯离开疗养院,也确实把他的出院推迟了一段时间。
然而,尽管弗洛伊德对这一案例的解释在现在看来似乎方向有误,他本人确实将妄想(作为疯狂的典范)看作是人类真实、有意思的创造。在弗洛伊德看来,妄想的创造是一项工作,一个过程—— Wahnbildungsarbeit,或称“妄想形成工作”。更关键的是,弗洛伊德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妄想系统是一种让病人继续生活下去、让世界维系为一体的方式:
世界末日是这种内部灾难的投射:在偏执狂撤回他对世界的爱之后,他自己的主观世界也走到了尽头。然后偏执狂又把世界重建起来,并不是把它建得更了不起,但至少足以让他再次生活在其中。他通过妄想的工作建构世界。妄想的形成尽管被我们当做病理性产物,但它实际是一种恢复的尝试,重建的过程。[着重为弗洛伊德所加。]
这样的洞见对许许多多的“弗莱希格”和“韦伯”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如果说保罗·施瑞伯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妄想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周遭的真实世界,我们也可以透过它看到那抚养他长大的莫里茨·施瑞伯式育儿系统的结构。正如莫里茨的三十多本书里详细阐述的,它的确是个险恶的东西。它的基调是压制、控制、完全顺从。儿童的“粗野天性”和“低劣成分”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抹除。服从必须是盲目的:“孩子根本不应该想到他的意愿有可能占上风。”甚至婴儿也要服从:“郑重的威胁性手势”足以让他们安静下来。书里有时还配有特殊器械的插图,这些器械似乎和弗莱希格在疗养院里用到的器械别无二致:头托、床带、下巴带,当然还有笔直固定架。书中无疑也提到过爱的态度:偶尔“一起玩”“一起开玩笑”。但是人们可以感觉到,施瑞伯家庭里的“一起开玩笑”可能也具有某种严肃色彩。
施瑞伯妄想世界中的任性、惩罚性的上帝似乎是按照他父亲的形象塑造的。这个上帝就像育儿手册里的大家长一样,“并不真的理解活人,也不需要理解他,因为按照世界秩序,他只和尸体打交道”;这一点“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我的整个生命”。实际上,莫里茨·施瑞伯也相当于抛弃了他的儿子,因为他陷入抑郁并早早死去了。此外,男孩施瑞伯一定也是在莱因(R. D. Laing)等作家认为是精神分裂患者家庭典型特征的矛盾信息中长大的:孩子听说一切做法都是为了你好,同时接收到的却是愤怒或仇恨的信息。而在疗养院里,一个极不理性的上帝折磨着他。尤其不幸的是,养育他的不仅是一个严厉的父亲,还是个著名的育儿专家,他的矫正机构、他的著作和施瑞伯花园(Schreberg?rten)都赫赫有名。他怎么可能错了呢?
埃利亚斯·卡内蒂以及后来的精神分析家海因茨·科胡特都把莫里茨对盲目服从的要求、保罗与之相应的全能妄想和德国极权主义联系起来。也许这个联系过于牵强了。然而,在希特勒一代人成长的时代,莫里茨·施瑞伯的“家庭极权主义”著作——这是沙茨曼(Schatzman)的巧妙说法——依然流行。至少,莫里茨·施瑞伯的系统似乎反映了德国人对极端服从的痴迷,这种服从也是军校灌输给纳粹党卫军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兹维·洛瑟恩在《为施瑞伯辩护》一书中指出的,《回忆录》是对莫里茨传达给世人的信息的改写,一个替代版。在疗养院里,保罗发现了一个操纵着整个宇宙的可怕系统,并把破解它当做自己的使命,以“补上”世界的“豁口”为己任。弗莱希格、韦伯和他们的疗养院据说都在照顾他,但传达的消息却与此不同;他的妻子据说爱他,却没有来探望。因此一定有个阴谋……
把我转交给一个人类……把我的灵魂交给他,而我的身体——以一种误解了上述提到的世界秩序之基本倾向的方式——将被变成女性身体,被丢给那个人实施性虐待,然后被随意“弃置”(forsaken),即任其腐烂。像这样被“弃置”的人将遭遇什么……似乎不完全清楚……当弗莱希格教授作为人类面对我时,当然没有提过这样的事。但在本章开头讲到的神经语中,也就是在他同时作为灵魂与我保持的神经连附中,这个意图表达得很明确。……我与外界彻底隔绝,和家人失联, 被丢在那些粗暴的护工手里,内部声音说,我有责任时不时地反抗他们,以证明我的男子气概,我别无他法,一切死法无论多么恐怖,都好过那般屈辱的结局。
弃置是这里的关键词。《回忆录》讲述了被一切熟悉的真实之物弃而不顾,以及取代其位置的妄想世界的发明是怎么一回事。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妄想就像一块补丁,贴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最初裂开豁口的地方。”
施瑞伯在他被囚禁期间创造出了一个复杂的神话世界——由光束和奇迹、低阶和高阶上帝、灵魂和灵魂谋杀、神经语的声音、违背“世界秩序”的斗争构成——它涉及到真实与非真实性、同一性与融合、权力与被动性的问题。他自己的身份同一性遭到入侵,被碎片化、扭曲、摧毁,必须找到一个能解释这一切的故事。侵扰越是严重,解释就越宏大。他被弃置;于是“自从世界诞生起就几乎不曾有像我这种情况——某一个人类与全体灵魂……以及上帝全能本身展开了持续的接触……”他被隔绝、遗忘;于是“由于上帝进入了与我单独的神经连附,我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对上帝来说唯一的一个人类,或者说是一个一切都要围着他转的人”。没有人关心他是死是活;于是,“在我死后上帝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我想我很难做出预测”。一切意义都从他生命中失落了;于是“我至今依然对其真实性确信不疑——我必须解决人类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为错综复杂的问题,必须为人类的最高福祉做神圣的斗争”。他彻底孤独;于是神秘的形象成群结队地在他的身体里进出(有一次是带领着至少240个本笃会修士的耶稣会神父!)。他的头脑空了;于是它被强制性占据——“强制思考的本质在于,一个人必须不停思考;换句话说,人……让他心灵的神经获得必要休息的自然权利在我这里从一开始就被和我接触的光束剥夺了。”他病房的空虚也被折磨人的活动充斥。而当他的困境变得更可怕时,“噩耗从四面八方传来,说就连这颗星、那颗星、这个星座和那个星座都要被‘放弃’了,有一次据说金星也被‘淹没’了,又有一次据说现在整个太阳系都要‘被断连’。”
施瑞伯的妄想系统像是一种对哲学沉思的无意识模仿:他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谁?他人存在吗?时间是什么?是否存在自由意志?尤其是: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真实?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根据他被抛弃的状况形成的。当他被从弗莱希格的私人疗养院转移到韦伯更严酷的公共疗养院,他相信他人真实存在的能力也减弱了, 于是他得出了“被草率捏造的”人这个概念。这些造物随机地出现又消失(也许对婴儿来说就是这样),不再具有原本归于他们的稳固性。前往松嫩施泰因公共疗养院的旅途中他瞥见外面的世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我经过的莱比锡街道仅仅当做舞台布景,可能就像传说中波将金王子为俄罗斯皇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布置的那样,在她必经的荒郊沿途搭起布景,为了给她营造一种繁荣乡村的印象”。无论如何,他倾向于相信其他人实际上已经过世,因为“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段在人类的计算中只有三四个月的时期持续了无比漫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认为我已经是最后一个真正的人类了, 我看到的……那几个人形都只是奇迹创造的‘被草率捏造的人’。” 他没有钟表,晚上卷闸窗又被紧锁;于是“我认为星空即使没有彻底熄灭,也基本上已经熄灭了。”
施瑞伯的身份同一性也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这不禁让人想起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对精神失常时自我碎片化的描述:
一个病人认为有另外一个自己对他复述他所有的想法…… 还有人有两个身体,躺在不同的床上。有些病人觉得自己像是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失去了牙齿、大脑、胃等等。还有人觉得身体是用木头、玻璃、黄油之类的东西做的。
“还有种种企图,”施瑞伯说,“想尽一切办法来歪曲我的精神个性。”他被投进更低等的身体、不得不与其他灵魂共享头盖骨、被安上好多个脑袋。弗莱希格和韦伯的灵魂潜入他的身体。他的头骨内部甚至被衬上一层外来的脑膜,让他忘记自己是谁。他遭受了数不胜数的折磨:压缩胸腔奇迹(沙茨曼等人把它和佩戴笔直固定架联系起来)、头部勒紧机、胃被偷走、肺虫入侵。他坐着、躺着、站着都不行:“光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类必须存在于某处。”
还有一次,他说,他被注射了毒素,尽管有声音也曾对他说,如果他必须被弃置,他也要作为纯净之躯被弃置。有时,声音说的话听上去像是出自施瑞伯的父亲:“不要想你身体的某些部位”,“已经开始的工作必须完成”。有时,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听到外面的鸟说希腊语一样,他喂鸟的时候也有声音从鸟的身体里面喊道:“你不觉得可耻吗?”
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施瑞伯的论文中没有探讨这些“声音”的奥秘:这些话语,多半是病人头脑中的话语,为何会如此强烈地从外部传来?实际上,弗洛伊德本人也和苏格拉底、圣女贞德一样,亲自体验过这种情况。他在早期的一篇关于失语症的论文中描述道:
我记得我有两次面临生命危险,每次都是突然间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两次我都感到“结束了”,通常,我的内心语言都只是作为含糊的声音表象和嘴唇的轻微运动展开的,而在紧急情况下,我听到的这几个词就像是有人冲着我的耳朵喊话,同时我也看到它们像是印在一张悬浮在空中的纸上。
在疯狂想象力的丰饶之中,蕴含着一种令人惊赞的文学性。当光束说施瑞伯要转世重生,它先是说他会变成一个“极北女人”,然后是“奥塞格见习耶稣会士”,再是“克拉托维镇长”“一个必须在取胜的法国军官面前捍卫自己尊严的阿尔萨斯女孩”,最后是“一个蒙古王子”。一出超现实主义戏剧的演员阵容跃然纸上。如果说不幸的施瑞伯从他的痛苦中得到了什么补偿,那么就是这些图像充盈了他从理性中释放的心灵。他谈到了“描画”(picturing)的乐趣——
在我永无止境的乏味生活中,在声音无意义的蠢话对我的精神折磨中,“描画”确实经常是一种慰藉和安抚。能够在心眼中重新描画关于旅行、景色的往事是多么愉快啊——在光束比较配合的时候,它们逼真得惊人,有真实的色彩。
山川、人物、整部歌剧都可以被任意唤起。他自主的描画成为对抗不自主的幻觉的武器:“看见图画可以净化光束……然后它们进入我身体时就不再有通常的破坏力。因此,反奇迹经常试图遮蔽我‘描画’的东西;但我通常都能获胜……”
还有另外一些想象性工作在施瑞伯恢复岌岌可危的理智、最终成功出院的过程中起了作用。首先是弹钢琴。他的房间里有一台钢琴专门供他使用,他引用了一段出自《唐怀瑟》(Tannh?user)的台词来表达他看到钢琴时的感受:“我只记得,我已失去再次向你问好、或是再次抬眼看见你的一切希望。”他开始想起自己忘记了多少东西。音乐有它自己的回忆法则,也能击退光束:“弹钢琴的时候,那些对我说话的声音无意义的蠢话被盖过了……所有通过‘心境操弄’ 来‘展现’我或诸如此类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因为人们在弹钢琴时可以投入真实的感受。”当他弹奏《魔笛》(The Magic Flute)中的咏叹调时——“哦,我感到了,它已消逝,永远消失了”——他发现音乐体现了他从别的渠道认识到的真理。看到街上儿童的游行队伍、收到亲戚寄来有清晰邮戳的信也都缓解了他被遗弃的感受, 让他逐渐相信人类依然存在。他通过背诵诗歌来盖过声音,还和其他病人下棋。直到最后依然缺席的是情感本身:他不曾提到流泪。
尽管我们对保罗·施瑞伯的父亲有不少了解(主要都是过于严苛的方面),对他生命中的女性却了解甚少。根据他家人的说法, 他的母亲是个强悍的女家长,当丈夫长期陷入抑郁时,她也的确必须强悍。尽管他父亲留下了许多关于男子气概的训诫,但让儿子认同的更强的形象可能是母亲。也许莫里茨身上被压抑的女性气质必须由他的儿子表现出来,也许儿子像甩掉笔直固定架那样,甩掉了钳住他的虚幻男性气质。总之,讽刺的是,发号施令的莫里茨·施瑞伯如今是作为一个疯子的父亲被人铭记的。
人们对保罗·施瑞伯的妻子萨宾娜也了解甚少。起初为了谨慎起见从《回忆录》中删除的那一章,可能有不少和她相关的秘密。人们知道她和她有权势的父亲关系密切,她钦佩弗莱希格,还把他的一张照片摆在桌上,她同意把丈夫强行转送公共疗养院,也并不期待丈夫回家。这一切都可能是施瑞伯痛苦和抗议的理由。这对夫妇的养女弗里多琳(Fridoline)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她的养父“对我来说比我母亲更像母亲”;她更偏爱他,因为他“慈爱、公正、善良”。关于弗里多琳的收养还有一些未解之谜,甚至有人认为她是萨宾娜的私生女,但没有证据。施瑞伯家族里可能还藏有更多隐情。
《回忆录》无疑还会继续被后人评论。不曾有人像施瑞伯这样疯狂、有如此生动的幻觉,同时又如此详细清晰地记述了自己经历的一切。当我们追随施瑞伯对于心智解体时会碎裂成怎样的纹路的见证时,仿佛也倒叙观看了一部记录现实如何从婴儿期开始被拼搭而成的电影。一个普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将时间、空间和身份拼搭起来。施瑞伯则解构了它们。
罗斯玛丽·戴纳奇(Rosemary Dinn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