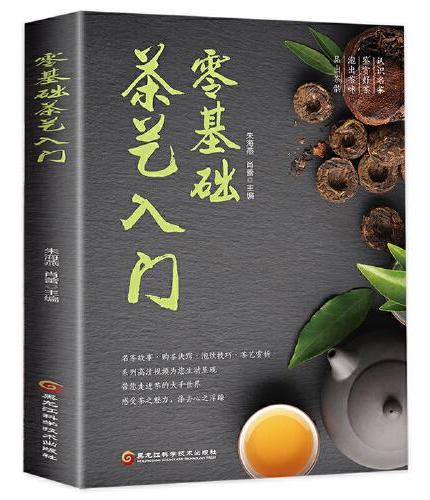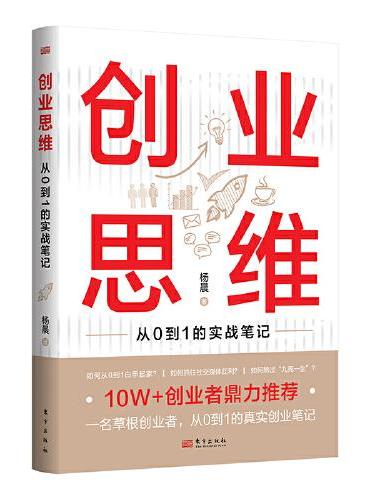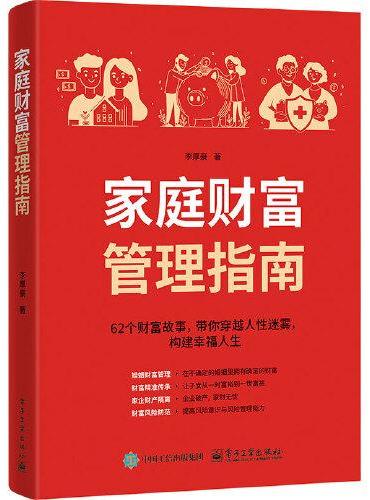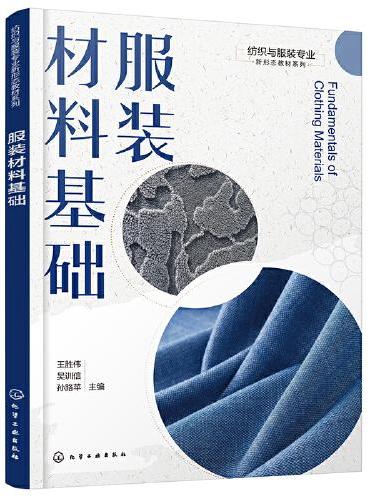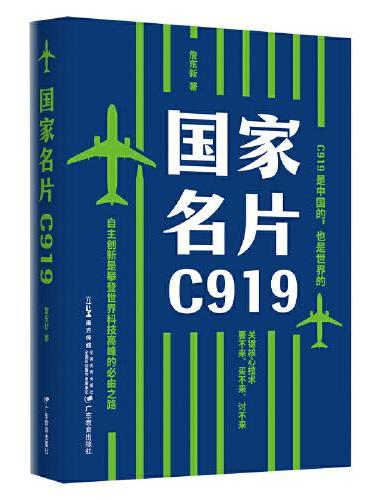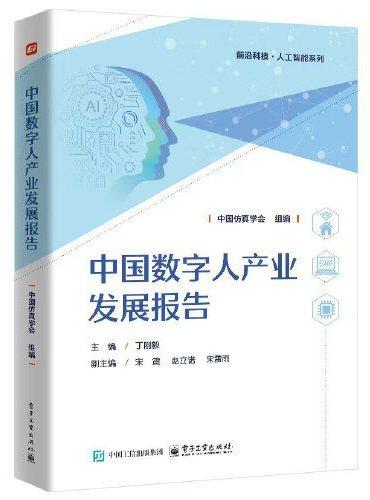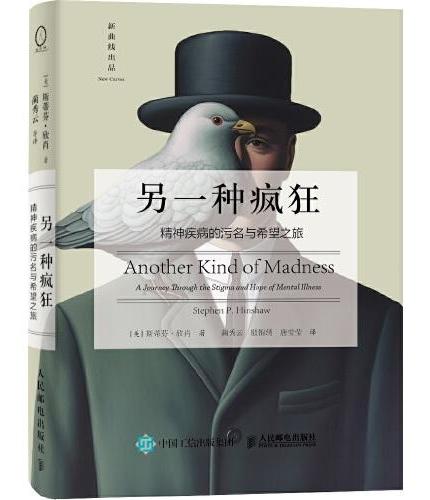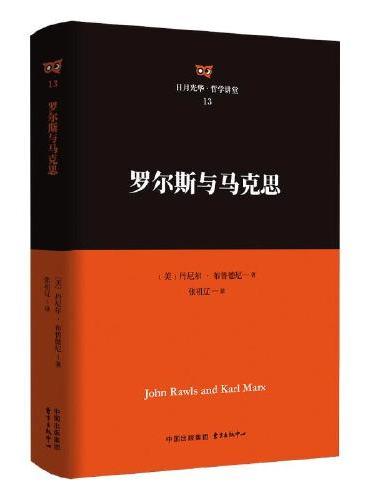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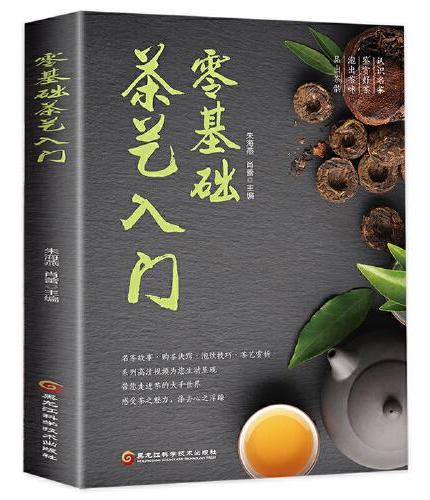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HK$
3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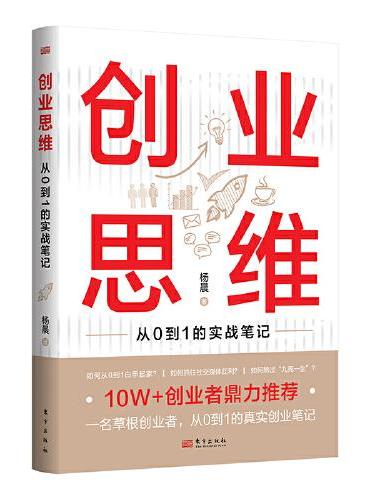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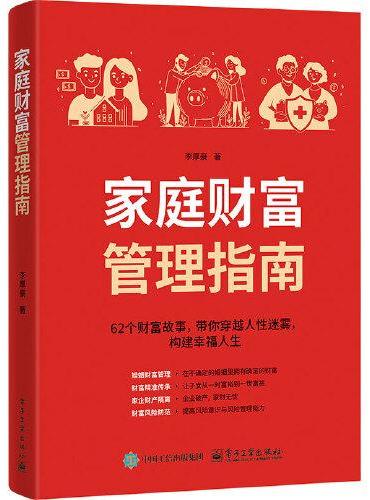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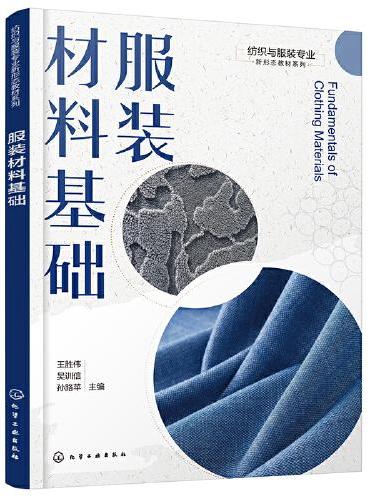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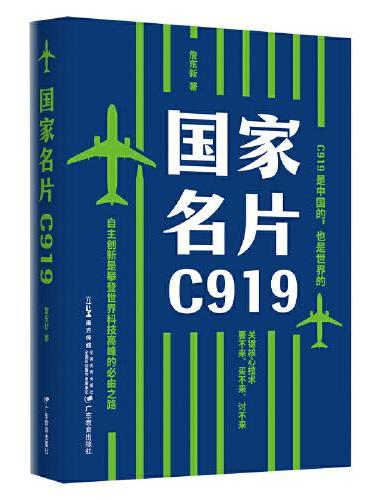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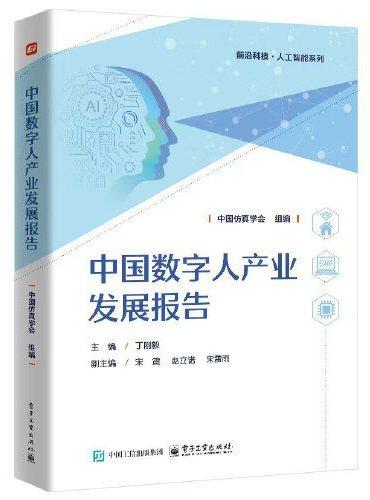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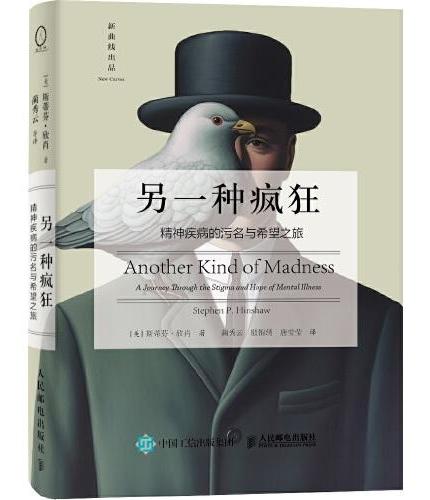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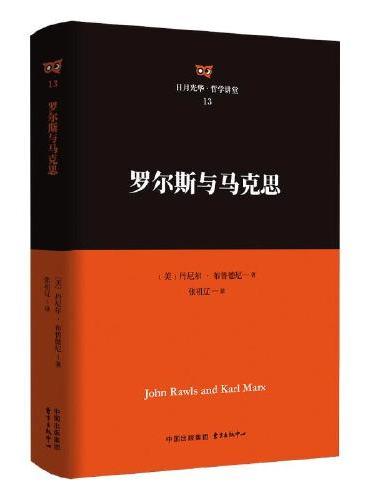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
《安娜·卡列尼娜》代表了托尔斯泰乃至长篇小说这一领域的最高艺术成就。《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活着”的书,在书中自成了一个完整运行的社会,尽管故事的背景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人物和情节却永远不会过时。这是一部关于爱情、家庭、幸福乃至人生的终极之书,不管多少次重读,都会产生对人生新的领悟,尽管它不会提供任何答案,但是却会帮助你越来越清楚地听到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
| 內容簡介: |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故事以安娜和列文两个看似天差地别却具有相似精神内核的人物为线索分别展开。这两条线索看似泾渭分明、齐头并进,其实互为表里、相互印证,一方面涵盖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广袤的俄国乡村,还原了一个完整而逼真的俄国社会全貌,另一方面也清晰地展示了托尔斯泰本人,或者说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必将遇到的精神危机及其背后的原因。
安娜是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贵妇,在一次旅途后偶遇符朗斯基,她强大的爱情力量开始觉醒,这股力量如暴风雪一般席卷着周围的一切,并最终将她推向毁灭。然而,她的故事不仅仅是一场爱情的悲剧,而是反映着所有社会施加于个体的桎梏,体现着所有多数与少数间的压制与反抗。列文是一个乡村地主,他衣食无忧,生活本该幸福,但他却对社会和人生有着不解的疑问,因此而陷入几乎自毁的恐惧之中。在列文身上,更加具象地映射出托尔斯泰本人的困境,也在思想和哲学范畴拆解着世界运行和每个个体自洽的根本逻辑。通过安娜和列文两条线索,托尔斯泰构成了一个无比完整的社会结构,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外部世界一同进步,使得《安娜·卡列尼娜》成为了一部永远不会过时的经典。
|
| 關於作者: |
|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三部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代表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将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同时,托尔斯泰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界限,在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是俄罗斯民族毋庸置疑的精神象征,俄国著名文史学家米尔斯基将托尔斯泰称为“行走在俄国大地上的最近几代人中最大的一位”,这里的“大”即指托尔斯泰思想之博大。或许托尔斯泰作品的现实意义总是随着时代变化而潮起潮落,但是托尔斯泰之永恒毫无疑问。
|
| 內容試閱:
|
《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细节
刘文飞
安娜从彼得堡去莫斯科调解兄嫂的家庭矛盾,却在莫斯科车站下车时迷倒与她偶遇的符朗斯基,在舞会上与符朗斯基热情舞蹈之后,安娜有些乱了方寸,她赶紧逃离莫斯科,返回彼得堡,符朗斯基则乘上同一趟列车,一路紧随。
到了彼得堡,火车一停下来她就下车了,首先吸引她注意的就是丈夫的脸。“啊呀,我的天!他两只耳朵怎么变成这样了?”看着他冷冰冰和神气的形象以及这时特别使她吃惊的那两只支着圆礼帽边沿的耳朵,她心里想。
纳博科夫注意到了这个场景,他在给美国学生讲解《安娜 · 卡列尼娜》时特意提及这一细节:
在卡列宁于彼得堡车站迎接安娜归来的那个著名场景中,她突然发现他那两只平平常常的耳朵大得出奇,支棱着的样子令人生厌。之前安娜从未注意到卡列宁的耳朵,因为她从未带着批判的目光看待丈夫,因为他是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她早已无条件地接受了这种生活。但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她对符朗斯基的激情就像一束耀眼的白光,原先的生活在这束强光的照耀下就像是死亡星球上的死亡风景。
安娜发现了卡列宁的大耳朵,托尔斯泰发现了安娜的发现,纳博科夫又发现了托尔斯泰的发现,于是,我们也就发现并记住了小说《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这个著名细节。
细节描写是托尔斯泰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写作方式之一,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自然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细节描写对于典型性格的塑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小说中的所谓“细节”,就是被作家强烈关注的某个细微之处,人物或环境的某个局部。作家像是拿着一个放大镜,甚至架起一台显微镜,把这些他认为无比重要的细部放大,并将其置于叙事的焦点,就像置于舞台的追光之下,以使读者更快、更多、更敏感地注意到它。细节是文学叙事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细节就没有鲜活的形象和具体的场景,没有细节也就没有小说叙事。
《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细节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人的细节和物的细节;而这两大类细节又可再做细分,与人相关的有肖像细节、动作细节和心理细节等,与物相关的则有物件细节、场景细节和风景细节等。
《安娜 · 卡列尼娜》的故事围绕三对夫妻展开,即安娜和卡列宁夫妇、列文和吉蒂夫妇以及斯吉瓦和陀丽夫妇,而符朗斯基作为一个交叉性人物将这三对关系勾连起来,他是斯吉瓦的朋友,又先后插足另外两对夫妻的关系。这七个主要角色都活灵活现,都具有其性格独特性和生命力,而他们的性格逻辑往往就是通过他们的相貌、语言、动作和心理等方面的细节描写体现出来的。在这七个人物中,安娜、卡列宁、符朗斯基和列文四人又是主角中的主角。
安娜是这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小说中的一号女主角,是托尔斯泰这部小说中最光彩照人的女主人公,但是,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的相貌描写其实着墨并不太多,仅突出了她身上的三个细节,或者说是三个“亮点”:眼中的亮光,黑色的鬈发,轻盈的步态。安娜的首次出场是在小说第一卷第十八章,对于一位小说女主角来说,这样的出场可谓姗姗来迟。对安娜的第一次相貌描写是借助符朗斯基的眼睛来完成的(这也是托尔斯泰的惯用手法,他小说中的人物肖像描写几乎全都从其他人物的视角来展开),符朗斯基去火车站迎接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母亲,在车厢门口遇见与他母亲乘坐同一个包厢来到莫斯科的安娜,安娜的美貌和气质让他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一眼,安娜恰好也在同时回头,于是,符朗斯基在安娜“那双浓密睫毛下显得昏暗的闪闪发亮的灰眼睛”里看到了“一道闪光”,“她故意使自己的目光变得暗淡,但那光辉还是违背她的旨意,流露在微微的笑容里”。在这之后,托尔斯泰一次又一次地写到安娜眼中的“闪亮”(блеск)、“光”(свет)或是“火”(огонь)。
符朗斯基结识安娜之后,“她的眼睛和微笑时闪耀的光辉使他的心燃烧起来了”。符朗斯基追随安娜回到彼得堡,在彼得堡车站的站台上再次看到安娜,发现“她的一双眼睛里有某种东西闪烁了一下,尽管它立刻就熄灭了,他已经为此感到了幸福”。而在安娜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爱丈夫卡列宁之后,“她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自己眼睛的光芒”。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陷身于生活漩涡中的安娜却开始不时眯起眼睛,这与她眼睛近视不无关系,但托尔斯泰也在强调,这是安娜的一个“新习惯”。小说第六卷第十八至十九章写安娜与嫂子陀丽谈心,在这一个章节之内,托尔斯泰就三次写到安娜的眯眼(щуриться):“安娜的一双眼睛离开了自己朋友的脸,并眯起眼睛(这是陀丽所不知道的她的一种新习惯)”;“安娜说着,眼睛眯得只让人看到连接成一道的睫毛”;“安娜眯起眼睛,像在凝视远处的什么东西似的”。
陀丽“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了安娜的那种眯起眼睛的古怪新习惯。接着,她回想起来了,安娜总是在接触到她内心问题时眯起眼睛”。安娜在自杀前最后一次拜访陀丽时,陀丽问她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去乡下庄园,“安娜眯起眼睛望着前方,没有回答她”。安娜眼中的光芒,是她激情的自然流露和投射,这是丘比特的箭,是一团烈焰,到她开始遮蔽自己眼中的这道光芒时,她可能已经意识到,这道目光已经点燃了一场终将吞噬一切的大火。
安娜身上的第二个细节特征,就是她优美的黑色鬈发(черные курчавые волосы)。符朗斯基第一次见安娜时,并未看到她的黑发,可能因为安娜当时戴着帽子,但在后文,托尔斯泰却多次让安娜这头鬈发从帽子里钻出来,翘出来,以展现安娜这满头鬈发的任性和不服帖。陀丽去符朗斯基家的庄园做客,在马车上远远地就看到骑在马上、英姿飒爽的安娜,“她那美丽的头上,高筒礼帽下露出卷曲的黑发,肩膀丰满,黑色骑马服显出她纤瘦的腰身”。安娜的儿子谢廖沙在思念母亲时,满大街找妈妈,认为“任何一位丰满、优雅和留黑色头发的女人,都是他的母亲”。俄国当代作家巴辛斯基新近出版一本讨论《安娜 · 卡列尼娜》的新书,书名是《安娜 · 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他在书中谈及安娜这头黑色鬈发的来历:托尔斯泰在一次聚会上被普希金的长女玛丽娅的美貌所惊倒,因为玛丽娅作为具有八分之一非洲人血统的普希金的女儿,生有一头鬈曲的黑发,这给托尔斯泰留下深刻印象,托尔斯泰后来就把这头黑色鬈发留给了安娜。此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黑发也往往具有某种东方的异国情调,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诱惑力。出现在莫斯科舞会上的安娜,没有如吉蒂所预料的那样身着紫色长裙,而是一袭黑色长裙,她最终迷倒符朗斯基,或者说诱惑了符朗斯基。黑色的鬈发和黑色的长裙一样,都构成安娜肖像的基本色调。小说中关于安娜头发的另一个细节也很传神:安娜在生孩子时得了产褥热,在病中被剃去秀发,她的脑袋于是似乎成了一把黑色的刷子。这是安娜的禁欲阶段,是她的忏悔期,她的黑色鬈发也因此消失,但待她逃离丈夫,逃离家庭,她的黑发也就更自由地飘逸起来,如陀丽在符朗斯基庄园看到的那样。直到她卧轨自杀之后,符朗斯基还注意到,躺在车站一张大桌子上的安娜,“盘着浓密发辫的完整的脑袋向后仰着,鬓角和美丽的脸上粘着一缕缕鬈发”。
安娜的第三个相貌细节特征就是她“轻盈的步态”(быстрая, лёгкая походка)。小说中的安娜既丰满又庄重,走起路来却迅捷轻快,动作也很干脆有力,比如在与人握手的时候,这应该是她丰盈的、甚至过剩的精力和活力的外溢。在安娜刚出场不久,托尔斯泰就写道:“安娜快速地走出车厢。她的身材那么丰满,脚步竟那么轻盈,真是让人惊奇不已。”而在生命的最终时刻,她依然“步子矫捷地下到从加水站通向铁轨的阶梯上,然后停在了紧挨着车轨的地方”。
可怜的卡列宁,自从他那对无辜的大耳朵被安娜盯上之后,他就在安娜眼中乃至所有《安娜 · 卡列尼娜》读者的眼中失去了任何魅力,并被涂抹上某种漫画色彩。在安娜开始有些见异思迁之后,她曾回顾她与丈夫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共同生活,她的内心里响起两个声音,一个在说丈夫的好话,一个在反驳这些好话:“毕竟他是个好人,诚实、善良并在自己的领域里很出色。”但就在此时,卡列宁的耳朵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安娜突然想到:“不过,他的两只耳朵,为什么这样奇怪地支棱出来!还是因为他剪过头发?”在这之后,安娜就要被迫每天面对卡列宁“支棱着的大耳朵”(торчащие уши)了。卡列宁的耳朵原本可能并不十分难看,可自从它成了安娜心目中丈夫的种种不可爱之处,即虚伪、枯燥、冷淡和一本正经等性格特征的象征物之后,安娜就再也无法忍受这对耳朵及其主人了。除此之外,卡列宁的另一个习惯动作也让安娜忍无可忍,这就是扳手指(пожимать пальцы)。看到妻子在晚会上与符朗斯基当着众人的门躲在角落的小桌子旁长时间私聊,卡列宁提前回家,并决定等妻子回家后好好与她谈一谈。这时,他“双手交叉,手心向下地扳手指,指关节便咯吱咯吱响起来”,“这个成了坏习惯的动作——双手交叉扳得指头咯吱咯吱响——往往使他安下心来”。听到安娜上楼的脚步声,卡列宁“站着,同时扳着自己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什么地方还有咯吱声”,结果,“一个关节咯吱响了一声”。在与安娜谈话期间,卡列宁再次扳响指头,这响声与卡列宁那些“谆谆教诲”一样令安娜厌恶,她忍不住喊道:“哎呀,请你别再弄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来,我不喜欢这样。”之后,每逢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卡列宁依旧会扳指头。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他的这个“怪习惯”却似乎逐渐变得有底气了。比如,在安娜请求卡列宁让她见符朗斯基最后一面时,卡列宁“扳了两下指头,垂下了头”。这一次,安娜没有再表示反对。(第四卷第19章)比如,面对十分欣赏卡列宁的丽季娅伯爵夫人,卡列宁扳起指头来也很放松,甚至像在炫耀:“皱起眉头,弯曲起手掌,弄得手指咯吱咯吱响。”(第五卷第二十二章)
与一些电影和戏剧舞台上的符朗斯基形象不同,也与许多《安娜 · 卡列尼娜》的读者想象中的符朗斯基形象不同,托尔斯泰笔下的符朗斯基其实并非一个十足的美男子,他“身材不高,体格壮实的黑发男子”,还早早地有些“谢顶”。但是,符朗斯基外貌上的两个细节却在小说中被反复提及,即他“结实密集的牙齿”(крепкие сплошные зубы)和“笔挺的身体”。笔挺的身体来自他的军人身份,他毕业于武备学校,又是宫廷侍卫,终日戎装,自然有此身姿,但作者一次又一次写到他的牙齿,则让人有些不解。在第一卷第三十四章结尾,符朗斯基听战友讲了一个笑话,他笑得前仰后合,之后很久,一想起这个笑话,他就“发出朗朗的笑声,露出一嘴结实密集的牙齿”。在第二卷第四章,他在剧院中与表姐贝特西说话时面带微笑,同样“露出密集的牙齿”。第四卷第3章,他与安娜谈话时也“露出自己一嘴洁白整齐的牙齿”;第四卷第23章,在符朗斯基自杀未遂之后,安娜决定离开家庭,跟符朗斯基出国旅行,大难不死的符朗斯基再次“微笑着露出自己结实密集的牙齿”。有人发现,符朗斯基“结实密集的牙”很像马的牙齿,符朗斯基爱马,也善于骑马,他在障碍赛马中的落马却歪打正着,迫使安娜最终向丈夫坦白了她的背叛。符朗斯基无疑有着比赛用马一样的标致和英俊,也有着比赛用马一样的大胆和莽撞。让人意外的是,在小说结尾,当列文的哥哥柯兹内舍夫在站台上遇见以志愿兵身份前往塞尔维亚战场的符朗斯基时,却发现后者正被牙痛所折磨,“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满是口水,妨碍他说话”。符朗斯基一口密实的白牙最终成为他的痛苦之源,这无疑也是某种暗示。
如果说符朗斯基的牙齿所具有的寓意还比较隐蔽,那么小说中在描写列文外貌时反复出现的两个细节,其含义则比较明显。小说中的列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在晚会还是舞会,无论是与人交谈还是独自思想,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脸红”(краснеть),这个俄语动词数十次地出现在关于列文的描述中。时时处处的脸红,无疑是列文淳朴善良的天性之自然流露,也是他倔强执拗的性格在面对现实环境时所做出的激烈反应,同时也象征作为乡村乌托邦之代表的列文在都市文明中的尴尬处境。第三卷第26章写列文前往县首席贵族斯维亚日斯基家做客时的一个场景,就特别传神地写出了列文的性格。斯维亚日斯基很想撮合自己的姨妹和列文,列文对此心知肚明,当晚,宾主在一起喝茶聊天:
列文坐在茶几边,旁边就是女主人,他不得不同她及她妹妹谈话,那姑娘正好在自己对面。女主人是一位圆脸蛋、白皮肤、个子不高的女人,带着两个酒窝和满脸笑容。列文力图通过她找到她丈夫提出的那个重要之谜的答案;但他无法进行思考,因为感到特别不自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面坐着那位姨妹,她穿着一件呈梯形露出洁白胸部的裙子。他看来这可能是特地为了他而穿的。尽管她的胸口非常白,或者说恰好因为她的胸口特别白,这个四个角的开口使列文没法自由地进行思考。他暗自设想,也许是错误地想象着,以为这个开口是打他的主意,于是认为自己无权看它并竭力不去看它;不过他感到,人家做了开口这一点已经是他的错了。列文仿佛觉得自己欺骗了什么人,他应该解释清楚,可是这种事情又无论如何不能解释,因此他不断地脸红,总是惴惴不安,很是尴尬。
……
“您亲自教书?”列文问,竭力看着开口的旁边处,可是不管他往哪个方向看,总是看到那个开口。
斯维亚日斯基姨妹白皙的胸口和列文涨红的脸庞,构成了一个鲜明的比照。
就这样,安娜黑色的鬈发和闪亮的眼睛,卡列宁支棱着的耳朵和扳手指的动作,符朗斯基密实的牙齿和列文涨红的脸庞,都是托尔斯泰在人物肖像描写上的点睛之笔,这些肖像细节在小说中始终伴随着四位主人公,构成他们醒目的识别符号和个性名片。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将托尔斯泰的创作手法命名为“心灵辩证法”,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的确是一位人物心理描写的大师,而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首先就体现为人物对外部细节做出的心理反应。《安娜 · 卡列尼娜》中最典型的心理细节描写,无疑就是对安娜卧轨前四次乘车时的内心感受之再现。安娜三次乘坐马车,两次是去与嫂子陀丽告别时的往返,一次是去火车站,而在火车车厢里的几十分钟,则是安娜人生中最后的旅程。这四次乘车构成小说第七卷的最后四章,即第二十八至三十一章。
在乘坐马车去哥嫂家的前夜,安娜与符朗斯基爆发了激烈争吵,她一夜没睡好,还服用了鸦片。早晨,她从窗口看到符朗斯基与索罗金娜伯爵小姐在门前交谈,那是符朗斯基母亲托索罗金娜伯爵小姐给符朗斯基捎来文件,但安娜知道符朗斯基的母亲试图让符朗斯基娶这位伯爵小姐,随后,符朗斯基去了离莫斯科数十公里外的他母亲的庄园。妒火中烧的安娜连续给符朗斯基送去一张便条,发去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回家,但符朗斯基没有接到便条。在此之前,安娜已得知卡列宁最终拒绝离婚的消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安娜陷入绝望,她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乘马车去哥嫂家的。安娜坐在马车的角落里,望着窗外不断变换的景物,她看到的每个细节都会在她心中激起剧烈的心理波动。菲里波夫面包铺:她想到他们会把面发好之后送往彼得堡,因为莫斯科的水好,安娜是从莫斯科嫁到彼得堡去的,她由此回忆起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油漆的味道:他们为何老是不停地油漆呢,气味真难闻;一位男子向她鞠躬致意:是她的女仆安努什卡的丈夫,丈夫一词让她想起符朗斯基,又进而想到卡列宁;街上有两个姑娘在笑:她们大概是想到爱情了吧?她们还不知道爱情有多么无聊;三个男孩在跑:安娜想到了谢廖沙,想到她会永久地失去儿子……
离开哥嫂家的返程路上,安娜的心情比来的时候更糟,在痛苦之上又添加了屈辱。路上有两个行人在说话:难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感觉说给另一个人听吗?她感觉到陀丽和吉蒂都会看不起她的;迎面驶来的马车上有一位胖胖的、脸色通红的先生,他错把安娜当成熟人,脱帽致敬,露出闪亮的光头,安娜想到:他以为他认识我,可是他不认识我,天下没有谁认识我,我自己也不认识我自己;两个男孩在买冰激凌:我们都喜欢吃甜的、香的东西,没有糖果吃,就吃这脏兮兮的冰激凌,吉蒂就是这样,没有符朗斯基,就要列文;丘特金理发店:我常在这里做头发,我要把这告诉符朗斯基,不过,现在没有谁可以告诉了;晚祷的钟声响了,一位商人在认真地画十字:这钟声和这装模作样的动作有什么意思呢,只是为了掩饰我们相互间的仇恨,就像这些破口大骂的车夫……
回到家里,安娜依然没有看到符朗斯基的回信,只接到一封冷冰冰的电报:“无法十点前赶回。符朗斯基。”于是,她决定追到符朗斯基母亲的庄园去。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安娜持续着她由外部细节所引发的紧张的心理活动。一些乘坐马车去郊游的人:你们带着狗出去玩,也是枉然,你们无法摆脱烦恼;一个被警察带走的醉鬼:我和符朗斯基都没找到这样的乐趣,符朗斯基的爱情不过是虚荣心的满足,我从他的荣耀变成了他的累赘,他的耻辱;一位骑在马上的店员:这个人是想出风头;一条条街道,一座座房子:有多少人啊,却都是相互仇恨的;一个带着孩子要饭的女人:她以为会有人可怜她呢;几个中学生:我以为我爱谢廖沙,可是没有他我居然也照样过日子,我拿他去换取了另一种爱……
上了火车,安娜的心理活动依然是在视觉细节的触动下进行的。“一个丑陋的、浑身污迹斑斑、头发乱蓬蓬地从制服帽下露出来的男人在窗外走过,向车轨方向弯下身去。”安娜突然感到“这个污秽、难看的男人好像有点儿面熟”,这就是她多次梦见的死神;一对夫妇走进来,男的与安娜搭讪,安娜立即感觉到这对夫妇彼此间的仇恨;站台上响起第二遍铃声,人们发出一阵喧闹和笑声,安娜感到恼火,因为没有什么可欢呼、可高兴的事情;列车开动时,坐在对面的那位丈夫画了一个十字,安娜恶狠狠地盯了他一下,真想问问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夕阳映照着车窗,微风吹拂着窗帘,安娜陷入沉思;列车到了车站,安娜看着站台:“为什么这个列车员顺着横杆跑过去,他们,那个车厢里的一些年轻人在嚷嚷什么?他们为什么说话,他们为什么在笑?全都是假话,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欺骗,全都是恶!……”
安娜眼中这些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众多细节,在她近乎崩溃的意识中串联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构成最终压倒她的一根又一根稻草。这一组组密实的细节蒙太奇,为她的卧轨自杀做了充分的心理铺垫。
除了与人物相关的外貌细节和心理细节之外,《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细节也体现为物的细节。物的细节有大有小,有虚有实,有的一闪而过,有的反复再现,有的是简单的象征,有的则是复杂的隐喻。
第二卷第二十二章,在卡列宁家位于彼得宫的别墅的露台上,已经怀孕的安娜面对前来约会的符朗斯基,心里一直在犹豫是否把怀孕之事告诉符朗斯基,她对符朗斯基说她正在想一件重要的事情,被吊起胃口的符朗斯基不断追问,安娜“没有回答,稍稍低下头,蹙起眉头,长长的睫毛下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询问地瞧着他。她的一只手颤抖着在把玩一片摘下的叶子”。在符朗斯基一再追问下,安娜“依旧一个劲儿地瞧着他,并感到自己一只拿着叶子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最后,安娜告诉符朗斯基:“我怀孕了。”这时,“她手里的叶子颤抖得更厉害了”。从“颤抖着”到“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再到“颤抖得更厉害了”,从把玩树叶的手的颤抖到手中树叶自身的颤抖,安娜手中这片小小的树叶(листок)在一页不到的篇幅里出现了三次,这片树叶传导出安娜手的颤抖,也传导出了她心灵的震颤,她情感的波动。
与安娜手中的那片小小的树叶相比,列文两次目睹的天空(небо)无疑就是“大的细节”了。第三卷第十二章,割了一天草的列文躺在草垛上过夜,快到黎明时,一切都安静下来,只能听到沼泽地里的蛙鸣和草地上的马在晨雾中打响鼻的声音,列文仰望星空,他把自己这一夜的思绪归结为三种:一是抛弃过去的生活,抛弃他过去所接受的无益的教育和无用的知识;二是过他现在所希望过的生活,也就是像农民那样纯朴、正当地生活;三是如何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新的生活,这一点他虽然还没想清楚,但毫无疑问,“就是这一夜把我的人生道路决定了”:
“多美啊!”他望着停留在头顶上蓝色天空中一片由浪花般的白云组成而像珠母贝壳的奇形怪状,暗自在想,“这个美妙的夜晚,一切都很美妙!这片贝壳状的云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不久前我仰望天空时,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道白白的薄云。是啊,我对生活的观点也是这么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这个场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负伤之后仰望天空、内心突然产生顿悟的那个著名段落。在《安娜 · 卡列尼娜》的结尾(第八卷第十九章,即小说的最后一章),列文再一次仰望天空:
他没有到本来要去的客厅,那里传出阵阵说话声,却停在露台上,一只胳膊靠在栏杆上,仰望起天空来。
天已经完全黑了,他眺望的南边没有云。乌云在相反的一边。那里迸发出闪电,还听到远远有雷鸣。列文凝神细听着从椴树上均匀地徐徐滴落在果园里的雨水,看着自己熟悉的三角形的星群以及从它中间通过的支流错综的银河。每一次闪电时,不仅银河,就连明亮的星星都消失了,但是闪电一过去,它们又好像被一只精确的手抛出去,又重新出现在原来的那些位置上。
这夜晚的星空让列文最终意识到,这就是“上帝对整个苍茫人世的普遍显现”,如果不能理解善,不能理解永远可以在我们自己心中找到的善,如果不能以这种理解为基础,生活就将是毫无意义的。列文的所思所想,无疑也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天问”之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