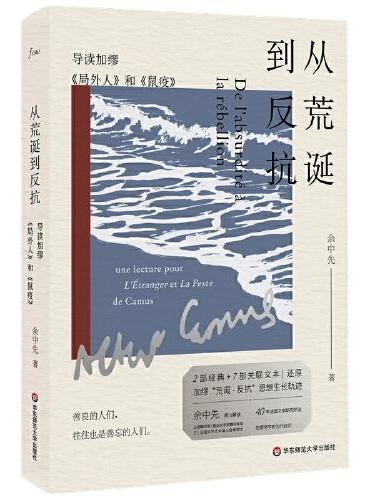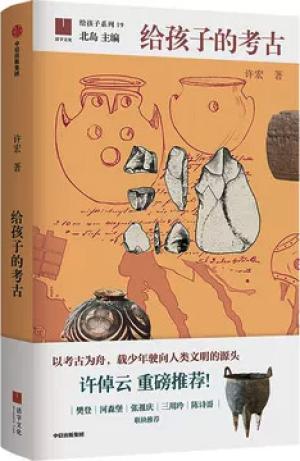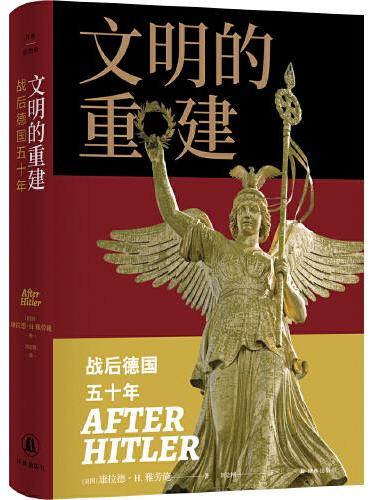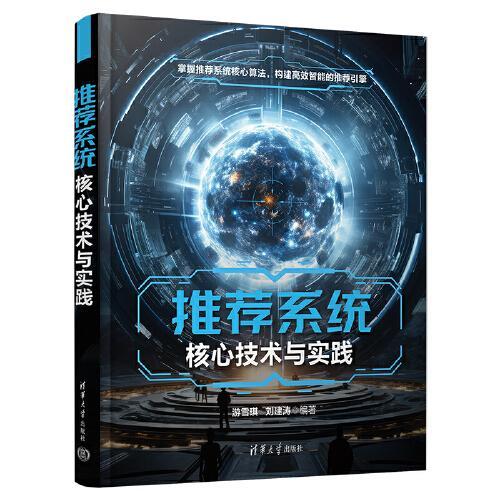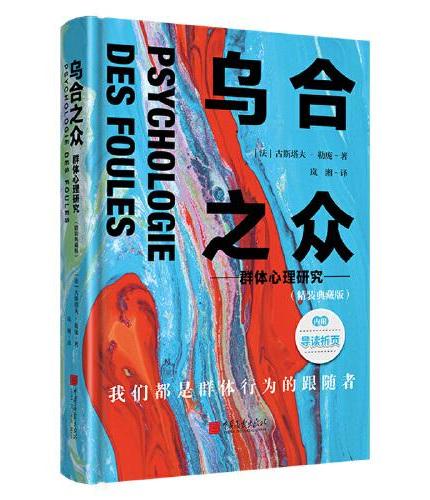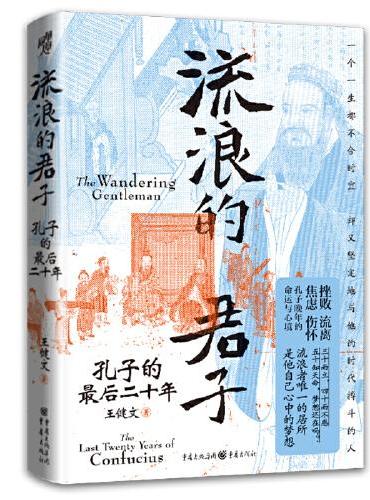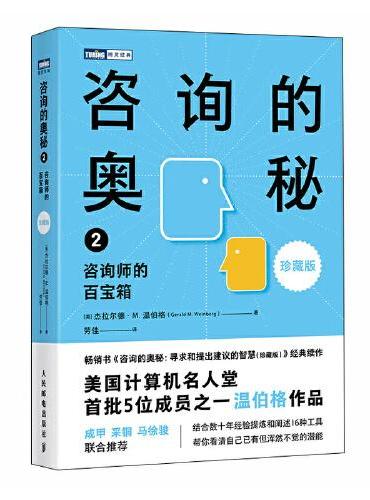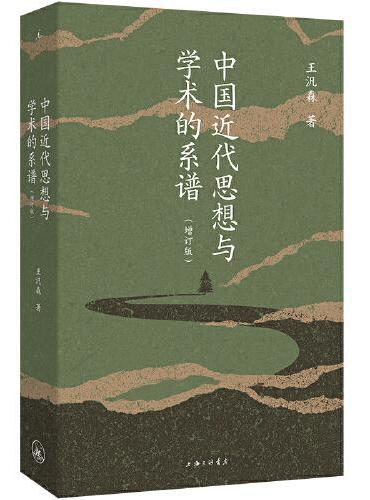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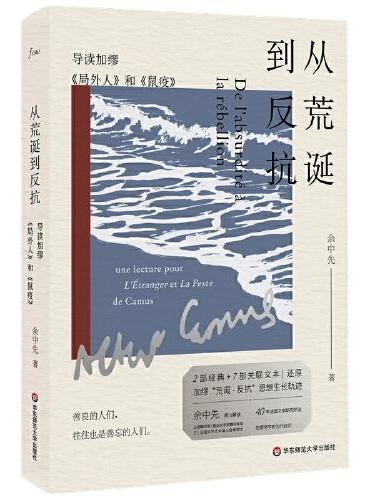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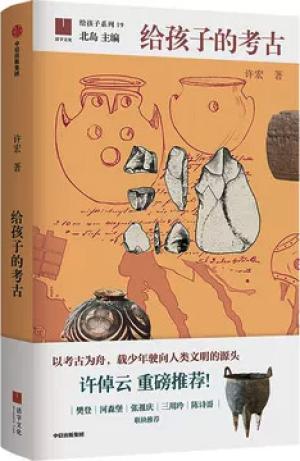
《
给孩子的考古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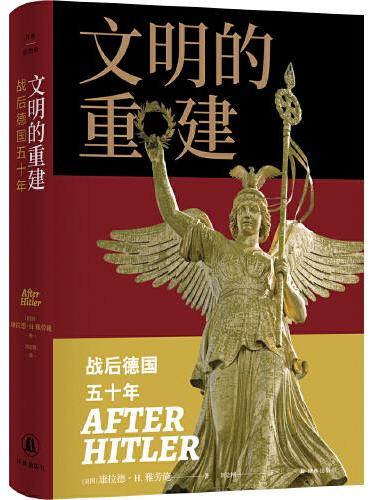
《
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译林思想史)从大屠杀刽子手到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揭秘战后德国五十年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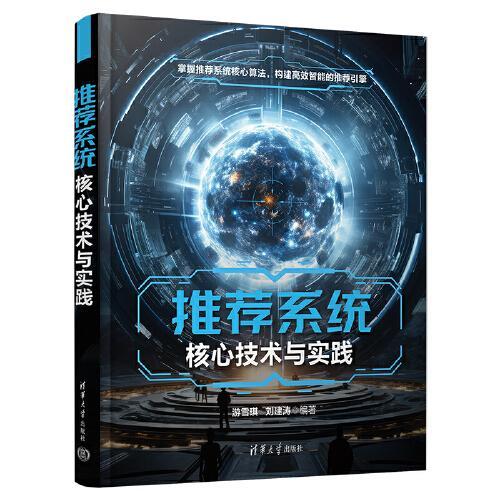
《
推荐系统核心技术与实践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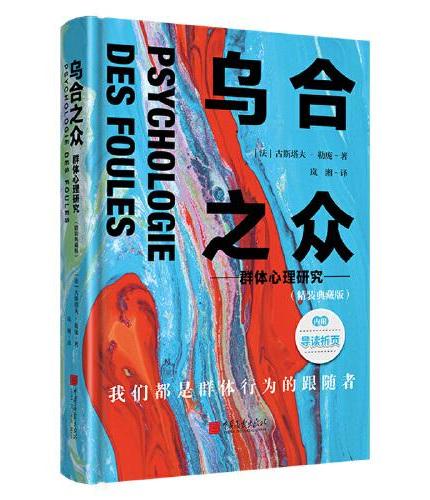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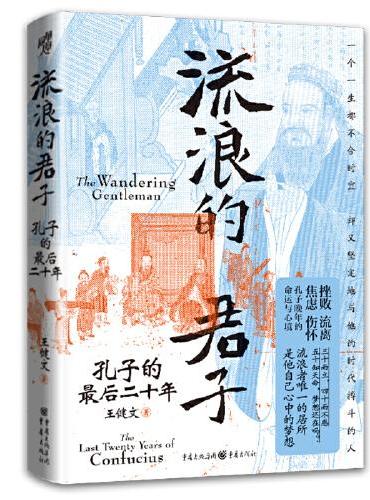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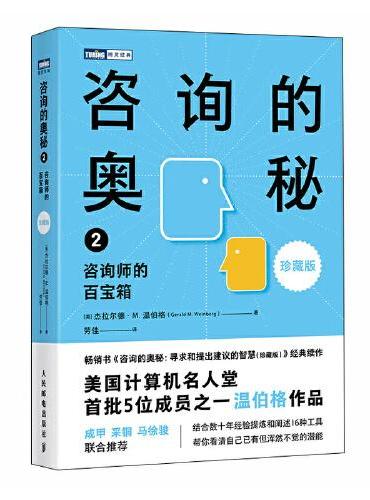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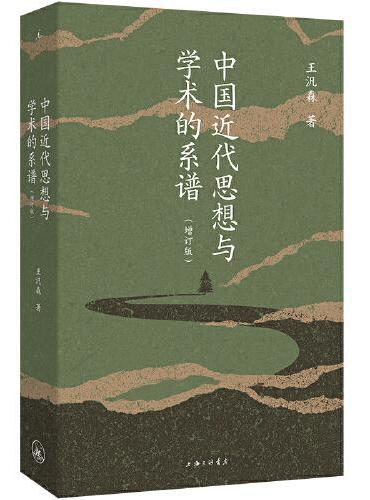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荐
《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书评》推荐
※“科技界的达尔文” 史蒂文·约翰逊经典作品
※深度分析延长人类寿命的20 项发明,人类如何为自己赢得20000天
过去三百年,科学、医疗与公共卫生的突破让人类寿命翻倍——平均多活20000天!本书揭秘了这场“生命革命”的幕后英雄:从疫苗的生死博弈、随机对照试验的诞生,到战胜饥荒的隐形战役。本书试图揭示这一进步的根源:是哪些突破、合作与机制推动了这一奇迹的实现。与17世纪英国旨在了解死因的死亡报告不同,本书聚焦于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今天的我们活得更久?通过梳理20项关键发明与创新,本书揭示了人类寿命延长的背后故事,展现了科学与社会的共同努力如何为挣得这20000天“意料之外的生命”。
※跨学科视角揭示寿命延长背后的科学、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
100年前,70岁寿命还是天方夜谭;今天,这已成全球常态。本书突破传统历史叙事,以人口数据为镜,揭示这场“长寿革命”的真相:不是个别英雄的壮举,而是疫苗、公共卫生、营养改善等系统性变革的合力。通过跨学科视角,本书解码了寿命延长的深层逻辑——从科学突破到制度创新,
|
| 內容簡介: |
大多数的历史书都以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地点为核心,而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数字的:
过去三四个世纪里取得的所有进步,包括科学方法、医学突破、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让我们的寿命平均延长了大约20000天。
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让我们在短短几个世纪里设法为自己获得了额外的寿命。这本书通过围绕人口趋势进行组织架构,试图了解这种进步从何而来,究竟是何种力量让现在的我们活下去,是何种突破、创新、合作及机制使得延长寿命这一目标成为现实,并指明未来的方向。
书中详细阐述了延长人类寿命的20项发明:
拯救了数百万人生命的创新:
鸡尾酒疗法
麻醉
血管成形术
抗疟药
心肺复苏
胰岛素
肾透析
口服补液疗法
起搏器
放射学
冷冻
安全带
拯救了数亿人生命的创新:
抗生素
分叉针
输血
加氯处理
巴氏杀菌
拯救了数十亿人生命的创新:
人工肥料
马桶/下水道
疫苗
|
| 關於作者: |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知名科普作家、媒体理论家
其著作多聚焦于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以引人入胜的观察揭示伟大创意的起源,被称作“科技界的达尔文”,著有包括《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伟大创意的诞生》《远见》《海盗经济》《死亡街区》《长寿简史》在内的10多部畅销书,作品被译成1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他创建了众多有影响力的网站,同时还是美国公共电视台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系列纪录片《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主持人和联合制作人。2010年,他被《展望》杂志评选为“数字未来的十大大脑”之一。
|
| 目錄:
|
引言 两万天
第一章 长期存在的“天花板”:衡量预期寿命
第二章 灾难列表之天花:人痘接种和疫苗
第三章 生命统计:数据和流行病学
第四章 牛奶安全:巴氏杀菌和加氯处理
第五章 超越安慰剂效应:药品监管及检验
第六章 改变世界的霉菌:抗生素
第七章 鸡蛋下落实验和火箭橇试验:汽车和工业安全
第八章 喂饱世界:饥荒的减少
结语 再访波拉岛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
| 內容試閱:
|
引言 两万天
章克申城镇以北的堪萨斯河流域驻军的历史可追溯到1853年。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后的几年里,那里设立了一个哨所,以保护西行的旅行者。几十年间,这个被称作赖利堡的地方逐渐为人所知,它一度还被当作美国的骑兵学校。1917年,当美国军队正为美国参加一战做准备时,一座5万人的小城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用来训练赴海外参战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士兵。
曾被称作芬斯顿军营的地方有3000座临时建筑,除了常规的营房、食堂、指挥官办公室,还有杂货店、剧院,甚至一间咖啡馆。对年轻的新兵来说,这座新兴城市有很多便利设施。一名士兵在家书中提到在芬斯顿军营中能够欣赏到劳军的交响乐。但临时建筑意味着大部分营房几乎没有相互隔绝。营地建好后的第一年,那里的冬天出奇地寒冷,迫使本就住在紧挨着的营房中的士兵在宿舍和食堂的炉灶旁扎堆取暖。
1918年3月初,冬日接近尾声,一名叫艾伯特·吉切尔的27岁二等兵来到医务室,自诉出现了肌肉疼痛和发热的症状。吉切尔是屠夫出身,作为炊事员,在芬斯顿军营的食堂工作,为数百名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战友准备伙食。医生诊断其患有流感,将其送至了传染病房,希望以此阻断疾病的传播,但这一防治措施为时已晚。一周之内,芬斯顿军营中数百人报告了流感症状。到4月,芬斯顿军营中有超过1000名士兵住院,其中38人死亡——鉴于这是一种通常只对老幼产生威胁的疾病,这一死亡率高得惊人。
最早表明堪萨斯军事基地情况不妙的,是人满为患的医务室和芬斯顿军营太平间里堆积的尸体。但直到几十年后,随着电子显微镜的发展,那里的真实情形才为科学家所掌握。在艾伯特·吉切尔的肺里,一个长满刺状物的球体附着在其呼吸道表面的细胞膜上。球体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质,将自己有限的遗传密码与吉切尔的遗传密码融合,并开始自我复制。大约10个小时之内,细胞中便充满了新复制的球体,将细胞膜撑至临界点,直至细胞在一个灾难性的瞬间突然爆炸,在吉切尔的呼吸道内释放出数十万个新球体。有些球体通过咳嗽或者打喷嚏进入食堂和营房的空气中,其他的则留在吉切尔的肺部,以同样野蛮的自我复制机制占有其他细胞。
芬斯顿军营的医生当时无法知道,侵袭艾伯特·吉切尔肺部的球体形成了一种新的H1N1病毒,它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俗称“西班牙流感”的疫情中席卷全世界。如同病毒本身在吉切尔的呼吸道中自我复制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芬斯顿军营的情形将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上演,这是因为士兵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各地和欧洲前线。美军将病毒带到法国布列塔尼大区西北部边缘的布雷斯特军港,病毒随后于4月下旬在巴黎暴发。意大利紧随其后。5月22日,马德里《太阳报》报道称,“一种尚未被医生诊断出来的疾病”正在马德里驻军中肆虐。至5月底,该病毒已在印度、中国和新西兰蔓延。
与大多数流感病毒相比,1918年春席卷全球的H1N1 病毒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它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且引发许多人的肺部细胞破裂。但它并不十分致命。这种流感能以可怕的速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席卷全球,也就是说,“球体”在肺部快速地进行自我复制。但很多人都从这场流行病中康复了。用专业术语来讲,该病毒显示出较高的发病率和较低的死亡率。它有惊人的自我复制能力,但一般不会让宿主死亡。
而1918年秋暴发的H1N1 病毒就没那么仁慈了。
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在争论,为什么1918年的第二轮“西班牙流感”病毒比当年春天首次出现的病毒的毒力强得多。一些人认为,这两轮流感由不同的H1N1 病毒的变种引发。另一些人则认为,两种不同的病毒在欧洲相遇,以某种方式组合成一种新的更致命的变种。还有人认为,最初流感症状较轻的原因在于,病毒刚从动物宿主传播到人类宿主,需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很好地适应其在智人呼吸道中的新生境。
无论根本原因是什么,第二轮流感带来的死亡结果都是令人震惊的。在美国,新的疫情首先出现在德文斯军营。这一军事基地位于波士顿郊区,人满为患。到9月的第三周,军营中1/5的人员感染了流感,其发病率超过了芬斯顿军营H1N1 流感暴发时的发病率。但真正让德文斯军营的医务人员震惊的是死亡率。一名军医写道:
仅仅几个小时就会死亡,这太可怕了。看到1个、2个或20个人死去,我们尚可忍受,但这么多可怜虫像苍蝇一样纷纷倒下……平均每天有大约100人死去……患上肺炎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意味着死亡……我们失去了大量护士和医生,阿耶尔小镇的景象惨不忍睹。运送死者需要用专列。好几天都没有棺材,尸体堆积如山……这比法国任何一场战斗结束后的场景都更为惨烈。超长的营房已被腾出,用作太平间。死去的士兵被穿戴整齐,排成了长长的两排,路过的人惊恐万状。
紧随德文斯军营,世界各地暴发了更多灾难性的疫情。1919年美国的死亡人口中,有近半数死于这种流感。数百万人在欧洲的前线和军医院死去。印度部分地区感染者的死亡率接近20%,比第一轮疫情的死亡率高出一个数量级。今天最可靠的估计表明,在世界各地疫情暴发期间,多达1亿人死于流感。约翰·巴里著有关于这次疫情的权威著作——《大流感》,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1918年,世界人口约为18亿。这一最高估值意味着两年之内世界上有超过5% 的人口死亡,而大部分人死于1918年秋的12周内。”
死亡率报告揭示了这一流行病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1918—1919年的H1N1流感对年轻人尤为致命,通常情况下他们是在普通流感季节抵抗力最强的人群。巴里指出,在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人群是25岁至29岁的男性和女性,30岁至34岁的人群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是20岁至24岁的人群。而且,上述以5年为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任意一组的死亡人数都多于60岁以上人群的总死亡人数”。这种不寻常的情况部分是因为病毒在军营和军医院的密闭空间中近距离传播。科学家还认为,1900年出现的一种类似的病毒使得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对“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变种产生了免疫力。
后来计算并制作的有关这一时期的预期寿命图表,清晰地展示了“西班牙流感”不同寻常的年龄分布。在H1N1流感暴发期间,50岁以下人群的预期寿命急剧下降,而70岁人群的预期寿命则未受影响。但总的来说,情况不容乐观。在美国,几乎一夜之间,平均预期寿命骤降了整整10岁。印度则可能遭遇了人类有史以来——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或狩猎采集社会——的最低预期寿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预期寿命已经连续增长了半个世纪,结果在短短3年内就被因战争而扩散的病毒抵消。一战前夕,不仅是精英阶层,总体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都已达到55岁。然而,等世界大战和大流感的双重灾难结束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生儿预期寿命只有41岁,和伊丽莎白时代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
随着H1N1病毒在世界各地不断蔓延,陆军科学家维克托·沃恩早在估算出这些数据之前就开始分析来自欧洲前线的大致伤亡人数。他在一封亲笔信中推测:“如果疫情以数量级的速度加速扩散,文明很可能会消失……再过几周就会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
假设你回到1918年年末,你在德文斯军营查看堆放在临时太平间里的尸体,或者你漫步在孟买街头,在那里,超过5%的人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死于流感。假设你在参观欧洲的军医院,看到许许多多年轻的身体被机枪、坦克、轰炸机等新式战争装备以及H1N1流感摧毁。假设你知道战争和疫情带来的伤亡会折损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全世界的健康状况会从20世纪倒退至17世纪。在战争和疫情结束之时,身边的尸体堆积如山,你会对接下来的100年做何预测?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进步是否只是侥幸,很容易被战争和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加的流行病风险抵消?还是如同维克托·沃恩所担心的,“西班牙流感”是否预示着更为黑暗的结果,某种呈“数量级增长”的毒力更强的危险病毒会导致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崩溃?
随着全世界慢慢从大战和H1N1流感的双重风暴中恢复,上述两种可怕的情况似乎都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它们都没有发生,这着实令人惊讶。人们并未走上预测的惨淡道路,而是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纪。
1916年至1920年是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将出现重大逆转的最后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预期寿命确实短暂下降,但无法与“大流感”期间的严重程度相提并论。)1920年出生的英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1岁,他们的后代现在的预期寿命为80岁。虽然西方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取得了大量进步,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预期寿命在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100年前,生活在孟买或德里的人活到年近而立就很不错了;而今天,南亚次大陆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岁。沃恩说的对,未来的确有非同寻常的“数量级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是积极的:越来越多的生命没有被摧毁,而是得到了挽救。
但这一进步的步伐也并非不可阻挡。新冠疫情几乎恰好出现在大流感结束后的100年之际,它提醒着我们一个可怕的事实:在快速传播的传染病面前,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的世界更为不堪一击。迄今为止,新冠疫情已使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缩短了大约一岁,非裔美国人群体则缩短了大约两岁。疫情尽管带来了恐惧和悲剧,但也展示了人类自1918年以来的100年间所取得的进步。全世界总人口是1918年的4倍左右,但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不到1918年大流感的1%。某些评估显示,虽然在疫情暴发早期的2020年上半年走了一些弯路,但其间的公共干预措施仍然挽救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然而,另一种病毒可能将新冠病毒的隐性无症状传播与1918年大流感病毒高得多的病死率相结合,像冠状病毒杀死老年人一样无情地杀死儿童和年轻人。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如此大规模的健康危机,并继续在延长人类寿命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我们就需要了解过去100年间推动此等重大变化的力量—不仅是为了庆祝取得的成就,还要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大流感结束之后的100年间,人类健康的总体发展情况可以用三张图来说明。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图开始,回到17 世纪中叶,看看当时英国人的预期寿命。
这张极其重要的图展现了人类以及地球发生的变化。在17世纪60年代初,当人们首次尝试计算预期寿命之时,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刚刚超过30岁。今天,英国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已经增长了整整50岁。而且,这种惊人的增长在世界范围内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过去三四个世纪里取得的所有进步,包括科学方法、医学突破、公共卫生机构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让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两万天。数十亿原本没有机会活到成年,更别提拥有自己孩子的人,现在都享有了这些最为宝贵的机会。
在人类进步的衡量标准中,很少有像这一点那样令人惊异。从长远来看,这延长的两万天应该成为每份报纸每天的头条新闻。但是,延长的人类寿命几乎从未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上,因为它几乎完全不具有推动新闻传播的传统戏剧性色彩。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关于进步的故事:杰出的创意与协作在远离公众关注焦点下展开,由此带来的进步是循序渐进的,历经数十年才能显示其真正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何新闻会选择关注短期内引起轰动的事件,如即将进行的选举、名人丑闻等,它们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核心问题转移至肤浅的轰动性事件。如果缺乏长远眼光,我们就会遗忘那些曾让祖辈感到恐惧的威胁,如今它们早已转变为平凡且可控的情形,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考虑它们。尽管这种选择性记忆也是进步的一大标志,但它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如果不去考虑那些已经被人类解决的威胁,我们很容易被分散注意力,而忽视过去100年来人类健康和社会福祉方面取得的基本进步。如果不反思过去,我们就无法从中吸取教训,无法利用那段历史来更为清晰地思考我们目前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过程中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进步,也无法利用那段历史来应对这些进步带来的不可避免、意想不到的后果,也不太可能相信现有的资源和机制能应对诸如新冠疫情等新出现的威胁。我们有关于比尔·盖茨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植入微芯片的荒谬阴谋论,也有针对佩戴口罩等简单行为的公然敌视,部分原因是我们忘记了科学、医学和公共卫生作为一种文化,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人的平均寿命的质量(和长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道隐形屏障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逐步建立起来,而人类越来越依赖这道屏障的保护,它让我们更安全,离死亡更远。它通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干预措施来保护我们:饮用水中的氯,消除天花的“包围接种”技术,掌握全球最新疫情信息的数据中心,等等。我们对这些创新和机制的关注远远不及我们经常给予硅谷亿万富翁、好莱坞影星甚至军事指挥官的关注。但它们在我们周围建立的公共卫生屏障(最显著的衡量标准就是人类预期寿命翻了一番),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所有这些进步的新视角。疫情的有意思之处是,它会使隐形的屏障突然变得暂时可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日常生活对医学科学、医院、公共卫生机构、药品供应链等的高度依赖。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还能起到其他作用:它帮助我们了解屏障上的漏洞、薄弱之处,了解保护自己免受突发威胁所需要的新的科学突破、新的体系、新的方法。
大多数的历史书都以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地点为核心,如一位伟大领袖、一场军事冲突、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相比之下,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数字的: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在短短一个世纪里让我们获得了额外的寿命。本书试图了解这种进步从何而来,是何种突破、协作及机制使得这一目标成为可能,也尝试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在这延长的两万天中,有多少天来自疫苗的使用,有多少天来自随机对照试验,又有多少天来自饥荒的减少?第一份让人们开始思考预期寿命的死亡率报告是为了了解17世纪英国人的死因。而本书则完全不同,它所探究的是:究竟是何种力量让现在的我们活下去。
总体预期寿命图的确很重要,但确实传递了一个略带误导性的信息,让人们幻想在不久的将来就能长生不老。如果把目前人类延长的寿命视作平均值,那么增长就会失控。假设你按下快进键,想象这一趋势在未来一个世纪将会如何发展:按照目前的上升趋势继续下去,人类的“平均”寿命将达到160岁。
但如果把本书中的故事仅仅看作图上的一个分布区间,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死亡率最为显著的下降发生在生命的头10年。当代成年人当然比工业革命鼎盛时期的成年人寿命更长,如今全球的百岁老人人数是1990年的4倍,但从平均预期寿命图来看,这种差异并没有预期的那么显著。超过两个世纪以前,就有许多人活到了60岁以上(如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麦迪逊和富兰克林都活到了80多岁,亚当斯活到90多岁)。但婴幼儿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如果大量人口在5个月或者5岁时死亡,这些人的死亡就会大幅拉低总体平均寿命。但如果这些孩子中的大部分能活到成年,平均预期寿命就会大幅上升。
设想一个只有10人的群体,你就能更为清楚地理解这一结果。如果他们中的三人在两岁时死亡,也就是说这个群体的儿童死亡率约为30%,而其余人能活到70岁,那么这个群体的平均预期寿命则约为49岁。如果这三人一直活下去,和其余人一样活到70岁,总体平均预期寿命就会达到70岁,直接提升了约21岁。但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的寿命并没有增长,只是孩子的死亡率下降了。
早夭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人口统计学家区分“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和其他年龄段的预期寿命的原因。在许多社会中,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明显低于15岁或20岁时的预期寿命,因为婴儿期或幼儿期的死亡风险非常高。比如说,一名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可能只有30岁,而一名年轻的成年人则很可能活到50岁或更长。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儿童死亡率都较低,人们每活一年都会降低后续可预期的总寿命,也就是说,每增长一岁,离生命的尽头就更近一年。但儿童死亡率较高的社会则是相反的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预期死亡反而会越来越远,至少会持续到成年早期。
这一切都意味着,预期寿命失控增长的图应始终伴随着第二张图,该图记录了同样不可思议的儿童死亡率走向。
本书从两个简明但惊人的事实开始: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将预期寿命翻了一番,而且我们将儿童死亡这一人类最悲惨的经历的概率也降低了90%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