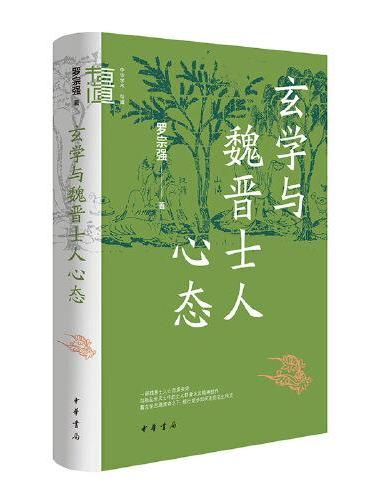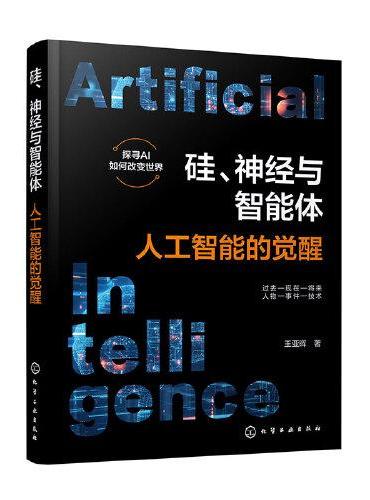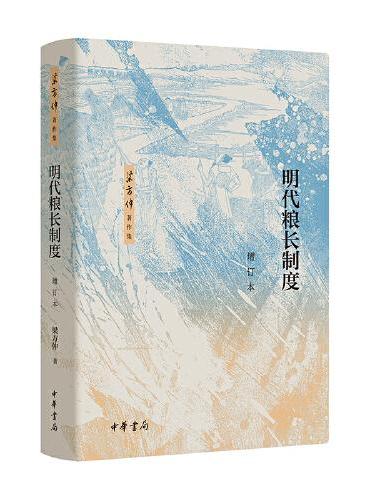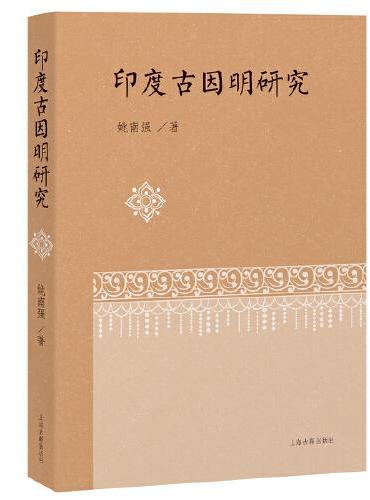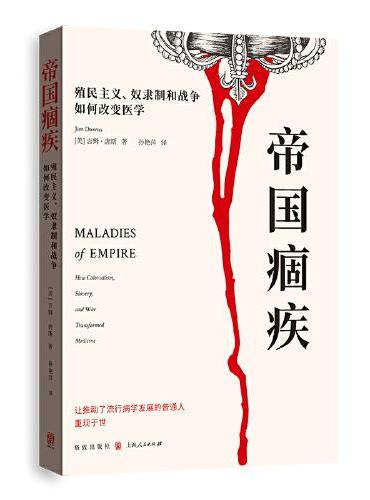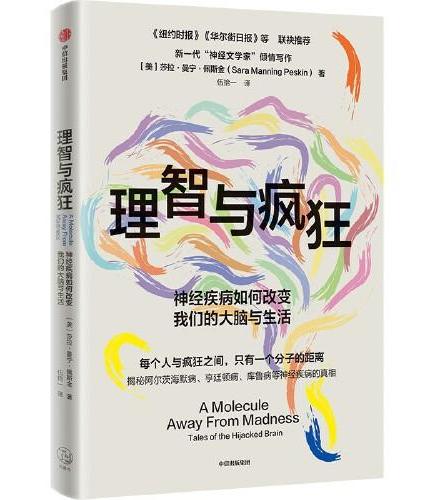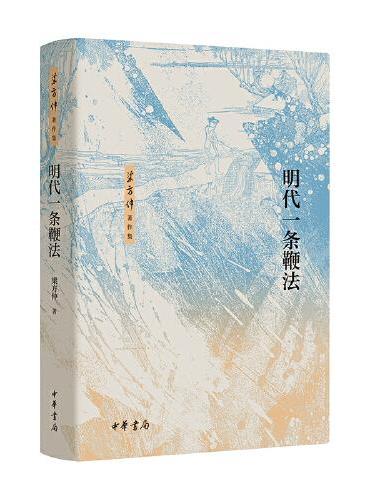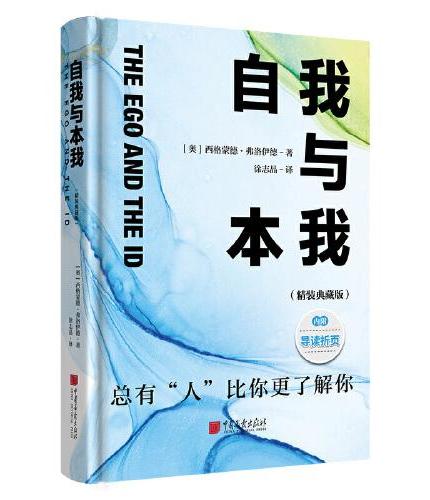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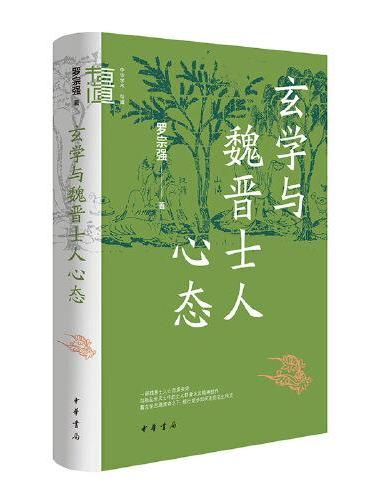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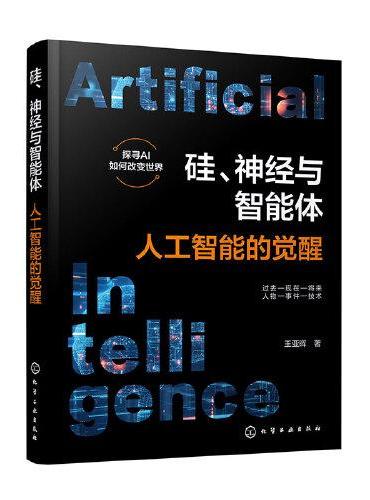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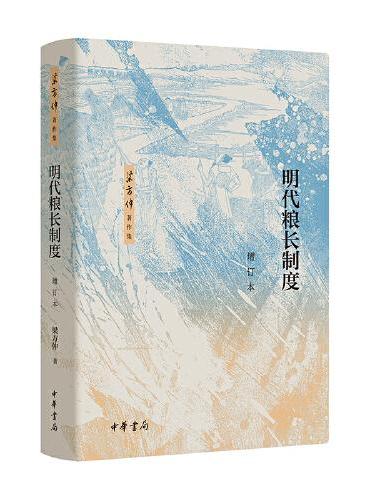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6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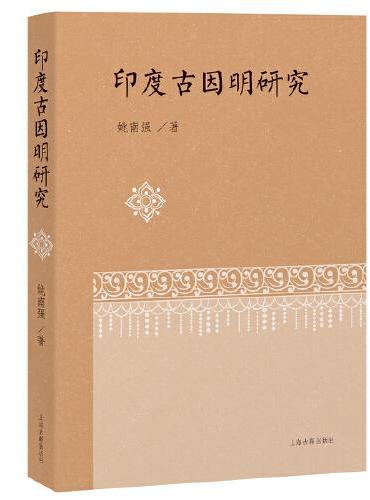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HK$
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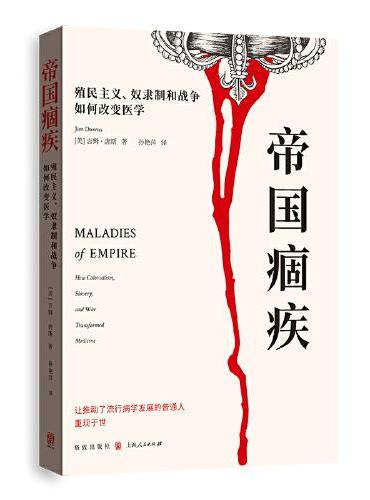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HK$
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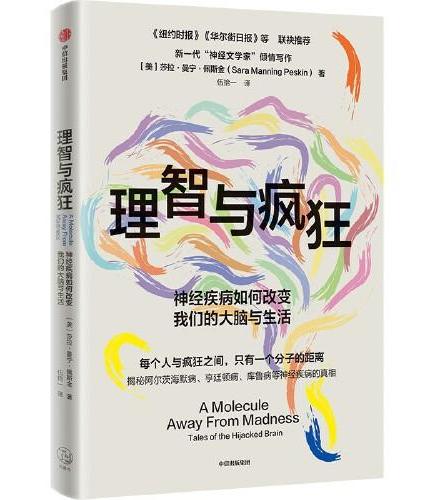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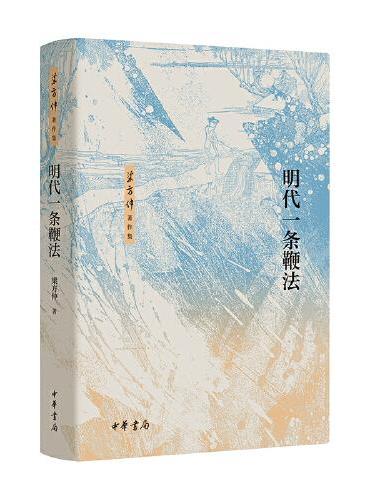
《
明代一条鞭法(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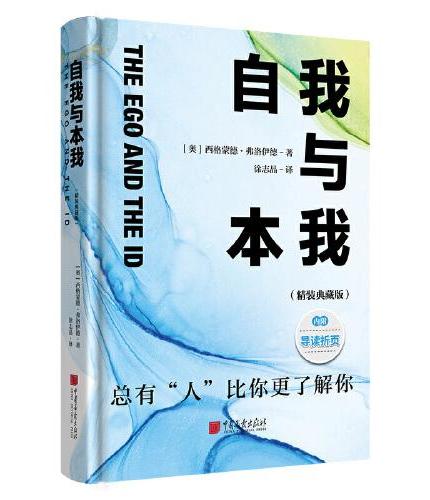
《
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经典心理学著作(精装典藏版)
》
售價:HK$
74.8
|
| 內容簡介: |
一次飞机失事,夺去了荷兰纪录片制作人阿图尔的妻儿。此后,他变身旅人,客居数地。没有“窝”,只有居间的驿站。他去往柏林,等待下一份工作。
柏林负雪,众灵环绕。他漫游其间,穿越寒冷与飞灰的记忆,以摄影师之眼,一寸一寸地悉数检验柏林的伤痕,如同他的指尖一点一点地抚触艾力克伤疤的轮廓。伤痛,从不轻易赦免一个人、一座城。有名历史的摧毁重建与无名个体的失语命运组成了他眼中柏林城的过去与现在。“通过柏林这个棱镜,可以窥透整个人类的历史。”
随着他脚步的牵引,我们结识了哲学家阿尔诺、雕塑家维克托、物理学家和画廊老板芝诺比娅,通过电话熟悉了埃尔娜,偶遇了艾力克。艾力克是塞壬的化身。他为她所吸引,所占有,所召唤。为了逃离,他远赴四国岛,又无力抗拒追随她到马德里,直到最后……
我们是谁?旁观者。
|
| 關於作者: |
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
生于荷兰海牙,当代重要作家,亦是诗人、旅行文学作家与艺术评论家。一生热爱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世界,被誉为“最具有世界公民意识和风度的作家”。
他被视作卡尔维诺与纳博科夫的同类,在文坛备受推崇,拜厄特称其为“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之一”。代表作:《仪式》《众灵日》《西班牙星光之路》《流浪者旅店》等。
自1950年代起,已出版五十余部作品,至今仍笔耕不辍。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德国联邦十字勋章、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西班牙福门托尔文学奖、飞马文学奖、荷兰语文学大奖、康斯坦丁·惠更斯文学奖、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等,并获得伦敦大学学院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近年来屡次入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
|
| 內容試閱:
|
阿图尔·达内在离书乐书店几步远时,发觉有个词卡在意识的夹层,而且已经被译成了母语。他的大脑识别出德语Geschichte(历史),旋即将它转换成荷兰语的geschiedenis。出于某种原因,荷语发音好像要祥和一些。他怀疑这与最后三个字母有关,尾缀nis,本意“窝”。这是个特别的词,它虽然短促,但与许多短词不同,听起来没有不恭不敬,反而教人安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藏储的地方,有人藏身,有人藏物。其他语言里没有这样的词。他加快脚步,希望能甩掉卡在意识中的Geschichte,但在这里,在这遍地历史的柏林,这样做没有用。“历史”在此地是难以忘记的。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脑中卡住过许多词。“卡住”这个表达无疑很准确:词一旦出现,便打死也不再动了。它们甚至还发出声音——因为每个词都自有发音,即便它自己不出声。有时,它们甚至似有回响。对语词敏感的人会发现,一旦将词从所属句链中拆下,它们就会变得认不出,甚至有点吓人,在它们身上流连、斟酌是危险的,现实世界可能会就此不知不觉地从脚下溜走。我之所以如此,说到底还是闲的,他想。但“有闲”恰恰是他的志向。他记得在一本旧教科书上读过一篇《爪哇人》:有个爪哇人,每赚到合二十五美分的薪资,就会找一棵棕榈树坐下,不花光最后一文钱,他绝不再干活。看来在久远的殖民时代,这点钱还可以称“笔”,还可以支撑好一阵子。但用最少的劳动换取勉强度日的钱,按教科书的说法却是一种陋习。阿图尔·达内读了却很受益。他自导自拍电视纪录片,遇到别人的片子有趣时,便自荐为摄影,每隔一段时间,如果缺了周转或有了兴致,他也会帮一个朋友开的公司拍广告。这种项目只要不经常做,还是蛮有意思的。项目终了,他便远离工作,无所用心一段日子。他曾有过妻子,也有过孩子,二人均死于空难。而今所剩只有每看一次就远一层的照片。茫茫十年。十年前的一个早晨他们坐飞机去马拉加(Málaga)后一去不归。他拍下那个画面,却再无机会看到。一个金发女子,她背上的幼儿。西佛尔机场,等待出关的队伍。其实儿子已不必再背。他喊她的名字,她转过身。记忆就此定格。他们遥遥相望,彼此呈九十度的角,长达一秒钟的时间。她抬起手,孩子也潦草地挥挥手。到达目的地时自会有另一个人替她拍摄抵达的影像,而所有影像又都会连同平房、泳池、大海的影像一起,消逝在吞噬两人的那坨巨大的焦黑之中。他走向队伍,将小型摄影机递到她手里。最后匆匆一眼,从此阴阳两隔。他将自己与记忆的碎片隔绝,拼图过于宏大,他没有复原的信心。他卖掉房子,将衣服、玩具送人,好像每件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都被污染过。他从此变成一个轻装旅者——只留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影机、一部手提电话、一只可接收世界各频段的收音机,外加几本书。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可以收电话留言,朋友的办公室可以收传真——他就这样与机器一起过日子。自在,却也不尽然是自由,因为有看不见的电缆将他与世界绑缚在一起。因为还有人声,有信息。他交际的人大多也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把自己的房子借给他们,同时也借住他们的房子。或者在便宜酒店和寄宿公寓一类的地方落脚。纽约,马德里,柏林。每一处在他看来都是一个“窝”。他的意识依然没有摆脱这个词。不仅没有摆脱这个词,也还没有摆脱那两个、有或没有这个尾缀的长长的名词。
“德国怎么把你迷成这样了?”他的荷兰朋友常这样问。好像他这是一种毛病。
他想出一个大家常用的答案来搪塞:“我喜欢在德国生活。德国人很严肃。”
“好吧。”荷兰朋友通常会给出诸如此类的回应。但一个荷兰人给出这样貌似肯定的答案,其实要表达的却是怀疑。这种社交暗号很难对外国人解释清楚,即使这个外国人懂荷兰语。
上述种种思虑流经大脑的时间里,他来到克内泽贝克大街与蒙森大街交会处的酒品店。一般他都在这里驻足,决定继续往前还是原路返回。他停下来,看看马路对面汽车店里的新车,又看看选帝侯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交通,最后在烟酒店的香槟广告牌上看了看自己。镜子有一种讨厌的热忱——就算你不想,它也要把你的影像反馈给你。今天他已经见过自己一次了。所不同的是,现在的他穿着衣服,有了掩护。他自己是很了解自己的,但不知别人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他?“全都看得见,但全都看不穿。”埃尔娜曾说。她突然在蒙森大街拐角浮现,这令他不知如何面对。
“你真这么想?”
“瞎说是狗。”只有埃尔娜会说这种话。于是除了埃尔娜,他还要安放她的狗。已经开始下雪。他通过镜像看见雪粉落在大衣上,这很好,这样自己就不那么像广告人物了。
“不要发傻。”这话也只有埃尔娜会对他说。关于他像广告的事,他们已经讨论过许多次。
“不想像广告就去买点别的衣服啊。别总穿阿玛尼。”
“这不是阿玛尼。”
“嗯,但这很像阿玛尼。”
“问题就在这里。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大减价的时候买的,跟土一样便宜。”
“衣服穿在你身上都好看的。”
“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我像广告一样,假假的。”
“你只是自我厌恶罢了。很多男人到了中年都这样。”
“不,这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觉得自己看起来表里不一。”
“你是说其实你也有很多想法,但是因为你不响,所以我们不知道?”
“差不多。”
“那你要不要换个发型?说不定是你头发太多,遮盖了你的想法?”
埃尔娜是他老朋友里的老朋友。也是他与妻子相识的原因。还是他唯一与之聊起洛劳弗耶的人。其他男人交际男人。他虽也交际男人,但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是埃尔娜。
“都不知道你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
他有时会在午夜从地球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给她打电话。她总是在家。男人进入她的生活,又离开她的生活,与她一起生活,对他感到妒忌。“那个达内,装什么大师?拍几个破纪录片就以为自己是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了?”这样的牢骚通常会导致关系的结束。但她从每一个男人那里都得到一点东西,加在一起,一共三个孩子,每一个长得都随她。
“谁让你总跟一些庸碌之辈交往呢。全球这么大的基因池让你挑,你却总是挑些废物。真还不如跟我在一起。”
“谁叫你是我的禁果啦。”
“这是我们享受友谊之爱所付出的代价。”
“完全正确。”
他转身否决了选帝侯大街,向萨维尼广场走去。而这同时意味着他将再次经过书乐书店。nis在荷兰语里真是一个百搭的尾缀。什么词它都能不知不觉地插一脚:bekommernis、gebeurtenis、belijdenis、besnijdenis——关切、事件、信条、割礼。雪越下越疾。可能因为总与镜头打交道,他时常关注自己走路的样子,这与其说是虚荣,不如说出于好奇。好奇里还掺杂一些……呃,这个话题他也跟埃尔娜聊过。
“你干吗不干脆说出来?”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
“胡说。你明明有。连我都有,你就更有了。你只是不想说。”
“好吧,是什么词?”
“是惶恐。是惊叹。”
他喜欢“惊叹”。
他在臆想中用一个镜头悉数收入克内泽贝克大街的白雪皑皑、楼宇的巍然与弓腰驼背、顶风冒雪的寥寥行人。而他是其中一人。这个画面表现了人生某特定时间呈现的偶发的画面。那个行走在街中、经过书乐书店又经过画廊的孤独人影,就是你。为何这样轻如鸿毛的日常在某一时间、某个神奇的片刻,会突然变得重如巨山?它难道不该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许在你心里,一直都住着一个永远好奇的少年。
“这跟少不少年没有关系。有些人一辈子都庸庸碌碌,从来不动脑子。其实不解与惊叹才是一切的开端。”
“比如什么的开端?”
“比如艺术、宗教、哲学。没想到吧,我偶尔也读书。”
在转修文学前,埃尔娜学过几年哲学。
即将拐进萨维尼广场时,一阵突如其来的小雪使他雀跃。它令大陆性气候的特征愈发明显。这是他喜欢柏林的另一个理由:自己正处在直达俄罗斯心脏的广袤平原上。柏林、华沙、莫斯科,不过是居间的驿站。
他没戴手套,因此手指冰凉。在与埃尔娜的同一次对话里,他就手指也发表过一些看法。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手指,阿图尔。”
“没错,同时也是夹取物品的工具。你看。”
他拿起一支笔,转了两圈。
“很精巧吧?人总为机械而惊叹不已,对自己却司空见惯。人看见机械拿笔就觉得非同小可,自己每天都做这个动作却视为理所当然。人是血肉铸就的机械——这才真非同小可。这比喻真精彩!总之,人这种机械无所不能,甚至能自我复制。那眼睛!又是镜头,又是屏幕。兼具拍摄与显示两大功能。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但反正如果我们不是内含计算机,就是计算机本机,有着与计算机一样的电子指令、化学反应,凡你想到的都有。”
“计算机没有化学反应。”
“只是现在没有。而且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中世纪人,是那些根本不知道电子技术、神经科学的人——不,甚至是更远以前的那些尼安德特人和上古原始人——就身体构造而言,他们与我们是同样精密的机械。虽然他们自己意想不到,但他们的发声设备与我们的同样先进,也有音箱,也有扩音器……”
“哎呀,阿图尔,差不多得了。”
“我说过,我心里还有个少年。还为着许多事惊叹。”
“你说的惊叹可不是指这个吧。”
“不是。”
我说的惊叹,他原想说,是目睹闪电第一次照亮原野的惶恐,是面对人们视之泰然、在我的年纪也早应习以为常的事物时依旧感到奇异的战栗。
他经过朋友菲利普开的小饭馆。菲利普不知道他在柏林。他随性来去,从不向任何人透露行踪。
康德大街的转角亮着红灯。他左顾右盼,未见行车,很想过马路,但还是站住了,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同时处理着两条相反的指令:在某种令人费解的神经波动下,一条腿留在原地,另一条却想要迈出。他透过雪幕与马路对面安静等待的人群相望。荷兰人与德国人的区别在这一刻昭然若揭。在阿姆斯特丹亮着红灯的路口,如果你看不到车却不过马路,你就是白痴;在这里,情况正相反。德国人会毫不留情地啧你,指摘你是“不知死活的疯子”。
他问过维克托,一个现居柏林的荷兰雕塑家,如果视野里没有车,他会不会过马路。
“会啊,除非有儿童在场。那我会树立良好榜样。”
他决定用这“进退维谷”的荒诞时刻来进行一项他称为“即时冥想”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任何一个有自我要求的路骑者都不会戴盔,更不会在红灯前停车,绝对不会沿正确方向使用单行道。荷兰人喜欢依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新教的反叛精神与无政府主义在这里调和出了一种积习难改的混乱倾向。上次回国时,他发现就连机动车和公交车都开始无视红绿灯了。
“你德化得这么严重了呀?规矩就是规矩了?从此‘秩序’第一了?下次坐地铁时,别忘了仔细听听他们喊的‘上车请注意!关门请当心!!’。不过绝对服从使他们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可都是知道的。”
“荷兰人讨厌规训。”“德国人喜欢纪律。”这类偏见似乎永无消除之日。
“但阿姆斯特丹的马路确实危险呀。”
“话是这么说,但你想想德国人在高速上的车速吧。那真叫凶神恶煞、怒火中烧。”
绿灯亮了。马路对面的六个雪影同时迈步。诚然,人们不该过度泛化,但国民性这种东西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来自历史。”埃尔娜说。
历史是宿命、机缘与人为设计的总合,因此尤其令他着迷。三个元素加在一起,引发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事件又引发另一连串事件,每一串事件的发生或被认为是注定的,或被认为是随机的,或被认为是遵循了某种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神秘法则;一切事件累积至今,其背后的因缘已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他想要不要去“墨鼠”读报。至少里面不会太冷。虽然顾客他一个也不认识,但每张脸却仿佛都见过,每个人也都跟他一样闲,虽然没有人像他一样长得像平面广告。店里临街是一大块平板玻璃墙,墙与吧台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摆了几张桌子。如今店里再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坐着——外界如此精彩,谁还愿意面向吧台?从人行道上看,店内是一排凝视户外的人,沉浸在缓慢滞重、只有小口啜饮啤酒才能忍受的长时间思考里。
他的脸冻僵了,但他这几天正好在享受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就像有人喜欢在暴雨中跋涉斯希蒙尼克岛(Schiermonnikoog),有人偏要在酷暑中徒步比利牛斯山,前往某个为人遗弃的孤村一样。某些路跑者咬牙切齿的表情也有类似的意味:一种基督徒向各各他朝圣时对自己惨状的毫无顾忌的公开展示。但路跑不适合他;路跑会干扰他的思考节律,或者说“脑部活动节律”,他在十五六岁时决定将这种脑部活动权且称为“思考”,虽然它并不一定就是思考。为了这种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他必须潜心,必须隔绝外界。虽然有点可笑,但这已成习惯。
起初他只能在特定场所进行这项活动;现在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只要不必说话。对此,洛劳弗耶是理解的。他们曾一起散步数小时而不发一言。这不是事先商量的结果;她天然地懂得这对他工作的重要性。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但每次即时冥想后他似乎都能不仅从概念上,而且从细节上回忆起自己的电影构思。回忆——确实是“回忆”。 他所拍的一切都似曾相识,仿佛来自回忆,无论是镜头角度、打光,还是画面推进。就连那几部他带学生一起拍的短片,也都是这样拍出来的,虽然这令与他一起工作的人深感绝望。他总是还一点想法都没有就开始拍,拼着一死,在帐篷上空悬吊腾挪,惊险刺激到令人忘了呼吸,最后落地。这样拍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一开始对金主的承诺风马牛不相及,但只要东西好,金主就会原谅他。怎样描述这个过程呢?首先必须“空无”—没有什么词比它更达意。拍摄当天必须一片空白。故此他自己也必须一片空白。散步时他觉得自己可以放空,好像已经变得透明或失踪,不再属于这个别人的世界,甚至可以说不再存在。散步后,他从来无法精确还原自己的所思所想,虽然用“思想”来描述那模糊的记忆,那混乱的影像与碎片化的语词,似乎言过其实。整个过程很像一幅他看过却记不起名字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一个由碎片组成的女人,攀登一架没有尽头的阶梯。她还没有攀得太高,楼梯的顶端深入云霄。虽然人物肢体破碎,某些部分甚至有所缺失,你还是能看出她是个女人。事实上,这幅画如果定睛看久了,甚至有点恐怖。雾霭洞穿她的身体、她的眼睛、她的胸,以及原本应该是她性器的部位。好像某种不断变形的软体动物,侵入她的体内——现阶段还看不出是什么——有一天当时机成熟,会将她改造成一副他现在还预判不出的模样。
在歌德大街,风刮得他难以呼吸。蒙森、康德、歌德——这一街区总有良友相伴。他经过维克托常去的土耳其咖啡店,未见维克托在内。维克托曾为(依照他自己的说法)“深深潜入德国的灵魂”而与二战受害者和迫害者都聊过天,以他们为蓝本写了一本书。书中隐去人物姓名,用一系列并不胡乱煽情的短篇打动了读者。会吸引阿图尔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都“扮演着多重角色”;如果此人的各个角色间还相互矛盾,他就更为其所吸引。维克托或许其貌不扬,内心却几乎包含了一整个剧的人物:画家,登山爱好者,静看人类生活的观察者,沉迷战与血的瓦格纳派诗人,雕塑家,草草几笔便能传神、每幅画的标题直至今天都还在影射那场早已结束的战争的艺术家。柏林与二战是维克托的游猎场。他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谈起时则只作笑谈,将它们归因于儿时在德据荷兰的经历。“小时候看大兵,感觉兵真的很大很大”。而且因为当时与父母住在德军基地附近,他见过的大兵又着实很多很多。他的衣着风格令人想起战前的音乐剧笑星——花格夹克、丝质领巾——两撇大卫·尼文的小胡子像两道眉毛一左一右挑起,仿佛在用自己的外貌说明战争不该发生、1930年代原该永续。
与维克托在柏林街头的散步常常这样开始:“你看见那些弹孔了吗?”甫一到街头,他就立即化身城市本市,把城市的记忆当成自己的记忆,掏心掏肺地给你讲——政治谋杀、全境逮捕、焚书、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具体淹死在兰德韦尔运河的哪一段、1945年苏联向西方推进的终点。他像照本宣科一样读出这座城市与吞噬这座城市的历史——盖世太保的刑讯室,曾经起降希特勒的飞机、如今已成荒芜的空地,所有内容都被源源不断地诵出,好像念经。阿图尔曾经提议拍一部讲瓦尔特·本雅明的纪录片,以他提出的“行走的记忆”为题。城市街头游荡的本雅明由维克托来演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世上还有人会踩着记忆行走,这个人肯定是维克托。然而荷兰电视台对本雅明毫无兴趣。他还记得制片人的样子:一个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硕士毕业生,头上还密布着马克思主义与天主教的阴云—— 一个盘踞丹麦某行将干涸的造梦工厂内、某潮湿发霉的办公室中的陈腐中年人,身边流水般出入着包裹在精心晒黑的皮囊里、拿捏着似有喉癌的嗓子说话的名流过客。阿图尔是幸运的,由于常常出国,他不需要去记忆这些名流的名字,虽然脸都是熟的。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脑子,由两个极端分裂的部分组成,”制片人说(他本来想说“灵魂”),“具体来说,是行动的部分,与反思的部分。但反思不会让片子得高分呐。”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破碎与天主教徒耽于逐利的腐朽—— 一个人兼具二者很难不堕落—使面前这位制片人将自己的灵魂之宝押给了能收获最多养老金的节目。
“你那个危地马拉工会官员神秘失踪的片子,就堪称一流。还有那个里约热内卢警察射杀儿童的片子,也在渥太华获了奖。那种片子才是我们要的片子。虽然成本高,但都收得回来。德国三台买去播了,几个瑞典频道也都买了下来……但是瓦尔特·本雅明!我以前倒是能背好几篇他的东西……”
阿图尔眼前出现一片大理石铺就的瓷砖地,地上陈列着七八具儿童尸体,尸体的脚从灰布下伸出,脚踝上戴着标签,标签上写着尸体的名字。这些标签正与尸体一同腐烂,也终将与尸体一同消失;这些名字大可以相互交换也无损于尸体本身。
“可怜的本雅明,”制片人继续道,“命运多么悲惨。当初他从比利牛斯山出逃碰到西班牙边检,威胁把所有偷渡者解回给盖世太保,如果不是他丧失了希望,或许能活下来也说不定。西班牙人当然是贪得无厌的法西斯,但他们终归没有把自己的犹太人交出去给希特勒。可他呢?竟然自杀了。虽然不知道原因,但自杀这种事我一向不能容忍。他只要再多等一小会儿,说不定就能像其他人一样穿越国边境了。想象一下,本雅明要是到了美国,碰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三个人联起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