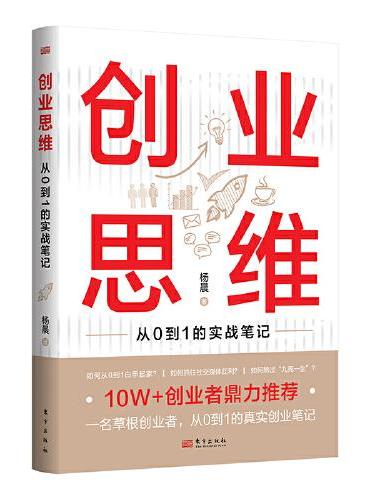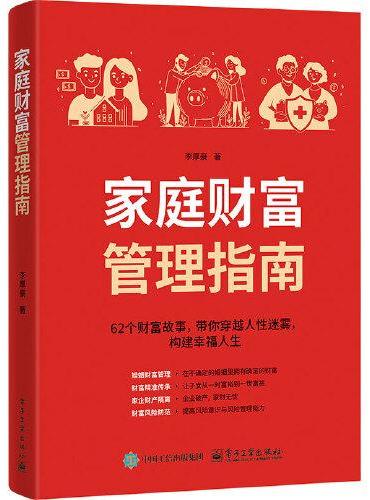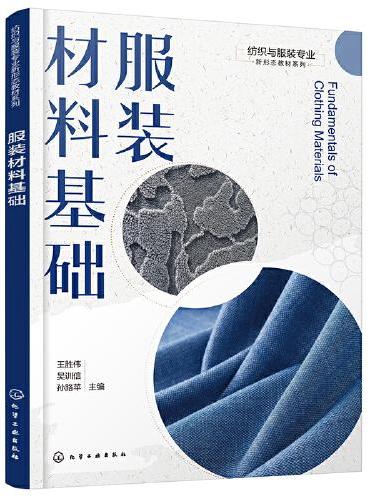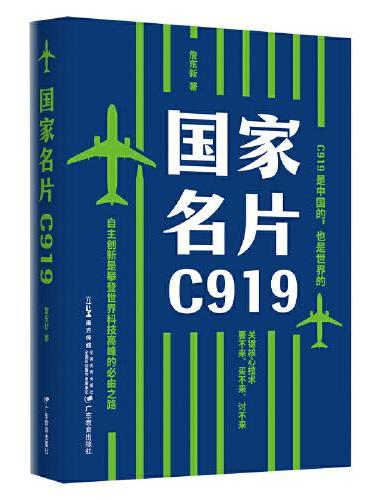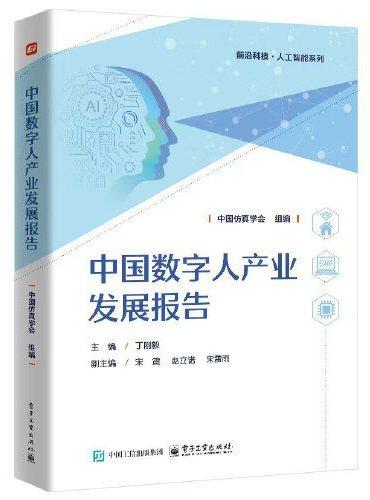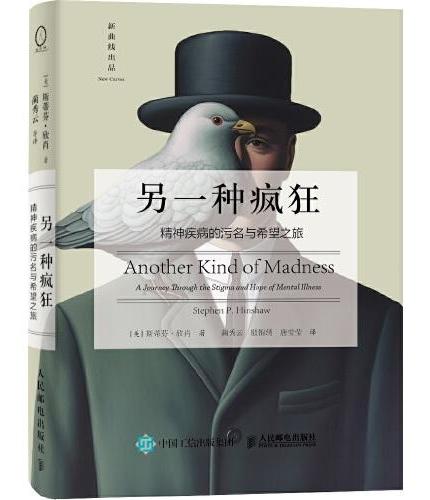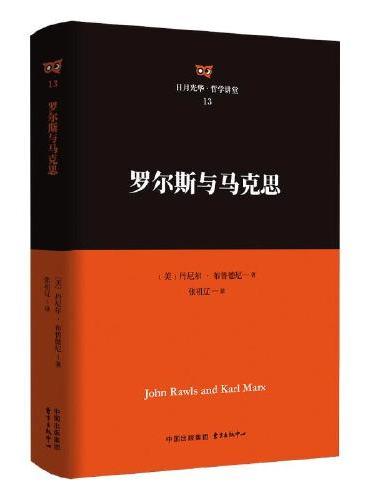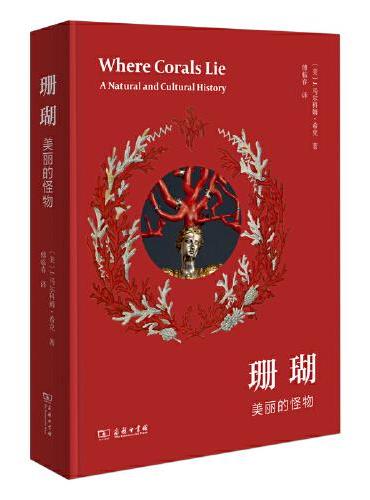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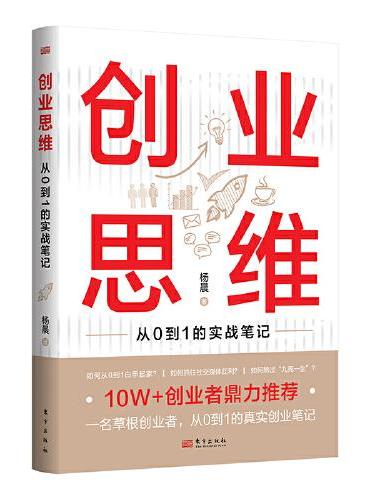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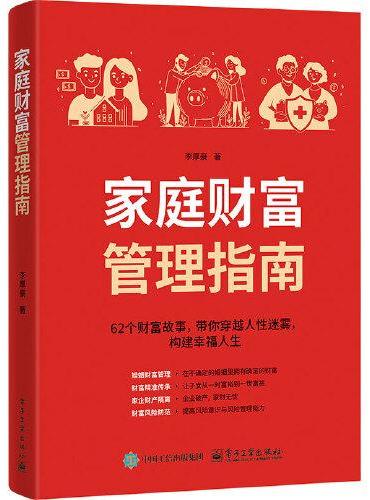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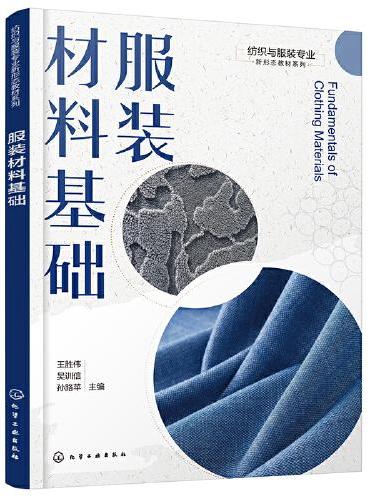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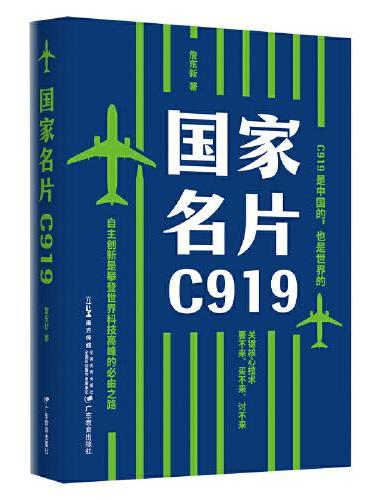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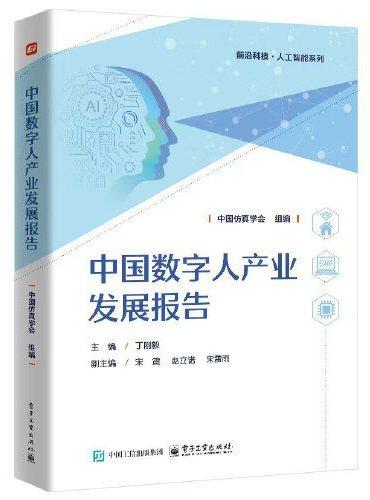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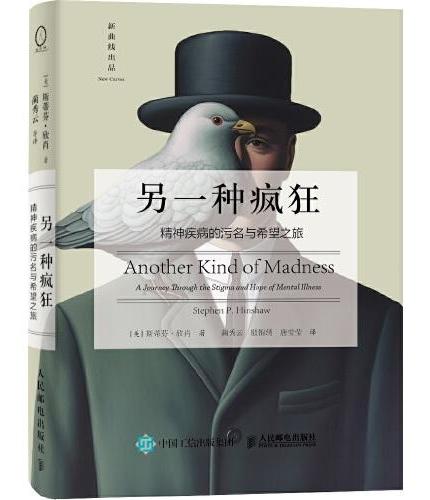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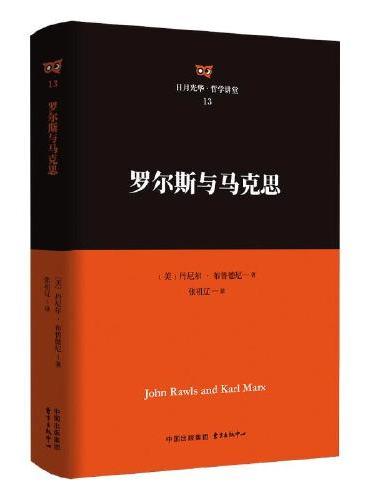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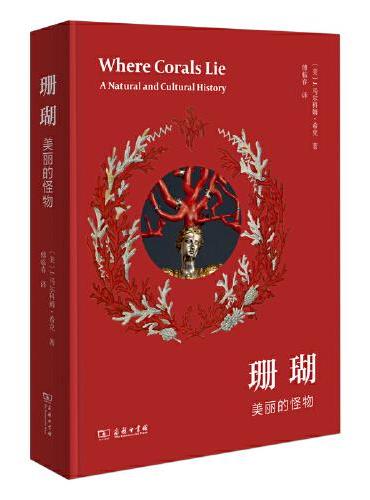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HK$
126.5
|
| 編輯推薦: |
著名艺术家、中央美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2020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获得者杨先让的彩绘随笔集,90幅作品与淳朴、典雅的文字相得益彰,对其独树一帜的彩绘艺术创作进行整体记录与全面呈现;描绘自然风景、城乡风貌、故土风致、域外风情,记叙自身经历,反思艺术与时代,以古典与现代的叠加方式展现一代老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对家国的深深眷恋;作者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家,其作品与记叙具有独特的当代艺术史料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中国最美的书”获奖者鲁明静精心设计,兼具阅读与收藏的价值。
编辑推荐
《光与色:我的彩绘之路》是对杨先让彩绘创作历程进行整体记录与全面呈现的彩绘随笔集。90幅作品描绘自然、小城、乡村、故土,域外,间以回望自身经历,反思艺术与时代,从画面到文字都蕴含着浓郁的故国之思。作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家,也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画家,其彩绘作品独树一帜,随笔呈现其艺术道路、人生阅历,反映社会风尚,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
| 內容簡介: |
|
“彩绘”是杨先让采取西方绘画写实构图及光色处理,以中国纸墨的渲染,再加入版画黑、白线条效果的艺术创作。本书是一部对杨先让彩绘创作历程进行整体记录与全面呈现的彩绘随笔集,按作品内容分为六部分:一、银杏和梨渊,温暖和记忆在心间涌动;二、乡愁倚在他乡的窗前,诉说着绵绵不绝的思念;三、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四、山河辽阔,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五、异域风光别样好;六、我对花的爱,是我爱世界,世界也爱我。这些彩绘多创作于作者退休后侨居海外之时,描绘自然与风景,小城、乡村、故土风貌、域外风情,间以文字记录对往事的回忆,回望自身经历,也反思艺术与时代。其中隐藏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对故乡与祖国的思念之情,以古典与现代的叠加方式一一呈现。
|
| 關於作者: |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939年随家人迁居朝鲜,1944年回国求学,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
曾获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中国文联第11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第14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第16届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文旅部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等国内外荣誉,作品被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和个人收藏。曾出版《刀与木:我的版画之路》《黄河十四走》《杨先让文集》《徐悲鸿》《中国乡土艺术》《海外漫纪》《艺苑随笔》等著作。
|
| 目錄:
|
银杏和梨渊,
温暖和记忆在心间涌动/ 5? 乡愁倚在他乡的窗前,
诉说着绵绵不绝的思念/ 19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39
山河辽阔,
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 61
异域风光别样好/ 83
我对花的爱,
是我爱世界,世界也爱我/ 101? 附录 杨先让艺术简历/ 156
|
| 內容試閱:
|
自 序
我的彩绘历程
我的版画集,江丰和李桦为我写了序言,而我的彩绘谁来为我写个序言呢?想了想还是我自己先写写吧。
事情得从1948年我考入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说起。国立北平艺专是徐悲鸿领导的严格遵循写实主义教育宗旨的学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改为中央美术学院。从1948年至1952年,四年里,我是唱歌、跳舞、扭秧歌、演戏的打头人,却也未误了绘画技能的锻炼。1948年至1949年,由孙宗慰先生启蒙的素描课程,使我“第一口奶”吃得扎实,那年年底预科成绩评选,我的图案设计获奖了。二年级由蒋兆和、李瑞年先生教授素描课,我的成绩优秀,三年级由冯法祀先生负责素描、油画课,同时带我们班去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合作社实习体验生活,受益匪浅。1952年毕业班,由彦涵先生带领我们去为治理淮河而兴修的河南白沙水库工地收集素材体验生活,回校进行毕业创作。当时的绘画科毕业创作都是创作年画或连环画,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是创作的方向。我们班在彦涵先生指导下,要完成歌颂治淮水利战线上的英雄事迹和耿长锁劳动模范事迹的两套连环画、两套画册,主要构线造型全由我主笔。后来,这些作品被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优秀作品出版发行了。就是说,我在中央美院四年里,打下了较好的写实绘画技能的基础。毕业分配到了新成立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画册图片编辑室工作,遇上了好领导邹雅、安靖和王角。六年中,我不仅大开眼界,还不断受到重用。新华社举办第一期摄影培训班,让我去学习,掌握彩色摄影技术;唯一一个留学苏联名额给了我,后来因为父亲在仁川、哥哥在美国而作废。社长邵宇带我游南方两个月,最后我被调到沃渣领导的创作室,与徐燕荪、王叔晖、刘继卣、林楷、任率英等在一起工作。
我没有辜负出版社对我的关爱:为出版“泥人张”画册及张景祜创作的《惜春作画》不遗余力拍彩照,之后为《艺用人体解剖学》的摄影出版而努力,也为出版苏联领袖别尔乌辛的肖像救过急。我先后创作出版了近十幅宣传画、两幅年画、一本连环画和四五套组画,后来搞起了木刻版画,第一、二、三、四幅作品皆出版了独幅画,还有套色木刻《延安组画》、版画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奖,后来成了“版画家”。—总之,我的成绩是突出的。
“反右”运动后,我和妻张平良丢下八个月的小女儿杨阳,与古元、刘继卣、陈兴华、王角等下放河北遵化县整一年。其间调我和古元到县里去完成一套四扇屏,反映“大跃进”景象,古元画春、冬,我画夏、秋,作品完成,被镶框挂在县委办公室。
1958年年底,古元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我被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点名要到文化部研究室,负责新成立的《新文化报》美编,画画速写、插图,写点小评论文章。近两年内,我创作了几幅套色木刻。《公社突击队》被力群赞扬谓“自行车进入木刻版画首例”,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还创作了一幅套色木刻《毛主席在工地上》,当时美术界少见以主席形象进入艺术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当时正遇“反右倾”运动,我因为“反大跃进,同情江丰右派集团”而被批斗。之后,这幅画被我压在箱底,没有发表。
李琦1962年创作了一幅水墨画《毛主席走遍全国》,轰动一时,而我1959年创作的这幅画被我忘记了整整四十六年。2005年,它被我女婿马路发现,方被拿出展览了。
1960年年底,我被调回中央美术学院。古元说:“你不来版画系,还能到哪里?”从此就在版画系任教了。后来我体会到,自己在社会上经历了一圈,比一毕业就留校任教者更有优势。
在此之前,我到生活中去写生收集创作素材,都是背了大油画箱。有两件事教训了我:
一、1956年,我到陕北去完成一套反映防治水土流失的组画。我背了大油画箱,当然也有水彩、速写本等。我画了一批小油画,钉在绥德县招待所房间的墙上晾干,并嘱咐服务员帮我看好。未料当我再次下乡住了两天后,回来一看,墙上的画全没有了。我问服务员,他说召开三级干部会,没想到墙上的画都被农村来的干部取走了。这能上哪里去追回呀,急得我直叫娘。看来下乡画油画太不方便。
二、1962年,版画系系主任李桦先生规定教员进修,要观摩,我守规矩去努力完成。记得观摩时,我准备了两幅套色木刻作品,一幅油画肖像以及临摹“八十七神仙”线勾,油画肖像我自认为属于我的精品,记得靳尚谊也赞赏。未料,李桦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以后不要画油画!”
我懂了,李桦视版画为首要。他曾主张“素描要版画素描,色彩要版画色彩”。他怕我对版画不专,因此让我断了画油画的念头。
从此,我再下乡画写生,就用彩墨了,轻便,我也熟练了。
我这个人,感性多于理性。优点,工作认真;缺点,不安分。跟着喜欢走,性情太活。
既然选择了美术这个行当,而美术的天地广阔,让我迷恋的东西不少。
首先说写实。我学了点写实的技能,知道其中有优劣雅俗之分,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在纷纷攘攘中,我还是钟情于它,也知道与众人拉开点距离不易,但我愿去追求。
油画,光色笔触造型迷人,我也曾尝试过。2016年,我在一画廊办了个小型习作展,有人评论我的油画精彩,还有人为我惋惜未坚持画油画而搞了木刻(是好意,因为油画值钱而版画不值钱,可能是这个意思,我只能一笑)。
中国画的水墨,变化莫测,工与写,诱人千古。我临摹,我尝试磨炼,其乐无穷,愿掌握它,去实践,企图能画出一个自我来,达到一点创新,获得一丝新鲜的味道。
书法,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特殊天地,我绝不敢梦求自己是个书法家,绝不。我只求能欣赏其中的美感,自己能将名字题得不难看而已。
木刻版画,是我鬼使神差地走到它那黑白、刀法变化的艺术魅力之中了。以刀代笔向木直干的快感,刀刻木的声声节奏,亲手印刷的喜悦,是一种特殊艺术制作过程的享受,令我入迷。
遇上了社会的迭革,我忽然对民艺面临消失产生了紧迫感,以及爱惜之情和去抢救、去继承、去研究的责任,花时间精力为之呐喊、著作,无怨无悔。
年迈退休后,脑子里一些零碎知识慢慢串联了起来,形成一种论点,有写出来、讲出来的欲望,加上身处海外,又属职业本能,也是文化交流,何乐而不为?
我本来就没有当一名大画家的思想,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工作者,起个基石作用足矣。不过,我愿意在绘画艺术各领域,去品尝各自特有的艺术美感和趣味。
1983年,我到美国访问一年多,临走之前要办个画展。拿什么展现呢,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出来的,虽然油画也画过,但更多是画水粉,画工笔作宣传画、年画,后来搞起了木刻版画,看来都沾一点边,又都不够精到。在人家美国,油画我是绝对拿不出手的—也尝试画了几幅,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画水墨,又不是我的本行,虽然也抹几笔山水花鸟,但跳不出老套子。版画我不想展。在美国,木刻版画少有人去搞,中国木刻版画反而有些新鲜了。可是我的版画大都反映现实题材,又不是新作,不合适(后来我的版画在休斯敦美术馆、圣地亚哥人类学博物馆以及路易斯大学展出过)。
又想搞点新鲜,取悦于人家,想来想去还是在我的写实能力和中国画材料上琢磨吧。
采取西方绘画写实构图及光色处理,以中国纸墨的渲染,再加入点版画黑、白线条效果,有点新鲜,西方人能接受。
当然,艺术作品总要与其他人的作品拉开点距离,又不可能有本领将距离拉得太大。因为距离的一点点拉开,那是一个艺术家一辈子的功夫,谈何容易。
我称自己这种不中不西四不像的画为“彩绘”,其实外文翻译还是“水墨”“水彩”之意。
在美国,虽然充满了五花八门的现代流派艺术,但写实主义绝对有它永恒的魅力,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更是牢固不变的。虽然有人用摄影的出现来反对写实的存在,事实证明摄影永远取代不了写实绘画艺术。写实主义,那是一个无限艺术创造的天地,工写兼备,艺术风格千变万化,百花争艳。当年徐悲鸿告诫我们,避开那些油滑俗气的,要在高雅处立,才能在宽阔处行。
何况艺术离不开作者的真情实感,感情的浓淡将是艺术创造的第一要素。
在以徐悲鸿为首的师长们中间,能中能西、能工能写者大有人在,是楷模。
我是学西画出身,版画也是西方的创作版画。出于喜欢,我也曾去荣宝斋学过中国传统雕版技术,而对中国绘画笔墨也热衷,能画两笔山水花鸟至关重要。中国社会讲应酬,用油画、版画相赠不太实际,你是画家,因此求你一纸“墨宝”是人之常情。
山东人更热情,回家乡受到接待,最后求你一幅笔墨,这也促使我必须练几手。我生性爱花,就画“四君子”、牡丹、荷花、令箭水仙……慢慢形成我的特点。记得“文革”后,我们美院教师一次画展,我拿出了两幅中国花卉画。河北美术出版社来选作品,用于挂历出版,我的一幅令箭荷花被选去做挂历,发表了。1980年左右,我们美院教师作品赴香港办展,我的一幅彩绘,副院长艾中信惊问何人所作,后来此画在香港被盗了。
还有一次美院教师绘画展,中国美术馆选了三幅画希望收藏,其中就有我的一幅葵花彩绘。
而另一次谷牧副总理帮我调靳之林、叶毓中来北京,他点名要了我一幅彩绘《瓜叶菊》。
中国是亲情、礼仪浓郁之邦,生活中婚丧嫁娶应酬频繁,会画会写两笔就占了优势。写个扇面,画个册页,书写两句诗词,画幅有寓意的山水花卉,裱个片儿或轴儿相赠,都显得雅致,这对我是个动力,也是个乐子。
何况社会上也提倡一专多能,也是一个技不压身的事。比如在美国,我的一幅彩绘风景被一对美国夫妇收藏,彩绘是要有玻璃镶框的,他们拿回家挂墙上反光,只好向我提出可否将此画改画一幅油画,价格他们愿增加。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重画了一幅增添了光色表现力效果的油画作品。
休斯敦美术馆东方部负责人奎士汀提出希望我写大幅《兰亭序》。我用四幅六尺宣,找了《古文观止》上的《兰亭序》一文,一字不差地完成了行书。接着,做建筑师的儿子要求我在布面上书写“陋室铭”,每字一尺见方,我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香港回归,休斯敦电视台向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提出,希望找一位书法家帮忙写“香港回归”四个大字,总领事馆找到了我,而我不负所望,顺利完成了那四个大字。
1981年,中央美院与广州美院要共同为广州白天鹅宾馆画一批壁画,我们美院分了十二幅壁画,要求绘画内容是祖国名胜风景。我分了一幅表现敦煌秋色的,可以用油画或丙烯完成,后来还出版了台历。我自认这批作品中《敦煌秋色》最好,总之,身上有点技能,能为社会完成点事儿是个乐事。
在美院教学,我主张教员应多些知识和技术能量。搞版画的人,到生活中去体验和收集素材,总不能带上木板和刻刀,你首先应该是个画家。几十年来,我练熟了对宣纸笔墨的掌握,可以说得心应手,当然,画得好坏是另一回事儿。
我画宣传画组画,敢用水墨色彩在生宣纸完成,这是少有的情况,而我敢我能,并且很自然,不勉强,画得不错,够出版水平。
2017年,在江苏宜兴参加纪念徐悲鸿的活动。徐悲鸿艺术馆当时正展览几位西班牙写实主义油画家作品,我看了,很欣赏,来不及与那几位画家交往。
在回北京的前夜,我主动要求给傅建龙馆长画一幅四尺宣花卉相赠。我想悄悄画完,不要张扬,可还是围观了几位,其中就有西班牙画家。我不理睬,只顾低头作画。我画水仙、石头、梅花,题“春讯”及落款、盖章,有半个多小时。未料一位画家突然过来抓住我的手,说他感动得要哭了,并告诉我他们去北京会到中央美院访问。我未当回事,因为我这两下子,在中国画界能算什么,不新鲜,他们洋人会逢场作戏吧。
过了不久,我女婿马路(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在一次晚饭时说,他接待了几位西班牙画家,说在宜兴时见到我作画,至今感动得很。—说这些,还是那个意思,技不压身,一专多能有点优势。当然,也有人只专一技,不占他行。这是性格和选择的道路不同所致,各有各的乐趣,不必强求一致。
1977年“文革”刚过去。北京举办全国工业大展,负责人石峰带领工作人员到中国美术馆正举办的全国美展上去选作品,石峰对我说:“我们跑遍几层楼,唯一选中的就是你的大幅木刻版画《会师大庆》。”为此调我去放大一幅比丈二匹还大的中国水墨画。我完成了,开幕式上获得谷牧、余秋里两位副总理赞扬,此画后来被谷牧收藏。最近竟拍卖了一百余万元。
爱好所驱,我临摹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永泰公主墓壁画、山西晋祠宋代侍女群像、八十七神仙图、陈老莲和任熊的人物,也临隶书,是一种乐趣,也是丰富我在艺术创作中的多样性补养。
彩绘是我对木刻版画洗手不干后(因为版画对我,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在绘画创作上顺理成章的一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不再进行人物情节艺术创作的蜕变。彩绘,更注重对美、对情感的追求,以景以花卉为主体。
尤其在海外,我更多的是借景叙情。画乡情、画江南小景、画湘贵系列、画小街小巷、画宅门深院,画北方乡间将消失的门楼、画乡间家园、画小城春秋、画小城城门楼、画长城、画水乡、画家门老宅、画渡口牧归,也画秋后的残荷以及园外的景色、金色的池塘、费城市中心(曼果老板说:“这是我见过画费城最好的一幅风景画。”1983年)。
可以说,我画这些彩绘时,篇幅大概一致,不大不小。架上画,充满了我的感情,它是我晚年在艺术道路上心中的歌。
1998年,我妹妹杨学勤(西安美术学院美学理论教授)来美国访问,在休斯敦“上尚艺苑”看到我的彩绘画展,她惊讶,为此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美南新闻》副刊上,从文字上,我看到一股知音之真情。
1990年,台湾“老爷画廊”老板杨金龙一定要收藏我和妻张平良的一些彩绘,199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我俩的彩绘集。
2010年,广东美术馆要为我举办木刻版画展,目的是要收藏我三十幅版画作品,同时展出了三十八幅彩绘作品。广州美术学院老同学郭绍刚、袁浩、张文、王丽莎、郑爽,还有老朋友郭兰英看了,都感觉我的彩绘新鲜,有生命力。
2021年春,我整九十周岁,中国美术馆可能为我举办个展览,彩绘一定会展出,我等待大家的评论。因为我的彩绘还未在北京完整地展出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为我的彩绘出本画册,前言就用我妹妹杨学勤的那篇,是一个纪念。她2001年七十岁时患癌症去世了,她比我小一岁,仁川华侨小学时与我同班级,不少人误认为我俩是双胞胎。
最后,我再重复说一遍: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工作者,起个基石的作用。好好做人,努力干活,深知“有你一个不显多,少你一个不显少”的真理。
杨先让
2021年5月于京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