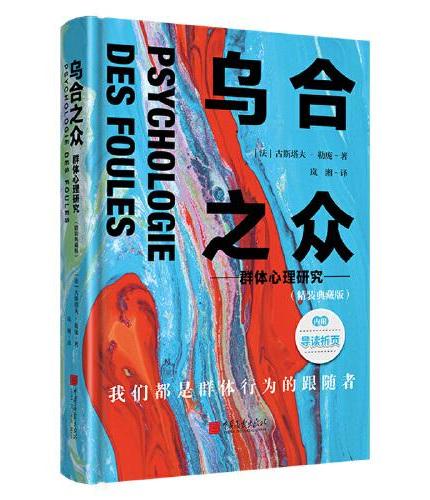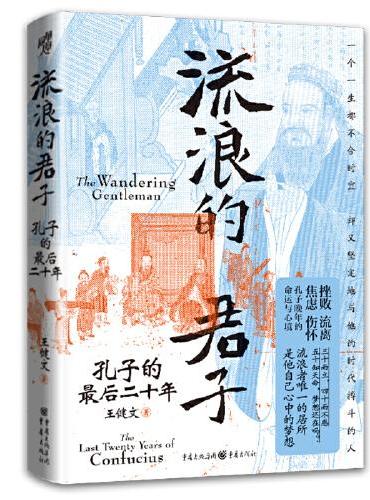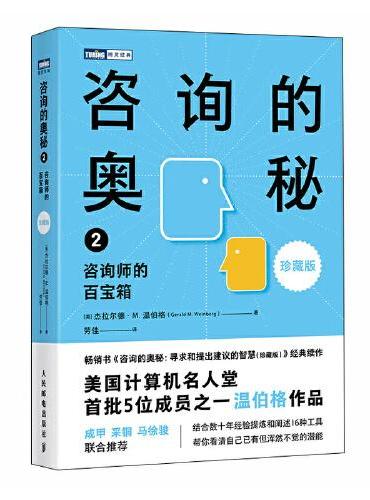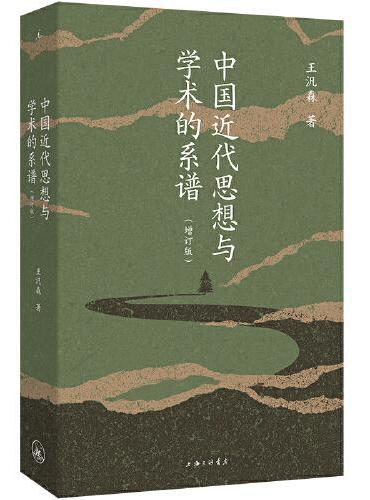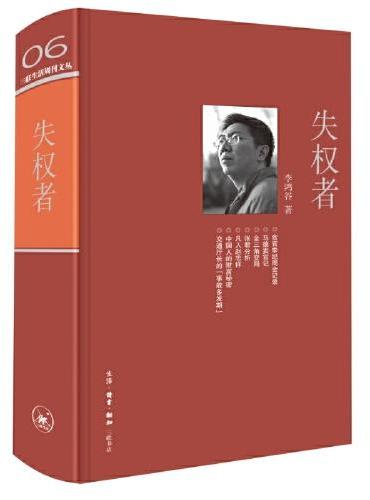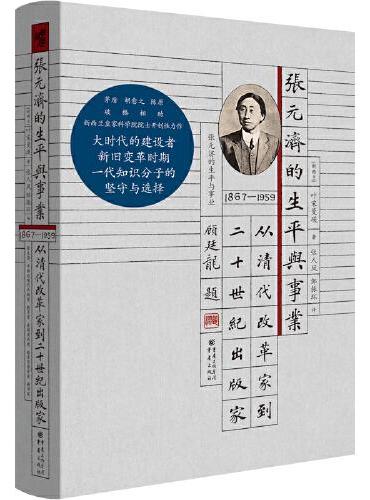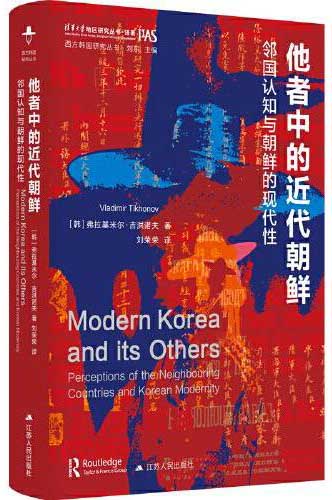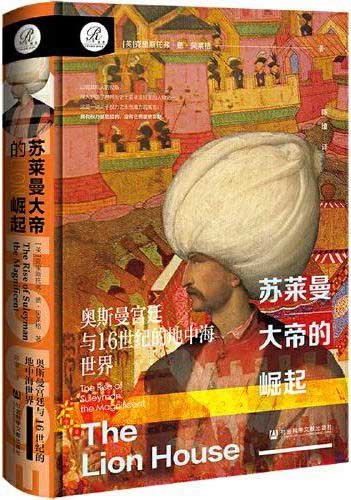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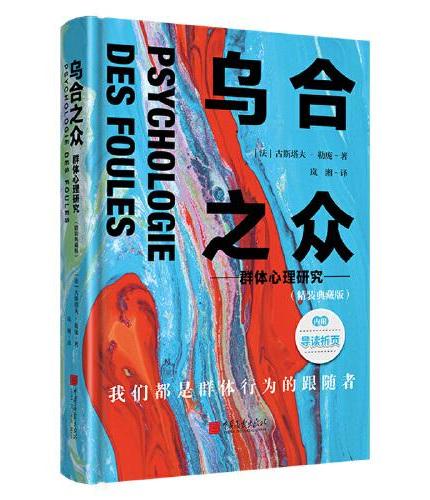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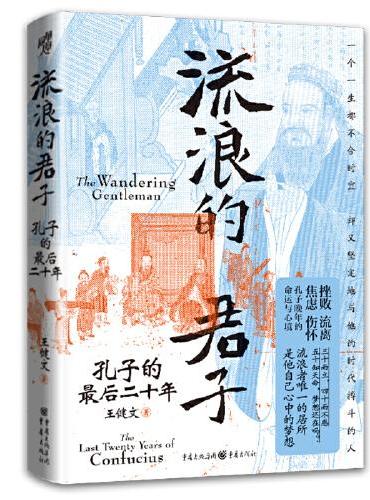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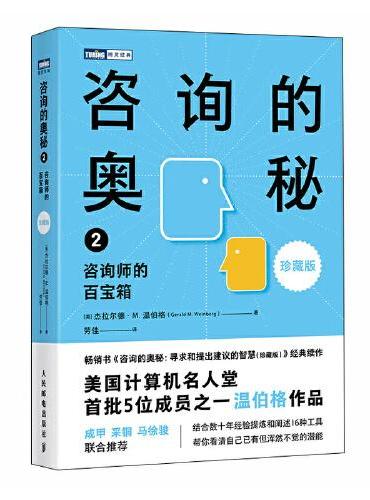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HK$
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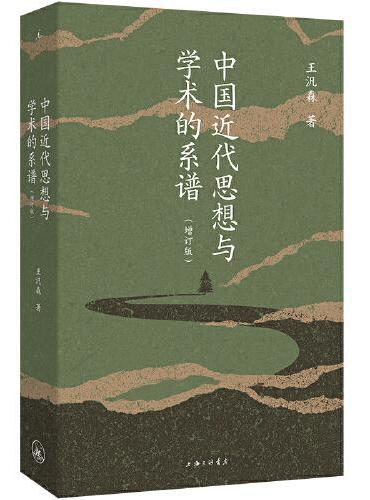
《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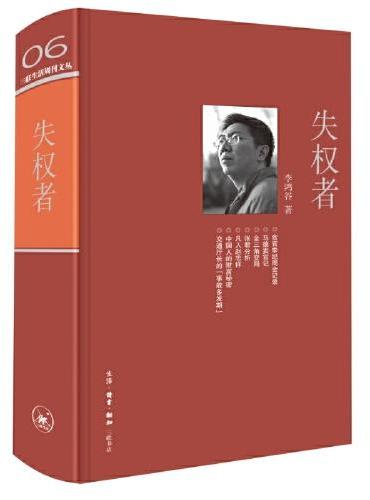
《
失权者(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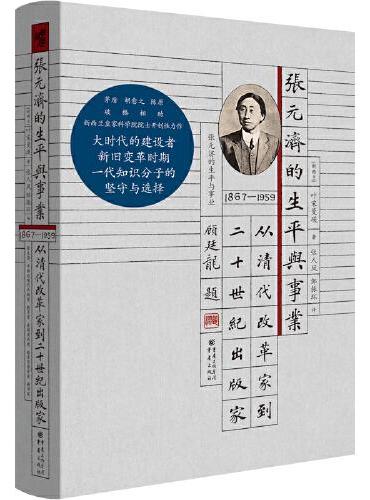
《
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从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纪出版家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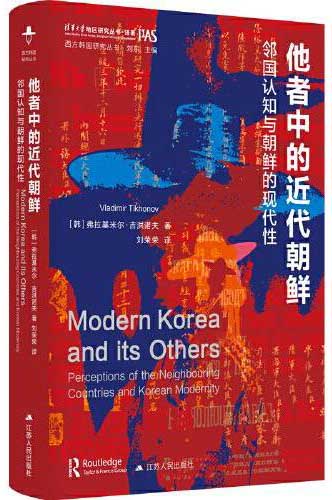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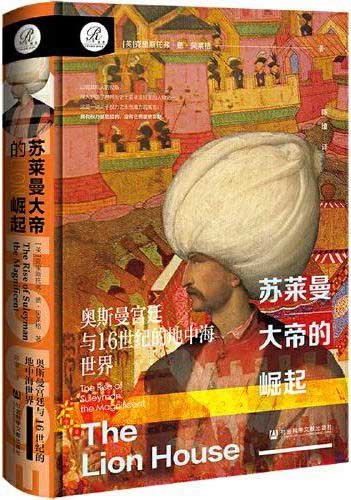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经典解读:周汝昌先生是红学研究的大家,也是诗词大家,他的观点深刻而独到。
*通俗易懂:语言平实,适合所有热爱诗词的读者。
*适合人群: 红学爱好者、文学研究者、想要深入了解诗词的普通读者 。
|
| 內容簡介: |
|
收入周汝昌先生《读词杂记》《“赢得青楼薄幸名”正解》《谈唐诗史上的“三李”》《关于古典诗词的鉴赏》等六十余篇讲论诗词的文字,熔铸了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体会,集中体现了作者在古典诗词方面的研究收获,兼顾内容的难易程度、读者的接受水平及阅读兴趣,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中国古典诗词、文字、对联等优秀文化做了细致深入的评点和分析。
|
| 關於作者: |
|
周汝昌(1918年-2012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市,是中国优秀的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书法家。他被誉为“红学泰斗”,在《红楼梦》的研究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周汝昌的研究不仅限于《红楼梦》,还涵盖了诗词、戏曲等古典文学的诸多领域。
|
| 目錄:
|
目录
读词杂记???001
旁听诗话???063
“诗律细”以外的“细”???068
定庵诗境证红楼???071
“赢得青楼薄幸名”正解???076
一篇《锦瑟》解人难???084
南宋诗人杨诚斋???093
南宋诗人范石湖???101
陆放翁诗漫举???109
从《剑南诗稿》中的农村诗说到“俗气”???120
诗应也为儿童作???136
诗词杂话???144
讲诗宜自根基起???158
诗的存在???163
关于古典诗词的鉴赏???170
《千字文》之话???184
清新睿王题《红》诗解???186
诵杜微音???196
李杜文章嗟谤伤???200
“思无邪”辨义???202
中华诗义???206
学诗???209
汉字的声调美???211
中华美学的民族特色???214
“对对子”的感触???233
诗人型和诗文化???236
“诗化”的要义???248
中华诗论悟“三才”???258
中华要典有“葩经”???262
“言志”与“抒情”???265
|
| 內容試閱:
|
读词杂记
高中的同学已经够忙了。七八门的科目,每天每科,都要留些功课、题目给你做;再稍稍做些课外活动,休息休息,谈谈闲话,弄弄乐器,一天便很快地度过去了。能够另外找几本书看的——尤其是旧诗词——实在不多见。有的同学喜欢文学,听到人家讲一首词,也喜爱得了不得,可是临到自己去研究,有时会因为种种关系中止的,譬如字句的古僻啦,意思的空洞啦,一提到它的中心思想,便感不到趣味,于是,渐渐地停止了他的阅读!
不过我以为,词这种优美的文学,大多数的同学却没得充分的机会去欣赏它,实在是可惜的事情!
最初,我是酷爱着旧诗的,诗的专集杂选,都被我急切地搜罗着,那时我以为天下最好的文学要算诗了。它的韵调、风格,读起来是多么优美啊!后来从同学处得到一部《燕子笺》传奇,读了一遍,觉得曲的韵调、风格,别有风味!记得当时最爱“风吹雨过百花残,香闺春梦寒”的一阕《醉桃源》。于是那几本有名的曲子,像《长生殿》《牡丹亭》《桃花扇》《西厢记》等等,又做了我的新朋友。
后来又知道了曲前还有词,读了些首,觉得词比诗曲更别有情趣,深恨相知之晚,又笑以前自己的见闻太少了。除了诗以外,却有这些好的东西留待我们去鉴赏!
心情是由爱曲转变到爱词了,于是又像迷症似的向多方面搜寻词集、词话之类。结果,种下了我对词喜爱最深的根子,一直到现在。——诗、词、曲的爱好,像走马灯一样地萦回在我的心头,但总是爱词的程度最深刻!所以读的词要比诗、曲多一些。
词虽然读得不少,但是因为贪多却发生了毛病:就是读的方法不彻底,大率是走马观花,看两遍就算!很少细细地推究词里用字遣词的妙处。有时觉得这是名句,也不过暂时心头一动,以后便漠然了。所以早就想把那暂时心头的感念记下来,只是迄今未果。
现在好了,一面我为了把读词的兴趣介绍给同学起见,一面又得完成了上面所想做的工作,在闲散时候,便把那霎时思潮一转的影像捉住,集成了一篇不大像话的东西。目的在专和新与词发生兴趣或还未曾与词发生兴趣的同学讨论。
不过我们现在的造诣太浅,知道的东西极有限,从来谈词,所见到的,无非是些浅陋的地方,至于词的深意、字的妙处,我们还未能窥透,所以我只是竭力避免用些空洞渺茫的形容词假作解人,来乱人观听,遮人耳目,真实地写自己的私见,以为初进的同学参考,并求先进的同学们指正!
因为我的目的是偏重于对初学的同学们谈话,所以我不得不从头至尾地把词的全体介绍出来,使初进的同学对于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现在便先言何谓词。
什么叫作词呢?词是上承诗、下启曲的一种文体,《词选》序里说:“词者……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诸位看了以上一段话,便可大概明白词是怎样一种文艺了。
词便是文章中的一种特别体裁,好像赋之于诗,诗之于散文一样,各有它的特点:格式、韵调。那么词诗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一、诗有定句、定字,词则无定,此仅相对而言。若绝对地说:词每调有一定的字句(诗每体有一定的字句)。
二、诗最普通的形式分四、五、七、六言四种,各句字数相等(杂言诗除外)。又分绝句、律诗、排律、古体等。词则有若干调,调皆有名,各调字句数目,皆不相同,变化多体。
三、诗韵平仄皆单押。词则平、入,独押;上、去,通押;有时平、上、去亦通押(如《西江月》)。
四、诗韵严,词韵宽,可通诗数韵为一部相叶。
五、诗可平起仄起,相对而言,全句平仄无定,如“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可起作“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并不限定首句或某句必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是也。绝对而言,每句平仄一定,如“平平平仄仄”却不可作“平仄平仄仄”是也。词则必须按谱填字,平仄绝对固定,不能擅自更改(除可平可仄之字不计外)。
简单地说:诗词是同种异形的文章。或者说词是诗的一种,诗的别体,也可以。此后诸位看的词多了,便知道词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
词的正式确立,是在中唐时候;但词的渊源,却渺不可索。有人把“平林漠漠烟如织”的《菩萨蛮》和“秦娥梦断秦楼月”的《忆秦娥》拿来作为词的鼻祖,并且托为李白所作,这种不可靠的传说,前人已驳辩无遗了。我的意见是李白生时恐怕还没有“词”的名字产生,可是词的雏形在老早以前就胚胎了。本来长短句之生成,我们无法断定它绝对是从哪一方面来的,前人固执己说,纷歧不一,实在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我们不能硬指词是生于什么方面,只能认为它是从多方面自然地逐渐演变而成的。大概韵文最初是仅于末字韵脚的调叶注意,却不计句子的长短。后来为求音调优美,才有整齐的等字句子生出。这两种句子同时进展着,但整齐的句子——诗句——成熟比较早些,于是当它盛极一时的当儿,没有人注意到长短句的作品,可是长短句的势力却随时随地地潜伏着,并未消灭。一旦诗被人玩腻了,它的势力便完全崩溃,于是作品的趋向纷纷转到长短句的方面,故而“词”才渐渐确立,有了它的地位。
譬如前人主张词出于诗,以词为“诗馀”,后来有赞同的,也有反驳的,却没有一个能以充分的理由来推倒“词为诗馀”说之必为不通,或咬定必为可通者。近人胡云翼论词以为此说——词出于诗——为大谬,且主张词出于“音乐的变迁”,他说:“……词的起源,并不是哪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也不能说是起源于哪一篇词,只能这样说:唐玄宗的时代,外国乐(胡乐)传到中国来,与中国古代的残乐结合,成为一种新的音乐,最初是只用音乐来配合歌词,因为乐辞难协,后来即倚声以造辞。这种歌辞是长短句的,是协乐有韵律的——是词的起源。”他的理由非常充足,使我们觉得此说近情理,合实际,值得我们真诚地发自内心地佩服!
他又曾引过汪森序《词综》的话作为反驳“词为诗馀”的证据:“古诗之于乐府,近体(‘近体诗’之简称)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这段话非常有价值。细品起来,立论至当,见地独到,可是古诗与乐府,近体诗与词“怎样”地“分镳并驰,非有先后”呢?汪森没有细给解释,胡先生也没有引申。如果不细想,不易使人心服。并且胡先生主张词出于音乐的变迁,也明明说起初绝句入乐,后来因新调发展,不易协乐,乃把那些泛声、散声、和声的地方,都填以实字,才成长短句,如此说来,词之与诗,究竟有无关系呢?词出于诗之说也有一些理由没有呢?
我这样说:谓词不尽源于诗则可,谓词与诗了无关系则不可。谓词为诗之变则或可,谓词为诗之馀则绝不可!如词之体制往往尚未脱诗之本形可为一证。好在这问题,并不关重大,留待异日研究吧。
次再谈到,词为什么到了宋代那样兴盛起来呢?顾亭林说历代诗文之变乃“势也”——“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当指乐府),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骈文),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诗)也,势也。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说得最好!大概经过唐代,诗之盛已达极点,极乃及衰,自然之势也!为什么呢?唐朝偌长的年代,全是诗得意的时候,不算不长久了,所以及入晚唐,诗之盛已不复再增高了。到了宋初,文人对于诗已渐渐感到厌了。加以诗字句太死板,繁复的情怀,不易充分地表现,调的长短句,恰能补足这种缺点,又以当时有一二爱好者,风气所趋,众归如聚,所以文人都走向这条路上去了。
又说:唐代诗风极盛,名家辈出,各立门户,竞求古奥,越来越和平民们暌隔,这种文学不复为平民所知了。于是一般平民们才走向长短句的方面去,以抒发他们的“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当时倡伎家都善于歌唱小词来取悦于人,那时的文人有很多是风流放荡的,天天在那“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的生活中过度着,于是词才流到了文人手里,试看《花间集》十卷,哪一首不是浓艳妖丽地描写歌舞流连的生活?可为明证。这也就是词的本色!直至后来众家蜂起,或清新,或隽永,或凄婉,或豪放,格调才为之大变,词也就大盛起来!
话又转回来说,表面上看词对诗的格式、规律,好像是解放的,实际却大不然!因为诗句仅求平仄的调适,而词却除了平仄的固定外,还要讲求五声,以求协律,才能入乐。简单地说:如上声去声字都属于“仄”,可是有的字要用去而不用上;甲乙两个字都是上声字,但有时宜用甲而不要乙,以求协音律。诸如此类,十分难辨,原来音律是最难精通的学问,历代精通音律的文人,恐怕只有少数的几个!连苏轼这样绝顶聪明的学者,他的词也往往以不谐律贻世讥!陆游曾经引晁以道的话,以为苏公会自歌《南阳关》,便算懂音律,恐怕那也是替苏轼掩饰的话;也许苏轼恰只会唱《南阳关》一调,否则,为什么不再有别的记载说他又会唱过什么“今阳关”呢?又如李清照说晏殊、欧阳修等“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往往不协音律”,可见音律之难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