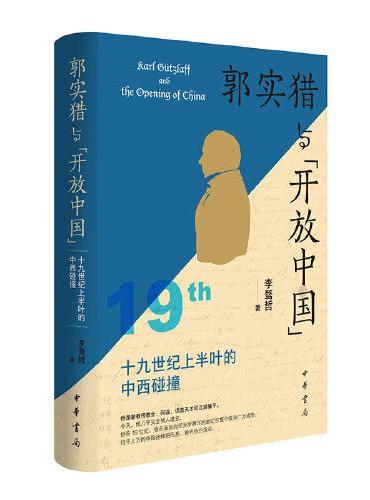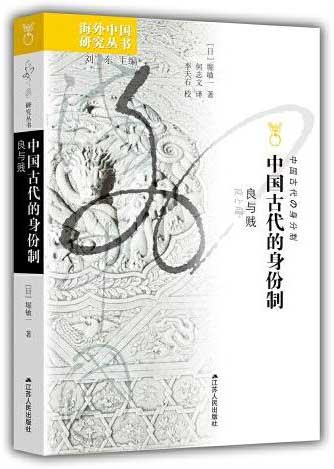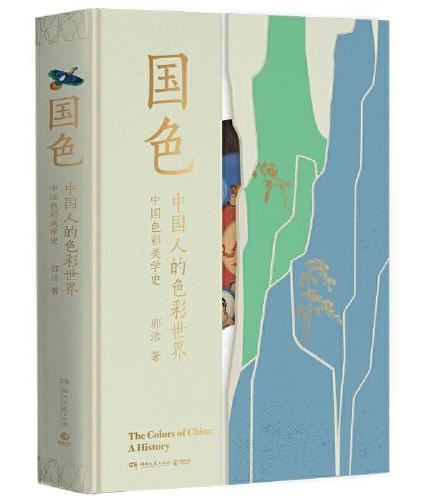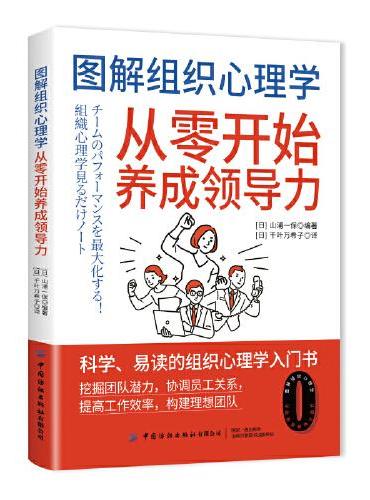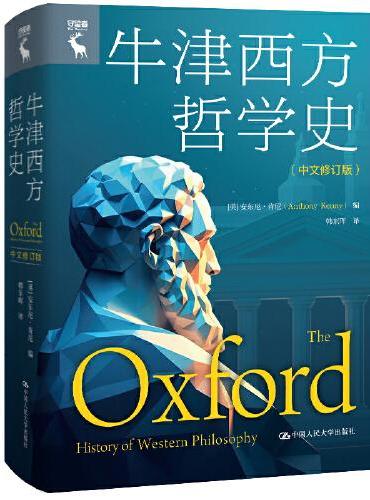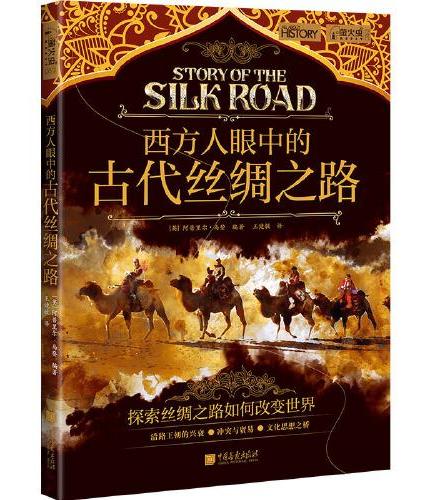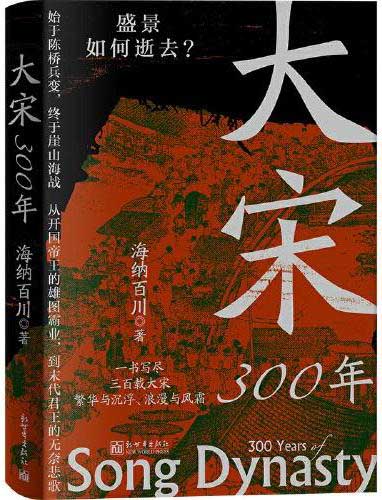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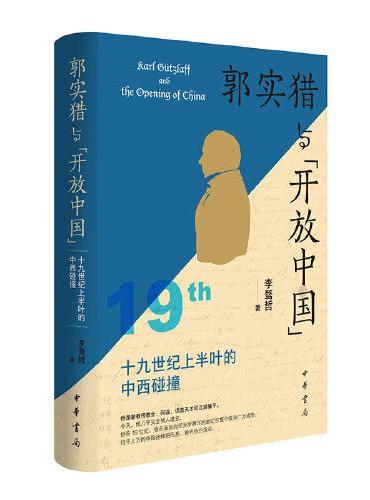
《
郭实猎与“开放中国”——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碰撞(精)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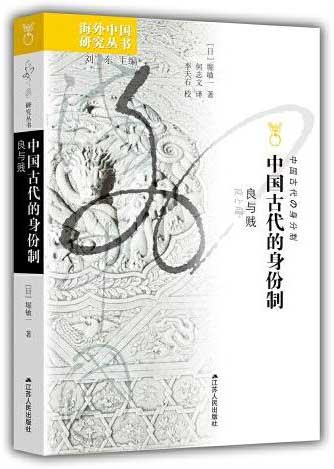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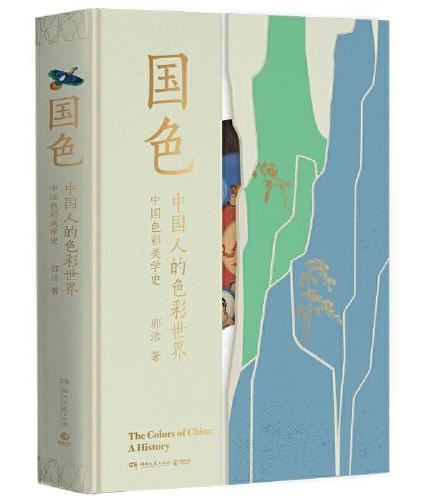
《
国色(《寻色中国》首席色彩顾问郭浩重磅力作,中国传统色丰碑之作《国色》,探寻中国人的色彩世界!)
》
售價:HK$
2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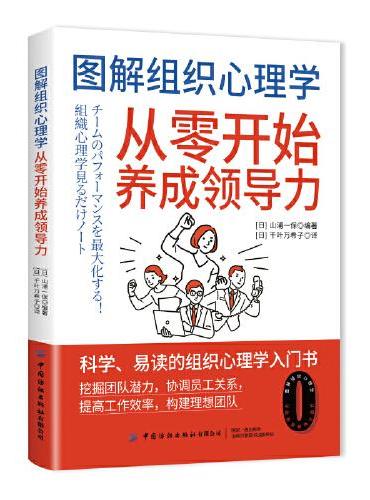
《
图解组织心理学:从零开始养成领导力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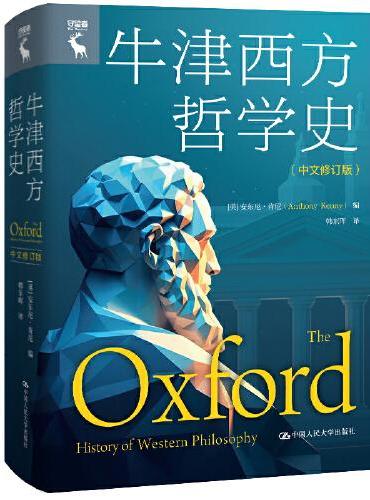
《
牛津西方哲学史(中文修订版)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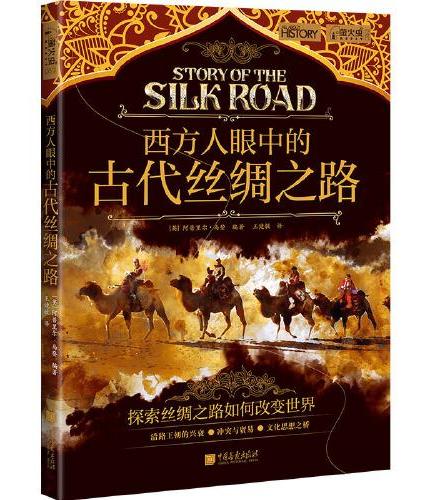
《
萤火虫全球史:西方人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
》
售價:HK$
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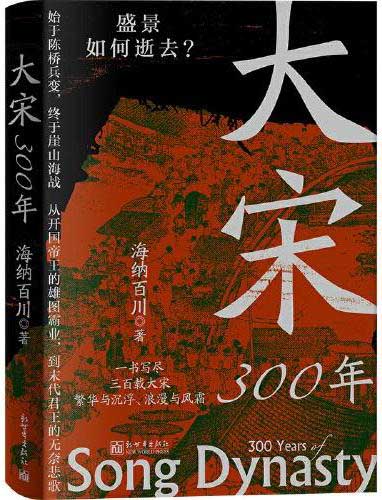
《
大宋300年(写尽三百载大宋繁华与沉浮、浪漫与风霜)
》
售價:HK$
75.9

《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一、法语文坛的叛逆之声 莫尼克·威蒂格 自传体小说 中文版重磅推出
影响朱迪斯·巴特勒、萨拉·艾哈迈德、《燃烧女子的肖像》导演瑟琳·席安玛的女性主义先锋。
玛格丽特·杜拉斯、娜塔莉·萨洛特、克洛德·西蒙、阿兰·罗伯-格里耶一致推荐。获法国最高文学荣誉之一“美第奇奖”。
基于作者童年的自传性书写,呈现一个不羁女孩的成长与爱恋。
二、 通过女孩的目光,重返所有人的童年
各种气味、光线、声音、质感、印象混合交织着涌来,一切在面前平等地呈现,童年世界无限伸展、无比清晰。
晕开的墨水,课间的游戏,反复诵读的诗句,风或泥土或草叶湿漉漉的气味,蝴蝶颤抖的翅膀,以及涌动的情愫。
然后是奥波波纳克斯。创造出来的名字,不能公开的秘密,一个谜。骤现、消失,又现形。“我是奥波波纳克斯。”
三、 颠覆规范的先锋写作,用纯粹语言塑造崭新的世界
摈弃分段,精简标点, 以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还原童年接踵而至的事件与不间断的印象,混乱中充满活力与节奏。
模糊的主语创造出一种普遍性视角,让每个人都能进入鲜活的童年现场。
用剥去性别、等级的纯粹语言,展现性别身份未经社会构建的孩童的世界。所有孩子
|
| 內容簡介: |
“奥波波纳克斯:
可以伸展。无固定形状,因此不可描述。
界,既非动物界,也非植物界,亦非矿物界,即无法界定。
情绪,不稳定,不建议与奥波波纳克斯来往。”
《奥波波纳克斯》是法国作家莫尼克·威蒂格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也是她的自传性写作,从孩童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本书颠覆了语言和叙事的规范,还原了未被性别和社会秩序约束的孩子对世界的感知。以纯粹、细腻、介乎诗与散文间的书写,邀请每个人重返童年的涌流。
|
| 關於作者: |
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1935—2003)
法国作家、哲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提出了“异性恋契约”(heterosexual contract)的概念,是性别研究无法绕开的人物,影响深远。威蒂格同样因其文学作品享有盛名,她的写作打破了文体和语言的规范,超越了性别界限。代表作有《直人思维》《奥波波纳克斯》《女游击战士》等。
译者 张璐
法语译者,法国新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翻译学院博士在读,译有《黄金年代》《好咖啡为什么好》《莫里索:亲密时刻》等。
|
| 目錄:
|
奥波波纳克斯 /001
后记 一部振聋发聩的作品 /241
注释 /247
译后记 /251
|
| 內容試閱:
|
中文版导读
与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莫尼克·威蒂格(1935—2003)很少谈论自己。她最喜欢做的事是实验新的写作形式,以此跳脱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类别范畴。1964 年第一版《奥波波纳克斯》的封面上印着“小说”,它也的确作为虚构作品获得了“美第奇奖”(这是法国最权威的文学奖项之一,嘉奖最具智慧、美感,最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把“美第奇奖”颁给威蒂格的正是当时最重要的一批作家:娜塔丽·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克洛德·西蒙等,他们都是“新小说”的代表人物,和他们一样,威蒂格的作品也在午夜出版社出版(午夜出版社也出版了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威蒂格与“新小说”派的关系可见一斑。直到20 世纪 80 年代,“新小说”派一直主导着法国文化界。也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小说作家的美学和文学倾向开始发生转变:在此之前,他们与自传体的写作形式一直保持着距离,从 80 年代起,虽然他们依旧坚持自己一贯的美学和写作原则,但个人生活开始成为他们的写作题材,如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获 1984 年龚古尔文学奖)、阿兰·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午夜出版社也借着这股回归“传记”的风潮在 1984 年再版了《奥波波纳克斯》,让这本在二十年前作为小说和虚构作品来阅读和接受的作品,得以作为自传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一部代替自传的小说?
然而,在《奥波波纳克斯》中,读者却几乎找不到关于莫尼克·威蒂格童年经历的确切信息。1935 年,莫尼克·威蒂格在离法德边境线不远的阿尔萨斯出生。四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阿尔萨斯被纳粹德国占领,威蒂格一家只得逃离家乡,来到位于法国南部“自由区”的小城罗德兹(洛泽尔省)。这种当时许多法国儿童都拥有的逃亡经历没有在威蒂格的第一部小说中留下任何痕迹。书中仅仅提到孩子们在“积满了水的弹坑”中玩耍,那是战争轰炸的遗迹,以及“烤饼的香味”,那是法国南部特有的地方美食。作者对风景的描写,尤其是让卡特琳·勒格朗兴趣盎然的众多树木、花卉、禾草,都不足以成为事件发生地点的判断依据,毕竟作者最常提及的植物在法国各地都能见到。威蒂格写作中的一切似乎都在抹去地域特色,而地域特色却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尤为突出。总之,《奥波波纳克斯》可以发生在法国的任何一个乡村。同样地,威蒂格也没有在卡特琳·勒格朗和她同伴们的故事中打下任何历史时期的烙印,书中没有提到德国占领法国,没有提到随着德军不断推进,大批法国人背井离乡,除了一处非常隐晦的数数暗示:“一起数数。七十一,七十二。嬷嬷是比利时人。”。因此,威蒂格在《奥波波纳克斯》中讲述的是一个共同的童年,所有人的童年,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所有人的童年。
“所有人的童年”(玛丽·麦卡锡)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大部分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中,城市聚集着工厂和其他经济生产场所,但是家家户户依然保留着关于祖辈务农的记忆,他们生活在乡村,与卡特琳·勒格朗以及她的同伴们一样,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季节更迭、田间劳作以及农业生产周期展开(比如收割完麦子便会迎来采摘葡萄的季节)。《奥波波纳克斯》的第一批读者对于这种对乡间生活的怀念依然可以感同身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众对它的喜爱,因为透过威蒂格细腻的描写,他们在书中看到了田野间的游戏、漫步,以及童年日常生活的一切,哪怕读者本人未必亲身经历,父母和祖父母也一定把这些回忆传递给了他们。同样,大多数读者也未必拥有书中描写的校园经历。卡特琳·勒格朗就读的学校是由天主教修女授课的“私立”学校,而大多数读者上的学校则是国家创办的“公立”学校。但是威蒂格从来没有强调私立学校的特别之处,反而极力突出两个教育系统在课程、课外活动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外出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走出课堂,教孩子们识物,教授他们植物、地质、农业经济等方面的知识)。至于大篇幅的宗教仪式(弥撒、朝圣、游行),1964 年的读者对它们并不陌生。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宗教活动在法国依然盛行,人们即使不是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也会在重大节日(圣诞节、复活节)频繁前往。然而,如今宗教活动在法国已经十分少见,今天的法国读者面对书中大篇幅的仪式描写也会感到惊讶和困惑。再加上威蒂格所写的宗教仪式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4 年)推行改革之前的天主教仪式:弥撒用拉丁语吟诵,神父背对信徒主持仪式,圣体显供架、香烛等仪式器具必须彰显教会实力。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改革旨在使崇拜仪式现代化,拉近信徒与教会的关系,改革后,弥撒用法语吟诵,神父面对信徒,流程也得到了简化。所以今天的法国读者其实与中国读者一样,也会对神秘的宗教信仰和仪式感到费解。这也正是威蒂格的天才之处,她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将天主教的礼仪和仪式展现在读者眼前,而小女孩自己也无法理解这些礼仪和仪式的意义,在弥撒中,她百无聊赖,却发现了另一样重要的东西——爱。杜拉斯也在文章中提到天主教仪式的晦涩以及孩子们对它的厌倦:“一个主教死了。他的死会造成或带来什么?在隆重、奢华的主教葬礼中,在中殿的阴影下,在一切引人注目之物的阴影中,在一切之下,小女孩的一绺头发被她旁边的小女孩看到了。多美啊。[……]经过的天主教修女们盲目地见证了她们并不知晓的另一种耀眼的至福。”
从个人视角到普遍视角
虽然卡特琳· 勒格朗的童年扎根于 20 世 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但威蒂格努力淡化了时间和空间对小说的限定,而是选择突出童年经历的共性。80年代,威蒂格在评论朱娜·巴恩斯的写作时提到,《奥波波纳克斯》的写作不在于描述一种“个人视角”(即喜欢同班同学的法国小女孩卡特琳·勒格朗的视角),而在于构建一种可以容纳所有读者的“普遍视角”。
这种将视角普遍化的成功尝试引起了“美第奇奖”评审委员会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读者能在《奥波波纳克斯》中找回自己的童年回忆,才使得今天的法国读者对它情有独钟。为了将视角普遍化,威蒂格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手段,但是它给文本带来了极其精巧、复杂的风格特征。一般而言,小说通常由第三人称书写[借助用于描述他人的人称代词“il”(他)或“elle”(她)],而自传一般用第一人称书写[借助人称代词“je”(我)],但威蒂格选择了一个特殊的代词—“on”。这个法语人称代词功能特殊,只在极少的语言中存在,它是一个第三人称代词,却能指代说话者(等同于“je”)。它既是“je”,也是“il/elle”,是一种可以同时提及说话者(第一人称)和被指涉对象(第三人称)的语言形式。“on”的使用让《奥波波纳克斯》既不属于小说体裁,也不属于自传体裁。不同于第三人称代词“il/elle”,“on”既可以指代女性,也可以指代男性,这是它的另一个优势。威蒂格利用“on”的这一特性构建了一个性别身份还未经社会构建的儿童人物:卡特琳·勒格朗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人,她正在接受的教育也尚未将她完全限制在小女孩的身份之中。而“on”也让《奥波波纳克斯》的读者,无论男女,都能代入其中。克洛德·西蒙也对“on”带来的独特阅读体验赞
赏有加: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是在阅读一段历史或故事,它在忠实而有趣地诉说可能发生在一个小女孩身上的事情,而是通过她的眼睛、嘴巴、双手和皮肤去看,去呼吸,去咀嚼,去感受。*“on”创造了一个新颖、奇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孩提时代的感觉,或者说学习成长的感觉。《奥波波纳克斯》没有讲述故事,而是呈现了那个叫卡特琳·勒格朗的小女孩所感知到的一切,没有叙述主体来组织她的感知,区分故事与现实,将
事件放置在空间或时间之中。毫无征兆地,地理课紧接着弥撒,田间散步紧接着课间休息,摘豌豆紧接着背寓言。经历过的场景、观察到的事实、听到的故事、孩提的恐惧以及青春期的遐想接踵而至,它们交织在字里行间,展现出孩童对宇宙强烈的探究欲和记录知识的激情。这就是玛丽·麦卡锡所说的“所有人的童年”,也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所谓的“我们都写过这本书”。诚然,读者无法与一个缺乏外表与性格描述的人物产生身份认同,但《奥波波纳克斯》通过人物的成长节奏、“纯粹的描述材料”让读者仿佛置身于故事中,化身为卡特琳·勒格朗。
学习读写
卡特琳·勒格朗的活动和学习让我们意识到她在长大,年级在上升。她学习写字,先用“黑色的铅笔”在本子上吃力地画出“m、l、b”,接着写出单词、句子,比如“莱昂学功课”,最后铅笔换成了令人讨厌的蘸水钢笔:“食指总是滑到蘸满墨水的笔头上。本子上有紫色的手指印……”她也在学习读书:“你高声朗读完整的句子。磨坊里的磨坊主磨玉米。磨坊主的丈夫拉来绵羊。绵羊吃磨坊主磨的玉米。”从其他材料中借来的引文、语句贯穿全书。首
先,学生们高声拼读句子,随着年级的升高,句中的词汇也越来越复杂。在第二章中,井里发现的宝藏取代了磨坊主和她的磨坊:“对—这—个—穷—人 —家 —来 —说 —是 —一 —笔 —意—外—之—财”。在第四章中,卡特琳·勒格朗登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假期里,她和表兄弟在看各自的书。当樊尚·帕尔姆因为“阿道克船长在追威士忌泡—泡—泡时变成了一只小鸟叽—叽—叽”(《丁丁历险记》之《月球探险》)而哈哈大笑时,卡特琳·勒格朗则在背诵课本上的《萨朗波》(福楼拜)片段:“鬓角的珠串垂到嘴角,粉色的嘴巴像半开的石榴。胸前的一组宝石……”接下来到了高中时期。为了记住《阿利斯坎》武功歌的片段,卡特琳·勒格朗和同学们一整天都在背诵古文:“德拉姆王指髯为誓 / 吾当以五马分尸……余知其髯不能守信”。她们阅读拉丁语的维吉尔,她们学习诗人,卡特琳·勒格朗从庞大的诗词库里摘出零散的诗句,将它们散落到自己的文本中,比如马莱伯的“乡村已在我面前展开”。她把查理一世的诗句“思想中除我以外之一切禁锢我”和兰波的诗句“洁白的奥菲莉亚像一朵大百合花漂浮着”写在给瓦莱丽·博尔热的植物标本集上。卡特琳·勒格朗引用诗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
杂。她将《阿利斯坎》武功歌的古法语诗文作为第五章的开篇,而波德莱尔《旅行的邀约》中的三个诗节(而非叠句)则贯穿最后一章。从“你说,我的孩子 / 我的姐妹 / 想想多甜美 / 去那儿一起生活 / 悠然相爱 / 相爱至死 / 在像你一样的国度里”开始,到最后一页的“你说,落日的余晖 / 给田野、运河与城市 / 洒下风信子 /与金黄的色彩 / 在温暖的柔光中 / 世界在沉睡”。全书最后一句则借用了文艺复兴诗人莫里斯·塞夫的爱情诗:“你说,我曾爱她之深我仍活于她身。”在最后一章中反复出现的“你说”(on dit)代表后面的内容是一句引语,它们也让这一章成为全书最模糊的一部分。你说现在是九月,你说现在在下雨,你说瓦莱丽·博尔热的嘴唇像佩涅洛佩的一样闪耀……谁在说话?是思绪还是梦境?谁在引用波德莱尔和塞夫的诗句?或许是卡特琳·勒格朗,但也可以是任何人,每个人,甚至是作者本人。全书最后一句的人称和时态让它脱离了那个已经成长为少女的小女孩的故事,而隐隐勾勒出作者本人的形象。不过,既然引用诗文是少女卡特琳·勒格朗钟爱的消遣方式,而且这些抒情诗也与她和瓦莱丽·博尔热的情愫相互呼应,即便是最后一句,莫尼克·威蒂格依然与卡特琳·勒格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奥波波纳克斯》是自传体文本的第三人称变体,威蒂格对文体的探索也延续到了她的第二部史诗小说《女游击队员》(Les Guérillères)中。
一种写作的到来
《奥波波纳克斯》是一种写作的到来,是与作者本人经历极其相似的写作实践。首先,威蒂格与卡特琳·勒格朗的写作都与前人的文本密不可分,威蒂格在《文学工地》(Le Chantier littéraire)中说,“与作家首先产生关联的是浩大的古代与现代作品库”,卡特琳·勒格朗,抑或是莫尼克·威蒂格本人,都喜欢裁剪、挑选、拼凑他人的文本,从孩童时代起便把阅
读与写作结合起来,把读到的段落背诵下来,以便日后使用。其次,威蒂格与卡特琳·勒格朗进行的都是一种实践性的写作。在《文学工地》中,威蒂格将作家比作那些在工作室或工地上处理具体问题的工匠、建造者。而卡特琳·勒格朗的写作活动更像是 DIY :她先试着画出奥波波纳克斯的模样,再用文字对它进行描述;她在页脚写字;她自己制作书,做植物标本集……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妹妹韦罗妮克·勒格朗以及后来瓦莱丽·博尔热在地上画的形状和字母。最后,卡特琳·勒格朗为了博得瓦莱丽·博尔热的注意和爱而写作,这让人联想起作者本人自青春期起就将写作与女性之间的情愫紧密相连:“我的写作一直与被禁止的女同性恋密不可分。我在十二三岁时开始写作,那时我爱上了一个女生。”*威蒂格在写作生涯中不断追寻普遍性,而这一切都始于《奥波波纳克斯》—一个关于法国童年的故事。威蒂格以极少的文学手段,慷慨地为读者提供了找回童年的机会。卡特琳·勒格朗是她,但同时也是我们这些阅读《奥波波纳克斯》的人,无论是男是女,无论出生在 20 世纪还是 21 世纪,出生在法国还是中国。这部惊人的小说讲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无比欣喜地得知,在中文译本的帮助下,卡特琳·勒格朗也变成了中国人。
卡特琳·埃卡尔诺 和亚尼克·舍瓦利埃
奥波波纳克斯
叫罗贝尔·帕扬的小男孩最后一个走进教室,大喊着谁想看我的小鸡鸡,谁想看我的小鸡鸡。他重新扣上裤子。他穿着米色的羊毛袜。嬷嬷叫他闭嘴,为什么每次最后一个都是你。这个上学只用穿过一条马路的小男孩总是最后一个到。从校门望出去就能看见他家,门前有几棵树。课间休息的时候有时能听到他妈妈喊他的声音。她在最高的窗户后头,越过树梢就能看到她。床单晾在墙上。罗贝尔,过来拿你的口罩。她的声音大到所有人都能听见,但是罗贝尔·帕扬不理她,所以喊罗贝尔的声音继续回响着。卡特琳·勒格朗第一次来学校的时候在马路上看见了学校的院子和铁丝网旁边的草和丁香,那是用光滑的铁丝编成的网,勾出一个个菱形的图案,下雨时雨滴会挂在菱形的四个角上,网比卡特琳·勒格朗高。她攥着推开门的母亲的手。院子里有很多孩子在玩耍,但是一个大人也没有,只有卡特琳·勒格朗的母亲,她最好也别进学校,学校是小孩待的地方,要告诉她才行,要不要告诉她呢。教室里面很大,有很多课桌,有一个大圆炉子,炉子周围也围着菱形铁丝网,一根管子伸到靠近天花板的位置,管子上有的地方像手风琴的风箱,嬷嬷踩在靠窗的梯子上做着什么,她想关上最上面的那扇窗。卡特琳·勒格朗的母亲说,您好,嬷嬷,于是她从梯子上下来,接过卡特琳·勒格朗的手,然后让母亲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离开,放心吧。卡特琳·勒格朗听到院子里传来吵闹声,为什么不让她跟其他孩子一起,也许是因为她还没有真正地来到学校,因为这要是学校的话也跟想象的太不一样了。它看起来就像家一样,只是比家更大。下午有时候孩子们也会被要求睡觉,但不是真睡。所有人把手臂交叉放在桌上,把头埋在手臂里。闭上眼睛。不许说话。卡特琳·勒格朗时不时会睁开一只眼睛,但这也是不允许的。你们经常站成一排唱歌,在我右手边/有一棵玫瑰树/它会在五月盛开,然后举起右手。卡特琳·勒格朗向右手边看去,现在不是五月,所以玫瑰树还没发芽。你吃点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点心篮,一到四点嬷嬷就挎着所有人的点心篮大喊,这个篮子是谁的,篮子的主人就会回答,是我的。点心篮里有一块面包、一条巧克力、一个苹果或一个橘子。卡特琳·勒格朗总是在上学路上吃掉自己的水果,虽然她不该这么做但她就是忍不住。有时她只是咬上一两口,嬷嬷就会问,有个咬了一半的苹果的篮子是谁的。她经常故意在点心时间之前忘记自己是不是已经把苹果或橘子吃了,为了给自己一个惊喜,也为了看看水果会不会在她忘记的时间里自己长回来。卡特琳·勒格朗作弊了,她知道这不是游戏,因为她不可能完全没有印象,当她拿到点心篮看到篮子里没有苹果或者只剩一个苹果核的时候,她也只会有一点点惊讶,毕竟她没办法完全忘记自己篮子的模样。嬷嬷在削橙子。她用刀抵着旋转的橙子,橙子皮打着圈从橙子上脱落下来。削完所有的橙子,她把最大的圆圈挂在门上,也就是那些没被削断的完整的皮,它们顺着门垂下,被碰到的时候会转圈,嬷嬷不愿意把它们给别人。
后记 一部振聋发聩的作品
昨天我读到了第一篇关于莫尼克·威蒂格的《奥波波纳克斯》的文章。果不其然,文章作者和我读出了不一样的奥波波纳克斯。
我的奥波波纳克斯,它可能是,甚至几乎是,第一本关于童年的现代著作。我的奥波波纳克斯,它为之前百分之九十的写童年的书宣判了死刑。它是某种文学的终结,谢天谢地。这是一本既值得钦佩又举足轻重的书,因为它遵循了一条丝毫或几乎丝毫未被触犯的铁律,那就是只使用纯粹的描述材料,且仅依靠纯粹的客观语言。最后这点非常重要。儿童正是用它来梳理和清点童年的世界,而作者用它谱写了一支素歌。所以我说我的奥波波纳克斯是一部书写杰作,因为它是用奥波波纳克斯自己的语言写成的。
但是别担心,成年人即使不懂奥波波纳克斯的语言,也对它不陌生。只要读一读莫尼克·威蒂格的书就能回想起来。当然你也不是不可能拖着沉重的眼皮读着一部虚假的文学作品,甚至怀疑作者写的是不是文学作品。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孩子。十个,抑或一百个小女孩和小男孩,他们有着自己被赋予的名字,但也可以把它们当作筹码来交换。这本书讲的是一千个小女孩在一起,一大群小女孩向你涌来,把你淹没。就是这样一种流动的、宽广的、洋流般的东西?一个浪卷来一大片、一大群孩子。毕竟在书的开头,孩子们的年纪非常非常小,正处于无尽岁月的深处。韦罗妮克·勒格朗差不多只有三岁吧?
首先,在这个巨浪里生活、翻滚、攒动着千千万万个小浪花。小浪花们共生,像连发的子弹一样前赴后继,甚至遵循着一种绝对的秩序。接着每一朵小浪花扩展开来,放慢速度,与另一朵小浪花交叠、拥抱,最后融合在一起—童年老去了。作者非同寻常的艺术让我们丝毫没有察觉这种老去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就像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我们会困惑,会惊讶。接下来到了学乘法的年纪,然后是学拉丁语的年纪?但要注意,即便已经老去,童年依旧是童年,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座铜墙铁壁、坚不可摧的城堡。我们这才发现我们进不去。我们被邀请去观察,去见证。童年在制造,在成形,在我们眼前呼吸。
这种推进令人称道。时间在流淌,如同深邃的源泉,伴随着我们看到的童年,一起充盈着我们。
刚开始,一个小女孩在剥一个橙子,她咬了一口,吞掉了一整片天空,吞掉了另一个死去的小女孩,吞掉了一切的一切。接着,小女孩换了一个橙子,她吞掉了另一个橙子,她以闪电般的速度用眼睛遮住另一片天空,她吞掉本子上写了一个小时的“横竖撇捺”。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了。比如在第一个橙子和第二片被吞掉的天空之间,什么东西无声地颤抖了一下。在面包屑做的小人和被撕掉翅膀的蝴蝶之间,什么事情发生了—做小人的小女孩和肢解蝴蝶的小女孩是同一个人。
在童年的尽头,在故事的末尾,在城墙崩塌的时刻,联结永远地形成了。这时精神已经被心灵的颤抖荼毒,大家不再一起玩耍,不再共生。友情诞生了。
作为城堡理想的守门人,一模一样、不知其名的天主教修女们就像成年人的范本,在过道、宿舍里一字排开。童年的涌流拍打着她们暗淡的黑裙。在她们虔诚的阴影下,暗藏着对死与生世俗的、纯真的、可怕的审视。
一个主教死了。他的死会造成或带来什么?在隆重、奢华的主教葬礼中,在中殿的阴影下,在一切引人注目之物的阴影中,在一切之下,小女孩的一绺头发被她旁边的小女孩看到了。多美啊。跪在地上的小女孩的头发的运动被发现,一种空间上的发现,头发与小女孩同时运动,因她而动,但又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它在小女孩的身旁呼吸,同时在她的头上呼吸,像植物在地上呼吸。没有借助任何形容词来形容这一对美的发现。头发的运动被描述得与亡者弥撒飞扬的管风琴乐曲一样。音乐让墙壁倒塌,它无处不在,而在这下方,在它的包围中,一个孩子的头发,对另一个孩子来说,穿透了原初的黑暗。经过的天主教修女们盲目地见证了她们并不知晓的另一种耀眼的至福。
她们有自己的作用。她们的作用在这本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用毫无意义、隐晦不明的义务来点缀童年,她们给了童年违背义务的自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学拉丁语的时期也是令人难忘的战争时期。小女孩们被荨麻鞭打,大腿被撕咬,叛徒被发现。等着跟其他的孩子去偷一块不知道能用来做什么的大铁板,其他的孩子没有赴约。所以,也许黎明就是这个被叫作黎明的短暂时刻。但它是那么短暂。
我的话到此为止。你也好,我也罢,我们都写过这本书。一个人把这本我们都写过的奥波波纳克斯挖掘了出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在合上书的那一刻我们分道扬镳。我的奥波波纳克斯,它是一部杰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
《法国观察家》,1964年11月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