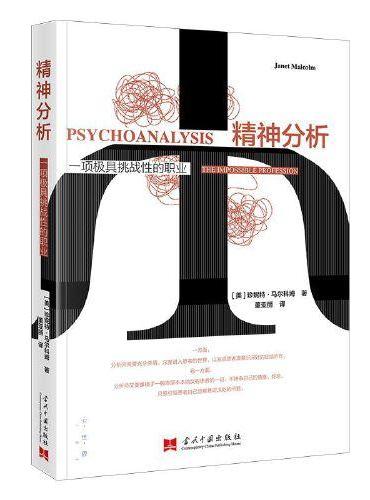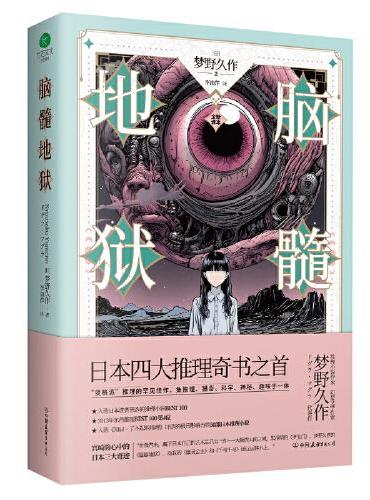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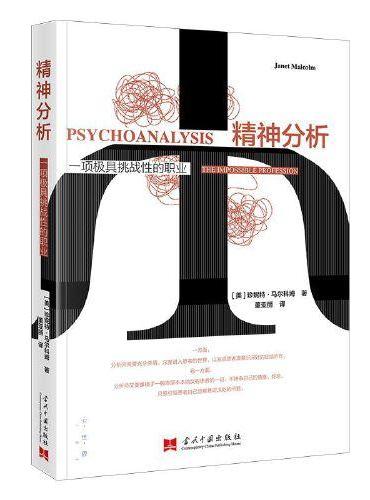
《
精神分析: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职业
》
售價:HK$
74.8

《
虚拟货币及其犯罪治理实务
》
售價:HK$
63.8

《
辽史纪事本末(历代纪事本末 全2册)新版
》
售價:HK$
107.8

《
产业社群:超级群体引领新经济浪潮
》
售價:HK$
68.2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HK$
119.9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74.8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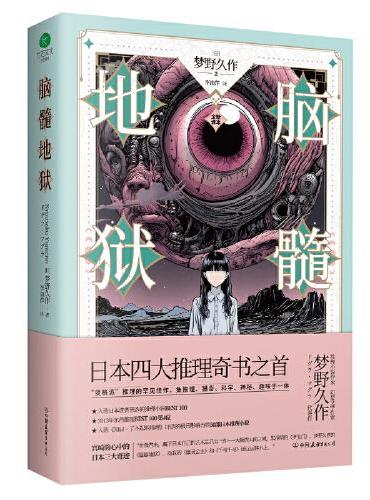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
| 編輯推薦: |
☆尘封六十余载世间仅存手稿首度面世。
☆《羊舍一夕》珍贵手稿,被收藏家收藏,汪家后代之前都无从得知。小楷抄就,在汪曾祺手稿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寂寞和温暖》是汪老写了5遍的稿子,现收藏于汪家。从手稿中不仅可以看到作家写作时的状态、修改的情况等,更重要的是,书写、手泽,这是一般读书人、爱书人非常愿意亲近的。
☆汪曾祺手稿 黄永玉插图,两位大家的激情碰撞,颇具收藏价值。
☆文字平淡质朴,深得自然之妙趣,于不经意间渗透出睿智、从容的生活智慧。
☆本书文本由李建新汇校,他对汪曾祺作品的校勘工作获得了汪先生家人与研究界的普遍认可。
|
| 內容簡介: |
1958年,汪曾祺到张家口农业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人民文学》刊发五十年代中期曾活跃一时作家的新篇章,汪曾祺创作了一篇描写果园劳动生活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副题又名为《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
《人民文学》于1962年2月号推出此小说,同时还请画家黄永玉绘了插图。给《人民文学》交稿的时候,汪曾祺先生用毛笔小楷亲自手抄写了一份稿子,这份稿子后由收藏家收藏,世间仅存一份。
本书以这份“珍贵手稿”为主要内容,加以释文,同时附录汪曾祺先生同时代创作的两个短篇小说《看水》《王全》,并收录《寂寞和温暖》的手稿。
|
| 關於作者: |
|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以短篇小说、散文和样板戏闻名,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端午的鸭蛋》等。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 目錄:
|
序:也是旱香瓜/汪朗
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
寂寞和温暖
《羊舍一夕》汇校
附:王全
看水
整理、汇校说明/李建新
|
| 內容試閱:
|
序言
序:也是旱香瓜
汪朗
汪曾祺生前身后出版的几百种作品集中,这本小书算是比较独特的。书中只收录了老头儿两篇作品的手稿和三篇小说的汇校本。手稿一篇是1961年11月25日写成的《羊舍一夕》,另一篇是1980年1月24日改完的《寂寞和温暖》第三稿。没啥看头。也还有点看头。
没啥看头,是说内容太单薄。随便翻翻,个把钟头也就翻到头了。再想看点别的,没了。有点看头,是说除了读文章,还能从手稿中悟出点道道,值得花点功夫。
老头儿作品的手稿,留存不多,毛笔写的手稿,更是少之又少。而《羊舍一夕》,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篇,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篇。此次《羊舍一夕》手稿能够出版,要感谢陈晓维先生从拍卖会上拍得此物,并愿意公之于世。
这篇小说是汪曾祺在张家口沙岭子写成的。这是1949年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也算是标志性作品。当年汪曾祺去沙岭子,可不是什么体验生活,是正儿八经的劳动改造,必须定时定点完成各种农活,还要时不时提交思想改造汇报,里里外外累得很。像扛麻袋、刨冻粪之类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这样的环境中,这个汪曾祺居然还要写小说,还要用毛笔。真是不可救药。
爸爸1958年下放劳动时,我刚上小学。我还记得,他在来信常说的一件事就是要东西,要稿纸,要毛笔。毛笔还指定要一种鸡狼毫,说是适合写小字。当时市场供应紧张,鸡狼毫只有大文具店才偶尔有售。于是逢到星期天,妈妈便都会带着我们几个跑到西单把角的文华文具店转转,遇到鸡狼毫,赶紧买几支,上邮局寄走。当时我们住在宣武门附近,去趟西单,走路十几分钟就到了,不算事。由此观之,汪曾祺能用毛笔写成《羊舍一夕》,本人也“与有荣焉”。虽然只是买过几次鸡狼毫。
《羊舍一夕》写成的时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汪曾祺的身份又是摘帽右派,刚刚结束劳动改造。然而小说却充盈着乐观向上的气氛,看不到悲观颓丧的情绪。这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吗?应该是。从手稿中能够看出,他写作时十分放松,用笔很少犹豫,大段涂抹反复修改的地方也不多。这说明他在动笔时,对小说的基调已经有了明确的把握,并不是临时抱佛脚、走到哪儿算哪儿。看一篇文学作品的手稿,比起看铅印书籍,会给人更丰富的感受,因为笔迹中蕴含了更多的作者信息。
老头儿写过一篇散文《随遇而安》,详细回忆了当年下放劳动的生活。口气也挺平和。他居然说当过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不然他的生活就更平淡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和《羊舍一夕》对照看看。这些作品折射出他的文学创作主张,即“美化生活”。用他的原话,就是“人间送小温”。美化生活不是倒转乾坤,指鹿为马,不是满嘴跑火车,而是在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状态中发掘美好的东西,将其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轻轻说一声:“活着多好啊。”老头儿作品至今有不少人喜欢,与他的“人间送小温”有很大关系。
这本书收录的《寂寞和温暖》第三稿手稿,应该算是“买一送一”,白饶的。当时商量出版《羊舍一夕》的手稿,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人家拍下的物件,我们当然不能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单出一篇《羊舍一夕》有点单薄,正好手头有一篇《寂寞和温暖》的手稿,便拿了出来,增加点分量。说来也巧,这篇小说也是写老头儿在张家口那段生活的,尽管文章中主角改了名字,换了性别,但不少事情都是他经历的。两篇文章放在一起,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尽管是买一送一,这篇手稿也还有些值得说说的地方。《寂寞和温暖》第三稿,从来没有发表过。现在读者能够看到的《寂寞和温暖》,已经是第六稿了。一篇小说写了六遍,这在汪曾祺几十年创作生涯中是仅有的一次。若是将这篇手稿和最终发表的成品放在一起翻翻,多少能看出汪曾祺家庭地位之低下与文学主张之固执。这篇小说是家里人建议老头儿写的。当时反右题材十分热门,有过这一际遇的作家,不少人将自己的经历敷衍成篇,见诸刊物,甚得好评。于是我们撺掇老头儿也写上一篇,套用时下的流行用语,就是“蹭蹭热点”。他倒是没有拒绝。可是小说写好后大家一看,完全不是那个调调。人家打成右派后都是天崩地陷死去活来,他倒好,基本是波澜不惊,最多增添了几分寂寞,还有不少好心人给予关照。这哪行?必须改。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就这样,老头儿皱着眉头把这篇小说重写了六遍,结果还是那个温情脉脉的调子,始终不会“卖惨”,或是不屑。就连题目也从《寂寞》变成了《寂寞和温暖》。改来改去,最后弄得大家都很疲倦,只好由他去,温暖就温暖吧。
《寂寞和温暖》的六稿,都是从头到尾重新写过的,因此中间的几篇手稿才能留下来。我以前觉得这些改稿的基调没有变,文字改动好像也不多。但是负责整理、汇校文本的李建新先生却说并非如此。他原来想将第三稿和发表的第六稿中的文字差异做些校注,结果发现改动甚多,弄不来。看来汪曾祺尽管在文学主张上十分固执,绝不趋时,但是对于文字的表达,还是力求精准,不吝修正的。若有人愿意将这部手稿与最后的刊发稿做一番比较,也许能看出老头儿写作时遣词用句的深层考虑。顺便说一句,建新对老头儿文章的不同版本多有研究,还发现过不少疏漏错讹,堪称专家。由他负责这本书的汇校事宜,让人放心。
这本书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经黄永玉先生同意,将他当年为汪曾祺出版的一本少儿读物《羊舍的夜晚》所做的木刻插图收入书中。这在老头儿作品集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些年好像只有《羊舍的夜晚》羊皮书出版时,曾将黄先生的这些木刻作品照原样收入其中。那本羊皮书书是纯粹的收藏品,价格不菲,一般人很难见到。
《羊舍的夜晚》的书名原本就是《羊舍一夕》,收入了汪曾祺所写的与张家口有关的三篇文章。编辑觉得“一夕”一词小孩子可能不太懂,才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其中的插图是老头儿建议找黄永玉刻的。前些年到黄叔叔家闲聊,他还回忆说,老头儿在张家口下放劳动时还写信要他买毛笔和颜料,他都照办了。这个汪曾祺倒是不见外,要知道黄永玉当年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经常要在晚上刻木刻挣点外快度日。一幅木刻的稿费只有五元钱。这是他亲口说的。
黄叔叔如今也不在了。他的木刻和汪曾祺的手稿眼下出现在同一本书中,也算是两人几十年情谊的一个见证吧。
老头儿在《豆腐》一文引用过一句歇后语:旱香瓜——另一个味儿,以此形容松花蛋拌豆腐的独特风格。这句话用来描述这本书的特色,也挺合适。时下,不少人阅读老头儿作品到了相当高的段位,那种大路货的选本和鸡汤式的书名已经提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希望看到不一样的“硬货”,品尝更丰富的滋味。对于这类读者来说,翻翻这本手稿集会是不错的选择。除了阅读文章内容,还可了解一下汪曾祺盛年时的书法,揣摩揣摩该人运笔行文时的心态,顺便做些文本对比,写作背景研究,感受可能会更加多样,更堪回味。
不知读者是否认可。
羊舍一夕
——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
一、夜晚
火车过来了。
“216!往北京的上行车。”老九说。
于是他们放下手里的工作,一起听火车。老九和小吕都好像看见: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汽,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铮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
这些,老九和小吕都太熟悉了。夏天,他们睡得晚,老是到路口去看火车。可现在是冬天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小吕想象,灯光一定会从树墙子的枝叶空隙处漏进来,落到果园的地面上来吧。可能!他想象着那灯光映在大梨树地间作的葱地里,照着一地的大葱蓬松的,干的,发白的叶子……
车轮的声音逐渐模糊成为一片,像刮过一阵大风一样,过去了。
“十点四十七。”老九说。老九在附近山头上放了好几年羊了,他知道每一趟火车的时刻。
留孩说:“贵甲哥怎么还不回来?”
老九说:“他又排戏去了,一定回来得晚。”
小吕说:“这是什么奶哥!奶弟来了也不陪着,昨天是找羊,今天又去排戏!”
留孩说:“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常在一起了。”
老九说:“咱们烧山药吃,一边说话,一边等他。小吕,不是还有一包高山顶吗?坐上!外屋缸里还有没有水?”
“有!”
于是三个人一起动手:小吕拿沙锅舀了多半锅水,抓起一把高山顶来撮在里面。这是老九放羊时摘来的。老九从麻袋里掏山药—他们在山坡上自己种的。留孩把炉子通了通,又加了点煤。
屋里一顺排了五张木床,联成一个大炕。一张是张士林的,他到狼山给场里去买果树苗子去了。隔壁还有一间小屋,锅灶俱全,是老羊倌住的。老羊倌请了假,看他的孙子去了。今天这里只剩下四个孩子:他们三个,和那个正在排戏的。
屋里有一盏自造的煤油灯—老九用墨水瓶子改造的,一个炉子。
外边还有一间空屋,是个农具仓库,放着硫铵、石灰、DDT、铁桶、木叉、喷雾器……外屋门插着。门外,右边是羊圈,里边卧着四百只羊;前边是果园,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点葱,还有一堆没有窖好的蔓菁。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外边是无边的昏黑。方圆左近,就只有这个半山坡上有一点点亮光。夜,正在深浓起来。
二、小吕
小吕是果园的小工。这孩子长得清清秀秀的。原在本堡念小学。念到六年级了,忽然跟他爹说不想念了,要到农场做活去。他爹想:农场里能学技术,也能学文化,就同意了。后来才知道,他还有个心思。他有个哥哥,在念高中,还有个妹妹,也在上学。他爹在一个医院里当炊事员。他见他爹张罗着给他们交费,买书,有时要去跟工会借钱,他就决定了:我去作活,这样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我哥能够念多高就让他念多高。
这样,他就到农场里来做活了。他用一个牙刷把子,截断了,一头磨平,刻了一个小手章:吕志国。每回领了工资,除了伙食、零用(买个学习本,配两节电池……),全部交给他爹。有一次,不知怎么弄的(其实是因为他从场里给家里买了不少东西:菜,果子),拿回去的只有一块五毛钱。他爹接过来,笑笑说:
“这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吗?”
吕志国的脸红了。他知道他偶然跟同志们说过的话传到他爹那里去了。他爹并不是责怪他,这句嘲笑的话里含着疼爱。他爹想:困难是有一点的,哪里就过不去呢?这孩子!究竟走怎样一条路好:继续上学?还是让他在这个农场里长大起来?
小吕已经在农场里长大起来了。在菜园干了半年,后来调到果园,也都半年了。
在菜园里,他干得不坏,组长说他学得很快,就是有点贪玩。调他来果园时,征求过他本人的意见,他像一个成年的大工一样,很爽快地说:“行!在哪里干活还不是一样。”乍一到果园时,他什么都不摸头,不大插得上手,有点别扭。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原来果园对他说来是个更合适的地方。果园里有许多活,大工来做有点窝工,一般女工又做不了,正需要一个伶俐的小工。登上高凳,爬上树顶,绑老架的葡萄条,果树摘心,套纸袋,捉金龟子,用一个小铁丝钩疏虫果,接了长长的竿子喷射天蓝色的波尔多液……在明丽的阳光和葱茏的绿叶当中做这些事,既是严肃的工作,又是轻松的游戏,既“起了作用”,又很好玩,实在叫人快乐。这样的活,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不论在身体上、情绪上,都非常相投。
小吕很快就对果园的角角落落都熟悉了。他知道所有果木品种的名字:金冠、黄奎、元帅、国光、红玉、祝;烟台梨、明月、二十世纪、蜜肠、日面红、秋梨、鸭梨、木头梨;白香蕉、柔丁香、老虎眼、大粒白、秋紫、金铃、玫瑰香、沙巴尔、黑汗、巴勒斯坦、白拿破仑……而且准确地知道每一棵果树的位置。有时组长给一个调来不久的工人布置一件工作,一下子不容易说清那地方,小吕在旁边,就说:“去!小吕,你带他去,告诉他!”小吕有一件大红的球衣,干活时他喜欢把外面的衣裳脱去,于是,在果园里就经常看见通红的一团,轻快地、兴冲冲地弹跳出没于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丛绿之中,惹得过路的人看了,眼睛里也不由得漾出笑意,觉得天色也明朗,风吹得也舒服。
小吕这就真算是果园的人了。他一回家就是说他的果园。他娘、他妹妹都知道,果园有了多少年了,有多少棵树,单葡萄就有八十多种,好多都是外国来的。葡萄还给毛主席送去过。有个大干部要路过这里,毛主席跟他说:“你要过沙岭子,那里葡萄很好啊!”毛主席都知道的。果园里有些什么人,她们也都清清楚楚的了,大老张、二老张、大老刘、陈素花、恽美兰……还有个张士林!连这些人的家里的情形,他们有什么能耐,她们也都明明白白。连他爹对果园熟悉得也不下于他所在的医院了。他爹还特为上农场来看过他儿子常常叨念的那个年轻人张士林。他哥放暑假回来,第二天,他就拉他哥爬到孤山顶上去,指给他哥看:
“你看,你看!我们的果园多好看!一行一行的果树,一架一架的葡萄,整整齐齐,那么大一片,就跟画报上的一样,电影上的一样!”
小吕原来在家里住。七月,果子大起来了,需要有人下夜护秋。组长照例开个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小吕说,他愿意搬来住。一来夏天到秋天是果园最好的时候。满树满挂的果子,都着了色,发出香气,弄得果园的空气都是甜甜的,闻着都醉人。这时节小吕总是那么兴奋,话也多,说话的声音也大,好像家里在办喜事似的。二来是,下夜,睡在窝棚里,铺着稻草,星星,又大又蓝的天,野兔子窜来窜去,鸹鸹悠叫,还可能有狼!这非常有趣。张士林曾经笑他:“这小子,浪漫主义!”还有,搬过来,他可以和张士林在一起,日夜都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