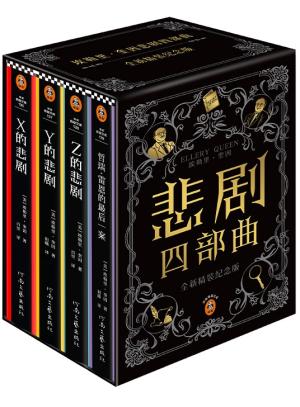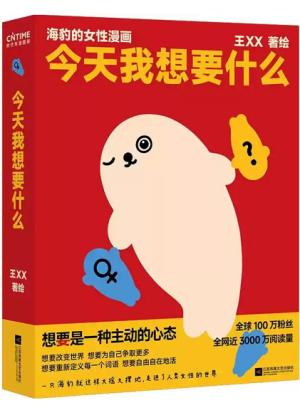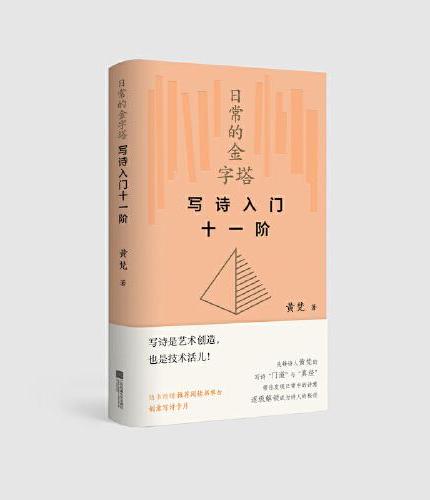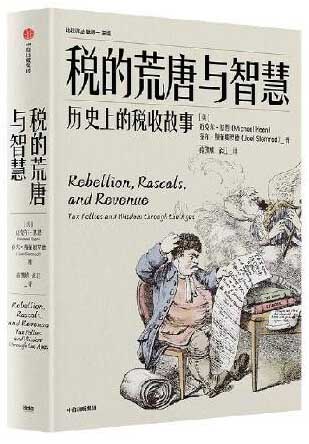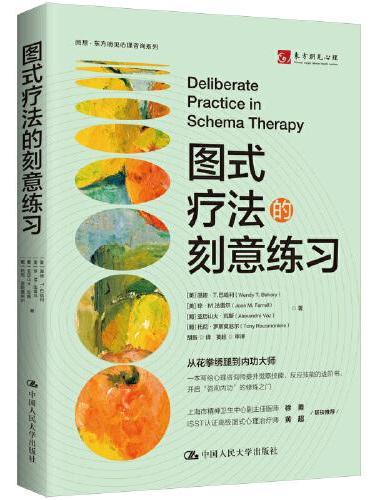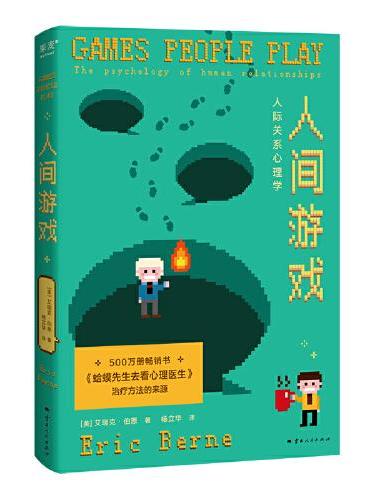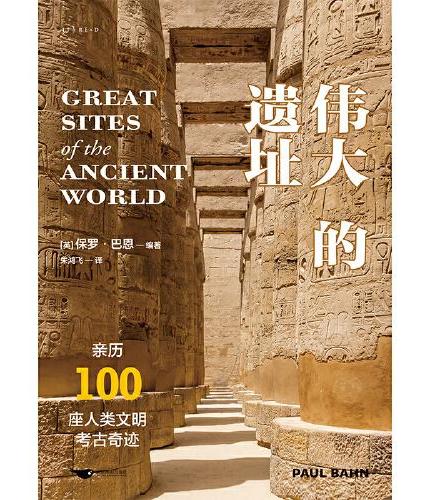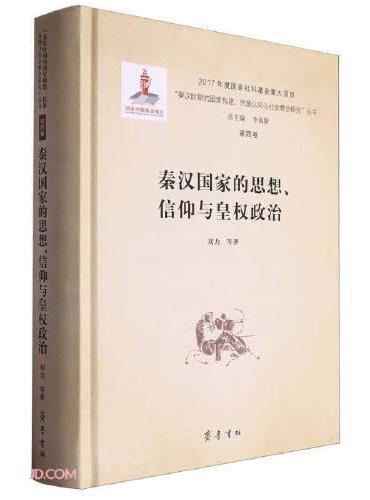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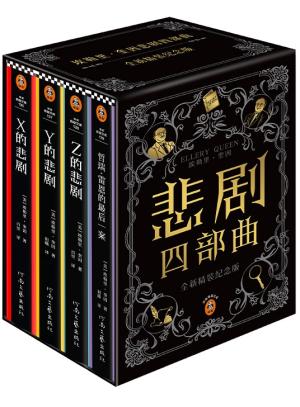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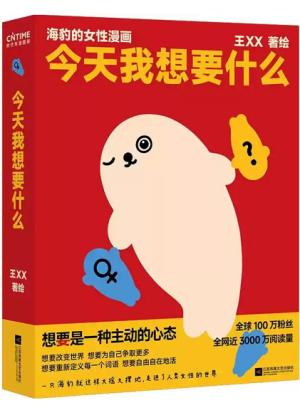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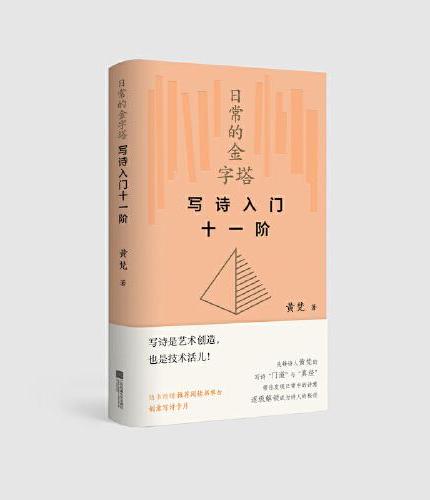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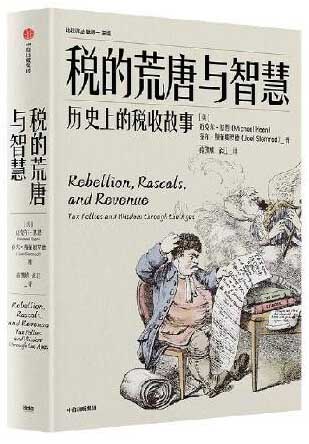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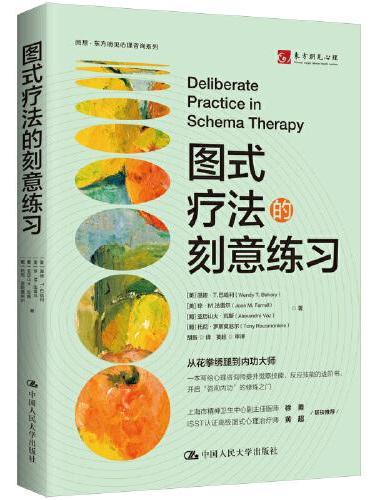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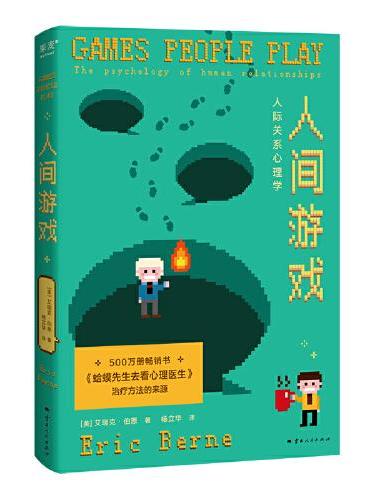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HK$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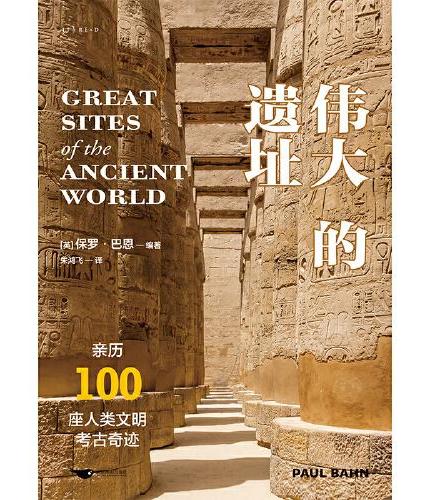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HK$
2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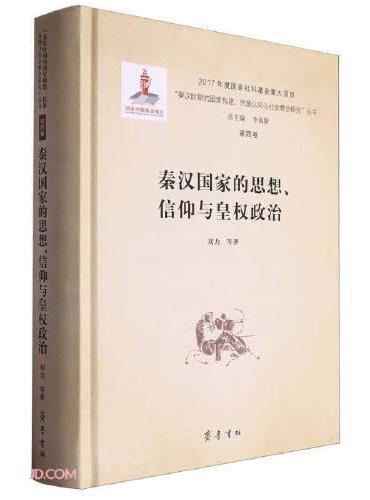
《
秦汉国家的思想、信仰与皇权政治
》
售價:HK$
215.6
|
| 編輯推薦: |
马永霞忧郁的眼神里,深藏生活与岁月的闪电和流云。她目击命运对人的镂空与重塑,把怀念与感伤同时刻画在无人知晓的黑夜四壁。“天空还是蓝的。春天/正以一棵树倒下的速度铺开/四周,一下子空阔了许多”就像一棵桑树的守望、等待和奉献,她的诗句里,闪烁人类情感中脆弱的甜蜜与旷大的悲悯。她甘愿从善如流,并且坚信,与手中散落的桑葚、星辰与露珠一道,迎来一个比桑林的阴影面积更大的黎明。
——堆 雪
|
| 內容簡介: |
|
《桑树下的迁徙》收入新疆回族女诗人马永霞关于故乡,尤其是对出生并成长的鄯善县多民族聚集区的生命景象和具体生活场景的抒写,传递出回族家庭、亲人、乡邻和族群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反应。作者以鄯善县最具人文和地域特点的“桑树”为切入点,用诗歌方式关注社会变迁,尤其是将鄯善人群的生活,投射于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之中,进行观照和思考,从而呈现作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认识,展示出国家在改革开放深入,经济文化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无数的年轻人离开家园涌入城市寻求美好的生活等方面的诸多变化,以期达到反映时代的文学站位。在书稿中,作者还力图通过记录时代迁徙、民族变迁、人群心灵嬗变,将乡村的纯真,乡村的坚守与城市变迁进行对比,表达出对具体生活的思考和关注,弘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源,不要忘记那些默默坚守在乡村的人们。
|
| 關於作者: |
|
马永霞,回族,1989 年生于新疆鄯善。 系新疆作协理事、会员,乌鲁木齐市作协理事。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化润疆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当代》《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西部》《民族文汇》《回族文学》等刊。现居乌鲁木齐。
|
| 目錄:
|
桑树的指向和证词 王族 /1
第一辑 请用一棵桑树纪念我
出生地 /3
暗光里的亲人 /4
桑树下的迁徙 /5
请用一棵桑树纪念我 /6
重返 /7
等一年过到秋日 /8
一颗会开花的石头 /9
雪重建了大地 /10
你能为我带路吗 /11
试着飞行 /12
最后一场纪念 /13
荣光 /14
一生 /15
院里的光阴 /16
葡萄园里除了葡萄还有什么 /18
故乡凌晨四点的鸟鸣 /19
成长的视野 /20
学习沉默 /22
这世间一定有一个孩子让你流泪 /23
那些受命于人的云 /24
鸟儿在高处 /25
三只飞过乌拉泊的白鸟 /26
搏斗 /28
漫长的冬天 /29
拥有 /30
无畏的告别 /31
偷窥灵魂 /32
热烈而随风自由 /34
过往寄回的信件,请查收 /35
关于一只流浪狗 /37
猫 /38
记一位修鞋的老人 /39
第二辑 验证
身世 /43
远逝的诗人 /44
语言的镰刀 /45
钉子 /46
用语言填满美 /47
星光的无字歌与诗 /48
十行诗 /49
验证 /50
我的河 /51
病症 /52
生命的输赢仗 /55
界限 /56
合页 /57
大隐之人 /58
冬天的声音 /59
等待时间淹没的老屋 /60
给M的情歌 /61
致R.卡佛 /62
梦想家 /64
妹妹 /65
苍老的等待 /66
让阳光来敲门 /68
第三辑 你是谁
爱 /71
索取 /72
竖琴 /73
她回来了,她没有回来 /74
你是谁 /77
等 /78
扮演者 /80
我与矛盾的辩证关系 /81
孤独 /82
创造遗忘 /83
一个有温度的名字 /84
自私 /86
在山顶在风中 /88
调整 /90
空白的擦肩而逝 /91
风筝和看客 /92
状态 /93
谁得到了整个世界 /95
“无我”之殇 /97
虚构的时光 /98
在人间 /99
时间吝啬者 /100
寻觅 /102
有时候 /103
镜子 /104
春醒 /106
明镜 /107
避风港 /108
后记——记忆、变迁与归宿 /109
|
| 內容試閱:
|
桑树的指向和证词
王 族
从历史和现实境况而言,桑树都是极富诗意和梦幻般的植物。桑树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曾留下古代东国公主暗传蚕种的典故,亦有东汉刘秀在生命危急之际因桑葚得以活命的事件,还有于阗王国的丝绸与高昌(今吐鲁番)以物易物的交流,都让桑树在发黄的史册中散发出光芒,使桑树与人类命运的结合,以熠熠生光方式震古烁今。
那么,在素有“火洲”之称,年降水量极为有限、植被极难生长存活的吐鲁番,桑树与诗歌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对本诗集作者马永霞的出生地吐鲁番鄯善县来说,桑树又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它在诗人马永霞眼里,又具有怎样的生命和使命召唤,促使马永霞把“桑树”作为吟咏意象一再抒写,这里面蕴含着怎样的关系?在诗集第二辑篇章页,马永霞引用的诗句,或多或少是一种印证:
在吐鲁番盆地,北风
会把一个人的脸雕刻得更加干净
西北腹地,空气则潜藏得很深
代替它流动的是羊群和阳光
或许,地域问题与诗歌没有多大关系,它可能更适合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范畴。如何归置,则取决于个体(思考者)的出发角度,或者如何在精神方面进行取向。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有一个对话,池田大作问汤因比,假如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你愿意让自己出生在哪里?汤因比回答,如果真的可以选择,我愿意让自己出生在西域时期的塔里木盆地,因为开启西域历史的钥匙就遗落在那里。汤因比假设的出生地,自古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交汇,形成璀璨夺目的丝绸之路文明,为东方丝绸走向西方、西方瓜果器皿走向东方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历史犹如深邃的眼眸,不论谁与它对视都会被其摄魂吸魄,陷入厚重的时间长河中不可自拔。这也就是当下诗人如何观望历史,如何衡量地域或出生地对自我(诗歌写作)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或制约的关键所在。
吐鲁番盆地的桑树,无论是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马永霞的具体生活场景里,都有言之不尽的深远意境。因此,她的诗歌相比于历史或学术研究,就多了一份灵动和自由优势。比如《索取》:
你的眼睛
走不出我的眼睛
它们夺走我,把我放在
行走在沙漠的骆驼背上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雨会一直下在我的沉默里
现在,我只想说
请离开我的视线
那样,我会一直寻找你
那样,你会一直看着我
马永霞的诗歌,大致就给人一种既有桑树作为历史之物,在她的成长中成为具体指向,又有颇为深刻的个体生命的展示,让人觉得她的诗的出处,犹如庞大的桑树一样具有深远的根源。作品的根源,无论在小说、散文和诗歌中,都显得尤为重要。它会让诗歌和诗人呈现出可信可靠的信息,也就是说一位诗人写下的诗句,一定在字词之间潜藏着某些确切的影子——生命、家族、故乡、精神、灵魂、记忆、怜悯等,不一而足。有了这些诗意幻化中的具体物象,会让阅读者寻觅到诗人从哪里来,借以诗歌表达要到哪里去。
读马永霞的诗歌,最直接的感觉是,她诗歌的生活亮色和气息会扑面而来,让人感到无论快乐还是痛苦,都犹如正在呼啸的狂风骤雨,在苍茫大地上恣肆旋转,把人世生生不息的力量,听命或完成于使命和责任。犹记得在吐鲁番地区鄯善县的吐峪沟村,曾见到一群老人成排坐在桑树下晒太阳,仔细一看便发现了有趣的一面,他们严格按照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顺序依次而坐,绝不打乱年龄而乱坐。他们就那样坐在桑树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什么,太阳照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显得安然从容,怡然自得。在吐峪沟的另一户人家门口,每到用餐时间,便有一位老人从大门里出来,揪住桑树枝条捋下桑葚,吃上一阵后心满意足归去。老人因年迈吃不了多少东西,每顿吃桑葚即可解决。这样的具体场景或生存景象,在马永霞的诗中比比皆是,她敏感地将其抓住,写出了她体验和感触到的诗歌。譬如《桑树下的迁徙》:
古老的桑树下
一位老人头枕树荫
一汪岁月的山泉
流经他正午的梦香
我看到这片失落的文明
还有山坡上层层叠叠的灵屋
正以另一种形式繁衍——
生者无声无息
亡者雀跃不已
同样的诗歌还有《暗光里的亲人》,对桑树的贴近则更加确切,并呈现出“人在桑树下”的具体生活,亦将人归结为对命运安排的思考,所见所闻已不是昔日记忆,而是历经岁月蹉跎后的沉默和厚重,并从中找到生存于此的人群(也可视为诗人自己),其精神支柱和世界形态合二为一的神秘密码。在这一刻,诗人的目光落到了实处,“出生地”或者“故乡”不再是符号或名词,而是沉淀于内心的宁静湖泊,在于无声处涌现出生命激流:
当她归来,桑树
还没有结果。红桑葚,白桑葚
她不知道,已被私下买卖
巷口打馕的年轻师傅
如今已经老了。他依旧
为众多来往的人
制作香喷喷的馕
当她归来,看见一棵棵桑树
已被人砍掉。晌午的巷口
正飘出新鲜馕饼的味道
天空还是蓝的。春天
正以一棵树倒下的速度铺开
四周,一下子空阔了许多
从一棵桑树出发的并非只是人生,也许还有精神和心灵的不自觉漂泊。马永霞诗歌中的桑树,虽然很明显地附着于吐鲁番这一具体地域,但却不是单一的依附,相反却更多地呈现出精神与外界(世界)撞碰后的火花迸溅,让人不仅看到诗人的阵痛,亦看到世界的复杂和秘不示人的纠结。这时候的诗人,因为难舍近在咫尺的心灵渴望,总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故乡—心灵—外界”的繁复扭结之中,目光为之不适,身体为之隐痛,而生命之甘苦或个中滋味,却犹如桑树上慢慢升高的月亮,越加皎洁反而越加遥远。此时唯一青睐诗人或光顾于其内心的声音,一定是犹如喃喃自语或若有若无的诗句。写作,是此时此刻的诗人获得救赎的唯一方式,即使其诗意犹如精灵一样一闪即逝,但给诗人带来的慰悦感仍然是别的事物无法替代的。
但即便如此,马永霞仍然在诗中谨慎地选择了告别。她知道,任何一种事物都会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必然存在“再出发”,或者迟早会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与自己的命运重新相遇,所以,她小心翼翼地把故乡作为出发地,开始了一种观望。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痛苦这把刀子,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生命新的水源。田野又是开花,但已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因为从阵痛和裂变中出发的马永霞,身上明显附带着难以割舍的根源(也许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割舍)。这样的边走边想,让她犹如听到很多声音,在倾听和感念的绵密交织中,慢慢在心灵中感受到了慰勉。在《试着飞行》一诗中,这种“旧我—嬗变—新生”的心灵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没经过那样的陡坡
刹车失灵的自行车上
我借着惯性,完成了一次极速俯冲
在惊心动魄中实现了飞翔的梦想
我曾骑在父亲的脖颈
在一段平路上有过类似的冲刺
父亲,你是否也借爷爷的肩膀
有过同样的飞翔?你们不用自行车
而是用速度更慢的架子车
再比如这首《学习沉默》,亦是诗人在命运变化下的阵痛体验。有了这样的阵痛,生命便变得越来越具体,其内心充满强大的自信和安全感。亲人是上帝安排的镜子,从对方身上可以看到影射自己的具体信息。这首诗既有马永霞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又有对亲人的理解和宽容,在她看来,任何时候的生存都有意义,因为不论轻松或者沉重,其实都是对生活的屈从或接纳。人活着,又有谁不在这种情况中挣扎和沉浮:
儿时,为了将黄昏拥入怀中
我爬上后院的桑树
与桑叶一起被风吹
黄昏一直沉默不语
我将沉默交给黄昏
小小的沉默,随母亲在
清贫而富足的锅里沸腾
后来,我见过众多沉默
见过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孤儿
在眼泪中的沉默
见过女人沉陷在眉睫上的沉默
见过大千世界的沉默
而我,在学习母亲
那样沉默,那样从容
马永霞的这部诗集中的作品,给人总体的感觉是扩展开了“出发—观照—思考”的精神嬗变过程,从中也可看出她的成长或者为成长付出的代价。一个人走得再远,遭遇的欢乐或痛苦再多,都会被世界(命运)刻画成心灵上的生命年轮,经过岁月打磨之后,最终会变成与诗人暗自对应的密码,并孕育诸多感悟和体会,让诗人不知不觉写下诗歌。比如《三只飞过乌拉泊的白鸟》:
当布谷鸟从树林里出发
当六月的秧苗
等到蓝天和水田的好时光
金灿灿的金鸡菊和露珠
敲打出一个个金盘
潜心聆听,总有一只寂静的鸟儿
每天都会戛然而止
鸣叫的鸟,沉默的鸟
更像小榆树在金色倒影里的
流动,或者不流动
我曾经以为那是明亮的光
我曾经以为光不会有倒影
飞过乌拉泊的三只白鸟
不认识的鸟更像是鸟
它们不曾存在
我无法表述它们和一只乌鸦的区别
无法区别芦苇的叶子
低垂向水面的速度
一个用诗也无法捕捉的清晨
这么快地离开了我
从故乡出发的马永霞,在出发的一刻也许就已经在回归。只是她出发时在凝视世界,而回归时却在凝视自己。读马永霞的诗歌,得到的收获或启示便是如此。马永霞的所见、所思、所感,都有确切而牢固的根源,无论是抒情还是反思,都格外引人注目。马永霞的诗歌凸现出强烈的“我手写我心”的特点,她有生活,于是就有了这些诗歌。她将精神向度和心灵深度统一到了和谐的抒写之中,突出了诗歌艺术效果,亦让她的出生地、故乡和桑树,都在这部诗集中变成了证词。这种证词,是诗人与诗歌相遇时紧紧抓住的光束,历久弥坚,永远闪烁光芒。
2024年7月7日于乌鲁木齐
第一辑
请用一棵桑树纪念我
我能记住的事情越来越少
我爱的人都已离开库木塔格沙漠
只剩下这只乌鸦
和它眼里落日的苍黄
——《无畏的告别》
出生地
当她归来,桑树
还没有结果。红桑葚,白桑葚
她不知道,已被私下买卖
巷口打馕的年轻师傅
如今已经老了。他依旧
为众多来往的人
制作香喷喷的馕
当她归来,看见一棵棵桑树
已被人砍掉。晌午的巷口
正飘出新鲜馕饼的味道
天空还是蓝的。春天
正以一棵树倒下的速度铺开
四周,一下子空阔了许多
《当代》2024年第1期
暗光里的亲人
底色越来越淡
一位老人带走了黑夜
奔跑的猫,无处栖息
无法调低目光的亮度
就像无法拉长影子的长度
影子也会燃尽
像多年前,我们围坐过的篝火
火光里,有我们的亲人
黑暗里,有我们的亲人
桑树下的迁徙
古老的桑树下
一位老人头枕树荫
一汪岁月的山泉
流经他正午的梦香
我看到这片失落的文明
还有山坡上层层叠叠的灵屋
正以另一种形式繁衍——
生者无声无息
亡者雀跃不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