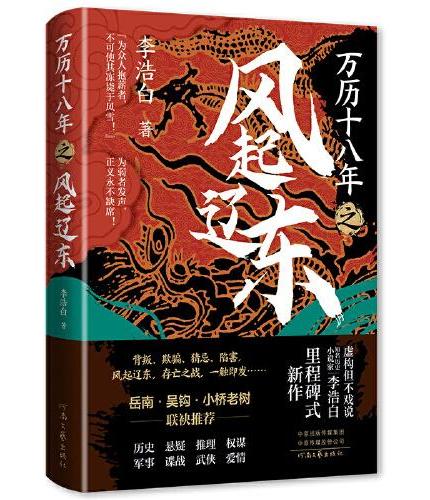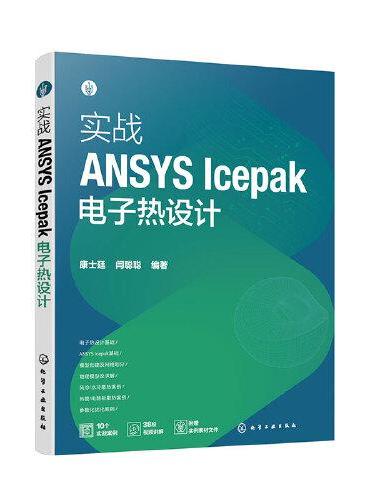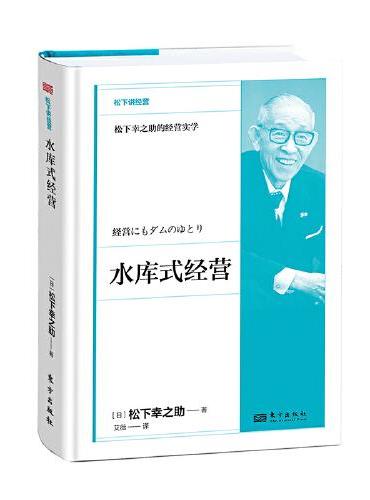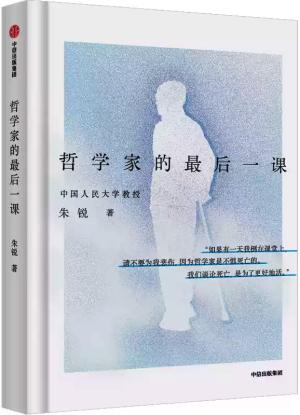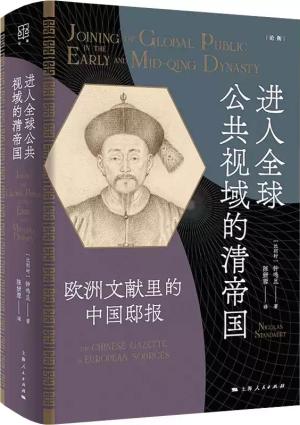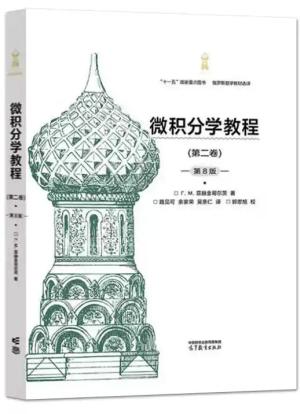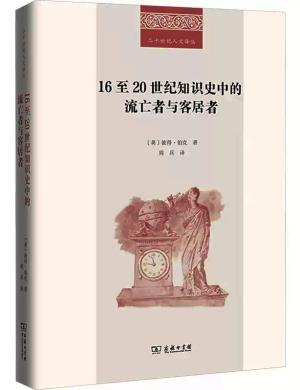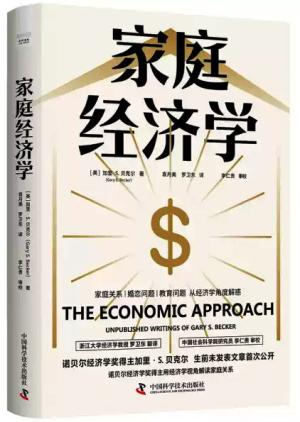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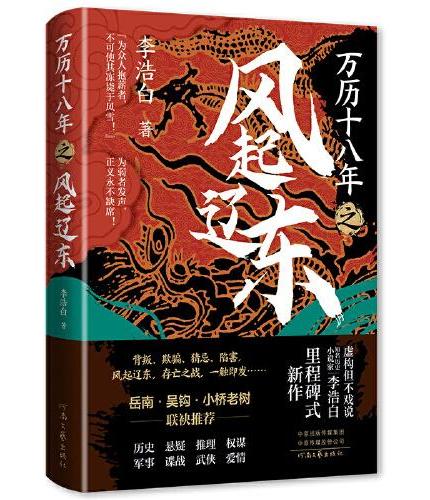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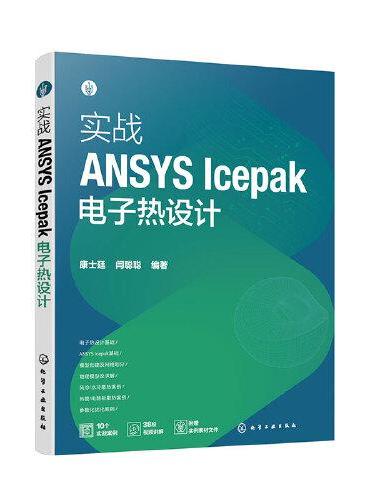
《
实战ANSYS Icepak电子热设计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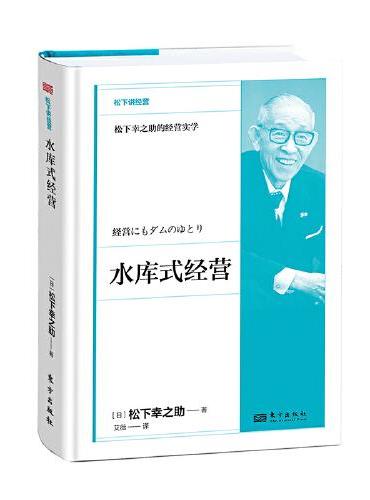
《
水库式经营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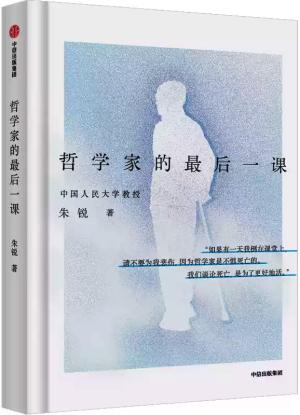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HK$
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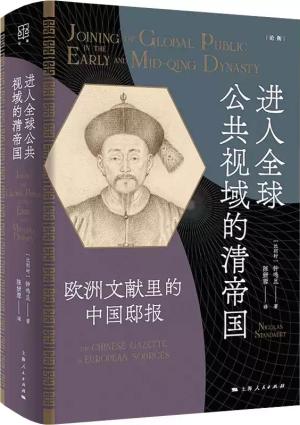
《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
售價:HK$
1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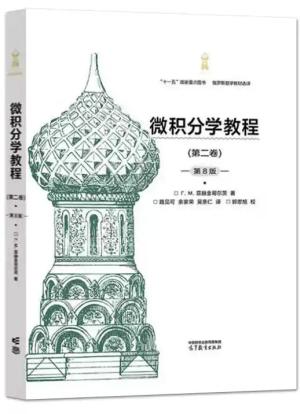
《
微积分学教程(第二卷)(第8版)
》
售價:HK$
1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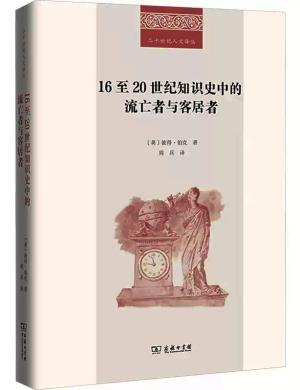
《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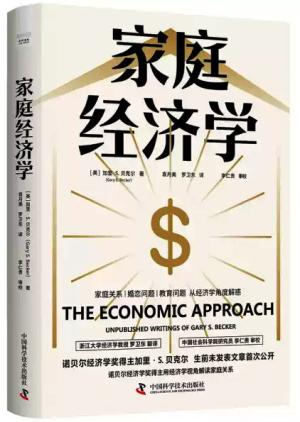
《
家庭经济学: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家庭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S. 贝克尔全新力作)
》
售價:HK$
81.4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课程与教学论新问题研究丛书”之一,作者从兴趣价值论的视角,检视了课程领域两种不同的关于课程知识价值的设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以及“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剖析了其背后所隐藏的客体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谬误以及在这样的课程知识价值观谬误下学生与知识关系的异化。通过对知识、价值以及知识价值等概念的重新界定,本书确立了关于课程知识价值的一种新的提问方式——“什么兴趣指向的知识最有价值”,并试图构建一个基于学生兴趣的课程知识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课程知识的选择、组织与呈现都应基于学生的兴趣,依循学生兴趣发展的规律,学生在与感兴趣的知识互动中生成个人知识,最终实现精神的充盈和人生的完满。这对当前的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 關於作者: |
|
邓素文,湖南株洲攸县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分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课程论分会理事。研究领域为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发展等。在《教师教育研究》《现代大学教育》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
|
| 目錄:
|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本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第一章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第一节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科学知识抑或人文知识?
第二节 科学知识作为最有价值的知识的意义及其矛盾和困境
第二章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第一节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出场与“学生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隐现
第二节 “学生的知识最有价值”的诘问与反思
第三章 什么兴趣指向的知识最有价值——课程知识价值观的转向
第一节 知识、价值的重新释义
第二节 走向兴趣取向的课程知识价值观
第四章 什么兴趣指向的知识最有价值——历史上的兴趣课程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赫尔巴特的“多方面兴趣说”及其评析
第二节 杜威的兴趣说及其评析
第三节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儿童兴趣的观照及其误区
第五章 什么兴趣指向的知识最有价值——课程知识的选择
第一节 谁来选择——课程知识选择的主体
第二节 如何选择——学生兴趣的类型与课程知识的选择
第三节 如何选择——学生兴趣的发展与课程知识的选择
第六章 课程知识价值的实现
第一节 呈现更有趣的教材文本知识
第二节 兴趣作为教学的第一原则
参考文献
后记
|
| 內容試閱:
|
课程知识的价值问题是一个引发颇多争议的话题。从历史的线索来看,人们关于知识价值的设问方式存在着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变迁。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在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发生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斯宾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科学知识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中后叶,西方和我国都开始将科学知识引入课程领域。这不仅顺应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也在课程本体层面促进了教学内容发展与教学方法革新。但是,随着科学知识在课程中霸权地位的建立,教学也就逐渐蜕变为“只见知识不见人” “以知识遮蔽人”的教学。从知识价值观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正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种设问方式所蕴含的客观主义知识价值观,最终导致了“人”在教学中失落的命运。
随着对知识的主体性以及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揭示,人们对知识价值的设问方式继而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转向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从其提出的背景来看,人们(以批判课程理论和新教育社会学为主)最初的意图在于揭示课程知识选择过程中权力冲突的实然状态,但逐渐地被人们用以思考应然的知识选择。在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由此出现了一种“学生的知识最有价值”的呼声。从其具体表现来看,这种知识价值观凸显了学生创造知识的权利,体现了将学生确立为教育主体的愿望和诉求。但通过对其关于学生、知识等概念的分析又可以看出,它最终走向了“以学生遮蔽知识”的困境。分析其知识价值观则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完全从主体角度出发来衡量知识价值的观念,其实质是相对主义的知识价值观。
通过对知识、价值以及知识价值等概念的重新认识和界定,一种新的提问方式——“什么兴趣指向的知识最有价值”也就孕育起来。这种提问方式,也就预示着“兴趣”是进行知识选择的主要依据。学生始终是知识价值的主体,但知识选择的主体却应该由学生、课程专家、学科专家、教师等组成。从个体层面考虑,兴趣有自然兴趣与文化兴趣之分,知识的选择应基于自然兴趣但最终要以文化兴趣为目的,而知识的选择应尽力避免个体兴趣的冲突;从群体的角度来考虑,知识的选择则既要注意学生兴趣的差异性,又要注意学生兴趣的普遍性。一种“生态式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就应运而生。
事实上,并不是今天我们才意识到需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来考虑课程知识。强调兴趣、自由、目前需要等有着从古希腊教育开始的漫长的历史。从历史上看,第一次大张旗鼓地提出“兴趣”应被视为学习的原则和目的的是卢梭。而赫尔巴特第一次系统地从兴趣出发,将课程设置建立在学生多方面的兴趣的基础上。自赫尔巴特之后,对学生的兴趣、需要给予极大重视和关注的当属杜威了。杜威的《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一书对兴趣,以及兴趣与努力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和论述,阐明了兴趣与努力的辩证关系。这是人们对于构建兴趣课程从理论上做出的努力。在课程实践中对于学生兴趣的发扬最典型的例子则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凸显的对学生兴趣、需要等的关注也总是以不同的提法出现在后来的教育改革中。虽然如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学生兴趣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危险,甚至最终演变成一种极端的儿童中心主义。
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立足于兴趣取向的课程知识价值观,我们认为,正是学生兴趣的可知性、自发性和未分化性为教师、家长、课程专家以及学科专家等参与课程知识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建基于学生兴趣的分类,教师、家长、课程专家以及学科专家等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如自然兴趣和文化兴趣、相容的兴趣和冲突的兴趣,以及群体的普遍兴趣和相异兴趣等作出课程知识的选择。由于学生的兴趣总是发展变化着的,因而也要考虑从学生兴趣发展的角度(如根据学生兴趣发展的精细化模式、学生兴趣发展的通道模式、学生兴趣发展的交叠模式等)对课程知识进行选择。
在经过课程知识的选择后,课程知识的价值要真正实现,实际上还需要将课程知识转化为教材知识,并通过教学将教材知识转化为学生的个人知识。这就是说,课程知识的价值的真正实现只有在其既是学生认识的对象,也是学生兴趣的对象时。于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教材文本知识的表达、教材文本知识的编排、知识内容本身等出发呈现更有趣的教材文本知识是必要的。而在教学中,把兴趣作为教学的第一原则也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们需要创设充满趣味的学习环境,构建“行动识知”的学习方式,以帮助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在知识学习与其生活之间建立联系,把知识学习与其人生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互关联起来,帮助他们欣赏知识的价值,并从知识的纯粹消费者转化为知识的创造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