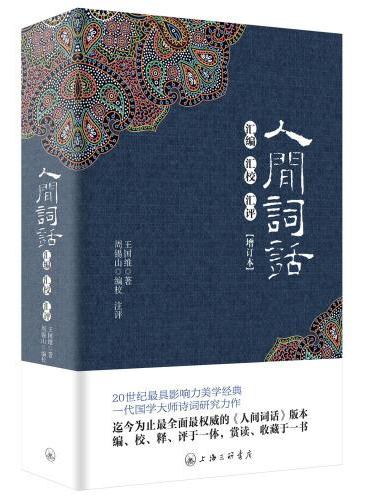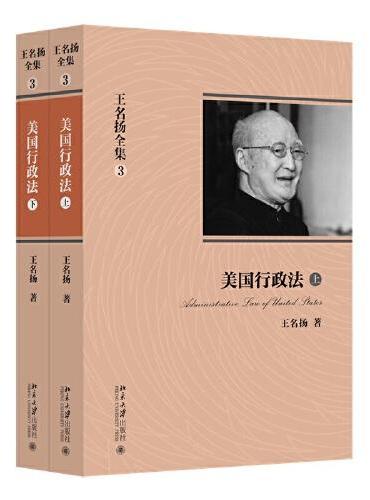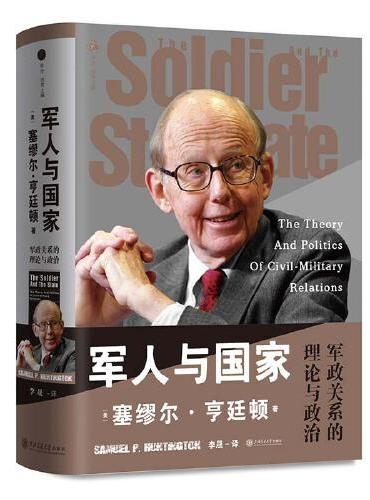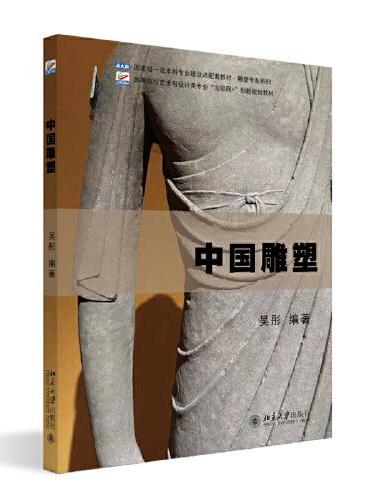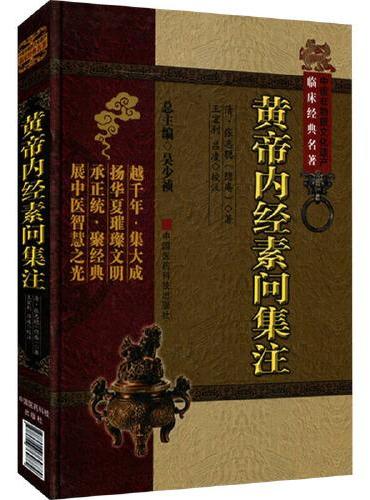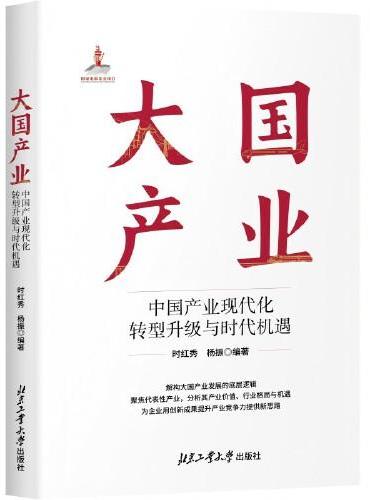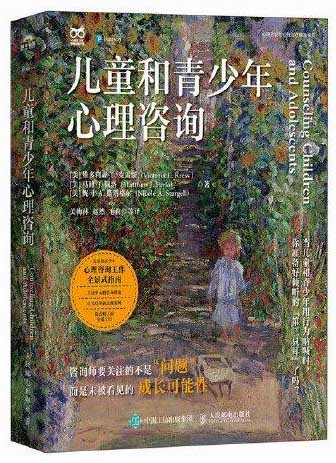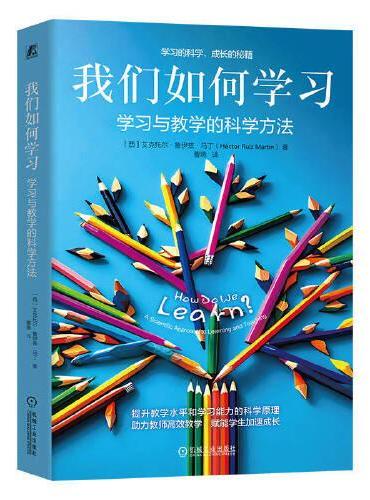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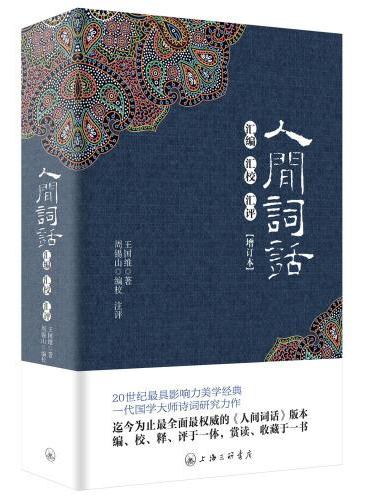
《
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新)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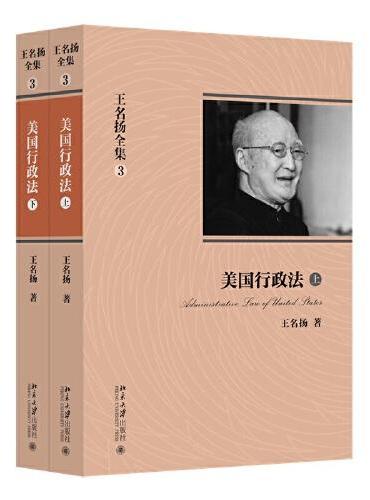
《
王名扬全集:美国行政法(上下) 王名扬老先生行政法三部曲之一
》
售價:HK$
1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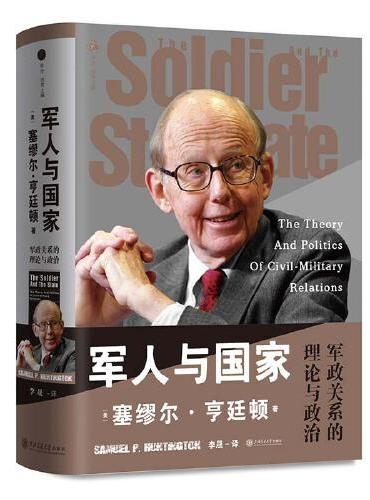
《
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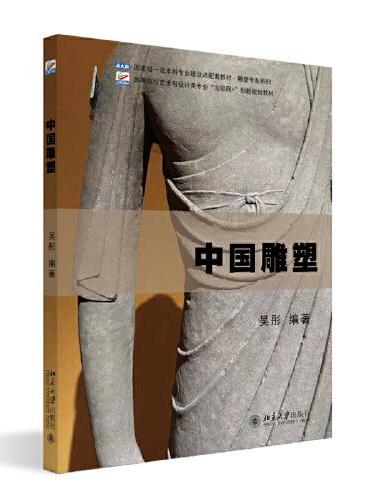
《
中国雕塑 高等院校艺术与设计类专业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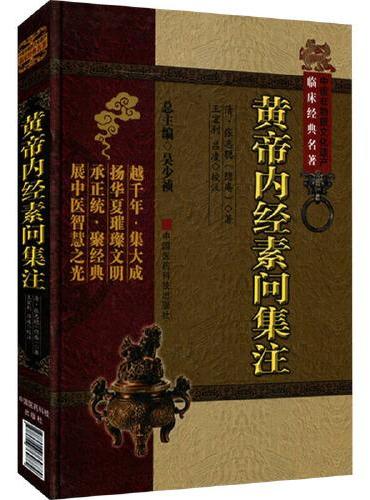
《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
售價:HK$
6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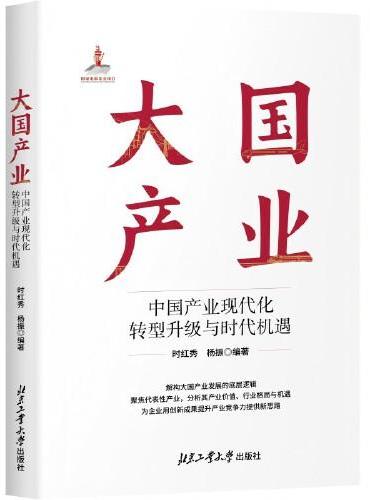
《
大国产业—中国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与时代机遇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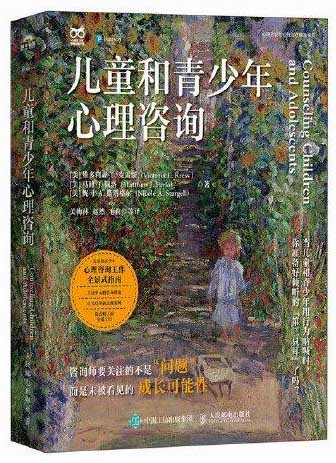
《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询
》
售價:HK$
1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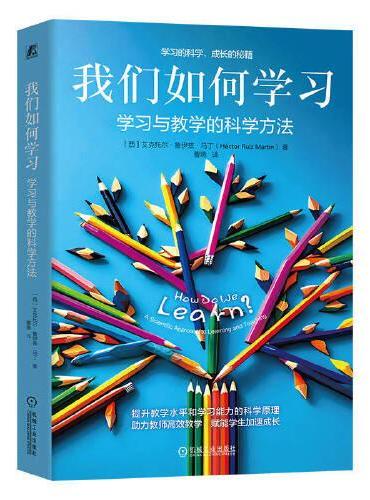
《
我们如何学习:学习与教学的科学方法 (西班牙)艾克托尔·鲁伊兹·马丁
》
售價:HK$
86.9
|
| 內容簡介: |
|
从丝绸之路、丝路精神及丝路共有认知区间等维度廓清丝路学的形成,从西方学术霸权、丝路学三大学派及中国丝路学困境等维度剖析丝路学的发展,以及从重释核心议题、探明西域议题所烙霸权胎记及“一带一路”引发全球丝路研究热等维度探究丝路学的转型,旨在彰显“一带一路”这一重塑“中国与世界古今丝路关系”的新实践,为全球丝路学转型与中国丝路学振兴带来的新机遇,使中国学者在中外共研“一带一路”新态势中快速成长,并在助力全球丝路学由西方化向全球性蜕变中维护了“一带一路”首倡国的学术话语权。
|
| 關於作者: |
|
马丽蓉,复旦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上外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政治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导/硕导、区域国别研究方向博士后合作导师、《新丝路学刊》主编暨教育bu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阿友好协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会理事等,荣获“中国高校‘一带一路’影响力人物”称号、“天山学者”特聘教授暨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等。主要致力于国际关系、丝路学、区域国别及人文外交等研究。已出访20多个国家,开展访学、参会、办会、调研等学术活动。发表中英文权威、核心期刊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主持课题近30项,26份内参报告被采用,获优秀学术成果奖或优秀内参奖25项等。本人所主讲的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中阿文明交往史”,已在“爱课网”等平台播放,成为特色鲜明的丝路学课程之一。
|
| 目錄:
|
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3)
第一节中国丝路外交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评估(3)
第二节中外丝路交往中软治理的经略之策(24)
第三节建构丝路人文共同体价值共识的案例分析(37)
第二章丝路精神与“一带一路”软环境研究(49)
第一节丝路多元文明交往与丝路精神的形成(49)
第二节“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应对(58)
第三节“一带一路”人文共同体构建案例分析(68)
第三章丝路共有认知区间与全球丝路学的形成(80)
第一节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互构性研究(80)
第二节中外共研丝路所致统一“认知区间”剖析(87)
第三节丝路学百年聚焦核心议题的研究范式分析(95)
中篇中外学派构建与丝路学的发展
第四章西方大国学术霸权与中国丝路学再出发(109)
第一节文明对话中西方霸权话语挑战及应对研究(109)
第二节美国霸权政治中的“学术因素”案例分析(123)
第三节大国话语博弈与中国丝路学话语窘境剖析(135)
第五章多维度推进中国丝路学的学科体系建设(149)
第一节周边关系视角的中国丝路学学科体系探究(149)
第二节“一带一路”视角的中国丝路学学科体系探究(158)
第三节中外关系史视角下的中国丝路学学科体系探究(167)
第六章三大学派历史演进与全球丝路学的发展(175)
第一节丝路学三大学派的形成及其影响(175)
第二节丝路学“三化现象”的产生及其影响(189)
第三节中国丝路学派发展困境及其破解意义(208)
下篇中外研究“一带一路”与丝路学的转型
第七章“一带一路”与重释丝路学核心议题归因研究(215)
第一节“一带一路”重塑中拉人文伙伴关系案例分析(215)
第二节“一带一路”重塑中俄人文伙伴关系案例分析(230)
第三节“一带一路”与重释丝路学核心议题关联性探究(240)
第八章西方操弄西域议题抹黑“一带一路”学术溯源(251)
第一节全球安全治理视阈中的西域议题研究(251)
第二节中美战略博弈视阈中的西域议题研究(262)
第三节西方丝路学术大国操弄西域议题学术惯例演进(274)
第九章共建“一带一路”新实践与全球丝路学的转型(283)
第一节“一带一路”与“中国叙事”的时代之遇(283)
第二节“一带一路”与中国丝路学话语体系的构建(298)
第三节“一带一路”与全球丝路学转型的路径探索(309)
附录(323)
附录1:全球丝路学主要经典著作多语种文献目录辑成
(1877年—)(323)
附录2:“上外丝路学”学科建设影响力反馈信息辑要
(2016年—)(338)
后记(354)
|
| 內容試閱:
|
|
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本章尝试从丝路学的“丝绸之路”这一元概念研究范式出发,在立足中外丝路交往历史文献与现实案例基础上,通过研究中国丝路外交、中外丝路治理,以及丝路人文共同体等相关问题,旨在探讨丝绸之路影响文明交往、全球治理、国际关系等的原因、规律、路径及其意义,力求进一步探究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这一重要课题。第一节中国丝路外交的历史贡献及其影响评估一、中国丝路外交的重大贡献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大一统国家多具有“传导作用”与“和平心理”,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层的古老文明,还体现为自汉唐宋元明清至今不同时代相继涌现的大一统国家,以朝贡为主的结伴制度的“传导作用”与汉唐、元明的交友政策的“和平效应”上,并形成结伴机制与交友政策相结合的“丝路外交”。张骞出使西域之所以具有“凿空”意义,是由于他首次“开外国道”,揭开了中国古代外交的新时代,使汉帝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一划时代重大事件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崭新阶段,使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走向世界。”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此外,张骞“凿空之举”还标志着国际性朝贡制度的正式诞生,尤其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西汉政府对朝贡进行优厚回赐,使得经济利益占主导的朝贡活动异常频繁,朝贡者往来不绝,且出现了贡赐贸易,拉动了中国与东南亚、欧洲的海外贸易,从经济、人文、安全三方面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结伴外交机制。郑和的“七下西洋”壮举又使得朝贡制度达到鼎盛:在他“七下西洋”的28年外交实践中,与亚非近30个国家开展了丝路外交,并形成了丝路伙伴关系。与结伴制度相应的是对外友好政策,这在汉、唐、明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汉武帝的外施仁义、推行德治的外交政策大大提升了汉朝大一统国家的软实力,并将汉武帝德治观所构建的大一统国家形象、张骞等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形象,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所弘扬的儒家文明形象等通过丝路远播世界。作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的唐朝实施的对外政策主要包括:友善的纳贡政策、优惠的外贸政策、包容的社会政策等,这些政策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极大地推动了中外人际交往和物质交换。郑和在其外交实践中,忠实地执行了明政府用“宣德化、柔远人”的和平方式与长治久安的方针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外交政策,彰显出中国“和平外交”(和平方式、平等关系、不干涉他国内政)思想与缔结“伙伴关系”(谋求经济互惠、文明共享与丝路安全等共同利益)的努力。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寻求军事伙伴的“结伴”外交到开辟中外经济、人文交流的大通道,从郑和七下西洋“宣德化、柔远人”的“交友”外交直至“朝贡之使相望于道”的成效,以及形成于汉、发展于唐、鼎盛于明的谋求结伴的朝贡制度等,标志着由“结伴的机制(朝贡制度) 交友的政策(和平友好) 丝路意识(命运共同体)”所组成的中国特色的丝路外交的正式诞生,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起步于中国但永无终点的中国丝路外交,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等关系的探索实践中,结成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二是朝贡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但基于朝贡体系基础上的丝路体系的构建,为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一种新方向,且蕴含了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合作型的安全观,并在丝路文明交往中形成了“丝路精神”,成为丝路多元文明的共处法则。三是郑和七下西洋壮举表明,中国不仅能向世界提供丝绸等商品,还能向世界提供“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强而不霸”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和平与发展并重的“郑和文化”,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郑和将“丝绸之路”最终成就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公共产品。四是在中外上千年的丝路交往中,中国丝路外交不仅传播了商品、技术、大一统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华文明等,还形成了“贡而不朝”的朝贡制度、“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官民并举的双轨交往,以及宗教、贸易为抓手的交往模式等,更将“伙伴关系”落实到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衍生出互惠型的经济关系、合作型的安全关系、包容型的人文关系。其中,人文关系是中国丝路外交的内核、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是其两个抓手,旨在构建大一统国家形象,进而传播中华文明形象。中国丝路外交的历史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不仅对新中国外交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影响,还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着难以割断的丝路情缘,集中体现在中国丝路外交与周恩来的人民外交、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具有同构关系。周恩来对“人民外交”的贡献,在理论层面上主要包括:他的“外交为民”、文化与经济是“外交的双翼”、求同存异精神、和平共处原则,以及“外交就如交朋友”等重要论述,标明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初步确立。在实践层面上的贡献主要包括:他以私交促外交、创建了人文型的首脑外交;亲手开启了新中国夫人外交,批准成立“夫人工作小组”;指导并参与了新中国医疗外交;支持并参与了以包容促沟通的宗教外交等。周恩来所缔造的人民外交不仅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对新中国的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外交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内涵、外延、主体、特点、作用、途径和目的等诸要素分析后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具有同构性,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类外交的目标都是结伴交友,所缔结的双边关系的性质均属伙伴关系,所涉及交往领域主要包括经济、人文与安全等,且三者均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实践中所积累的“中国经验”的影响产物。二是“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结伴交友的外交制度,尤其是“贡而不朝”与“厚往薄来”为特质的朝贡体系向结伴体系的成功演变,使得中国上千年“和平发展的结伴实践已开始对美国的结盟体系产生微妙的塑造作用,美国的盟友在中国的结伴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结盟体系之间开始出现尴尬的两难选择。亚太地区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结伴体系与美国的结盟体系在竞争中比较的问题” 苏长和:《世界的结局不像好莱坞电影,中国应推行结伴外交》,引自《复旦全球治理报告2014》(2014年5月28日发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8302。(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三是“丝路外交”属于双轨外交,即由使节往来、贡赐贸易等组成的官方外交与商旅、教旅和学旅“三轨并存”的民间外交组成。周恩来界定“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人民外交即为典型的三轨外交;大国外交则是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多轨外交。四是起步于丝路上的“丝路外交”影响深远,不仅传播了由丝绸、瓷器等商品形象,四大发明等科技形象,路畅国盛的安全形象等组成的“大一统”国家形象,还传播了“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形象,且影响持久。五是三类外交均为世界提供了公共产品,包括丝绸之路、丝路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广播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目前,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由“给世界提供商品”向“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新阶段,应在“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作用”《王毅在联大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发展理念和国际作用等》, 中国新闻网,2013年9月28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3/09-28/5332996s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的具体实践中构建多元、民主的国际话语体系,并以贡献公共产品的方式深化文明交往中的价值沟通。尤须强调的是,弘扬“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新实践,力求在借鉴中国丝路外交成功经验基础上来盘活历史外交资源,使得同构性的“丝路外交”“人民外交”“大国外交”得以良性互促。这既弘扬了中国的和文化精神、彰显了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还将有助于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外“伙伴关系”而非“结盟关系”,凸显中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特殊而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二、中国丝路外交的主要影响郑和的外交实践实为中国丝路外交最具样本研究价值的典范案例,其出色的丝路外交实践影响深远,且集中体现为由“郑和崇拜”“郑和文化”及“郑和精神”构成的“郑和符号”上,使得“历史郑和”成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的“符号郑和”。而“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郑和被符号化后所能感知的基本“携带意义”又产生了“文化信码”的功效,使得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页。,并借助“郑和符号”“共享”了和合、仁爱、协和万邦的儒家文化观,劝善、戒恶、普慈的多元宗教“文化信息”,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等,并逐渐形成了郑和“符号现实”,不同程度地塑造了中外丝路文明交往的社会民意基础,助力形成丝路伙伴国家和地区间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研究发现,“郑和符号”对海丝与陆丝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首先,“郑和符号”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崇拜”(即以伊斯兰、佛学、道学为主的混合型信仰崇拜)上,主要包括:1有关郑和的寺庙印尼三宝垄三保庙、印尼雅加达的三保水厨庙、印尼井里汶的威勒斯·阿茜庙、印尼泗水的三保庙、印尼巴厘岛的郑和厨师庙、印尼泗水的郑和清真寺、印尼邦加岛的三保庙等;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宝山亭、马来西亚登嘉楼的三保公庙、马来西亚槟城的三保庙、马来西亚砂捞越的三保庙、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三保庙等;泰国大城府的三宝公庙、泰国吞府的三宝公寺(弥陀寺)、泰国北柳的三宝公佛寺等,以及菲律宾苏禄的白本头(郑和随从)庙及其茔墓、柬埔寨的三保公庙等。2有关郑和的遗迹与传说在印尼有三保太监与爪哇公主的爱情故事、郑和向苏门答腊北部须文达那·巴赛王国赠青铜钟、郑和在邦加岛的“足印”、郑和把斋故事、郑和与榴莲、三保公鱼、爪哇三保井及三宝墩的传送、郑和的石碇、手杖和大炮的故事、郑和斩妖蛇、取地名等。在马来西亚有马六甲的三宝山、三宝井、“官厂”、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郑和与猴枣、郑和打老虎、郑和请教建房、求医、登嘉楼三保江、马六甲郑和鱼等,以及在文莱、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印度、斯里兰卡等的遗迹与传说。3郑和布施的寺碑现存于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用中文、泰米尔语、波斯语三种文字记载了1409年2月郑和再访锡兰时的宗教外交:中文记载郑和船队出使这个尚佛之国时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颂佛世尊功德的祭拜之事;泰米尔语碑文表达郑和一行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恭敬之意;波斯语碑文流露郑和等穆斯林成员对“至高无上的胡大”的虔诚信仰之情。同一块石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的碑文,“一方面反映了郑和对各主权国人民的尊重和他本人的宗教宽容性;另一方则反映出,郑和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致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故此碑是“郑和和平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表明中国当时已经有世界性的眼光”,彰显出“一代航海家郑和博大的胸怀、宽容的精神和非凡的世界性目光” 陈占杰:《斯里兰卡:郑和遗迹今尚在 石碑犹自颂海魂》,新浪网,2005年6月1日,https://newssinacomcn/w/2005-06-01/11246049361ss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4郑和传教的事实因海外传教不属明朝朝廷赋予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故造成正统史家的“不屑记载”与郑和团队的“不便记载”,再加上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借阻挠东南亚华裔皈依伊斯兰教之机否认郑和传播伊斯兰教的事实,以及在东南亚反华意识的误导下所出现的“去中国化”的社会倾向更将“去郑和化”推向极致等,使得郑和传教遭多重屏蔽,但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就连印尼著名伊斯兰组织领袖哈姆加都认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促进我国(印尼)伊斯兰教发展的,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马拉巴人、古吉拉特人和高罗曼特人,还有来自中国的穆斯林。” Hamka, Buya, Cheng–H0 Laksamana Muslim Yang PernahMengunjungi Indonesia,Jakarta: Majalah Star Weekyl,18 Maret, 1961由于郑和下西洋正值东南亚从佛教占统治地位渐向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因此郑和将中国化的伊斯兰文明从东向传入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从西亚、南亚等西向传入的伊斯兰教,为温和的东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注入了中国的和合价值观、贡献了“中国智慧”,故“研究郑和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课题,有助于全面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情况,尤其是他在15世纪东南亚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 孔远志:《论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其次,“郑和符号”对中东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文化”(即由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合作型安全观构成)上,主要包括:1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中国与丝路沿线的中东国家,不仅建立了“丝路天然伙伴”关系,还形成了以经促文的相处模式,“频繁的商务往来和贸易活动”促进了“各方面文化的交往”而推动了“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张阳:《沙特驻华参赞:中沙友谊从丝绸之路时代开始》,环球网2013年5月23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ACJ9。(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中阿关系自古即如此,中阿间以互惠型经贸合作带动包容型人文交流的独特相处模式,赢得了丝路中东国家民众的普遍欢迎:据马欢等回忆,郑和曾三次到访的佐法尔,当地居民欣闻郑和船队的到来便齐聚码头、敲着传统阿拉伯大鼓欢迎。又据阿拉伯学者的研究发现,“这一年10月22日,从光荣的麦加传来消息说:有几艘从中国前往印度海岸的祖努克,其中两艘在亚丁靠岸,由于也门社会状况混乱,未来得及将船上瓷器、丝绸和麝香等货物全部售出。统管这两艘赞基耶尼船的总船长遂分别致函麦加埃米尔、谢利夫-拜莱卡特·本·哈桑·本·阿吉兰和吉达市长萨拉丁·易卜拉欣·本·麦莱,请求允许他们前往吉达。于是两人写信向苏丹禀报,苏丹指示要好好款待他们” 伊本·泰格齐·拜尔迪:《埃及和开罗国王中的耀眼星辰》,黎巴嫩学术书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一研究揭示了郑和船队在阿拉伯国家深受欢迎的历史真相,也门至今“流传着当年郑和把中国的古老而神奇的‘拔火罐’医术,就是在那时由郑和船队的医官教会阿丹(也门亚丁)国民的传说”,“也门当地的医务人员也对此深信不疑。” 孔远志等:《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在阿联酋“六国城”购物中心的中国城内,摆放于主厅内的郑和塑像的标题为“西方海洋之霸主”,表达了中阿共同持守至今的“郑和情结”与千载累积的丝路情谊……郑和下西洋采取的是经贸互惠与人文包容的和平交往方式,故“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欢迎。所以,郑和宝船到处,立即欢声雷动,额手称快” 许在全:《郑和外交的伟大成就》,http://bbstiexuenet/post2_5658805_1htm。,产生了“既满足民生需求又赢得民心”的双重效应,尤其是郑和采取的包容性宗教外交举措,又加深了“民心相通”的互信基础。因此,此种丝路相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中东外交的传统与特色。2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宗教外交系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以特定宗教价值观念为指导,通过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授权或者委托各种宗教组织实施的外交行为以及默许宗教组织开展的针对另一个国家政府的游说行为。宗教外交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使命的行为,比如借助宗教组织对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传教,并动员教众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的行为;另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外交手段为宗教扩展服务的行为。两种行为都属于宗教外交行为。” 涂怡超等:《宗教外交及其运行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郑和受命遣使出访天方国即为一次典型而成功的宗教外交:在“宣德五年,蒙圣廷命差内官太监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等见本国差人往天方国,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亦差使人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贡献于朝廷。” 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页。郑和指派年富力强、懂阿拉伯语、信仰虔诚、颇具才干的副使洪保与马欢、费信等7人率队携带丝绸、瓷器等物乘船赴麦加,不仅开展经贸交流,还完成了朝觐功课,带回“中国人最早绘出的一幅克尔白圣寺写真图《天房图》”,“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并促成对方也派遣使者随其船队来中国访问 盖双:《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披览阿拉伯古籍札记之二》,《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此次由郑和受命于明政府而派遣“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的外交活动,实属“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使命”的一次宗教外交,在经贸合作之际开展宗教交流,有助于践行明朝“协和万邦”的对外政策,且使朝觐成为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3双向宗教交流所催发的非传统安全观郑和肩负“宣德化、柔远人”的出使使命,不仅为丝路传统安全贡献了“强而不霸”的和平外交理念,还为丝路非传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且主要体现为尊重伊斯兰教、营造内外良好社会环境进而传达宗教包容性的非传统安全理念,郑和在泉州灵山圣墓行香之举即为明证:永乐十五年五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经泉州到灵山圣墓上香祈佑后,属下为之立碑纪念,此举具有“一种政治象征,传播朝廷对国内宗教的宽松政策,对穆斯林国家的宣德柔远”。亦即,对内,“灵山圣墓长期是泉州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作为钦命高官,在伊斯兰教遭受欺凌的境遇中,亲临这一圣地行香,蕴涵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而“郑和亲临灵山圣墓行香,传达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这种尊重给予曾受欺凌的泉州穆斯林以极大的鼓舞和慰藉,营造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社会氛围”;对外,“为了与西亚国家将要开展的交往相配合,明王朝必然要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至少要考虑到朝贡使团在华的文化环境。朝贡贸易是有来有往的,朝贡使团成员在华一般要逗留半年,宜有供其过宗教生活的环境。”“在永乐朝重新调整宗教政策的情况下,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正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权威示范”,表明“永乐初年以后开始重兴中国与南洋、西洋诸国开展朝贡贸易所须要‘宣德柔远’的宗教政策。作为钦命高官的郑和亲临圣墓行香,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权威性,从而在当地发挥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 郭志超:《郑和圣墓行香与泉州伊斯兰教的重兴》,载《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此外,马欢的《灜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及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为国人正确认识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不同视角描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的世风民俗,如认为阿丹国因“国势强盛,邻邦畏之” 马欢:《瀛涯胜览·阿丹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祖法儿国在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男女长幼皆沐浴” 马欢:《瀛涯胜览·祖法儿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天方国“妇人俱戴盖头”“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 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转引自万明校注:《明抄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等,成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形成双向宗教交流模式的重要动因:四大圣门弟子等本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宗教使命“走进来”、马欢等穆斯林外交使节肩负“宣德柔远”的外交使命“走出去”,借助双向宗教交流来消除疑虑、增进理解、释放善意,并催发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理念,郑和更被中东穆斯林视为“和平使者”,这对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郑和符号”对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精神”(即和平与发展精神)上,“直接影响”主要包括:1文献记载据《明实录》载,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布剌瓦(布腊瓦)、麻林(马林迪)诸国“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据南山寺碑记载:在郑和第五次远航时,“木骨都束进花福鹿(即斑马)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即鸵鸟)。”据费信《星槎胜览》记载,郑和船队用中国特产在当地交换物品,如在竹步国,“货用土殊、段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在木骨都束,“货用金银、色段、檀香、米谷、磁器、色绢之属。”在卜剌哇,“货用金银、段绢、米豆、磁器之属”。中国从非洲也进口当地特产,如象牙、犀牛角、乳香、红檀、紫蔗、龙诞、生金、鸭嘴胆黔、没药等……随郑和出使非洲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所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著作,既“提供了关于非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较为准确的资料”,又因非洲的落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观” 李安山:《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 期。。在相关文献中,《郑和航海图》的重要性在于,其所反映的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促进了中国人对丝路沿线地区地理与人文的了解,为深化中外友好关系提供了便捷、安全与良好的社会基础。2传说与遗迹据肯尼亚帕泰岛上的桑加人的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海上,这也是桑加人(shnaag)名称的来历。 Report on Shanga excavation,1980,by Mark Hort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hilip Snow,The Star Raft: Chinas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1988,p33。同样,在非洲东部肯尼亚的拉穆群岛(Lamu)的帕泰岛(Pate)上存在着“郑和村”。有人认为,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抵达非洲后,其中的一艘因迷失方向驶近帕泰岛后不幸触礁下沉。由于后来朝廷实施海禁,船上的数百名船员只好在当地定居下来。至今该地的几个村仍有人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参见叶北洋:《非洲“郑和村”》,《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论文汇编之一》,中国·福州,2005年,第380-381页。在李露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出版后,由于书中提到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有郑和后代,新华社曾派记者去岛上考察后发现,有渔民曾在距桑加海岸70公里处发现过一艘中国沉船,并打捞了一个刻有双龙戏珠的中国陶瓮;不仅帕泰当地的妇人不像非洲人,在岛上还发现过刻有中国字的墓碑,岛上至今还有丝织业,并曾养过蚕。 赵明宇:《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封尘:非洲肯尼亚疑有船队后裔》,新浪网,2005年1月16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5-01-16/0829258773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18日)“东非沿岸的帕泰岛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物质文化因素,这很可能与郑和非洲之行有直接的关系” 李安山:《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如在东非各地发现的一些瓷器碎片和在距帕泰岛70公里处发现的中国陶瓮,以及清真寺等。3后裔归祖据肯尼亚《民族报》2007年7月21日报道,600多年前,郑和船队的一艘船在桑加附近的外海倾覆,有几名水手逃生后与当地妇女通婚,且渐被斯瓦希里人同化,如今拉穆群岛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不仅持守着祖先为中国人的家族血亲认同,还将中国瓷杯、中国建屋风格、中国渔船等融入日常生活,更有拉穆姑娘来中国认祖归宗。 孔远志等:《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又据索马里驻华大使默哈迈德·阿威尔于2010年1月在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披露,索马里有一个名叫“郑和村”的地方,“当地人自称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船员的后裔。以前索马里还有郑和纪念馆,郑和做礼拜的清真寺还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语也受到汉语的影响……很多当地人都对中国非常关注,知道中国的很多事情,谈起中国来就好像谈论自己的亲人一样。” 彭玉磊等:《索马里驻华大使:索马里有个“郑和村”》,《广州日报》,2010年1月7日。相比较而言,“郑和符号”在非洲以“文献记载”“传说与遗迹”及“后裔归祖”等方式“残存”至今。但“间接影响”更揭示出“郑和符号”之于中非关系的外交意义。“就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影响而言,郑和之行则有新的含义。这种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就直接影响而言,中国遣使对非洲各国的访问使非洲人对远在亚洲的中国有了感性的了解。有感于中国的慷慨大方,这些国家或派遣使节随船回访以表感谢,或送上特产贡物以表尊敬。非洲的物产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也使双方的交流更进一步。对中国人而言,间接影响是多重的。这种交往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他们对世界之大的了解有进一步提高。虽然他们仍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但非洲大陆带给他们的新奇和震撼是不言而喻的。” 李安山:《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换言之,“郑和符号”对非洲国家和地区更多投射的是一种间接影响,亦即主张和平与发展的“郑和精神”的潜在影响:一是郑和非洲行“使带偶然性的中非民间交往上升为定期的官方关系;在交往中,中国的强势和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使中国与北非和东非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到相对亲密的地步,双方互派使节,互赠礼物,这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使中国对非洲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各种论及郑和船队航线的文献中,提及的非洲国家和地名有61个之多。费信等人的游记中不仅提到各地的地理、物产、人文,还论及当地的风俗、制度和文化。由于这些记录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所了解的,所以对当时中国人了解非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四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洲的商贸关系,这从各种游记中列出的货物单、非洲各地的考古发掘物和中国的进口货物中即可看出。这种商贸活动促进了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海洋贸易;对这一地区的商业网络和地区经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安山:《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也正是由于“郑和精神”的影响,使得中非在古丝路贸易合作与人文交流中结成了丝路合作伙伴,凝成了丝路情谊,且因“坦赞铁路精神”与“中国非洲医疗队精神”等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三、中国丝路外交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第一,在郑和多轨丝路外交中,其人文外交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下西洋中,郑和忠实地贯彻了明朝睦邻友好政策,“每到一国,往往先宣谕明成祖的诏书,宣传对外友好政策,表达同各国通好往来的愿望。然后为诸国国王和王公大臣册封,并给赐冠服、印诰、金银、锦罗等物,再与其进行各种官方或民间的贸易,让海外番国得到种种实惠,深切感受到与明朝修好的好处。不仅如此,郑和使团还‘宣敷文教’,以中国先进的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各国建立健全国家制度、礼仪制度、法律制度等。考虑到西洋许多国家都信奉宗教,郑和所到之处,便布施传教,联络当地人民的感情。” 刘占峰:《郑和“以海屏陆”的国防思想》,《郑和研究》,1993年第3期。此外,郑和的“清倭除寇”,既是其船队遭沿线国武力威胁后的自卫之举,也是受托出面解决当事国热点问题的调停之举,对清除东南沿海的倭寇、营造良好周边安全环境及维护世界和平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折射其军事外交的积极意义。可见,郑和丝路外交实为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及人文等在内的多轨外交,且郑和借助人文外交中的宗教资源在丝路沿线国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且达到“柔远人”之目的。郑和是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现实背景下远播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尽管传播中国伊斯兰文化不是郑和下西洋的外交目的,但宗教交流却成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途径,使得“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务的” 肖宪:《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此种以宗教交流为抓手的人文外交,也成为密切中国与丝路沿线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助力,尤其是郑和组织开展的官民双轨人文交流,扩大了中国的人文影响、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并推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丝路伙伴关系发展。第二,在郑和人文外交中,其包容性的外交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历来成为学界的争议话题:一是认为“郑和主要的或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 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二是认为“郑和是修持‘菩萨戒’的佛门弟子” 朱育友:《郑和是修持“菩萨戒”的佛门弟子》,《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三是认为郑和信奉道教;四是认为郑和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很深的信仰” 郑一钧:《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等。事实上,郑和的“奉佛”之举并非“自己的主观行为”,多为完成“皇帝的意志”,且在郑和随行人员中信佛者亦不少,作为首领与外交使节的郑和,“参加信佛部众和所访国家的佛事活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邻国出现的郑和寺庙等更不能将此作为郑和奉佛的证据。作为船队首领,郑和“决不可能忽视滨海渔民、舟师的宗教信仰,也不可忽视成千上万舰队成员长期在海上跟惊涛骇浪搏斗时祷告神灵化险为夷的呼救方式和习惯” 林松:《从回回民族特殊心理意识综观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郑和研究论文集》,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故郑和“崇道”实为团结随行的信仰道教的船员能与其他不同信仰的船员共同完成远航任务,妈祖文化成为凝聚民心、战胜风浪的精神动力,但这也不能将此作为郑和崇道的证据。“郑和作为中国穆斯林,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肯定会在保持自己内心信仰的同时,也要适应中国文化的实际,与中国当时的包括佛教与道教在内的宗教及现实融洽相处”,故其“从事和参加佛教和道教的活动,只是他为了完成航海事业而进行的行为” 赵国军等:《从穆斯林的角度看郑和及其航海事业》,《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表象又与其所采取的包容性人文外交举措有直接关联。郑和在持守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参与佛事、拥有法名、兴建天妃庙宇、参加道教活动等,旨在顺利完成下西洋使命:对内,郑和船队在远航期间常遇风险与不测,故在每次远航前举行佛教、道教甚至伊斯兰教名下的祈福祷告仪式,均发挥着稳军心、壮国威、造声势等重要作用;对外,在出访各国时,据对象国信仰不同而采取“因俗治之”的包容性的外交举措(或捐款建寺修庙或立碑建亭),强化了与丝路沿线国的价值沟通与民间联系,如“郑和崇拜”在东南亚不仅影响了伊斯兰国家,还对“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泰国人民从宗教文化上来讲,在郑和那里找到了认同感,说明郑和对当时当地的佛教信仰与活动的尊重” 向广宇:《郑和崇拜与南海区域文化认同》,《沧桑》,2014年第1期。。又如,现存于斯里兰卡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引人瞩目之处,在于碑文分别用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却能在一块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表示同样的礼敬与尊重,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 刘咏秋等: 《解开郑和在斯里兰卡的历史谜团》,《参考消息》特刊,2005年7月7日。……郑和包容性的外交举措,便在某些情况下发挥了“提供广泛的非官方的解决冲突和促进和解的服务”[美]路易丝·戴蒙德等:《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在冲突地区拥有最广泛的基础,而且保持着幕后调停成功的最好纪录”“拥有真知灼见和组织群众的高超技巧,以及对政策问题中的人性因素的深邃认识”[美]路易丝·戴蒙德等:《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等作用,最终达到了“以不治治之”的外交境界。第三,在郑和丝路外交中,其经济外交和人文外交的互促产生了联动效应。郑和的丝路外交,主要以经济外交与人文外交为双翼。前者“尽管其交往的媒介表面上是商品和服务”,但却“创造了诸多途径,使善意、信息、友谊和互相尊重得以自由流动”[美]路易丝·戴蒙德等:《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8页。。后者通过坚信“团结或同一性”“爱与同情心”“和平使命”等笃信行动来“觅得解决冲突的工具”[美]路易丝·戴蒙德等:《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102页。以缔造和平。郑和团队通过贡赐贸易、互市贸易开展经济外交,又通过进香祈福、教界交流、建寺立碑、公派朝觐等展开人文外交,体现出互利共赢的丝路经济观与平等包容的丝路人文观。因为,“在十五世纪初期,亚非国家的民情风俗,是比较淳朴的,其宗教信仰,也是很诚笃的。因此,明朝政府对他们古朴淳厚的民情风俗,加以表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给予应有的尊敬,以示珍视他们固有的礼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的传统政策之一。正是这种传统政策的体现。实行这种政策,不仅是为了增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交流,也表现出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求同存异’的大国风度”。 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海洋出版社, 2005年版,第1015页。这既为郑和开展人文外交提供了政策保障,还促成由“信教、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入华落脚所形成的聚居区—蕃坊的出现,且具有文明交往与贸易往来的双重功能,折射出郑和丝路外交触角由民生直抵民心,海外贸易与宗教交流成为郑和外交的重要选项。郑和团队除因满足了丝路沿线伊斯兰国家穆斯林的“两世诉求”而获“民心相通”之成效外,还因其“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故使丝路伊斯兰国家、佛教国家在“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美]牟复礼等:《剑桥明代中国史》,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的同时,也使丝路贸易在客观上带动了多元宗教的进一步交流,贸易与人文的互动关系由此建立:一方面“郑和所到之处,便布施传教,联络当地人民的感情” 刘占峰:《郑和“以海屏陆”的国防思想》,《郑和研究》,1993年第3期。。另一方面,基于宗教交流的密切联系又深化了郑和团队与对象国间贸易互信的社会基础,进而带动了贸易往来,双方易产生好感、消除误解、建立互信等,故能达成互利共识、实现互惠目标,经济外交与人文外交的互促便产生了联动效应,出现了“郑和所到国家和地区几乎都遣使随郑和船队来华朝贡”的盛况,“郑和下西洋打破了朝贡贸易只来不往的消极局面” 江淳等:《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4页。,表明“民心相通”才是“郑和符号”依然影响“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根源所在。四、研究郑和丝路外交的多重意义第一,华人华侨与穆斯林已成为郑和“符号现实”的主要建构主体。符号聚合理论强调,“符号现实在人类意识中聚合成分层式符号化的‘意识图景’” 吴玫等:《美国衰落符号的背后》,《公共外交季刊》,2014年秋季号第6期,第58页。,郑和“符号现实”则由三层式“意识图景”构成:1外层的“郑和崇拜”在丝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出现了“华人华侨与穆斯林越多、郑和崇拜则愈甚”的一种信仰现象,实为将历史英雄人物神化的“一种个人崇拜的极端形式”。“它一般由某个社会群体(或者全社会)共同参与,崇拜者通过利用一些手段,如修建庙宇、举行仪式活动、尊奉遗迹遗址、编撰神话传说等来巩固和强化自己对崇拜对象的虔诚与信仰,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宗教力量来维护崇拜对象的权威。” 施雪琴:《郑和形象建构与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郑和崇拜”已从“个人崇拜”演化为伊、佛、道等多元宗教甚至准宗教成分渗入的“混合型信仰崇拜”,“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是郑和宗教文化包容性的收获” 向广宇:《郑和崇拜与南海区域文化认同》,《沧桑》,2014年第1期。,使得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成为“郑和崇拜”的建构主体。2中层的“郑和文化”“郑和作为一种信仰符号”,“具有整合移民族群、团体与社区以及延续与巩固华人文化认同的功能” 施雪琴:《郑和形象建构与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也具有传播友好邦交、商贸互惠、清剿倭寇及包容多元宗教等和平文化的功能,且已形成“宣德化、柔远人”“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等凸显国家意义的郑和话语,并演化为由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合作型的安全观组成的“郑和文化”,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基因、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以及中国丝路外交的持久影响力。3内层的“郑和精神”郑和下西洋壮举,反映出中华民族走出国门、融入全球的“世界意识”,和合共生、谋求合作的“战略文化”,播撒和平、缔结友好的“外交传统”,以及开放进取、经略海洋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中国人勇于进取的开拓冒险精神、不侵略与不称霸的和平精神、尊重与理解不同信仰群体的包容精神,以及“贡而不朝”与“厚往薄来”的合作精神等。郑和下西洋便成为肩负国家与民族发展使命的成功之举,其所表现出的和平与发展精神即为“郑和精神”,使得明朝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友好合作中缔结了丝路情谊,出现“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的外交成效。据统计,永乐帝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 肖宪:《郑和——中国和平外交的先行者》,《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总之,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成为郑和“符号现实”的建构主体,也是儒伊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于丝路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使得丝路沿线国家的华人社区、穆斯林社区成为“郑和符号”产生、发展与传播的核心场域,华人华侨与穆斯林也因此成为丝路沿线国家亲华、友华的核心力量,并在深化我国与丝路沿线伊斯兰国家战略合作互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第二,“郑和符号”在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构建与维持的作用。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思维、战略取向、战略意图等产生影响的“深层次文化因素”的话,那么,“郑和符号”所包含的郑和崇拜、郑和文化与郑和精神实为中国“文化传统、哲学思维和社会观念”等“深层次文化因素”在国家与民间层面的不同表达,尤其是“郑和精神”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核,“郑和符号”已在中国战略文化形成中发挥了构建与维持的作用:郑和下西洋壮举成功地证明了中国即使具有称霸世界的实力,也无动武称霸的“霸道”,而是谋求通过和平与合作来树立“王道”,进而彰显出中国“强而不霸”的合作型战略文化。亦即,郑和团队用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美化了中华文明形象、用“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强化了明朝“大一统”的国家魅力、用包容性的宗教外交举措柔化了中国国家形象、用“宣德柔远”的和平外交践行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因此,是“郑和将‘丝绸之路’最终成就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公共产品,郑和用‘七下西洋’壮举、近30年的和平外交实践、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到访足迹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能向世界提供丝绸等商品,还能向世界提供‘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强而不霸’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和平与发展并重的‘郑和文化’,以及互惠与包容的‘丝路精神’等,由此形成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互惠、人文包容、安全合作”。 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的的诞生,又折射出中国战略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在边倡导边实践中已赢得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中国丝路外交的魅力再度显现,尤其是海合会成员国积极推出对接项目:科威特计划投资1300亿美元在其北部沿海地区建造一个“丝绸城”,2035年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新丝路的重要战略枢纽;除筹建“杜库姆经济特区”外,阿曼还规划在萨拉拉港打造“郑和纪念园区”,主要包括郑和纪念碑、文化休闲区及中餐馆等,纪念郑和船队三访阿曼的友好之举并吸引中国及世界各地游客;卡塔尔计划建设一个大型园区项目“多哈新港区”……“从科威特的‘丝绸城’到阿曼的‘杜库姆经济特区’,再到卡塔尔的‘多哈新港区’都显示了中东国家想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发展经济的雄心。‘一带一路’确实不是中方的独奏曲,而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的合奏曲。” 薛小乐:《中东为“一带一路”做规划:科威特1300亿建“丝绸城” 阿曼建郑和纪念园区》,环球网,2015年4月1日,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JJsaC。(访问时间:2022年2月21日)因为,“丝绸之路的基本价值在于各国、各民族间的平等交往,互通有无,增进相互理解,因而是文明文化和平互动之路,各族人民平等交往的友谊之路。对国际社会而言,丝绸之路的概念具有共享性,没有排他性。它由各个国家携手共建,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逐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深富创新涵义的国际合作模式。” 杨公振:《中东前特使吴思科:中海共建“一带一路”升级版》,中国网2014年12月4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4-12/04/content_34230640htm。(访问时间:2022年2月21日)总之,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丝绸之路、郑和崇拜、郑和文化、郑和精神等一系列丝路公共产品的现实影响力将得以凸显,“郑和符号”对我国与丝路沿线伊斯兰国家战略合作的现实影响尤甚。因为,“在当代中国迅速变迁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郑和话语被国家所强化与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外交理论的价值观念与认同的重要构成”。 施雪琴:《郑和形象建构与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三,“郑和符号”成为深化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的互信酵母。****强调,中国应“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以“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访问时间:2022年2月21日)。其中,丝路外交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基石、“郑和符号”已成为深化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伙伴关系的互信酵母,其重大现实影响日益凸显,且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得以彰显:一是巴基斯坦,除其“安全与稳定对中国西北边境省份有直接影响”外,还因“巴基斯坦拥有17亿人口,是世界排名前三的伊斯兰大国,也是穆斯林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成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交往的重要桥梁与渠道。通过中巴友好,中国近年来与穆斯林国家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关系都取得长足进展” 许利平:《当代周边国家的中国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224页。,为构建我国与伊斯兰国家伙伴关系网提供了示范效应。2015年中巴“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将中巴关系塑造成为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交流互鉴、友好合作的典范”,并从经济、安全与人文三个领域明确了中巴战略合作的方向,使得中巴伙伴关系建设更具战略意义;二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首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5年5月又落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表明“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是中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合作对象”《背景资料: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大事记》,新华网,2015年5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5/07/c_1115214110htm。(访问时间:2022年2月21日),中哈战略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战略对接”,也将带动中国西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合作;三是中国在印尼首倡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致力于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的“对接”。2015年中印尼“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强调,双方同意推进文化遗产旅游合作,邀请中国游客赴印尼体验“重走郑和路”旅游新项目。作为东盟第一大国和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激活“郑和符号”已成为深化彼此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这将对东南亚地区和国家产生重要引领作用,借此显现“郑和符号”对“一带一路”软环境的“建构与优化”的双重功效。比较而言,“郑和符号”对这三个伊斯兰国家的现实影响程度不同、表现各异:对巴基斯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郑和文化”上,包括中巴一贯秉持“包容型的人文观”而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且产生了“巴铁”成效、以“合作型的安全观”做指导联手反恐且形成“三管齐下”的安全合作模式、在“互惠型的经济观”引领下深化了两国经贸合作且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抓手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示范项目等;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郑和精神”上,包括“和平与发展”是古丝路上中哈两国成长的共同诉求,也是新丝路上中哈两国壮大的共同愿景,还是中哈两国实现战略对接的共同目标,以及“郑和精神”已成中哈两国打造“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重要影响因子等;对印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郑和崇拜”上,包括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有关郑和的祭拜活动及其集体潜念的形成、郑和传播的中国和合文化对东南亚伊斯兰的柔化作用、郑和团队开展的贡赐贸易与互市贸易对中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影响等。综上,中国丝路外交历史贡献巨大、现实影响深远,尤其是郑和丝路外交更具样本分析的学术价值,其所关涉的丝路伙伴关系、丝路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等议题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二节中外丝路交往中软治理的经略之策一、丝路文明蕴含全球治理经验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将世界上主要的文化体系归为四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体系。四者又可合为两个更大的体系:前三者为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他说,“这些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世界上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新疆。”这番总结揭示了东西两大文明、四大文化体系都曾在中国西部周边的中亚、西亚、南亚等遇合成丝路文明的历史现实,并得益于历史上三次中外交往高潮,形成了以西域文明为核心的多元化的丝路文明:第一次是在丝绸之路初辟时的汉代,以中原与狭义西域(今新疆)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二次是晋至唐朝时期,以中国与印度、中西亚、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往为主;第三次是明代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东来,天主教传播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为主要内容,亦即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西到地中海沿岸,将亚、非、欧三大洲亦即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因此,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间的联系与交流,这使丝路文明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其中,丝绸之路之于中国西部周边国家和地区,不仅关乎文明联系和交流,还关乎“世界心脏地带”欧亚大陆的“全球治理”问题。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深谙“西域安则中原安”的固本铁律。因为在丝路腹地的西域这一广大区域内,两千年来,十多个强大帝国和数十个中小国家既通过商贸往来、文化传播、文明交汇等方式,也通过人口流动、部族迁徙、民族融合等社会演化进程,还通过战争征伐、抢劫侵占等极端方式相互交往,这使世界文明“汇流的地方”也面临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甚至演化为治理难题。值得强调的是,丝路文明恰恰是在应对丝路腹地诸多外部挑战的过程中得以快速成长。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文明生长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其动力来源于“挑战激起成功的应战,应战又反过来引发新的挑战”。中华文明的生长是在连续不断的“挑战—应战”中获得发展动力,外部环境的征服与内部韧劲的强化相随相伴于其初期的生长阶段,并在丝绸之路的中外文明交往中得以成长。因此,身处丝路腹地的中国西部周边国家和地区,不仅因世界文明“汇流的地方”而成为丝路文明的诞生地,也因丝路难题的集结地带而成为全球治理的“示范区”,更因高频次的“挑战—应对”过程而成为人类文明成长的加油站。在中国倡建“一带一路”的新实践中,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严峻挑战。因此,如何借鉴丝路文明交往中所蕴含的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软治理的成功经验,成为探讨中外丝路交往中软治理经略之策的关键。在古丝路上,中国不仅输出了丝绸、瓷器、四大发明等商品和技术,还传播了“大一统”的国家形象与中华文明,以及丝绸之路、丝路精神等影响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表明“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言谈、信息交流、沟通、理解、对话等传播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某类传播在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对稳定,由此表现了某种文化与社会结构,形成文化意义的分享和文化创造形式;在应对环境、群体间竞争、内在发展需要等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又不断进行共享文化的创造、修改和转变,使文化具有流变的特点”,“如‘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的贸易更加频繁,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开来”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即为明证。在中外丝路交往中,我们既要接受文化差异性的现实,也要建立对话意识,在对话中建立互惠性理解。这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传播中的主体双方共同分享着经验,进而形成意义分享,由此搭建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在对话与合作中达到“互惠性理解”,凸显“在文化差异中形成互补性知识,强调文化观念的互相印证,把在刻板印象、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等基础上达成的理解当作对他者的敌意,努力基于生活事实与文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对话式理解”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的特点,使孤立的个人与他人分享“共同价值”,丝路精神所蕴含的经济互惠、人文包容、安全合作的核心思想赢得了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与分享。其中,宗教交流成为“丝路天然伙伴”在助力形成“丝路精神”中达成“互惠性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上,宗教外交“轨道中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感知”[美]路易丝·戴蒙德等:《多轨外交》,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但因“宗教界潜在的消极面是其排他性的历史倾向”[美]路易丝·戴蒙德等:《多轨外交》,李永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而使宗教外交的消极性也难以避免,也使宗教资源本身兼具正面与负面双重社会功效。但是,由于郑和宗教外交根植于其多元宗教的包容性与多轨外交的统筹性,故在某种程度上发掘了宗教资源的积极性、规避了宗教资源的消极性,使其宗教外交在“扬长避短”中产生了“宣德柔远”的外交效应,如郑和在下西洋中成功开启了中国与天方国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促成宗教资源向外交资源的成功转化,使得朝觐外交演化为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交流的特色与传统,且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就强调要“进一步开创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编:《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1949~1991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今,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间官方、半官方及非官方等多渠道的人文交流已夯实了双方的互信基础,宗教交流在双边关系发展中发挥了基础和引领作用。其中,朝觐活动成为中国与沙特丝路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纽带,随着朝觐人数的平稳增长,中国有组织、有规模、各大部委联手参与的中沙朝觐外交已初见成效,在深化中国与沙特、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伙伴关系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与2004年1月“中阿合作论坛”的相继成立,使得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多边人文交流与合作进入制度支撑的历史新阶段,宗教交流在丝路多元文明交往呈现积极活跃的总体态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3年中国倡导建设“一带一路”,旨在弘扬“丝路精神”、落实“五通”举措,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民心相通”举措的实施过程中宗教交流的重要性得以凸显。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钱彤:《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访问时间:2022年2月21日)为此,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不仅“奋发有为地开展周边外交”,还主张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其中就包括重视宗教交流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3月28日,****在第十四届博鳌论坛致辞中再次强调:“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2015年3月28日,海南博鳌)》,《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2版要闻。2015年3月29日,博鳌论坛举办了以“中道圆融——凝聚善愿的力量”为主题的宗教分论坛,这是博鳌论坛自2001年成立以来,首次举办宗教分论坛,三大宗教领袖与文化学者与会,提倡中道,反对极端,用宗教来对话、沟通,以及正视宗教对现代生活的影响等,表明中国政府已洞悉了宗教事务的外交战略价值,早在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前所未有地全面论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与意义。5个月后,****出访印度等中亚南亚四国,以佛教、丝绸之路等宗教历史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展开国与国交流,全力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此行标志性的国家赠礼《玄奘之路》、为印度总理莫迪定制的纯素生日蛋糕,以及****数次讲话中提及的诸位古代高僧等,标志着“宗教外交”成为集中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名片,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看到了宗教事务的重要性与现状的差距, 萧潜:《剑指何方:独家解读2015博鳌宗教分论坛》,凤凰网,2015年3月30日,http://foifengcom/a/20150330/41028889_0s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21日)表明中国政府在实施“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举措中正视宗教沟通、意识到丝路沿线国家战略合作中“宗教因素”的现实存在。毋庸置疑,从郑和的丝路外交→周恩来的人民外交→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宗教已然实现了社会资源向外交资源的成功转化,并成为夯实共建“一带一路”社会民意基础的助力之一,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宗教极端主义与部落文化的风险性影响、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宗教交流的纽带作用、中印战略合作互信建构中的佛教交流的作用,以及宗教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伙伴关系深化中的桥梁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看,“一带一路”使中国外交最终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且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盘活“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所蕴含的外交历史资源优势,使“传统友谊”发挥务实性作用。在两条丝绸之路上绵延千年的中外文明交往,不仅积淀了一份深厚的丝路情感,还升华为一种经济互惠、人文包容、安全合作的“丝路精神”。其中,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因其近30年在近30个国家留下的访问足迹而彰显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郑和文化”已成为“丝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也跃升为成功的国际公共产品,并成为中国外交的宝贵历史资源,如何发掘并利用丝路外交实践中的“中国经验”,已成为如何盘活“一带一路”历史资源优势的关键,也是“传统友谊”之于当代丝路伙伴关系的作用所在。二是可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有的竞争力来“奋发有为”地开展周边外交。两条丝路沿线人口30多亿,中国既有为沿线合作国家的注资能力,还倡导义利兼顾甚至舍利取义,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等方式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打造丝路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实践中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在经济合作与宗教交流的互促互进中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切实推动宗教资源向外交资源的成功转化,力争在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由“丝路天然伙伴关系”向“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转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总之,“宗教因素”既是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缔结“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历史助力,也是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动力,这是丝路文明交往所蕴含的全球软治理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影响。二、丝路治理中宗教变量影响评估由于宗教资源本身兼具正面与负面的双重社会功效,使得“宗教因素”既可以成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文交流与合作的纽带,也易被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利用而异化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诱因,管控宗教极端主义风险因素已成为关乎“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宗教发展态势,始终都是古今丝路治理的关键变量。在全球信仰群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现实背景下,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宗教发展呈现出的新态势,不仅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也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面临的新问题,更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在对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宗教人口做定量分析后,发现了以下几个事实:一是古代丝路宗教信仰的基本分布走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宗教发展基本格局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二是古代丝路多元宗教并存的历史传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多元宗教并存的发展态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三是古代丝路宗教信仰历史人口相对比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宗教信仰现实人口相对比值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有如下现象引人注目:在71个沿线国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占比超过半数以上的有37个国家,且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地区;天主教、东正教与基督教三大信仰群体人口占比超过半数以上的分别是9个国家、7个国家与2个国家,共计18个国家,表明基督教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仍不容忽视;佛教信徒占比超过半数的国家有7个,除蒙古国外,其他6国均属东南亚地区,佛教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依然强大,甚至包括华人华侨社区;华人华侨中信仰孔教、道教及佛教的居多,但也有信仰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的,表明宗教既是他们融入对象国的重要社会纽带,又是他们持守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重要生存策略;“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民众信奉伊斯兰教或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但即使如此,沿线国家绝无单一信仰现象,多元信仰结构已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在穆斯林人口高达99%的伊斯兰国家亦不例外;多元信仰结构的形成得益于古丝路多元宗教文化的包容性交流与合作,但中国道教文化沿丝路外传后多囿限于汉文化圈甚至仅在新加坡等国的华人社区而难以远播;印度佛教远播影响力较大但却在本国消失,取而代之的印度教在印度与尼泊尔有了众多信徒……这些值得深究的现象,既是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民心相通”所面临的教情现状,也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化宗教交流的社会现实。据皮尤研究中心报告预测,全世界印度教徒的人口数量预计在2014—2050年间将增长34%,从目前略超过10亿增长到2050年的近14亿。届时,印度教徒将占世界总人口的149%,成为世界第三大宗教。穆斯林人口从2010年16亿人增长至2050年约28亿人,2070年后,伊斯兰教将成为世界信徒最多的宗教,印度将取代印尼成为拥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2050年印度教将成为第三大宗教》,《参考消息》,2014年4月4日。该报告表明,信仰人口结构变化已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主要体现为:1“宗教因素”对我国周边外交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人口比由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表明影响我国周边外交的“宗教因素”已由伊斯兰教、佛教变为伊斯兰教、印度教与佛教,折射出“宗教因素”在我国周边外交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强的发展趋势。2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重要的战略风险因素。伊斯兰教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信仰人数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现实影响最大的宗教,且因宗教极端主义与种族、教派、部落、能源、领土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使其成为重要战略风险因素之一,“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宗教极端主义所致的人文风险正向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蔓延。3中印关系中“宗教因素”的影响力日益趋强。随着全球宗教信仰人口结构出现的新变化,印度教徒与印度国内穆斯林人数的激增,都使得印度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发展中的教缘影响力空前增强,且对我国周边外交中的人文影响力也随之增强,更使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4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的政治影响力将不断扩大。2070年后的伊斯兰教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且印度将取代印尼成为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影响印度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客观上造成南亚将取代东南亚而成为中东之外最重要的伊斯兰信仰板块,南亚与西亚、北非这三大伊斯兰信仰板块间的密切联动,又会对大中东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使得我国西部周边外交面临严峻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严峻。5宗教极端主义将对“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冲击。2010—205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埃及、伊朗、土耳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皮尤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的未来:人口增长预测(2010-2050)》, Resource: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2010-2050),https://bsullivanorg/wp-content/uploads/due-to-the-high-birth-ratepdf。(访问时间:2022年2月22日),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其中,穆斯林人口列前三位的国家均在南亚与东南亚,且人口比值由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印尼,意味着极端伊斯兰主义影响的人口几率将大于温和伊斯兰主义影响的人口几率,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凸显将成不争的事实。西亚与北非人口居多的伊斯兰国家,占全球穆斯林人口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以埃及、伊朗、土耳其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仍因人口众多、教派矛盾、种族恩怨、部落纷争、地区冲突等诸多因素而在中东地缘政治与教缘政治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并在不断平衡政教关系中实现社会转型,并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值得警惕的是,自“9·11”事件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并主要渗入民间、精英、组织等三个层面,表明“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布道宣教名义的掩盖、庇护下,利用宗教从事暴力恐怖、分裂国家等极端主义活动,就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197页。,已对“一带一路”的战略安全环境造成了极大冲击。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超过25万外国人加入了像‘伊斯兰国’和‘基地’这样的‘圣战’组织”。其中,“2014年中旬到2015年3月期间,全球的外来战斗人员数量增长71%,欧洲和亚洲国家出现大幅增长。” 《逾25万外国人加入极端组织》,载《参考消息》,2014年4月4日。量化分析表明,“宗教因素”在我国大周边外交中既是一个历史变量,也是一个现实变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宗教人口分布对中国周边国家宗教基本格局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尤其是伊斯兰教发展出现的“去中东化”趋势,使得“一带一路”面临宗教极端主义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周边国家宗教发展新态势已然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新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如何有效管控宗教极端主义所致的战略风险,将是关乎中国参与丝路安全合作、提升全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治理能力的重大现实问题。三、基于宗教发展新态势的经略周边新对策倡建“一带一路”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将更多地与世界发生联系,尤其是与那些比较复杂甚至相对落后的地区发生联系,这实际上对中国社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以更为灵活、务实和开放的心态,超越传统的民族交往模式,去寻求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 储殷:《应重视“一带一路”机遇中的风险》,《法治周末》,2014年12月23日。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主流媒体肆意渲染“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必霸论”来肆意歪曲中国形象。因此,“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对西方的反对作民族主义式的强烈反应,而是要理性地寻求改变西方认知中国的途径和方法。” 郑永年:《中国:大国思维与大国责任》,《中国外交》,2008年第11期,第14—15页。我们既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捍卫中国的丝路话语权,还要积极“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密切机构联系、拓展对话渠道、努力增进共识” 《俞正声作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03/7097207shtml。(访问时间:2022年2月22日)。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域宗教的入华以及中国儒教等信仰传统的西渐,基本上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得以实现。这样,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成为具有动感及活力的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 卓新平:《丝绸之路的宗教之魂》,《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21页。,凸显丝路宗教资源的比较优势。其中,对宗教团体的思想资源、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与和平利用,是对原有的世俗化场景下的外交模式的一种修正和更新,也是深化战略合作的新途径,如2015年的中印、中日外交,为宗教资源转化为外交资源乃至战略资源的可能性提供了示范效应:2015年5月14日,中印首脑外交中因大慈恩寺、玄奘取经、菩提树苗等宗教元素的融入而唤起了中印友好交往的“丝路记忆”与“丝路情怀”,旨在用佛教文化认同来提升首脑外交的成效。此外,中印“双方认识到,通过边境贸易、香客朝圣以及其他交流加强两国在边境地区的合作是增进互信的有效办法”,故“中方于2015年开通的经乃堆拉山口的朝圣路线,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宗教交往,为印方朝圣香客提供了便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人民日报》 ,2015年5月16日第2版要闻。此次中印宗教外交的战略性起步,对于增进中印战略合作的互信度,激发丝路命运共同体意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的讲话中,不仅强调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还指出“隋唐时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当年很多来自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僧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期间,“不仅传播了佛教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15年5月23日,https://wwwmfagovcn/ce/cemr/chn/zgyw/t1266332htm。(访问时间:2022年2月22日)事实上,发掘、利用丝路宗教资源的比较优势来重续丝路民间交往传统,已成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探索的实际行动,2015年2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时表示,中方对中、斯、印三方合作持开放态度,愿积极探讨三方可能合作的领域和可行途径,尤其强调,“三国都有丰富的佛教旅游资源,可以考虑合作开辟旅游路线” 王慧慧:《王毅:愿积极探讨中、斯、印三方合作》,新华网,2015年2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27/c_127526053htm。(访问时间:2022年2月22日)。鉴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宗教发展态势这一关键变量,对“一带一路”共建新实践产生了正面与负面的双向度影响的事实,特提出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