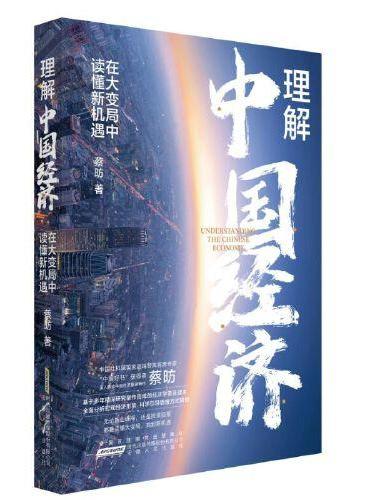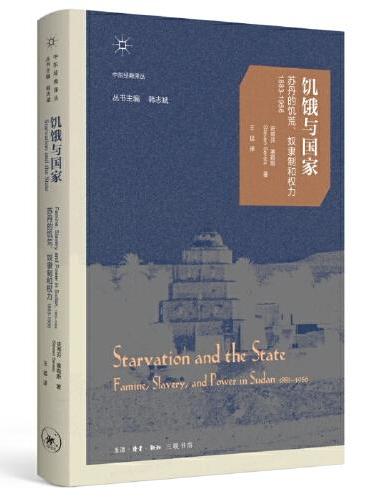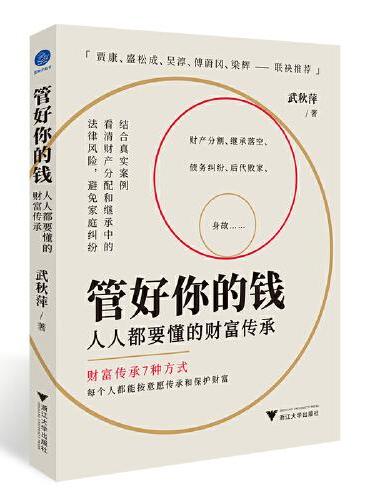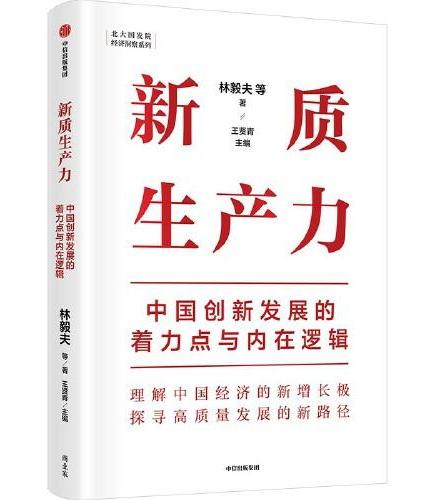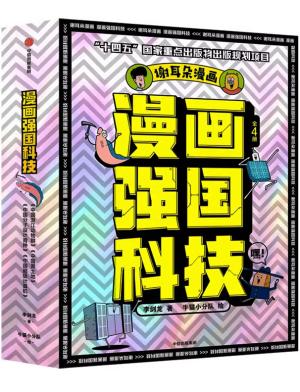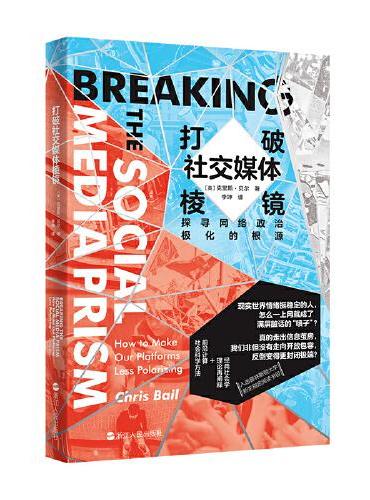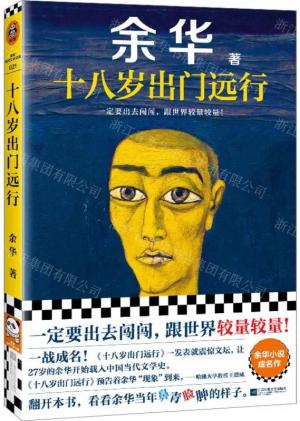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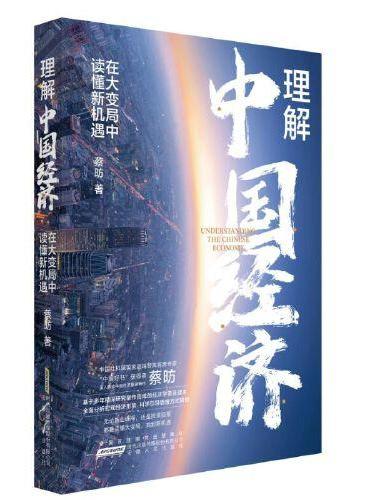
《
理解中国经济:在大变局中读懂新机遇
》
售價:HK$
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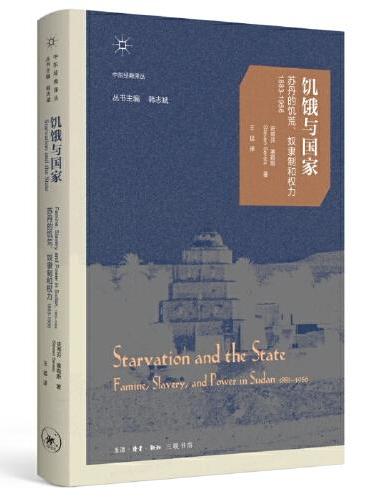
《
饥饿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956)
》
售價:HK$
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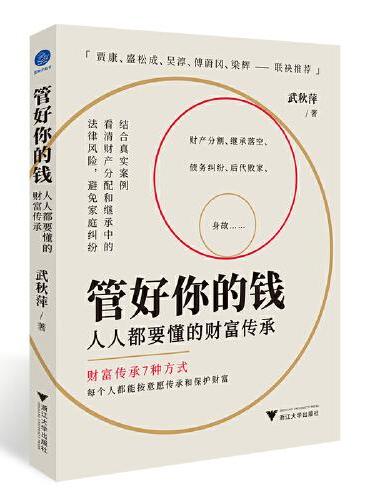
《
管好你的钱:人人都要懂的财富传承(一本书带你了解财富传承的7种方式)
》
售價:HK$
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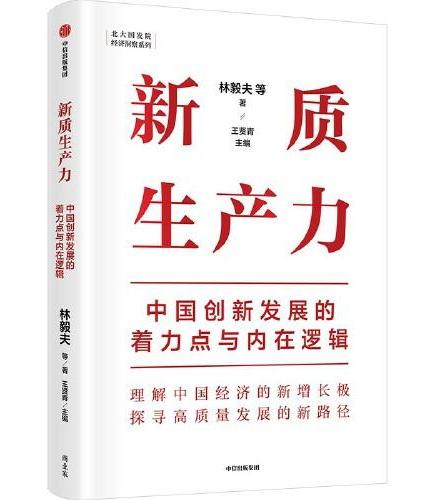
《
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
》
售價:HK$
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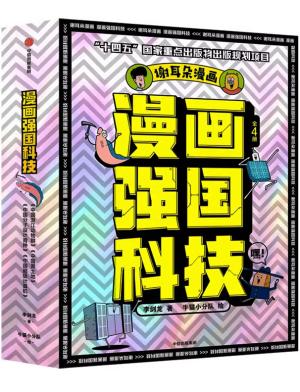
《
“漫画强国科技”系列(全4册)
》
售價:HK$
16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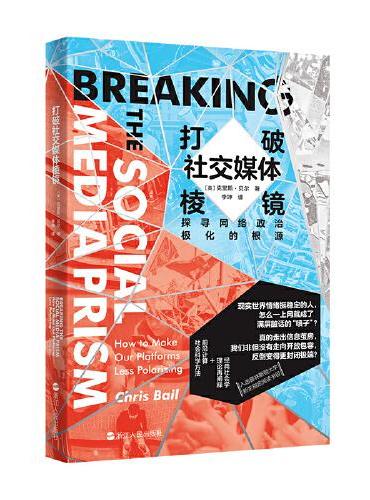
《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
售價:HK$
69.6

《
那一抹嫣红
》
售價:HK$
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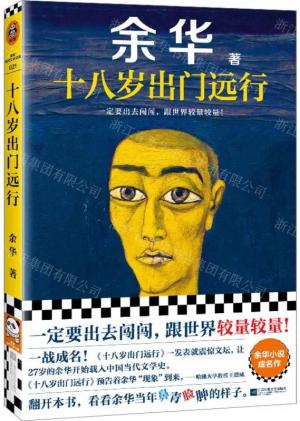
《
十八岁出门远行
》
售價:HK$
54.0
|
| 編輯推薦: |
★以喜马拉雅高分播客节目为底本
《世间没有白走的路》以刘心武先生在喜马拉雅的播客节目“听见·读书与人生感悟”声稿为底本,该播客评分高达9.6分,135万播放量,是一档优质的文化类节目,在听众群中口碑优良。
★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八十自述,细品人生之味
本书作者刘心武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他以80岁高龄回顾自己一生读过的书、见过的人、历过的事、走过的路,洗尽铅华,朴素真挚。这本书里,既有书香弥漫,又饱含人情味和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名家
作者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与多位国内知名作家、学者、艺术家如冰心、汪曾祺、周汝昌、启功等交往的往事。这些记录能使读者对以前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产生更多新的认识。
★随书附赠刘心武手绘小画明信片
刘心武在写作、研红之余,还喜欢去乡野采风。书中就收录了几篇跟画有关的文章,如《失画忆西行》《听郁风聊画》等。读刘心武的文章,品味其哲理小画,感受文学名家的笔端趣味。
|
| 內容簡介: |
|
《世间没有白走的路》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纪念自己的亲友以及抒发人生感悟的随笔集。本书以作家在喜马拉雅的播客节目为底本,按三大主题分为三辑整理成书。第一辑为作者记念其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的文章,比如父母、儿时玩伴等;第二辑所写为作者交往过的文艺工作者;第三辑为作者就生活中的经历提炼出的一些哲思、感悟。在这本书里,作者将自己一路走来的坎坷经历向读者倾诉,将记忆深处那群善良又可爱的人介绍给大家,也将自己对当下生活的反思付诸笔端,以供读者参考。世间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
| 關於作者: |
|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4年推出长篇小说《飘窗》,2020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邮轮碎片》。
|
| 目錄:
|
|
第一辑 陪我长大的他们003 神圣的沉静007 一床被子012 一盒如意膏018 高处的药匣023 免费午餐030 我的彭娘037 一场五分钱的电影048 王府喉掸第二辑 握过他们的手055 茅盾关注我的成长060 怀念恩师周汝昌067 老诗人严辰071 我和冰心的交往077 失画忆西行085 女评论家李子云091 文兄从维熙、邵燕祥097 汪曾祺一度想写的小说100 我接触到的夏志清106 听郁风聊画113 我与吴祖光118 十六朵玫瑰124 我与丁玲及《杜晚香》132 为家乡向启功求字139 大甜桃儿第三辑 这就是生活145 手捻陀螺149 果袋婶153 框住幸福157 抱草筐的孩子163 喜鹊妈妈167 狸狸的来历172 在巴黎宠物墓园读诗177 话堵话182 为你自己高兴187 美与完美191 悲欣交集是人生195 皱皮苹果200 一道金光203 看倒影208 远香近臭
|
| 內容試閱:
|
序
北京植物园刚刚更名为国家植物园(北园)了。我很爱这处地方。它的北边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卧佛寺,西北有樱桃沟风景区。卧佛寺东边有利用原僧房改造成的宾馆卧佛山庄,我多次自费入住卧佛山庄,享受那一派幽深雅静。今年春天疫情稍缓,助理焦金木陪我到那里小住。除了看花品茶,他对我偏要到寺西一隅去寻找一座广慧庵,大惑不解,因为在游览指南上,并没有广慧庵字样。及至终于找到,那里已是一所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我在门前徘徊良久,感慨万端。
我的一位姨妈,名叫王永强。这名字挺男性化是吧?那是因为,他们王家是个大家族,到她这一辈,排行永,最后一字,规定一律要木字偏旁。他们家女性把桃李杏梅杨柳榆楸橘橙柑柚椰樱榴檎等,男性把树林松柏槐椿枫材棕榈檀榕栾臬桑采等,几乎全都用上了。棺材的棺,那不能用;樗树因为是臭椿,所以樗不能用。到我这位姨妈落生,父母觉得木字边的好字眼已经被家族用尽,因此干脆弃木而给她取名为强。
这位姨妈,大学学的植物保护,后来在农科院搞研究,创办了《中国养蜂》杂志。1958年,在杂志基础上组建了养蜂研究所;196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的关怀下,将卧佛寺西边本来驻军的广慧庵腾出,让养蜂研究所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定名更加准确——蜜蜂研究所。王永强姨妈应该是新中国蜜蜂研究的元老之一,她长期担任《中国养蜂》杂志主编。说是主编,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从组稿、审稿、定稿、排版、校对、选择封面照片到下厂付印等环节,她都忙得团团转。有次母亲约她来我家吃晚饭,她到得很晚,说是去邮局给杂志的作者们汇稿费去了。母亲笑她:“你真是全挂子本事啊!”她乐乐呵呵,满脸放光。她自己也撰写关于养蜂的论文,记得有篇论文,配有表格、曲线图、饼图什么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占了一整版,刊发后,很快有几个国家级的科研机构来联系交流事宜。
那时候卧佛寺以南刚辟为植物园,总体还很荒芜,公共交通也远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方便。她上班要先从东城坐公交车到西直门,再乘郊区车到卧佛寺附近,再步行二十多分钟,才抵达广慧庵;下了班,再这么跋涉一番。但她对养蜂研究乐此不疲,毫无怨言。只是有一回我问她卧佛好不好看,她才“啊哈”一声,笑道:“你看你看!我天天在卧佛隔壁,偏还没有去拜见过吔!”
我从王永强姨妈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蜜蜂的知识。古人咏蜜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常引出今人许多喟叹。姨妈却很理性地告诉我:“蜜蜂分三种:蜂王、雄蜂、工蜂。蜂王养尊处优,吸食蜂王浆;雄蜂的使命则是与蜂王交配以衍生族群;其余众多的都是工蜂,采百花成蜜,是它们一生的辛勤。只有工蜂生有蜇刺,但遇到危害以蜇刺自卫的同时,它们也便捐躯。”我说:“我要学工蜂的辛勤劳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姨妈颔首,却也笑着告诫:“不要以为工蜂就是钻花心,有时候,它们还到茅坑里采一点无机盐呢!再说了,蜜蜂的社会有一套复杂的伦理秩序,最好不要简单地拿蜜蜂来作类比!”
王永强姨妈于1990年因心梗去世。她一生也有不少的颠簸坎坷烦恼欠缺,但她走过的人生之路,没有哪一段哪一步是白走的。忆念起她,我脑海里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寒冬腊月,她穿着棉猴,裹着围巾,步行在大马路与广慧庵之间的丛林小径,周围的空气是严寒的,她身躯里的心是火热的。我过去的人生之路,有着她的启发,如今我寿数已超越于她,在这世间走过的路,又何尝是白走的呢?
2021年至2022年,我在喜马拉雅平台设立了个人电台,推出二百多期的系列音频,总题为“听见·刘心武·读书与人生感悟”,吸引到不少粉丝,交流互动中,收益匪浅。把文字转换为声音,是一种交流;把声音整理为文字,又是一种二度创作。读者有因文字而盼声音的,也有因声音而寻文字的。我庆幸自己生正逢时,在耄耋之年,竟能音频、纸书两栖,向自己的听友、读者交心,享受这巨大而切实的人生乐趣!
2022年5月2日
那次西行,公刘给我的印象非常之端庄、整洁、理性。我总以为诗人应该都是把浪漫形于外的,不修边幅,思维跳跃,言谈无忌,公刘却大异其趣。我和他谈《阿诗玛》,那部彝族民间长诗,最早的采风及整理,他都是参与的。一听要谈《阿诗玛》,他立刻郑重申明,大家看到的那部拍摄于1964年的《阿诗玛》电影,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确实遇到过太多的那种询问:“电影《阿诗玛》的剧本是你写的吧?”他必得费一番唇舌才能解释清楚。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不用解释。我读过他于1956年写出并刊发在《人民文学》上的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真是云霞满纸,诗意盎然,而且极富视觉效应,我读时甚至有种冲动:我要能当导演把它拍出来该多过瘾!又放诞坦言:“1964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的那个《阿诗玛》,只是有两首歌好听,反面人物极度夸张,场面不小却诗意缺席,我是不喜欢的!现在创作环境大好,应该把你那个剧本拍出来,让观众不是被说教,而是沉浸在人性善美的诗意里!”公刘听了先是惊讶,后来觉得我确实不是庸俗恭维,而是真心激赏他那个只刊登于杂志未拍成电影的文学剧本,又很高兴。他说:“25年后得一知音也是人生幸事。”我说要给他画像,画出诗人气质,他微笑,那微笑是觉得我狂妄但可宽恕吧。画成后,我要他在我的画上签名,他依然微笑,那微笑是坚定的拒绝。后来他的同代人告诉我,公刘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习惯,绝不轻易留下自己的笔迹,而且总是及时销毁不必存留的字纸。西行后我们多次见面交流。2003年他在合肥去世。画公刘的那幅“诗潮”,我一直保留至今。
谌容虽然比我大几岁,但我从未对她以姊相称,因为就步入文坛而言,我们算是一茬的。谌容于我,有值得大感谢处。我发表《班主任》以后,暴得大名,在各种场合出现时,多有人责怪我骄傲自满,我也确实有志满意得的流露吧。检讨、收敛都是必修的功课,但有时也深感惶恐,不知该如何待人接物才算得体,颇为狼狈。有次当时的业余作者聚会,谌容为我辩解:“我写小说的,看得出人的内心,心武不能主动跟人握手,生人跟他说话,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应答,种种表现,其实,都不过是面嫩,不好意思罢了!”她的这个解围,也真缓解了一些人对我的误解。我呢,也有值得谌容小感谢之处。谌容始终把自己的姓氏定音为“甚”,但当时若查字典,这个姓氏的发音必须是“陈”。某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就坚持称她为“陈容”,并且劝说她不要再自称“甚容”,而谌容绝不改其自我定音。我就在一次聚会时说,我们四川人就把姓谌的说成姓“甚”的,我有个亲戚姓谌,我就一直唤她“甚孃孃”,后来都在北京,还是唤她“甚孃孃”,应该在字典的“谌”字后也补上发“甚”的音,而不应该让谌容自己改变她姓氏的发音。后来在文坛上,绝大多数人提起她发音都是“甚容”,再无人站出来去“纠正”了,如今查“谌”字,则已经注明作为姓氏发音也可为“甚”。
谌容走上文坛的经历十分曲折。但自从1980年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收获》刊发,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项后,她一路顺风,有人戏称她是“得奖专业户”。那次西行,我俩也言谈甚欢。记得我偶然聊起,说“鼻酸”这个词不错,她的反应是:“什么鼻酸?依我看,要么坚决不悲伤,要么就号啕大哭!”我想这应该是她天性的流露。14年前,她在恩爱夫君范荣康去世后不久,又遭遇大儿子梁左猝死的打击。从此不见她有作品面世,也不见有信息出现于传媒。她淡出了文坛。也许,她是大彻大悟,把文学啊名利啊什么的全看破,在过一种“雪满山中高士卧”的神仙般生活;也许,她竟是在埋头撰写流溢自内心深处的篇章,将给予我们一个“月明林下美人来”的惊喜。
人生就是外在物件不断失去的一个过程。我给宗璞大姐的那幅贺生画的流失实在算不得什么。但人生也是努力维系宝贵忆念的一个心路历程。失画忆西行,我心甚愉悦。
女评论家李子云
评论家往往不被读者所重视,记得小说家、诗人的人很多,记得剧作家的人相对少一些,而记得评论家的人就很少了。
我认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评论家,她叫李子云。我跟她相识是在1987年,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这个年份,那时我收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去美国访问,她也受到了邀请,而且我们俩收到的邀请有时是重合的,经常被安排在同一天的同一地点做演讲,于是我们俩在美国常常是一起旅游,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我们俩一起去过的地方有纽约、波士顿,去过的学校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
李子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她是在北京上的初高中,所以虽然她后来长期生活在上海,住在淮海路上的一个小洋楼里,看着像个地道的上海人,她说的却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基本不说上海话。
她为什么会从北京去到上海呢?原来,当时她和她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住在北京,她念书时受地下党的影响,向往革命,于是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结果被特务给盯上了。有一天她回家后跟她父亲说:“糟糕,我有‘尾巴’了,怎么办?”
她父亲非常支持她参加革命,同时又很疼爱她,于是对她说:“好办,咱们全家迁到上海去,你在北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受革命影响的女高中生,咱们家都迁到上海以后,北京的特务系统上哪儿去盯你?也犯不上派人跟去上海。”
所以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她全家就在解放前夕从北京迁到了上海。她家原来比较富有,在淮海路上有小洋楼。到了上海以后她接着念书,上了大学,在她念大学期间,解放战争爆发,上海被解放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了,而是一个参加了革命的大学生,所以她很快入了党。
入党以后,因为她学的是文学类专业,本身又很有文学才能,所以就被分配在上海的文化部门工作。当时上海的文化部门的领导中有一位名人,名叫夏衍。
夏衍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篇揭露20世纪30年代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面。他还有一部有名的剧本叫《上海屋檐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电影事业方面不但是一个领导者,还亲自撰写电影文学剧本,比如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以及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剧本等。
当时他在上海领导文艺工作,需要一个秘书,最终从一众待选者中选中了李子云。直到后来夏衍调到北京的文化部做副部长,李子云留在上海,两人才分开。当了夏衍好几年秘书,李子云跟我说,夏衍对她有两方面的教益:一方面,夏衍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人,因此对她坚定革命信念、适应革命工作,有父辈般的关怀和指点;另一方面,夏衍是一位作家,能写报告文学,又能写舞台剧剧本,又能写电影剧本,所以对她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熏陶和指导也挺多的。在他们共事期间,夏衍发现李子云对一些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新放映的电影挺有一套她自己的见解,于是有意培养她,鼓励她写文学评论,李子云果真就写了一些评论,发表在一些重要的报刊上,反响不错。
改革开放以后,李子云是《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之一,她在《上海文学》重点负责文学评论这一块儿。她曾亲自撰写过一篇文章,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发表,署名是“本刊评论员”,宗旨是呼吁让文学回归文学的本位。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很多人都很佩服她。
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文学界和海外文学界的交流,渐渐地,海外的文化界也开始注意到她。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她是最早在中国用女性视角来评论女作家作品的评论家。当时西方的一些文化界人士一直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中国的文学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落后的,可没想到,失敬了,中国竟然也有李子云这样出色的评论家,能够用女性视角对女作家的作品进行一番独特的评论。他们很佩服李子云,所以就邀请她去国外演讲。
1987年那次出国演讲,我们俩恰好遇到一块儿了。原先我就认识她,但是不熟,后来我俩一路上说说笑笑的,慢慢熟悉了起来。她比我大,于是我叫她子云姐。
我们一起去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演讲。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世界知名的理工类大学,但是它也开设文科专业。去之前我有点发怵,我说:“子云姐,在耶鲁、哈佛讲一讲我倒是不慌,它们有东亚文化系,有汉学家,有学汉语言的学生,我用中文演讲他们听得懂,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理工类大学,它开设的文科专业只是陪衬,我去演讲,有人听吗?他们听得明白吗?”
子云姐说:“不要紧,虽然美国这些大学是英语教学,咱们不能用英语去演讲,但是他们有很出色的同声翻译。我就认识几位很了不起的同声翻译,能够很精确地把你表达的意思传达给听众,更何况还有中国留学生呢,他们也一定会来听咱们的演讲,会给咱们捧场的,乡里乡情嘛。你别怵,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有她打气,我心里有了点底气,没想到到现场一看,主办方安排的场子还挺大,是一个大礼堂,大概能容纳七八百人,我一下子又紧张起来。我演讲的次序被安排在子云姐前面,上台前子云姐跟我说:“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你慌什么?来的这么多人都是自愿来的,人家来了就说明人家愿意听。而且咱们中国改革开放了,人家也挺想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界有什么新气象。你就结合你自己的情况,放开了讲。”
我在她的鼓励下上了台,讲着讲着我逐渐镇定下来。我觉得我讲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底下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讲完以后有几个互动提问,问题提得挺好的,我自我感觉答得也不错。
我讲完以后就轮到子云姐讲了。我讲的时候她坐在第一排听我讲,等她上台我就坐到一角听她讲。说句老实话,我下台的时候心里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讲得不错,反响也很好,不知道子云姐她要讲什么,心想:她也能受到我那样的欢迎吗?结果我一听,她讲的是《从中国女作家的新作品看中国女作家写作当中的女性意识的萌发和升华》,这是一个带有一定学术性的题目,她讲得特别好,我很受启发。虽然我们来时一路上都在聊天,但是我还没有听她系统地梳理过到那个时期为止的中国女作家的女性写作。
她讲完以后,掌声比我讲完时的要热烈得多,而且互动也比我的更精彩。对于提得很刁钻的问题,她也始终微笑着,很从容地解答了。
她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下台,这时候我心中突然生出一个意象,我觉得她是一朵雅云。她梳了一个得体的发型,穿着一身蓝色的衣衫,一点都不俗气,也一点都不奢华,她那样不疾不徐地走下台来,像一朵雅致的云朵飘下来。子云姐也算是老革命了,她是一个能够把革命和高雅非常自然巧妙地融汇在一起的文化人。
很可惜,在2009年的时候,她不过是发了点低烧,到医院去打点滴,没想到出了一起医疗事故,造成了她的非正常死亡,我非常悲痛。
我永远怀念那一朵雅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