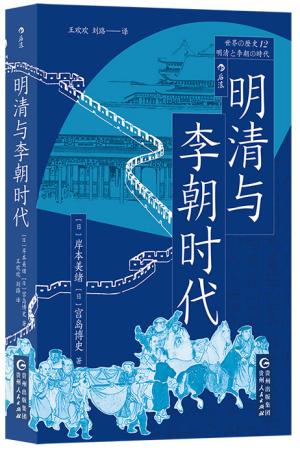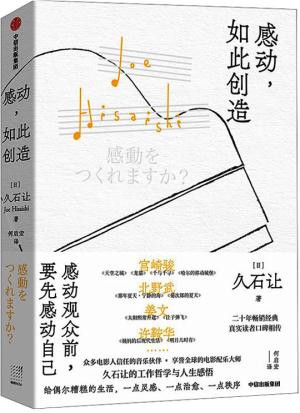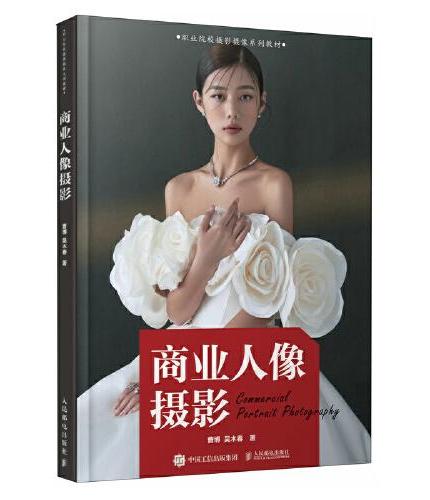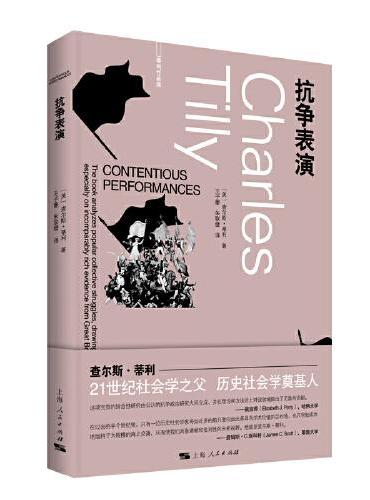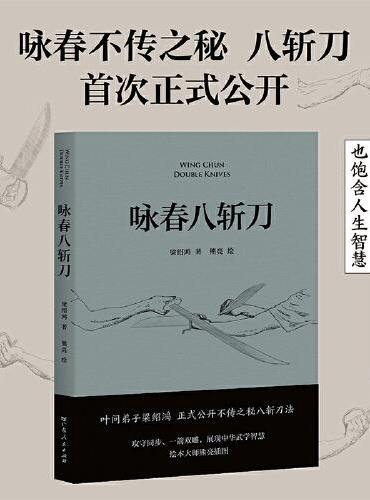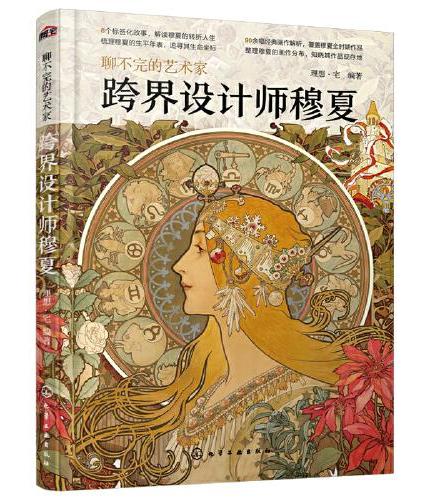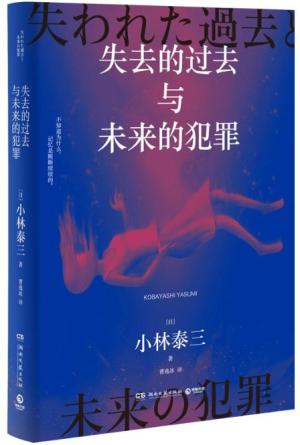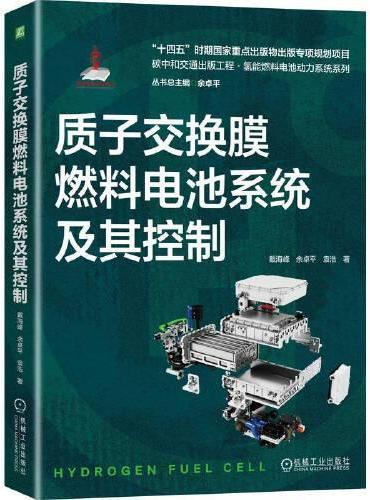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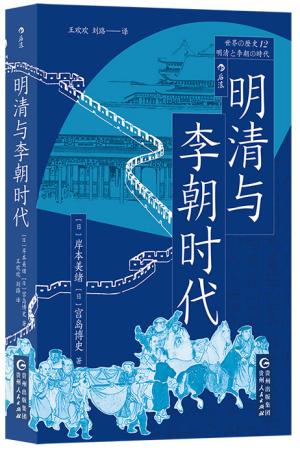
《
明清与李朝时代
》
售價:HK$
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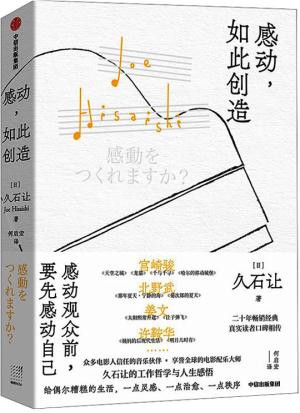
《
感动,如此创造
》
售價:HK$
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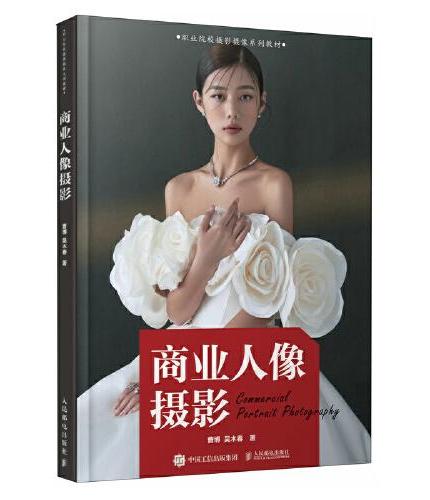
《
商业人像摄影
》
售價:HK$
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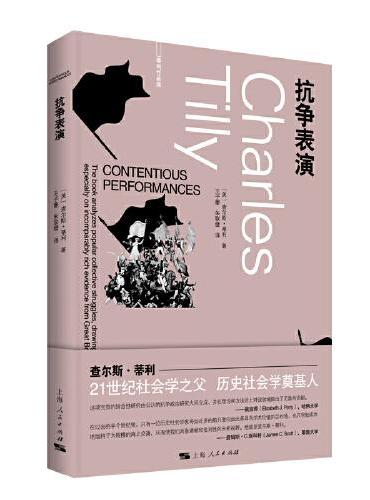
《
抗争表演
》
售價:HK$
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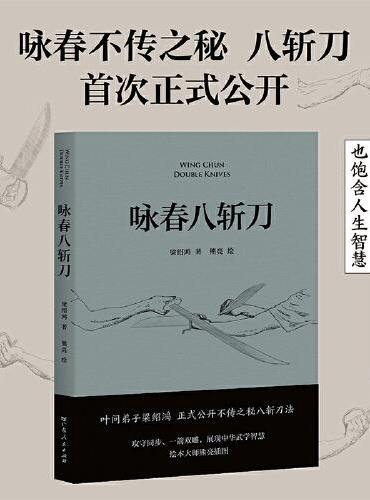
《
咏春八斩刀
》
售價:HK$
8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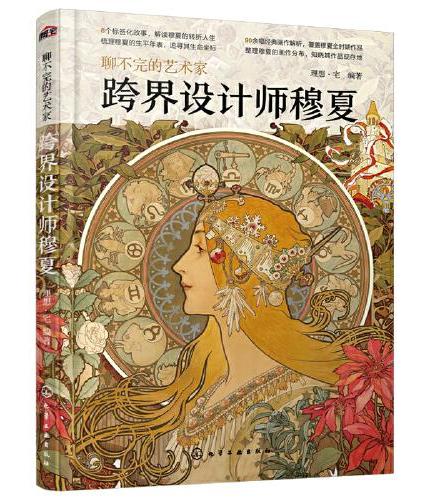
《
聊不完的艺术家:跨界设计师穆夏
》
售價:HK$
1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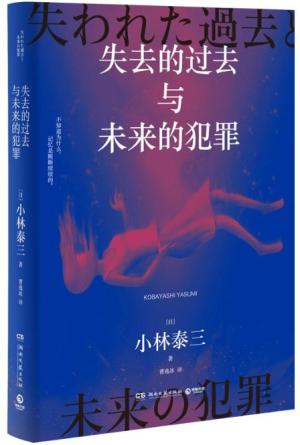
《
失去的过去与未来的犯罪
》
售價:HK$
5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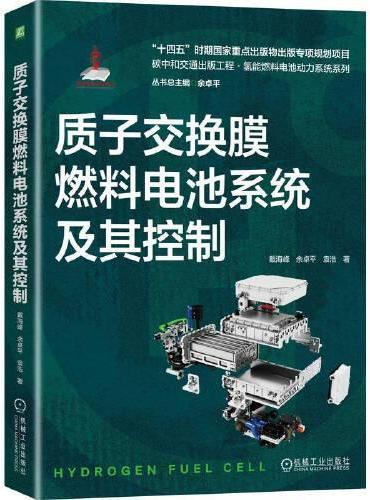
《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及其控制 戴海峰,余卓平,袁浩 著
》
售價:HK$
238.8
|
| 編輯推薦: |
|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为线索,由搅动人生的小小痛点出发,抖落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将文明进程的断裂与传承、保守与开放、交融与坚守,化为欲望个体的喧哗与沉默、谎言与伤痛、奇遇与选择拥有经典名著所的架构、气势与时空感受,个人身体的疼痛、家族的伤痕、民族的记忆交错重叠,三者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和人物身上得到集中的爆发式呈现以精雕细琢、浑然天成的描摹,完美展现了福建历史和文化的复杂面貌:中原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下的罕见文明样本反思剧烈变动、喧哗不止的当代文化景观,用冷感十足的荒诞故事,将人性暴露于欲望、情怀、历史、现实的种种裹挟下,书写渺小个体如何守护生命本质这一永恒的文学命题极具本土色彩和黑色幽默的疾病心理叙事,堪称现代寓言版的《疾病的隐喻》先锋文学和家族小说交锋之作。融合先锋小说的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带领读者探索汉语文学的未知之境明快、精巧、细密、有力的林那北式语言风格,展现了强大的文字包容性、生命力和当代感
|
| 內容簡介: |
《每天挖地不止》是当代著名作家林那北的长篇小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作为载体,讲述了福建沿海地区一个奇特家族百转千回的故事。从主人公赵定力口中一笔虚幻的财富出发,制造出一个真实的精神事件,将人生小小的痛点出其不意地扩大搅动起来,与古老的历史、人性的深度以及喧哗的当代文化景观紧密交织。
临海的青江村是北宋溃散前遣散到福州的皇族后裔所在地,村里有座罕见的以传统大漆做门的乌瓦大院。年底,大院的主人赵定力去福州城看病,回来后就开始不停歇地挖地。一个家族故事由此展开:酷爱大漆的祖母谢氏,下南洋在槟城谋生的祖父赵礼成、身为满族后代的母亲何燕贞、战争结束前随军舰逃往台湾的大伯赵聪圣……时隔百年,几代人的秘密为何在这时被提起?谢氏死前究竟把装有稀世珍宝的铁罐埋在何处?闻风赶来挖地的人越来越多,乌瓦大院的荒诞故事终将如何收场?缈小的个体能否穿透林林种种,守住生命的本质?
小说以一个百年家族的历史和一个当下的生存故事,把文明进程中必然遭受的断裂、传承、保守、开放、交融、坚守等概念,化为普通人的喧哗与沉默、谎言与伤痛、奇遇与选择,由此呈现中华文明在沿海地区得以保存并走向世界的历史与现实,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经典气质的文学时空。
|
| 關於作者: |
林那北
本名林岚,福建闽侯人,现居福州。当代著名作家,福建省作协副主席,《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锦衣玉食》《我的唐山》,小说集《寻找妻子古菜花》《请你表扬》《唇红齿白》,长篇散文《宣传队,运动队》等二十六部著作及九卷本《林那北文集》。小说被翻译成法、日、俄等语言译介到海外或改编为影视作品。
|
| 目錄:
|
章 铁罐
第二章 个故事:谢氏
第三章 第二个故事:赵聪圣
第四章 挖地吧
第五章 陈细坤回来了
第六章 第三个故事:谢氏与何燕贞
第七章 第四个故事:赵聪明
第八章 蓝花楹与髹
第九章 李翠月啊李翠月
第十章 细米死了
第十一章 打开西髹房
第十二章 大漆门
|
| 內容試閱:
|
章 铁罐
一
2019年6月底,赵定力进了一趟福州城。他独自去,说表弟谢玉非病了,其实是他自己病。身体这东西,每一个零部件既然长了,长年累月一成不变地长在固定位置上,就一定有它们各自的道理。嘴是用来贪吃的,屁眼是用来拉屎的,突然吃不香,拉不利索,人再上下不自在,一脚一脚踩下去都是虚的,全身力气都不知去向,不用说,肯定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不知道,越不知道越心慌。赵定力忍了一个多月,再忍就没法忍了,于是起个大早。
第二天他才回到青江。
青江不是江,是村子的名字,它临着海,是内海,水面四五百米宽,像一条海的尾巴偷偷伸进来,拐了几个弯后,与一条大江衔接到一起。江水从这个省西北部高高耸起的武夷山灌下来,横穿过大半个省,本来要直接去海里的,半道却被溜进来的海水一把拦住了。每天海水得涨得退,涨时水向西,退时水向东,但海水与江水的交汇地却固定不变,它就在青江村码头附近。站在码头砌得潦草随意的青石板上望去,水面有一道清晰的分隔线,一边浑一边清,一边黄一边蓝,倒也一直相安无事,几千几万年下来像约好似的,从来没有交错浑浊到一起过。码头上密密麻麻排着船。以前船小,看着像一群蚂蚁挤在一起,如今船大了,远远看去仍然像蚂蚁。如果再细看,会发现没有哪艘船是新的,船身上的清漆早已褪尽,船板被长时间水浸日晒后,身体又僵又硬,每一道开裂的纹路都像弃妇幽怨的眼神。从前村里的人并非都捕鱼,闲时也种地,该出海时就出,该下地时就下,海里取回荤的,地里扒上素的,一应俱全,荒年也不怕。但这些年男人女人一个接一个往外走,外面毕竟现钱挣得快,鱼就没人打,地也少人种,就一点点寂寥下来,村子便越发显出了无生趣的老态,日出与日落的演出在这里少了观众,每天都显得懒洋洋的。
村东头是几座山,不高,很柔和地微微上翘,山头彼此相连,拉出一个个柔和的半圆形弧线,看上去就有一股与人为善的谦逊。靠近村子的那座小山丘花瓣般缓缓上扬,周围簇拥着几百亩高低连绵的山地,种着茶、茉莉、果树,就是一些荒掉的地里,杂草也茂盛地连成一片,深浅绿着。整个村子其实就是山的延伸体,从东面向西面倾斜,斜到底,就是那个码头了。而东面半高城上,孤零零立着一棵大榕树,不算特别高,树冠却有五六十米宽,叶子密实有力,彼此互相重叠,树身差不多得两三人才能合抱。离榕树十来米远是一幢三进式的房子,风火墙围出长方形的大院子,墙根砌着一人多高的菱形青石,上面则是用糯米浆、碎贝壳和黄泥巴捣到一起的三合土垒出一尺厚、两米多高的墙体,抹着白灰。马鞍形曲线山墙的墙头上,乌瓦已有一些破碎或缺失了,歪七扭八,但大部分仍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即使有几片已经滑到墙的边沿,瓦身仍显出韧性与硬度,结结实实地支楞出一股谁也不服的气度,举在半空示威着。
整个青江村没有第二幢房子能及它一半阔大气派,也没有哪家用这么黑沉厚实的瓦片,村里人就把这座房子称为乌瓦大院。院子左侧还有一扇拱形偏门,门上方挂简陋的牌子,杉木底、黑漆字,正楷写着:谢婆鱼丸店。大院是赵定力的,鱼丸店也是赵定力的。谢婆则是他祖母,有名字,叫春妹。
已经七十八岁的赵定力是村里的名人。往前几十年,他的伯父赵聪圣和父亲赵聪明比他出名。再往前几十年,他的祖父赵礼成又比赵聪圣和赵聪明更有名。现在赵聪圣、赵聪明和赵礼成都死了,赵礼成死在去马来西亚槟城的海上,赵聪圣和赵聪明本来也应该死在槟城,但后赵聪圣死在台湾,赵聪明则死在乌瓦大院。大院还死过赵定力的母亲何燕贞和个子娇小的谢春妹。建起乌瓦大院的人就是谢春妹,建房的钱则是赵礼成从槟城寄回来的。现在谢春妹死了,赵礼成死了,赵聪圣、赵聪明死了,何燕贞也死了,剩下赵定力。
年轻时赵定力是村里个子的人,高却瘦,主要是骨头细,肉怎么长也撑不起来,看上去就像一条竖起来的带鱼晃来晃去。现在他背驼了,脚也用不上劲——人老不都是从脚开始的吗?腿太长,自然也更容易弯,膝盖往前拱,走起路来背、腰、腿、脖子,浑身到处都是长短不一的弧线。老了,所以病就来了。究竟什么病呢?他得去趟城里的医院。
医生就是表弟谢玉非,比他小十四岁,已过了退休年纪了,却还没正式退。当医生就是这点好,越老越值钱,白发和皱纹都可以拿来当金子贴门面,贴多了,反正不管真假,连自己也慢慢信了。赵定力以前很少麻烦他,一辈子不麻烦才是人生赢家哩。诊室不大,摆一张白色旧桌子,除了谢玉非,还有两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坐在桌子的对面,也穿着白大褂,但两眼怯生生的,浑身都是学生味,一看就是来实习的。
赵定力在桌子侧面的椅子上坐下,先盯着谢玉非的白大褂看,布已经不太白了,泛着黄,有点皱,袖口那里还微微起了一层细密的毛边。在医院这种地方混久了,自信是靠一个个倒霉的病人、死人赠送的,赠得越多,脸上的自信就会堆得越丰厚,谁还在乎披在外面的一层衣裳?然后赵定力眼光慢慢上移,移到谢玉非脸上——脸皮居然是粉色的,其实是因为白,色素浅,皮底下布着密密的血点,白和红混在一起,就成了粉。像所有的病人一样,赵定力开始惶惶说起自己身体情况,谢玉非问一句他说一句或者三五句,说时眼睛一直盯着谢玉非。表弟脸上在起变化,皮还是粉的,但眉头那里曾一闪而过地微微皱几下。赵定力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呢?他十四岁那年舅舅来信,说已经生了三个女儿的谢家终于添丁了,早产,只有四斤半。父亲赵聪明于是让他进了一趟城。他提着自家养的两只公鸡和一筐鸡蛋跨进谢家,看到在床上一团小小的肉,脸像宰杀时忘了放血的死猪肉,红得发紫,鼻头堆满星星点点的黄斑,眼紧闭,双拳握住举在肩膀上方抽搐般胡乱舞着,气都喘不匀。这是他次见到谢玉非。
谢玉非说:“你先去做个心电图和血凝全套检查吧,看能不能做肠镜。”
“肠镜?”他嘟囔着,定定看着谢玉非。已经活了七十八年他都不需要做这项检查,突然要查,出什么问题了?人一生下来就明里暗里配齐了各种器官,看上去它们像是为了服务主人而来的,却在几十年里反复向人索要服务,无论哪一个出点毛病都要整得鸡飞狗跳。现在轮到他,他的肠子到底怎么了?
谢玉非笑了笑。“毕竟有年纪了,”他说,“有点毛病很正常。你先去缴钱,然后去抽个血,再查一查心脏。哦,我走不开……”说着他冲对面的实习生抬抬下巴,其中一个清瘦的女孩马上就站起,对赵定力一笑,说:“我是小林,我带你去。”
赵定力只好站起,跟着小林在医院各处走了一圈。几年前他曾来做过青光眼手术,与上次比,医院主楼扩建了,旁边还立起一幢二十多层的新楼,看上去宽阔了很多,但来看病的人却更多。上次挂号、缴费、取药的人挤挤挨挨的,这次更是密集得像是来抢钱,迟一步仿佛就吃了大亏。究竟是生活好了,身体反而更差,还是腰包鼓了,能看得起病的人更多了?不知道,反正乌压压一片,每个有病的身体互相毫不见外地碰来碰去,气息呼来呼去,脸色都不是太好,表情也基本没有。瞅准一个空隙,赵定力边走边侧过头问旁边的小林,他说:“我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小林客气地笑笑,说:“先查一下。”
赵定力突然发现笑这东西真是再恐怖不过了,刚才谢玉非的笑,现在小林的笑,都有一层阴森之气,嘴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根本不知道里头究竟藏着清水还是浊泥。他觉得这样不行,得继续问。他说:“要多久才能查出来?”小林说:“不用太久,一两个小时吧。别急,您先安心等着。”
能不急吗?她越说别急,赵定力越急。但急又如何?消化内科诊室外的走廊上有几排蓝色塑料椅,抽过血转回来后,小林让他坐到那里等着。两个多小时后,报告单出来了,谢玉非低头看一眼,说:“你身体素质不错啊,比预计的还好。那就做个肠镜吧。”
赵定力眼虽看着谢玉非,视线却是虚的。他注意力在脑里,脑里正把谢玉非刚才说的话又细细过了一遍。医生这个职业某种程度上跟演员是相似的,越老的医生在病人面前就越能演,尤其是当这个病人偏偏还是医生的表哥……亲情在这时候显得多么奇怪,特别近又非常远。赵定力吸一口气,他说:“你什么都不用瞒我……究竟我有没有问题?话直接说,我也好安排剩下的日子。”
“说什么话啊!”谢玉非打断他,又笑起,“你看你,还是老毛病!这都还没查呢,怎么就有问题了?你这样还真应该尽快查一一而且,鉴于你家的情况,还是查一下好。有病就治,没病就放宽心。有麻药的,别紧张。哎,这两天在家你都吃些什么?”
赵定力说:“我没吃什么,我吃不下……”
谢玉非打断他:“我的意思是吃什么油腻的东西吗,鱼呀肉呀之类?”
赵定力愣愣地看着他,半晌才摇头,“鱼肉都不想吃,吃了就乱拉,拉完又几天不拉。”
谢玉非说:“既然这样,我看就干脆直接做了吧,晚上不用回去一一噢,我家也可以住。我安排下,争取明天早上就查了。”
“这么急?”赵定力感觉到问的时候自己舌头都有点打结。
谢玉非边在处方签上写着边说:“也不是有多急,你既然来了,索性就查了吧,免得到时候还要再跑一趟。一会儿我就下班了,你先在外面等着,到时跟我车一起走。”说着他把处方递给对面的两个实习生。赵定力跟着小林出门,缴了钱,取了药,然后等了一阵,太阳落下去后,真的就坐谢玉非的车回去,在他家住下了。
谢玉非是一年多前刚搬到这里的,是个别墅区,全部是独栋、双拼或者联排的房子。谢玉非把车停在一户带有四五百平方米草地的独栋别墅前,到处是花,院子外圈围起的篱笆上,紫红色的三角梅和橘红色的炮仗花已经开始攀爬,人口则是一道挑高的拱形门,两旁黑色大理石砌出来的方形大立柱上,端正立着两盏古铜色的欧式复古灯。赵定力在进门前迟疑地停下,以前只在电影电视里看到外国人住这样花花绿绿的房子,居然近在眼前的谢玉非家也这样了。谢玉非笑起,说:“这全是小娥弄的,这边房子还在建哩,她就提前雇人把谢家大院后花园里的树能移的都移了过来。人搬个家都累半死,她却让树也跟着搬,就是吃饱给撑。”赵定力点点头附和,心里却一阵诧异。谢家大院花园居然有这么多树?他完全没有印象了。
小娥是陈小娥,谢玉非的妻子,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圆脸,中等个,架一副眼镜,看上去跟普通路人没有两样,没料到种起花草来竟这么洋气。于淑钦有一阵也喜欢种花,但只是用检来的大小不一的盆盆罐罐胡乱种,哪像陈小娥这样有章有法成规模地种,就如同都是钢筋水泥堆出来的房子,城里这些别墅和村里胡乱搭起的房子哪能是一回事?乌瓦大院后院比谢玉非家这个院子大,要是按陈小娥这种捣鼓法,非得弄成小公园,而于淑钦想到的无非种点菜罢了。青江村离城里二十公里左右,这么近,很多东西还是不一样。
这个房子赵定力是次来。十多年前,市里把唐朝时开始陆续兴建的坊巷格局的南后街全拆了,弄成旅游景区,整天挤满人,慢慢周围的街坊也被圈人,包括跟南后街只有一路之隔的青灯巷。谢家的老房子就在青灯巷口,两千多平方米,前后共五进,拆迁时补偿了一大笔钱——究竟多少,赵定力其实并不知道。房子拆之前谢玉非曾打电话问赵定力要不要去看看?赵定力脱口问看什么?谢玉非顿一时,半晌才又重复一句:“你确定,真的不来看吗?”赵定力没有犹豫,还是说不看。那幢房子这几十年里他已经去得越来越稀疏,但毕竟是熟悉的,还有什么稀奇可看的?过一阵就听说谢玉非买别墅了,听说而已,听过就丢脑后,现在一看,还是一惊。得花不少钱吧?是拆迁补偿了很多钱,还是谢玉非本来腰包就很鼓?
谢家大院是谢氏的父亲谢瑞林置下的,前院是春来药铺,一格格药柜子顶天立地围成一圈,谢瑞林在药柜前摆着桌子坐诊替人看病,开了方,旁边直接抓药,左右手都赚钱。院子后面还有四进,则是住人。已经传了几代,每代各自分家,房子早就不是当初的气象了。大部分人几十年前拖家带口去了台湾,美国、北京、上海也另有几支,后留在老房子里的只剩下谢玉非一家。但房子要拆时,各房都派人从各地回来处理房产,却没有哪一片瓦哪一块砖跟赵定力有关,谢玉非多让他去看看,有什么可看的?他不去。细算起来,谢玉非的父亲是赵定力的表舅,表舅的父亲就是赵定力的舅公谢乐施,赵定力祖母谢氏的大弟。也就是说对于那幢前后五进的大院子来说,赵定力和谢玉非一样,都是第四代子裔,理论上老房子跟赵定力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政府给老房子拆迁补偿,赵定力却啥好处也没得到。现在他有病了,去得到老房子那么多好处的谢玉非家里住一住,确实也不算什么过分之处啊。
陈小娥很晚才回来,她退休后被私立中学聘去上课。说到底还是有学问好,社会越正常学问越管用。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读博士,刚结婚,娶了个同样在那边读博士的上海女孩做妻子。这些都是谢玉非的底气,一家人没一个季种,谢家嫡传下来能混成这样,也算祖上积德了。但祖上对旁枝爱理不理,谢氏从城里嫁去青江村,运气似乎就被谢家截留了,赵定力现在什么都没有。
住在谢玉非别墅的这一夜,赵定力基本上没有合眼。早上从乌瓦大院出门时本来跟妻子于淑钦说好当天就回去,结果没回,竟住到谢玉非家里了。他给于淑钦发微信说要迟一两天回,于淑钦好像也没太意外,只回了他一条微信说:“就你贱,他家有什么好住的?”话里明显带着怨气。他来福州,于淑钦以为真的是探表弟的病,什么病她都懒得问。于淑钦只见过谢玉非一次,是八年前结婚不久,赵定力带她进城去谢家大院,算串个门认个亲。刚迈进去时,于淑钦还是很恭谦的,笑得老老实实,但很快笑就凝固住了。谢玉非根本没拿正眼瞧她,陈小娥更没有。作为主人,他们虽然都客气地招呼坐招呼喝茶招呼午饭,但脸都只冲着赵定力,话当然也定向说给赵定力听。也就是说谢玉非和陈小娥欢迎的是表哥赵定力,而作为表嫂的于淑钦,却一星半点的尊重都没得到。谢玉非后来把自己的想法私下告诉了赵定力,他的意思是,即使是这么大年纪了,再婚仍然是值得鼓励的,但如今又不是从前,无论如何都不该再把门槛降得这么低吧?凑合真没必要啊。女人多如牛毛,怎么能把文化程度这么低、看着又这么土气的女人娶进门?好歹谢家当年在福州城里也算一户掷地有声的豪门啊。赵家不是谢家,但至少算半个谢家,怎么说也是家门被辱了。
谢玉非又说:“我老婆也这么认为。”
单单自己的表哥不满就算了,陈小娥是外人,怎么轮得到她说三道四?赵定力当时嗯嗯几声忍下,明白这些话很得罪人,他必须全部吞在肚子里消化掉,但某次闲聊时,不知怎么还是嘴一松就和盘对于淑钦说了出来。一说完他当即就后悔了,但话既然已经出口了,就无法追回来。于淑钦脸马上拉长了,翻出白眼,重重地骂道:“放他妈的狗屁!”
她先是用重庆老家话骂,又用福州话重复了一句。在于淑钦没娶进门之前,赵定力完全没有想到女人竟能有这么大的嗓门,平日里,哪怕喊吃饭,门板似乎都会被震得颤动起来。一开始真不习惯,但慢慢他就无所谓了,是耳朵先开始适应,然后他觉得这样也好。乌瓦大院已经安静了这么多年,太静了,终于有一个女人来了,声音以一当十,把闲适太久的屋檐门板震一震,人气就不免涌了出来,从这一点看,意思还是有一点的。
那次之后于淑钦再没去过谢玉非家。所以赵定力说要去福州探望谢玉非,于淑钦是不以为然的。一个当医生的人需要你一个乡下人探病?于淑钦嘴一撇,一脸都是不高兴。赵定力没顾得上她高不高兴,他是为自己去的,每天活在七上八下中,他不去不行。
谢玉非开的药叫“甘露醇”,自色粉末状的。谢玉非说已经约好,肠镜明天就查,得把药先喝下清肠。家里号铝合金锅被拿出来,泡上开水,晚上喝下一大锅后,拉了一夜。本来凌晨还得再喝一锅,然后再拉,再然后就是一大早坐谢玉非的车一起去医院,进人检查室。但早上赵定力独自走了,他没有把另一锅药水喝下。
别墅共两层,谢玉非和陈小娥睡楼上主卧,赵定力睡楼下客房。与主人隔开一层楼板,倒让人松弛了很多,但赵定力哪里睡得着?上一趟刚拉好,转眼又急急坐到马桶上了,裤子像手风琴似的拉上折下,一波未消一波又起。这些日子他就是因为拉稀拉怕了,才进城找谢玉非,哪想到谢玉非给他药,让他这一夜肚子像一池堆满鱼的水,反复咕噜闹腾。他腿发软,不敢再喝,也不想查了。查就能查出是与非?即使查出了,接下去怎么办?开刀、化疗、没完没了地吃药……这么一想,心就荡到半空。趁着谢玉非夫妻还睡着,他在马桶旁抽了一大把卫生纸出了门。走之前他留下一张字条:“我先回家去。抱歉打扰你们了。”
天还没亮,到处都很安静,没人,没车。昨天坐谢玉非车从医院到这里,车拐进小区前,他往窗外看,恰好就看到路边戳着一幢斜屋顶的房子,外面挂着WC的标志。当时谢玉非还跟他炫耀,说这一带别看离市中心远,但市政设施已经很到位,你看连公共厕所都弄得这么漂亮了。赵定力出了大门,保安警觉地盯他看几眼,他屏住气,把身子挺了挺走过保安岗,然后找到厕所,确实漂亮,外型也跟一座小别墅似的。他在厕所后面的草丛里坐下,肚子还在响,仿佛一台热闹的戏正在里头开唱,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老实守着这个漂亮的WC,随时一跃而起,大跑几步,朝着蹲位火速褪下裤子。
这些日子,拉稀对他是件多么习以为常的事,他的肚子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造屎机器,哪想到喝下谢玉非开的那一大锅药水后,他才领教了拉稀的真正伟力——每根肠子都像安上了抽水泵,马达开足,轰鸣震天。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瘪瘪的,没有任何肚腩,它究竟靠什么藏得下这么多的屎?而且居然这么臭,是几十年老粪坑被使劲搅动之后才会有的那种恶狠狠的腐臭味。他揉揉肚子,如果屎这么多是个意外,那么肚子密封性这么好是更大的意外。屎关在肚皮里平时含而不露,一旦冲出来,竟然如此刺鼻。
所有香的东西吃下去,经过一个肚子,为什么竟臭成这样?
太阳起来了。太阳升高了。太阳弱下去了。肚子终于也慢慢消停下来,这期间他进出厕所共六次,有时拉多些,伴随着不绝的响声呈喷射状,有时好半天才安慰性地勉强挤出一点;有时肚子揪起,仿佛要滂沱,结果蹲半天却毫无建树。世界这么大,但至少这一天,除了厕所,其他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竟然活成与屎奋斗,终于便意没有了,他一开始还不敢相信,踟蹰一阵,捧住肚子像是跟它商榷,确认后才敢离开,先拦的士,再转公交。无论如何也得走了,再迟点公交车就停了。
从城里去青江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坐船,沿江而建的公路是四车道的,铺着沥青,因为黝黑显出几分厚道。公交车也早通了,车站在村口西侧。他下了车,沿着那条十几年前槟城华侨集资捐建的水泥路慢慢走到村东头,爬上坡,跨进乌瓦大院。这一整天除了在路边买一瓶矿泉水喝下外,他什么都没吃。其实他什么都不想吃,喉咙那里像谁用塞子堵酒瓶似的,嵌下一个大塞子,气都喘不过来,哪里还吃得下?
二
乌瓦大院那扇对开的大门虚掩着,中间竖着一条巴掌宽的缝。离着还有大老远,门就被顶开,一条浅色的光蓦地闪出来。细米,米白色的拉布拉多犬,它凭嗅觉提前知道赵定力回来,兴奋跑出,吊着舌头,发出吱吱吱的呻吟,并立起半个身子扑向他。狗真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东西,爱恨都不掩饰,你低了就看你低,你饲养了它就排山倒海对你好。赵定力侧过身,伸出手在狗头上摸两下。“细米,好了好了,回家吧。”他说。细米听懂了,绕着他腿转几圈,鼻子嗅着他裤管,好像那里有什么意外。难道是屎不小心喷在上面了?这让赵定力心里滑过一丝尴尬,就不想再跟细米纠缠了。天已经快黑透了,门打开、关上的声响和太阳对着干,白天阳光一烈,门的声音就黯下去,晨昏时却格外刺耳,轻轻一碰就吱地叫起。
一张女人的脸从屋里探出来,紧接着整个身子就跨出门槛,立在过道上,看着赵定力。“怎么才回来?”于淑钦有点不满。“嗯……”赵定力一时找不出什么话来。于淑钦唇角动了动,身子一扭,抬腿又往屋里跨进去。
赵定力站在原地,叹了口气。他前后共结过三次婚,于淑钦是他第三任老婆。前两任他从来没怕过,多喜欢、心疼或者在乎,但于淑钦不一样,他说不清哪里不一样,不是喜欢,没有心疼,但也还是在乎。
乌瓦大院是座三进式青砖木构的院子,进了门迎面就是一个凹下两个大台阶的天井,两侧各有两间并排的偏舍,福州人更习惯把它们叫作披榭,读音相似,但写起来雅致了很多。披榭比后面的厢房低一尺,木板墙,每间都有一道齐膝高的门槛,跨出门槛,向左向右分别走向厅堂或者大门。披榭第二间是厨房,这个格局在谢氏手上就定下,始终没动。这几年村里老房子除了乌瓦大院外,都已拆光,没拆之前,他们的厨房都习惯安在后院,紧挨着厢房,这样烟囱就出现在整个院子的中间段。福州人觉得炊烟其实就是房子的嘴,高出屋顶一大截的烟囱日复一日吐出自烟,烟像一面帅旗在空中飘着,向八方证明屋里住着活人。同时烟囱还能把天地之气徐徐吸人,房子才能喘过气来,不腐不蠹,而紧挨大门的披榭便于出人,别人让用人或老人住,谢氏直接当厨房和饭厅,所有来客走到披榭就止步了。与前天井相连的是前厅堂,厅堂中央摆一台棕色翘头横案,案前是一张用旧床板改的大桌,铺着自毡布,上面放着砚台、墨汁、笔架等物,两侧是四间高阔宽大的东西厢房。从前厅堂太师壁侧面绕过到后厅堂,跨过门槛也有一个与前天井一样长宽各三十米的天井,天井与花园相连处是两间长方形的瓦房,中间有扇矩形门,穿过这扇门就到了比两个天井合起来还要大的花园。
除了三进主宅外,厅堂的右侧有一道拱形小窄门通向旁边的花厅。花厅前后也有四个房间,每间都不足东西厢房四分之一大,也矮一截,因此光线就差了不少。乌瓦大院建起时,人就不多,房间从来没住满过,人多的是村大队部搬进来办公那几年,后来大队部又搬走,院子就重新空下来。可能是习惯,从谢氏起,就一直只使用右侧的房子:右披榭一间做厨房,一间做饭厅,而饭厅里除了摆一张小八仙桌,靠门槛的侧边还摆一张两米八长、一米八宽的茶台,是块嵌有青石马槽的沉船木做成的,一尺厚,木上用细瓦灰调红锦漆裱上苎麻布,一层层阴干磨平,然后红漆戗金粉抹上,台面左侧有两枝梅花伸出来,枝条是黑色漆皱,花瓣是寿山石薄片嵌的,两个粗大的桌脚则上着黑漆,贴过金箔,打磨出犀皮肌理,已经有百来年了,被茶水无数次浇过泡过,竟色泽不改,锂亮如镜,摸上去,细腻度与婴儿皮肤相似。这就是大漆的好,它们自己有命,人在时光中老去,它们却一点点往外活,日日常新。
于淑钦在花厅,两人的卧室都安在这里。赵定力一路找去,边走边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去医院的事跟她说一说。昨天去之前不说,是因为他自己心里不踏实,也隐约有些忌讳,怕一说就成真了。这些日子他动不动就拉稀腹胀的事,于淑钦确实不太清楚,他只字不提。如果换一个人,即使他闭口不说,日夜待在身边这个女人多少也应该注意到。又不是多么复杂高深,吃喝拉撒,日子里重要的事总共只有这四件,都明明白白摆在眼皮底下,可以不知详情,不能不知大概。可于淑钦就是连大概的一半都所知不多,她就是不知道。“没心没肺”这个词以前赵定力一直觉得在远处,跟他没有半点关系,结果于淑钦一进门,他就不得不领教了。他因此常想起李翠月,李翠月是他个老婆,是父亲赵聪明死去前半年帮他办的亲事,然后在赵聪明死后第九天就不见了。当时说是去对岸的姨妈家玩,可出了门就消失了。跟于淑钦正相反,李翠月唇像被粘住了,整天抿着,万不得已了,吐出的话也短、细、轻。李翠月总共只在乌瓦大院生活半年,赵定力还猜不透她,她就走了。女人心思太细密是过不得日子的。于淑钦脑神经粗得跟水泥柱似的,可以细一秒,却细不了第三秒。偶尔她也奇怪赵定力吃得怎么越来越少,随口问了,赵定力说没事没事。七十八岁的人了,少吃点确实能有什么事呢?所以看上去于淑钦也没当一回事,相信他确实没事。
细米仿佛怕他迷路了,跑前跑后,一路把他带到卧室。于淑钦的卧室不是他的卧室,结婚第二个月他就搬到隔壁一间了。非常意外,女人也会打出那么巨大的呼噜,雷声似的一道接一道,拖出长长尾音。原来人跟人吃喝拉撒的区别如此大,赵定力不能睡,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经常在夜里醒着。死是永远的睡,所以活着时少睡似乎就占了便宜,然而不行,不睡脑子就嗡嗡的,胸口堵。于淑钦躺在旁边,他的不能睡从大半夜扩大到一整夜,一脑袋的嗡嗡声就从黑夜一直延续到自天。忍了一个月,他不打算忍下去,就搬到另一间。于淑钦当时意外了一下,但也不介意,仿佛之前早就想到了,看上去挺高兴的。
于淑钦屋里这会儿乱糟糟的,棉衣、毛衣、毛裤摊得到处都是。已经人夏了,天很快会热得划根火柴就能烧起来,为什么上个月刚收拾起来的冬装要重新拿出来?一见他进门,于淑钦就说:“细萌让我不用带厚衣服,可不带的话,冬天怎么办?那边会下雪啊。”赵定力看着她,一时脑子没转过来。于淑钦看到细米低着头在衣服上钻来钻去,恼火地喝起:“细米出去!”细米一点都不肯搭理,它看上去很兴奋,鼻子抵到衣服上嗅着。于淑钦一把抓住细米的项圈往外拖。细米屁股往下坠,不情不愿的,后还是被拖到后面的花园。厅堂太师壁侧面有一扇门,她返身就带上了,阻断细米跑出来的路。
细米是八年前于淑钦嫁进来时带来的,事实上现在反而赵定力跟它关系更好。原先听说这是一种从国外来的狗种,赵定力还以为它有多高贵难伺候,没想到整天傻呵呵地开心,肚子永远没有饱过似的,给任何东西都吃相难看。每次正吃什么时,只要细米出现,赵定力都管不住手,一定得匀出一点给它。细米尾巴三百六十度风扇般殷勤打转,这种全心全意的感恩,人有吗?即使有也不可能像细米这般纯粹彻底。这个星球再没有任何其他生命可以做到这么极致吧?狗对主人的爱甚至比被反复歌颂的母爱更宽广激烈。
于淑钦重新走回卧室时,赵定力还站在原地,低着头,眼光仍然盯住满地的冬衣看着。见于淑钦进来,他吸一口长气,缓缓吐掉,说:“你这是……要去哪?”于淑钦说:“去北京呀。中午不是给你发好几条微信告诉你了吗?你理都不理。我打电话去,结果关机。”
中午?中午赵定力正独坐在公共厕所后面的草丛中,一心只等着肚子里残留的那些水状臭屎往下走,一直走近肛门口,然后他嗖地冲进厕所,解腰带,下蹲,让屎走好不送。他没有听到手机响过。他手伸进裤袋掏出手机,摁几下,屏幕是黑的。没电了。手机是八年前和于淑钦结婚时买的,虽用得不多,但手机跟处女一样,再不用也照样会一天天老去。先老化的就是电池,已经不耐用了。谢玉非家里肯定有通用的充电器,但他没有开口借。昨晚他要全力对付的是肚子里那些弯来绕去挤在一起的肠子,哪还想得起手机?
于淑钦是重庆人,初嫁到青江村的邻村紫江村,生有一女一儿后,日子渐渐好转,网会织,船会驶,浮箱虾类贝类会养殖了,连本地话都说得很地道,乍一看都没有半点外来者的痕迹。前夫陈卫财个子矮黑着脸,几天不说一句话,但男人脸黑有什么关系?不爱说话更不是毛病,只要能种地能打鱼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后来才知道陈卫财脸不是没来由地黑,那股黑是从腹底深处肝那个位置那里一路向上蔓延的。有一天他突然开始爱说话,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就是“疼”。后来声音越来越大,频率也越来越快,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的肉也越来越少,好像肉是被喊疼的声音带走的。终于有一天他瘦得连床都下不去,肝癌晚期,治了一年多,还是死了。家里刚有的一点积蓄都耗进去了,人财两空。好在儿女很争气,都考上北京的大学,先是女儿陈细萌,然后是儿子陈细坤,一个学外语,一个学中文,毕业后都留在京城工作。
于淑钦说:“细萌昨晚打电话来,说胎动不正常,她很害怕,让我过去。”
陈细萌去年五一节结婚,已经怀孕八个月了,于淑钦要去的就是北京女儿家。
赵定力咳起。这事太突然了,陈细萌怀孕他知道,但他从来没听于淑钦说过要前去照顾。之前明明说好是陈细萌的婆婆去,怎么突然换成了于淑钦?于淑钦说:“小齐他爸昨天突然脑中风了,还在医院里抢救哩。”
小齐就是陈细萌的丈夫,与陈细萌是大学同学,父亲老齐以前在建筑工地挑砖,六十岁都不到,没想到却突然中风倒下了。于淑钦说:“这不就乱了套吗?小齐的妈妈得在医院伺候,她去不了,只好我去嘛。”说这话时,于淑钦嘴咧得很大,像是这件事她已经盼了很久。赵定力脑子麻了一下。于淑钦会像李翠月一样也转眼消失吗?
李翠月走后第六年,赵定力娶过第二任老婆。有人把重庆女子罗玉玲带来了,个子矮小,嘴大眼细鼻子塌,但赵定力无所谓了,李翠月之后他什么都无所谓,将就着也凑合吧,在床上反正一样可用。用到第三年肚子大了,分娩时却生不下来,卡在半道,母子都死了。站在罗玉玲尸体前赵定力想到李翠月。李翠月结婚半年都没怀孕,他们从来没在同一张床上睡过,不可能怀。幸亏没怀啊,要是怀了,生时李翠月也可能死掉——相比较,走了怎么都比死了好啊,他不愿意李翠月死。他也不愿意罗玉玲死,但罗玉玲还是死了。之后赵定力就一直一个人过了,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不算什么了。每天种茶、制茶和喝茶,他把时间都花进去了。用茉莉花容茶时,一层花一层茶叶铺好后,过一阵过去搅一次就行,他却常常不走,蹲一阵站一阵,围着箩筐转,很像从前站在田径场边,给比赛中的人喊加油。整个过程他嘴张着,毛孔也张大,很贪婪地大口吸着,似乎跟茶争着被容。茶之外,仍然剩下一些时间要打发,他就站到厅堂那张旧床板改的大桌前写字。一岁多谢氏就让他拿毛笔了,六七岁起半村人的对联都出自他手。一年又一年,日子总之一晃,就这样过去了,再有人托媒,他都摇头,或者干脆掉头走掉。罗玉玲死时,一地的血,从里屋一直溢出来,一开始是鲜红的,慢慢就暗了黑了,后凝结成疤,硬邦邦地像铺着一块劣质地毯。到处是血腥味,味渗进了四面木板墙的缝隙里,再一点点缓缓往外吐出。三年?八年?不记得了,反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赵定力都活在罗玉玲的血气里,早晨闻着它醒来,夜里再嗅着它睡去或根本无法睡,脑子里就再没有女人的影子出现过了。不料八年前突然又结婚了,新娘就是于淑钦。从李翠月到罗玉玲再到于淑钦,掰指一算,赵定力的老婆一共三个。并不是所有人一辈子都可以有三个老婆的,他有,但这并不值得庆幸。
八年前是同村王瑞生的老婆徐巧琴突然到乌瓦大院,带来了于淑钦。那天赵定力正站在厅堂写字。他订有报纸,村里私人掏钱订报纸的只有他一人,每天看过,都攒在那里,这会儿铺到桌上,沾上墨写几笔。侧脸见徐巧琴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陌生人,大脸大眼,连凸到唇外的牙齿也一颗颗像被水泡得肿起来的,岩石般肥大结实有力。他点点头算打过招呼,笔并没有停下。两个女人进大门后从披榭前的石板道一直走到厅堂,在大桌旁站定。“哇,你看看你看看,写得这么好,是不是很厉害!”徐巧琴指着报纸上的字,口气明显是夸张的。一张报纸已经划拉满了,赵定力放下笔,看着徐巧琴。有事?他突然心里一动。
“她叫于淑钦。”徐巧琴的手指头从报纸转向旁边的女人。赵定力对于淑钦点点头,说:“噢。”徐巧琴说:“哎,你说她怎么样?”赵定力不知道她要怎么样,他眼皮下垂,眼光落在于淑钦的脚上。徐巧琴提高了声音说:“我老乡啊,虽然没读过书,但喜欢的就是你这样有文化的人。”赵定力怔住了,看看徐巧琴又看于淑钦。于淑钦已红着脸低下头,也看着自己的脚。赵定力摆摆手,嘴刚张了张,徐巧琴就跨前一步,拉住他胳膊。“这样吧,我们单独聊一聊。”说着她转过身,推了推于淑钦,说:“你先回去吧,我跟他聊一会儿。”于淑钦迟疑了一会,才慢慢转过身,走几步又停下,看着徐巧琴,小声说:“你也走吧,别……”徐巧琴打断她,手连连甩着,说:“你走你走。”
赵定力看着于淑钦背影,目光一直落在她脚上。平足,赵定力心里嘀咕了一句。平足不是病,只是看起来有点怪。哪里怪呢?走路的样子。欧洲人走路都一阵风,脚板起落灵活,应该很少是平足的,这是赵定力看电影得出的结论。亚洲人却不一样,脚底中央多出一小坨肉后,身体的弹性马上丧失或消减了,走路笨拙生硬。他自己正相反,脚弓非常高,脚底像是被谁一勺子把肉挖走了。按体育老师的说法,这种人能跑能跳,所以赵定力进了小学就被招到校田径队,主项百米短跑,兼项跳高跳远。青江村早属于县,他拿到县冠军,后来村划归郊区了,他就拿到区冠军。他本来就高,又跑又跳后就更高了,但他没有一直跑和跳下去,上到中学,正要高考,学校停课了,他回到乌瓦大院,没有人再让他跑和跳。
徐巧琴让于淑钦先走,自己留下来,跟赵定力至少聊了两小时,从于淑钦出生,一见是女的差点被丢掉,到后来想上学上不了,然后从重庆嫁过来,又早早守寡。赵定力静静听着,他跟王瑞生很熟,跟王瑞生的老婆徐巧琴并不太熟,几十年说过的话不足现在的百分之一。一个他不太熟的女人,花这么多唾沫对他说另一个完全不熟的女人,用词用句都急不可耐,身子还一耸一耸的,手势很多,仿佛一个大亏正摆在面前。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好几个重庆女子嫁到这一带,先是一个,后来来了一长串,包括徐巧琴和赵定力第二个老婆罗玉玲。徐巧琴比罗玉玲小五六岁,两人不同村,但她跟于淑钦老家在同一个村。罗玉玲嫁给赵定力时,徐巧琴还小,于淑钦更小,总之互相不认识,但彼此都听说过对方。在老家不认识的女人,前后脚嫁过来后,就熟了,开始走动。当地人说的是古怪福州话,发音靠前,有很多现在普通话里没有的人声。她们虽然已经学会了,但有机会聚在一起时一定说重庆话,感觉上就跟回一趟老家似的。
于淑钦守寡后该织网该下海养殖也都去了,但时间还是一下子比先前空出很多,主要是心空了。那天她闷得慌,就到青江村徐巧琴家闲聊,聊到快中午了,王瑞生没回来,徐巧琴就开了冰箱取出鱼丸。没多久,徐巧琴就把鱼丸煮好端上了,她说:“嫁这里,单单能吃到赵定力打的鱼丸,我就觉得很值啊!”这样话题就很自然拐到赵定力身上了。赵定力懂古诗古文,毛笔字还写得非常好,村里婚丧喜庆过年过节都由他写红白联子。恰巧徐巧琴家门外的对联还在,虽然旧了,但字迹仍看得清楚。于淑钦好奇地站起来,走到门外看了看。徐巧琴跟出来,突然说:“喂,我看你们成个家吧。走,去见一见面!”按于淑钦后来的说法,当时她是摇头拒绝了,根本没想再嫁,只是拗不过徐巧琴,连拉带拽被带到乌瓦大院了。
赵定力已经很久没有跟女人这么近、这么久地面对面了,更没有听她们说这么多话。原来王瑞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声音和肢体之中。
他十三岁才上小学,年纪大无所谓,赵定力主要是个子高。开学那天他就迟到了,柳枝般从教室外飘进来,从坐在排脑袋浑圆的小胖子身边经过时,小胖子立即站起,前倾着身子仰头看。小胖子就是王瑞生。赵定力知道小胖子的惊诧来自没想到居然成为同学了,而且是同班。因为讨厌所有的课本和老师,王瑞生基本上在课堂上坐不稳几分钟,余下的时间他学猫狗鸡牛各种村里常见的动物叫声,很像,几乎乱真,座位就从排,一步步赶到后一排,这样全班的赵定力就和矮的王瑞生成为同桌。王瑞生敢惹全班任何一个人,男的女的都不怕,放过的人是赵定力。两人同桌了四年,第五年王瑞生不读了,学校不让他读,他自己也不想来。然后初中高中,赵定力读他的书,王瑞生撒王瑞生的野。有一天突然听说王瑞生在镇里拿刀把人捅残了,进了牢,一关十几年,出来后就去广东打工,中途托人介绍了重庆女人徐巧琴,婚后两人又一起去广东,前些年才回到村里。一个坐十几年牢,再打几年工的人,就好像一生平自无故被截掉两大断,断掉的那部分都是赵定力一无所知的,他好像也没太大兴趣知道,就淡淡地各过各的,平时并不怎么来往。哪想到突然有一天王瑞生老婆竟搬出这么一副冒着热气的心肠,追上门来要给他当媒人。徐巧琴说:“这可是千里挑一的好女人噢,又勤快又吃苦又不计较。你现在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娶了她,至少这么大的房子也有个伴嘛。”
赵定力心里动一下。乌瓦大院从建起的天起,就很少有女人说话,无论谢氏还是赵定力的母亲何燕贞,大多时候都闲置着唇。到了李翠月,李翠月在的那半年,整天拉长脸,不说不笑不言不语,他倒是挖空心思想着她怎么去宠她疼她让她高兴起来,却无从下手,他的话也都被李翠月的脸色噎死在喉咙下面了。后来的罗玉玲是不敢说,每天小心翼翼躲着赵定力。这两小时肯定是赵定力在乌瓦大院听到女人说话多的一次,似乎很好,整个房子都刹时一新似的。徐巧琴又说:“都这把年纪了,还犹豫什么?定了定了!”赵定力看着徐巧琴,嘴角动了动。徐巧琴巴掌一拍,立即站起说:“太好了!”说过转身,很兴奋地跑出门。
第三个月婚礼就在乌瓦大院里举办了,五十一岁的于淑钦嫁给七十岁的赵定力。天井里摆下三张酒桌,请了村里一些长辈和村书记、村长之类的头面人物。临时检来的砖块在天井上搭起灶台,架上大锅,买些松木块烧出又猛又烈的大火,火焰从锅四周呼呼往上蹿,松香味在整个大院里弥散开,看上去也很红火。赵定力提前一天打好两百零八粒鱼丸一一他过手的鱼丸每斤十六粒,非常精准,半两不多也不会少,算下来就有十三斤。这么多年真没想到竟也有为自己打这么多鱼丸的时候啊。负责操持的人是王瑞生和徐巧琴,他们主动扮演起家长的角色,仿佛成了赵定力的爹妈,安排这个,指挥那个。赵定力心里不适应,有几分别扭。疏远了这么多年,王瑞生竟又突然亲近回来了;一向疏远的王瑞生老婆,居然会这么贴心贴肺地替他打点一切。当时就觉得很像一场梦,也没觉得于淑钦有多重要。但八年过下来,过到现在,现在他可能病了,病得很重,会越来越重,将独自躺在床上苟延残喘奄奄一息,他不能让于淑钦就这样离开,去那么遥远的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