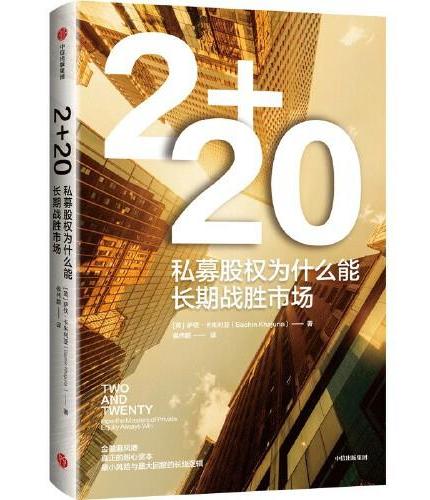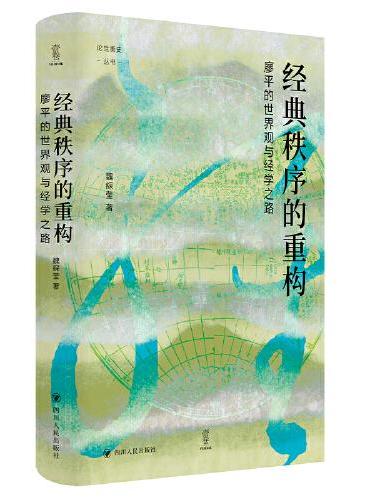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HK$
41.8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HK$
74.8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HK$
54.8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HK$
63.8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HK$
86.9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HK$
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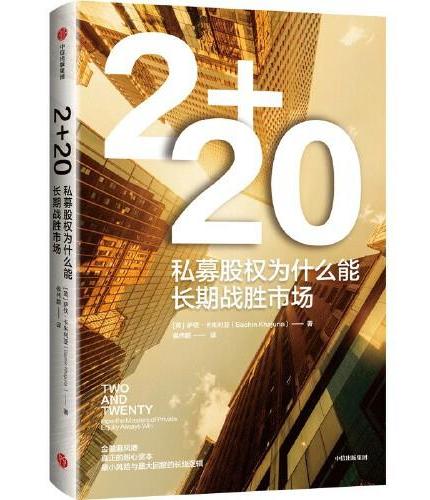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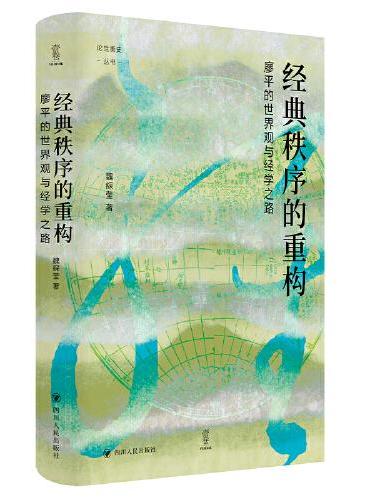
《
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探究廖平经学思想,以新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转型)
》
售價:HK$
97.9
|
| 編輯推薦: |
★《收山》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京版的《繁花》。相比沪语的呢喃温韵,京字京韵来得更猛烈而深入骨髓。
★古典叙事的写法,塑造的人物特点与矛盾冲突,细水流长地展现了一个时代悲与欢。
★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补白了大众对七十年代以来老北京勤行(餐饮)的面貌。从灶前锅角的世态人情,到饭庄的变化11:19:13与改革,生动复原了北京风味老字号的发展兴衰。
★一部绘声绘色的美食图鉴,从刀工到摆盘,煎、炸、烹、煮,令人垂涎欲滴,读罢能咂摸其滋味。
★一部记忆小说,七十年代无惧无畏的青年,着迷人间烟火中的热辣滚烫;九十年代后的声色犬马,写尽了百态人生。
★影视剧筹拍中
|
| 內容簡介: |
《收山》起笔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将老北京饭庄的景象寄于北京万唐居三代厨师的人生沉浮,书写了一段氤氲着饭菜香的时代悲欢。
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几辈传统技艺人的辉煌与凋零,承袭与断裂,固守与退让次第上演;正如万唐居宫廷烤鸭的传承,在大时代的裹挟中辗转历练,且进且退,终尘埃落定。
|
| 關於作者: |
常小琥:
北京作家。曾获第十一届《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第四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五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奖、《北京文学》2019年度优秀作品奖。
出版小说作品《琴腔》《收山》等。
|
| 內容試閱:
|
我挺怕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厨师的故事。没有为什么,对我来说,一开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写这部小说的中途,其实挺怕被人打扰,整天就跟刚打完狂犬疫苗似的,精神上特别脆弱。尤其是那种看谁都不顺眼的状态,一逗就毛,是挺招人烦的。所以身边的几位,知道连喘气儿都离我远着点。遇到过不懂事的,拉我去参加同学聚会,我觉得那种场面挺傻的,平日恨不得就住一个小区,十年未见,非要借这个由头,互相套套近乎,摸摸底细。
因为感觉他们的话都不是用嘴说的,所以全程我一言未发,这点儿事我还是懂的。
后来班长举杯祝酒,却不知道该讲什么。我开口说,菜不错,人呢,凑合活着吧。
也许很多人都和我那些同学一样,觉着活在这个世上,总有数不清的事情做,有数不清的东西抓在手里,这辈子他才赚了。其实未必,真正刻在你心里,在你记忆婆娑的那一刻,映在眼前的,不过还是那一两个瞬间而逝的画面而已。它们曾经于某段时光,停留在你的生命里,就此扎根。我想,这样的画面,就是宿命,是任凭你穷尽一生,都不会改变的。因为有它,你才成为这样的你。
所以如果有人向我诉说他的宿命,他生命中挥之不去的那一点光亮与黯淡,我能做的唯有倾听,因为那是上天对于写作者的某种恩赐。人得惜福,是吧。
我至今还记得,厨行里一位承袭开宗立派之真传的老先生,在自己家中,对我讲起早年间他的师父,遭人菲薄,无有善终时,他那老泪纵横、喉咙发颤的样子。无论他这一世在行内的地位有多高,贡献有多大,徒弟有多爱他,一讲起师父,他还是会变成一个老小孩的样子,笑不断,泪也不断。在我看来,他与师父的宿命,合在了一起,并且延续到了今日。这是福,人得惜福,是吧。
说点松快的,为了写这本小说,我跟不少厨师下过馆子,多数都是我掏钱(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他们这本小说的事)。他们会告诉我每道菜的规矩,然后说,现在全乱套了,京城好的鲁菜馆,里面的川菜特别绝,这话搁从前,比扇脸还疼。
我喜欢看他们喝到微醺的时候,关起门来说谁家的买卖缺了大德, 谁家的头灶和经理有过节,谁家的东西越做越不行。其中大部分,都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听着听着,就有重复,但是以前美啊,现在不美了, 现在没劲。
以前的每个人,基本上都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自己能做主的, 都是些针鼻儿大小的事。给孩子走个后门,从单位顺点儿东西,处了个对象说家住景山,见面后才知道介绍人大意,少说了个“石”字。都是这样的,现在想想,可气可叹,但那日子过起来,真的有种美感。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走路走累了,还能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走。
可现在不成了,走这条路的人,太多了,慢一点,别人就会撵你。
很多人说,这是好事,比如我想吃饭,家门口整条街里,山南海北的地方菜,我都能吃到,这叫什么?这叫繁荣。但是行内的老师傅对我说,恰恰相反,这叫败象,为什么?自己体会。
所以在《收山》里,屠国柱同样也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当他在灶上,一站就是几十年,想赴命,想还债,想替自己的两位师父找出答案时,他发现师父们未必不清楚答案是什么,但是此时已经没有谁在乎这个问题了。
因为人都不在了。
高个男的,就是我,从大兴插队回来的我。
那时,我爸在雪池胡同抬冰,我妈是宣武副食品公司供销科的调度员。像我这种双职工子女,每天饭点一到,见邻居家孩子,捧上热饭热菜,满院儿蹦跶着吃,那是什么滋味,我都不愿意提。我妈想我踏实养伤,特意舀一碗高粱米,给隔壁曹阿姨送去,让她中午管管我。人家嘴上自然说好,添一双筷子的事,白天也真来敲我的门:“屠国柱,家里贴饼子烙多了,过来帮我们吃一点儿吧。”我会隔着窗户说:“和同学约好的,出去吃。”
为填肚子,我试过用凉水化淀粉,再拿开水冲红糖,兑好,仰脖一灌,又香又甜。后来觉得胃里还是空,就抓把盐,去街上逮蚂蚱,抓知了猴,烤着吃。好些孩子宁可不正经吃饭,也要挤在绿莹莹的桃树和杨树叶下,围着我。总之,只要不挨饿,我招儿多了,逼着自己想。
那年是早立秋,稍一见凉,即便盐都顺着裤线洒没了,也难见到几只活物,馋虫倒是勾出不少。后来忘了听谁说的,十七号大院里一小光头,精豆子似的,在家能炒土豆丝,会熬茄子,我就总跑过去看。他以为我是想蹭饭,每回就单盛出来一份。我摇头,给他搁回到砖台上说:“你吃你的。”他又递了过来:“哥,你吃,脆还是不脆,熟没熟透,我放了一点白胡椒粉,提味,替我把把关。”我捏起一片浅棕色的茄条说:“那我就帮你把把关。”
我们会挨家挨户地串,看街坊怎么抻莜面,怎么蒸花卷儿,怎么把猫耳朵推撮出花纹。我从哪儿新学了几手,不方便动,就尽着他先在家里试。从白天到傍晚,他跟在我身后,像一块甩不掉的粘面团。
他的脑袋又宽又扁,手总在上面抠,我问过他:“你的光头怎么回事?”
他说以前头发很多,还留过小辫,后来里面老是长虱子,就越剪越短,直到剃光,天天洗,还是会长。我盯着他的脑瓢又问:“现在怎么没了?”他说, 后来他爸干脆拎起暖壶,朝他头上浇开水,说这样能把虱子、虮子全都烫死。我仰头直笑:“你爸真下得去手,虱子不是他亲生的,难道你也不是? 真这样,该烫出你满头脓疮才对,我怎么瞅不见?”小光头眨着眼睛说:“是真的,真的。”空了一空,他又说,整天晃荡下去,也吃不出意思来。不如去专做风味菜的老馆子,尝尝手艺,我爸说,白广路的万唐居,有真东西。
我照着他的光头上一拍:“等你脑袋上的毛长齐了,再说。”
————
终于有一天,办事处的人打来电话,叫我过去参加分配。我就把绷带剪掉一小截,套了件长袖褂子,再去。那是一幢用朱红色火砖砌的苏式矮楼,外面挂着磨花了的旧黑板。多如喷漆总厂和电表三厂,哪家单位招工, 就拿黄粉笔写在上面。办公室里,那个人拎着竹劈包的暖瓶,刚打完水回屋。他见我把四盒五毛八的红梅,从报纸里一亮,就故意板起脸,怪我瞎花钱。等我把烟卷好,又坐了回去。他说:“有个情况,你得先弄明白。像首钢、二机床厂那种地方,都是给退伍兵预备的,厂方直接跟武装部招人。人民食品厂这样的全民单位,少,也轮不到你们这帮知青。我这里,都是集体的。你去,就聊去的办法。不去,再说不去的。”我眼皮一闭,一睁, 点了点头,说:“这些都懂。”
他说:“懂就好办,这片儿的集体单位,那是卢沟桥上的狮子,数都数不清。”他揪出软木塞,将水倒进生满茶垢的搪瓷缸里,来回吹。然后还说:“我这人实在,冲你妈跟我是发小这层关系,像东街塑料厂, 做大脸盆的,都不跟你提。”
他从三角柜里抽出一张表,说:“单给你留的,灰大楼拔丝厂,出盘条, 这东西,紧俏。菜市口的羽绒服制品厂也行,去就当天开手续。”我问:“去那儿做什么?”他说:“流水线呗,工帽往头上一套,扎袖子,缝领口,出蓝棉大衣。”我说:“老坐着,干不了。”他一愣:“老坐着不行?那东风市场的售货员,总行吧?”我说:“老站着,也不行。”他把缸子一撂,横话就出来了:“躺着行,你够资格吗?有这好地方,我还要去。也不过过脑子,年前你在四平园把一崇文的孩子,吊起来打。开春,又给里仁街张家二儿子眼眶拍折了,人刚在同仁医院把假眼装上。这你妈才来求我,快把你搓出去。明告诉你,我还不管了,家待着去,仨月不分你。”
我又坐近,从两边裤兜里各掏出一盒“前门”,按在他跟前。再问:“您手里的单子,给我看看。”他半张着嘴,一面朝我的手上瞄,一面把表递过来:“再不济,你不是会游泳么,北海当救生员怎么样?给你条船,有想不开,跳河的,你上。冬天活轻,船都靠岸,光刷刷漆。”
我对着尽下面两个单位的名字,看了再看。
他顺着我的眼神说:“糕点二厂,远是远了点,在城外的湾子,可福利好。”
我问:“这个万唐居,就是那个万唐居吗?”他说:“废话,全北京,能有几个万唐居。”我把手从烟盒上松了回来说:“就这儿吧。”他冷笑着,拿起蓝圆珠笔,在那三个字旁边,打了一个细小的对勾。
后来我妈怎么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包,好端端的工人队伍不进,偏往五子行里钻。伺候人吃,伺候人喝,白糟践我为你打点前程的一片苦心。
————
万唐居里面的院子很深,西边辟出的几间耳房,建了水饺部,小吃门市和面点也是新设的。穿过去以后,要走一条由屏门和花墙围挡住的紧凑扁长的通廊,才是主楼。我贴着墙身,勉强望见制高点的观景阁,可向东,还是看不到头。我混在刷房师傅们中间,要进楼面试。踏上钉着钉子的木头楼梯时,会听到那里有叮叮咚咚的敲凿声。我松开领口,想晾一晾身上生出的燥汗。
这里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姓齐,总说自己是刚从外交部调过来的。他手里捧着青瓷茶杯,一件卡其布的灰色中山装,立陡陡地穿在身上。他用后脑勺对着我,弯身看完字台上的笔试和体检结果后,转过来问:“你一米九?”我不好不笑,又不好多笑,只是把手上的疤缩在袖管里,想藏一藏。他举起一个荔色的铁皮暖壶,说:“店里是想按征兵的标准,紧着体力好、底子干净的招,以前我在礼宾司招人,门槛更高。你的档案我看过了,用不用你,我个人而言,是有保留的。但你以后的路还长,考虑再三,店里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我鞠躬谢他。齐书记单手一拦,说:“别谢错了人,不是有人点名要你,我也不好出面。先把职工登记表填了,我再领你见他。”
按现在的论法,杨越钧应该算万唐居的第三代总厨,当时叫掌灶,也就是大厨师长和热菜组组长。他很好认,那张肉蓬蓬的圆脸,一笑,总会眯缝起柔和的双眼来看你。宽厚的身板配了件簇新的白色号衣,下面是炭黑的制服呢工裤。头上一顶带松紧的豆包帽,也戴得正正方方。齐书记在我们旁边,也没有多讲,只给了我三个字——“叫师父”。
我至今都还记得,杨越钧教给我的句话。他说,做厨子,要紧的是有一颗孝心。当时我根本没听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天,老人还特意问了我家住哪儿。我答:“就在这片儿。”他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从兜里摸出一个蓝皮小本, 慢条斯理地抹平折角,铺在桌上。他迟缓的动作,像一颗黏滞中还未滴下的蜡油。
“我是问你家的住址,包括你父母的名字、年龄和单位,都帮我写上。”
其实,这些材料政审时早就填过的,可是见他那么郑重,我只好再拿起笔。
后来听说,老人真的会提着水果,找到徒弟家里,告诉对方父母,你儿子在我手下学徒,店里会照顾好他,请二位放心。
————
既然叫掌灶,火上的事可以全听你的,但你头上,还有东家。以前万唐居的东家和掌灶都是山东福山帮的,从不传给外人。后来把手艺和账本都留给这位保定人,论老礼儿,是破家法了。但杨越钧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八大居之首的位子,他托得住。
老年间的掌灶,活儿既要做全,还得看着徒弟。有不服管教,调处不当的,生出事,东家先把掌灶师傅请过来,甭管是不是你的错,你回家,全因你挣的那份钱。当时,万唐居的厨子平均工资二十块,我师父一人就拿一百五。不论谁家婚丧嫁娶,认不认识的,他一律随十块钱份子。人肯定不会去,但是钱一定要给到。想那年月,谁肯掏出八毛来,算俩人交情不错了。
不过有位爷,工资却比杨越钧还高出五块钱,他就是烤鸭部的葛清。凭着独创的技艺和配方,这人树起了宫廷烤鸭的招牌,连着救活好几家店。杨越钧是花了大钱,从大栅栏把他挖过来的。葛清是个活儿极细的人,他在后院的鸭房,别人不能踏进半步。他说过,老杨,这摊事儿交我,钱你绝不白给,但我挣的只就这份工资,旁的事,你也别找我。以前店里有个公方经理,存心让他黑白着干,连烤带片,填鸭扫圈,一肩挑不算,还要他切墩上灶,亲自走菜。气得老头抄起手勺,站后院柿子树下,当所有人面,骂对方是杂种操的。
杨越钧担心葛清因为这事被人上纲上线,便问齐书记,能否将那个经理请走。接着他叫来我,说分你头一项差事,就是把你匀到鸭房。我自然不乐意了,因为师父的烧鱼是一绝,谁不想跟着掌灶,长些本事。刚进店就被支开,那不成了晓市里扔满地的烂菜叶,有人丢,没人捡。可杨越钧不管,派我去的时候,他连一盘菜也没教过我,只扔给我八个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现在是有人说:“你屠国柱命真好,一口气就拜在两位高人门下。”可当时不是这样,去劳资科领工服时,那里的人看我,就像在看一只翻了盖的乌龟。传达室的老谢来换新锁,想跟我逗会儿闷子。他说:“你也要去鸭房了?”我听了,便把衣裤一撂,梗着脖子问他:“怎么着?”他笑着摇摇头, 说:“不怎么着。对了,见过你俩师哥了吗?”我眉头一张:“什么师哥?” 科里的人像捡着钱一样,笑翻过去。我转过身,来回瞧了他们两遍,拿起东西就走。老谢在后面伸着头喊:“可别惹你葛师傅不高兴。”
————
那是一身藏蓝色的开襟布衫,抬肩宽松,里料干糙,穿起来像是披了件床单,走路兜风。
我系好裤腰后,弓身,贴着内厅的落地镜,对着自己的钟罩脸,照了又照。那两道剑眼上,眉骨外凸的凶相,加上峭立的驼峰鼻,怎么瞅, 都不像是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我抠掉手臂上的那几粒血痂,把衣扣挨个别好,用手掌抹平褶子,冲镜子轻轻叫了一声:“屠师傅。”
一个清凉的、阴郁多风的下午,我站在烤鸭房门前,点上一根烟,想抽完再进去。这是个马蹄形的院子,两侧各栽着一棵老柿树,褐色树皮, 沟纹严密,一片接着一片的,有许多殷红色的柿叶飘下来,在明暗交接的斜晖下,如同烧着的纸钱。
抽完烟后,我又在风里多站了会儿,散散烟味,然后呼一口气,把腿迈进了屋。
一股臭烘烘的苜蓿味,差点儿将我熏一跟头。我捂住鼻子,看见一团镂花般交互覆叠、朵朵丰满的白烟。用手扇了扇后,总算辨出眼前有一轮黑线。我对那道黑线说:“葛师傅,我是屠国柱,杨师父派过来的。”他继续抽着手里的卷烟,没有答话。我又重复了一句后,他把烟灰直接弹在地上,张起眼瞪我。我很自觉地向后退,直到被他瞪出屋外。
我原想在院里找个下脚的地方,坐下来,等他喊我。结果是我像尿裤子一样,一直被晾在院墙下面。看着前院的人,和我初来时一样,伸着脖子往我这里瞧。
我希望他们同样瞧不到这里,更不会认清我的样子。
————
这一晾,就是半个月。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每当天刚蒙蒙亮,我便来拍店门,把老谢从被窝里喊出来,让他放我进去。我说要签考勤,老谢鼓起眼睛说:“记考勤的都还没来,签屁。”我径直走到后院,看见那个精瘦的老头正拿着镊子,拔鸭头上的细毛,就好声好语地向他打招呼。然后和其他新徒工一样,我开始扒炉灰、添火、砸煤、拾掇灶台。我会往老头的茶壶里倒一丁点儿热水,闷上半杯高沫儿,等他一找水,再续满,那时喝起来,不凉不烫,正合适。
结果无论我怎样表现,也换不回他的一句话。
于是我的下手活一干完,就像要饭的一样,自觉地找个背阴处,歇脚。我发现街面上,总有人透过铁栅门,往院里看。我就假装找东西,在院子里转圈儿。当时万唐居的人,一提店里新来了个驴师傅,就是说我呢。那些天,我总想,假如葛清真能打我,骂我,该有多好。
葛清照看鸭圈时,人手一件的蓝蚂蚁工装,被他随便地搭在肩上。 耳边,还总别着一根皱巴巴的卷烟,有时摘下来,嘬一口,叼在嘴上,也不耽误给鸭子填食。
风日渐凉了,院子里那些老树上的枝枝丫丫,被吹得慌促。他却面如平湖,握着破茶壶,放腿上,往把角那么一窝,瞧着那群呆头呆脑的东西。
其实远远看上去,他自己就像一只垂老的兀鹫。
————
那时的万唐居,是靠自造的土冰箱,来给菜肉保鲜。每天,会有专人从德胜门的冰窖采天然冰进来。我爸在那里干了半辈子,这套活儿,我熟, 不用人教的。如何上冰,同样是门手艺。一整块冰足足一见方大,半米厚, 合四百斤,要靠几个人,合力用冰夹子抬下来,砍成八块,再拿刀铲平撒盐,码到水泥池里。店里给葛清配的不是水泥池,而是半人高的木桶, 要垫好冰后,放进小坛子,里面盛着新切的鸭肉。肉不能碰冰,那样会脏了原料。整个过程费神费力,谁都不愿意干。以前葛清身边没人,杨越钧会叫伙计帮他上冰。现在我来了,便没人再管。就这样,耗了半个多月后, 我等到了自己的个活。而且,这份差事只能我做。
我拿出一把两尺长的冰镩子,去凿领到手的冰块,寒气和碎渣跃进皮肉里,又痒又麻。我小心地往坛子和桶的缝隙里塞碎冰,这让我想起儿时在羊肉胡同,刚入伏,我们只等批冰的驴车一到,就用小手拼命擖哧凉飕飕的冰。细细粒粒的冰碴和成瓣的冰疙瘩洒在地上,要抢着捡进手心,直冻到指尖像涂了红药水般一片晶亮,往嘴里一含,特别过瘾。因为心神走得远,便没在意,要对这把钢制冰镩留一些力。我紧握住上头的木柄,斜着一拉,这根前有尖刺,尾有倒钩的四方棱,直奔肘关节滑去。
昏昏默默中,浅浅的血渍渗到冰面,流向砖地。
我用手胡乱擦了擦伤处,紧闭住眼,把头仰靠在院墙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