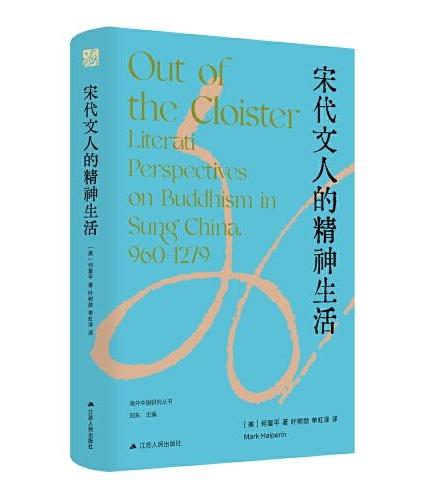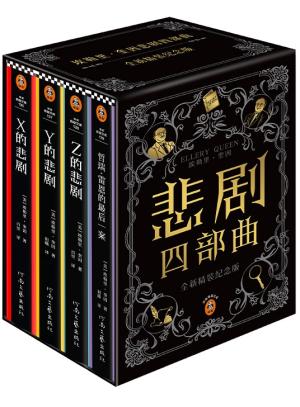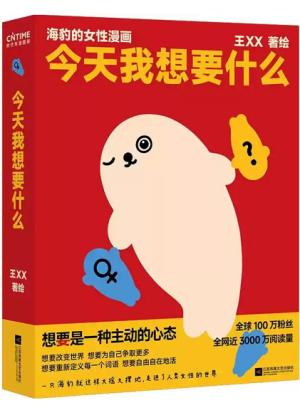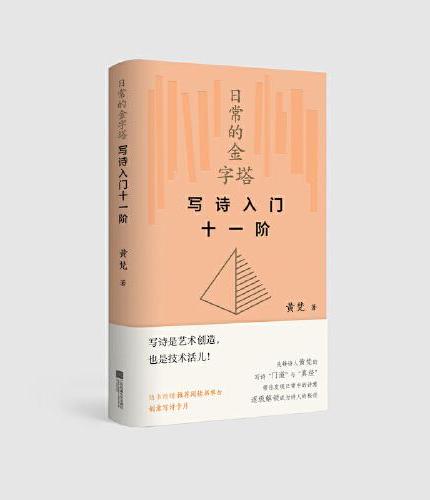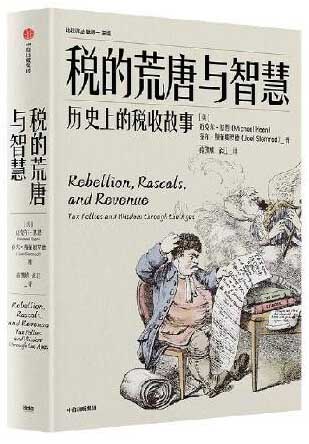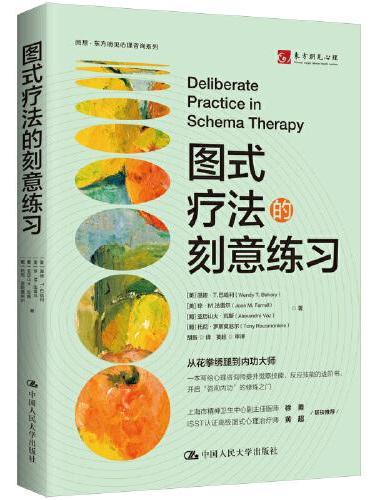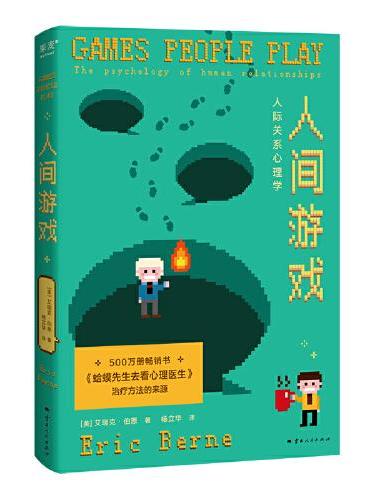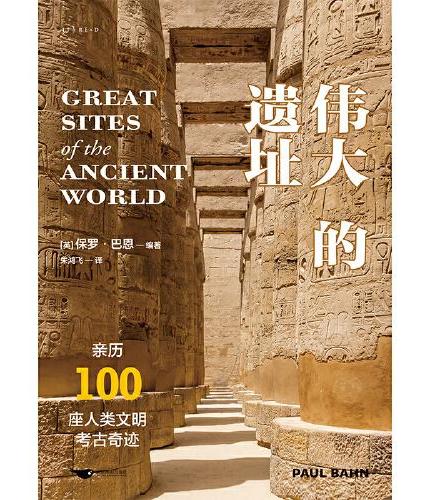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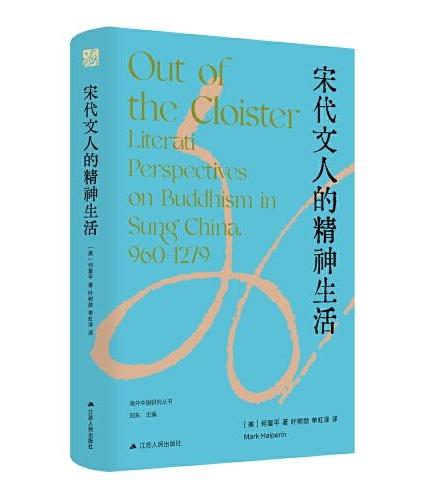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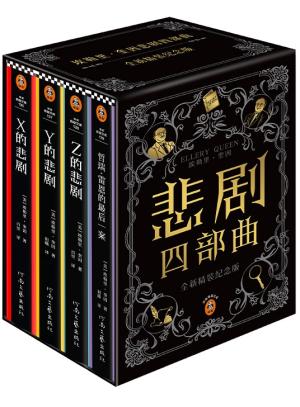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HK$
30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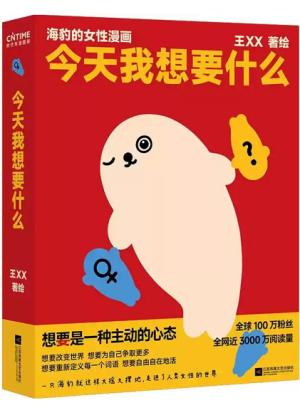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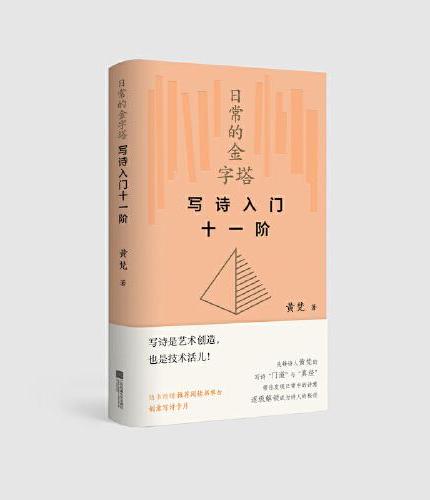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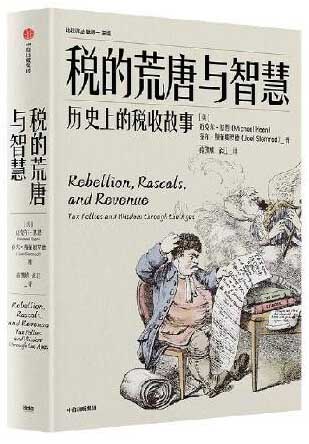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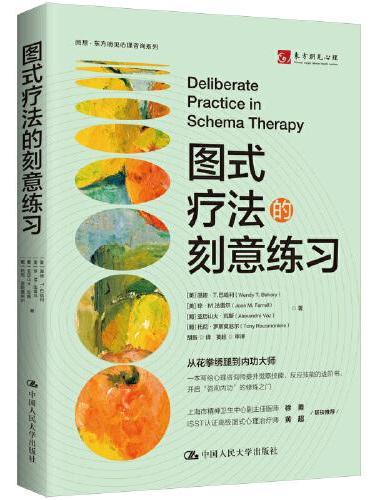
《
图式疗法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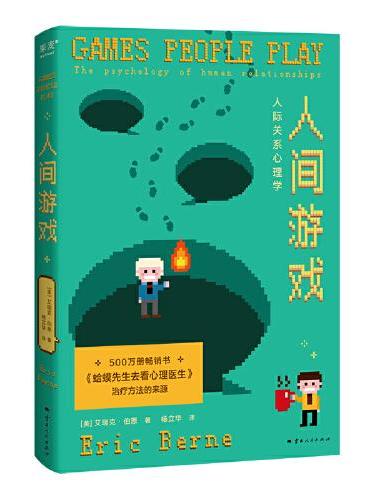
《
人间游戏:人际关系心理学(500万册畅销书《蛤蟆先生》理论原典,帮你读懂人际关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售價:HK$
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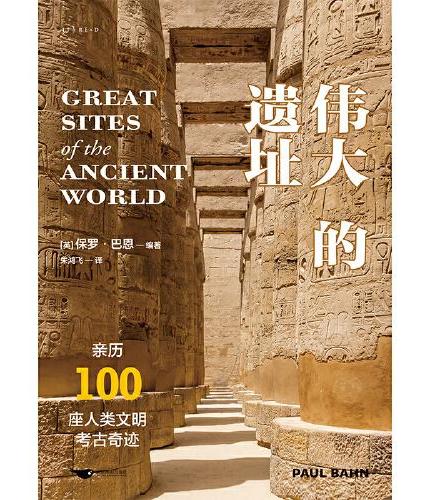
《
伟大的遗址(亲历100座人类文明考古奇迹)
》
售價:HK$
206.8
|
| 編輯推薦: |
※《经世大典》首次系统整理出版
※ 全面收录大典现存佚文,*限度恢复大典原貌
※ 辑录来源明晰,编排佚文合理,校勘文字精审,附录资料丰富
※ 研究元史和考校元代史籍*基本的史料
|
| 內容簡介: |
《经世大典》是元代文宗时期修纂的大型政书。大典八百八十卷,为君事四篇、臣事六篇,十篇之下又分一百二十八类以上,分类记载了元朝自漠北兴起至文宗朝的帝王谱系、诏训,以及职官、礼乐、经济、军事、法律、匠作等典章制度,尤其是总结了元朝立国以来典制的更替演变,是元代典制之集大成者,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明初修《元史》,多取材于大典。明后期大典失传,清中叶以后才逐渐为学者重视,出现了一些辑佚和研究成果,然至今仍未有一部较全面的辑本。《经世大典辑校》一书在前人辑佚、研究的基础上,更为全面地收录大典现存佚文,*限度地恢复大典原貌,为学界提供一部便于利用的重要史籍。
本书为《经世大典》的首次系统全面整理(辑佚、点校)。本书辑校的思路清晰明确:以史源学的原则收辑散见于各种古籍的《经世大典》佚文,尽可能恢复佚书原貌,充分体现辑本的还原性和可信度。本书辑佚以《元文类》所存佚文、《永乐大典》残本所存佚文、文廷式辑本、其他史籍文集所引佚文为先后顺序,依次辑入大典框架;佚文有重出者,择善而存,删去重复;又以清人多种辑本为校勘。并收入《进经世大典表》、《经世大典地理图》。辑校本在各类目之下,附有考校记,记述佚文出处,考证有关类目的设置和佚文的归属,以及文字取舍的原因,交代异文校勘的情况。文后附录有关记述、考证《经世大典》的诗词、题识、跋语,列《〈永乐大典〉残本所存〈经世大典〉佚文表》等。
|
| 關於作者: |
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已出版《古籍目录学》、《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藏书与文化》、《元代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出版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等专著。
魏训田,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已出版《中国近代文献典籍散佚史略》、《德州碑刻文献选注》等著作,发表《元代政书的史料来源》、《元代政书之体例探析》等论文。
谢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史、海外汉籍。整理出版《郭氏易解》等,编有《明清之际西学汉籍读本》,参与编纂《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等。
|
| 目錄:
|
整理前言
凡例
总序
第一 帝号
第二 帝训
第三 帝制
第四 帝系
第五 治典
第六 赋典
第七 礼典
第八 政典
第九 宪典
第十 工典
进经世大典表
附录一相关题咏跋语
附录二《永乐大典》残本所存《经世大典》佚文表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
| 內容試閱:
|
整理前言
《经世大典》是元代文宗时期修纂的大型政书。元天历二年(一三二九)九月戊辰,文宗弑兄夺位,第二次登基之后,下诏由翰林国史院同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经世大典》。至顺元年(一三三〇)二月,为集中编纂力量,乃命奎章阁学士院专率其属为之,以赵世延、虞集为总裁。秋七月,赵世延以疾退,由虞集专领其事。是年四月十六日开局,第二年五月一日即草具成书,缮写呈上。此后大概因虞集目疾加重,大典初稿的加工转由他人负责,经修订润色,装潢成帙后,由在奎章阁任职的欧阳玄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三月表进皇帝。
大典分类记载了元朝自漠北兴起至文宗朝的帝王谱系、诏训,以及职官、礼乐、经济、军事、法律、匠作等典章制度,尤其是总结了元朝立国以来典制的更替演变,是元代典制之集大成者。明后期大典失传,清中叶以后才逐渐为学者重视,出现了一些辑佚和研究成果,然至今仍未有一部较全面的辑本。《经世大典辑校》一书就是希望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更为全面地收录大典现存佚文,最大限度地恢复大典原貌,更好地保护这部已严重残缺的古代史学名著,也为学界提供一部便于利用的史料。现就辑考整理过程作一介绍,以就教于方家。
一 《经世大典》的编纂体例及特征
分析《经世大典》的编纂体例及其特征,是开展大典辑佚的前提和基础。《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另附《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全书暗分君事、臣事两大部分,君事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等四篇,因要使用大量蒙古材料和档案,专设蒙古局纂修;臣事分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六篇,由奎章阁学士院修纂,共十篇。
大典的编纂源于元朝君臣对于治国方略和国家典制总结的需要。早在蒙古政权建立初期,成吉思汗就在一二一九年出征花剌子模国之前专门召集会议,重新规定了自部落兴起以来颁布的各种约孙(习惯)、札撒(法令)和训言,用蒙古文整理成卷,名为《大札撒》。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又据当时所新增的一些仪制,修订并再次颁布了《大札撒》。《元史太宗本纪》曰: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大札撒》内容庞杂,涉及军事、行政、外交、宗教、民事、刑罚诸多方面,然零散杂碎,不成体系,因而不是一部真正意义的成文法典,而只是对于习惯法的确定和文字记录而已。蒙古政权在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以后,为了更好地治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首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吸收了中原地区汉文化的进步因素,在国家体制法规的建设上不断发展丰富,在《经世大典》之前,元廷已颁布或编定不少法规法令。忽必烈即位不久,就在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八月颁定新立条格,定官吏员数、均赋役、劝农桑、平物价等等。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他又命何荣祖简除繁苛,始定新律,编修《至元新格》,其内容包括公规、治民、御盗、理财、赋役等十篇,并予以刻板颁行。此后成宗曾于大德三年(一二九九)三月命何荣祖更定律令,次年何荣祖选编了《大德律令》,但据《元史何荣祖传》记载,此书并未正式颁行。仁宗时,曾允中书所奏,令臣下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命宰执儒臣取前书而加损益焉,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大元通制》在英宗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审定颁行,全书八十八卷,包括《制诏》、《条格》、《断例》三部分,是元朝第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法典,惜至今已严重残佚,仅存《条格》二十二卷,故通称《通制条格》。几乎与此同时,又有《元典章》刊行问世。此书编集刊行者不详,然从内容上看,并非新颁典制,乃法令公牍文书汇编,书分正集、新集两部分,正集所收文献自元世祖中统元年至英宗至治元年,新集则补收正集所缺,并续收至至治二年。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下分八十一门,四百六十七目,收文二千三百九十一条,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文献。
《经世大典》的编纂在《元典章》刊行后不久,因此在编纂体例上也颇有借鉴《元典章》之处。在《经世大典》修成之后,元顺帝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十一月又修成《至正条格》,并于次年四月颁《至正条格》于天下。其体例仿照《大元通制》,分《制诏》、《条格》、《断例》三部分,所收条文《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刊印颁行时仅有《条格》、《断例》两部分。此书是元代后期官修的重要法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历来被认为已经亡佚。二○○二年在韩国庆州发现残本,并于二○○七年由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整理出版。元顺帝至正七年(一三四七)还曾诏修《六条政类》。次年三月,《六条政类》书成,然此书不传。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此书性质与《经世大典》相仿,可看作是大典的续篇。所谓六条,当与《经世大典》的臣事六篇相同。元代新修政书恐还不止以上所述,惜多已亡佚,至今仍有一些线索者,如《成宪纲要》,作者与年代不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有著录,现存《永乐大典》残本卷一九四二五录有此书关于驿站的相关文字,曾有学者加以辑录。
梳理元代政书修纂的大致线索,以其他政书与《经世大典》作简要的比较,可以对大典编纂的性质和体例特征有以下认识。
第一,从编纂性质来看,大典是一部重在表现国家机构组织体系,叙述制度沿革更替的政典。元朝自成吉思汗起就很重视制度法令的整理颁行,后来又陆续修纂颁布了多种政书。然而从内容和形式上审视这些政书,它们的编纂性质又是有所不同的。《四库全书总目》将这类典制体史籍又区分为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等六个子目。其中通制目著录以一代之书而兼六职之全者,如《唐会要》、《元典章》之类;法令目收官著为令者也,刑为盛世所不能废,其中如《至正条格》等。由此可见,元代所纂政书也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政府机构和职掌为体系,叙相关制度条令和事例,以明国家行政制度之沿革,为后世政务提供规范和借鉴的政典,如《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一类是按刑事的涉及事类为体系,叙相关律令格式和事例,以明裁断刑法,是以服务现实为主要目的的法典,如《大元通制》、《至正条格》。正因为性质的不同,元代后期才要将《大元通制》和《经世大典》、《至正条格》和《六条政类》两两配套而行,以完善国家典制法令的规范。然而,从更长远的角度讲,《经世大典》思辑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则,它从通制编纂的需要,对国家体制作全面总结和确定,也必然包括刑法和民法的内容,因而范围更广,意义也更为深远。
第二,大典的十篇作为一级大部统辖具体类目,提纲挈领,条理清晰,在编纂结构上优于唐、宋会要。《经世大典》的编纂,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仿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别。从大结构上看,大典分君事、臣事两部分。君事中的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无疑是参酌了《唐会要》前六卷有关帝号、皇后、储君、诸王、公主等体例。臣事则主要是仿六典之制。六典之制始于《周礼》,《周礼》设官分职之法,即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系统;六大系统的官职分别是治官、教官、礼官、政官、刑官、事官,此六官到隋唐之后,则用以统称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职官和职掌;六官所遵循的典章制度则所谓建邦之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经世大典》臣事六篇所仿则《周礼》之六典,以其名略为改易而成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和工典,并以此六篇分叙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职掌和典章制度、条令法规。大典臣事六篇的分部克服了唐、宋会要没有大部门区分、直接以细目分类,显得杂乱无章的缺点。以现有的《唐会要》来看,一百卷的内容分立为五百七十一个细目,由于全书不设部门以为统筹,导致结构散乱,类目琐碎,后世学者只能依靠其事类性质和内容起讫,大致将其归类为十七大项或十三大项。《经世大典》虽然也属于会要体典籍,然其绝大部分内容由于有臣事六典的分辖,则具备了提纲挈领、条理清晰的优点,这是会要体编纂在元代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大典结合元代的具体情况,创新二级类目,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大典在君事、臣事十篇下的类目,是它的二级分类。由于君事的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四篇序录外的佚文已经难寻,其二级类目今已不详。然从现存佚文中,仍可确认臣事六篇的一百二十八个二级类目,因臣事内容在大典中超过三分之二,则可从六典以见大典在编纂体例上的继承和创新。六典的治典之下,分官制、宰臣年表、入官、补吏、儒学教官、军官、钱谷官、投下、封赠、承荫、臣事等十一类。其中宰臣年表、钱谷官、臣事等三类为新建,其余官制、承荫、军官、投下、封赠五类则分别沿用《元典章吏部》或《兵部》中的二级或三级类目,入官、补吏、儒学教官则从《元典章吏部》的《官制选格》、《吏制》、 《官制教官》等类目加以改造而来,当然内容范围也不尽相同了。
赋典之下,分都邑、版籍、经理、农桑、赋税、海运、钞法、金银珠玉铜铁铅锡矾鹻竹木等课、盐法、茶法、酒醋、商税、市舶、宗亲岁赐、俸秩、公用钱、常平义仓、惠民药局、市籴粮草、蠲免、赈贷等二十一类。其中都邑、经理、宗亲岁赐、赈贷、海运、公用钱等六类为新建。如海运类,反映了元代漕运业中以海运为主、内河运输为辅的新格局;公用钱也为元朝官俸的特殊现象,记述政府在官员俸廪之外,另赐资供官吏贷人以取息,为贺上、燕集、交好之用,这也可以看作是元廷对官员的一种养廉之法。农桑、钞法、市舶三类直接沿用《元典章户部》中的二、三级类目,其余十二类则分别利用《元典章户部》中的二、三级类目加以改造而成。
礼典之下,分朝会、燕飨、行幸、符宝、舆服、乐、历、进讲、御书、学校、艺文、贡举、举遗逸、求言、进书、遣使、朝贡、瑞异、郊祀、宗庙、社稷、岳镇海渎、三皇、先农、宣圣庙、诸神祀典、功臣祠庙、谥、赐碑、旌表、释、道等三十二类。其中燕飨、求言、进书、遣使、朝贡、三皇、先农、赐碑、艺文等九类为新建,尤其是艺文一类,则专述元朝之文事机构,并特别表彰自我朝之所作者,如制国字以通语言文字于万方,以及至若奎章之建阁,断自宸衷,缉熙圣学,表章斯文等新气象。因元代礼仪也多承儒家传统,变动不大,故其他二十三类目,多承袭或改造唐、宋会要和《元典章》之类目而来。
政典之下,分征伐、招捕、军制、军器、教习、整点、功赏、责罚、宿卫、屯戍、工役、存恤、兵杂录、马政、屯田、驿传、弓手、急递铺、祗从、鹰房捕猎等二十类。其中征伐、招捕、教习、功赏、责罚、宿卫、屯戍、工役、兵杂录、弓手等十类为新建,军器、整点二类直接沿用《元典章兵部》的类目,存恤、屯田直接沿用《通制条格》的类目,马政类则从《唐会要》卷七二的马、诸监马印、诸蕃马印等类目组合改造而成,其余五类据《元典章兵部》类目改易。
宪典之下,分名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赦宥、狱空等二十二类。其中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食货、大恶、恤刑、狱空等九类为新建,诈伪、诉讼、杂犯三类直接沿用了《元典章刑部》的二级类目,捕亡沿用于《通制条格》,其他九个类则分别由《元典章刑部》和《通制条格》的类目改易而成。
工典之下,分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之工、石工、丝枲之工、皮工、毡罽、画塑、诸匠等二十二类。其中宫苑、仓库、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之工、石工、皮工、毡罽、画塑、诸匠等十六类为新建,城郭、桥梁直接沿袭了《唐会要》卷八六的类目,其余四类则分别由《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的类目所改造。从现存大典一百二十八个二级类目来看,创新类目即有五十三类,接近总数之半。类目承袭其他政书者仅二十类,其余则据实际情况对内容作必要的合并或离析,并适当改易类目名,而且这种承袭或稍作改易也以参照元代政书者居多,参酌唐、宋会要者居少,因而较好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第四,在会要体例中首创于每篇每类正文之前加以序录,起到介绍内容梗概、勾勒演变原委的作用,也反映了大典述典制以经世的思想。序录分为四个层次:全书有总序;十篇有大序;一百二十八类有小序;有的类目之下又分子目,子目也有序录。刘向在序录中揭示书籍的各种情况,以便皇帝观览。这些书前之序录后来结集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书目《别录》。《经世大典》吸收了刘向序录的优良传统,当时的主观意图自然也是为了便于皇览,但客观上却具有创新体例、提纲挈领之意义。除总序对于修纂背景和过程作扼要交代外,大典的各篇各类序录都具有提要的性质,或交代各篇各类的设立宗旨,或阐明内容梗概,或勾勒典制的演变原委和线索,为读者了解各部分内容、把握元代典制之因革大势,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序录还深刻反映了大典述典制以济世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序录的经世意识中,有几点是比较突出的。一是高度总结了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发展。自唐朝以后,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宋、辽、金、夏等分立政权。大典在《帝号》、《赋典》序录中肯定了元朝致四海之混一的历史功绩,叙述了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皆归于一,八纮万国,文轨攸同,总总林林,重译归化这种多民族组合、国家一统的宏大规模,因而盛赞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至于在臣事各典大小序录中对元朝立国几十年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成就的叙述,更是反映了大典对元朝历史发展的深刻认识。二是从典制总结中提倡和彰扬爱民厚生的经世思想。大典序录把养民厚生的方略作为元朝的基本国策反复强调。《赋典》大序就说:我祖宗创业守成,艰难勤俭,亦岂易言哉。大率以修德为立国之基,以养民为生财之本,布诸方策,昭示后裔,以垂宪万世者,宁有既乎?至于如何具体地实施养民厚生之道,大典序录中则有多方面的论述,如《赋典农桑》序录中提倡重农桑,使民有所养;《赋典经理》序录中认为养民厚生要善于理财;《工典》大序中则提出要重民力,节国用的主张。三是在典制总结中强调德治教化的社会作用。这一思想在《宪典》各篇序录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比如认为天地之道,至仁而已。国以仁固,家以仁和。把仁道作为治国治家之本,提倡以王道德治管理和教化百姓。《宪典》本是记载刑狱诉讼制度的,但是大典认为国家刑法只是德治之余的辅助手段,古者圣人以礼防民,制刑以辅其不及,他们所期望的是以王道德治达到无讼、无刑、狱空的局面。
第五,大典在具体的编纂中注意前后呼应,使之详略得当,又采用灵活的表现手法,为后世的元史研究保存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一是使用互见方法编排材料,使之该详者详,该略者略,各篇之间又可互相照应。大典编纂中当遇到不同类目的内容有联系或交叉时,力避重复,同时又注意标明内容可参见之处。如《治典军官》中曰:武臣之入官也,其始以功,其子孙以世继。兹著其大概,详在军旅之典矣。也就是说,《治典军官》与《政典》内容相关,此处略述,他处详记,可参照阅读。在同典同类之中也有互见之例,如《政典征伐占城》曰:二十一年之征,则以安南道阻,不果,语在《安南》事中。则指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四)元军攻打占城,假道安南受阻之事,详情记载在《政典征伐安南》中。二是大典一些类目中还善于用灵活的表现手法,对传统政书的体例适当变通。从现存佚文可以看出,大典有些内容不限于叙述典制,而较多地记载了政治事件和人物传记,用以佐证典制。如《政典》的《征伐》、《招捕》,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元朝国内统一战争中对南宋、云南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招降过程,另一方面则记述了对周边国家如高丽、日本、安南、占城和南海诸国的征伐与政治、经济交往。《治典》的《臣事》则收录了一批在元朝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文臣武将的传记。上述内容虽不属于典制范围,然亦可佐证相关的政治制度,同时为后来修撰《元史》和元史研究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史料。
二 《经世大典》辑佚和研究的学术史观照
元至顺三年(一三三二)三月,大典纂成,装潢成帙,表进皇帝,群臣振奋。惜大典表进后数月,元文宗去世,之后随即因皇位的变易又陷入混乱。又因大典卷帙浩繁,故无暇刊印颁行而束之高阁。明初,大典被运往南京,修《元史》、《永乐大典》时皆曾取资于大典。永乐帝迁都后,《经世大典》也被运回北京,初贮在左顺门北廊,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今传《文渊阁书目》卷一一盈字号第三、四橱记:《元朝经世大典》一部,七百八十一册,阙。《经世大典纂录》一部一册,阙。苏振申据《千顷堂书目》所载明弘治十年(一四九七)修《明会典》时参考《经世大典》事,又查万历三十三年(一六○五)张萱撰《内阁藏书目录》已不载大典,认为大典应在此段时期散佚,所言极是。
大典在明后期散佚后,并未引起重视。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批佚书,或因大典卷帙浩繁,也未组织人力进行辑佚。此后,随着学界对元史研究兴趣的提升,才出现一系列对大典的辑佚和研究成果。为了深入展开大典的辑佚和考校,在此有必要对以往大典的辑佚和研究作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