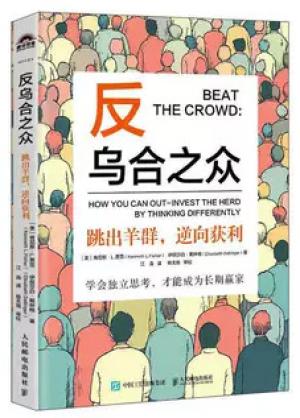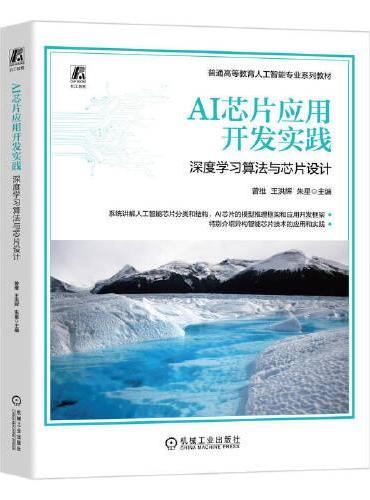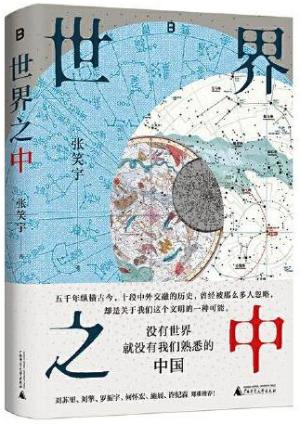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1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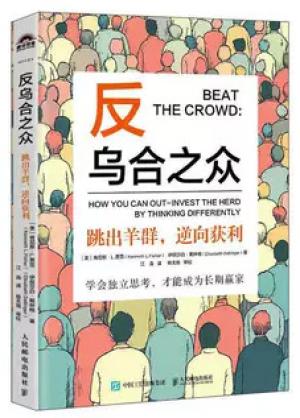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HK$
76.8

《
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
售價:HK$
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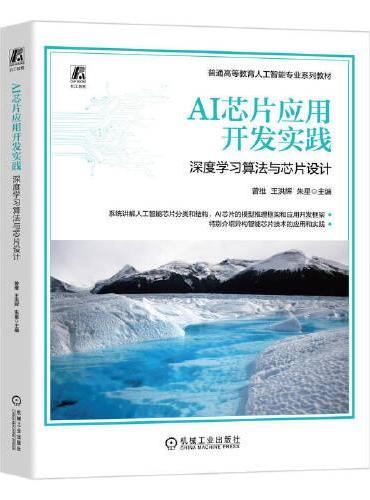
《
AI芯片应用开发实践:深度学习算法与芯片设计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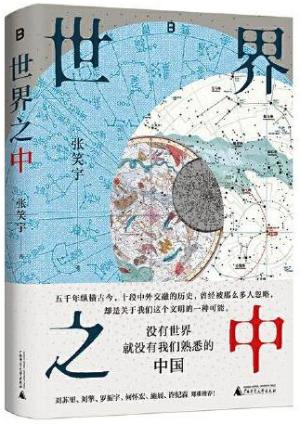
《
世界之中(文明三部曲之后,亚洲图书奖得主张笑宇充满想象力的重磅新作)
》
售價:HK$
86.9
|
| 內容簡介: |
|
《家庭与性别评论》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集刊之一,展示了海内外围绕家庭与性别领域相关专题的多样化视角和*成果。本辑精选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在流动家庭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三大议题: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内部差异、影响因素、数据争论;家庭化进程中的困难与流动家庭的应对调适方式;流动人口家庭化背景下的政策改进方向。
|
| 目錄:
|
第一编 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段成荣 吕利丹 邹湘江】
我国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 问题与对策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段成荣 吕利丹 王宗萍 郭 静】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周 皓】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盛亦男】
外出还是留守?农村夫妻外出安排的经验研究【李 代 张春泥】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杨菊华 陈传波】
城市规模、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汪建华】
第二编流动家庭的困难与应对调适方式
离散中的弥合农村流动家庭研究【金一虹】
打工家庭与城镇化一项内蒙古赤峰市的实地研究【王绍琛 周飞舟】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汪永涛】
义务教育阶段提高流动儿童学业成绩所面临的障碍【张 绘】
第三编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政策应对
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李 强 陈振华 张 莹】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张 翼】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二维路径选择
以户籍改革为视角【辜胜阻 李 睿 曹誉波】
|
| 內容試閱:
|
动人口家庭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重要议题(代序)
汪建华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在这支产业大军近40年的城乡往返迁移历程中,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逐渐在城市稳定下来。他们不再是城市的临时劳动力和过客。成为城市的主人,享有与本地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是他们最核心的诉求。农民工携妻带子,以家庭化而非个人化的方式迁入城市,是其城镇化、市民化最重要的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可以说,这是对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和流动人口发展诉求的明确回应。不过,从国家发展战略到具体可操作政策的出台和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以大量严谨的研究工作为支撑。有鉴于此,精准地把握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详细地考察其流动过程中的主要困境和调适策略,并在体制和政策层面探求改良之道、回应其核心发展诉求,是摆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相关领域研究者面前关键而又迫切的议题。围绕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流动家庭的困难与调适方式、家庭化背景下的政策改进方向等而展开的议题,学界已有一定积累,本文将择其代表性成果而述之,并在前人的启发下讨论如何在经验、理论和政策层面加以深化。
一 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
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讨论,相对该领域其他研究议题,论述最为丰富、方法最为成熟。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多以大样本调查数据为讨论依据,相关数据既有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0~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全国层面的数据,也有北京、武汉、厦门等城市范围的调查数据。已有研究广泛涉及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历史趋势、影响因素、区域与城市间的差异等主题,当然在调查方法上也有一些争论。
1.总体趋势
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测算,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2.4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从0.66%攀升至17.9%。流动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家庭化趋势。六普数据显示,独自一人流动者只占家庭户的26.76%,两代户、三代户则分别占38.52%、5.04%,流动人口正从夫妻共同流动阶段迈向核心家庭化阶段(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2013)。2010年、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也显示,单人户比重仅占14左右。2011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46人,两代以上家庭户比例为52.3%,47.1%的被访者实现了整个核心家庭的迁移(盛亦男,2013;杨菊华等,2013a,2013b)。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似乎更强。在2014年的监测调查数据中,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夫妻共同流动,61%实现了完整的核心家庭迁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
虽然不同研究数据来源不一,流动人口家庭定义和测算标准差别也很大,不过,从大多数数据看,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在逐年增强。从普查数据看,1990年流动人口生活在纯外户中的比重仅为7.44%,2000年则提高到46.06%,其中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户主分别占64.36%、61.49%(周皓,2004;段成荣等,2008)。同样的趋势也在武汉、北京等城市的调查数据中得以印证(陈贤寿等,1996;翟振武等,2007;洪小良,2007)。
在普查数据中,流动儿童数量的增长速度却相对有限。2010年我国0~14岁流动儿童有2291万人,比2000年增加881万人,不过,流动儿童数量在流动人口总体中却占比不高,仅为10.35%,反而比10年前降低了3.43个百分点(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等,201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留守儿童规模的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5290万人,而2000年仅有1981万人(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2013)。考虑到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增长,流动儿童增长幅度远不及留守儿童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流动人口长期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之外也是流动儿童增速缓慢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2000年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开始在流入地稳定下来,2010年后流动儿童迅速增长,留守儿童占比则相应下降。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2010年0~17岁流动儿童达4659万人(普查数据测算结果为3581万人),2014年增长到5981万人;不过,流动人口子女留守老家的比例由四成下降为三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鉴于普查数据与监测调查数据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对流动儿童随迁的规模尚难下定论。但连续四年监测调查数据的纵向比较还是可以说明,近年来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地将子女带到务工地共同生活,尽管在绝对规模的测量上可能存疑。
45~64岁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的监测调查数据中仅占8.7%,在2014年则增长到12.7%,这预示着三代家庭户的增多。不过65岁以上的流动老人所占比例非常小,且在四年间有所下降(从0.3%降至0.2%)(杨东平,2017)。这显示在流动家庭中,老人更多地通过工作和家务为子代提供支持,到了需要赡养的年龄,则大多要回到老家,减轻子代的生计压力。
2.区域与城市差异
对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分析不可忽略区域与城市类型差异。对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相对而言,中部地区、跨县流动者,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最复杂、完整核心家庭流动比例最高、家庭流动批次最少、批次间隔最短;东部地区、跨省流动者则相反。在东部相对较发达的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跨省流动人口占70%以上(杨菊华等,2013a,2013b)。沿海发达省份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本就紧张,跨省流动者要想获得流入地公共服务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地区流动人口的家庭化无疑面临巨大的制度障碍。
大中小城市间的差异也值得重视。2014年南京大学农民工抽样调查覆盖东中西部地区7省12个城市,共有2017个样本。统计结果显示,相比大、中城市,小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化趋势最强,这体现在农民工与家人同住与配偶同住与子女同住与父母同住家庭代数核心家庭共同居住等各个指标上。家庭化趋势未在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间呈现显著的差异。但大城市农民工与子女同住与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对较低,一代户较多,三代户较少。不同类型城市间的差异可能与农民工流动的行政跨度有一定关联。越是大城市,越可能吸引人口跨省、跨市流动,农民工家庭化的制度障碍也越大。县区内、跨县区、跨地市、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家庭化趋势依次降低(汪建华,2017)。不过由于该调查涉及城市和样本量有限,难以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进行细分。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家庭化趋势差异是否真如数据显示的那么小,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3.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多沿袭欧美国家的理论视角,强调流动人口在家庭迁移决策中的理性选择。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视角的研究往往强调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职业、迁入年限等因素的影响;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则强调家庭规模、劳动人口总数、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有老人、是否有小孩、住房面积、住房类型等家庭层面因素的效应(周皓,2004;洪小良,2007;侯佳伟,2009;陈卫等,2012)。
毫无疑问,流动人口会根据个体和家庭的收益最大化做出家庭迁移决策。但类似的研究,并不能说明中国流动人口的迁移在制度和文化情境上,与欧美国家有何区别。从制度上看,户籍和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可及性对流动家庭化的影响最为关键。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内陆城市,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异地城镇化、跨省流动者相比就近城镇化、市县范围内流动者,更难在流入地获得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资源,社保接续转移、异地高考等也面临更多障碍(李强等,2015;杨菊华,2015;汪建华,2017)。从文化上看,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孝道伦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农村夫妻的外出-留守安排。他们既要考虑自己在赚取生计、赡养父母、照料子女方面的责任和角色,也要评估父母在农业生产和照看子女方面的可能性。比如,当子女处于婴儿期时,妻子更可能选择留守照看,此后夫妻双方更有可能外出打工;丈夫更可能因为有年幼子女而外出,妻子则更可能因此而留守,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倘若丈夫是长子或独子,夫妻外出的可能性就更小(李代等,2016)。
4.调查方法的争论
过往研究多使用流入地调查数据,这类数据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抽样对象过于偏重流入地的家庭户,难以捕捉居住在集体宿舍、工地工棚等非家庭户的流动人口。二是仅仅考察被访者在流入地的家庭共居状况,那些留守在老家、流动到其他地区的家庭成员,往往不在考察范围,所有家庭成员基于传统伦理和家庭分工而做出的复杂细致的外出-留守安排亦难以被洞察。三是流入地的调查也难以被追踪。基于对流入地调查方法的反思,李代等(2016)的研究同时纳入2010CFPS数据中的流入地和流出地劳动力样本,综合考察农村核心家庭中夫妻的外出-留守安排。研究结果发现,在农村夫妻中,单人或双人外出的夫妻约占14。在外出群体中,只有28.2%的被访者为夫妻同地外出。与以往基于流入地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同,该研究认为夫妻分离、家户分离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
不过这种调查方法也可能存在问题。流出地的被访者是否会报告其扩展家庭、直系家庭中那些已经举家外出的核心子家庭的情况,是否将其视为家庭成员,都成疑问。考虑到2010CFPS问卷正文长达168页,被访者很有可能会选择漏报这些家人的情况,而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被访者甚至可能因为怕麻烦而漏报核心家庭成员的情况。至于那些整个扩展家庭、直系家庭都迁出的流动人口,就更不可能存在于流入地的调查样本中。另外,过往基于流入地调查数据的研究也纳入不少单人流动的样本。流入地调查到底遗漏了多少单人流动的样本?通过纳入流出地调查样本进行纠偏是否导致矫枉过正?由此看来,流入地和流出地调查样本的偏误都有待进一步评估。
二 流动家庭的困难与调适方式
流动人口的家庭化、城镇化,并不仅仅体现为数字上的逐年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子女教育、住房、医疗、赡养父母等问题都有待解决。为此,传统大家庭不得不重新调整成员间的责任与分工,改变家庭资源分配的重心,为流动家庭的团聚和城镇化尽可能地提供支持。长期离散导致的家庭矛盾和情感问题更需要尽力化解、弥合。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不得不穷尽各种策略,努力将家庭离散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负面影响保持在可控范围。
1.流动与离散家庭的困难调适
过去30多年,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发展,流动人口不断涌入。而那些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经常面临两难:在老家附近的中小城镇就近工作,固然比较容易实现核心家庭的团聚,并与大家庭保持密切联系,但就业机会、薪酬待遇、发展空间往往是瓶颈;到沿海地区打工,在经济收入和发展机会方面无疑要大为改善,但很难支付举家迁移的成本,也很难获得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在赡养父母、抚育子女方面往往难以兼顾周全。
对于期望城镇化的农民工而言,当前的主要选择包括以下三种:举家迁往沿海大城市,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同时将小孩留在老家或附近的中小城镇,举家迁往老家附近的中小城镇。无论哪一种,只要牵涉买房,都离不开传统大家庭和父辈的经济支持。如有孩童需要抚育,则往往需要老人帮忙照料看护。父辈对子辈的支持主要包括城市购房、婚姻彩礼、隔代抚养。可以说,当前年轻一辈农民工的城镇化和家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压缩老人养老和医疗需求、依赖老人经济和劳务贡献的基础上的。在这一过程中,代际关系严重不平衡,资源往下走,子女本位取代孝道伦理(汪永涛,2013;金一虹,2014)。面对当前日益高昂的城镇化成本,农民工很少尝试向打工城市争取基本公共服务,更没想过如何抗议、约束推升住房及生活成本的掠夺之手,他们很自然地转向传统大家庭寻求解决方案;本应是社会、政府、市场间的博弈和利益调整,最后却内化为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和成员牺牲。
对于那些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同时将子女留在老家或附近中小城镇的农民工来说,传统大家庭的支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角色分工往往来得更复杂,且具有阶段性。王绍琛等(2016)对内蒙古赤峰市外出务工家庭的考察颇具参考价值。为了子辈的婚姻和孙辈的教育,父辈大多要倾尽全力帮助子辈在城镇购房,至于在城区还是在附近的镇区购房,则要看各自的经济实力。在小学阶段,年轻夫妇外出打工,老人中选一人到城镇看护陪读,另一人负责农业生产;到初中阶段,孩童具备一定自理能力,陪读的现象相应大为减少,老人又回到乡村务农;高中阶段被视为孩子教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外出的母亲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回来陪读,同时在城区找工作,老人如身体允许则仍然操持农务;等到孙辈成家立业,则如接力赛一般,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那些处于离散状态的家庭而言,如何在家庭成员间维系感情、处理矛盾冲突,是许多外出打工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学龄前将小孩带在身边、寒暑假将小孩接过来团聚、尽可能在农忙和春节期间回乡、频繁的通信互动、寄钱买礼品等,是维系家庭成员情感、预防化解家庭冲突的常见方式(金一虹,2009)。另外,外出务工者往往选择生活在亲缘、地缘网络中,通过亲友同乡聚集的方式缓解外出打工过程中的孤独、应对工作生活中的困境(金一虹,2010;汪建华,2016)。当然,这些调适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离散家庭的问题。
2.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子女教育毫无疑问是摆在许多流动家庭面前最棘手、最紧要的问题。应该说,随着2001年两为主(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政策的确立,各级政府逐渐加大经费投入,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状况逐渐得到改善。2010年,6~14岁义务教育年龄段的流动儿童在校比例超过96%。2009~2015年,接近八成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政府还对一些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儿童予以补助。
不过,流动儿童教育还存在许多实质性的问题,解决不好,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从教育阶段看,学前和高中阶段面临的问题比义务教育还要复杂。学前教育没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流动儿童入园难,入公办幼儿园更难;而由于异地升学难、高中学位紧张,许多儿童从初二开始,就陆续选择回到老家就读。从区域来看,北京、上海垄断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高招名额,珠三角因产业聚集吸引的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户籍人口,上述地区的入学门槛最高、异地升学最难,流动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也最为严峻。从流动跨度看,那些跨省流动的家庭和儿童最容易被异地中考、异地高考政策影响。性别方面,重男轻女的现象在流动家庭中仍然很普遍。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更愿意将男孩带到流入地共同生活、接受教育,结束初中教育后,则有越来越多的女孩进城打工。六普数据表明,处于义务教育学龄期的流动儿童,男孩占比更高;然而在15~17岁,男孩占比却陡然下降(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等,2013;杨东平,2017)。
在北京、上海、珠三角等地,公办学校的进入门槛非常高。大部分流动儿童只能进入民办学校或者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通常面临师资不足、设施不齐、班级规模过大、课外课程和实践机会少等问题。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可能存在校园歧视、难以融入、基础差、学习跟不上之类的情况。加上异地升学问题,部分公立学校和老师并不愿意花精力培养这些孩子。外来务工者由于文化水平、经济实力等方面的限制,在育儿方式、日常沟通、幼儿教育、家庭学习环境等方面,也往往不尽如人意(杨东平,2017)。当然,最大的障碍仍然来自制度层面。由于流动儿童难以进入公办学校、无法取得异地升学的机会,即便流动家庭再怎样努力学习中产阶级的科学育儿方式,向上流动的愿望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般的想象。因此,所谓子女教育投入不足、家庭教养方式存在缺陷,很可能是许多流动家庭在洞察现实后的无奈选择(肖索未等,20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