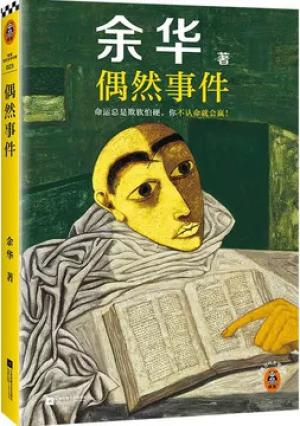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HK$
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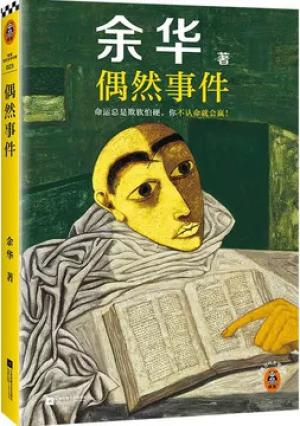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HK$
54.9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HK$
206.8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HK$
76.8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HK$
87.9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HK$
107.8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HK$
65.9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148.5
|
| 編輯推薦: |
|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曲艺名人以及河北地方戏等领域的名人的艺术生涯和追求,一方面追溯了曲艺名人们的艺术道路,另一方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有很强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
| 內容簡介: |
|
本书遴选作者近十年间在全国、省级报刊发表的文化艺术方面的纪实文章,大都是亲历亲闻的回忆。全书分为“国剧探微”“艺海拾贝”“非遗巡礼”三个专辑。“国剧探微”主要是写现当代京剧名人的从艺生涯和历史故实;“艺海拾贝”侧重地方戏、电影、音乐、杂技、书法、美术等领域名人的艺术追求及业绩;“非遗巡礼”主要展现河北省部分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的文化底蕴和特色。
|
| 關於作者: |
|
王德彰,1938年11月生,河北省蠡县人。编审。196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河北省戏曲研究室主办的《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编辑、河北省艺术学校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河北省肃宁县副县长、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河北省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河北文化音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河北省政协主办的《乡音》杂志主编。出版《艺术家的风采》《相思子》《名角》《谈戏说史》《燕赵十三梅·梁维玲卷》等专著。多篇文章被收入《百年春秋》《京华感旧录》《神州轶闻录》《梨园往事》《燕赵风云60年》《河北那些事儿》《河北省会在保定》《蠡邑名流》等图书中。
|
| 目錄:
|
国剧探微
梅兰芳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
京剧“四大名旦”的最后岁月
京剧“四大须生”的绝唱与归宿
奚啸伯和他演出的现代戏
我所知道的“领袖武旦”宋德珠
盖叫天三次断腿内情
响九霄是怎样一位演员
梁斌的戏剧生涯
孙犁与戏剧之缘
排演“样板戏”的年代
京剧史上的义演善举
“堂会戏”演出中那些事儿
京剧演出中的“插科打诨”
爱唱戏的皇帝
《走雪山》,发生在怀安的一个真实故事
艺海拾贝
香港艺术节上幸会邵逸夫先生
河北梆子《宝莲灯》拍电影
抗震救灾中的文艺演出
师伟的银幕内外
影片《早春二月》从“毒草”到香花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8年前我与李亚林的一次交往
那年我在县里接待贾又福
三缘斋主冯大彪
电影人高放的水墨乾坤
歌曲《我是一个兵》的诞生
二胡大家王曙亮的传奇故事
杂技奇才“画眉张”
刘丽霞:杂坛上的幕后功臣
魔术名家李丽的苦乐年华
于金生:“杂技是我的生命”
《白毛女》创作演出70年
晋剧《三上桃峰》事件
非遗巡礼
燕赵多豪杰,不平吼高腔
百年评剧唱新歌
保定有宝 老调不老
东路二人台,坝上一枝花
苏东坡与定州秧歌
硕果仅存的“深泽坠子”
载歌载舞哈哈腔
永年西调,老树春深发新枝
西河大鼓百年兴衰
燕南赵北响吹歌
享誉中外的徐水舞狮
武林英豪出沧州
虚实杂糅的“杨家将传说”
历史上有孟姜女这个人吗?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梅兰芳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
中国京剧的历史并不长,迄今不过200多年的时间。自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丰庆、四喜、春台、和春)进京形成京剧以来,作为国剧的京剧在这200多年间,出现了难以数计的京剧名伶、大师。但若问京剧史上其表演艺术最具代表性,且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谁?答案应该是不会有争议的——梅兰芳。
京剧“四大名旦”产生80多年来,业界和广大观众一直为此津津乐道。“四大名旦”艺术上确实各有千秋,相互之间的某些艺术特点也没有什么可比性,所以长期以来业界对“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争议,盖有三种意见:一是“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二是“梅、荀、尚、程”,三是“梅、程、尚、荀”。这三种意见中,无论尚、荀、程三位排序怎样变动,梅兰芳总是居于冠首,由此可见梅兰芳在京剧界的地位。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又名鹤鸣,字畹华,艺名兰芳;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他8岁学戏,擅演青衣、花旦、刀马旦各行当剧目,并与有“通天教主”之誉的王瑶卿一起将这三个行当的表演特点融为一体,形成了京剧的“花衫”行当,表演端庄华贵。他创演的代表剧目《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抗金兵》《太真外传》《游园惊梦》《天女散花》等,不仅成为京剧艺术的经典,饮誉海内外,而且成为京剧界一代又一代演员的传习剧目。抗战时期,他留居香港、上海,在敌伪统治下蓄须明志,坚拒演出,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病重期间,周总理从北戴河专程回京到病榻前看望。梅兰芳去世后备极哀荣,其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等61人组成,陈毅任主任委员。治丧委员会共收到280多封唁电,引人注目的是其中40多封来自于海外。
一位中华民族的京剧艺术家,为何逝后引起海外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应该说,这与梅兰芳作为一位文化使者将中国的京剧艺术推向世界有直接关系。
有资料准确记载的,梅兰芳一生中曾3次赴日、1次赴美、4次赴苏,1953年还曾赴朝慰问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时间跨度41年!前后9次赴海外演出,传播了中国京剧艺术,增进国际友谊,让世界了解中国,其贡献本身,已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梅兰芳海外巡演,书写了中国京剧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现在虽不敢妄说“后无来者”,但迄今为止可肯定地说“前无古人”。
三渡扶桑,岛国刮起“京剧旋风”
梅兰芳第一次赴日演出,也是第一次出国,时在1919年4月。
当年,25岁的梅兰芳在京剧界已是声誉鹊起,尤其是在演出剧目上,他勇于创新,排演的古装新戏不仅国内观众欢迎,而且各国外宾也颇感兴趣。在此之前,北京茶园式的戏馆里几乎看不到外国人的踪迹,可是在一次旅京美籍职员举办的联欢会上,梅兰芳应邀演出《嫦娥奔月》,受到热烈欢迎。从此,中国戏馆里有了国外观众。梅兰芳为了迎合观众的观赏习惯,净化舞台,革除陋习,不久就有开明(今北京珠市口电影院)、真光(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新式剧场开张,对号入座,使观众感到舒适卫生。
此后,梅兰芳的外事活动日渐频繁。一些国家的报刊及个人纷纷来函索取照片,尤其是同中国近邻的日本友人,到了北京几乎都要看京剧演出。当时外宾到中国旅游,往往向外交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观光长城;二是游览颐和园;三是访问梅兰芳。梅兰芳在布置的极富民族色彩的缀玉轩接待外宾。他先后接待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瑞典考古学家、王储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日本歌舞伎名演员守田勘弥、村田嘉久子等一批又一批的国际友人。这些来宾均由梅兰芳自费接待。
日本人对中国京剧的了解,要先于欧洲人。早在1918年,日本帝国剧场董事长大仓喜八郎来北京旅游,观看了梅兰芳演出的《天女散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于是决定邀请他赴日演出。
梅兰芳欣然接受了邀请,他说:“我出去的目的,一方面想把中国戏曲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是借此观摩吸收外国艺术来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
梅兰芳赴日演出团,阵容强大,名角济济,行当齐全,计有:姚玉芙、姜妙香、贯大元、高庆奎、芙蓉草(赵桐珊)、何喜春、陶玉芝、董玉林、王毓楼,还有齐如山等。准备赴日访问演出的剧目,梅兰芳主演的有《天女散花》《御碑亭》《黛玉葬花》《贵妃醉酒》《春香闹学》《游园惊梦》《虹霓关》《千金一笑》《琴挑》《游龙戏凤》《嫦娥奔月》,其他演员的剧目有《战蒲关》《文昭关》《思凡》《乌龙院》《鸿鸾禧》《武家坡》《洪羊洞》《监酒令》《乌盆记》《举鼎观画》(到日本后应剧场要求又增加了《空城计》)。
梅剧团于1919年4月21日起程,坐轮船于24日下午到日本下关,然后转乘火车于25日晚到达东京。在东京车站,日本各界欢迎者如堵,演员们几分钟也难走动一步。
据许姬传著(徐国航整理)《梅兰芳传略》记述,在东京,梅兰芳演出的《天女散花》,由贯大元饰文殊师利菩萨,高庆奎饰摩诘居士,姚玉芙饰花奴,赵醉秋饰伽蓝。(在梅剧团回国后,日本剧团学演了《天女散花》,不少名优模仿梅兰芳的舞姿,称为“梅舞”。)《御碑亭》演出时,许多妇女掩面而泣,因为像王有道休妻的事,在日本是屡见不鲜的。戏中由梅兰芳饰孟月华,高庆奎饰王有道,姜妙香饰柳生春,赵醉秋饰德禄。梅兰芳与姜妙香演出的《玉簪记》中“琴挑”一折,姚玉芙演出的《孽海记》中“思凡”一折,引起了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青木正儿的重视。他曾著文系统分析昆曲源流并评述“琴挑”与“思凡”的表演技巧。
梅剧团在东京演出后,又赴大阪、神户演出,于5月26日离开神户,取道下关回国。梅剧团第一次赴日演出月余,场场引起轰动,日本《国民新闻》《东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大阪日报》等报纸,发表了大量评论,都认为梅兰芳的表演是卓越的,无与伦比的,是象征主义的高超艺术。报道说京剧不使用布景,只用简单的道具,但演来有声有色,令人钦佩。还说看了梅兰芳的戏,纠正了他们过去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
1924年10月,时年88岁的大仓喜八郎董事长再次邀请梅兰芳访日演出。梅剧团一行40余人于10月9日取道天津赴日,10月14日到达东京。梅兰芳第二次赴日本巡回演出时,正值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年。梅兰芳为了支援帝国剧场的复兴,所以在东京演出的时间比较长,还义演募捐,救济日本灾民。随后,又到京都演出了《贵妃醉酒》《洛神》《奇双会》等,并到小阪电影厂拍摄了《廉锦枫》《红线盗盒》《虹霓关》三部无声黑白片,使梅派艺术在日本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梅兰芳第三次访日演出是在1956年。与第一、二次赴日演出不同的是,此时已是新中国成立第八个年头,抗日战争胜利也已11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今非昔比。这一年,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以梅兰芳(时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为总团长,欧阳予倩为副总团长和以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赴日演出。这是梅兰芳历次率团出国阵容最整齐、规模最大的一次,由86人组成。演员有李少春、姜妙香、李和曾、袁世海、梅葆玥、梅葆玖等,乐队有王少卿、白登云、姜凤山等。
据刘彦君著《梅兰芳传》记载,对于这次赴日演出,开始接受任务时梅兰芳心里很不是滋味,思绪万千。八年抗战,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历历在目,而自己蓄须拒演的隐居生活更是刻骨铭心……仿佛是洞察了梅兰芳的心思,周恩来总理约梅兰芳谈话。一见面,总理便进入了正题:“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啦,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儿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中国访日代表团到日本旅行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周总理还说,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访日代表所负的责任是打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门。文化和经济是两个翅膀,现在文化打先锋开路。这次一定要打胜仗,接着我们的经济团体也将前往……梅兰芳这才明白,此次访日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演出,而且肩负着巨大的政治任务。他坚定地说:“我遵照您的指示去办。”
5月26日,以梅兰芳为总团长的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登上飞机,下午3时45分到达东京机场,日方举行了欢迎大会。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在所致欢迎词中说:“感谢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梅兰芳在答词中也道:“中日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密切的悠久的历史关系,我们都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不断的加强。”现场人声鼎沸,欢迎的人群唱起了《东方红》《东京—北京》等歌曲……
5月30日,代表团在东京进行首场演出,演出的剧目是四个折子戏:《将相和》《拾玉镯》《三岔口》和《贵妃醉酒》,引起轰动,票价是1800日元,转让价是10 000日元。
访日期间,代表团先后在东京、福冈、大阪、奈良、京都等地演出,在全岛演遍。
演出期间,日本观众反应强烈,岛国刮起“京剧旋风”。他们虽然不懂中国话,但对剧情和京剧表演的上马、开门、过桥、登楼的虚拟动作,大部分是能够理解的。比如《将相和》中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一场,《拾玉镯》的做针线活儿、轰鸡,《三岔口》的摸黑儿开打,《贵妃醉酒》的过桥、看雁、闻花、衔杯等身段都引起强烈的反响。每场演出,剧终谢幕多次,日本各界朋友纷纷上台献花,群众有节奏地鼓掌。
代表团演出期间还有一个“插曲”。那是第一天在东京演出《贵妃醉酒》,当梅兰芳扮的杨贵妃上场后,忽然听见三楼有人怪叫一声,接着撒下许多传单,有些落在观众身上,但观众不去理会,依旧聚精会神地看戏。第二天,《读卖新闻》的晚刊上登载了这个消息:“有些坏小子向梅兰芳的舞台上扔反共传单,这些混蛋像垃圾一样,在任何角落里总有一些的。”孙平化把捡到的传单给梅兰芳看,只见上面写着:“抗日的梅兰芳先生为何来到日本?”梅兰芳看了付之一笑,把他撕碎,随手扔到便桶里去了。
在中日两国未恢复邦交的情况下,日本国会议员破例在国会大厦招待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的梅兰芳、欧阳予倩等主要成员。代表团还在广岛车站观看了原子弹受难者的畸形面貌,大受触动,梅兰芳、欧阳予倩创意,义演两场,收入悉数捐献给受害者。
7月17日,代表团圆满完成演出任务,乘飞机回国。此行,梅兰芳不仅向日本传播了京剧艺术,更主要的是发挥了“和平使者”的重要作用。
齐如山悉心策划,赴美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说到梅兰芳赴美演出,不得不提齐如山。
齐如山(1875—1962)是河北高阳县人,著名戏曲理论家、剧作家,早年留学西欧,涉猎外国戏剧,后致力于戏曲工作。他经常为梅兰芳演出进行策划,不仅是梅的“智囊”,而且是梅的编剧。梅兰芳演出的时装戏《一缕麻》,古装戏《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千金一笑》等,都是以他为主编演的。
早在1919年,齐如山随梅兰芳第一次赴日本演出期间,他发现热情的观众中,除日本人外,还有驻日各国使馆人员以及众多在日经商的欧美商人,他们对中国京剧称誉有加。此情此景,坚定了齐如山将中国京剧打入欧美市场的信心。
为促成梅兰芳赴美演出,齐如山先找到他的老朋友、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征求意见。司徒雷登完全赞同,说:“梅兰芳的面貌、歌舞,到美国演出肯定没问题。”并爽快地答应帮忙。留美归来并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多年的张彭春也帮助出谋划策,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最后商定:梅兰芳以个人访问演出的名义赴美。
演出方案确定后,首先是准备剧目。齐如山与梅兰芳商定,由梅兰芳主演的剧目共16出,即《霸王别姬》《贵妃醉酒》《黛玉葬花》《拷红》《琴挑》《洛神》《思凡》《游园惊梦》《御碑亭》《汾河湾》《千金一笑》《虹霓关》《金山寺》《打渔杀家》《木兰从军》《天女散花》。其他演员的戏有《群英会》《空城计》《捉放曹》《青石山》《打城隍》等。
由于这次是梅兰芳以个人名义赴美演出,这就涉及路费问题。这时,齐如山想到自己的亲戚、留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李石曾大力支持,说“自己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这样,李石曾为之筹措5万元,由友人在上海又筹集5万元。一切准备就绪,梅兰芳带领精干的20余人的赴美演出团,于1929年12月下旬乘“加拿大”号轮船从上海出发,经日本、加拿大,于1930年1月到达美国西雅图。
梅剧团一到美国,就受到各界人士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加拿大”号抵西雅图当天,会场外已站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西雅图,中美商界联合会举行了“欢迎梅兰芳大会”。梅剧团所乘火车刚进纽约车站,欢迎的人们就围了上来,警察忙从月台到车站外门两边,拉起绳子,让梅剧团通行。两边的人们热情地摇着手绢,有的挥动帽子致意,还有人把鲜花抛向梅兰芳,梅兰芳一路脱帽表示感谢,身上头上都是鲜花。
据李仲明著《梅兰芳》一书记述,梅兰芳剧团的首场演出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公使馆举行梅剧团演出招待会,除了美国总统胡佛不在首都外,副总统及以下官员、各界知名人士200余人出席了招待会。招待会上,梅兰芳演出了《千金一笑》(《晴雯撕扇》),朱桂芳、刘连荣、王少亭出演了《青石山》。
正巧张彭春应美国某大学邀请赴美讲学,也应邀观戏。他到后台来看梅兰芳,梅兰芳忙问:“今天的戏,美国人看得懂吗?”张彭春答:“不懂,因为外国没有端阳节,《千金一笑》中晴雯为什么要撕扇子,他们更弄不清楚。”梅兰芳紧握着张彭春的手说:“张先生,照您的说法要另选剧目,请您帮忙带我重新组织安排一下。”张彭春说:“我愿意帮忙,但讲学若延期,必须得家兄伯苓的同意。”
梅兰芳立刻打电报给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很快复电同意,梅兰芳便请张彭春担任剧团总导演。这是梅剧团第一次建立导演制,也是第一次由懂得戏曲的话剧行家做京剧导演。
考虑到演出时间不宜过长,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每场戏演4个剧目,规定两个小时。把前后时间安排好,并选定了3组剧目。据许姬传、许源来著《忆艺术大师梅兰芳》记载,这3组剧目为:第一组:《汾河湾》《青石山》、“剑舞”(《红线盗盒》片段)、《贞娥刺虎》;第二组:《贵妃醉酒》《芦花荡》、“羽舞”(《西施》片段)、《打渔杀家》;第三组:《汾河湾》《青石山》《别姬》(只演《巡营》一折)、“杯盘舞”(《麻姑献寿》片段)。为了演出时间准确,梅兰芳剧团反复排练,张彭春看着手表计算时间,《汾河湾》规定27分钟,《青石山》9分钟,《红线盗盒》舞剑5分钟,《刺虎》31分钟。演出时间的准确程度使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
1930年2月16日,梅兰芳在纽约百老汇演出更是盛况空前。据《梅兰芳传》记载,观众一进场,先被剧场内外浓重的异国情调深深地吸引住了。剧场门前满挂宫灯,堂内全场也挂满了纱灯,身穿中式服装的招待员穿梭期间,使剧场内外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的东方景象。
舞台也修饰了一番。第一层幕布仍用该剧场原来的旧幕,第二层则换成了中国式的红绸缎幕;再往里,第三层是两根中国戏台的外檐龙柱,上挂一副对联:“四方王会夙具威仪,五千年文物雍容,茂启元音辉此日;三世伶官早扬俊采,九万里舟轺历聘,全凭雅乐畅宗风。”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对;最里面的第六层就是旧式戏台了。
2月16日晚开戏之前,全体演职员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时间已近8点50分,剧院还没有几个人,琴师徐兰沅有点儿紧张地问姚玉芙:“今儿还有戏吗?怎么不上坐?”姚玉芙宽慰他:“票都买完了,美国人掐钟点,会来的。”到9点前,果然坐满了人。
9点整,身穿礼服的张彭春走上台,向观众介绍中国京剧的特点,梅剧团在美国邀请的华侨杨秀女士用流畅的英语报幕,她首先介绍了《汾河湾》的剧情:“薛仁贵因为一只鞋,就怀疑柳氏品行不端。柳氏知道鞋是儿子的,就借机气他。后来说明情由,薛仁贵再三赔礼,柳氏不理,后来到适当的时候,才赶紧笑脸相迎,夫妻和好。”观众听了,觉得这戏的情节挺有意思,就议论起来。梅兰芳一上场,全场马上报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就静下来看演唱。梅兰芳优美的扮相和演唱,形象传神的身段姿态,深深吸引了很多第一次看京剧的美国观众,柳迎春进窑这场演完,观众热烈鼓掌。后边梅兰芳表演的“舞剑”,演出的《贞娥刺虎》,更是征服了美国观众,掌声不断。当地报纸发文,好评如潮。
三天之后,两个星期的戏票预售一空,不得不在国家剧院续演了三个星期。
离开纽约,梅兰芳一行人来到芝加哥,在公主戏院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演出。结束后,又到了美籍华人密集的旧金山,先后在三个戏院共演出13天,后赴洛杉矶演出12天,最后乘船到夏威夷,演出12天。
半年多的访问演出期间,无论梅兰芳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在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等地,都是市长亲自迎接。在观众眼里,梅兰芳不仅是中国戏曲的化身,更是中国文化的使节。对于来美演出的梅剧团,政界、学界、商界等社会各界,都竭心尽力地竞相表示出友好热情。如到达纽约的当天,就有两位女士——都是纽约社交界的领袖人物——同时举行茶会,为梅兰芳一行接风。一家茶会所约的人大多是学者、批评家、新闻记者、大资本家等,共有100多位;另一家茶会的客人则都是戏剧界、美术界、新闻界中人,也有六七十位。盛情难却,梅兰芳等人只好两边都到,才得以应酬下来。
纽约社交界重要人物之一的沃拂兰女士,在梅兰芳演出的前3个星期中,一共看了16场。演出结束后,她请梅兰芳等人到她家吃饭。当得知梅兰芳那年36岁时,便特意买了36株梅树,她那200多亩大的花园里另开了一块地,请梅兰芳破土,当天栽种,并将这片梅林命名为“梅兰芳花园”。
令梅兰芳一行最为感动的是那些旅美华侨的深情厚谊。每到一处,侨胞们总是先一步迎上去,嘘寒问暖,照应得无微不至。他们或是在当地的一些报纸上大力宣传并盛赞这次演出,或是请梅兰芳等人游览名胜古迹、学校、工厂等,或是赴中华会馆的盛大欢迎茶会,或是在演出过程中跑前跑后,充当翻译,并为他们代买舞台上的不时之需,或是同车同船相送,安排运输,沿途办理或指导一切相关事务……
5月12日,梅兰芳剧团到达洛杉矶时,在欢迎酒会上,通过经理介绍,梅兰芳结识了美国著名戏剧大师卓别林。当他惊喜地和卓别林握手时,卓别林高兴地说:“我早就听到你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你这么年轻。”梅兰芳也很高兴,但他难以把在银幕上见过的幽默、滑稽的艺术形象同眼前这位风度翩翩、具有绅士风度的电影大师联系起来。梅兰芳在美国访问演出,更受到美国教育界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梅兰芳是沟通中美文化的使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等高校特别为梅兰芳举行了欢迎会或座谈会。
梅剧团在洛杉矶演出时,波摩拿学院院长晏文士召集全体校董教授开会,建议借此机会授予梅兰芳文学博士学位,大家一致赞同,原定于该校6月16日毕业典礼时同时颁发。院长征求梅兰芳同意,梅谦逊婉拒。院长诚恳地说:“您这次访美演出,宣传东方艺术,联络美中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世界文化,这样伟大的功绩几十年还没有过,所以本校才议决把这个荣衔赠给您。您不敢当,谁敢当呢?”梅兰芳觉得盛情难却,方才同意接受。因梅兰芳6月6日要赶赴檀香山演出,学院便特别做出决定,于5月28日提前颁授学位。是日,梅兰芳换了衣服,坐在礼堂第一排,院长致开幕词,弗里曼、邓肯两位博士先后发言,然后由院长亲自把博士文凭交给梅兰芳,两位博士将“博士带”披在梅兰芳的肩上,全场热烈鼓掌致贺。
四赴苏联演出,誉满欧洲
在梅兰芳海外演出生涯中,去的次数最多的是苏联,前后共4次,跨度25年。
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成功后,便产生了到欧洲旅演的念头,旨在把京剧艺术介绍给更多的国家,让更多的人民了解、欣赏中国戏曲。
从美国回来后,梅兰芳就与驻英、法、德的外交官联系准备赴欧洲访问演出,并和旅华欧籍友人以及曾在欧洲留学的中国朋友交换意见。梅兰芳原打算到英、法、德、意等国演出,但考虑到费用较大、筹备复杂,一直未能成行,但他要赴欧演出的消息,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1935年1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库里雅科向梅兰芳发出正式邀请书,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派汉文参赞鄂山萌送交梅兰芳。访苏演出是梅兰芳的夙愿,所以他立即复电接受邀请。但接受邀请有一个前提,即旅途中不经过被日本侵占的中国的南满路。
苏方同意这个条件,苏联政府即特派北方号轮船,到上海迎接梅兰芳剧团(当时梅正在上海)。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赴苏参加电影节的电影明星胡蝶也随团前往。北方号到达海参崴后,1935年3月2日,梅兰芳剧团乘火车西行,于3月12日到达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苏联戏剧家协会等代表团到车站欢迎。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梅兰芳怀着崇敬、哀悼的心情,准备了花圈到红场拜谒列宁墓。当天,梅兰芳到高尔基大街一家美术商店买了一尊列宁像。1960年梅兰芳回忆道:“二十五年来,这尊塑像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身边,成为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在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残酷环境里,流离颠沛的崎岖道路中,我看到他就增加了勇气,意志坚定地与恶势力做斗争。”
梅兰芳剧团即将演出的消息,引起莫斯科观众和文化艺术界极大的兴趣。各场戏票从3月5日开始出售,不到一周,也就是梅剧团尚未抵达莫斯科时便销售一空。为了让观众了解中国京剧,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特意编印了三种俄文图书,在剧院出售。这三种图书是《梅兰芳与中国戏剧》《梅兰芳在苏联所表演之六种戏及六种舞之说明》和《大剧院所演三种戏之对白》(这“三种戏”是指《打渔杀家》《盗丹》和《虹霓关》)。
梅兰芳原定在莫斯科演5场,列宁格勒演3场,但因观众购票踊跃,应苏方要求,在莫斯科演6场,在列宁格勒演8场。
从3月23日起,在莫斯科演出6场的戏码是《宇宙锋》《汾河湾》《贞娥刺虎》《打渔杀家》《虹霓关》《贵妃醉酒》等,同时还表演了6种舞:《西施》之“羽舞”,《木兰从军》之“鞭卦子”,《思凡》之“拂尘舞”,《麻姑献寿》之“袖舞”,《霸王别姬》之“剑舞”,《红线盗盒》之“单剑舞”。4月5日、6日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演出的戏码分别是《贵妃醉酒》《锺馗嫁妹》《木兰从军》《盗仙草》《贞娥刺虎》和《汾河湾》《钟馗嫁妹》《红线盗盒》《青石山》《贞娥刺虎》。在列宁格勒演出场场爆满,全城兴起“京剧热”。
据《梅兰芳传》披露,梅兰芳在列宁格勒演出结束后,又回到莫斯科。4月13日,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要求,在莫斯科大剧院加演一场,作为临别纪念招待晚会。莫斯科大剧院历史悠久,建筑辉煌,闻名世界,是苏联戏剧界的最高学府,向以演出歌剧和芭蕾舞著称。而这一天,却破例演出中国京剧,无疑显示出苏联对梅兰芳京剧表演的推崇。那天,梅兰芳演出的三出戏是苏联官方提出的,即《打渔杀家》《盗丹》和《虹霓关》。出席晚会的苏联党政领导人有莫洛托夫、季维诺夫、伏罗希洛夫等;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梅耶荷德,文学家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著名芭蕾舞演员谢苗诺娃,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专程赴苏观摩梅兰芳表演的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也参加了晚会。演出中,剧场里出现了观众意想不到的一幕——前台后台戒备森严,在下场门的第二个包厢里不许有灯光!事后人们才听说,那是苏联最高首脑斯大林在包厢里观看演出。 梅兰芳、王少亭合演的《打渔杀家》,1930年出访美国时就很受欢迎,这次在苏联演出,仍然备受欢迎,并得到相当高的评价。苏联艺术家对于梅兰芳、王少亭二人,只凭一柄木桨,在并无其他道具的宽阔舞台上,表现出父女二人在水面上划船前行的生动、逼真的姿态大加赞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中国戏的表演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动作。”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的演出后,于1936年发表一篇题为《论中国戏曲与间离效果》的论文,对梅兰芳在《打渔杀家》中的表演极为佩服。
这场告别演出受到苏联各界人士热烈的欢迎,梅兰芳被剧院内经久不息的掌声请出来谢幕,竟达18次之多。苏联《工人与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应被视为苏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里程碑。”
梅兰芳在苏联演出一个半月之后的1935年4月中旬,离开苏联,前往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考察戏剧。6月到达英国伦敦,结识了萧伯纳等众多戏剧家,后取道埃及、印度回国,胜利完成了第一次赴苏演出。
1952年底,梅兰芳第二次赴苏。这次不是专程演出,而是到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归途中访问苏联。莫斯科火车站站台上的欢迎者众多,著名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乌兰诺娃也在其中。
在苏联对外协会的热情接待下,梅兰芳等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观游览了12天。12月30日,梅兰芳等应邀到莫斯科“演员之家”参加联欢会,梅兰芳演出了昆曲《思凡》和《霸王别姬》的剑舞。苏联艺术家也穿插表演了歌舞、杂耍节目。
1953年元旦,梅兰芳等到了列宁格勒,3日晚在该市的“演员之家”演出,梅兰芳仍演了《思凡》和《霸王别姬》。演出之余,梅兰芳和著名电影演员契尔卡索夫谈论戏剧表演和电影艺术。
回到莫斯科,梅兰芳参加“电影之家”和莫斯科作家协会合办的联欢晚会,梅兰芳第三次演出了《思凡》和《霸王别姬》。
1957年11月,梅兰芳第三次赴苏,随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铺。在莫斯科,梅兰芳参加了隆重的红场检阅观礼。令梅兰芳尤为高兴的是,与芭蕾舞表演艺术家乌兰诺娃再次见面并观看她的演出。一天上午,梅兰芳和田汉、老舍、阳翰笙、王昆等来到莫斯科大剧院,梅兰芳代表中国文化艺术界把一本彩色套印的《中国戏曲服装图案》赠给乌兰诺娃,还热情邀请乌兰诺娃参加1959年中国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演出。乌兰诺娃笑着说:“我愿意和中国人民一同庆祝这个节日……芭蕾舞是一种残酷的艺术,到那时我能不能演出,完全没有把握。”话虽这样说,两年后她还是随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到北京,演出了《吉赛儿》《天鹅之死》和《仙女们》。
1960年2月,梅兰芳第四次访问苏联,他还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访日、访苏,继续了他二三十年代访日、访苏的历程,每一次都完成了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使节的重要任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