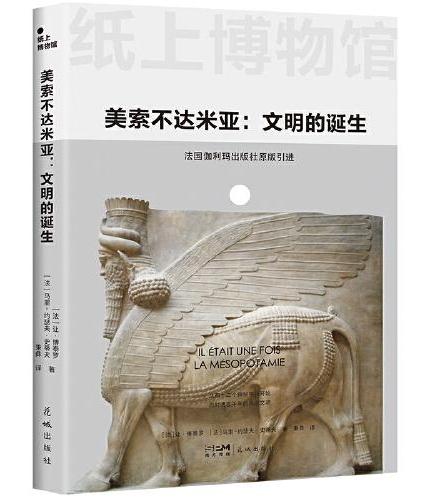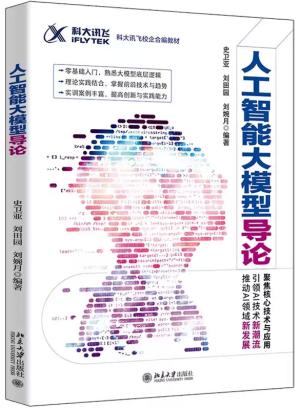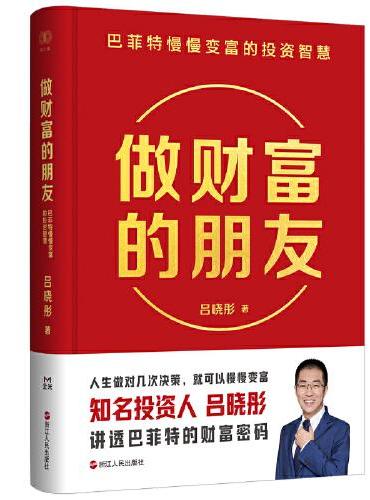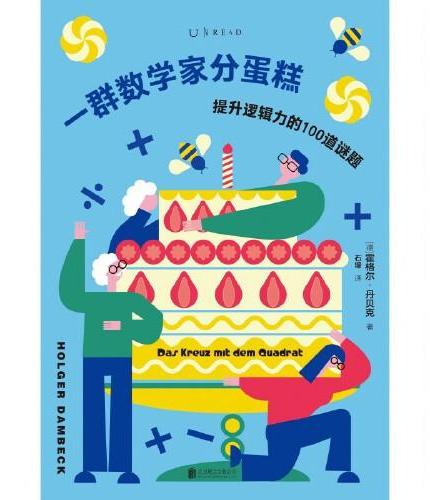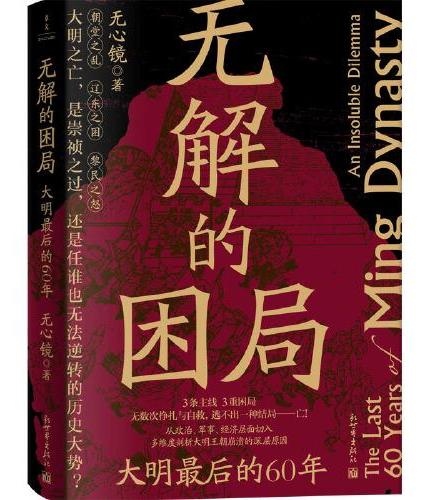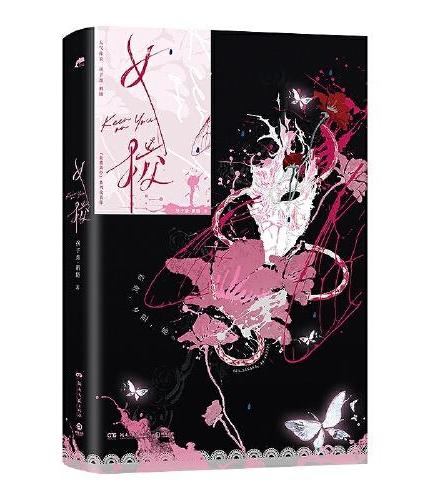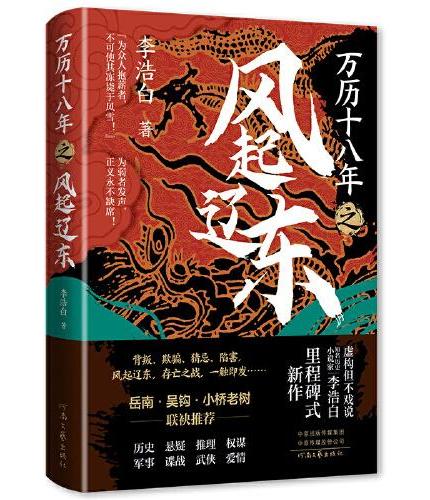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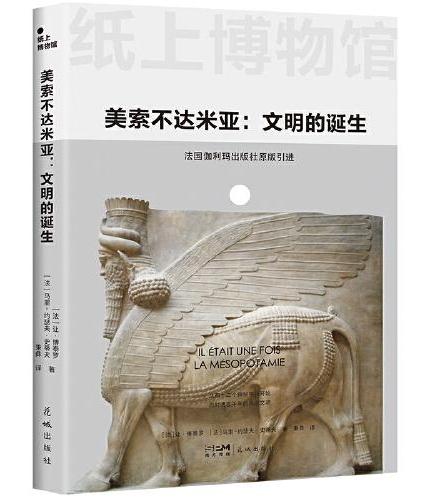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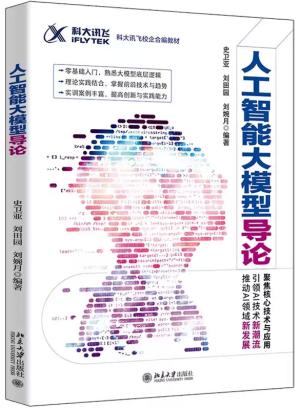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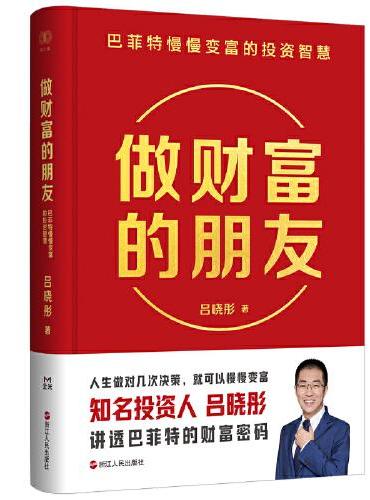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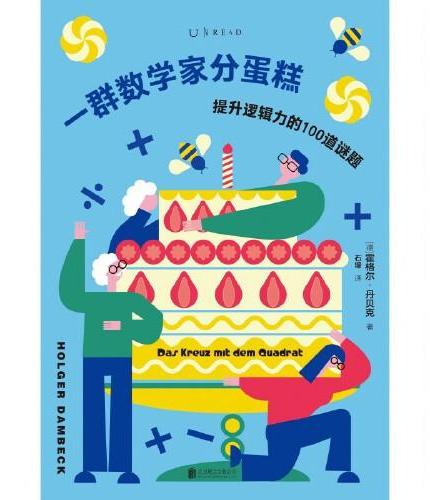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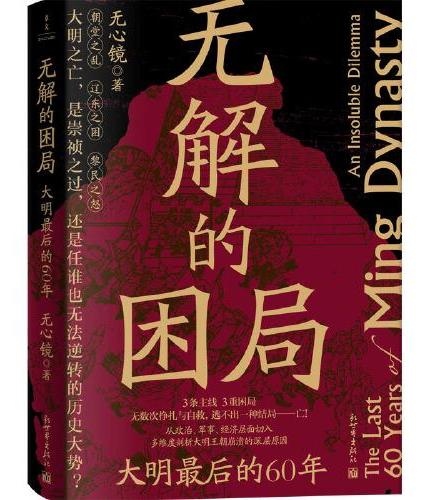
《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
》
售價:HK$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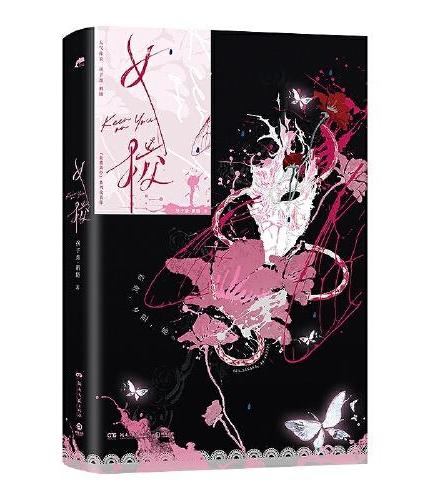
《
女校(人气作家孩子帮·鹅随“北番高中”系列代表作!)
》
售價:HK$
6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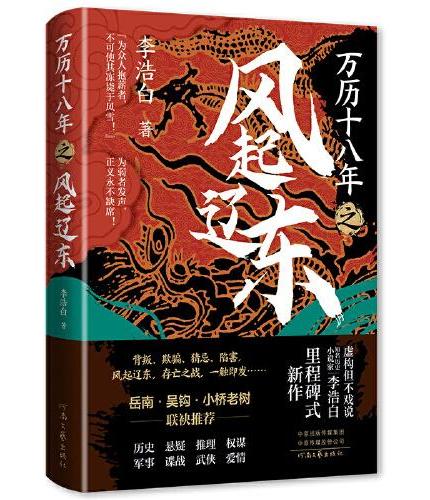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
《古典与现代》一直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第六卷延续这一系列的既有品质,挖掘中西古典文化中的精华,汇集当代学者和作家对之所作的新阐释。本卷在翻译理论、制度遗产和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均有佳作。
|
| 內容簡介: |
|
著名学者杨国良教授主编的《古典与现代第六卷》,集结了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最新文章。此卷秉承以往各卷经典阐释与当代关怀相结合的宗旨,内容涵盖海南文史、文学品评、思想漫谈、人物春秋以及其他的文化探讨,既有深度的学术前沿解读,也不乏至情至性的生动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知识分子的热忱情怀与理想坚守。
|
| 關於作者: |
|
杨国良,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应用语言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1996 年留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主要从事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
|
| 目錄:
|
卷首语
特 稿
【俄】罗扎诺夫著;田全金译 《俄罗斯文学启示录》1917—1918 1
胡艳秋 什么样的人,才敢写“启示录”? 29
唐逸专辑
我们的制度价值遗产 35
价值的本原 53
正义集释 82
思想边界
张志扬 古典学:扣两端而执其中 94
谢天振 从钱锺书的翻译理论看杨绛的翻译实践 107
胡新文 英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借鉴与思考 112
笔记摘抄
李 溢 溢斋笔记之《大学》发微六则 121
王 新 视觉笔记五则 130
陈 刚 格奥尔格《词语》一诗读后外一章 140
薪火相传
肖 峰 正在消失的鼎城传统农具 144
周伟民 唐玲玲 黎峒文化考察记 148
林 秋 马蒙丹美术馆记 185
李荣南 悼屈原 193
野 叟 游君山有感外一首 196
刘子铭 徒步读经纪行 197
孙凌昱 给小陈陈的信 198
胡艳秋 暂歇的驿站抑或永久的港湾? 210
主编手记 213
|
| 內容試閱:
|
从钱锺书的翻译理论看杨绛的翻译实践
谢天振
我想从杨绛请求钱锺书为其批校译作《吉尔布拉斯》的一则趣事谈起。
解放初期,钱锺书、杨绛得到母校清华大学的聘请。钱锺书的工作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按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当专任教授;杨绛那时是兼任教授。她在清华的授课任务不重,业余时间就从事文学翻译——首先选译了非常适合自己趣味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1954年1月,杨绛四十七万字的译作《吉尔布拉斯》开始在《世界文学》分期刊出,受到主编陈冰夷的表扬。但她自己觉得翻译得很糟,“从头译到尾,没有译到能叫读者流口水的段落”,就请钱锺书校对一遍。
钱锺书拿了一支铅笔,使劲在稿子上打杠子。杨绛急得直求他“轻点轻点”,划破了纸她得重抄。钱锺书不理会,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成了名副其实的“校仇”。他只说:“我不懂。”杨绛说:“书上这样说的……”他强调:“我不懂。”——这就是说,译作还没把原文译过来。杨绛领悟了他的意思,再斟酌修改。钱锺书看了几页改稿,点头了,杨绛也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
杨绛是钱先生翻译理论的最佳实践者。
我们通常知道的钱锺书的翻译思想是其“化境”理论,这在《林纾的翻译》一文有比较全面的反映。早在1934年,他就明确使用过“翻译学”和“艺术化的翻译 ”(translation as an art)两个术语,另有大量见地独到的有关翻译的片断论述,散见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中。他曾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等类”的标准;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又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可见,无论在翻译实践或理论层面,钱先生都堪称大家。
当然,我们最好把杨绛的翻译与他联系起来看待,会有新的发现。
1978年,杨绛译《堂吉诃德》开始发行。该译初本凡八十余万字,经过一番认真“点烦”,一举去除十万字,形成了七十余万字的定译本。
在《翻译的技巧》一文中,杨绛详细解释了她的“点烦术”:
简掉可简的字,就是唐代刘知几《史通》《外篇》所谓“点烦”。芟芜去杂,可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这是一道很细致、也很艰巨的工序。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在这道工序里得注意两件事。一“点烦”的过程里不免又颠倒些短句。属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和属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不能颠倒,也不能连接为一句,因为这样容易走失原文的语气。二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如果去掉的文字过多,读来会觉得迫促,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这都需译者掌握得宜。
上世纪末,在钱锺书和他们的爱女钱瑗去世半年后,杨绛“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她选择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记录先师苏格拉底临终之言的《斐多》篇,也是这样操作的,效果非常好!她“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 所以“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如此,译就的哲学对话录竟然能像小说般引人入胜、奥妙无穷!傅雷先生曾说,“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文字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杨绛《斐多》之译无疑站到了这样的高度。
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翻译存有一种偏见,总以为翻译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只要懂一点外语,有一本外语辞典,任何人都能从事文学翻译。这种偏见同时还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文学家和翻译文学的看法:前者被鄙薄为“翻译匠”,后者则被视作没有独立的自身价值。
这里,我必须为翻译“正名”,希望大家重视翻译。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功不可没。当时有十五个亲临颁奖典礼的机会,莫言把其中两张“门票”给了我的同事——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夫妇。这是在莫言的亲人范围之外,将其作为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中国区唯一推荐人,以此表示他对陈教授在现当代文学评论、文化译介工作方面突出贡献的肯定。我曾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葛浩文先生谈论翻译问题。他说,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翻译,译者们为树立他的国际声誉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必须注意到中国作家对翻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莫言曾就“文学走出去”的话题发表看法:“今年翻译一百本,或者明年一本没翻译,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世界可能会以上百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译介可以是多渠道的,汉学家也要主动发现,兴趣化、个性化的翻译更有意思。作家同行们也应该互相推荐,利用国际讲坛等各种形式积极主动地向认识的汉学家推荐介绍同行作品。”并不是所有作者都如莫言一样懂得翻译、懂得译介学,以山东作协主席张炜近期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为例,张炜称很多译者“只翻译故事不翻译语言”,他没法容忍,因此终止了许多作品的译介出版,并采取了严格的翻译要求:译者的选择要经过作者认可,长篇小说每翻译一章都要给作者检查审核,作者觉得翻译得不够好就推倒重来。这些要求听上去有些道理,体现了作家的认真严肃,但其实是对翻译作品的外行话。作家为自己的读者而创作,译者也是为他的读者而翻译,为了让他的读者接受、认可作品。如果读者不接受,翻译是不成功的。
我认为,西方读者接受华语作家时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译介西方作品,而西方读者则是在近一二十年才渐渐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兴趣。也就相当于严复、林纾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水平。当时的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删节,将故事本土化,改成章回体小说。现在我们翻译出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读者的接受程度,这也是一种策略,不要操之过急追求全译本。
再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例说明。从语言文字的转换方面,杨宪益翻译的版本做得很不错,而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的译本则改动很多,受到很多批评。但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奉献出很忠实的译本,但没有读者去看,这样的翻译活动能算是成功的吗?
使中国文化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应当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有关中国文化的译介工作。
在国内建立中译外常设基地,为国外汉学家、翻译家与国内专家学者、作家搭建沟通的桥梁。
我们的翻译工作者要确立现代化的译学观念,要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最好都能学一点翻译学理论。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就是要理解翻译的本质,理解文化的交际,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由此而言,杨先生多年来在翻译工作上贡献突出。她成功翻译《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巨著《堂吉诃德》、哲学对话录《斐多》等,都可以认为,正是有了文化层面的理解和“可翻译”这一维度,她的翻译作品才能被称誉为“在忠于原著基础上进行的翻译”。
这很适用于现代翻译。
我始终坚持,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新的形式,或新思想、新形象”,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原作难以代替的作用”。而翻译的重要文化意义在于: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钱锺书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严肃认真而不失偏颇,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翻译观体现了从传统翻译理论向现代翻译理论的过渡,并由杨绛先生成功实践,意义非凡,希望重新引起学界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