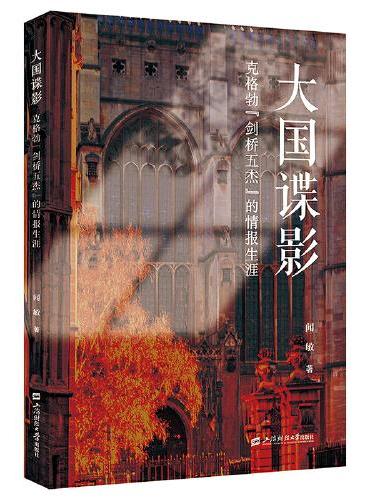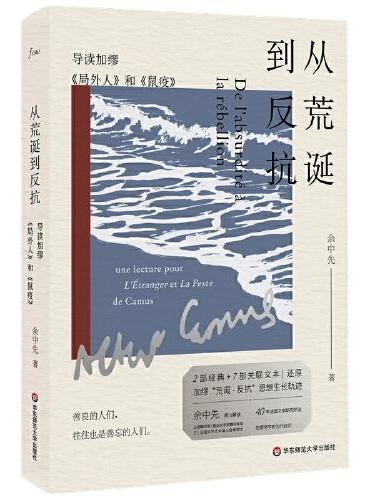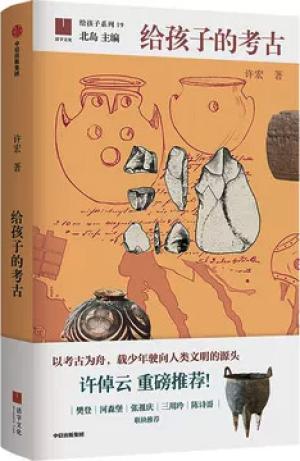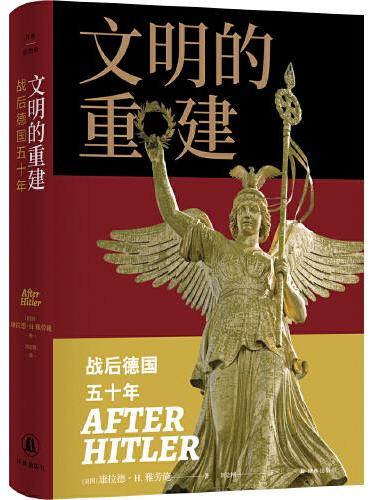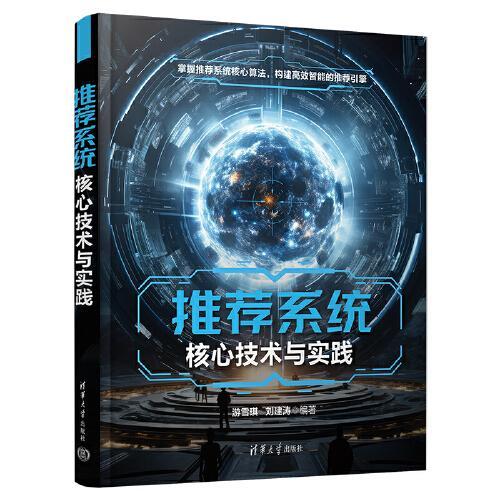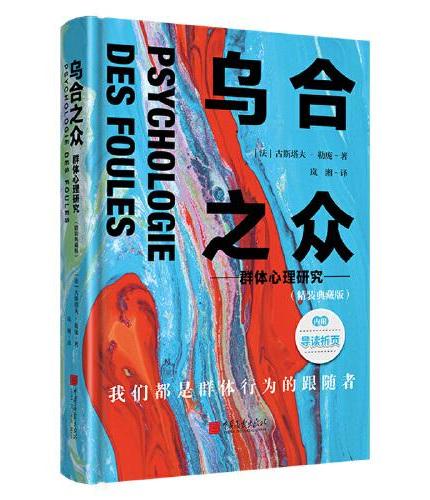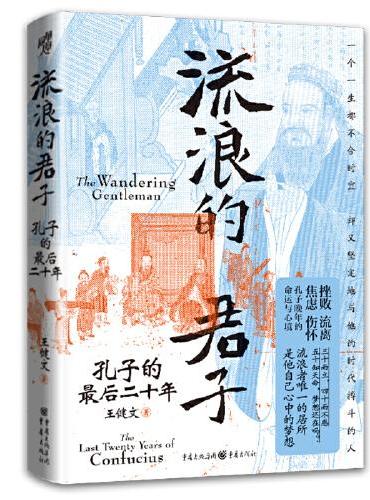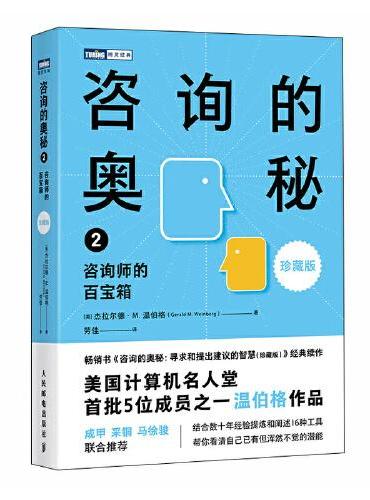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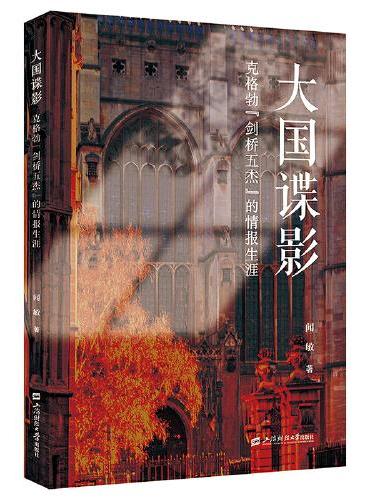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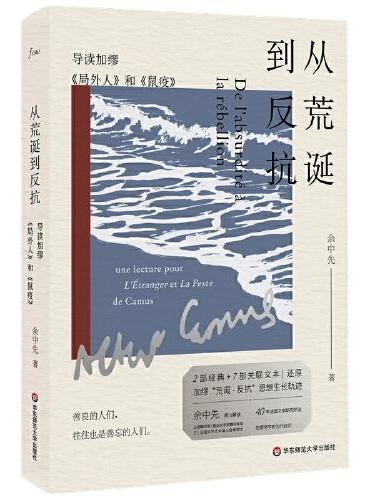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HK$
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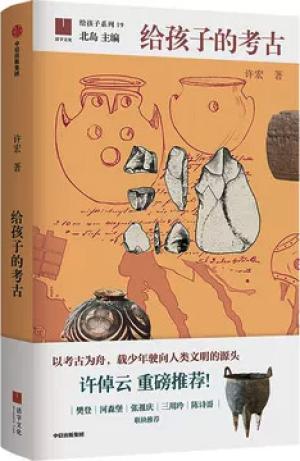
《
给孩子的考古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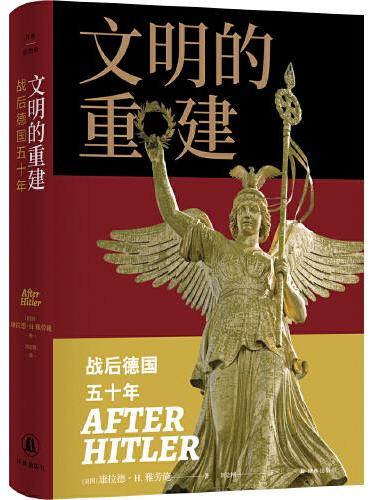
《
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译林思想史)从大屠杀刽子手到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揭秘战后德国五十年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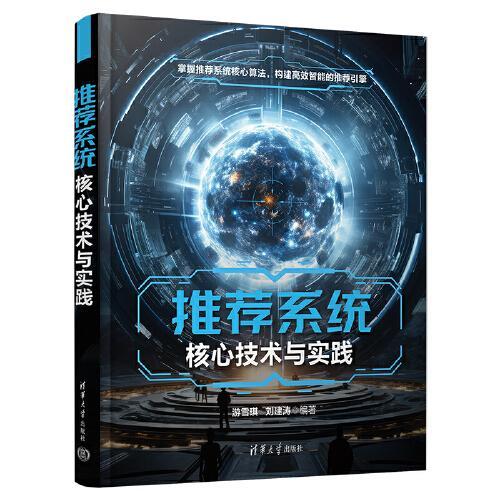
《
推荐系统核心技术与实践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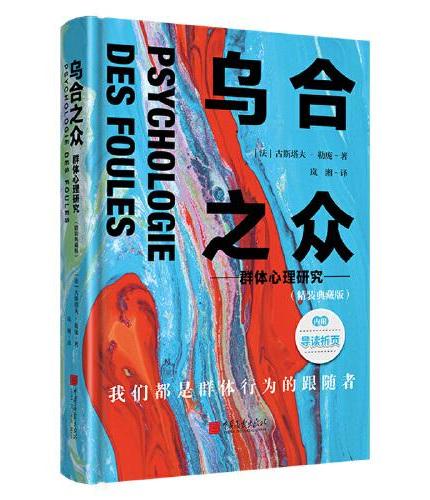
《
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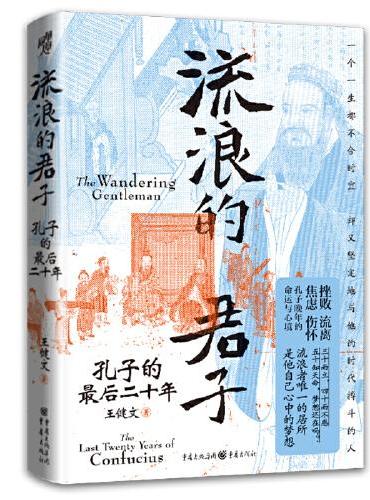
《
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 王健文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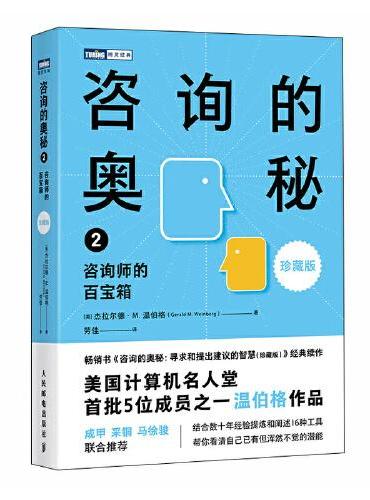
《
咨询的奥秘2:咨询师的百宝箱(珍藏版)
》
售價:HK$
76.8
|
| 編輯推薦: |
经典的北京口语翻译,《大卫科波菲尔》最独特最幽默最通俗最好读的译本。翻译界争论研究的样本。
林先生说,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林先生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
---周永光
|
| 內容簡介: |
|
《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第八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他“心中最宠爱的孩子”,于一八四九至一八五O年间,分二十个部分逐月发表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语气,其中融进了作者本人的许多生活经历。 本书林汉达先生以非常经典的北京口语翻译,译文风趣幽默。
|
| 關於作者: |
|
狄更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
|
| 目錄:
|
巨匠与先驱1
陆志韦先生序9
让翻译这本书的人说几句话12
一我是怎么生下来的1
二我懂事了7
三我换了一个地方15
四我现了眼23
五他们送我出去35
六我交朋友41
七我在撒冷公学的头一个学期45
八放了假,我乐了半天51
九多咱也忘不了的一个生日57
一○家里没有人照应我60
一一我自个儿过日子67
一二我下了一个顶大的决心74
一三姑姑的主意86
一四我又开了个头92
一五来了一个人97
一六回想起我做学生的时候102
一七我去见见世面108
一八我挑个行业;我浪荡116
一九天使跟恶魔122
二○我当了俘虏129
二一屈来达134
二二两个灾害140
二三魂灵飞上天145
二四一个跟斗栽到地152
二五拼命干158
二六朵若——一朵小花儿161
二七成了亲的那些日子166
二八娃娃夫人172
二九到外国去178
三○爱格尼丝——我的明灯183
|
| 內容試閱:
|
一我是怎么生下来的
人家说我是礼拜五晚上十二点钟生下来的。挂钟“当当当”,我“哇哇哇”,响到一块儿了。我跟邻近的老太太们压根儿就没见过面,更甭说谁认得谁了,可是她们倒挺喜欢照应我,说我生在这个坏日子,坏时辰,命里注定了一辈子倒霉,还说在礼拜五半夜子时生的孩子能瞧得见鬼。就拿头一句话说,用不着我赖,我这半辈子就可以看出是真的还是假的了。再说第二句话,我可还没这份本事。要是真能见鬼的话,倒挺好玩儿的。我是带着衣胞生下来的。人家说这样的衣胞挺贵重,谁买了就一辈子也淹不死。我的衣胞贱卖,报上登着广告,要价十五个基尼(每个基尼值二十一个先令)。不知道水手们那时候手里紧手里紧——经济情况拮据。呢,还是他们乐意花钱去买软木背心,我可说不上了。反正,花了广告费,衣胞也没人要。一直等到过了十年,我亲眼瞅着自个儿身子的一小块东西当着好些个人吆唤着卖。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出了有限的两钱就买了我的衣胞。后来全村都知道我的衣胞真挺灵的,甭说那个老太太没淹死,正格的正格的——说真的。,还活到九十二岁,挺自在地归了天了;因为她一辈子没挨着过水,除了喝茶的时候。
我生在勃伦特斯东,是个暮生儿暮生儿——遗腹子。。我眼睛一睁开,我爸爸的眼睛早就闭上六个月了。爸爸压根儿没见过我,我光见过爸爸坟头上的石碑。我快生下来的那天,我妈一点儿没有精气神儿,身子又挺软的,一个人坐在炉子旁边,掉眼泪,叹气,心里想着自个儿这一辈子,跟快见世面的这个没爸爸的小累赘。那当儿正是三月里头,整天介刮着风。她又伤心,又害怕,猛一下子瞅见一个不认得的堂客堂客——妇女。打园子里走进来。那就是我的姑太太贝翠·屈牢沃小姐。
大卫·科波菲尔1我是怎么生下来的贝翠·屈牢沃小姐是我爸爸的姑姑,我的姑太太。她嫁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小白脸。那个小白脸不光长得漂亮,打起老婆来也是一把好手。他老跟姑姑要钱,(原文姑姑跟姑太太通用,以后都叫姑姑,显着亲热,其实就是姑太太。)有一回拿不着钱,就一死儿一死儿——决心。要把她且且——从。二层楼上扔下去。因为这个,姑姑给了他好些个钱,两人都乐意分开。钱刚一到手,他就上印度了。听说后来死在那边了。姑姑也满不在乎,一分开了,就又使她自个儿的名儿,在老远的海边上买了一所小房子,怪清静地住下来。
姑姑本来挺疼我爸爸的,后来为了不答应他的亲事,说我妈是个小蜡人儿蜡人儿——泥娃娃,洋囡囡。,娘儿俩就别扭开了,打这儿不再见面。姑姑可没见过我妈,光知道娶她的那年,妈还不到二十呢,爸爸可有她两那么大两那么大——大了两倍。,再说爸爸又是病病歪歪的,娶她才一年,爸爸就死了,又待了半年,才生了我。
我妈也没见过姑姑,可挺怕她,连提都不敢提。那天见了这位进来的堂客,瞧她那个神气,就猜准了是姑姑。姑姑也不拉铃,也不敲门,反倒一转身站在窗户外头,鼻子尖贴在玻璃上,挤得又扁又白。我妈见了,抽冷子抽冷子——忽然。吓了一大跳。也许就因为吓了这么一跳,才害得我在礼拜五晚上生下来。
我妈慌里慌张地站起来,躲在屋子的墙犄角里头。姑姑冲着冲——向,对,朝。我妈皱了皱眉,拿手一比划比划——做手势。,叫她出来开门。我妈只好听她的,开开了门。
姑姑见我妈穿着孝,就说,“你大概就是科波菲尔家的吧。”我妈怪没气儿地说了个“是”。姑姑说,“我姓屈牢沃,你大概听说过这个人吧。”我妈心里虽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和颜悦色地说当初听见提说她的时候就挺高兴。姑姑说,“早先你光是听说,这会儿让你瞧瞧吧。”妈请她进来。两人儿一坐下,妈可就哭起来了。
姑姑一连串地说,“咄,咄,咄!别这么着!”妈老哭,哭,哭了个够。姑姑说,“孩子,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瞧真照真照——清楚,仔细。点儿。”妈不能不依着她,手打着哆嗦,赶紧把帽子摘下来,又密实又好看的长头发都披在脸上了。姑姑说,“哎,哎,哎,简直是个小姑娘儿!”
说真的,妈真挺年轻,她的模样可比她的岁数还透着年轻。她耷拉着脑袋耷拉着脑袋——低着头。,整跟年轻是她的错似的,一边抽搭着,一边说,“是呀,我是个小姑娘儿,还是个小寡妇儿,要是死不了哇,又快当小妈妈儿了。”姑姑拿手撩了撩妈的头发,妈觉乎着这一撩倒还有点儿体贴劲儿。
太阳压山老半天了,娘儿俩坐在炉子旁边,半天谁也没言语。末了儿,姑姑言声说,“呃?你约摸着什么时候儿能生啊?”妈吞吞吐吐地说,“我老觉乎着浑身打战儿,知道我非死不结不结——不可。!”“不,不,不!别这么说。喝点儿茶吧。”妈没指望似的说,“啊唉,喝茶顶什么呀?”姑姑说,“准保顶事。别胡思乱想了。我问你,你的丫头叫什么名儿?”
妈挺孩子气地回答说,“妈,我怎么知道准是个丫头呢?”姑姑摇晃着脑袋说,“真是!我是问你:你的使唤丫头叫什么名儿?”妈说,“哦,她叫排高第。”姑姑眉头一皱,说,“什么?排高第?这像个什么名儿!是个人名儿吗?”妈低声下气地说,“是她的姓儿。她的名儿跟我一样,科波菲尔活着的时候儿就叫了她的姓儿。”
姑姑拉开客厅门,扯开了嗓门嚷着,“来呀,排高第!端茶来!少奶奶不舒坦舒坦——舒服。。别闲着。”她发了令,等着,直到排高第吓了一大跳,一手拿着洋蜡,一手端着茶进来,姑姑才把门关上。完了按原来的样儿坐下,撩起裙子,两只脚搁在炉子上,两只手按在大腿上,又跟妈说,“你刚才说不知道生下来的是男是女,我可敢说,准是个女的,还非是个女的不结。孩子,等你的丫头一生下来——”
“也许是个男的呢,”妈大胆说了一句。姑姑立时驳她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是女的,准是女的,你别跟我闹别扭。你的丫头一生下来,我得好好儿照应她,当她的保护人,你得管她叫‘贝翠·屈牢沃·科波菲尔’。这一个贝翠·屈牢沃准保一辈子不受人欺负,不能乌头蒙乌头蒙——糊涂。。得好好儿有人管教着她,保护着她,不能让她傻拉瓜唧地傻拉瓜唧——愚蠢地。把真心送给不配给的人。她的事儿我都得给她担待着担待——负责。。”她说一句话,脑袋上的筋一爆,整跟使劲儿压着自个儿委屈,不让它显示来似的。妈光觉着害怕、迷糊、不塌实,不知道该怎么说。
姑姑歇了歇,换个口气,问妈,“孩子,科波菲尔活着的那当儿待你怎么样?你们两口子合得来吗?”妈说,“那时候儿我们挺好,他待我挺好。”
“哦,”姑姑说,“也许把你惯坏了惯坏了——娇养。。”妈抽搭着说,“是,也许把我惯坏了。到这会儿一个亲人也没有,孤孤零零地光凭自个儿过日子,更觉乎着是他把我惯坏了。”说着,又哭了。姑姑拦着她说,“别哭,别哭。哭不光于你没好处,就是于我赶明儿赶明儿——将来。要管教的小姑娘儿也没好处。歇歇儿吧。”
妈太伤心了。排高第拿着洋蜡一照,瞧见她的脸色变了,就搀她上楼,让她躺在床上。一边打发她的侄儿汉姆请大夫去。(汉姆是排高第偷偷儿请来帮忙的,连妈都不知道。)工夫不大,汉姆领着戚力浦大夫来了,才瞧见客厅里还有一位不认得的太太坐着,左胳臂肘上挂着帽子,耳朵里塞着棉花,真绝!真绝——真奇怪。妈妈又没告诉排高第,汉姆跟大夫更不知道。戚大夫急着上楼,也没留神。等他瞧过了妈,又下来,才跟这位堂客脸对脸地坐在客厅里。
这位戚大夫是男人里头顶腼腆腼腆——(念免舔)怕难为情。的了,走道怕踩了蚂蚁,说话怕吓着人,谁也没听着过他发脾气。这会儿坐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着才显着有礼,又不敢说话,光是歪着脑袋显出又恭敬又丧气的样儿。为了不叫人闷得慌,献个殷勤,戚大夫冲姑姑行了个礼,轻轻地拿手指头槌了槌槌了槌——(槌念第三声)碰了碰,触了触。她左耳朵里头塞着的棉花,说,“有点儿小毛病吗,太太?”
“什么!”姑姑猛一下子把棉花揪出来,好像揪出个木塞似的。戚大夫有点儿慌了。后来他告诉妈说,那时候总算还没吓坏,就挺温和地又说了一句:“有点儿小毛病吗,太太?”
“胡说!”姑姑一下子又把棉花塞进去。
戚大夫不敢再言语,愣头愣脑地坐着,瞅着炉子里的火苗,直顶到直顶到——直等到。再给叫上楼去。
待了一刻钟,他又下来了。姑姑揪出了棉花塞,问他,“怎样喳喳——着的转音。?”戚大人回说,“没什么,太太,慢慢儿来,太太。”
“咄,什么话!”又把棉花塞上了。
又接不上碴儿接不上碴儿——搭不上话。。他胆小地坐在那儿,眼睛冲着火苗,楞格争地楞格争地——埋头埋脑地。坐了两钟头,直顶到再给叫上去。待了一会儿,又下来了。姑姑又揪出棉花塞来,问他,“怎么着?”戚大夫又告诉说,“没什么,太太。咱们,咱们慢慢儿来。”
“哟!!!”姑姑大声直嚷。吓得戚大夫差点儿没趴下。他再也钉不住了,就偷偷地溜了,坐在黑咕隆咚的黑咕隆咚——擦黑的,黑暗的。楼梯上,直到再给叫上去。末了儿,他下来跟姑姑说,“哎,太太,大喜,大喜。”姑姑尖着嗓门问他,“喜什么?”戚大夫吓了一跳,强扎争着劲,定了定神,赔着笑脸冲她哈了哈腰哈腰——弯腰,打弓。,可说不出话来。姑姑大声地说,“嘿,你干吗!你这个人会说话不会呀?”
戚大夫挺和气地说,“太太,您别着急呀!太太,您放心吧。”没想到姑姑还真没重重地摇他一下,光是起劲地摇着自个儿的脑袋,这就够叫戚大夫打颤的了。他鼓足了气说,“大喜,大喜,太太,什么都挺好,挺好。”姑姑瞪着他,光等着他说出来孩子的事,他可没说。姑姑叉着手,胳臂肘上还挂着帽子,问他,“她怎么着了?”
“哦,她挺好,什么都顺当。年轻儿的产妇像这么个样儿总算不错。您去瞧瞧吧,好叫她宽宽心。”姑姑说,“那她呢?她怎么着?”戚大夫歪着脑袋,怪纳闷地怪纳闷地——很奇怪地,莫明其妙地。瞅着姑姑,正像一个小鸟儿。姑姑就说,“我问你,孩子,那个小丫头儿怎么着了?”
“哦,哦,哦!”戚大夫这才明白过来。“我当您早知道了呢。哦,是个学生学生——男孩子,少爷,公子。。”
姑姑没言语,拿起帽子,往脑袋上一扣,转身就跑出去了。打这儿再也不露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