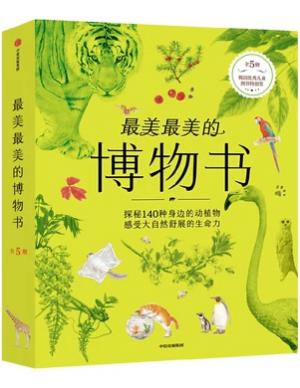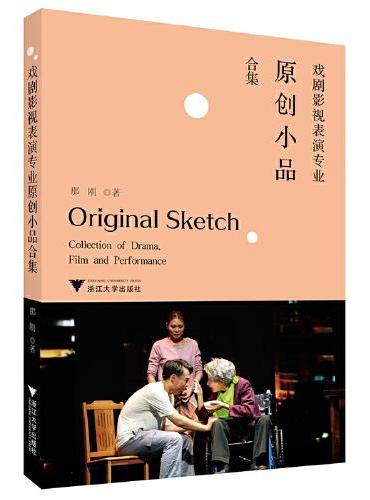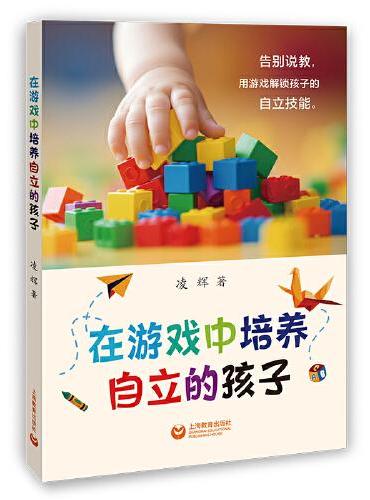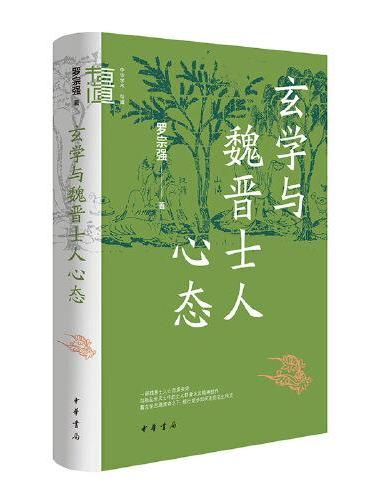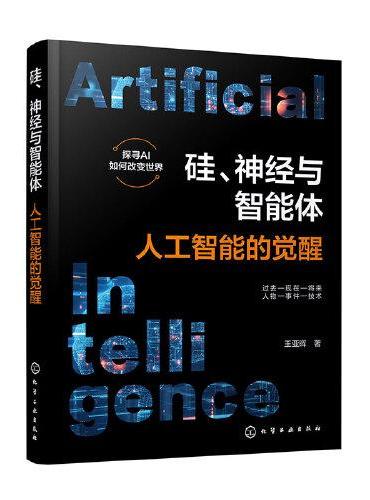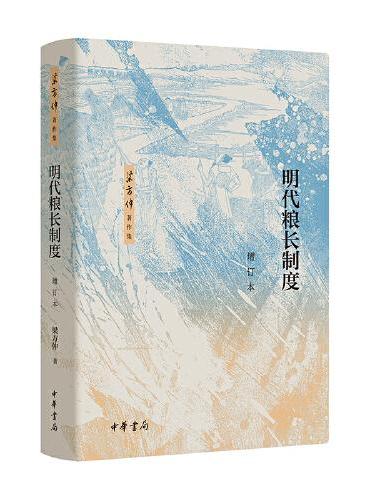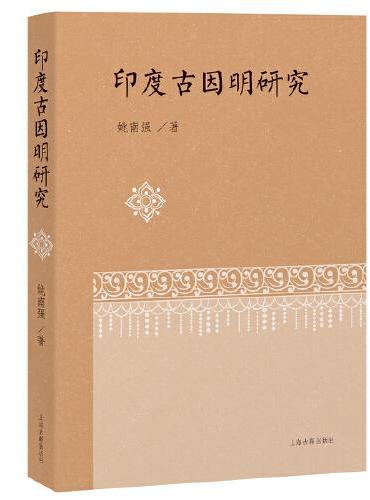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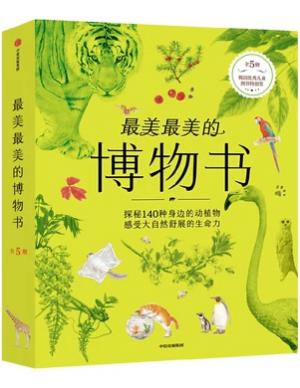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HK$
16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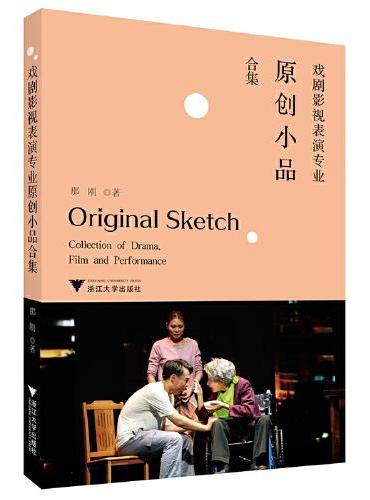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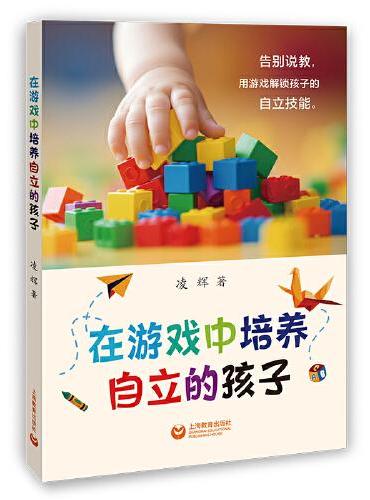
《
在游戏中培养自立的孩子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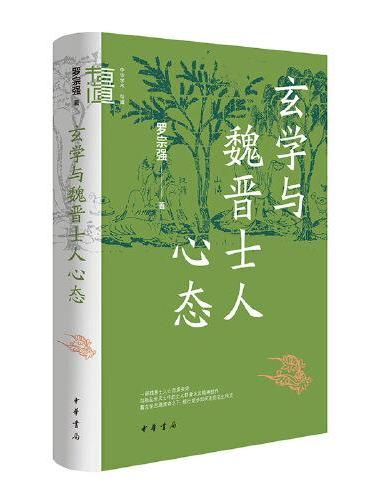
《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精)--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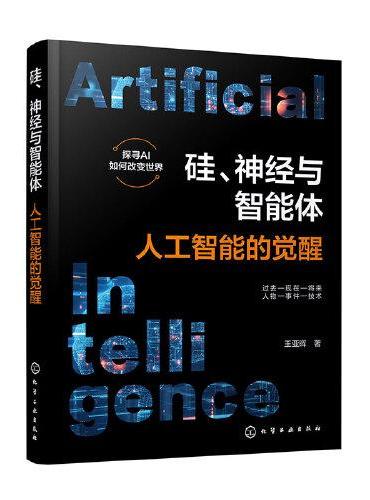
《
硅、神经与智能体:人工智能的觉醒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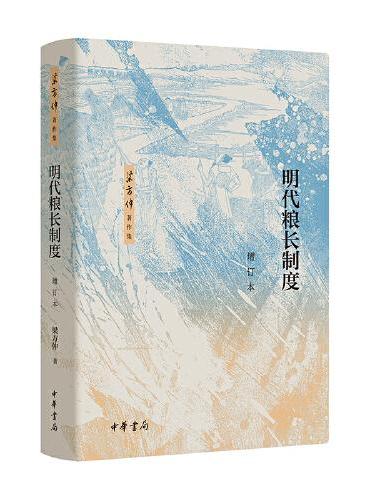
《
明代粮长制度(增订本)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68.2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精选集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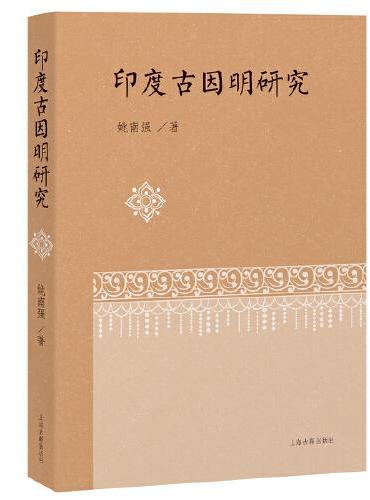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HK$
129.8
|
| 編輯推薦: |
已经60多岁的大学者李欧梵不仅在学术领域独领风骚,而且在文学评论、音乐赏析等方面也颇有造诣。而他与妻子李玉莹在中晚年相知相爱的故事,更是一幅辗转芝加哥、波士顿、香港三地的爱情图谱。本书是他们共结伉俪之后合著的第三本书(前两本分别是《过平常日子》、《一起看海的日子》)。书中,李欧梵与妻子继续用炽热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婚后平淡而隽永的恩爱点滴,从相伴漂泊的浮城岁月中一起分享相依为命的幸福。
在这个世情凉薄的时代,这是一本带给人间温暖的书。
|
| 內容簡介: |
真爱总是存在的,你抓住了吗?
佛家说:今生太苦。但我偏偏贪恋今生。
人生的缘分可遇不可求,得来不容易,碰到之后就要紧抓不放,这就是我们的爱情哲学。
这是李欧梵教授及其夫人李玉莹合作的一本书,讲述两个人的生活、感情、行踪以及对艺文的评论、对亲人的怀念,充满了蜜意柔情。
在这个浮生乱世,两个人能在一起过平常日子是修来的福气,而夫妻之道或许也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需要用心呵护的人际关系。
两位作者都不再年轻懵懂,都有过痛苦甚至绝望的人生经验,却仍然看来年轻,天真无邪。苦尽甘来之后,他们都明白,并没有什么童话故事中所说的他们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快乐那回事。
幸福像鲜花一样,需要灌溉调养,人更是如此。养生之余也要花功夫养情和调情,这就是夫妻相处的艺术。
|
| 關於作者: |
|
李欧梵,一九三九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
| 目錄:
|
鹣鲽七年 白先勇
我的丈夫李欧梦 李玉莹
我的妻子李玉莹 李欧梵
第一部 香港
我们又回到香港
缘分
过年
寻根
住在清水湾畔
我家的后花园西贡
写作的乐趣
张国荣的忧郁
如花的梅艳芳
范柳原和白流苏
妈妈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
给老公的一封信谈妈妈的去留
妈妈的心灵抉择
爸爸的心事
我们的母亲
两人的回忆
戏梦人生
一生的凝视
日常生活琐记
寻常幸福
第二部 剑桥
在剑桥过平常日子
然而,我并不寂寞
一盘七色菜
床上故事
华盛顿的樱花
看美式足球
看美国新闻
游哈佛广场
睡前的仪式
拿着面包的男孩
吃法国薄饼
一件博士袍的两种心情
惜别剑桥
再另康桥
从波士顿到旧金山
第三部 旧金山
三城生活杂感
三城记芝加哥、波士顿、旧金山
斯坦福大学和柏克莱大学
烘蛋饼香不及亲情热
两地双情
恋恋双城 李欧梵
|
| 內容試閱:
|
过年
文=李玉莹
小时候,过年是个大日子。我们家境不算丰裕,每年过年,爸妈会从英国多汇来一些钱。外婆早在腊月下旬就开始张罗,买年货做萝卜糕、年糕,还有豆沙油角子。她向来患有哮喘病,每到冬天,病发的时间多,很多个忙碌的过年日子里,她都是病兮兮地支撑着身子来预备过年的食物,因为她很迷信,总觉得过去每年做的事情,都要按例做下去才吉利。我和哥哥在这些日子里也特别兴奋,在旁帮忙捏角子,但得小心说话,因为外婆忌讳不吉利的言语。好不容易等到糕点蒸好了,油角子炸得金黄耀目,虽然我们看得垂涎三尺,但还得耐着性子。待至大年初一才可大快朵颐。
新年买新衣也是件大事。外婆给我买的新衣都是一身的大红色,连绑辫子用的丝带也是红色,哥哥的新衣颜色选择比较多。儿时对于新鞋子有种特殊的喜爱,鞋子买了,不能立即穿上,等到年初一作踩小人用。这半个月的等候日子,给我和哥哥带来了欣赏新鞋子的乐趣。每天晚上,吃饭和漱洗过后,兄妹二人就蜷在暖和的被窝里,各自拿出新鞋子来把玩一番,才带着满足的笑容进入梦乡。
好不容易待到大除夕夜。吃过团圆饭,祖孙三人团坐在被窝里包红封包,预备给来拜年的小孩。在那个年代,红封包多用硬币,但外婆通常都给我和哥哥一包软嚼(纸币)作压岁钱。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枕头底下,直到过了正月十五日才可开启。这封压岁钱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增加了一份心事,想着以后如何花费这笔小钱。外婆平日对我们管教极严,每做错一些小事,都会挨一顿打,但在过年期间,她的脾气忒好,未过年初二,通常不会打人骂人,哥哥和我每年总会利用这几天稍微淘气一番。
外婆在我十六岁那年去世。从此我再也不喜欢过年,加上后来在美国度过了十多个不过中国年的年头,回港后,一个人度岁的日子多,渐渐遗忘了过年的习俗。直至今年的春节,我又重新有了一个家,又再记得在除夕的夜里,给老公及自己的枕头底下放红封包作压岁钱。
文=李欧梵
香港人过农历年,气氛十足,特别是过年前,大家赶着办年货,使我这个数十年都忘了过年的异乡人第一次感受到一点过年的温暖。
儿时在北方过年的记忆早已褪色,只剩下六七岁时随父母回父亲的老家河南太康过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也是过年前几天,就开始兴奋起来,祖父一向笑口常开,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祖母也不时露出温馨的笑容。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孙儿、孙女。八年抗战刚结束,我们从河南南部的信阳北上,长途跋涉,先乘汽车,后乘牛车和手推的独轮车,只记得雪后的道路泥泞不堪,寸步难行,还有过黄河时的惊险一条支流的水竟然在天上流,河床高高在上,两岸都是堆砌如山的防波堤,要先爬到堤上乘船到彼岸,然后再爬下来。这一趟旅行至多也不过两三百公里,竟然花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
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在爷爷奶奶面前,父母亲这一对典型的五四反传统知识分子也变得温顺起来。父亲不再谈西洋文学和音乐,只问候老家的亲友。母亲是南方人,这还是第一次见李家的翁姑,她弹得一手好钢琴,也没有用场,被一大群姑嫂包围着,大家一齐动手包饺子,愈包愈多,谈笑声也愈来愈大。我和妹妹则每天随着叔叔伯伯们去野外玩,还记得那个会踩高跷的叔叔大概是爷爷家里的长工或佃农,我们最喜欢看他表演各种杂技。多年后读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里面的那个有二伯就使我想到这位佃农叔叔。
大年除夕到了,北方农村的规矩是要守岁通宵不眠,我们小孩子当然例外。但大年初一大清早,我就被叫醒,穿上新衣服,去向爷爷奶奶拜年,辈份愈小,愈要早拜年。到了大年初三,就要走亲戚了,坐着牛车,到附近村庄去向远近各房亲戚家串门送礼,凛冽的寒风也压不住心中热乎乎的温情。
香港的西环街市,竟然令我无端想到儿时的河南田野,那股农家特有的节庆感觉,依然浮现在这个亚洲国际大都会的一个角落,她似乎早被外来的游客和半山豪宅中的贵族遗忘了。但对我和玉莹而言,这才是香港,我俩不约而同地把西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麦加;每周末必去买菜,顺便也吃碗皮蛋瘦肉粥或艇仔粥,或去附近的麦当劳听老年妇人聊天,她们的广东乡音传到了我耳中,都变成了乡土气十足的河南话!
也许,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对乡土的回忆本身就是一种偶发的奢侈感觉,是真是假,是回忆还是一厢情愿的联想,谁知道?反正我们过平常的日子过得快乐,就心满意足了。我每次去西环,都觉得是在过年。
|
|